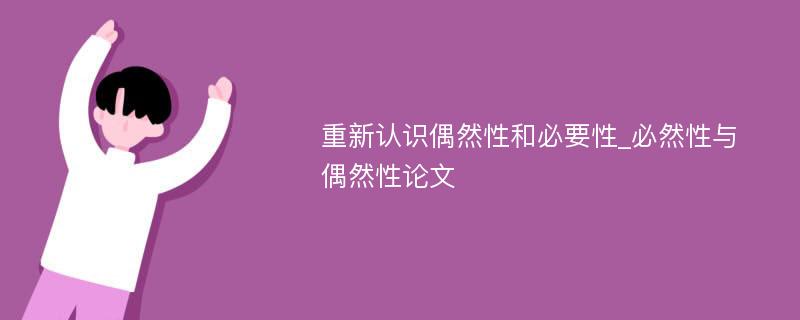
重识偶然性和必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偶然性论文,必然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1)02-0105-07
一
偶然性和必然性及其关系问题,早在古希腊,就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认为自然界中只有纯粹的必然性,偶然性只是出于人们思想上的无知;而伊壁鸠鲁则与此相对,指出只有偶然性才是现实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必然性乃虚幻的代名词。在欧洲中世纪,德谟克利特强调必然性的观点颇受青睐。基督教教义认为,世界的一切以及人自身的命远是由全知全能的上帝决定的。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遂滋生出这样一种因果决定论的哲学信念:现在与未来的一切事件都是有定数的,是完全由过去的事件所决定的,因而现在和未来的一切都是必然的。近代唯物主义虽然从根本上摆脱了宗教神学的宇宙观念,用“自然”代替了“神”,但是这种“一切皆前定或预定”的哲学信念却保留了下来。如霍尔巴赫认为:“在自然界中所引起的一切运动,都遵循着一些不变的和必然的法则”,因而超自然的原因是没有的,“宇宙本身不过是一条原因和结果的无穷的锁链”[1](P45-51)。而当时牛顿力学的成功尝试,极大地支持了这种哲学上的因果决定论。后来,拉普拉斯将二者结合,提出了支配科学界100多年的拉普拉斯决定论,从而将德谟克利特对必然性的崇尚推向极致。
然而自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以来,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强调偶然性的倾向。这缘于现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首先是达尔文,他通过大量的实证考察,得出了生命起源于偶然事件的结论。正是在达尔文这一划时代成就的基础上,恩格斯从广泛存在的偶然性出发,分析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真实联系,他指出:“是偶然性推翻了人们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必然性的原有观念失效了,把它保留下来,就等于把人类任意做出的自相矛盾并且和现实相矛盾的规定当作规律强加于自然界。”[2](P544)20世纪兴起的量子力学,更是对排斥偶然性的决定论观念的一场革命。薛定锷方程表明,微观客体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具有概率性的,不能对它作完全因果性的描述。海森伯不确定原理也表明,我们根本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微观客体存在的初始条件;即使在因果律严格成立的场合,也不能得到未来的确定性结果,因而事物发展并不具有牢不可破的必然性。不过由于海森伯不确定性原理的表述中包含着一个“观测者”,因而其“不确定性”并不是指一种纯粹客观的不确定性,而是包含了观测者本身所具有的主体认识的局限性。
总的来看,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日益表明偶然性存在的普遍性。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偶然性问题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从讨论的整体情况来看,对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依然未能给出一个新颖而清晰的解答,多数论者仍然未能超出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某些陈旧解释框架。目前,哲学教科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大体可归结为如下两个命题:(1)凡是必然的都是偶然的,凡是偶然的都是必然的;(2)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对于第一个命题本文留待最后作出解答,这里先就第二个命题作出分析。第二个命题是有的论者从恩格斯的如下两段论述中得出的推论:“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3](P197)。笔者认为:(1)恩格斯的如上论述旨在表明,在任何偶然性的事件中,其深层都存在某种必然性,并且偶然性是受其内在规律支配的,但并没有强调必然性比偶然性更根本,我们并不能从中得出“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这一结论。(2)如果说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那么二者的关系就转化为一种现象和本质或者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然而由于这种观点同时又承认必然性对偶然性的绝对支配作用,那么我们由此便只能说,本质永远决定现象,或者内容总是决定形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因果决定性反映的是一种历时性的本质联系,它只存在于同一事物发生变化发展的前后两种状态中,而无论是现象和本质,还是形式和内容,反映的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属性在共时性上的某种本质联系,因而我们不能将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等同于现象和本质或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由于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在承认偶然性和必然性都客观存在的同时,支持和强调了伊璧鸠鲁所认为的偶然性是万物形成的源泉,是世界创造性和多样性的源泉等观点,于是有人便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该论者认为马克思过分强调和夸大了偶然性的作用,是不成熟的早期思想的反映,而恩格斯的观点则是在当时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因而在此问题上只有恩格斯的观点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4]。其实不然,从他们二人的不同表述看,马克思只是强调偶然性存在的本体论地位,而恩格斯则着重阐明在一切偶然性事件中肯定有必然性成份的存在,他们只是在当时的自然科学水平上各自解答了二者众多相互关系中的某一个方面,因而二人之间并不构成矛盾。
二
从通常使用情况来看,必然性和偶然性这对范畴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事物在其变化发展过程中先后两种状态之间的联系;二是发生变化之后的状态属性。在必然性事件中,先后状态之间的因果决定性联系和结果状态的确定性构成了必然性事件的两个基本组成要件,二者缺一不可,在同一逻辑层面上,如果一事件不是必然的,那么它便是偶然的,反之亦然。
(一)偶然性的存在分析。
偶然性与必然性既然在逻辑上构成一种矛盾关系,那么一事件只要不具备必然性两个基本构成要素中的任何一个,此事件便是偶然性事件。这样偶然性事件便会有如下两种表现情形:一事件的未来状态是不确定的,我们即使按照严格的因果律也不能对其作出精确预测(偶然性之一);即使一事件的先后两种状态的表现是确定的,我们也不能确定出这两种状态之间主要表现为一种因果决定性联系(偶然性之二)。
1.关于“偶然性之一”。自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科学家们就笃信在世界的纷繁复杂性之下,必定潜藏着某种“简单物”和“简单力”。这使得我们习惯于从秩序的角度看世界,而认为世界具有相对简单的秩序。如今这种“简单性思想正在瓦解,你所能去的任何地方都存在着复杂性”[5](P271)。现代复杂性科学认为,在自然界中,规则简单的秩序事实上是例外,而非定则。复杂性的出现是由于在自然界这一大系统中,简单的组成因素以无数可能的方式自动地发生相互作用,而这种持续相互作用意味着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将系统的一部分取出来孤立地加以研究。从而与经典科学所强调的有序性和稳定性相反,我们在观测的所有层次上都看到了涨落、不稳定性、多种选择性和有限预测性。因此,经典科学给予我们的只是“自然的碎片”。这基于西方自近代科学以来所一直依赖的还原论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把世界分解得尽可能小,尽可能简单。为一系列或多或少理想化了的问题寻找解题的答案,但因此而背离了真实的世界,把问题限制到了你能发现解决办法的地方”[6](P72)。用这种传统方式表述的物理学定律描述了一个理想化的、稳定的且与我们生活中动荡的、演化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非线性打破了还原论者的迷梦”[5](P271)。的确,除了一些非常简单的系统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被笼罩在一张充满刺激、限制和相互联系的巨大的非线性之网中。浑沌理论揭示,一个系统中最小的不确定性通过反馈耦合而得以放大,在某一分岔点上引起突变,使一个简单的系统也可能发生惊人的复杂性,从而令整个系统的前景变得完全不可预测。本来,牛顿定律在20世纪已被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所取代,然而牛顿定律的基本特性——确定性和时间可逆性——却幸存下来。虽然量子力学不再涉及轨道而是与波函数相关,但量子力学的基本方程式——薛定锷方程是具有确定性和时间可逆性的。依靠这种方程,一旦初始条件给定,一切便都是确定了的。惟其如此,普里高津通过将时间不可逆性引入对“新自然法则”的描述,从而揭示了“确定性的终结”。在普氏的宇宙中,未来不能被确定,因为它受随机性、涨落的支配。为与海森伯不确定性原理相区别,普氏称此是“新不确定性原理”。这一新原理描述的是,在某个复杂性阈值外,系统沿不可预见的方向演变,它们丧失其初始条件,不能被逆转或恢复。因而这种由时间不可逆性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并非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是出于我们人类的“无知”,而是我们这个“演化”世界的本真属性。因此,世界无论在本体论还是在认识论意义上,都是偶然性的。
2.关于“偶然性之二”。现代复杂性科学认为:“一个系统只有正好能够在稳定性和流动性之间保持平衡时,才能够产生复杂的类似生命的行为。”[6](P432)这就是现代浑沌理论所揭示的“趋于浑沌边缘的相变”,即系统只有达到这一状态时,才有可能通过各种随机性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新颖性”,进而创造出生命和智能。正是从这个意义讲,随机性是生物界每次革新的源泉,即“浑沌乃结构和秩序之源”[5](P282)。当然,在导致产生这种“相变”的各种随机联系中,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决定性因素,那就是物质生命所具有的自发性、自组织性倾向,但无论如何,这种因果决定性因素在这一阶段上并不能替代总体表现上的随机性联系。因此从本体论上看,对自然界这样一个复杂性系统而言,总体上是由各种随机性联系为其进行“建构”的,各事件之间的随机性联系是其总体表现特征。从认识论上讲,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事件中寻找因果性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根本方式,用休谟的话说:“唯一所能推测到我们感官以外,并把我们看不见、触不着的存在和对象报告于我们的,就是因果关系。”[7](P90)但事实上,复杂系统的演化是不可能通过因果细节来得到解释的,因为复杂系统本身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一个部分都影响着其它部分;同时人类的认识存在着某种局限性,很多情况下,人们无法穷究某一事件的初始条件,因而也就很难对其进行准确的因果性分析。总之,复杂的、非确定性的世界系统的演化,是以随机性联系为主要表现特征的。
(二)必然性的存在分析。
强调随机性联系在生物进化中的普遍的、带有根本性的创造作用,并不意味着就是对必然性的否定。现代复杂性科学揭示,复杂的具有自组织性的系统可以自我调整,从而保持一种将秩序和浑沌融入一体的特殊平衡能力。这种可能性潜存于复杂系统的演化过程中,随着这种可能性的增大,在某个分岔点上,这种随机联系的偶然性事件就有可能表现出一种必然的过程和趋势。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现实性,因为系统在某一分岔点上,既有可能走向一种浑沌,也有可能走向一种秩序。不过这种可能性有一种确定的“可能性空间”,这就像投掷硬币,尽管硬币每一次投掷的结果是随机性的,但硬币的出现只能有“正”和“反”这样两种可能性,这是确定性的。同样,我们周围的宇宙也只是许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8](P57)。由于这种可能性潜存于一复杂系统的随机演化之中,因而将其称之为潜在的必然性。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必然性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性,因而从本体论上讲,这种必然性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这样,在认识论上只能根据一事件的初始状态进行因果性分析,对这一事件的未来状态作出预测,以确定其出现的可能性范围或趋势。这种对一事件进行“可能性估计”的认识方式,构成了我们认识这个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对这种潜在的必然性,我们需要用概率来表示其出现的可能性范围或趋势。普里高津指出:“由于这种可能性具有普遍性,因而概率成为一种新的自然法则的表述。”[8](P107)根据这一“新自然法则”可以说,确定的世界观是解构了,但这个世界并不是纯机遇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可确定的概率世界中,生命和物质在这个世界里沿时间方向不断演化。
人们面对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非确定的世界,往往是经过一种人为的简化、理想化等手段而获得一种相对确定性的系统,然后从中寻找事件发生的因果性联系,此后便根据这种因果决定性进而对这一类事件做出相对确定性的把握。这也是我们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近代科学正是沿用这种方式而兴起的,因而当我们把自然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囊括进来重新表述自然法则、以整体性思维方式代替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和特定场合下保留这种已被实践证明相当成功的西方科学的分析观点和还原论思维方式。我们把通过这种理想化的方式所获得的必然性称之为一种抽象的必然性。显而易见,这种必然性由于存在于一种“理想化”的相对确定性系统中,因而在认识论上它只具有一种相对的意义,其实质上乃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近似的把握”。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概括:偶然性和必然性这对范畴并不具有同等的本体论地位,偶然性是一种绝对的存在,而必然性则是相对的。二者在认识论上也是如此。因而无论在本体论还是在认识论上,偶然性都要比必然性更根本。在这一问题上,笔者还想将目前学术界对著名分子生物学家莫诺思想的错误批判做一澄清。大多数学者认为莫诺是排斥必然性的,是一个绝对的偶然论者。其实不然,莫诺在强调随机性联系的创造和选择作用之同时,也看到了生命物质在进化中由不稳定性向稳定性过渡,由浑沌向秩序转化的这一趋势,他指出:“从纯粹偶然的范围中延伸出来以后,偶然性事件也就进入了必然性的范围,进入了相互排斥、不可调和的范围了。”[9](P88)因此,从伊壁鸠鲁到马克思,从达尔文到恩格斯、莫诺,在承认偶然性的本体论地位上,他们的思想在与现代科学精神相符合的基础上取得了一致。同时,由于偶然性和必然性存在着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因此在探讨二者的相互关系时我们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就非确定系统中作为绝对存在的偶然性与作为相对存在的必然性而言,二者在同一事件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中,处于不同层次:前者是对这一事件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的表象观照,后者则隐藏于这种表象之下,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前者从总体上表征着一事件的一种现实存在状况,而后者反映的是这一事件的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趋势。因此在非确定性系统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处于不同的层次,二者之间是一种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统一于同一事件的存在和发展过程中。而就相对确定性系统中作为一种相对存在的必然性而言,由于这种必然性只在一定范围内或特定条件下才有可能存在,因而相对于普遍的随机性联系和偶然性存在而言,它的存在只是一种特殊性表现。在人类的认识和科学活动中,人们把这种由特殊性存在反映出来的因果决定性关系通过分析和综合等多种认识手段,获得一种抽象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的存在完全依赖于这一相对确定性系统,一旦超离这一系统,它便成为一种偶然性存在。因而作为普遍存在的偶然性与这种作为“特例”的必然性,从本体论上看,二者是一种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统一于这一相对确定性系统之外的复杂性世界中;从认识论讲,作为真实存在的偶然性与这种作为理论存在的必然性之间是一种具体和抽象的关系,统一于主客体的相互联系之中。因此,偶然性和必然性这对范畴具有一种多重意义的即多元的辩证统一关系。笼统地谈论二者辩证统一的作法是不足取的。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偶然性和必然性这对范畴一般只是对事物或现象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的一种哲学描述,而不是作为事物或现象之间本质联系的一种反映,因而我们就只能确定二者在宇宙中的存在地位,而无法论及它们在事物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因为事物或现象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是由事物或现象之间的持续的相互作用决定的,这种持续的相互作用从历时性关系上看,表现为一种因果决定性联系或一种非因果的随机联系。因而我们只能去谈论因果性和随机性在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当因果决定性占主导地位时,因果性决定事物或现象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随机性起加速或延缓的次要作用,事物的发展表现为一种必然的过程。同样,当随机性占主导地位时,随机性决定着事物或现象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而因果性则处于潜在的存在地位,事物处于一种浑沌的存在状态。因此,笔者不同意目前学界的这种常规表述:“必然性是由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决定事物发展的主要趋势;偶然性是由事物的外部矛盾、次要矛盾决定的,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被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加速或延缓作用。”这种分歧并非仅出于概念理解上的不同,而是一种根本的思想分歧:首先,偶然性和必然性本身就是事物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的描述,因而如上论述的结论只是“同义反复”;其次,无论是偶然性还是必然性,都是由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这种主要矛盾就是事物内部各因素的持续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因果决定性关系或随机的非决定性关系,正是这此因素决定或支配着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
其实,以上我们只是对这对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静态的纯粹逻辑的分析和概括。而如果我们将偶然性事件和必然性事件放在事物发展变化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进行动态的、历史的考察,就会进一步发现二者进行相互转化的趋势。从本体论上讲,物质世界的演化是一个充满各种复杂随机性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偶然性过程,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总存在着必然性事件出现的一种可能性空间,这是确定性。这种可能性的概率在实践中是一个变数,当这一概率达到足够大的程度时,物质世界的演化就表现为一个必然性的过程。从而使原来的偶然性事件转化为一种必然性事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必然性只是原先潜存的可能性的一种实现形式,同时它的出现伴随产生出一个相对确定性系统,此后它的实现便依赖于这一系统,因而这种由偶然性转化所形成的必然性依然是一种相对性存在。而当一必然性事件由于其系统内部各要素的持续相互作用使其远离既有的秩序,并达到且超过这一秩序存在的某种“临界状态”时,将会使原有的秩序趋于浑沌,使其所依赖的相对确定性系统破坏,从而原来的必然性事件就转化为偶然性事件。从认识论上讲,由于人类的认识本性和实践能力以及人类的现实需要,总是促使人类不断地从各种浑沌的“无知之幕”中探索因果性、必然性,去把握确定性和规律,从而使原先被人们看成难以认识的“偶然之物”逐渐转化为人类可以把握的“必然之物”;然而由于现实世界的变动不居和复杂多样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使得人类所把握的这种“必然之物”总带有某种片面性,而当人类能够认识到这种片面性时,原先所认识的“必然之物”就会变为“偶然之物”。人类的认识在对这种“偶然之物”与“必然之物”的认识转化中不断地得到发展。人类科学的发展历程早已证明了这一点。譬如在20世纪以前的人们看来是普适的牛顿定律,在20世纪的人们看来却是一种“特例”,是一种简化和理想化的极致。总而言之,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相互转化,不仅构成了世界演化的历史,也构成了人类认识的历史。这构成了世界演化和人类认识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因而,把必然性和规律等同起来,而把偶然性排斥在规律之外的作法,是极不恰当的,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力图用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对付偶然性。按照这种观点,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简单的直接的必然性”,“确信一切都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必然性上面,这是一种可怜的安慰”[2](P541-543)。
至此,我们可以对本文前面所遗留的“凡是必然的都是偶然的,凡是偶然的都是必然的”这一命题作出辨析。这一命题出自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一句话:“这两者是同一的,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的东西是偶然的——这怎么可能呢?常识和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作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范畴。一个事物、一个关系、一个过程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不能既有偶然的,又是必然的。”[2](P540)联系整个上下文来看,恩格斯的主旨在于批判那种一味地把必然性和偶然性当作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规定,孤立、静止地考察事物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认为应该对二者进行动态地辩证地把握。后来恩格斯又有如下更为明确的表述:“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10](P240)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偶然性和必然性在事实上是不可分离的:二者在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中,是同一事件在不同存在层次上状态属性即现实性和可能性的一种辩证统一;在人类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二者是一种一般和特殊、具体和抽象的辩证统一;动态地看,无论是在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中还是在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二者相互联结,相互转化,辩证统一于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历史进程。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偶然性和纯粹的必然性都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才可以说,凡是偶然的都是必然的,凡是必然的都是偶然的。“只有把两种描述结合在一起,才能给出现实的图景。偶然性和必然性在这里表现为互补的原理,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事物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同一过程。概括地说,互补性观念类似于过程思想”[11](P53)。
收稿日期:2000-04-27
标签:必然性与偶然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