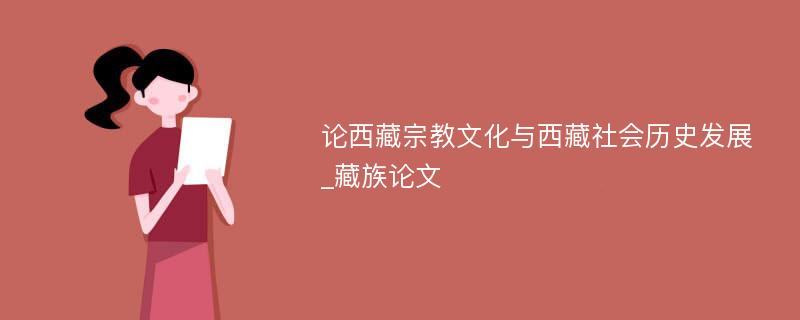
西藏宗教文化与藏族社会历史发展管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族论文,管见论文,西藏论文,文化与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根置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西藏就有原始人类居住。从藏文记载中的“六牦牛部”到吐蕃王朝的统一,这些“食肉赤西人”〔1〕一直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笨教是这一时期吐蕃社会的主宰。松赞干部(?——650年)统一吐蕃以后,佛教便正式传入吐蕃社会。 随着吐蕃社会的崩溃和瓦解,封建社会的因素逐渐增加,藏传佛教于公元10世纪末以其独特的面目跃上了藏族社会的历史舞台。藏族社会经历了氏族制、奴隶制、封建农奴制的历史发展过程。笨教、佛教、藏传佛教等文化现象也在这些历史发展中应运而生,与藏族社会协调发展。
一、笨教泛神论与吐蕃游牧社会相适应
藏族先民是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一带的发羌等羌人的游牧部落,他们长期以游牧业为主。《说文·羊部》记载:“羌,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范晔的《后汉书·西羌传》则云:“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可见,藏族先民曾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后汉书·西羌传》以及一些古藏文文献都记载着“越嶲”“牦牛”、“六牦牛部”等古代藏民的游牧生活。可见,这时的藏族社会并没有进入阶级社会,而是处于原始的氏族部落发展阶段。
在吐蕃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游牧经济是单一的、脆弱的,游牧民从事牲畜的牧养,乳饮肉食,寝毡服皮。牲畜既是生活资料,又是生产资料。手工业虽然根据各自社会发展的需要或多或少地已经产生,但始终处在以满足自身简单需要为最高目的的极不发达状态。西藏高原的气候比较恶劣,一次大风或雪崩就可以导致牲畜的大量死亡,加上疾病和牧草的匮乏,使牧民的生活与生产时常遭受致命的损失。单一的生活,脆弱的经济,使藏族先民不得不过多依靠大自然的力量,崇拜大自然。牲畜的兴旺,草场的繁茂,狩猎物及采集物的多少都听命于大自然的“神旨”,人们不得不祈求大自然保佑自己的生活。正如恩格斯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2〕。
与游牧社会相适应,藏族先民最初的宗教是笨教,“西藏民间,原已盛行笨教”〔3〕。笨教是藏族社会中的原始宗教, 是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它所崇拜的对象包括天、地、日、月、星辰、雷电、冰雹、山川,甚至土石、草木、禽兽,包括一切万物在内〔4〕。 笨教产生于吐蕃原始氏族制度下,是原始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又是对吐蕃游牧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一种适应。历史证明,它可以适应于游牧业生产方式,以及在这一生产方式上产生的奴隶制或者带有浓厚氏族制外壳的宗法封建关系。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的。
产生于游牧社会中的笨教具有游牧社会的特征,适应游牧民族的心理和要求,更能靠近游牧民的生活。笨教神灵众多,诸神灵的形象多与游牧生活有关。藏民曾将牦牛、绵羊、山羊、狗、豺、狼以及马、骡、虎等作为崇拜对象。还出现了绵羊头地神、鹿头地神、猪头地神、公牛头地神、鼠地神等的崇拜”〔5〕。 这些神灵形象多数是现实社会中游牧民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笨教崇拜的出现显然是吐蕃游牧生活的折射和反映,它根置于现实社会的生活中,又为现实社会服务,笨教的众多神灵,既是人们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又是人们的信仰不可缺少的。
吐蕃游牧民族的笨教崇拜处于原始宗教的初级阶段,与游牧民族单一的经济生活相适应,其宗教仪式比较简单。游牧经济具有流动性、季节性。牧民虽逐草、水而居,具有冬夏两个相对稳定的牧场可供放牧,但生活总是不固定的。与此相应,信仰多神和以偶象崇拜为主的笨教,没有寺院,只有简单的祭坛。在浩瀚的高原上,用一块块石头堆成的嘛呢堆散见于高山、路口、道旁,它们既有境界和路标的功能,又可供随时而至的牧民祭祀、祈祷。祸福灾祥可随处发生,而朝拜的神祗也随处可见,可随时随地在牧民身边“保护”他们。
宗教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统治者根据自己需要,对宗教给予扶持,甚至将其变为巩固自己统治的文化工具;另一方面,宗教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得到统治者的扶植,不得不根据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变化,服务于政治。吐蕃仍处于原始的氏族社会发展阶段,虽有阶级因素存在,但尚未形成成熟的阶级社会。青藏高原散居着许多氏族部落,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远溯春秋时代,“散处河、湟、江、岷”间的古代西羌部落大约有150种。 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上虽然出现了‘王’,但这不过是小部落或较大的部落联盟的首领〔6〕。吐蕃统一以前,虽有奴隶制因素萌芽, 但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社会。笨教从侧面反映了这种政治格局。第一,吐蕃部落众多,群雄并起。笨教也神灵众多,地位平等。“在西藏任何一座山峰都被认为有神灵居于其上”〔7〕。战神、地方保护神比比皆是, 而且在吐蕃社会中,它们的地位是平等的。都得到牧民的信仰和崇拜。每座山头都可能居住过一个部落,每个地方神都可象征着这里曾出现过的一位部落首领。这便是多神设教的政治功能,也是宗教与政治关联的内涵之一。第二,笨教的主张与频繁战乱的社会现象相一致。由于吐蕃社会诸雄并起,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而笨教是不反对战争的,相反却出现了对于战神的崇拜,对于战神的祈祷是笨教祭祀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笨教与吐蕃社会的政治是相适应的。
吐蕃社会以其独特的游牧生产方式造就了笨教,它是藏族先民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一种尝试,尽管是非科学的东西,但它毕竟是吐蕃社会生活实践的一种反映,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然而,社会不断发展,人类的认识不断提高,宗教文化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二、佛教文化与吐蕃奴隶制社会接轨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了吐蕃各部, 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新唐书》记载:“其地与松茂嶲接,南极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员万里,为汉魏诘戎所无也”〔8〕。 随着吐蕃社会的统一和发展,佛教从南北两方传入,与吐蕃社会的这一变化和发展接轨。
吐蕃社会政权统一后,最深刻的变化是农业经济已开始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成份。据有关藏文文献记载,吐蕃统一前,雅隆悉补野部在恰墀在位时,今山南雅隆河谷地区已能“犁地耦耕,垦草原平滩而为耕地”,“耕种庄稼之农事首始于比”〔9〕。 这可能是吐蕃社会出现最早的农业经济,但这时的生产规模小,分布地域小,不足以对吐蕃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吐蕃政权统一后,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为集中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吐蕃农业首先在雅鲁藏布江中游两岸发展起来。随后与汉地接近的川、甘、青等地从汉族地区学来了农耕知识和技术,农业生产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唐朝王建诗《凉州行》写道:“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这是吐蕃社会发展农业生产的最好写照。随着农业生产的兴盛和发展,单一的游牧经济一变而成为农业经济。因此,农业经济已成为吐蕃社会主要的经济成份,是吐蕃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动力。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构成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社会意识也或迟或早发生变化。建立在分散、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上的笨教,其思想内容和形式都已不适应当时以农业经济为主要成份的吐蕃社会。因此,佛教乘虚而入,与吐蕃现实的社会发展接轨、吻合。
第一,佛教基本理论与奴隶制条件下藏族群众的心理契合。在原始氏族制条件下,藏族先民抵御自然威胁的力量非常微小,笨教所主张的天赐一切、万物有灵的观念与当时人们的心理和愿望相适应,只要崇拜神灵,祈求万物保佑便能达到心理平衡。霍夫曼指出:“那时的西藏人完全屈服于它的自然环境之下。他们的全部信仰扎根于自然和由自然界所控制的宗教概念始终是围绕着他们的荒野高原,他们崇拜的神祗是无数他们认为存在于这些地方的善恶的神灵”〔10〕。石泰安在《西藏的文明》一书中也指出:“通过男子之神便可增加男性,可以确保许多后裔世系;通过女子之神可以增加兄弟姐妹,女子的财产可以得到增加;通过舅神便可以与其他人保持良好关系,拥有充足的幸运;通过战神可以多得财富和少树敌;通过生命之神便可以得到长寿和坚强的生命力”〔11〕。但是,随着原始氏族制的瓦解,奴隶制经济的兴盛和发展,生产部门不断齐全、分工进一步完备,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人们虽然没有彻底摆脱自然力的压迫,但从农谷物的生产、种植,到城市的建设等,都显示了人间的力量在不断增强,人们不再完全依赖和屈服自然的力量。而佛教正是主张自我修行、自我完善,谁不做恶、安分守纪、好好劳动,谁就能得到一个好的转世,进入极乐世界,谁只要一心诵念“六字明咒”、供花敬佛,谁就能开登佛界。
第二,佛教“不杀生”的宗教活动促进了吐蕃经济的发展。牦牛、马、驴等牲畜是吐蕃发展农业经济的主要生产资料,佛教禁止杀生的活动,有利于保护各种牲畜,保护劳动生产资料,适应了吐蕃经济发展的要求。据有关文献记载,笨教活动每天要将公鹿、牦牛、绵羊、山羊等公畜各一千头活活肢解或杀死,以血献祭〔12〕。“在一年一度的大祭祀活动中,要宰杀马、牛、驴。甚至要杀人来祭祀天地”〔13〕。这些活动既极大地摧残社会财富,又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因此佛教的观念和主张,在新旧生产方式交替的关键环节上与吐蕃社会接轨,促进了吐蕃经济的发展。
第三,吐蕃社会经济发展为佛教宗教仪式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必须通过一定的物化形式表现出来,才能宣扬自己的主张,为广大教徒所掌握。这需要具备一定物质条件,通过宗教仪式才能实现。佛教有严密的宗教组织,不仅有教义、教规、经典、僧人,而且还要有寺院作为宗教活动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寺院是佛教的大本营,是佛教徒进行宗教活动、举行宗教仪式的固定场所,是整个佛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寺院建立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这样才能起到宣传主张,感悟众生的目的。在吐蕃游牧经济时代,牧民没有固定的生活居地,经济具有分散性。因此,当时的笨教活动只有简单的祭坛。只有当人们摆脱了游牧生产方式的流动性,在人口较集中,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居住下来,才能建立起佛教寺院。这就是农业经济给吐蕃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是宗教文化嬗变的主要原因。由印度著名的佛教大师寂护和莲花生所建立的吐蕃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就建立在雅鲁藏布江北岸发达的农业区。以后,甲德噶琼寺、杰拉康寺、康波且寺等著名佛教寺院便纷纷建立。佛教逐渐活跃起来。
第四,佛教一神教满足了王室集权统治的需要。由游牧经济发展为以农业为主要成份的经济,吐蕃由分散的原始部落发展成为统一的奴隶制国家,王室集权统一成为现实。王室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寻找各种舆论工具。佛教是一神教,在佛教教义中,佛的形象被描写得全知全能、至高无尚。象这样一个完全按照人间专制君主形象塑造出来的天上神灵,自然容易满足专制统治的要求,是他们最理想的思想武器。“松赞干布又使尼泊尔塑像匠人,按照松赞干布自己的身量,塑一尊观音像”〔14〕。因此,吐蕃王朝第一代统治者松赞干布积极扶持佛教。松赞干布曾派贵族弟子到克仔米尔学习,回来后用藏文翻译了一些佛教经籍。还“派人到锡兰请来蛇心旃擅的十一面观音像,又往印度和尼泊尔交界处请来诃利旃擅的观音像,作为供养修福的对象”〔15〕。此外,松赞干布还大修佛教寺院,以进行佛教宗教活动,并根据佛教经典,制定了法律,教育民众,使西藏民族逐渐强盛文明起来。另一方面,佛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紧紧依附于王室,神化各代赞普。这样,王室就利用佛教使自己的统治从宗教神坛获得了“王权神授”的地位。佛教也因王室的扶持在吐蕃社会找到了立足之地。
在吐蕃的奴隶制社会中,阶级分化是十分明显的,奴隶经常进行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恩格斯在分析欧洲天主教僧侣时指出:“在僧侣中间有两个极其不同的阶级。僧侣中的封建特权阶层形成贵族阶级”,他们“控制着大片土地,拥有许多农奴和依附农”,“是人民痛恨的对象”。〔16〕奴隶主、贵族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寻找一种理论工具来瓦解群众的意志和反抗精神。因此,佛教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忍辱无争”等说教便成了最好的精神麻醉剂。
佛教能够从异地传入吐蕃社会,说明它在吐蕃社会中有存在的必然性,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它适应了吐蕃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阶级统治的需要,历史表明,早期佛教确实为吐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就是文化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正象笨教在吐蕃社会由适应走向不适应一样,佛教也必然会由于社会的协调发展走向与社会相冲突的一端,从而让位于新的宗教文化。
三、藏传佛教与藏族封建社会的整合
特定文化要在异族文化中生存和发展,就必然受到异族文化传统的排挤和打击。佛教在藏族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与传统的笨教势力发生冲突。公元9世纪中叶,正当佛教蓬勃发展的时候, 笨教势力突然发难,“不信佛教的人,就说是弘扬佛教之过,请藏王停止弘法,民间喧扰不安”〔17〕。“松赞干布虽曾制定法令,教人民敬信三宝,学习佛经;笨教徒有暗改佛经为笨经的,也被禁止,但臣下和民间,仍有信奉笨教反对佛教的”〔18〕。最后,“朗达玛灭佛”〔19〕,演出了一幕佛教的悲剧史。继而,吐蕃王朝在风起云涌的奴隶大起义中崩溃。在社会历史转折的关头,藏族社会的思想意识也在发生急剧变化。笨教作为吐蕃游牧社会的产物失去了其存在的必然性。墀松德赞时期,民间有信仰笨教反对佛教的,墀松德赞“又使阿难陀等和他们辩论。笨教徒辩论失败,笨教书籍,除少数祈禳法外,都被废毁,不许传播”〔20〕。而佛教也无力独自与社会的发展再度吻合。然而,笨教和佛教毕竟曾是藏族社会思想文化的主宰,它们相互争斗,相互融合,终于在公元10世纪后半期,产生了一种新的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宗教文化,即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的产生,与藏族封建制的形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吐蕃奴隶制王朝崩溃后,广大奴隶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开垦,广大农奴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提高,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原来的奴隶主阶级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奴隶主阶级在同奴隶的斗争中丧失了实力,变成了自耕农民:另一部分奴隶主凭借过去的势力变成了一方的新的封建领主,即农奴主阶级。
藏传佛教文化迎合了新的历史交替时期人们的心理和要求。经过长期战乱获得人身相对自由的广大农奴,希望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下生产和生活,因此,佛教的反战思想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同时,由于广大群众长期饱受战乱和流离失所之苦,因此,佛教的人生无常、苦海无边、追求来世、往生极乐的一套精神说教,也就自然成了他们的精神依托:新兴的农奴主阶级,继承、吸收了以往统治者利用宗教文化作为统治工具的经验和教训,大力开展复兴佛教运动,为其统治服务。藏王智憧先派卫藏七人:卢梅慧戒、枳智德、聪格慧狮子、罗敦金刚自在、机巴智慧、宽罗卓协饶、云本德胜、往西康受戒学法。后来又派遣塔乙胜圣、惹希戒生、跋尊慧自在等五个人赴西康,先后都依止仲智幢、觉热慧菩提受戒(《藏王纪》)卢梅等回藏后,各自建立僧团,重立寺庙,建立民间信仰。“不久佛教传遍全藏,僧伽之众多、人才之涌现,都远非前弘时期(松赞干布和墀松德赞时期)所能比”〔21〕。统治者既可用佛教的宿命论思想来麻痹广大农奴,又可以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来豢养僧侣,并且,常常是自己亲自充当宗教界的头面人物,这就为西藏佛教与经济关系的“三位一体”性和“政教合一”的制度打下了基础。由此可见,吐蕃社会的笨教和佛教在遭受沉重打击后,公元10世纪后末期,佛教又重新从多康和阿里进入西藏,开始了佛教新的历史时期。
藏传佛教与初入吐蕃社会时的佛教其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的不同。藏族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有很大的差距,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带来了文化意识的差异性,传统的笨教势力仍有它存在的土壤,特别是在一些游牧和落后的地区。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要在藏族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藏族传统文化沟通和融合,吸收笨教的一些有利于自我生存的因素,同样,笨教必须吸收佛教一些思想内容和外在形式,方能沿续自己的活动。这样,几经周折,几经沉浮、变化,佛教最终与笨教融合,形成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的产生是历史和时代发展、变化的产物,在一定时期之内,它起到了协调藏族思想意识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积极作用。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封建割据的加深,藏传佛教逐步分成了不同的教派。因此,藏传佛教在社会制约下,自身也不断发生变化,以更好地适应和协调自身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无论是笨教、佛教、还是藏传佛教,作为文化现象,都是由特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都具有历史必然性,文化自身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历史继承性。因此,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宗教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藏传佛教仍然活跃于藏族社会中,它如何更好地与社会发展相协调,服务于广大群众,有待于广大宗教工作者进一步研究。
(审稿人 克珠群佩)
注释:
〔1〕《王者遗教》第1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42页
〔3〕〔8〕〔14〕〔15〕〔17〕〔18〕〔19〕〔20〕〔21〕《中国佛教史》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134、135、135、144、137、138、138、146页
〔4〕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第15页
〔5〕〔7〕内尔斯基《西藏的鬼怪和神灵》选自《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第244、169页
〔6〕《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9〕《智者喜筵》第7品第18页
〔10〕《西藏的宗教》霍夫曼著,李有义译,第4~5页
〔11〕石泰安著,耿升译《西藏的文明》第232页
〔12〕东噶·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13〕参见《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
〔16〕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