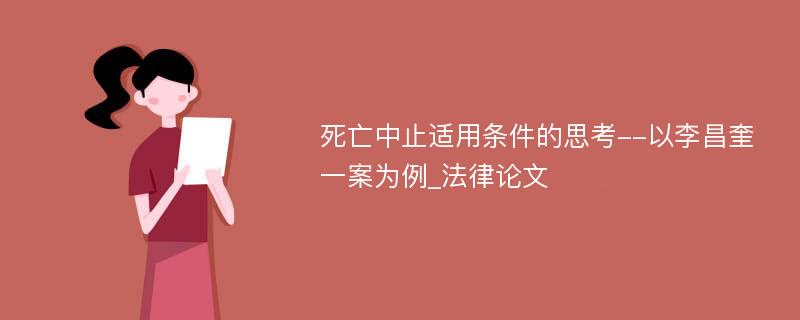
死缓适用条件之反思——以“李昌奎案”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死缓论文,为例论文,条件论文,李昌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生在云南省巧家县的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案(以下简称“李昌奎案”)早已审结,但该案在一年的时间里经历多次改判给人们留下了诸多疑问,其中之一就是死缓的适用条件到底是什么?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据此,“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便成为死缓的适用条件。但是,这个条件一方面“语焉不详,缺乏规范质量和法实证主义的风格,不太符合罪刑法定主义关于刑法语言明确性的‘形式侧面’和营造法秩序安定性和公民期待安全感的‘实质侧面’,导致学术界和实务界在具体裁量和斟酌认定上见仁见智,随意性和随机性过大”;①另一方面,“此种立法用语是不正确的,‘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从字面上讲就是要缓行。之所以对一个罪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就是因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而要缓行,这显然是循环论证。因此以是否‘必须立即执行’作为区分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的标准,从逻辑上讲,是难以说通的。如此看来,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之间并没有一个明晰的区分适用标准。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或死刑缓期执行可能就是主观衡量的一念之间,对于罪犯而言,却是生死两重天”。②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理解1997年《刑法》规定的死缓适用条件呢?笔者下面结合“李昌奎案”对该问题作些探讨。
一、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不是死缓的适用条件
审理“李昌奎案”的二审人民法院的领导曾向记者指出:“同样是死刑,社会危害不同,就要区别对待”。③其意思是说,在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下,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还是适用死缓的根据在于“社会危害不同”。其实,这种观点在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界比较流行,如“罪行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④“犯罪行为不是最严重地侵害国家或人民利益”,⑤“危害后果不是特别严重”,⑥等等,都是人们关于死缓的适用条件的表述。笔者在此将认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是死缓的适用条件的观点称为“肯定说”。但是,也有论者对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作为死缓的适用条件提出了质疑。例如,有论者认为:“凡是某一情节能优先被视为‘罪行不是极其严重’所考虑而不能适用死刑(包括死缓)的因素,就不能先适用死刑再将其作为适用死缓的因素来考虑,因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毕竟是‘罪行极其严重’之后的又一限制性条件,否则就是曲解了立法原意……将‘罪行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等视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就不妥当”。⑦笔者将这种观点称为“否定说”。
“肯定说”与“否定说”的对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究竟是否死缓的适用条件?的确,由于1997年《刑法》第48条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是“罪行极其严重”,即最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而死缓不是独立刑种,只是死刑的一种特殊执行方法,因此,死刑的适用条件不能再作为死缓的适用条件。换言之,既然在先期决定死刑适用时已经断定犯罪分子“罪行极其严重”,那么在后来决定适用死缓时就不能说犯罪分子“罪行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正如上述持“否定说”者所言,“罪行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就是“罪行不是极其严重”,应当据此不适用死刑,而不是据此不适用死缓。
持“肯定说”者认为,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大是死缓的适用条件,其理由是,作为死缓适用条件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大与作为死刑适用条件的社会危害性较大在含义上并不相同。具体而言,持“肯定说”者把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分为两种情形:(1)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分为极其严重与尚不是极其严重。这是死刑适用与否的界限。(2)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细分为以下3种情形:1)“罪行极其严重的下限标准”——刚刚达到罪行极其严重;2)“不过分地超过罪行极其严重的下限标准”——超过罪行极其严重的“距离”相对较近;3)“远远地超过罪行极其严重的下限标准”——超过罪行极其严重的“距离”相对较远。根据上述观点,只有前两种情况的“罪行极其严重”才有可能适用死缓。显然,3种情况的区别判断成为决定死缓是否适用的一个条件。持“肯定说”者以刚刚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所谓“下限”为界,认为确定死刑的适用条件是为了解决犯罪分子的行为是否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问题,而确立死缓的适用条件是为了解决犯罪分子的行为是否属于“罪行极其严重”中的“相对更为严重”的问题。死缓的适用条件与死刑的适用条件所判断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是一回事,并没有对同一事实情节作重复的评价。
应当承认,持“肯定说”者把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作为死缓的适用条件有一定的说服力,并且符合我国目前对死刑犯的最大容忍限度:如果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罪行极其严重”中的更加严重程度,那么无论有什么其他的从宽情节都不能原谅犯罪分子,更不应对其适用死缓。如果说犯罪分子在某种情况下杀死一个人刚刚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还可以考虑适用死缓,那么在同样的情况下犯罪分子杀死10个人就便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重中之重,对其没有考虑适用死缓的余地。正是这种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对死刑犯的有限容忍度,使得我国人民法院的法官在理解死缓的适用条件时,很难不把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考虑在内,审判实践中在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适用死缓时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目前仍是通行的做法。“李昌奎案”一审判决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的。审理“李昌奎案”的二审人民法院决定对李昌奎适用死缓,虽然判决结果不同,但从前面提到的二审人民法院领导说明的根据看其同样是持“肯定说”,这说明“肯定说”对司法实践的影响相当深远。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肯定说”存在诸多缺陷:(1)与法律规定不符。1997年《刑法》第48条“罪行极其严重”的规定具有概括性,既包括罪行刚刚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也包括罪行超过极其严重“下限”的各等程度,无论超过多少都是“罪行极其严重”,都是决定适用死刑的根据。持“肯定说”者对“罪行极其严重”所作的区分于法无据,也无法回答在何种情况才算达到“下限”。例如,在杀人案件中,杀死几个人才算是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下限”而可以判处死刑?是杀死1人还是杀死3人?把人刺成植物人或者重度瘫痪是否达到“下限”?(2)与实践不符。例如,就一个杀死10人的案件而言,人民法院往往是根据犯罪分子杀死10人的既成事实作出“罪行极其严重”的整体评价,而不是根据杀死其中的1人或者3人来评价“罪行极其严重”并决定适用死刑。换言之,适用死刑的决定是根据全部犯罪后果体现的社会危害性作出的,而不是根据部分犯罪后果体现的社会危害性作出的。既然如此,就没有什么从杀死10人到“罪行极其严重”的“下限”之间的所谓“距离”。总之,既然已把杀死10人的事实作为死刑适用的“罪行极其严重”来认定,那么就不能到考虑是否适用死缓时又自相矛盾地说适用死刑只是根据所谓“下限”作出的。(3)与刑事政策不符。死缓制度意味着对“罪行极其严重”而应判死刑的犯罪分子不一定非要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死缓制度的政策根据一方面是“少杀”的价值取向,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尽量减少死刑的适用,或者尽量减少死刑的执行;另一方面是“改造”的价值取向,犯罪分子只要还有改造的可能性就应当尽量给其出路,尽量通过改造使其回归社会。犯罪现象具有复杂性,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无论其危害程度处于极其严重的“下限”还是属于重中之重,都存在改造的可能性。尤其是那些事出有因、临时起意、偶然犯罪、事后又真诚悔罪、主动立功、全力赔偿被害人一方、以积极的态度和行动赎罪的犯罪分子,虽然其罪行称得上“更为严重”程度的“极其严重”,但不能说其完全没有改造好的可能性。持“肯定说”者把“罪行极其严重”的“重中之重”者排除在死缓制度的适用之外,与“少杀”和“改造”的刑事政策不相吻合,执行死刑的数量很难减少,也使自首、立功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失去功效,并有可能强化这类犯罪分子与司法机关对抗的心理。
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否定说”似乎更为合理,即死缓的适用条件中不应当包括判处死刑时已经考虑过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或者说,死缓的适用条件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之外的其他因素。在笔者看来,审理“李昌奎案”的二审人民法院作出判处李昌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决定的依据并不是该法院有关领导阐述的“肯定说”,而是“否定说”。李昌奎首先暴力强奸并杀死被害人,然后又杀害该被害人之弟——一个年仅3岁的无辜儿童,其犯罪手段极为残忍。也许有人认为与杀人狂相比,李昌奎所犯之罪还算不上“罪行极其严重”的“重中之重”,但笔者认为其行为也绝非刚刚达到“罪行极其严重”或者超过的距离明显较小,因为其行为起码比此前判处死刑并决定立即执行的药家鑫的罪行要重,药家鑫杀死一人,没有被认定为刚刚达到或者不多地超过“罪行极其严重”而适用死缓,李昌奎杀死两人并犯有数罪,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绝不低于药家鑫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由于民众期待判处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因此,如果二审人民法院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作为考虑是否判处死缓的标准,那么决定判处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更“顺理成章”且符合“民意”。然而,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没有考虑这种与“药家鑫案”相比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而是在判决书中强调“罪行极其严重”之外的其他因素。⑧显然,这些决定死缓适用的自首、认罪、悔罪、赔偿等因素都是犯罪之后能够表明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因素,而不是能够表明犯罪行为本身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因素。
由此看来,审理“李昌奎案”的二审人民法院的有关领导为死缓判决所找的“社会危害不同”的根据,与判决书中的具体根据对不上号。以李昌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达不到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度作为适用死缓的理由,显然不符合案件事实和判决书的表述,更经不起与“药家鑫案”相比较,因此引起民众的质疑也就不足为怪。“肯定说”与“否定说”不能兼容,同一个人民法院就同一个案件决定是否适用死缓只能选择一种法理根据。笔者认为,“否定说”是真正符合我国少杀刑事政策和刑法规定的学说。2010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9条明确规定:“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但只要是依法可不立即执行的,就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该《意见》第22条规定:“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据此,审理“李昌奎案”的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有根据的,至于该案事实是否符合死缓的适用标准,如李昌奎的自首能否成立、邻里纠纷与该案罪行是否有因果关系等,则是另一个问题。当然,即使审理“李昌奎案”的二市人民法院的有关领导不做“肯定说”的解释,民众也不会满意以“否定说”作为法理根据的二审判决,因为这一判决挑战了当前社会民众的宽容度。不过审理“李昌奎案”的二审人民法院的有关领导倒是表达了这种判决的“超前”性:“10年之后再看这个案子,也许很多人就会有新的想法……我们现在顶了这么大的压力,但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⑨这个透着尴尬、委屈和无奈的表达反映了实然的“肯定说”与应然的“否定说”之间的距离。⑩
那么在当前,人民法院面对“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犯在决定是否判处死缓时,究竟是应该选择“肯定说”还是应该选择“否定说”呢?笔者的意见是:(1)原则上应当坚持“否定说”,即“罪行极其严重”范围内的危害程度区分不能成为直接决定是否适用死缓的根据。(2)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中的“更重”者也要坚持“否定说”,即在人身危险性明显低的情况下,如重大立功,(11)对犯罪损失做了最大限度的补偿和挽回,同时有自首、悔罪、立功、赔偿等多种反映人身危险性低的因素,为立功、赔偿、赎罪等做出重大权益牺牲等,都可以考虑适用死缓。只有在人身危险性较高的情况下,如不存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形,或者存在与司法机关对抗、不思悔过、继续作恶等情形,才应考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3)在“罪行极其严重”并且属于“重中之重”者更难获得死缓的意义上,吸收和体现持“肯定说”者主张的对“罪行极其严重”作进一步区分的观点。
二、民意、舆论和媒体的压力不是死缓的适用条件
民意、舆论和媒体之间既存在联系又有区别。三者之间的联系是:民意,指民众的意愿;舆论,指民众的意见或言论;媒体,又称传媒,指传播信息的载体或物质工具,主要包括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其传播的信息会形成舆论、可以反映民意。三者之间的区别是:民意一般是指大多数人内心的真实意思;舆论主要指民众表达出来的意见所形成的倾向,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代表民意;媒体是舆论形成的媒介,常常承载民意,但舆论和民意也可用媒体之外的形式来表达。我们在讨论民意、舆论和媒体与刑事审判之间的关系时必须注意到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晚近以来,民意、舆论和媒体对刑事审判的关注度日益增强,这一方面反映我国的民主化水平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民法院面临的压力不断加大。“李昌奎案”的审判过程正好反映了这一事实。对于“李昌奎案”媒体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舆论反映强烈,民意沸腾,喊杀声一片,特别是在二审人民法院将一审人民法院判决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二审人民法院受到的压力可谓超乎想象。当然,对于“李昌奎案”的判决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主张判处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者主要强调李昌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严重;而持否定意见者并不直接评价李昌奎是否应该被立即执行死刑,而是从司法独立的层面,强调刑事审判不应受到民意、舆论和媒体的干预。(12)笔者认为,二者的不足之处在于其都没有把死缓的适用条件作为重点进行系统研究,因而都不能真正理性地回答李昌奎究竟应否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也不能合理地说明民意、舆论和媒体的关系。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具体而言,它是指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法律的规定定罪量刑。就“李昌奎案”而言,对李昌奎是应当适用死缓还是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所依据的标准只能是1997年《刑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李昌奎的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死缓适用案件,那么就应对其适用死缓;如果李昌奎的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那么就应对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因此,审判“李昌奎案”的人民法院无论遇到的民意、舆论和媒体的压力有多大,都应当并且只能根据1997年《刑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决。
在现代法治社会,涉及法律问题的民意首先应通过法律来表达。对犯罪分子是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还是应当适用死缓的民意已经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刑法体现出来,具体的表现就是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的适用条件的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与刑法的规定相符,就体现了民意;否则,就违背了民意。法律认可的民意是通过民主程序表达的多数人的意愿,人民法院审判案件既不能屈从民主程序之内的少数人的意愿,也不能屈从民主程序之外的多数人的意愿。具体而言,法律是以多数票通过的民意,一方面不能要求人民法院去屈从与法律不符的少数人的意愿,也不应将此称为“民意”;另一方面,不能要求人民法院去屈从尚未以多数票通过的多数人的意愿,尽管这在实质上可能确为“民意”。无论是少数人的还是多数人的未以法律形式表达的意愿,既有可能是非理性的,也有可能是理性的。人民法院既不能屈从于非理性的“民意”,也不能按照法律之外的理性“民意”办案,更不能考虑笼统抽象的所谓“民意”。未经过民主程序集中的民意往往说不清道不明。如果硬性要求人民法院考虑民意,那么就会重现审理“药家鑫案”的人民法院当庭给300余名旁听者发问卷以调查被告人是否该死之类的荒诞不经、贻笑大方的笑话。(13)其实,即便统计出的结果是多数人的意愿,它也可能是非理性的,人民法院也不能服从。人民法院更不能屈从舆论,迎合媒体。舆论作为民众的言论,既有正确和先进的,也有错误和落后的;既有意愿的真实表达,也有意愿的虚假表达。承载舆论的媒体同样如此,除了内容的鱼龙混杂之外,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往往从自己的主观意愿出发选择相关信息进行传播,而这样的传播往往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当然,笔者强调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不受民意、舆论和媒体的干涉,并不是说不要外部监督,而是认为民意、舆论和媒体对人民法院的监督绝不是以情压法、以众抗法,而应当是以法促法——监督人民法院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案。如果民意、舆论和媒体超出监督的范围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说三道四,那么人民法院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相反,如果民意、舆论和媒体监督的内容和手段合法且与人民法院的意见存在明显甚至严重的分歧,那么人民法院应当慎重细致地审视自己的审判工作是否严格遵循了法律的规定,在这个基础上再作出相应的决定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从审判独立的意义上讲,民意、舆论和媒体不能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不当干预;从监督的意义上讲,民意、舆论和媒体可以对人民法院产生影响。就“李昌奎案”而言,一方面人民法院应当依据1997年《刑法》的规定独立作出审判,不受包括民意、舆论和媒体在内的任何法外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人民法院是否依据1997年《刑法》的规定作出判决,应当接受包括民意、舆论和媒体在内的外部监督。
应当承认,人民法院对“李昌奎案”所进行的3次判决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一审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昌奎所犯故意杀人罪,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虽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昌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4)二审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昌奎在犯罪后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属自首;在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好;并赔偿了被害人家属部分经济损失,故上诉人李昌奎及其辩护人所提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的上述理由和辩护意见属实,本院予以采纳。鉴于此,对李昌奎应当判处死刑,但可以不立即执行”。(15)从上述判决书中不难看出,两份判决书的区别在于李昌奎的自首、认罪和悔罪、赔偿是否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情形。笔者还没有看到再审判决书,不过,从媒体的报道看,再审法官当庭宣布“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对李昌奎改判死缓属量刑不当,故再审合议庭决定,改判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法院核准”。(16)由于再审判决书没有说明“量刑不当”的理由,因此笔者只能推测再审人民法院同意一审人民法院的意见。显然,上述判决书的区别,体现了审案法官对死缓适用条件的理解不一。就此而言,审理该案的各级人民法院的判决都无可厚非。这里的问题是,一个案件在事实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不同审级的人民法院让同一被告人的刑罚在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之间多次变换,甚至同一高级人民法院先后作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决定就很不正常了。这说明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还未能准确理解死缓的适用条件。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民意、舆论和媒体已经对“李昌奎案”给予极大关注并就量刑问题提出质疑时,被质疑的人民法院并没有从死缓的适用条件方面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是大谈报应杀人不能解决社会矛盾,责怪民意、舆论和媒体的观念落伍。紧接着,又有法学专家出来支持这种说法,并认为该案的再审是民意、舆论和媒体损害了人民法院的权威性,仍然没有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对死缓适用条件的研究上,更没有作出深刻的学理解释。恕笔者直言,法官和法学专家都不屑于解读法律标准本身,而是热衷于在观念方面与民意、舆论和媒体展开论战,或者从刑事政策层面反复强调“宽严相济”、“少杀慎杀”政策,正是使人民法院陷于被动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在像“李昌奎案”这类涉及生死且引起民意、舆论和媒体极度关注的案件中,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唯一标准就是1997年《刑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面对民意、舆论和媒体施加的压力,只能在判决书和其他必要场合表达对1997年《刑法》相关规定的严格遵守及其理由,除此之外均为多余。就学术界而言,应当针对“李昌奎案”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开展对死缓适用条件的深入研究,为司法实务部门掌握法律标准提供理论根据。此外,专家学者就“李昌奎案”等类似案件出面回应民意、舆论和媒体时,也应当以死缓适用条件的研究成果为根据,而不能信口开河误导民意、舆论和媒体,并因此给人民法院增加压力。
三、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较小才是死缓的适用条件
1979年《刑法》第43条规定死刑的适用条件是“罪大恶极”,1997年《刑法》第48条将其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往往影响到人们对死缓适用条件的把握。一般认为,“罪大恶极”应从两个方面理解:“罪大”是指犯罪行为及其后果极其严重,给社会造成的损失特别巨大。“罪大”体现的是犯罪的客观实害,是社会对犯罪危害行为和危害后果的一种物质的、客观的评价。“恶极”是指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特别大,通常表现为犯罪分子蓄意实施严重罪行、犯罪态度坚决、良心丧尽、不思悔改、极端蔑视法制秩序和社会基本准则等,是社会对犯罪分子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17)人们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也有两种理解:(1)认为其是对1979年《刑法》相关规定的概括和精炼,内涵不变,既包括“罪大”,也包括“恶极”;(2)认为其是对1979年《刑法》的相关规定作了修改,减去了“恶极”,只剩下“罪大”。从语义上讲,后一种理解更为合适;从价值上讲,前一种理解更为合理。因为按照后一种理解仅凭客观危害就可以判处死刑,这比1979年《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更为宽松。显然,后一种理解并不符合我国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18)
笔者同意“罪行极其严重”等同于“罪大恶极”的观点,但不同意“恶极”包括人身危险性的观点。“罪行”只能是指犯罪行为本身,包括反映客观危害性的行为、对象和结果以及反映主观恶性的罪过、目的和动机等内容。“罪行极其严重”可以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客观危害极其严重而主观恶性还不是极其严重;(2)主观恶性极其严重而客观危害性还不是极其严重;(3)客观危害性与主观恶性都很严重。从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看,将上述第三种情况作为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更为合适,但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当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极其严重时对犯罪分子就有可能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笔者认为“罪行”体现的是社会危害性,不包括人身危险性。虽然量刑也要考虑人身危险性的因素,但刑法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对量刑的影响是分别规定的。1997年《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里的“罪行”强调的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那些体现人身危险性的因素不能改变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可以从预防犯罪的层面影响犯罪分子承担的刑事责任。体现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量刑情节不属于“罪行”,自然不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客观的行为和结果“极其严重”,也可以说主观的罪过“极其严重”,但不能说体现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因素“极其严重”。
刑法对体现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量刑情节与体现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量刑情节的区别规定还表现在1997年《刑法》第61条的规定上:“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从该条的规定不难看出,量刑的依据在于犯罪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具体而言,这里的“事实”指犯罪事实,“性质”和“情节”指犯罪事实的性质——社会危害性,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则是指犯罪事实的质与量。根据1997年《刑法》第62条和第63条的规定,无论是体现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情节,还是体现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情节,只要能够在量刑中起“从重、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的作用,都属于量刑情节。相应的,在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众多条文规定的各种从重、从轻和减轻的具体量刑情节中,既有反映犯罪事实本身的情节(如刑法总则规定的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犯罪未遂、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等,刑法分则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诬告陷害从重处罚、入户抢劫加重处罚等),也有反映犯罪事实发生之前的事实情节,如对累犯从重处罚实际上就考虑了已经审判处理的犯罪事实对目前犯罪案件量刑的影响;还有反映犯罪事实发生之后的事实情节,如对犯罪之后具有自首、立功等事实情节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减轻乃至免除处罚;更有反映犯罪事实发生之时存在的非犯罪本身的事实情节,如“战时”从重,“战时”只是犯罪事实存在的社会环境状态,它虽然与犯罪事实同时存在,但不是犯罪事实本身。此外,在人民法院掌握的酌定量刑情节中,也有反映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情节与反映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情节之分,如犯罪手段、对象、后果、动机等属于前者,犯罪分子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影响国家政治、外交、民族、宗教、国际事务的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情况等属于后者。(19)
由此可见,刑法对量刑依据的规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量刑依据指1997年《刑法》第61条要求人民法院考虑的犯罪行为本身的情节,其体现的是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广义的量刑依据指1997年《刑法》第5条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该法第62条和第63条等的规定,其内容既包括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也包括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既然体现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因素和体现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因素都能影响量刑,那么完整意义上的量刑就应该是指广义的量刑。201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3条的规定明确体现了广义量刑的含义:“对被告人依法判处刑罚,应当符合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与被告人的罪行及其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意见》第1条和第2条还揭示了广义量刑的价值内涵——“保障刑罚功能的充分发挥和刑罚目的的有效实现”。笔者认为,虽然作广义的量刑规定很有必要,但作狭义的量刑规定仍有意义。量刑首先要依据犯罪事实本身,考虑罪行轻重,在惩罚犯罪时做到罪刑相适应,在这个基础上,再着眼于预防犯罪,依据犯罪前后以及犯罪时犯罪事实之外的相关因素,考虑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最终决定犯罪分子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的大小。具体而言,量刑时应当首先根据犯罪行为本身的情节决定适用法定刑中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从中选择一个适当的刑罚,再根据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因素对这个刑罚或加或减,最终得出量刑的结论。遗憾的是,《意见》未能把这个逻辑顺序贯彻到底,其第4条规定:“基准刑是指对已确定适用一定幅度法定刑的个罪,在排除各种法定和酌定情节的情况下,仅依其一般既遂状态的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而应判处的刑罚”。虽然先根据犯罪事实决定基准刑是正确的,但这里的犯罪事实仅指“一般既遂状态的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而把各种法定和酌定情节对量刑的影响放在基准刑确定之后的第二步,这样就把同样是体现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犯罪事实情节与“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相割裂,而与第二步量刑中的体现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因素混为一体。这既不符合量刑所体现的在惩罚的基础上预防犯罪的价值根据,也不符合量刑操作的实际顺序。例如,“入户”是抢劫罪加重处罚的情节之一,如果量刑时仅考虑抢劫罪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不考虑“入户”的情节,那么就没法“确定适用一定幅度法定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刑格次,也没有办法在“已确定使用一定幅度法定刑”的基础上确定“基准刑”。
因此,法官在量刑时只有首先考虑体现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因素,再考虑体现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因素,才能较好地实现刑罚的惩罚功能和预防目的。死刑的判处亦不例外。死刑的适用首先要考虑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和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以判断某犯罪行为是否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1997年《刑法》第48条“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规定表明对罪行未达到极其严重标准的不能适用死刑,但这并不意味着罪行达到极其严重标准的就必然要适用死刑。确认“罪行极其严重”只是适用死刑的前提,最后决定适用死刑,还要在确认“罪行极其严重”之后进一步考量体现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因素,只有在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很大的情况下,才能确定对其应当判处死刑。由此可见,如果犯罪分子“罪行极其严重”又是累犯且没有任何自首、立功等体现其人身危险性较小的情节,那么就应当对其判处死刑;如果分罪分子“罪行极其严重”但不是累犯且有自首、立功等体现人身危险性较小的情节,那么就不应当对其判处死刑;如果犯罪分子同时具备从重、从轻、减轻等体现人身危险性的情节,那么就要进行综合权衡,以决定对其是否应当判处死刑。显然,按照这样的思路,死刑的适用会得到较为严格的控制。
将累犯、自首、立功等体现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情节作为死刑适用的条件在量刑中加以运用对于控制死刑的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那么这些因素就不可能再次成为对犯罪分子是否适用死缓考量的因素;如果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那么就表明这些因素还不足以成为对犯罪分子不判死刑的理由。这里的问题是,这些因素能否成为此后对犯罪分子决定适用死缓考量的因素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20)由于死刑的适用与死缓的适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是量刑的问题,后者是行刑的问题,因此,将同一案件事实用于不同问题的考量并不属于重复评价。换言之,在累犯、自首、立功等体现人身危险性的情节不足以否定死刑适用的情况下,其仍然可以作为否定死刑立即执行的因素。此外,在同样“罪行极其严重”的前提下,根据这些因素来决定是否适用死缓也具有合理性。总之,适用死刑的首要条件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而累犯、自首、立功等情节只能起次要作用;适用死缓的唯一条件是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较小,而累犯、自首、立功等情节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累犯、自首、立功等情节之外还有犯罪中、犯罪前、犯罪后等方面反映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诸多因素,至于这些因素究竟包括哪些、该如何评估,目前我国刑法学界还鲜有研究。不过,在考虑量刑情节时无论如何首先应当考虑法定情节,然后再考虑酌定情节,且前者的分量应当比后者更重。这里还须强调的是:(1)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是适用死刑的首要条件,人民法院不能以犯罪分子具有自首、立功等情节为由对犯罪分子不判处死刑,当然也不能单纯地或主要地以存在累犯等情节为由判处那些罪行尚未达到极其严重程度的犯罪分子死刑。(2)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也是死刑的适用条件之一,人民法院不能只依据“罪行极其严重”就决定对犯罪分子适用死刑,也不能屈从于被害人一方和民众的压力而不敢根据犯罪分子具有自首、立功等情节决定对其不适用死刑。(3)将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较小作为死缓适用的唯一条件并不意味着只要犯罪分子具有自首、立功等情节就一定要对其适用死缓。
注释:
①高铭暄、徐宏:《中国死缓制度的三维考察》,《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2期。
②傅义、周林:《死缓制度的法理探疑》,《当代法学》2002年第1期。
③转引自贾磊:《省高院“死缓解释”再遭质疑》,《云南政协报》2011年7月11日。
④张正新:《中国死缓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⑤马克昌:《论死刑缓期执行》,《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
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2002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⑦高憬宏、刘树德:《死缓适用条件设置的四维思考》,《当代法学》2005年第5期。
⑧(15)参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0)云高刑终字第1314号》,http://WWW.chinacase.org/? action-viewnews-itemid-961,2012-11-20。
⑨转引自刘子瑜、都力维:《云南省高院副院长认为,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人》,《新快报》2011年7月13日。
⑩如果此前审判“药家鑫案”的人民法院以“否定说”为标准进行判决,那么也可以让药家鑫活着,但从该案的审理过程看,当今社会的宽容度有限促使人民法院根据“肯定说”作出了判处药家鑫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
(11)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立功与重大立功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在现实生活中仍存在着,并且对死缓的适用仍具有影响。
(12)参见杨涛:《药家鑫死刑,李昌奎缘何死缓》,《深圳商报》2011年7月4日;贾宇:《舆论监督司法应回归理性》,《法制资讯》2011年第8期。
(13)李婧:《药家鑫案征量刑意见遭疑 西安中院回应称按省高院要求》,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1-04/14/c_121306166.htm,2012-11-26。
(14)参见《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0)昭中刑一初字第52号》,http://WWW.chinacase.org/? action-viewnews-itemid-960,2012-11-20。
(16)刘长:《李昌奎案再审全记录:重归死刑》,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10823/072210361059.shtml,2012-11-20。
(17)参见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18)参见赵秉志、肖中华:《论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的司法适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高憬宏、刘树德:《死缓适用条件设置的四维思考》,《当代法学》2005年第5期。
(19)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新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1-363页。
(20)笔者曾经认为这些体现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情节不应“一身兼二任”——或者作为量刑情节或者作为行刑情节,后来受中国人民大学冯军教授的启发改变了当初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