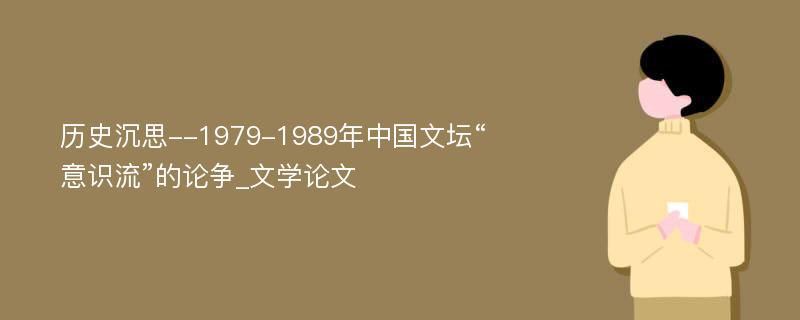
历史的沉思——1979-1989年中国文学界“意识流”论争轨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轨辙论文,意识流论文,国文论文,学界论文,年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03)04-0110-06
一、导火索:《现代小说技巧初探》
就新时期叙事文学中现代主义思潮在理论层面上最初萌动的源头而言,不能不首先提 到由叶君健先生作序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早在它问世之前,高行健自19 80年8月以来,陆续在《随笔》丛刊上发表“文学创作杂记”系列。当时它们并未引起 文学界的普遍注意,倒是正当程度不同地涉及了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表现手法的“ 朦胧诗”崛起的大讨论的火头上,它们被结集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小册子,由花城 出版社于1981年9月和1982年12月先后推出两个版次,印数高达35,000册之后,高行健 其人及其薄得不起眼的那本小册子才进入到文学界关注的视野。
叶廷芳在《美的流动》一书中指出:“中国新时期作家接受外来影响有的是局部的, 有的则是全局性的。前者居多数,他们只试图在技巧上有所革新,多半浅尝辄止。后者 则是观念上的转型。就笔者接触到的作家而言,他们中较早的当推高行健(着重号为本 文笔者所加)。1981年他推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当代西方小说 的各种新风格、新技巧,一时引起广泛兴趣。当时一些最有活力的作家如王蒙、冯骥才 、刘心武、李陀等都为之奔走相告(王蒙、李陀并在创作中有所表现)。”[1](P27)当时 的实际情况确乎如斯么?翻检一下新时期文学界中那段值得记忆的往事,不难发现:首 先,王蒙在《小说界》1982年第2期上发表了写于1981年12月23日《致高行健》的一封 信。信中称:“叶君健同志的序就够引人注意的了,而你的书呢?确实是论及了小说技 巧的一些既实际、又新鲜的方面,使用了一些新的语言,带来了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思 路。……感谢你的多方面的启发,使人扩大了眼界。”接着,《上海文学》1982年第8 期刊载了冯骥才写给李陀的信(1982年3月31日)《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他说, “刚刚读过高行健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我像喝了一大杯味醇的通化葡 萄酒那样”。“在目前‘现代小说’这块园地还很少涉足的情况下,好像在空旷寂寞的 天空,忽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风筝,多么叫人高兴!”而后,也就在这一年同一期 刊物上,李陀给刘心武的信(1982年5月20日)《“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中袒 露出他的思绪冲动和感慨心境:“我真希望《初探》这本小册子能够引起文学界的广泛 的注意。我不期望大家都如你我一样喜欢这本小册子,也不期望大家都同意书中的观点 ,这都不必。我只希望它能够‘吹皱一池春水’的‘乍起’之风。”最后,还是在这一 年同一期刊物上,《需要冷静地思考》则表露出刘心武给冯骥才的信(1982年6月8日)的 心路指向:“高行健放出了好大的一个‘风筝’(他那‘风筝’确实算得上漂亮——但 远非完美)……总是一种打破‘空旷寂寞’的气象,也即是春天的气象……我虽不才, 逢此阳春时气,又怎按捺得住心痒呢?”这些曾历经新中国诞生以及其风风雨雨的中年 作家不约而同地为一本小册子的问世而有感而发,以至引发了新时期文坛围绕《现代小 说技巧初探》展开的热烈讨论。
比较有代表性的“读后感”或许是刘心武发表在《读书》1982年第6期上的《在“新、 奇、怪”面前:读<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他认为:“集中介绍西方现代小说的写作技 巧,在介绍中把对作家作品、流派特色的分析与中国当前创作实际的考察紧密结合起来 ,既摆脱了学院式的引经据典、概念阐述之枯燥程式,不拘一格,又体现着深思熟虑、 融会贯通之生动活泼,粗成系统,而且文气流畅,涉笔成趣,读毕不免要掩卷深思。” “高行健同志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便是这样一本难得的好书。”文章对高行健著 作中主要的理论观点几乎一一给予了适度的点评。可是,《文艺报》1983年第6期上王 先霈的文章《<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读后》则不以为然:“说它是对新文学潮流的反应, 是要给这股潮流推波助澜。我又把它找来再看一遍。的确,统观约九万字的全文,不难 发现这本专谈技巧的书贯穿了一种明确的理论观点。在我看来,这种理论观点是很有些 偏颇,同小说发展史不那么吻合,同中外小说发展现状也有抵牾。”各方你谈我评他论 ,以至后来扩展成文学界较为集中地就西方现代派问题进行剧烈的思想交锋。
这种思想交锋主要聚焦在四个问题上:第一,怎样看待西方现代派文学?第二,中国当 代文学发展进程中要不要建立自己的“现代派”?第三,步入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创 新焦点是否仅仅在于艺术形式?第四,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现实 主义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围绕这些问题的激烈争鸣在某种意义上绝不亚于斯托夫人的一 本小书所触发的美国社会文明进程的嬗变。而这些问题的论争又不可避免地具体牵扯西 方现代文学中各种流派乃至技巧之出场。其中,文学“意识流”与新时期早先时候一些 先行者们的文学创新实践胶着在一起,成为当时文学界最为火爆的论辩话题之一。我想 ,这大概是《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作者所始料未及的。
二、合法性:众声喧哗
“合法性”概念出自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192 4-)的学术专著《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他认为,在一个后现代社会中,“ 科学知识并不是全部的知识,它曾经是多余的”,它总是处在与叙事性知识的“竞争和 冲突”中[2](P12)。由于科学知识以“中性化”、“符号化”的面目出现,在吸引人愉 悦人方面反而不如叙事性知识,从而导致研究者、传播者、教学者和学习者都对它产生 一种消极的抵触的态度。人们对科学家也产生了怀疑。因此,现代科学知识在今天便面 临着一个“合法化”(legitimacy,一译为“合法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被借用 来检视新时期文学“意识流”的论争,在我看来不也是个很贴切的关键词吗?
从文学角度来说,所谓“合法性”就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等方面曾受到批 判、排拒,甚至“颠覆”的外来的或本土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取 得了被认可、被采纳甚至被赞许的地位。一种不曾被理解、被接受的外来的或本土的或 两者兼而有之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受到了理解和接受的礼遇。这里主要是以相对于文 学与其外部关系层面而认定的。而文学内里的各种要素和形式的“身份”之确认也不乏 所谓“合法性”之认识。其实,不论文学与其外部抑或是文学本身,在“合法性”问题 上,它们时常是掺和在一起的,可以说它们是某种学术观点、艺术趣味、审美判断和价 值取向上的分歧甚或误解而导致争论之过程。新时期文学“意识流”的论争就不外乎这 样一个过程。
文学“意识流”是《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理论要点中备受新时期文学界关注的话题之 一。那么,高行健眼中的“意识流”观是怎样的观念呢?按照作者的说法:“意识流不 是一个独立的文学流派,也算不得一种艺术创作方法,它不过是现代文学作品的一种更 新了的叙述语言。然而,它又超乎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之上,不同的文学流派、用不同 的艺术创作方法从事创作的作家,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这种语言。”[3](P26)对此 ,刘心武认为高氏的看法是“有着雄辩的说服力”[4]的。可是王先霈却认为:“意识 流手法并不是同样地适用于描写一切人物,它同任何技巧一样有它的局限性,并且它还 有着更大的局限性。因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心理活动其内容与表现形式跟西方知识分子 、资本家和总统的心理活动内容与表现形式存在着重要的差别。怎么能够像引进西方技 术设备那样简单地搬用意识流手法来观察和表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正常生活呢?”[5]究竟 谁的见解分析得在理?
其实,维系到文学“意识流”“合法性”的这个“理”见仁见智,它与新时期早些时 候所奏出的关于它的各种学术音符交互成一个众声喧哗的局面。就结合中国当代文学发 展进程中的实际问题的讨论而言,比较典型的看法是:
其一,“意识流”流出了中国的气派。1980年7月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刘心武的短 论《他在吃蜗牛》,对王蒙尝试意识流手法表示推崇。陈骏涛在1980年8月27日《文汇 报》上发表了《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一文,声称:“王蒙的探索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的,他的小说很可能将成为我国文学创作的一个流派,汇合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总的 潮流。”
其二,“意识流”流得像雾里看花。1980年第2期《鸭绿江》刊载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两 位学生就王蒙的艺术创新实践而写给他的一封信,反映他们当中有些人“看不甚懂”。 在王蒙的《关于<春之声>的通信》中,有一位文学教师也同样表达了如此的看法:“愈 看愈不懂……”[6]更有甚者,陈俊峰在1980年7月17日《北京晚报》上发表文章,郑重 其事地叹息道:“我失望了!”
其三,“意识流向何方?”于逢不满于当时文坛意识流作品正在掀起新的浪潮,令“山 药蛋”派黯然失色以及“意识流将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的说法,在《作品》1981年第 2期《意识流向何方?——致杨干华同志》中义正词严地表示:“意识流至今已离开其原 有的含义,成为一般的心理描写手法,是完全可以纳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中的;但如 果要形成一个独立的流派,并要‘将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那就得经过广大群众的检 验和时间老人的考验。”于逢的看法得到了发表于《芒种》1981年第5期洪钧的《意识 流向文学》的回应:“‘意识’将会不顾一些人的阻拦而继续‘流动’,将会照‘流’ 不误地流向文学。”
其四,“意识流”作为一种叙述手法,我国自古就有。郑伯农在发表于1981年第4期《 文学评论》上的《心理描写和意识流的引进》一文中指出:“‘意识流’热衷于表现人 的联想、梦幻等等,传统文学何尝不写这些呢?在我国,庄周写过蝴蝶梦,唐人传奇《 南柯太守传》整篇就是写一场梦……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写梦幻、写人的心理活动的,多 不胜数。”《广州文艺》1981年第5期许翼心《关于‘意识流’的对话和断想》认为: “在传统戏曲中……《林冲夜奔》不也是一出典型的意识流戏剧么?还有汤显祖的名剧 《牡丹亭》……在舞台上表现梦境,不也是意识流手法么?”“汤显祖可算得是一位意 识流剧作家了。”
其五,“中国的意识流小说有自己特殊的艺术渊源”。据说,这种渊源可以上溯至唐 代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下及清代的《聊斋志异》、《红楼梦》。于此,《武汉师 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杨江柱的《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两次崛起:从<狂人日记>到< 春之声>》,恐怕从中获致“灵感”,竟考证出语惊四座的结论:我国的意识流小说的 诞生,“与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作品并无瓜葛,因为它们当时还没有产生。”凭借这些 议论依据,有人开始提出了“东方意识流”命题。它最早见于1985年《当代文艺思潮》 第1期石天河评析王蒙作品的文章——《<蝴蝶>与“东方意识流”》。
新时期文坛中关于文学“意识流”的议论乃至“出新”可谓是五花八门。据不完全统 计,从1979年至1984年,讨论文学“意识流”的文章就不下百余篇。那么,文学“意识 流”在中国当代文苑中到底有无它“合法”的生存空间?你说它是舶来品也好,本土的 东西也罢,甚或两者兼而有之也行,通过几年持续的争辩,它在文学界愈来愈使人感到 不那么陌生,不少文化人对它愈来愈显得大度宽容。但关于它的“合法性”论争并未全 然偃旗息鼓,不妨用国内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的话来说,“近年来,在对意识流的 介绍与评论中,的确存在着一些有待研究与探讨的问题”[7]。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
三、权威话语:学者们的“狂欢”聚会
针对文学“意识流”的“合法性”在新时期文坛之众声喧哗,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 学研究所“20世纪外国文学评论丛书”编委会于1987年5月20-22日在北京举行了“外国 文学中的意识流”学术讨论会。来自国内外国文学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对国外文学中的 “意识流”现象及其诗学展开了一次较为集中的整体观照和较为深入的具体探讨。可以 说,这是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学界首次以“意识流”专题的形式进行研讨的高规格、高水 准的聚会。相对于参加这次研讨会人士的社会身份来讲,它代表着国内文学“意识流” 问题论争走向深入的“权威话语”。这个话语的开场锣鼓由柳鸣九敲响。作为长期从事 研究工作的他,其话头是:“意识流问题……是国内不少书刊把它作为一个西方现代文 学流派来加以介绍,而后,当然又曾一度被作为西方现代派文学而加以非难以至批判, 批判的论据不外是,意识流是西方资产阶级心理学、是弗洛伊德学说的产物,它是一种 反现实主义的、非理性的、反理性的文学流派,它以表现潜意识与性意识为目的,必然 带来腐朽的内容与精神污染,等等。”[7]在他看来,上述那些非难与批判并不符合实 际情况,所以有必要“把问题讲清楚”。诸如:“文学中的意识流与心理活动中的哪些 层次、哪些内容、哪些形态有关,它所表现的是哪种层次、哪种形态?它是否就一定表 现潜意识,在表现内容上它是否就一定表现性意识,是否与泛性论有必然的关系,是否 就一定会与腐朽的内容有关,是否就一定会带来某种污染?它作为一种文学描述,是否 一定反理性或非理性?”那么,诸如这些问题又得到了(包括柳鸣九本人的)怎样的学术 回应呢?择其大端,概括地说。
首先,关于文学“意识流”的品性。来自异域的文学“意识流”究竟为何物?柳鸣九的 看法是:意识流不是一个流派,而是一种方法。它之所以不是一个流派,不仅因为它既 无统一的理论纲领,又无具体的组织形式,甚至连运用了意识流的作家们之间起码的横 向联系也不存在。袁可嘉认为,关于意识流应做两个层面上的理解:一是技巧手法;二 是小说品种。他指出,意识流技巧并不是现代小说惟一的表现手段,而意识流小说则是 指主要以意识流手法来表现人物意识活动的小说样式。慈继伟从意识流与内心独白的关 系出发提出的见解颇为深刻。他主张,作为人物意识活动的一种方式的“意识流”应与 作为叙述人物意识活动的一种手段的“意识流”区别开来。在意识活动的整体中来把握 前者,而在叙述手段的系统中来研究后者。他认为意识流既是内心语言活动,同时又是 意识叙述手段。此间,内容与形式上的自由契合,不同层次的意识与其不同的叙述手段 的逻辑对应至关重要。他最后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内心独白不等于下意识、潜意识。
其次,关于文学“意识流”的特征。域外文学“意识流”到底有哪些征象非其莫属?柳 鸣九认为同传统的方法相比照,“区别首先在于它的流动性”。传统的人物心理活动的 描写是合乎逻辑或逻辑关系较强的顺“流”,已经条理化了的“流”,已经整治过了的 “流”;而意识的流动则不一定是合乎逻辑或逻辑较强的“流”,其景观有些复杂,有 回漩,有倒流,有明流,有暗流,等等。其次,区别在于它的混杂性。传统文学中的心 理活动当然也存在着各种成分,但显然不如意识流来得丰富、庞杂。就心理活动的内容 与形式而言,后者有回忆、想像、联想,有完整语句的内心话语,也有语言的片断或个 别单词等。意识流手法并没有臆造与发明,它只不过是以一种适合的方法把人脑中固有 的复杂状态再现出来而已,这就构成了意识流与传统的心理描写的第三个重要的区别。 高中甫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视角强调非理性是意识流作品的一个主要特点。
再次,关于文学“意识流”的价值。中国学者面对异域的文学“意识流”又当做出何 种公允的评价?柳鸣九认为,意识流既然表现了人类心理活动中一种客观的存在,也就 不能算是一种过错,正好是它的一个贡献。意识流方法扩大了文学的心理描写的领域, 并把对人类精神心理活动的文学表现推进到一个新的真实的水平。而袁可嘉的认识是: 对意识流小说既要看到意识流技巧的特色,又要看到它所表现的意识之弱点;既要看到 意识流文学深刻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人真实的经验:诸如与社会的游离感,个人的失落感 等等,也要看到它对非理性强调得过分,对危机感夸张的过分。真实中有歪曲。总之, 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意识流文学,尤其不能孤立地看技巧本身,忽视技巧与思想的联 系。为此,他主张,要站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场上来看待国外文学现象,对意识流文学 无论在思想上或技巧上都没有必要过高地评价,全盘地承受。
上述种种“权威话语”是否述说得到位自有公论,但在我看来,就文学“意识流”的 “合法性”问题,无论从思想还是从技术层面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学术清理,可以见出与 会专家、学者们还原文学“意识流”之“庐山真面目”所做出的缜密而又实事求是的理 性的努力。
四、历史的沉思:论争轨辙的背后
一般而言,历史事实是不会陈旧的,而人的思想则充满变数。新时期的文学“意识流 ”论争业已成为过去,较之于当下“全球化”等热点问题来说归属于“边缘话语”,但 其轨辙给中国文学健康地走向文学本身进而向世界文学之林进发的征程积蓄了一定的可 供思考的学术批评资源。着眼于中外文学关系来寻思,它们主要是:
第一,高行健的小册子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似乎使人感到有些不解的是,他的约9万来字的那本小书,令那些曾倍受压抑而渴望新 变的中年作家们相互欣喜了好一阵,后来又居然在新时期文坛被捣鼓出如何看待西方现 代派文学的大论战。当然先于它之前,《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至1982年第1期) 亦曾发起过关于西方现代派文艺问题的讨论。但其波及面明显不及前者。1982年10月至 12月底,《文艺报》和全国文联研究室几次召开座谈会,专门就西方现代派文艺和现实 主义的发展等问题进行座谈。《文艺报》1982年第12期还对座谈会内容进行了报道。无 论从声势还是从规模可以说《现代小说技巧初探》“风头”出尽。
那么具体到文学“意识流”问题上,陈焜先生早就于1980年11月25日在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对“意识流”问题进行过演讲,而后他又推出收录了 他这次演讲内容并逐一加以细化的学术专著《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年版)。作者不独注重意识流理论背景的绵密透析,而且还举证了不少相关作品 的精彩片断乃至被誉为“意识流文学皇后”的伍尔芙的艺术见解,深入浅出地上升到理 论层面进行分析。陈焜的真知灼见显然要比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对“ 意识流”的探讨来得精当、深刻。但,奇怪的是,前者的影响力着实十分的有限。这究 竟是为什么?
我想,这是不是当时社会“解冻”机遇、文艺发展环境等诸多因素错杂之使然?或许是 的。不过,就两者“文本”言说的风格来讲,高行健着力于在“意识流”等现代小说“ 技巧”上大做浅显、轻灵、联系本土实际的文章,以至更符合当时还处在“春暖乍寒” 时节一些被压抑了许久而渴望有所作为的中年作家们易于操作的口味。这为其一。其二 ,艺术贵在创新,但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你怎么创新?而理论又从何而来?倘若不去实 践,你怎么能够知晓真谛所在?高行健是学法语出身的,自有他便于直接阅览或吸纳“ 新近”外来文化的知识结构的优势,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是他敢于“拿来出手”。他 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所探究的“技巧”,有哪一个不是来自现代异域之物?这些 舶来品经过他“通俗”的诠释,尽管在总体上不怎么“精致”,甚至还存有某些绝对化 之认识,但它毕竟先行触摸到了中国当代文学长期以往的艺术实践中一些“患病”部位 之脉搏。二是大胆率先实践。专司文学理论研究的工作者通常在这点上是力不从心的弱 项。《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还在面世之前,作者于1978年和1980年就分别尝试现代小说 技法,创作了中篇小说《寒夜的星辰》和《有只鸽子叫红唇儿》。前者的叙事视点固定 在叙述者“我”(青年人)的眼光来看“他”(老革命)的角度上;而后者则采用多声部的 叙事视角。后来,他又发表了意识流中篇小说《雨、雪及其他:一篇非小说的小说》(1 982年《丑小鸭》第7期)等。这样一来,他不但有着域外“先进”的理论导引,而且也 有着本人切身的创作体验,它无形中“功夫在诗外”地营造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 洛阳纸贵”之气势。
第二,学者们的“狂欢”聚会圆满吗?
学术的聚会不外乎学者们本着解决学术之问题,推动研究对象深化的步履而来,而高 规格、高水准的学术聚会就不单单是为此目的。因为在“局外人”看来,在某种意义上 ,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往往有着社会文化发展所赋予的学术问题定音的校准权。尽管这 种权利对他们来讲或许谁也不会公然自认,但它事实上客观存在。这种权利的使用者有 可能水平不一,但它所造成的社会文化之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外国文学中的意识流”学术讨论会的举行,根据主办方的话来说,就是鉴于“国外 ‘意识流文学’现象与文学理论,它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渗透等问题,近年来国内时有 不同水平的文字评价”,所以要发起推动“如何整体宏观地审视‘意识流文学’现象, 多视角多层次地探讨‘意识流文学’的本质特征,实事求是地评价它的美学价值”方面 的探索。当时这个预期目标达到没有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12月推出的柳鸣 九主编的《意识流》论文专集,就是这次研讨会精心打造的产物。在异域文学“意识流 ”研究问题上,这是我所见到的一部学术分量较重、理论色彩较浓、文本分析较细、国 别语种较多的专题性论著。从专业角度来讲,会议的主旨应当说得到了相当淋漓尽致的 体现。但站在中外文学关系最高意义的平台上,窃以为仍有某种缺憾之感觉。
外国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不外乎通过研究,使自身文学必然王国健康地向文学 自由王国迈进。那么又怎样落实到自身?滞留在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照系的 层面上诚然是一种上乘的选择。但仅此而已吗?原苏联学者费多连科真是一语破的:“ 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表明它同其他民族的各种文学,同世界文学史的相互联系和相互 作用。这就是说,要结合具体分析中国文学的民族特征,来研究各国文学所特有的共同 规律性。”[9]从对社会文化产生效益的程度来讲,文学研究按照美的规律自觉地直接 介入一般要比间接的关涉来得大一些,特别是在一些文学热点上表现得尤为如此。事实 上,国内文学界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1988年4月7日至8日《外国文学评论》和《 文艺报》联袂策划召开的“20世纪世界文学与中国当前文学”讨论会就是一个良好的开 端。与会者分别来自中外文学两个研究领域的作家、学者。大家为一个专题汇集到一块 展开研讨至少可以开拓你我之间的文学艺术视野。研讨后的结论固然是人们所希冀的, 但更为重要的在于过程。过程多走几遍甚至有的放矢地走下去,接近共识的基础岂不就 有了夯实之可能么?!
容我不客气地说,在文学“意识流”问题上,学者们的“狂欢”聚会在一定意义上却 成了参加这次聚会者们的“学术独白”,而这种“独白”还是姗姗来迟的。因为新时期 初始头几年,“意识流”在文学界逐渐“热”得鼎沸。当时,国内外国文学界的个别“ 大腕”尽管时而也趁势蜻蜓点水地露了几招,但没有真正触及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实际, 因而未能产生像《现代小说技巧初探》那样扣住本土文学现实来“指点迷津”的“轰动 ”效应。退一步说,对问题的观察总得有一个过程嘛。然而,“过”到学者们的“狂欢 ”聚会,有谁看见了国内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学者乃至作家的出席?文学“意识流”还牵 扯到心理学、哲学等方面问题,又有谁观察到这方面学者的到场?为此,在这个层面上 ,学者们的“狂欢”聚会能说圆满吗?这不能不说是有识之士积极参与中国文学发展进 程中一次高起点的学术对话的历史遗憾。无怪乎一些文化人时常按捺不住地要发泄不满 :理论研究总是滞后于文学实践。站在20世纪中国文学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这个制高点 上,中国文学的发展不能没有相关各方共同直接参与对话的界面。这似乎是一种已逝去 了的多余的期待。不过,当下文坛诸多“涛声依旧”的事实告诉我们,它同时也是现时 的一种期待!说不定将会是一种永远的期待!
收稿日期:2003-04-10
标签:文学论文; 意识流论文; 高行健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论文; 文化论文; 现代小说论文; 文艺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