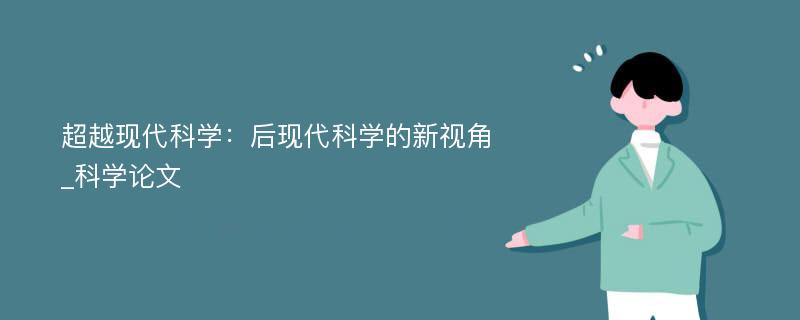
超越现代科学:后现代科学的新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后现代论文,新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4)01-0025-04
科学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性研究。科学的发展集中反映了人类对世界的态度和认识世界视野的变化。
从古希腊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类的意识形态定位在坚信大自然是魔幻、神圣并充斥着精灵和知觉上,因而,科学起初并不是在广阔而有益于健康的草原上发芽成长,而是在愚昧的草原和有害的丛林——巫术和迷信的丛林中发芽成长[1]。科学要取得进步,就必须对世界进行怯魅,从中清除掉所有把自然看作是充满生命和精灵力量的影响。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创立了怯魅的现代科学,对世界理性的科学解释从此代替神学的解释,知识不再被用来服务于上帝和支撑的信仰,而是进一步服务于人类扩充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近代以来现代科学不断开拓人类的视野,取得了瞩目成绩,但它的机械论世界观基础和还原论的认识论原则造就了“僵死的自然”,凸显了人类发展中的危机。自19世纪以来,许多理论集中批评和攻击了启蒙理性、科学的机械主义和还原主义及历史的进步观,这导致了后现代对人本主义、宏大叙事和对普遍与超验价值的寻求的攻击。在科学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理论成果引发了对后现代科学的筹划。后现代科学的现实可能性至今还有待商榷,但它在自然观、科学观、思维方式和终极意义上展示了对现代科学的超越,开辟了新视野,这对当今人类处理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科技与社会的困境和寻求科学新的发展道路有启示意义。
一、自然观的超越
“怯魅”是现代科学的依据和产生的先决条件,并几乎被一致认为是科学本身的结果和前提。从根本意义上看,这种“怯魅”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2],认为自然是僵死、无生命力的“空洞实在”,这实质上是机械主义自然观。后现代科学则展示了一种新的自然观,大卫·格里芬称之为“完整的整体”、“后现代的有机论”。
首先,后现代自然观强调世界是一个由有机体和无机体密切相互作用的网络。在整个宇宙中,整体和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都相互包含,即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为整体。整体中每一部分除与其它部分以及与整体的关系外,还存在更为重要的产生自决的、主体性的内在关系。
其次,现代科学否认自然实在中存在目的因,后现代自然观则强调不管是有机体还是无机物,除具有动力因外,还具有经验和目的因、终极因,且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事物的运动。
第三,与现代科学将不连续的物体当作首要的实在,把有机体的包容与展开当作第二位的现象相反,后现代科学将包容与展开的连续运动(即整体运动)看作是第一位的,分离的物体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第二位的。在整个宇宙中,每一个系统的较小部分只有置身与它们发挥作用的较大统一体中才清晰明了,且一事物的活动除对相邻的活动产生影响外,还对不相邻的活动产生影响,因而事物之间除了存在明晰的“因果链”之外,还存在“非局部的原因”和“非局部的效应”。
二、科学观的超越
与整体的、有机的自然观相适应,后现代科学也刷新了科学观[3]。
首先,现代科学自然观树立的客观实在性的现代观念是人类控制和统治自然兴趣的根源。这种观念把自然视作“空洞实在”和惰性物质的集合。后现代科学则寻求把世界理解为活生生的、活动的和有价值的世界的科学,而非疏离一个纯客观世界的科学。它强调,科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客观的”自然现象,还应包括意愿和意志、“深层直觉”以及超自然观现象;不仅仅包括事物的动力因,还包括目的因和终极因。在重建有关客观性的观念上,后现代科学允许科学去克服有关客观主义的神话,让其自身与其说被“傲慢自大的眼睛”所引导、还不如说被“爱之眼”所引导,从而在整体、有机的世界中消除人的独白。
其次,机械论观点的中心内容是否认自然事物有任何吸引其它事物的隐秘力量[4],这种否认自然实在中的目的因使得任何理想、规范或价值不能发生作用,更谈不上价值的实现了。与此相反,后现代科学强调科学研究的范围要扩展到“探讨时间和物质的真正本质以及宇宙是否有意义的问题”,把对科学前提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探讨和世界的意义价值问题纳入科学之中。正如格里芬等认为的,后现代科学更应该回归到自然、科学的本真状态,也就是让“怯魅”的世界和“怯魅”的科学“返魅”,此时,神性的实在、宇宙的意义和附魅的自然这样一些概念又重新为人们所接受,世界的经验、目的、自由、理想、可能性、创造性、暂时性都得到恢复,万物自身的、内在的价值得到承认和实现。宇宙是充满魅力和意图的,岩石、树木、河流和云彩都是神奇和有生命力的,所有创造都是一个巨大生灵链上的一部分。总之,宇宙是一个给人以回家感觉的归属之地。
第三,科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扩展意味着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成为科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被排除在科学之外。与科学宽泛的范围相适应,后现代科学还强调,科学理论的检验和证明不能局限于一种特殊类型,也应扩展开去容纳各种不同类型的证明。
第四,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部分,以致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是现代科学中受到精心磨练的技巧[5]。以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极其推崇从部分出发的还原论式科学解释。形象地看,还原论世界观内含一条基本的本体论前提假设,即所有原因都是侧向和向上发展,是从部分到部分或从部分到整体。这种原因可称为“向上的原因”,它导致现代科学用简单性解释复杂性,因而隐去了自然丰富性和多样性。后现代科学的整体论观点强调“向下的原因”,即从整体到部分。后现代科学还强调科学解释不是因果的解释,还包括目的论解释。这些观点无疑丰富了对自然的观念,加深了对物质的理解。
三、思维方式的超越
机器时代的传统科学对理性和普遍性推崇至极,它的思维特征是长于局部分析,缺乏整体综合。这种思维方式为人类提供了极为丰富和正确的科学知识,但根深蒂固的还原论、机械论和简单性思维倾向于强调稳定、有序、均匀和平衡,最关心封闭系统和线性关系[5]。这就让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现实世界是简单的,并一直把简单性看作是科学追求的最高目标,认为简单是真的标志。这种思维方式的后果是,科学的各部门之间出现被忽视的无人区,科学的各个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也被专门化的科学本身所割断。可以说,传统的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禁锢了人类思维力量,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事实上,世界绝大多数现象都是开放的系统,它们和周围的环境交换能量、物质和信息。因而,要真正认识现实世界,把握世界的本质必须摒弃传统的思维方式,从寻找世界万物终极之石的幻想中解脱出来,恢复人类的思维自觉性、创造性和多级性。后现代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而且它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目前科学的混乱。
以重现科学和自然的真正魅力和价值为主旨,后现代科学重建科学和重构全面的世界观,把科学看作一种在其中理论、隐喻、工具和科学时间共同组建其客体的一种建构,从而放弃科学是提供纯粹的客观真理的自然之镜的观念,并在科学中呼唤一种奠基于非决定论、非连续性、混沌、复杂性和熵的后现代转换。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系列理论(热动力学,生物进化论和生态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混沌理论和复杂理论等)促成了向后现代科学转化的筹划[8]。
后现代科学脱离绝对的确定性,拒绝有关一种固定的不可变动的秩序和绝对真理的观念,从而支持了关于演化着的复杂性和可能性的概念。后现代科学还打破了机械主义和机器隐喻,肯定了有机论和生物学模式,从而从一种自我封闭的和不可改变的宇宙观转向为一种始终存在着变化和演化的开放的、自组织的、动力学的宇宙观。这些都体现了新的思维方式,正如后现代科学的提倡者们所宣称的:现代科学的范式正让位于一种科学思考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奠基于一系列概念,诸如:熵、演化、有机主义、非决定论、可能性、相对性、互补性、诠释、混沌、复杂性和自组织[5]。
四、终极意义的超越
后现代科学的超越,不像激进的、否定的后现代主义那样,或去否定科学的真理性,将其贬低到现象的地位;或否定其价值意义;或去消融科学,模糊其与人文学科的界限,将其作为文化理解,而是致力于超越伽利略、笛卡儿、牛顿等人开创的现代科学传统,保留现代科学中的合理成分。现代科学排斥自由、价值及对终极意义的信念,引起了意义失落和价值观的混乱,带来了真理与德行、价值与事实、伦理与实际需要的二元分离,使人类的心灵饱受煎熬,精神失去了宿所。后现代科学赋予整体论和有机论以最高价值,主张把现代科学融入更宽泛的观念之中,并对现代科学世界观在社会上和精神上的毁灭性给予深刻的揭示,以克服其消极影响,正如斯坦利·克里普纳所说:后现代思想期望在保持“现代”世界观优点的同时,用那些本质上更有机的和整体的假设来替代那些机械的和还原性的假议。
首先,后现代科学提倡人们关注自己的内心体验,把主观经验和意识、无意识当作特别关注的焦点,并将深层直觉当成最终的权威。
其次,后现代科学认为人类不应只去追求冷冰冰的规律,决定和控制这些外在的东西,而更应看重人的自发性、能动性、创造性,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培育人的道德感。
再次,后现代科学主张社会不应再把人置于流水线生产技术的经济枷锁之中,而要增加人们的交往和交流,使人们通过集体强大的力量满足人们对相互间亲情和精神理解的需要,成功地处理社会和人际变化。
最后,在生态模式中世界万物都存在内在的价值和价值的实现等问题。万物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相互依赖和统一的特征;价值存在于这个完整的整体之中,而不是以人类为中心。这样,世界的形象就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这样,现代科学体现的人的异化和世界的异化就可以得到克服。
总之,后现代科学认为,科学作为认知体系或社会体系都不是价值中立的,已发现的科学真理的形式是片面的,只说明了全面真理的抽象的一面。后现代科学建立新的自然观和科学观的真正目的是要解决困扰现代科学和社会意义及价值问题。大卫·伯姆指出:“意义在此是价值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还有什么能够鼓舞人们向着具有更高价值的共同目标而共同奋斗?只停留在解决科学技术难题的层次上,或即便把它们推向一个新的领域,都是一个肤浅和狭隘的目标,很难真正吸引大多数人,它不能释放出人类最大和最广泛的创造能量,而没有这种能量的释放,人类就陷入渺小和昙花一现的境地,从短时期看,它导致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毫无意义的活动,从长远看,它正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2]
真、善、美的统一是自然和社会的自由之境,它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也是科学的永恒追求。现代科学在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指导下取得了瞩目成绩,但也严重剥离了真、善、美完整的含义。后现代科学则通过对现代科学的超越,使其统一性得到重塑。
五、后现代科学新视野对现实的启示
20世纪以来,科学除了表现了它的经济和学术价值,更大程度上表现了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日益巨大、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人们应用科学以谋求更多更大利益;另一方面,科学发展中否定性因素伴随着产生,其破坏性表现出蔓延的趋势:科学技术应用于战争和无人道的目的,其后果自不必说;在其他方面,人们对科技成果自觉和不自觉地滥用,不仅带来了有悖于人文精神的负面效应,有些甚至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与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环境污染、资源危机、生态破坏、核战争危险等现实,打破了对社会采取超然态度的“纯科学”的梦想,并向世人表明:科学所反映的客观规律的价值中立性是一回事,科学的应用及其社会后果是另外一回事;无论是单纯追求功利目的的科学研究与应用,还是强调学术价值而不顾社会后果的纯科学研究,都将使人类为此而付出沉重代价。这就要求人们用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科学观取代工具主义和理想主义科学观。虽然对后现代科学的可操作性还存在许多有待商议之处,至少后现代科学呼应了时代的需要,在观念上为人类探索科学未来和人类未来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一方面,它并非要求在自然的本性、社会的本性与占统治地位的科学世界观或所谓“范式”之间有过分的并列性,也不是把科学归结为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某种“上层建筑”,而旨在表明,科学不是一个“独立变量”,它受到其外部环境的有力影响,是嵌在社会之中的一个开放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
另一方面,它主要从自然观及其文化意义的角度去反思现代科学。它在肯定和重构现代科学的基础上,主张恢复科学的人性,消除“两种文化”(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和消除东西文明的隔阂。这些主张无疑有助于对当今现实世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的思考。当今社会正处于快速演化和不断调整的环境中,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就目前看,全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集中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则是全面落实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科技发展问题在当代尤为显得重要。后现代科学提倡开放式的科学系统正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合理方案,这将有利于我们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它展现给人类一幅美好的世界图景,也必将指引人类再次创造出自然与人和谐共存共生的现实家园。
收稿日期:2003-0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