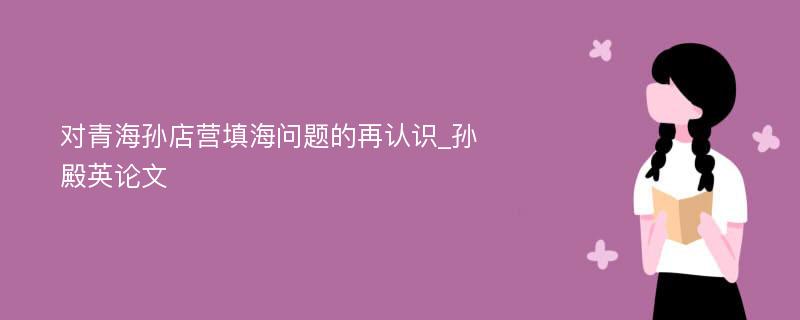
孙殿英屯垦青海问题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青海论文,孙殿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殿英屯垦青海问题指1933年6月下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并率所部四十一军屯垦青海之事。此后国民政府又放弃了屯垦青海计划,并由此引发了1934年春天振动一时的孙马大战,给宁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以往人们认为,国民政府命令孙殿英屯垦青海的主要目的是为挑起孙马大战,以便坐山观虎斗,待两败俱伤后,坐收渔人之利。笔者近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后认为,这一提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国民政府发布这一命令,除离间孙冯关系外,还迎合了当时“化兵为工”和“开发西北”的思潮,并试图以武力进入西北来试探回族军阀。由此可以说,挑起孙马大战不是国民政府的初衷。尽管我们说孙马大战不是事先预谋的结果,但却是国民政府投机性政策所致。当屯垦计划遭到西北诸马坚决反对后,国民政府为向回族军阀妥协,不仅放弃了屯垦计划,而且确立了以消灭孙殿英来讨好诸马的方针,这样孙马大战也就不可避免了。此时在孙马之间,国民政府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而不是坐山观虎斗的旁观者。从其最初的动机看,这一转变不仅没有达到武力控制西北的目的,反而进一步承认了回族军阀在西北的特权。当然,出现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政府对回族军阀重新认识后的抉择。
一、国民政府令孙殿英部屯垦青海的动因
1933年6月下旬,正当冯玉祥察绥抗日同盟军与日军展开激战之时,国民政府忽然委任身拥重兵、驻在平绥路上的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这种时候,发布如此命令,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无非是将孙部调离察绥,以便削弱冯玉祥号召抗日的势力。1933年6月26日何应钦在给汪精卫、蒋介石的电报中,明确表示了这一意向:“孙部驻在平绥路上,影响察事之解决甚巨。现其屯垦青海之名义,既经国防会议议决,既乞中央早日明令发布为祷。”(注:见《民国档案》1994年第4期,第28页。)可见,国民政府当局非常惧怕孙部与抗日同盟军合作,使华北局面复杂化,影响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总国策。在当时有这种可能,一是孙曾隶属冯部,二者有历史关系;二是冯已派人争取孙;三是孙部在长城抗战中,曾与日军遭遇,有抗日英名。故国民政府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因此才多方拉拢孙殿英,最终找到了对双方都比较合适的名义——屯垦青海。这一名义在当时来看,既符合“总理遗教”,又可赢得舆论同情。
民国以来,大小军阀蓄意养兵,人民备受其苦。正如时人所言:“无外患的时候,这些军队则从事内战,摧残生产,有外患的时候,这些军队又不能捍卫国土。全国上下,感受兵多的痛苦,已非一日。裁兵节饷,移作生产的经费,几乎是全国一致的希望。”(注:李庆磨《屯垦青海与开辟西北》,见台湾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八十八辑,第85页。)鉴于此,当时“化兵为工”、“裁兵节饷”之说非常盛行。孙中山先生也曾有过“化兵为工”、“垦发自然富源”的设想。但近代中国军阀统治的特点决定了这一主张很难实现。尽管如此,“化兵为工”之类的口号却被屡次提出,甚至成为军阀间互相争斗的借口。此次国民政府命令孙军屯垦青海,自然属老调重弹,各方也会照葫芦画瓢。西北方面就曾指出:“窃思中央命孙开垦青西,原为遵守总理遗教,实行兵工政策,凡属国人,莫不同情……”(注:见《民国档案》1994年第4期,第34-35页。)而孙殿英也心领神会,曾煞有介事地表白:“我国兵士素乏专技,一离兵籍,即成匪寇,已往事实昭昭俱在,与其裁而遗祸社会,不如留而兴利于国家,屯垦实边实为上策。”(注:见《民国档案》1994年第4期,第27页。)
此外,国民政府令孙军屯垦青海之时,正是其高唱“开发西北”之际。因此没有比这更合作的借口了。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一面对日妥协,一面提出“开发西北”长期抵抗的口号。为此曾作出以长安为陪都并定名为西京的决定。还专门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经委会西北办事处等机构,从事开发西北工作。并先后通过了“开发西北案”、“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请奖励西北垦殖以实边区而裕民生案”等多项决议。这些决定的主要依据是孙中山先生早年的建国构想及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是国民政府在尚未实现全国真正统一的前提下作出的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尽管如此,当时国内还是兴起一股强劲的“开发西北”思潮,到1933年夏,这一思潮正处方兴未艾之际。此时发布孙军屯垦青海令,正可向世人表明政府以实际行动“开发西北”的姿态,也可赢得舆论的同情。时人曾评道:“中央政府当国难方殷的时候,能考虑到西北边陲,令统兵大员率五、六万人,大规模的去开发西北的中心——青海,这确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并认为这是“中央政府试行移军殖边,寓兵于农的开端”。(注:李庆磨《屯垦青海与开辟西北》,见台湾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八十八辑,第85页。)对孙殿英来说,接受这一任命,远离察绥是非之地,既可保存实力以图向西发展,又可保住抗日英名,而且主动提出移屯边荒,确实起到了沽名钓誉之效。时人称孙“愿为国家养精蓄锐,培植实力,作为收复东北的准备”,“是孙军以身作则为军人大规模的开发西北的先锋”。(注:李庆磨《屯垦青海与开辟西北》,见台湾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八十八辑,第85页。)后来,即便在国民政府改变政策,令诸马堵截孙部之际,依然有人为孙说项,称“孙军遵命西北屯垦以固边陲,而备国家之缓急,为各将领中之难能可贵者,中央亟宜维护鼓励以转移各军之视听。”(注:见《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第9页。)可见,“开发西北”声中,孙部服从命令,移屯青海是得到舆论的同情的。
如果说,调孙部离开察绥是国民政府令孙军屯垦青海的直接目的,那么以孙军武力进入西北来试探回族军阀则是其更为深远的考虑。
事实上,30年代国民政府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依旧是民族独立和国内统一问题。因此,当时的“开发西北”口号也是围绕这两个问题而展开的。一方面为建立长期抵抗的根据地,国民政府对事关国防战略的西北交通、水利比较重视,另一方面,控制西北也是国民政府追求的政治目标之一。当时陕北、绥西皆有可垦之地,且自然条件远优于青海西区,国民政府为何令孙部舍近求远去遥远的青海屯垦?当然还有其更为深远的考虑。
如前所述,国民政府在“九·一八”后,虽策定西北为未来抗战的根据地。但反观西北的现实,情况却不尽人意。到1933年,国民政府在西北能直接控制的地方只有陕甘两省。当时的新疆,矛盾重重,加上列强的插手,致使问题更加复杂,国民政府中央除派大员宣慰而外,不能有任何作为。宁、青两省虽在中原大战后归顺了南京,但实际上却有相当的独立性。起初南京政府一直忙于消灭对其政权威胁最大的军事力量及“剿共”战事,也就容忍了宁、青两省的特殊局面。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也在寻找控制宁、青两省的机会。因此“统一军政”、“整顿土著军队”、“政治国家化”等口号一时成为“开发西北”的强音之一。因此令孙军屯垦青海,某种程度上说,是国民政府以武力进入西北试探回族军阀的一次尝试。当时的决策者认为:“孙殿英与马鸿逵早结为义兄弟,都是冯玉祥的旧部,宁青两马之间也有姻娅之谊,且四马一孙,均非中央嫡系,异地分驻,原无冲突。”(注:王剑萍《西北四马合击孙殿英的回忆》,见《宁夏三马》,第169页。)有孙殿英驻防西北,对诸马无异是一个牵制。当然这种一厢情愿的真实意图并未能瞒过诸马。孙马大战前,马鸿逵曾致信孙殿英称:“溯兄自班师移防绥西,弟已认为失机,曾以平心静气处之一言为进,嗣虽奉督办青西屯垦令,而事实里面情形本不简单,中央意旨所在,弦外另有余音。”(注:见马鸿逵《十年来省政述要》,第七分册。)此处的“弦外音”自然是指国民政府的一箭双雕之策,说明诸马早已洞悉了国民政府的真实用意。而对孙军屯垦的诚意,西北方面更是怀疑了,所谓“孙殿英在三、五年前,固系出冯玉祥部属,而全国非认为土匪式军队,既认为毫无纪律之杂牌军队,更何能推行开发西北之伟大政策,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之。不过假借屯垦之名,以攫取青海地盘,以造成西北唯一势力。”(注:见《民国档案》1994年第4期,第34页。)
尽管如此,国民政府依旧坚持原定计划不变,从1933年夏发布屯垦令到同年11月放弃屯垦计划,近半年时间里,国民政府为达目的,曾努力坚持西进计划,直到诸马以辞职要挟后才放弃。尽管屯垦消息刚一传出,即遭诸马反对,但南京方面仍旧百般辩解,不为所动。如马麟曾在7月5日的电文中例举了三项拒孙理由,诸如青海无可垦之地、蒙藏民族反对等,为此行政院长汪精卫回电称:“中央对于青省情况向极关切,无时不谋增进青省力量,以期开发,同臻福利,顷绎电中所陈三端,具见青省群众望治之热忱,思危之尽虑,惟中央此次遴任屯垦督办,也曾经深慎考量,良以青省蔚为边藩,亟宜多得各方之助,且可捍国圉边,导吾边陲同胞于生产增进之域。”(注:见《民国档案》1994年第4期,第30页。)后为回敬所谓“青省荒寒、实难供给”的问题,汪精卫在致朱绍良、邓宝珊的电文中称:“孙殿英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之命,系与蒋委员长、何部长再三裕酌,复经国防会议同人详细讨论,始行决定,各方面利害感情都已顾虑及之,回部猜畏既为顾虑之最大者,惟青海地旷人稀,而孙部给养每月仍有中央拔给,不致贻累地方,但能严整纪律,不扰民间,当能相安无事。中国各处地狭人稠,惟西北广漠有待开发,移民屯垦,事势当然,未可豫存逆臆而深闭围拒也,当祈两兄就近设法劝谕解释,消其疑虑。”(注:见《民国档案》1994年第4期,第32页。)8月份,蒋介石甚至亲自打电报给马麟、马步芳称:“中央派孙殿英率部赴青垦殖,系为青海谋福利,所有给养,完全由中央协助,决不增加青民负担,更无碍于青省军政,请转达青海各族领袖,勿予反对”。(注:见清海省图书馆馆藏资料《宁夏战争》。)直到11月命令孙部暂住原地,再待后命至,国民政府基本没有动摇令孙部西进之决心。说明国民政府在初期是坚决支持孙部西进的。
二、国民政府放弃屯垦青海计划的原因
1993年11月11日,蒋介石电令孙部暂住原地,再待后命,标志国民政府放弃了屯垦青海计划。该命令称:“查四十一军孙殿英前令其屯垦青海西区,虽已行抵宁边,但距屯区尚远,现时隆冬即届,边荒辽旷,冰雪载途,给养困难,大军远行诸多不便,应即停止西进,暂住原地,再待后命。”(注:见《民国档案》1994年第4期,第40页。)这一命令,表面上看,是体谅孙军困境而做出的考虑,实际上,这是国民政府迫于回族军阀的坚决反对而做出的妥协之举。正如何应钦所言:“中央屯垦青西之令甫下,甘宁青呼吁之声群起,盖惧该军移防所至地方将无法供应也。中央俯顺民情,明令暂在原地整理。”(注:见《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第10页。)当然所谓“俯顺民情”之类不过是盗用民意而已,真正的原因是孙部屯青问题在西北引起的强烈反响,特别是宁青两省当局的辞职要挟,最终迫使国民政府放弃了屯垦计划。当国民政府的任命消息传出后,立刻在西北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屯垦区的青海和假道之地的宁夏联合反对,国民政府在甘宁青的代理人朱绍良也不支持。从上到下,各种反对电文雪片似的飞往南京。与此同时,宁青两省各界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拒孙大会,邀请记者,发布通电,派代表到南京请愿等,以各种形式要求国民政府收回成命。另一方面,宁青两省厉兵秣马,准备以武力拒孙,朱绍良也下达了三省禁止孙军办兵站的命令。尤其到10月份,马鸿逵亲率省府全体委员以总辞职的方式进行要挟,而青海主席马麟也表示了辞职之意。此时,国民政府意识到,若仍坚持原定计划,则西北将会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
此外,国民政府没有料到平时矛盾重重,兄弟、叔侄间明争暗斗的回族军阀,在保护家族利益方面会下如此之大的决心,拒敌于家门外。这种为保护地盘而表现出的空前团结精神,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重新认识回族军阀在西北的特殊性,并进而确立了在西北依重回族军阀的政策。在此情况下,只能放弃屯垦青海计划。而放弃这一计划,即意味着抛弃了孙殿英。
此时,在孙马之间,比较而言,国民政府觉得孙殿英成了更直接的军事对抗势力。在孙军屯垦青海问题上,蒋介石自知理亏,因此为取得诸马的信赖,国民政府重新确立了以消灭孙殿英来讨好诸马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执行即从令孙部“暂住原地,再待后命”开始。因这一命令事实上是将孙军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此时的孙殿英部,若逗留晋绥,不为晋方欢迎,晋方宁肯发清协款,欢送其出境,忍痛送卧榻之客。另一方面,11月份的绥西,天气寒冷,难以过冬。这里人烟稀少,兵粮马秣均极匮乏,势非西行不可,否则五六万大军将无法生存。孙殿英曾称数万官兵“困处荒野,进退维艰,衣食缺乏,饥寒叫号……”(注:见《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第8页。)可谓孙军困境的真实写照。在此情况下,孙只能抱侥幸心理挺而走险以求生路。1934年1月10日,走投无路的孙殿英下达出动命令,孙部开始过磴口,向宁夏进发,并与马部发生冲突,孙马大战正式爆发。当然,孙殿英的强制西行和孙马大战的爆发还有其它方面的因素,但国民政府在孙军屯垦青海问题上的投机性政策是主要原因,也就是说由于国民政府重新确立了新方针的结果,即由原来利用孙殿英转变为利用回族军阀的新方针。因此,一纸“暂住原地”令后,不仅不替孙部着想,而且公开指示诸马消灭孙殿英。1934年1月14日,蒋介石致电马鸿逵称:“孙魁元部已明令暂住原地候命,如擅行冒进,除另电制止外,希秉承朱主任之命令,尽力防堵,勿稍瞻顾为要。”同时,朱绍良也电诸马曰:“孙部抗命西进,侵占磴口,勾结匪共,扰乱地方,自应作正当防御,予以痛击。”(注:见马鸿逵《十年来省政述要》,第七分册。)这两份电报就是人们再三提起的蒋介石明令孙部西进的同时,又密令马部堵击以挑起孙马大战的主要证据。事实上,如前所述,国民政府起初另有打算,并不想挑起战争。不管怎么说,这两份电报对孙殿英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它无疑成了国民政府令诸马消灭孙殿英的动员令。此后不论是国民政府还是西北地方当局,在各种通电中,态度明显强硬,措辞更加激烈,而且开始罗织孙的罪名,主要有三条。
一是擅自扩编,滥收匪众罪。1934年1月24日,朱绍良等在致各方通电中称:“曩者孙殿英部奉命屯垦青西,国家部队随处可调,绍良等既不容置喙其间,即亦无所用其迎拒,徒以该军广事扩充,逾编制定额不止倍,杨小猴等以厉扰甘宁之匪亦为收容……”(注:见《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第11页。)公开指责孙部罪责。不仅一直反对孙部西进的朱绍良等如此指责,就连积极促成孙部西进的何应钦此时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称:“查该军编制经本会核准有案者仅步兵一师计辖七团,乃迭据报告,该军招收溃军、土匪,积极扩充实力,现已自行编为步兵四师另一旅,骑兵三师另三旅,合计步骑兵约在四十一团以上,以一人之饷供七人之食,其饥饿窘迫自在意中。”(注:见《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第9页。)
二是封官许愿,图据西北罪。1934年1月19日,马鸿宾等在致各方通电中称:“据俘虏该部团长李殿宝等供称:孙魁元以闽变发生为之响应,乘此机会扰乱西北,已委于世民为青海主义,刘月亭为宁夏主席,甘肃自兼。为达目的,故令率部来攻等语,并下有攻甘命令已被查获,证据确凿。”(注:见《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第7页。)第二天,孙部席恩博等也发布了内容大致相同的通电,以证明孙殿英乘闽变之机,遥相呼应,阴谋图据西北的罪行。
三是勾结共匪,赤化西北罪。在1月24日通电中,朱绍良还罗列了孙部的勾结共匪罪,“……殊该军竟进逼不已,且所至封闭党部,扣押官吏,释放罪犯,掠劫人民,反动标语遁于城乡,韩麟符、宣侠父等素为共党重要分子,随军主持毫无避讳。”(注:见《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第15-16页。)除勾结共匪罪外,马麟等进一步指责孙部有赤化西北的企图,“又复收揽著名共党宣侠父、韩麟符等,宣传共党主义,是不啻移阶级斗争之祸重演于西北,其欲打通国际路线,联接赣鄂共匪之逆谋昭然若揭……”(注:见《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第13页。)这三点,条条罪大恶极。因此,国民政府在1月31日第一四五次会议上决定撤消屯垦督办公署及免去孙殿英屯垦督办之职也就成为预料中的事了。(注:见《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第13页。)而这样的决定更将孙置于“叛逆”的地位,至此孙西进已失去了最后招牌。此后国民政府不仅积极支持诸马抗孙,而且公开派飞机助战,并在舆论上对孙大加鞑伐,危言耸听的宣称:“此次孙逆之叛变实非偶然之事,盖承察哈尔及福建叛变之余绪,杂以赤色国际赤化吾国西北之阴谋者,吾人今能迅速剪除此叛逆,勿使坐大难图,则西北问题即可暂告一段落。”(注:《孙殿英叛变之严重性》,见上海《社会新闻》1934年六卷七期。)
我们说,孙殿英任意扩编,滥收匪众,封官许愿,阴谋图据西北,部队中有共产党员活动等都是事实。作为军阀,任意扩编,滥收匪众是其通病,并非始自孙殿英。就孙本人看,这一特点终其一生。至于封官许愿也是可以理解的,本来,为全军寻找出路就是此次孙部愿离开察绥的原因之一。至于“赤化西北”,“打通国际”之类不过耸人视听罢了。虽然孙在困难时找过中共地下党,(注:张述孔《流氓军阀孙殿英》,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115页。)部队中也有共产党活动,但人们都很清楚,孙是著名的“东陵大盗”,朝三暮四的军阀,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一切言行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取舍标准的,哪里谈得上“赤化西北”之类的壮举。总之,以上所列孙之罪行,一直存在于孙军中,而各方大加指责却是在1934年1月之后,即国民政府公开支持诸马后,自然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纵观全文,我们可以说,国民政府在孙殿英屯垦青海问题上的出尔反尔,执行了投机性很强的方针。调孙部离开察绥是为离间孙冯关系,令其屯垦青海是为控制回族军阀,同时又迎合了当时“化兵为工”和“开发西北”思潮。但当屯垦计划遭诸马坚决反对后,国民政府又改变初衷,放弃屯垦青海计划而向回族军阀妥协,并确定了以消灭孙部来讨好回族军阀的政策。这是国民政府对回族军阀重新认识后的抉择,即初步放弃了武力控制回族军阀的企图,进而确立了利用回族军阀为其统治服务的方针。这一政策的最终确立是在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前后。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有专论,此不赘述。(注:参见拙作《红军长征对西北国统区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标签:孙殿英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民国档案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民国论文; 朱绍良论文; 孙军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