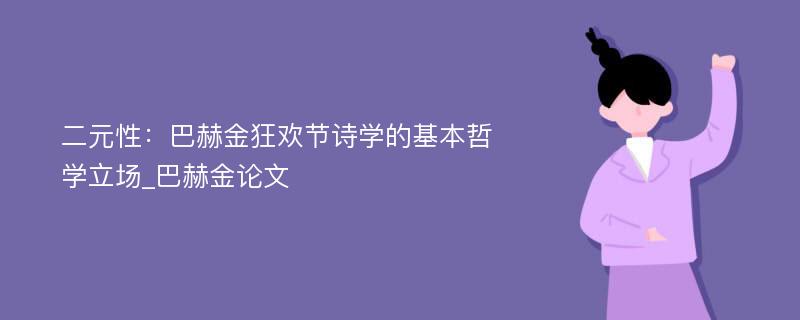
双重性——巴赫金狂欢诗学的基本哲学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双重性论文,诗学论文,立场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巴赫金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提出并阐述了许多重要的诗学和哲学命题,在艰苦环境中为现代学术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鲍恰罗夫所言:“在半个多世纪间米·巴赫金深入研究自己的一系列充满内在艰辛的诗学和哲学问题。在不同时期这些完整连贯的系列问题的不同方面充分激起了他的兴趣。”[1]其间狂欢问题则始终处于他的学术兴趣的中心。而他在关于狂欢文化和狂欢化文学问题的研究中,不断地提出和张扬着双重性(амбивалентностъ)(注:双重性,原文为амбивалентностъ,在巴赫金论著中频繁出现,但中文版《巴赫金全集》由众多译者译出,因而有“双重性”、“两重性”等不同译法。笔者以为,“双重性”较好地表达了成双成对之意,固本文采《拉伯雷研究》中李兆林、夏忠宪诸先生译法。)的思想和原则。在他的狂欢诗学里,双重性一直是一种基本的哲学立场,是他观照事物的基本尺度,价值判断的基本标准。
双重性范畴的正式提出,最早是在其诗学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在论及陀氏作品体裁的狂欢化特色时,巴赫金提出并阐述了双重性思想。在巴赫金看来,双重性首先是同一事物相反两极属性的对照共生。任何事物,在巴赫金眼里都不是单面的,纯粹的。生与死,新与旧,枯与荣,尊与卑,种种相反两极的属性往往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互相依存。在某一属性的表面之下潜在地包含着另一种属性。例如欧洲中世纪狂欢节的加冕和脱冕仪式。“加冕和脱冕,是合二而一的双重仪式,表现出更新交替的不可避免,同时也表现出新旧交替的创造意义。……加冕本身便蕴含着后来脱冕的意思。加冕从一开始就有两重性。……在加冕仪式中,礼仪本身的各方面也好,递给受冕者的权力象征物也好,受冕者加身的服饰也好,都带上了两重性,获得了令人发笑的相对性,几乎成了一些道具(但这是仪式用的道具)。他们的象征意义变成了双重的意义。……狂欢式里所有的象征物无不如此,他们总是在自身中孕育否定的(死亡的)前景,或者相反,诞生孕育着死亡,死亡孕育着新的诞生。”[2]显而易见,这里的双重性,意指事物的两个极端、两种倾向、两重意义、两个方面、两层内蕴,如此等等。在有关狂欢节的各种仪式和各种形象的象征意义的论述中,巴赫金深刻地阐明了这种思想。
巴赫金认为,“狂欢式所有的形象都是合二而一的,他们的身上结合了嬗变和危机两个极端:诞生与死亡(妊娠死亡的形象),祝福与诅咒(狂欢节上祝福性的诅咒语,其中同时含有对死亡和新生的祝愿),夸奖与责骂,青年与老年,上与下,当面与背后,愚蠢与聪明。对于狂欢式的思维来说,非常典型的是成对的形象,或是相互对立(高与低,粗与细等等),或是相似相近(同貌与孪生)。”[2]例如狂欢节上的火焰,是毁灭世界同时又是更新世界之火;狂欢节的笑声,既是死亡与再生的结合,又是否定(讥笑)与肯定(欢笑)的结合。相反的两极属性就如此奇妙地结合于事物中,构成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这种两极属性的对照共生是狂欢节形象的共同特点,也是人类亘古以来源远流长的生存状态。正是这种狂欢节形象的双重性,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西方作家的艺术思维,使他们在描绘事物、刻画形象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赋予其双重意义。作为狂欢化文学的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大多具有双重人格,其渊源正在于此。“那重要的主人公都在临近死亡(指遭到否定),目的是为了获得新生(指变得纯洁而超越自己)。”[2]这些人物身上无不打上深刻的双重性烙印。
此外,双重性也指不同事物的相反意义,或具有不同属性事物之间的正反对照。事物的特点往往是在对照中凸显出来的,事物的存在意义也往往在对照中来体现。按照巴赫金的思想,双重性也就是事物双方在相互观照、相互映衬中凸显出来的双重意义。例如老年——少年,夸赞——责骂,正面——背面,悲剧——喜剧,等等。“这一点可以表述如下:两个对立面走到一起,互相反映在对方眼里,互相熟悉,互相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按照此原则来构筑其狂欢化作品结构和表现其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在他那个世界里,一切都与自己的对立面毗邻而居。爱情与仇恨毗邻,爱情了解也理解仇恨;仇恨也与爱情毗邻,仇恨同样理解爱情(如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对德米物里·卡拉马佐夫的爱,伊万对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的爱,还有德米特里对格鲁申卡的爱,在某种程度上也属此类)。对神明的信仰与无神论毗邻,在无神论中反映出自己,并且理解无神论;无神论同样与信仰毗邻并理解它。上升和高尚与堕落和卑鄙毗邻(如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我毁灭的渴望毗邻(基里洛夫)。纯洁和贞节可以理解罪过和淫欲(阿廖沙·卡拉马佐夫)。”[2]相反事物的毗邻而居,一方面在对照中突出了双方的特色,另一方面彰显了自身的存在意义。这种毗邻和对照又体现了巴赫金双重性思想的又一层内蕴。
双重性既是巴赫金对欧洲狂欢文化的感性体验中把握到的文化精神,是他对狂欢文化的深层内蕴的追问结果,同时也是他的狂欢诗学理论的话语基石。换言之,巴赫金对狂欢诗学理论的阐述是建立在双重性思想的基础之上的,他对狂欢文化内蕴和特征的分析和发掘是遵循双重性这一基本原则进行的。他在总结狂欢文化和狂欢化文学的精神,分析狂欢节的种种现象和狂欢化文学体裁与人物时,总是从双重性的立场出发,从而使这种分析贯穿着双重性的思想和原则。由此,双重性在他的诗学里便具有了哲学方法论的意义。
在《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巴赫金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他的狂欢诗学理论。双重性思想在这里成为他打开中世纪狂欢文化大门进而了解其深层奥秘的一把钥匙,成为他对拉伯雷创作及其文化渊源进行把握的基本尺度。他对狂欢节的非官方色彩的分析,对狂欢节的世界感受的体验,对狂欢形象的物质、肉体性的研究,以及对狂欢文化的怪诞、诙谐特征的把握,无不置于双重性思想的观照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巴赫金首先明确强调了双重性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对立统一、矛盾统一思想的区别。他说:“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灭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这样可以说已经表达出了狂欢式的基本思想。但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这个思想在这里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体现在具体感性的仪式之中的生动的世界感受。”[2]双重性的世界是生动的感性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两极,死亡与新生,粗俗与神圣,卑下与崇高,精明与愚顿,都是新鲜活泼的感性实在。它不是严肃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体现出幽默风趣,生动可感。正如巴赫金所强调,它“不是关于平等与自由的抽象观念,不是关于普遍联系和矛盾统一等的抽象观念。相反,这是具体感性的‘思想’,是以生活形式加以体验的,表现为游艺仪式的‘思想’。”[2]加拿大学者A·萨杰茨基在论及巴赫金这一思想时也精辟地指出:“这古老的双重性不是僵死的遗迹,它是活生生的,在所有狂欢参加者那里都可以找到其主观回响。”[3]正是这种思想千百年来流行于欧洲的广大平民大众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文学艺术作品里,成为文艺狂欢化的渊源。
如果说,黑格尔哲学中的对立统一思想是对宇宙规律的先验的概括,是一种预设的抽象的观念形态,那么巴赫金的双重性思想则是对欧洲历史文化的存在方式追问的结果,是对西方实存的鲜活的文化形态的具体体验和把握。这种把握既不采取抽象哲理的方式,亦不使用宗教教条的方式,而是通过对文化和文学艺术的鲜活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形象的分析来实现。“整体上,黑格尔哲学人类学的思想范围正是‘纯粹理性’的深层理念所典型地给定的,这种纯理性假设了绝对观察者的原则,即非个人的、源自直接载体而无限独立的认识能力的存在,其创作是欧洲理性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而“巴赫金的人类学世界观则关联于另一个传统,它采用以理解世界的自然的、科学的方法为范例的合理的古典形式,建立在以20世纪人文意识研究问题的基础之上。”[4]因此,如果说黑格尔哲学的终极点是存在之上的价值的绝对精神实体,那么在巴赫金哲学中这一地位则是存在本身,他关注的是人类生活的事件,人的生存状况。如果说,黑格尔对立统一观念中的双方关系是矛盾和斗争,那么巴赫金双重性的两极则是对照和映衬。他们相互依存,互为表里,并且和睦相处。他们虽是事物的相反属性,甚至是具有相反属性的两种事物,却能够相互理解,互相接近,和平共处。再进一步,与对立统一观的鲜明区别还在于,双重性思想的两极没有主要和次要之分,也没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差别,他们不但和睦相处,而且地位平等,在两极相融和对照中,他们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生与死、上与下、爱与恨、高雅与粗俗、肯定与否定,在这时互相交融,互相对照反映,不分主次彼此,共同表现出狂欢文化的交替和更新精神,表达出狂欢节的世界感受!
其次,巴赫金在官方与非官方两极世界的对照中凸显中世纪狂欢文化的特色,即狂欢文化的民间性、非官方色彩。官方与非官方在其诗学话语中构成平行的双重世界。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指出,“对巴赫金来说,人处于一个社会历史体系之中,这一体系有‘最高的’(官方文化)和‘最低的’(民间文化)两层,每一层次各有其现象:上层,表现出一种以专横为特征的严肃性,一种以禁止和限制为手段的暴力。下层,则是带有民间真理和自由思想为特征的笑谑。”[4]巴赫金正是在两极对照中突出了狂欢文化的进步意义。狂欢文化作为民间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与官方文化相对的第二重世界。“狂欢节,这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5]它与教会官方文化构成了双重世界的关系,两者是相反的两极世界。官方文化与官方节日强调的是对现有世界秩序的维护,倾向于“将现有制度神圣化、合法化、固定化,”“官方节日有时甚至违背节日的观念,肯定整个现有的世界秩序,即现有的等级、宗教、政治和道德价值、规范、禁令的固定性、不变性和永恒性。节日成了现成的、获胜的、占统治地位的真理的庆功式,这种真理是以永恒的、不变的和无可争议的真理姿态出现的。”[5]而这种官方文化在狂欢节里则是被非官方的民间文化及其观念所颠覆。“决定着普通的即非狂欢生活的规矩和秩序的那些法令、禁令和限制,在狂欢节一段时间里被取消了。首先取消的就是等级制,以及与它有关的各种形态的畏惧、恭敬、仰慕、礼貌等等,亦即由于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等(包括年龄差异)所造成的一切现象。”[2]狂欢节超越官方的思想和道德理念,突破正常的社会规范和生活制度。它体现的是对官方文化的解构和对官方真理的否定。
再次,巴赫金在否定与肯定、死亡与新生的双重性中来体验“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所谓“狂欢节的世界感受”,实指狂欢节中人的生存体验,人在狂欢状态下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是对旧生活的否定同时也是对新生活的肯定,是对旧世界死亡的送别同时也是对新世界诞生的欢呼,也是对中世纪宗教道德的颠覆。由是,相反甚至对立的两种体验共生于人心,人心的双重体验构成了存在的双重性。“对于世界的神话感知具有独特的非道德主义,在那里善与恶处于某种共生状态,相互补充和制约。恶也是双重性的,因它代表的不仅仅是破坏,还有必须的宇宙要素。”[6]在日常生活,尤其是在官方的节日中,人们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等级、门第、财产、职位等成为人与人交流的屏障,官方节日甚至通过官服、官阶等标志来强化这种等级划分。而在狂欢节里,这种等级樊篱被打破,国王与小丑可在同一广场自由交往。“在中世纪封建制度等级森严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阶层、行会隔阂的背景下,人们之间这种不拘形迹的自由接触,给人以格外强烈的感觉,它成为整个狂欢节世界感受的本质部分。”[5]这时的人卸下了制度、秩序、等级的伪饰,回复人的本真状态。等级樊篱的坍塌,双重体验的共生,使人与人隔阂消失,自由平等的感觉充溢于人的心灵。“在节日游戏中重建了亘古以来存在的个体和整体的同一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同一性状态。节日性作为完整统一的世界观得以确立,这种世界感受在节日行为中得以表达和实现。”[7]这时候,人们自由交往,畅所欲言,进入一种不分彼此,完全平等的生存状态,从而构建了一种和日常生活及官方节日迥别的存在方式。与此相应,狂欢节显示的是世界的更新与交替、死亡与再生的节律:通过对非狂欢节生活的戏仿对其否定,同时在这种否定中又包含了对再生和更新的肯定。
在狂欢文化的渊源上诞生了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巴赫金对这种怪诞现实主义的分析同样渗透双重性思想。
巴赫金认为,拉伯雷作品中的形象都是物质——肉体现象,即与现实生活及非狂欢化作品中崇高的、精神层面的形象相对的一种狂欢化形象,其特点就是追求世俗的享乐和感官的、生理欲望的满足,以及欢快畅达的情感体验。如果说反映教会和官方思想的形象总是力图上升天庭、趋向崇高精神,那么怪诞现实主义的形象则总是贴近人间大地、贴近物质和肉体,表现出十分明确的世俗化趋势。“怪诞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是降格,即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5]由此,巴赫金便在精神与物质——肉体的双重对照中来把握拉伯雷作品的艺术形象的本质。在阐述拉伯雷将一切崇高的精神的东西降格、贬低使之世俗化和肉体化所具有的意义时,他说:“对崇高的东西的降格和贬谪,在怪诞现实主义中绝不只具有形式上的、相对的性质。‘上’和‘下’在这里具有绝对的地形学意义。……贬低化,在这里就意味着世俗化,就是靠拢作为吸纳因素而同时又是生育因素的大地:贬低化同时既是埋葬,又是播种,置于死地,就是为了更好更多地重新生育。贬低化更意味着靠拢人体下身的生活,靠拢肚子和生殖器官的生活,因而,也就是靠拢诸如交媾、受胎、怀孕、分娩、消化、排泄这类行为。贬低化为新的诞生掘开肉体的坟墓。因此它不仅具有毁灭、否定的意义,而且也具有肯定的、再生的意义:它是双重性的,它同时既肯定又否定。”[5]
这段文字表达了拉伯雷作品中的狂欢化艺术手法和艺术形象的精义,也典型地体现了巴赫金诗学话语的双重性思想。在这里,有上和下的双重性,吸纳与生育的双重性,埋葬与播种的双重性,以及毁灭与再生、否定与肯定的双重性,等等。显而易见,巴赫金就是站在双重性的立场上来审视狂欢文化和狂欢化文学的。双重性,是他用以观照狂欢文学中对崇高、严肃的精神形象加以世俗化的三棱镜,也是他对狂欢文化和文学的其他诸多因素加以把握和分析的基本尺度。在这里,“尤其应该强调怪诞现实主义的这一特征,作为形象的‘降格’(снижение)与‘贴近大地’(приэемление),作为粗鄙与崇高的对立,最后还有怪诞形象的流变特征及其多变性、双重性。”[4]他在论及狂欢文化和文学的笑、诙谐、怪诞形象、广场语言、讽刺、加冕与脱冕等问题或范畴的时候,总是从双重性这一基本立场出发来理解和阐释这些问题。从中我们随处可见官方——非官方,精神——物质——肉体,崇高、严肃——怪诞、诙谐,上身——下身,死亡——诞生,反面——正面,加冕——脱冕等等众多的两极存在,双重因素的同时共存,双重意义的正反对照。以他对笑文化的分析为例:“这种笑是双重性的:它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是否定又是肯定,既埋葬又再生。这就是狂欢式的笑。”[5]“笑谑仿佛记录这交替的事实,记录旧物死亡与新物诞生的事实。所以,节庆之笑一方面是嘲讽、戏骂、羞辱(将逝的死亡、冬天、旧岁),另一方面同时又是欣喜、欢呼、迎接(复苏、春天、新绿、新岁)。这不是单纯的嘲笑,对旧的否定与对新、对美的肯定紧密交融。”[8]又如他对狂欢化文学中怪诞形象的分析:“怪诞形象所表现的是在死亡和诞生、成长与形成阶段,处于变化、尚未完成的变形状态的现象特征。对时间、对形成的态度是怪诞形象必然的、确定的(起决定作用的)特征。它的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必然特征是双重性:怪诞形象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体现(或显示)变化的两极即旧与新、垂死与新生,变形的始与末。”[5]“真正的怪诞风格完全不是静止的:它恰恰力求在自己的形象中囊括的正是存在的形成、生长和永恒的未完成性、非现成性;因此它在自己的形象中表现着形成过程的两极——同时表现着消逝和新兴、垂死和诞生;它在一个身上表现两个身体,即新的生命细胞的繁殖和分裂。”[5]而狂欢节的广场语言则是一种不拘形迹的骂人脏话。“这些骂人脏话具有双重性:既有贬低和扼杀之意,又是再生和更新之意。正是这些具有双重性的脏话决定了狂欢节广场交往中骂人话这一言语体裁的性质。”[5]
这样,巴赫金以他的双重性思想全面而深入地考察了狂欢文化的诸要素,确立起他独特的狂欢诗学话语体系。双重性在他对狂欢节和狂欢化文学的研究中便具有了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如前所述,双重性在巴赫金那里既是事物属性的相反两极,又是具有不同属性的事物的两相对照。事实上,在巴赫金看来,双重性就是事物的存在方式,是一种狂欢化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存状态。在狂欢节话语模式下,生与死、新与旧、上与下、精神与肉体、崇高与诙谐、官方与民间等诸要素奇妙地融为一体,仿佛纸牌上人头像的上下两端,相伴相生,既互相否定又互相肯定,既互相区别又互相映衬,是为宇宙万物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存在方式。其实,何止狂欢节,现实中一切事物的存在何尝不是如此。一位俄罗斯学者在谈到狂欢节世界感受的当代意义时说:“在工业化的乌托邦主义时代,文艺复兴狂欢性的现实化决非个别现象,这就是两种因素的合二为一,即双重性——外部和内部、假象和真理、肉体和精神的对照共存。”[9]双重性思想就是对这一事物存在方式的哲学把握。他渊源于巴赫金对狂欢文化的诗学观照,却具有宇宙观的普遍意义。
由此可见,双重性是巴赫金狂欢诗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是他的诗学话语的基础范畴。巴赫金在对狂欢文化和狂欢化文学的分析中形成了双重性思想,同时这双重性思想又成为他剖析文化现象和文学精神、体裁、形象等要素的有力武器。他正是用双重性这把双刃剑开拓了文艺研究的新领域,开创了艺术思维的新途径,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诗学话语体系。双重性是他对狂欢文化和艺术作诗学观照的基本标准,是他诗学判断的基本尺度,是他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话语模式,一句话,双重性是巴赫金狂欢诗学的基本哲学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