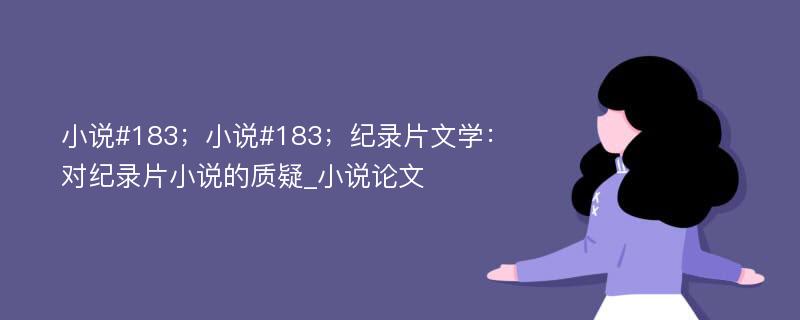
小说#183;虚构#183;纪实文学——“纪实小说”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纪实文学论文,纪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报告小说”、“纪实小说”相继行时,一度引起关注和讨论,有些论者还将原本作为实录文学或一般小说发表的作品追认为“纪实小说”,以扩充阵容,壮大声势,俨然构成文学门类的一个“新种”。其后又有“非虚构小说”,名目更奇,却没引起大的反响。
“名者实之宾也”,给一篇叙事作品安一个什么文体名目,与其本身的价值毫无关系,似无关紧要。但它关乎读者的接受心理,从而影响作品的艺术效果;如果那名目不是编者所加、评者所赠,而是作者事先拟定,则要影响创作心态,影响写什么和怎么写,从而关乎作品的内容、样态和艺术价值。笔者对“纪实小说”一类名目向有疑惑,难于认同,现就涉猎的相关作品略述管见,呈教于大方之家。
一、勿谓纪实为小说
对当今“小说”文体,虽有不同的理解、表述,但无不承认其共有的某种虚构性。全无虚构成份,也就不成其为小说,而属与小说对应的各种纪实文学。因此,将完全不事虚构的纯纪实之作称为“小说”,不仅给人以张冠李戴之感,也会降低它在读者心目中最受重视的真实性。数月前读到《中国作家》今年第一期发表的刘心武的“长篇非虚构小说”《树与林同在》,觉得内容确很真实、亲切、自然,不见任何艺术虚构的刀痕斧迹,大量综合性叙述与分析自不必说,对主人公和某些场景的描述也朴实无华,没有小说家的雕琢之笔,虽在“阅尽人间春色”题下对任众攀登山崖的思绪刻镂较细,但那是“笔者与任众交谈的共鸣中,一起升华出来的”,并非向壁虚构,未出纪实文学允许的范畴。这与作者另一些题作“纪实小说”的作品明显地加入虚构人事很不一样。但它何以也被称作“小说”呢?我于是想到主人公的名字或为虚拟,如王蒙的系列小说《在伊犁》那样。但我错了。日前在书店徜徉,见到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树与林同在》单行本,内有多幅主人公任众的照片,是以说明它是一部以真名写真事的地道纪实文学,是一部罕见的为普通人立传之作,具独特价值和开创性决非小说的衡器所能称量。冠以“小说”名目,非但名不符实,还会产生误导,对读者理解作品并无益处。
前苏联斯·阿列克茜叶维契的《战争中没有女性》和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都是作为纪实文学发表、出版的。三位作者长年奔波,四处采访,为数以百计或数百计的采访对象录音,并作笔记,两部作品就是那些口述实录的剪辑、整理和艺术加工,其间倾注了作者的心血和激情,却不掺入任何虚构,张、桑和期刊编者们恰当地名之为“口述实录文学”——纪实文学之一种。有些论著却将这两部作品追认为“纪实小说”,与那些用假名写真事或用真名写假事或既用假名也写了假事的具有明显虚构性的小说归在一类,相提并论。如此忽视文学品类之间有无虚构的重要界限,混淆纪实文学与小说的主要分别,不仅导致文学分类的混乱,也无助于对作品价值的理解与评判。
对于全无虚构的《北京人》等,为什么不像作者和编者那样实实在在地称之为“口述实录文学”或“纪实文学”,而定要另给它安上一个主词为“小说”的令人“颇感陌生”和费解的名号呢?我总希望论者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让人明白此等“实录”到底有什么小说品格。但论者好像觉得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无须浪费笔墨,反倒大讲其突出“纪实”、如何“平实”、“对职业文学技巧的否定更彻底”等与小说大相径庭的也是不言而喻的纪实“特点”。这种情况也告诉我们,《北京人》等实录文学并没有小说的本质特征,还是不叫它“小说”为好。
纪实文学也要发展和创新,“口述实录文学”就是它的新品种。从前的纪实文学家族,有传记、报告、回忆录、访问记、各种小品及生活素描。这些样式都有某种“实录”内容,但由于记忆和笔记的局限,对场景、细节不便多作描绘,对采访对象的长篇口述更难完整记述,否则就显得不真实,乃至羼入小说家之笔。便是被汉代史家赞为“实录”楷模的《史记》也被后世学者指出许多想象成份和有别于“记言”的“拟言”文字,这也是这部伟大史书同时又是文学经典的重要因素。近世报告文学、回忆录、访问记等也是这样,难于大铺大展,细画细描,引录人物话语较短较少。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不用合理想象,以求增加作品的具体性、完整性和感染力。但从录音机、录像机广泛使用以来,上述情况有了重大变化。如有必要,作者可以把采访对象的谈话、所要表现的情境借助这类现代化工具“还原”成口述或描述的实录文学,无论多长多细,都不影响“实录”的真实程度,无需借助想象弥补记忆的空白。《北京人》等展示的主人公谈话,远比以往的传记、报告文学、回忆录更完整、细腻,乃至繁琐,却比《史记》以来的任何纪实文学都更真实,更具实录性,从而成为前所未有的纯纪实文学。这种作品的某些部分,叙事样态或同小说拉近了距离,而其高度实录、不事虚拟、“对职业文学技巧的否定更彻底”等本质特征使它与小说的距离更远,是更地道的纪实文学。斯·阿列克茜叶维契多次谈到她用录音机采访那些当年曾投身卫国战争的苏联妇女,努力“把她们那生动的声音用录音磁带以及尽管单薄但却比最博闻强记的头脑更可靠的纸张保存下来”,以求作品具有文献的真实性。桑晔也说:“我们之所以选用口述实录文学的样式来写一百位普通人,是因为这种体例更近真实,它能使文字与读者、内容与现实之间的空间缩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录音机和录像机的应用不仅大大提高了纪实文学的真实价值,也为其发展和创新开出一片新天地。
当然,口述实录文学的真实性也不是绝对的,有时还要打很大的折扣,因为讲述人说的未必都是实话,甚至可能胡编乱适。《北京人》正文之前,就有作者这样的说明:“个别口述者可能没有说实话。”不过,这不关实录的真实性。相反,作品原原本本地录下了口述者不说实话的状况,也是实录文学所特有的纪实性。
二、勿谓小说为纪实
《中国心》是较早用“报告小说”名目发表的作品,副题是来自海外某人士“讲的故事”;两月后在另一刊物发表时,改题《海水下面是泥土》,副题同,亦冠“报告小说”之名。全文十三节,有三节书信体,一节日记体,各数千言,全是书面语。那位人士怎么讲法?怎能“讲”出那样长的信与日记的原文?分明是作者大力造作的产物。更可怪者,还有许多玄而又玄难以置信的情节;只身入虎穴捕获群匪,强令十八岁儿子在台风大浪中冒生命危险下海游泳,驱车与情敌追逐——决斗……离奇,惊险,还有巧合,传奇小说所不及,侦探小说庶可比。将它与“报告”或“纪实”的名目连在一起,实属南其辕而北其辙。大概作者也感到那内容离“纪实”太远,在第二次发表时,将原来引言中“彻头彻尾是一个真实的大故事”等语删去,而加上“这回我写的是小说”一句。但后来收入《军事文学经典》时,这后加的一句又不见了,想是考虑到它与“报告小说”不甚一致,便取了既不说“真实”,也不说“是小说”的折中含糊态度。三种版本引言的三种面貌,反映了作者的举棋不定和两难境地。
以“纪实小说”名目发表的《5·19 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王府井万花筒》等作品,一度以其新颖和亲切引起关注。其共同特点是将某种新闻报告性的背景与具有明显虚构性的人物融合在一起,半真半假,独具一格。这种小说自有它的开拓性和独特价值。但人物既属虚构,作品就是小说,而非“纪实”。这是不言而喻的。一篇纵论“纪实小说”特征的大文引述多篇原本未称“纪实小说”的作品,却未提及这几篇正式冠以“纪实小说”名目的有影响作品,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王蒙的“系列小说”《在伊犁》,被某些论著作为“纪实小说”的标本,反复引述。论者片面强调“作者的初衷是‘恪守那种力求只进行朴质的记录’,‘着意追求的是一种非小说的纪实感’”,却不理会作者为什么要称这样的作品为“小说”,讳言作品的虚构性。《在伊犁》八篇,确与一般小说不同,有很强的纪实性和散文化特点,但它也有明显的虚构性。这首先就是人物姓名的虚假。我们知道,王蒙在伊犁农村的几年,一直住在阿不都,热合曼老人家里,而《在伊犁》中经常出现并成为其中两篇主人公的老房东却叫穆敏。如此可爱可敬的形象,作者尚不擅用真名实姓,别的主人公(多被作品写出这样那样明显的弱点)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作者的谨慎之处和明智之处,也是将它们称之为小说的重要原因。王蒙在《关于小说的一些特征》中说:“小说所以是小说,不是科学报告……就在于这种虚拟性质。”他还特别谈到以假名写真事的小说:“你一改名字,这本身就带有虚构性了。”况且,名字改用假的,作品称作小说,创作就取得自由,作者不必也不会循规蹈矩,笔笔求真,会很自然地对所写的生活人事作出必要的生发,把零星、残缺的记忆写成相对完整的断片。从这种意义上说,《在伊犁》的不同篇章也有不同程度的虚构性。作者把具有很强纪实性的作品毫不含糊地称为“小说”,决非随意为之,而是出于对作品本身和文体观念的切实把握和理解,既恰当,又策略。论者以为,首篇主人公穆罕默德·阿麦德简直就是“维族的阿Q”, 却没有引起鉴赏功能紊乱者“对号入座”。其实,这首先是由于作品不是某个真人的单纯纪实,而是小说;同时也由于作者不在品目上赶时髦,不给小说妄加“纪实”之类误导模特儿“对号”的招牌。反之,既不用真名实姓,又谓小说为“纪实”,这种做法本身就招引关心者猜测;至于作品所用的模特儿,“对号”更是自然的事。一个时期以来,此等“纪实小说”被指为“不实”乃至对簿公堂者不乏其例。每到这时,作者就祭起“小说允许虚构”的法宝抵挡、反驳,无论奏效与否,都是对所谓“纪实”的自我否定。
论者还将《燕赵悲歌》《东平之死》等具有明显虚构性的小说归入“纪实”之列。前者无须多论;后者以新四军烈士丘东平之死为题材,而写其事迹全用细腻的小说之笔,甚至用千字篇幅刻划其谁都无法知道的从负伤到自杀的心理过程,分明是现代历史题材的小说。
三、“纪实小说”何处寻
从以上考察可知,一篇或一部写现实人生的叙事作品,无论样态如何,总有有无虚构的问题。有虚构便非纪实,而是小说;无虚构便是纪实文学,不是小说,二者必居其一。世间不可能有既有虚构又无虚构的“新种”、“变种”或“亚种”,也就无处寻觅名符其实的“纪实小说”。
人们对“纪实小说”的最大疑问,就是它到底有无虚构,是否允许虚构。论者多不正面回答这问题,而说“它不能不带有传统叙事小说的痕迹”,“绝对地排除想象和虚构是不可思议的”。把文章做在“痕迹”和“绝对”上,自然没有问题。什么文学作品“排除想象和虚构”能到“绝对”地步呢?报告文学、回忆录也不可能,也不能说没有丝毫小说“痕迹”。对文学创作而言,纪实与虚构是相对的,不仅没有绝对的纪实,也没有绝对的虚构。这样看来,等于没有回答上述问题。另一种不是回答又关乎回答的说法是:“纪实小说削弱艺术假定性而增强客观真实性”。然而,小说的虚构程度从来就没有定规,《西游记》是小说,《红楼梦》也是小说;《阿Q正传》称小说,《社戏》也称小说, 从哪一种作为削弱的起点?再削弱多少才是“纪实小说”呢?比之《西游记》和《阿Q正传》,《公共汽车咏叹调》和《啊, 穆罕默德·阿麦德》无疑是大大削弱了“假定性”即虚构性,增强了纪实性,但若与《红楼梦》(作者亦称“纪实”)、《社戏》相较,虚构的多少、纪实的强弱就不容易考量了。其实也无须作这种考量。小说的所谓虚构性只是不成文的社会契约付与小说家的一种驰骋想象发挥创造的权力和自由,至于他要将多少客观存在的真实生活原原本本地写进作品,是内容的绝大部分,还是微乎其微,都由他根据艺术需要自行决定,并不影响小说之为小说。这也是小说家的一种权力与自由。小说的写实与虚构因而具有极大的弹性。这种弹性使小说同没有虚构自由的纪实文学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却没有空白地带,因而也就没给介乎两者之间的“纪实小说”留有生长空间。被人称作“纪实小说”的作品,非各纪实文学,即属于小说(如前两节所辨析),原因就在这里。
“一般小说是去了解一百件事后,加以融汇提炼,写出第一百零一件事来。纪实小说是在了解一百件事后,从中选出一件最值得写的事来展现。”这种说法似是而实非。第一,各种纪实文学都是从许多事件中“选出一件最值得写的事来展现”,但它们并不是“纪实小说”;第二,综合多人多事的小说固然很多,以一人一事为原型、本事的小说也不胜枚举。问题在于对选出的那件事如何“展现”。原原本本地展现,就是纪实文学,而非“纪实小说”;虚饰、生发、廓大、变形变态地展现,就成为小说,但不是什么“纪实小说”。前面提到的《东平之死》,就不是由多人之死提炼而成,而是用大量的想象和虚构填补无法确知的事迹空白,因而成了地道的小说。《聊斋志异》中有篇《大力将军》,写清初发迹的吴大奇对周济过乞丐吴六奇的江浙名士查伊璜慷慨报恩之事。据有关记载,吴将查请到官署,极尽礼遇,先后赠银六千两,并将查喜爱的英石峰用巨舰载送其家,而聊斋与吴请查人署后,将所有家私登记造册,然后“以半奉先生”,表示“一婢一物所不敢私”。如此廓大、生发,俨然成了小说,而所据只是吴氏本人报恩一事,并未掺入他人的事迹。
这里有必要谈谈自传体小说。它们无疑都是以作者身事为题材,不是百人百事“融合提炼”的产物。其所以称小说而不称自传,是因为久远往事的记忆大都粗略而模糊,无法复原,要写得具体、形象、生动,必作合理的生发和虚似,从而具有小说特质,而非纪实文学。日本道纲母的《蜻蛉日记》作于十世纪,可说是最早的自传体小说,但那不是随时写下的真的日记,而是女作者在三十八岁时对二十一年不如意婚姻的征事与感受以“日记”形式所作的追忆。这样“追写”的“日记”无论有怎样的真实性,也必然是一种艺术的造作,所以被校注者川口久雄确当地称为“日记体小说”和“自传体小说”。所谓“自传体小说”,就是以作者身事为题材的小说,并不能作“纪实小说”的例证。
不过,要寻找真正的“纪实小说”也并不难。在我国小说史上,从汉至清的文言小说,纪实之作比比皆是。这是因为其小说观念不把虚构作为一种规定性,或者说,那时的所谓“小说”就根本没有规定性,与皇皇经史、诗文相对的种种“小”(不重要)的东西都被纳入“小说”之列,因而就有《世说新语》及后世仿作中大量的纪实之作。但它们偏又不叫“纪实小说”,因为那些作者只为传闻作记录和文学加工,连记述怪闻异说也称“实录”。既然没有虚构的观念,自然也就无所谓“纪实”。
四、纪实文学勿虚构
“纪实小说”、“报告小说”云云,不只是文体名目问题和文学理论问题,也是文学创作的实际问题,是要不要给纪实文学以原本没有的虚构权力问题。所谓“报告文学与小说杂交”、“兼有报告文学与小说之所长”,说到底就是允许纪实文学有某种程度的虚构造作。一篇“为报告小说鼓吹”之文先是说“不允许凭空杜撰,向壁虚构”,随后又说:“某些题材如果完全按真人真事写,作者会感到一种束缚,而运用小说手法,则可于束缚中求自由,不必完全拘泥于真实事件的描述”,“对一些次要情节、细节的虚构和某些变通…使之更生动,更富于感染力”。如此前后矛盾,恰如“纪实”(或“报告”)与“小说”合为一个概念之自相抵牾,决非偶然,但也直白地道出“小说手法”的真正含意,道出“纪实”(或“报告”)定要与“小说”联姻的底蕴;让纪实文学摆脱真人真事的“束缚”,以“次要情节、细节的虚构”求得“生动”、增强“感染力”。
众所周知,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灵魂和生命,是其价值的决定因素。在纪实文学中掺入虚构,无论情节还是细节,都会使作品失去纯为纪实的艺术品格和最可宝贵的可信性,戕害其灵魂和生命力。“兼有报告文学与小说之所长”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以失真为代价博取生动,不止舍本逐末,亦属缘木求鱼,不唯不能感人,还会令人生厌,向被视为纪实文学的第一大忌。“纪实小说”、“报告小说”等名目,实际是将这种做法合法化和公开化,倡导一种在纪实中公然掺些假的文学。这在法理上也许可以减少虚构的某种欺骗性,但其戕害纪实之真的本质却未改变。它不是“削弱艺术假定性增加客观真实性”,而是相反,使所谓“纪实”不打折扣。近期《文艺报》载:有些编者“在向纪实文学作者的稿时便言明,不求细节的真实,只要‘艺术的真实’就可以了”,正是“纪实小说”此种本质的体现和证明。
允许纪实文学掺杂小说的虚构成份,还会助长为现实人事虚美、溢恶的不良文风,从而失去纪实文学的客观严肃性。那种用真名写假事或半真半假的事,在“报告小说”的名义下成了名正言顺之举;而用假名写真事或半假半真的事,亦得冒“纪实小说”之名行隐喻、影射之实。溢恶、影射易受当事人责难乃至控告,或有所顾忌;虚美则多被当事人欢迎,所以更易成为风气。有的论者也看到这种弊病,一面肯定“纪实小说”观念,一面批评“目前的一些号称纪实小说的作品”;“与‘纪实’名实不符,出于某种功利的需要,写人物有悖于不虚美不掩恶的精神,用虚饰以至做假来代替‘纪实’。”其实,这种不良文风不只源于作者的思想和心态,也是“纪实小说”流行的必然产物,正是“纪实小说”观念为“造假”开了方便之门,使“虚美”和“掩恶”有了合法的外衣。如果与“纪实”完全相符,何得称为“小说”?可见,要想“纪实”不虚美、不溢恶,名实相符,就不能使它和小说联姻,取得虚构的权力和自由。
当然,纪实文学并非复制现实,还原现实,而是摹写、表现现实。它以抽象的语言文字造成的人生百态的艺术幻象——第二现实,不仅具有模糊性,也有很大的伸缩性、不确定性,与其摹写、表现的现实对象只是相似、相近而非相同、相等,允许有也必然有这样那样的差异。社会契约不给纪实文学以虚构——造假的权力与自由,却不要求它的描述与现实完全一致,达到“无差别境界”,而给它以虚构以外的表现与创造的艺术自由,包括某些不可或缺的合理想象。高尔基说,“艺术是靠想象而存在的”。没有想象就没有文学。完全排除想象,不但无法创作小说,也写不出具体可感的报告文学和回忆录。我由此想到格拉宁自称为“纪实中篇小说”的《克拉芙吉娅·维洛尔》(中译本题作《女政委》),人物用真名实姓,所写的“这个不同凡响的妇女在战争中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作者“就像人们写自传一样……力求最大限度的严格、朴实、客观,避免任何艺术夸张”。这不只是告白,也切合作品的实际,读来倍感真实、亲切。如此就是货真价实的纪实文学,无须由于某些“综合分析”、合理想象而小心翼翼地与“小说”桂钩。我们并不因为《左传》《史记》中有一些作者的想象成份而否定其为史传文学,将它们混同于历史小说,而且叹赏那些想象的文学意味和审美价值,那么,当今严肃的纪实文学中某些不可不有的想象成份,也会得到读者的理解以至叹赏,不可将它混同于小说的虚构,也无须造出“纪实小说”之类的名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