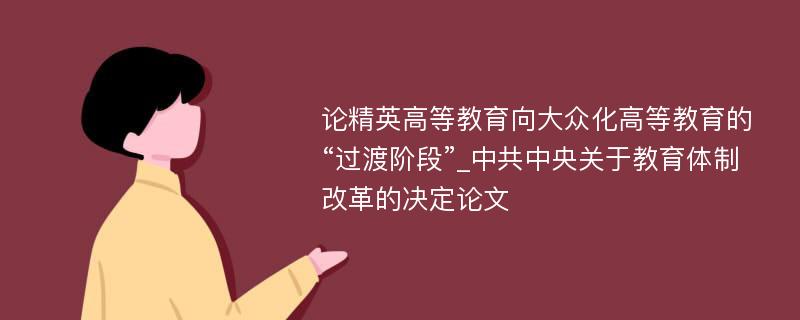
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高等教育论文,试论论文,阶段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1)02-0001-06
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适龄青年的15%[1],也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将于21世纪初迈入世界多数国家教育界所共识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重要代表马丁·特罗(Martin Trow,1926-)教授曾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划分为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下)、大众教育阶段(毛入学率15%-50%)和普及教育阶段(毛入学率50%以上)。那么,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是否尚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是否仍应根据精英教育的性质培养精英人才?这是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理论问题,对于这个过程的认识与把握,关系到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规划与部署。我们认为: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考察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在学生数量达到大众化阶段之前,必然有一个“过渡阶段”,我国当前正处于这一过渡阶段。本文试图从分析美国马丁·特罗教授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传播与验证入手,结合考察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践过程,探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渡阶段的特点,进而揭示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过渡的基本特征与规律。
一、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传播、验证与修正
美国高等教育以300 多年的时间跨越了西欧高等教育千年的发展历程,于20世纪40年代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至60年代末,在学大学生数超过18— 21岁青年人口的一半。在此期间, 西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规模也成倍增长[2]。规模的扩张引发了高等教育观念、职能、课程、管理、入学与选拔等方面的一系列质变。美国教育社会学家、伯克利大学的马丁·特罗教授就是以美国和战后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些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的问题,接连撰写了《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转化的思考》(1970)、《高等教育的扩张与转变》(1972)、《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1973)等系列长篇论文。他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探讨数量增长与性质变化的关系,将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他认为:“一些国家的精英高等教育,在其规模扩大到能为15%左右的适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之前,它的性质基本上不会改变。当达到15%时,高等教育系统的性质开始改变,转向大众型;如果这个过渡成功,大众高等教育可在不改变其性质下,发展规模直至其容量达到适龄人口的50%。当超过50%时,即高等教育开始快速迈向普及时,它必然再创新的高等教育模式”[3]。
接着,他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一发展观出发,剖析了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高等教育观念、功能、管理和课程等方面所存在的质的变化。他认为,伴随高等教育的对象从少数精英向大众化过渡,直至普及化的发展进程,在观念上,接受高等教育从“少数出身好或天赋高或两者兼备的人的特权”转变为“具有一定资格者的一种权利”和全体人的“一种义务”[4]。在目的和功能上, 从“塑造统治阶层的心智和个性”,培养政府和学术精英转向“提高人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为发达工业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做准备”[5]。在高等教育系统方面, 学校类型从单一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演变为包括全日制、部分时间制、远程教育、开放教育等多种办学模式共存的多样化系统,学校与社会间的清晰界限逐渐消失。学生的学习经历,从“住校的不间断学习”趋向延迟入学,“时学时辍”的现象增多。师生间原有的亲密关系逐步淡化。学术标准从共同的高标准趋向多样化。课程从“高度的专门结构化”趋向“灵活的模块化”,并逐渐泛化。在入学与选拔上,从根据“考试成绩、英才成就”到引入“非学术标准”,以及凭借“个人意愿”[6]。 在领导与决策上,社会公众逐步介入原来由“少数学术精英团体”所垄断的决策。在学校行政领导与管理上,也从“由学术人员兼任”转变为由“专业管理者、管理专家”专门管理并吸收校内外人士参与[7]。
由于马丁·特罗教授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欧美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之际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论,同时,他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是将高等教育量的扩张与质的变化两者结合起来研究,这使原先只以数据所表示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具有了丰富的质的内涵,也使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质的飞跃有了量的参照系。这种将以往关于学生选拔与录取、课程与教学方式、行政与管理等许多离散的、孤立的问题研究综合在一起,并置于从精英到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大跨度的历史发展背景下进行分析的研究思想和方法,不仅可为一个国家制订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而且也为人们综合考虑高等教育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所以,他的“三段论”一经提出,便为西方国家欣然接受,并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的流传。目前,他的论著已有希腊文、西班牙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希伯来文、丹麦文、瑞典文、波兰文、俄文、日文、和中文等多种文字的译本。
然而,当人们在应用特罗教授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去考察本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解答实际问题时,也发现特罗教授的“三段论”的不足之处。例如,日本广岛大学教育研究中心有本章教授在考察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演变历程中发现:90年代,正处于大众化阶段后期的日本高等教育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其管理体制、经费来源、发展道路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变化,已有越来越多的成人多次进入高等院校接受继续教育,这并非特罗教授所列举的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特征所能涵盖[8]。于是,他将90 年代日本高等教育出现的这些区别于马丁·特罗所言的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的特征和普及阶段的质的变化,冠之为“后大众(post—massification)阶段”,并将其定位在特罗教授所说的大众化阶段的“后期”与普及化阶段的“初期”。他还提出“大众化高等教育”通过“后大众”这个阶段的过渡之后,有可能转变为“终身学习”(long life learning)阶段,而非传统大学适龄青年的普及教育阶段。另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罗伯特·吉姆斯基(Robert Zemsky)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的佩特里夏·甘波特(Patricia J.Gumport)等人也以“后大众阶段”为题讨论了美国当代高等教育的特征[9]。
马丁·特罗教授在发表“三段论”之后,面对7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发展演变的实际进程,他吸收各国专家的修正性观点,结合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对其70年代初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构想进行了修正与补充。1998年5月31日,
他参加日本广岛召开的“日本高等教育研究学会(Japanese Society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学术研讨会”时,在所提交的论文《从大众高等教育走向普及》中,从新旧世纪之交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入手探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新特征,对自己早先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的“三段论”中的“普及教育”阶段的内涵作了新的解说:“高等教育大众化今后10年的主要任务是从大众化阶段迈向普及化阶段。但是大众化高等教育与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区别不再定义为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各种各样的学校学习。这是旧的普及高等教育观念。今后的普及高等教育不在于注册人数,而是在于参与和分享,即是与社会大部分人,几乎包括在家里或在工作单位的全体成年人密切相连的‘继续教育’。这种教育不再凭借传统的学院或大学校园,而是通过远程教育。大多数学生的学习并不是为了追求学位和学分,而是为了保持或改善其在就业市场中的地位,或者为了自娱自乐。其结局有点类似于‘学习社会’(learning society)”[10]。由此而观,在90年代末,马丁·特罗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后阶段是走向学习社会,而不局限于传统的青年普及教育。
综上所述,特罗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主要是根据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而构建的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简单的思想框架。他自己后来也承认:“构建这个图式或模式只是初步的尝试,存在甚多的局限和不完善。……在某些方面,特别是我关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也将沿袭美国的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假设性预示,现在被1973年以来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是个明显的错误。”[11]八九十年代,特罗教授虽然不时地对其“三段论”进行修正、补充,但仍局限于部分发达国家,并未在其他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广与验证。因而,其修正的重点是大众化阶段与普及化阶段的关系,并未涉及精英阶段与大众阶段的关系。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向大众阶段迈进的过程中,马丁·特罗的“三段论”也引起国人的关注。然而,我们在将马丁·特罗关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学术思想和理念用于解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时,同样感到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并未像马丁·特罗教授的“三阶段”论所断言的那么简单,即认为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一定程度的扩张,毛入学率达到15%时才出现质变。而是在量的扩张尚与大众教育阶段的低限有相当距离时,高等教育系统在许多方面就出现了局部性的质变,呈现出显著的大众化教育特性,甚至是普及化教育的特征。本文第二部分将着重探讨这些特征。
二、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的“过渡阶段”特征
首先,让我们把特罗所归纳的西方发达国家从精英向大众、普及教育阶段转化的量变指标和10个质变特征列表于后(见表1), 用以考察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教育转化的“过渡阶段”特征。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20余年来,在学大学生数扩大了7.2倍,2000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1%(注:此数据是根据我国教育部规划司制定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计算公式加以计算的。该公式为: 在学学生数=研究生+普通高校本专科+成人高校本专科+军事院校+学历文凭考试+电大注册听生注册人数×0.3(折算系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5(系数)。参见:纪宝成:《关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问题》,载《中国教育报》1999年1月16日·第2版。)但是,以表1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的量变指标来衡量,我国高等教育尚未达到大众化教育阶段。但若从“质”的方面来说,中国高等教育尚未达到大众化教育阶段。但若从“质”的方面来说,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具有马丁·特罗教授所言的大众化阶段甚至普及化阶段的若干特征。例如,在观念上,我国政府于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的第9条规定, “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12],体现了大众高等教育权利已得到法律的保障。在培养目标上,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提出了大众化的高等教育目标:“要造就数以千万计的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具有开拓能力的厂长、经理、工程师、农艺师、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和其他经济、技术工作人员。”[13]90年代以来,政府更是不断地强调高等教育发展重心应当下移,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一大批具有必要的理论和较强实践能力,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和农村急需的人才。学校类型和办学体系日趋多样化。1979年我国建立了广播电视大学,开展远程教育,至1996年,远程高等教育学生数多达142万,占高校学生总数的24.4%。1998年,教育部批准25所大学开展现代远程教育工作试点,1999年启动中国教育互联网(CERNET)工程,并与广播电视网联络,双管齐下,日益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自从我国苏南地区于1980年创立“市办职业大学”后,在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里,我国就创办了100多所高等职业大学。1985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使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更加生机勃勃,至1998年,我国高职高专院校共计1394所,在校生394.74万人,占高等院校的校生总数的63.53%[14]。我国于80 年代初建立的自学考试教育制度,十几年来也得到迅猛发展,1999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毕业生多达42万人,占高等教育毕业生数的19%[15]。近两年,深圳、浙江、河北等地还建立了能容纳三四万人的大众高等教育基地——“大学城”。1999年,教育部颁发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还提出了“2010年基本建立起终身学习体系”[16]。前面已述,“终身学习”教育系统在特罗教授和有本章教授等西方学者眼里是大众阶段后的高等教育特征。在招生制度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与相当部分的民办高等院校是实行“宽进严出”的招生与管理制度。在办学质量标准上,中国教育理论界也出现了办学标准多样化的大众高等教育质量观,如潘懋元在1999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一文中,就提出“必须树立有别于传统办学思想的大众化办学思想……质量观的转变包括:价值观、人才观、教学观和学生观等。”[17]在课程组织上,80年代之前,我国高校课程体系是以“专业”为单位,由“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构成,呈现高度结构化和专门化的特征。80年代后,在培养适应市场和科技发展需要的“一专多能”人才的思想指导下,各高校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选课制、主辅修制和“大专业,小口径”的“模块化”课程组,打通了公共课和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层级界限,呈现出课程结构灵活性的特征。在学校行政领导方面,伴随院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功能的多样化,学校管理日趋专业化,2000年教育部出台了《建议高等院校副校级以下行政领导由专职人员担任》的文件。这也反映了我国的大众型高等院校在数量上已占多数的特点。另外,伴随电大、成人高校、夜大学、社区教育和自学考试的发展,八九十年代我国走读的学生在不断增加,延缓入学和时学时辍现象也在增多。
表1 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的量的变化和质的10个维度变化
三段论 精英阶段 大众阶段普及阶段
高等教育规模
(毛入学率) 15%以下
15%-50%
50%以上
高等教育观 上大学是少数人的特权一定资格者的权利 人的社会义务
功能
塑造人的心智和个性 传授技术与培养能力
培养人的社会适应能力
培养官吏与学术人才 培养技术与经济专家
造就现代社会公民
课程
侧重学术与专业、课程
灵活的模块化课程 课程之间、学习与生活之间
结构化和专门化 的界限被打破,课程结构泛化
教学形式
学年制、必修制 学分制
与师生关系 重视个别指导法 讲授为主,辅以讨论
教学形式多样化、应用现代化手段
师徒关系 师生关系师生关系淡化
学生的学习经历 住校、学习不间断
走读、多数学生的学
延迟入学、时学时辍现象增多
习不间断
学校类型与规模 类型单一 类型多样化类型多样至没有共同的标准
每校数千人三四万人的大学城
学生数无限制
学校与社会间的界限清晰 学校与社会间的界限模糊 学校与社会间的界限逐渐消失
领导与决策 少数精英群体 受政治、"关注者"影响 公众介入
(质量标准) 共同的高标准 多样化"价值增值"成了标准
入学与选拔 考试成绩、英才成就引进非学术标准 个人意愿
学校行政领导
学术人员兼任高级教专业管理者 管理专家
学校内部管理
授控制
初级工作人员和学生参与 民主参与
校外人士参与
上述可见,从数量上衡量,8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2%— 3%,与西方发达国家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的规模指标有相当大的差距。迄今,我国高等教育也仍未跨入西方学者所言的大众教育阶段。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高等教育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思想的指导下,闯出了不断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以促进规模发展的“质变带动量变”的发展道路。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化教育阶段转变的这一“质变促进量变”的显著特征,与马丁·特罗所提出的“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学生数量的增长都先于其他方面的变化”[18]的“量变带动质变”的简单断言迥然不同。我们认为,可以将这种高等教育的“量”的积累尚未达到西方学者所说的大众教育的“度”,即毛入学率未达到15%,而“超前”出现的种种大众化高等教育新质的变化过程,称之为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过渡阶段”。
毋庸置疑,这个“过渡阶段”将延续至高等教育出现全局性的质变,包括量的增长,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达到15%。而这个“过渡阶段”的起始时间则可假定为1985年前后。因为该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必须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逐步建立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改革高等院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改变专业过于狭窄的状况,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19]这一系列决策不仅为我国高等教育指明了向世界现代化发达国家学习、看齐的发展方向,而且强调从体制改革入手,推动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的发展道路,并对高等教育办学类型、形式、招生制度、专业课程结构等方面提出改革方策。自学考试也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因之,可以说,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高等教育从中国实际出发,有计划、有组织地迈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起点。而1999年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则是目标十分明确和清晰地发起向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冲刺,并向“学习社会”迈进的行动。
三、从精英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具有普遍性意义
一般说,现代化“后发外生型”国家可以借鉴“早发内生型”国家的经验。因而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上,“量”的增长未达到大众化阶段的“度”之前,就可借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经验,进行某些“质”的改变,以促进“量”的快速增长。这是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必要选择,也是明智的选择。
那么,这种从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化教育阶段的“以质变带动量变”的发展特征是否具有普遍性?从发展中国家韩国来看,20世纪70年代韩国高等教育尚处于精英教育阶段,为了适应经济的高速发展,客观上要求进一步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并增加对高级技术人才的需求。因此韩国于70年代就大力发展大众型高等教育。如1972年成立广播函授大学,以招收继续进修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在职人员,着力发展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1977年,鉴于经济部门对所需人才质量要求的提高,韩国修订了《韩国教育法》,将五六十年代成立的二年制初级学院和招收初中毕业生的五年制实业高等专科学校,统一改为招收高中毕业生的二年制“专门大学”,使短期高等教育成为一个法定的高等教育层次,专门为产业界培养高等职业技术人才。大众型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使韩国高等教育规模得到高速发展,1970年至1980年间,高等教育学生数扩大了3 倍多,198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4.7%,进入大众教育阶段。
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史来看,英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阶段转变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总的量变为与局部性质变在推动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从19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英国高等教育开始向‘大众化’方向迈进的时期”[20]。19世纪中叶,英国就开始在传统精英大学之外兴办为当地经济部门培养技术人才的大众型“城市学院”,后与传统教育势力经过100多年的反复较量,至1963年,英国发表《罗宾斯报告》, 终于大张旗鼓地掀起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进军的运动。1964年,英国建立了高等教育“双重制”,一部分是传统的精英大学系统,另一部分是以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为主的“公共高等教育系统”,这个部分属于大众化型的高等教育,它有力地推动着英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总量变与局部性质变相互作用的推进,1980年英国高等教育终于迈入了大众阶段。其实,即使在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迈向大众教育阶段,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高等教育系统与类型的局部质变带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质变推动量变”的过渡阶段。就是特罗教授在断言“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学生数量的增长都先于其他方面的变化”时,也不得不把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特征划为例外。他说:“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赠地大学,在观念上是民主的,学校同时拥有学术成就和公共服务的功能,大大超前于时代的发展。这些学校已经对大众化高等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21]言下之意,美国高等教育早在19世纪下半叶建立“赠地学院”时,就出现了高等教育系统从精英向大众化阶段过渡的质变,并推动着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至20世纪40年代跨入大众阶段。总之,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阶段转变过程中存在局部质变带动量变的“过渡阶段”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要通过量的积累和总的量变过程中的许多部分质变才能完成。部分的质变需要一定量的积累,反过来部分的质变一旦发生又会促进量变,并为整个高等教育的根本质变准备条件。因此,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化阶段迈进的过程中,系统的部分质变对整个规模扩张的推动作用是重大的。所以,从精英到大众教育的转变必然存在着局部质变推动总体量变的“过渡阶段”。
基于上述对马丁·特罗教授于1973年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认识,以及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特征的了解,我们认为,必须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前在我国风行的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切勿削足适履,用其理论来框定我们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而是要充分发挥我国高等教育“后发外生型”的优势,借鉴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外先进经验,闯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同时在总结我们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正和充实舶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学说与理论。换言之,引进的马丁·特罗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其发展阶段论的思想,有助于拓宽我们的思路,预见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在实践中塑造自己的分析和解释框架,但我们还需化“洋”为“土”,建立起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框架,对洋人因袭之论作出富有挑战性的回应。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成就才会使人折服,并作为世界多元学术的一个流派而登上国际高等教育学术殿堂。
收稿日期:2001-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