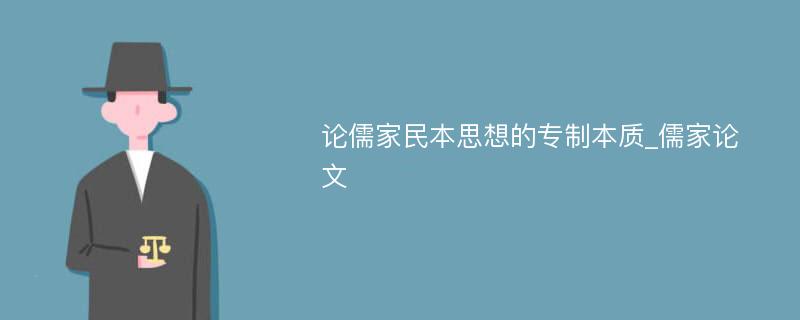
试论儒家民本思想的专制主义实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民本论文,专制主义论文,试论论文,实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本”一词来自于伪《古文尚书》中的《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用这个词来概括儒家的政治思想可以说再恰当不过了。据刘泽华先生研究,“民本”理论包括“君以民为本说”“民贵君轻说”“立君为民说”“君养民、民养君说”“君不可与民争利说”“富民足君说”“民弃君说”“得民为君说”“君为民主说”等九个分命题[1]。可以概括为保民、养民、富民[1](p.208-218]、教民四个层次,总之一句话,即“重民”,把“民”视为政治的根本。
“民本观”是儒家政治理论中最光彩夺目的地方,它强调温情政治,关注民众疾苦,在历史上或有制约绝对君权的作用。因此,现代新儒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民本思想中的“正德、利用、厚生”,孟子的民贵君轻和“人皆可以为尧舜”包含着大平等的精神,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民主,或者认为它包含了民主精神的种子,由此可以直接实现向现代民主制度的转化。受新儒家影响,也是出于弘扬传统文化的美好愿望,许多大陆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致力于论证“民本”与“民主”的关系。如,在2000年8月于青岛召开的“儒家传统与人权·民主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认为,现代民主既有制度层面的内涵,又有思想理念层面的内涵,作为制度层面上的民主,主要出现于近代社会以后,作为思想理念层面上的民主,则早已存在于儒家的民本主义学说之中,即“民本”与“民主”之间是相通的,即便“民本”不等于“民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民本可以实现向民主的转换[2]。显然,这种观点认为儒学的精神是民主的,在现代社会完全可能借尸还魂——这里,制度与理论被断为两截。也有一些人强调了“民本”与“民主”的不同,却认为民本思想虽然有为专制统治服务的一面,但也有与专制权力对立的另一面,因而具有反专制的积极意义(注:参看范正宇:《民本主义:在孟子和他身后》,《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陈寒鸣:《儒学与现代民主》,《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李俊琳《儒家民本思想的积极意义》,《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等等。)。
说“民本”等于或者孕育着“民主”固然是不论之言,认为“民本”服务或对立于专制权力却也似是而非:两者都割裂了思想与现实、理论与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都没有对一个制度的内在逻辑和君主个人的本能冲动作出区分。我的看法是,“民本”是专制权力的题内应有之义,是“农本”的另一个说法;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它不过是一种修辞术(注:修辞是一种说服的技术,是智者的策略,它的精髓是通过精心扮装把片面性的“道理”置换成普遍性的真理,通过暗中铺垫将有限的可能性贯通于无限的必然性。)。
一、“民本”是专制权力的题内应有之义
时下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商周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巨变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由“神本”向“民本”的转变。这种观点不无道理,周朝初期在思想领域确实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表现为巫术氛围的减弱和人文精神的生发(注:我认为,“人文精神”与“民本观念”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指的是针对自然鬼神等“非人”力量而对人的生命和道德价值的强调,后者则是权力对其对象的评价。我们说儒家思想具有人文色彩,是就其对个体人格和意志自由的追求而言,民本思想显然与此无关。),但若认为“民本”观念是这个时代的发明,却也不合历史实际。因为专制权力本来就是建立在对“民”的统合之上的。专制制度是一个等级分明的金字塔,没有“民”所构成的基础和级层,高踞顶端的君主也就失去了凭依。
同其他文明古国一样,中华民族也是随着专制王权的建立踏进文明时代的,不同的是,中华文化孕育了“重民”“保民”的政治理念。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绝对是大公无私的天下之主;帝喾高辛“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完全是为民众而生存的道德楷模。当然,司马迁依据的只是传说材料,但这些传说终究反映了一个民族具有普遍性的理想和价值取向。
至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简直就是圣王仁德所外化和展开的过程,如《尚书·尧典》称颂尧帝:“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似乎因为尧帝的存在,人类的生活才有了人性的亮光;《尚书·皋陶谟》是舜、禹、皋陶等人的一次会议纪要,讨论“安民”问题,皋陶强调为政之要是“在知人,在安民”,禹大力附和,并作了补充:“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
殷商时代的统治者已经形成了系统的重民、保民思想。商汤征夏,就是以捍卫民众利益为口实的:“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3]在日常政治中,商汤也非常关注民生疾苦和人心向背,在《尚书·多方》中,“明德慎罚”“以民为鉴”等儒家德政思想这时都已略具雏形。汤以后,凡是有所作为的商代帝王都是以“保民”为旗帜号召大众的。如盘庚迁都时,贵族们有抵触情绪,他搬出民众的意愿为挡箭牌,说自己迁都是“恭承民命”,要求贵族们“克黜乃心,施实德与民”[4],号召大家齐心协力“念敬我众”。
周朝是民本思想的成熟期。作为偏处西陲的撮尔小邦,周朝只是利用了商纣王内外离心的危局才一举颠覆了盘据中原数百年之久的宗主国“天邑商”。面对天下汹汹的危难局势,周初统治者心中充满了“天命靡常”“人心惟危”的忧患意识。商朝覆亡的教训使他们深刻领会了民众的力量,认识到民心向背才是一个政权兴废的关键,因而提出了一套逻辑严密的统治理论,这就是以明德慎罚为内容的保民思想。周人把天命转移的原因归结为统治者德行的修持与否,淫欲自纵如商纣则“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5],怀保小民如文王、武王则“皇天弘膺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6](p.21)。上天是公正无私的,他是天下人共同的保护者(注:如《诗·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他的意志必然体现绝大多数人的心愿,王者不过是上天所选定的“民主”(注:《尚书·吕刑》有:“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尚书·多方》有:“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因而通过“民主”可以判断“天意”,所以要“以民为监”。
周初统治者战战兢兢地以“保民”为务,绝对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思想解放的结果,而是完全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现实需要,这是一种严厉而“仁慈”的大家长专制:如果民众乖乖顺从,则悉心关照,“若保赤子”;倘若不思向化,“乃其速由兹义率杀”,即毫不犹豫坚决清除。因此,周朝的“重民”、“保民”思想只是“软化”而不是“弱化”了专制统治。与殷商相比,周人的统治是温和了一些,但其覆盖性和渗透性却空前加强了:通过天命在德、王权神授的意识形态灌输,周朝君臣在民众心灵中逐步建构了专制王权的神圣性,在《尚书》和《诗经》中到处都是周王受命于天的政治宣传。
据刘泽华先生研究,从成王开始,周王亦自号“天子”[6](p.31),这意味着最高统治者通过自我授权获得了双重代表资格:既代表上天抚育下民,又代表众生协和鬼神。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天子”一直是中华民众福祉所系生死所依的人间神明,而其合法性论证就是由周初诸贤完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周朝所有“重民”、“保民”的主张,都是专制王权之绝对必要性的直接论据。
我们知道,任何政权的长治久安都有赖于臣民的合作与服从。周朝“保民而王”这种新型政治理念的深意在于,它通过“德”的引进,在统治者和“天”“民”之间建立了一种稳定的三角关系,使原来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直接对立,变成了四周向中心、子民向家长的自觉归依,而“德”就是那个把天、民和统治者统摄在一起的圆心:天德无私普照,民敬天从上为德,王承天保民为德;民意上达于天,天将民意托付于王,王用心去贯彻执行上天之命,才是德民之主——“德”是“天”“君”“民”所共同关注共同趋向的东西。由于“德”的内容和标准主要是由权力决定的,因而它便成了据天地之中等待着最高权威就位的黄金宝座。周朝统治者只是围着它打转转,努力靠近它,对这件上天赠与的法器敬而且畏(汉朝皇帝则在儒家的帮助下毫不客气地一屁股坐了上去,从此皇帝成了当然的圣人)。这里,“天”显然承担了权力共谋者的角色:通过对“德”的确认宣布统治的合法性,它使王者得以以一种无比高尚的名义(施德于民)、无比神圣的旗号(天意)把民众所内含的那种蒙昧、深沉而又野性的力量加以驯化并据为己有。
周人的“天”(注:周人“天”、“帝”并称,如《尚书·召诰》有“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但周人的“帝”比商人的“帝”要抽象一些,实际上是“天”的另一个说法。)与商人的“帝”不同的地方在于,“帝”只是一家一姓的主宰,而“天”则是天下民众包括被征服的商民族共同的监护者。在大张旗鼓地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通过严密的宗法制度同时在广度和程度上加强专制王权的同时,周人把一种文化共同体意识带进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天”作为半人格的神明,实际上是民众(当然是不分阶级的)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的决定自己命运的伟大力量所折射形成的影像,它意味着民族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从此以后,中华先民摆脱了祖先神的全面笼罩(对祖先的祭祀不再是动辄得咎的义务奉献,而成了慎终追远的神道设教),而作为与天地为三的独立存在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三皇五帝开创的重民传统经过周朝人文主义的净化而成为一个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宣称“述而不作”、以王道继承和弘扬者自居的孔子在考察了三代的质文损益后,一往情深地宣布:“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民本思想在春秋时期已为社会所广泛接受。据《左传》记载,“重民”“利民”已成为当时开明君臣的共识。襄公三十一年,穆叔引用《泰誓》中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之语,反对襄公修筑楚宫;桓公六年,随国人季梁曾有“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论;庄公三十二年,史嚚鉴于虢公“虐而听於神”,发表议论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於民;将亡,听於神”;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迁于绎,史官占卜“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文公说:“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近臣提醒服从占言可以延长生命时,邾文公回答说:“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当时诸侯之间的兼并愈演愈烈,对他们来说,人口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谁能“保民”、“滋民”,谁就拥有更多争夺战伐的本钱,因此,凡是较开明的君主都意识到并强调“民”的重要性。这直接开启了儒家的民本思想。
儒家的民本思想直接继承了文武周公及春秋诸贤的遗产。孔子的民本思想体现于其“为政以德”的“仁政”,核心内容是“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8]。这里,“养民也惠”即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9],“节用而爱人”[10];“使民也义”是指“择可劳而劳之”[9],“使民以时”[10],“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11]。这些主张闪烁着人道主义光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大有教育意义的,但归根结底,它们仍然只是一种有关专制统治的理念和技术主张而已。孔子认为,“民”是没有责任能力的,离不开仁慈君主的关怀和教化。在《论语·里仁》中,他说:“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说,老百姓心地蒙昧欲望简单,让他们吃饱用足并加以积极引导,就能使他们甘心接受在上者驱使,自觉维护君主的权威。所以,不论是“惠养”还是“义使”,目的都是控制民众使之为我所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惠则足以使人。”[12]在《论语·为政》中,孔子直接道出了其民本政治诉求的目标——专制君主的权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孟子是民本思想的金声玉振者。他不仅以旁征博引的滔滔雄辩论证了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而且就“保民”“养民”提出了系统的制度设计,并且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3]的响亮口号把民本思想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大量引证历史上治乱成败的先例,孟子不厌其烦地告诫当时的统治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4],民心向背才是国家兴亡的关键。在《尽心下》中,他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在《离娄上》篇中,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怎样才能获得民众拥戴呢?他的观点是:“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15]就是满足民从最基本的生活欲求,用孟子自己的话说,主要措施为“制民恒产”和“取之有制”。他认为,要使老百姓尊上守礼,前提是让他们安居乐业:
《梁惠王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於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尽心上》: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
《滕文公上》: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於民有制。
在孟子眼里,民众是君主“得天下”所必须凭借的资源,“得民”只是一种必要且必须的手段。可以说,孟子的民本观并没有任何实质性新内容。作为孔子教言的弘扬者,他只是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热情把孔子提出的各个命题从不同的方向推向极致:他为“民”赋予了更重要的地位,对现实中的君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荀子从人的社会性定义认识君、民之间的关系。在《王制》中,他说:“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在《君道》中,则说“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天然呈现为一种混沌无序状态,靠了人君的制作礼仪,定分止争,才得以相安无事,和平发展。故而他又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16]因为“民”只有经过君主的用心修理——显设之、班治之,藩饰之——才得以过上人的生活。在荀子眼里,民众天生就是趋利避害的两条腿动物,像鸟儿选择树木一样选择能够善待他们的君主,因而他强调君主对民众应该“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认为“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者也”[17]。至于“利民”、“爱民”的具体措施,荀子所能提出的不过是“轻田野之赋,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17]。
随着民族走向王权大一统,儒家渊源久远的民本思想变得越来越冷寂苍茫了,在荀子这里已完全没有了孔孟式的人道温情。荀子之“重民”,只是因为“民”是一种不得不小心对待并加以利用的力量。请看《王制》:
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
“君舟民水”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的经典隐喻,它的含义是:君拥有整个世界,民众完全是为君而存在的,是君权存在的前提和保证;民众以其无穷数量累积而形成一种原始的、盲目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承载着君权的运行,却又内含着倾覆一切的致命危险。综观历史,儒家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乾嘉盛世之类,不过是这一隐喻的千载难逢的注脚而已。
通过以上对“民本观”寻波溯源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民本”是专制权力的题内自有之义,是专制权力与生俱来的自我制约机制:它使作为一种资源组织方式的专制制度得以克服个人本能冲动导致的溢出和过度,从而维持其基本的现实把握能力。因而,作为一种统治理论,它是统治阶级对自己统治基础的自觉,它不是站在权力对面,而是站在其旁边,时而恫吓时而利诱,苦心婆心地劝说,希望那因为没有制度性约束而随时可能走向极端的专制权力靠了自我警示适可而止。
二、“民本”是“农本”的另一个说法,是一种修辞术
如果不再就事论事,而在儒家整个统治理论的框架内审视“民本”思想,我们会发现,它不过是“农本”的另一个说法而已。因为,无论说得多么慷慨激昂,将“民本”折解开来,不过是“使民以时”、“取民以制”、“教民以礼”、“明德慎罚”几条而已。其中真正有实际意义的只是前两条,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轻徭薄赋。就是说,儒家所重的“民”不是所有的“民”,而是安分守己、能够为国家提供赋税的“农”民。这就是为什么自汉朝以后,儒家不遗余力地鼓吹抑制工商的“崇本”政策。比较一下孟子的“反本”之论和贾谊的“崇本”主张,我们就会明白“民本”与“农本”是曲径相通的。
《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新书·瑰玮》: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於本,则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民安性劝业,而无县愆之心,无苟得之志,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乐也。
“夫本者,农也。农者,民也。”其实董仲舒早道出了“民本”与“农本”的关系。“民本”不是一种权力宣言,而是一种深邃的秩序安排:最终的“本”是土地,“民本”主张落实下去就是要把民众变成附着于土地的农奴,成为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政治秩序的构成者。
我们知道,附着于土地上、匍匐于大自然意志之下的小农是封建社会秩序最稳固的部分,也是以专制君主为中心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和心理基础,因而对小农经济的维护便同时具有了一种政治和伦理意义:安分与勤恳既是致富的惟一途径,也是遵礼守法的表现,立命安身的美德——因为这意味着对天然秩序的维护和顺从。在专制主义社会里,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尊严就建立在小农的安分和顺从上。可以说,“以民为本”是一种战略性投资,投资人所追求的利润回报是被投资者本身成为秩序的表达者。
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民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修辞术:它是一种凸喻(注:尼采对凸喻的定义是:“将意蕴深长的辞语置于居子之首或尾而产生的强调”(《古屠友祥译《古修辞学描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页)。本人的用法有所不同。),强调的只是事物的某个方面,它是用一种外在的光对某个完整意义的部分进行的照亮。“民本”强调的并不是“民”自在自足的价值,而是它对于国家社稷,归根结底是对于君主的意义。因而,说穿了,“民本”就是“君本”,是“君本”的修饰性转义表达。
还有,我们不应忘记,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不是苏格拉底式的独立思想家,而是奔走于列国之间推销其政治学说的游说者,他们言说的对象是各国君主,这就决定了他们所有“重民”、“保民”的治国主张,首先是设身处地为君主进行的政治策划,它不可能走到君主的对面而成为现代民主的生发者。并且,“民”只是一个大类名,表征着一个整体性抽象存在,而凡是抽象的巨大存在都容易被僭取作高尚的名义和旗号。通过自立为“民”的代表,儒家增强了自己对君主说话的分量,扩充了参与权力的资本。
[收稿日期]2003年3月
标签: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孟子论文; 国学论文; 君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