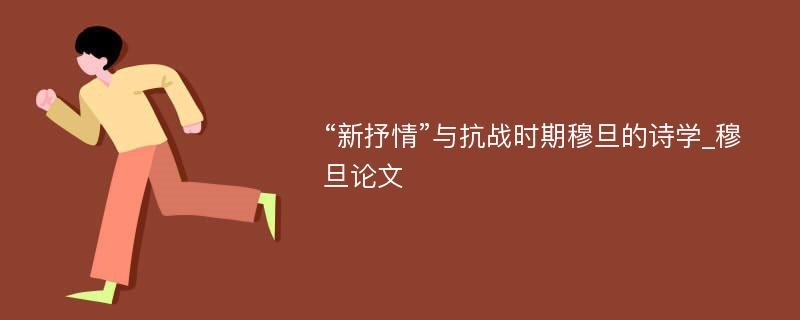
“新的抒情”与穆旦抗战时期的诗学主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诗学论文,抒情论文,穆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3)06-0038-04
在穆旦(1918-1977)生前和身后公开发表过的文字中,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文章极为少见。这可能表明穆旦不是一位长于理论表述的诗人,至少不是一位热衷于理论建设的诗人。在创作和理论二者之中,他似乎更注重前者。这一特点既表现在他40年代的表述中,也为他同时代的评论家所注意到。(注:穆旦在评论艾青关于“诗的散文美”的主张时表示:“而这就比一切理论都更雄辩地说明了诗的语言所应采取的路线。”见《大公报·综合(香港版)》1940年3月3日。另外,穆旦的同学和师友王佐良在《论穆旦的诗》中谈到:“他注重创作实践,对于理论家们不甚理会,自己也没有谈过诗学。”见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这和他所喜爱并有所师承的T·S·艾略特非常不同。
总的来说,穆旦是一流的诗人和诗歌文学翻译家而不是诗歌理论家,从以往对穆旦的研究论文中也极少看到对其诗学观念进行考察的内容。但无论如何,这决不意味着穆旦没有自己的创作观和诗学主张。如果要考察、索解穆旦在抗战时期的诗学追求,至少有两篇写于1940年的诗评文章不容忽视。两篇文章的出发点似乎只是分别对艾青、卞之琳抗战时期诗歌的批评,实际上却是通过批评提出了穆旦本人的诗论,因为它们十分鲜明、确切地表明了作为诗人的穆旦在抗战时期具有独特理论意义的诗学观。这两篇诗评分别是《他死在第二次》和《<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均写于1940年初的昆明西南联大校园,又先后发表在同年《大公报(香港版)》的“文艺综合”栏内(3月3日和4月28日)。但是在上世纪出版的有关穆旦的文献中,却一直见不到这两篇文章的全貌,而且似乎也没有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注:1996年9月,李方编《穆旦诗全集》出版,但未收录穆旦的文论;1997年4月,曹元勇编《蛇的诱惑》由珠海出版社出版,除穆旦诗选外,第一次选编了穆旦的文论和书信,但仍未收入这两篇文章;直到1999年10月,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编“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之一、梦晨编选的《穆旦代表作》才将这两篇文章作为穆旦的文论收入。笔者所用这两篇文章,《他死在第二次》的手抄件由李方先生提供,《<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的复印件则由朱少璋先生提供。)上世纪80年代以来,穆旦研究一时成为一门“显学”,但缺乏对穆旦诗学理论的关注,大约也和对这两篇文章重视不够有关吧。
两篇诗评的批评对象不同,但理论支点却又高度地保持一致,因而比较完整地传达出穆旦这一时期对诗歌创作的主导看法,至少是他对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论点。而这个重要论点,以往一直被严重地忽视。
穆旦首先对艾青的创作倾向发出了由衷的称赞。在《他死在第二次》这篇评论中,穆旦实际上是以艾青作为他的一个最圆满的论据,论证了他本人对抗战和抗战时期诗歌发展方向的论点。这篇评论的要点包括:1.抗战使疲弱的、病态的土地获得新生,这一主题在艾青诗中得到充分表现;2.如同惠特曼歌颂新兴的美国,艾青歌颂的是新生的中国,艾青的诗具有“本土化”特征;3.艾青的诗“是光明的鼓舞”,艾青是新生中国健壮的歌手;4.艾青以真实的生活做背景,以博大深厚的情绪涂写出真实、纯朴的图画,刻画出简单质朴的人格、牺牲精神和心理状态;5.艾青的诗有着“清新的爱慕的歌唱”、“高度的斗争的热情”、“擦过了一切艰苦的、胜利的信念”、“美丽的史诗”、“Herry James和Marcel Proust”式的心理刻画;6.艾青“诗的散文美”的主张“是此后新诗惟一可以凭借的路子”。随后,穆旦又评论了抗战时期另一部个人诗集,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在更为开阔的背景下讨论了抗战时期现代诗所应坚持的发展方向。如果说在前一篇评论中穆旦还只是以肯定艾青而较为隐晦地表示出自己的诗学主张,那么在后一篇评论中穆旦的态度就十分明朗地从正面提出来了。他把这种主张概括为“新的抒情”。
值得思考的是,穆旦是在英美诗坛盛行“机智”而国内诗坛也有人提出“放逐抒情”的背景下提出“新的抒情”这一不同寻常的诗学观念的。考虑到穆旦所置身的现代文化背景,这就似乎意味着“抒情”这个传统诗学概念的内涵将必然有着新的内容和对它的诠释。
事实上正是如此。在《<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这篇诗评中,穆旦没有像评论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那样单刀直入地切入批评,而是首先从个人的角度旗帜鲜明地立论,提出了在抗战背景下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方向。他从诗与社会、时代同步发展的观点出发,解释了英美现代诗玄学诗风盛行和抗战前卞之琳将这种诗风引入中国诗坛的社会原因。接着,穆旦分析形成这种诗风的社会背景。随后,他肯定了卞之琳在30年代将这种“机智”引入他的《鱼目集》同时也是引入中国诗坛的诗学意义。认为:“《鱼目集》第一辑和第五辑里的有些诗,无疑地,是给诗运的短短路程上立了一块碑石。自‘五四’以来的抒情成分,到《鱼目集》作者的手下才真正消失了……”[1]然而在穆旦看来,卞之琳的“机智”诗风是与他所表现的时代特征相协调的,或者说是特定的生活内容决定了特定的写作方式。这里表明了穆旦潜在的“创作与生活同步”的诗学观念。就此而言,穆旦和徐迟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同样面对抗战的时代背景,他却没有简单化地对徐迟“放逐抒情”的观点作出呼应,反而提出了“新的抒情”这一与“放逐抒情”有明显不同的诗学主张。
为什么同样的抗战背景,会使两个都具有现实关怀和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得出不同的诗学结论?所谓“放逐抒情”和“新的抒情”各自的现实依据是什么?而穆旦“新的抒情”又包含哪些具体内容?
在徐迟看来,无论是“西洋的近代诗”还是中国抗战时期的诗,其所以“放逐抒情”,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科学”的发达和“时代变迁”导致人类离开“大自然”而走向“都会”,使得“抒情确已渐渐地见弃于人类”,在“这个时代里,生命仅是习惯,开始没有意义了”。这就使英美诗坛艾略特以来的诗人“放逐抒情”成为一种必然。而中国的社会背景又有不同。由于抗日战争的“范围与程度之广大而猛烈,再三再四地逼死了我们的抒情的兴致”,因此出于“建设”的目的,也应当“放逐抒情”,“至于这时代应有最敏锐的感应的诗人,如果现在还抱住了抒情小唱而不肯放手,这个诗人又是近代诗的罪人。”[2]
如果说“放逐抒情”的前提是“无情可抒”,那么需要论证的首先应该是抗战期间究竟有否“抒情”的社会条件和心理条件。从徐迟的论点来看,显然他是否认具备这些条件的。然而他的论证却有不够严密之处。第一,徐迟对“抒情”的理解未免过于狭窄。徐迟在《抒情的放逐》中讲道:“因为千百年来,我们从未缺乏过风雅和抒情,从未有人敢诋辱风雅,敢对抒情主义有所不敬。可是在这战时,你也反对感伤的生命了。即使亡命天涯,亲人罹难,家产系数毁于炮火了,人们的反应也是忿恨或其他的感情,而决不是感伤……”[2]在这里,徐迟似乎把“抒情”仅仅理解为“感伤”与“风雅”,那么,除了“感伤”和“风雅”,“忿恨或其他的感情”就不算“抒情”了吗?第二,徐迟对“战争”给予中国的影响存在判断失误。如果“轰炸已炸死了许多人,又炸死了抒情”,也只能说炸死的是“风雅”与“感伤”的消极情感,但另一方面,战争又是一次“摧枯拉朽”、焕发民族再生勇气的最佳机遇。就是说,战争在放逐“感伤”与“风雅”的同时,也可以激发强烈的积极情感。用徐迟自己的话说,“而炸不死的诗,她负的责任是要描写我们的炸不死的精神的”[2],所谓“炸不死的精神”不正是一种积极性的情感吗?
穆旦正是在意识到徐迟论断不够周全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抒情”这一与“抗战”背景更为“契合”的诗学主张的。
他的论据是:一、“‘七七’抗战以后的中国则大不同前。‘灰色的路’现在成了新中国的血管,无数战士的鲜血,斗争的武器,觉醒的意识,正在那上面运输,并且输进了每一个敏感的中国人的心里。‘七七’抗战使整个中国跳出了一个沉滞的泥沼,一洼‘死水’。自然,在现在,她还是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泥污的,然而,只要是不断地斗争下去,她已经站在流动而新鲜的空气中了,她自然会很快地完全变为壮大而年轻。”[1]二、卞之琳的《鱼目集》那些“没有抒情的诗行是写在1931和1935年之间,在日人临境国内无办法的年代里,如果放逐了抒情在当时是最忠实于生活的表现,那么现在,随了生活的丰富,我们就应有更多的东西”[1]。这里实际上包含着一个清晰有力的推理过程:其一,(1)诗歌是抒情还是放逐抒情取决于生活的要求(大前提)。(2)在“七七”前“日人临境国内无办法的年代”,放逐抒情“是最忠实于生活的表现”(小前提)。(3)《鱼目集》之“放逐抒情”适应了生活的要求(结论1)。其二,(1)诗歌是抒情还是放逐抒情取决于生活的要求(大前提)。(2)“七七”后“新生起来的中国”不同于《鱼目集》所表现的时代,“战士的热血,斗争的武器,觉醒的意识”正在从前“灰色的路”上运输(小前提)。(3)“那么现在,随了生活的丰富,我们就应有更多的东西”(结论2)。
那么,这“更多的东西”是什么呢?穆旦接着从正面提出了他的论点:
一方面,如果我们是生活在城市里,关心着或从事着斗争,当然旧的抒情(自然风景加牧歌情调)是仍该放逐着;但另一方面,为了表现社会或个人在历史一定发展下普遍地朝着光明面的转进,为了使诗和这时代成为一个感情的大谐和,我们需要“新的抒情”。
《<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1]
穆旦并没有完全否定“放逐抒情”的观点,但他的论点的重心却是“新的抒情”。然而这“新的抒情”又并非是对传统“抒情观”的简单化回归,尤其不是对“自然风景或牧歌情调”(穆旦语)或者“风雅”、“感伤”(徐迟语)的迎合。穆旦强调指出:
这新的抒情应该是,有理性地鼓舞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我着重在“有理性地”一词,因为在我们今日的诗坛上,有过多的热情的诗行,在理智深处没有任何基点,似乎只出于作者一时的歇斯底里,不但不能够在读者中间引起共鸣来,反而会使一般人觉得,诗人对事物的反映毕竟是和他们相左的。
《<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1]
在这一段话里,穆旦表明了他“新的抒情”论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理性”,二是“鼓舞性”,三是“理想性”。由此,“理性”、“鼓舞”、“光明”构成了“新的抒情”论的三个关键词。如果说“鼓舞性”和“理想性”仍然属于传统的浪漫主义理论的因素的话,那么将“理性精神”注入“抒情”,就很难再把这种“抒情”称为“浪漫主义”了。而正是在这里,表现了穆旦作为一个清醒的现代诗人的超越性。
正如在《他死在第二次》中把艾青作为他诗论的一个圆满论据那样,在《<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这篇评论中,穆旦再一次对艾青抗战以来的创作发出了由衷的称赞。他把艾青的《吹号者》视为他的“新的抒情”理论“在现在所可找到的较好代表”。他由这首诗“情绪和意象的健美的糅合”、“离开了唯美主义以及多愁善感的观点”而“化进战士生活的背景里”的“自然风景”诸特点,生发出对“新的抒情”论进一步的期望和阐释:
所以,“新的抒情”应该遵守的,不是几个意象的范围,而是诗人生活所给的范围。也可以应用任何他所熟悉的事物,田野、码头、机器,或者花草;而着重点在:从这些意象中,是否他充足地表现出了战斗的中国,充足地表现出了她在新生中的蓬勃、痛苦和欢快的激动来了呢?对于每一首刻画了光明的诗,我们所希望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抒情”。因为如果它不能带给我们朝向光明的激动,它的价值是很容易趋向于相反一面去的。
强烈的律动,洪大的节奏,欢快的调子,——新生的中国是如此,“新的抒情”自然也该如此。
《<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1]
穆旦与艾青,通常似乎很难将他们的名字并列在一起论述。因为推崇艾青的评论家往往强调其现实主义的抒情趋向,推崇穆旦的评论家则往往强调其现代主义的诗学基点。曾经接受过象征主义诗学影响的艾青后来对4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风似乎也缺乏热情。但是通过穆旦对艾青的高度评价,我们却十分容易地发现了二人诗学观点的共同点,那就是一种具有理性化特征的深度抒情模式。在艾青那里,“深度抒情”常常表现为“深沉”、“忧郁”的情感特征;在穆旦那里,“深度抒情”则表现为思想者的沉思、鲁迅式的犀利、外科手术师一般的冷静与深情。不同的是,穆旦更自觉、更凝重、更深厚,忠于时代而又勇于超越时代。在《赞美》中,即使是热烈的“赞美”,也同时保留着对生活的深度思考和询问:“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许多孩子期待着/饥饿,而又在饥饿里忍耐,/在路旁仍是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一样的是不可知的恐惧,一样的是/大自然中那侵蚀着生活的泥土……”
对于忧患深重的中国人来说,抗战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同时也可能是挣脱枷锁、争取新生的历史契机。抗战给国人带来的,是流亡、屈辱、受难,但也是兴奋、热情与抗争。然而正像从事任何伟大的事业一样,仅有热情而缺乏深厚的理智是不行的。而抗战文学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恰恰是“在理智深处没有任何基点”而又“过多的热情的诗行”的泛滥。浅层次的热情往往导致理性精神的缺失,这也是国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大概这也是艾青诗歌浓重的“忧郁”色调不被理解的深层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说,穆旦之对于艾青的发现与高度评价,倒也是40年代新诗批评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当然同时,令新诗批评界感到意外的应该是,穆旦在实施批评职能的时候,也给新诗理论提供了新鲜的内容——“新的抒情”。
“新的抒情”是抗战时代催生出的、具有穆旦个人创造性特征的诗歌理论,其理论渊源则直接来自英美现代诗坛、特别是T·S·艾略特的知性诗学主张。尽管两个诗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而且穆旦又特别标举与抗战形势相协调的“抒情”,这就与艾略特以来的知性诗学理论产生了明显不同。但由于穆旦在西南联大对艾略特诗学的接近,其“新的抒情”主张中的“理智”成分显然还是与艾略特反对浪漫主义、主张“非个人化”的立场有紧密的关联,而艾略特的理论又来自他对17世纪玄学派(Metaphysical poetry)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重新发现,这使得穆旦等40年代重视知性的中国青年诗人和欧洲玄学派传统有了间接联系。只是穆旦并未照搬艾略特或者多恩,他从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形出发,提出了富有创造精神的自己的诗论。
除了对“理性”、“理想”、“鼓动性”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对“理性”精神的强调,穆旦也对“新的抒情”所应有的外在文体特征作出热烈的期待,他用“强烈的律动,洪大的节奏,欢快的调子”来概括这种期待。而他分别以艾青和卞之琳的抗战诗为例证,进一步论述了他所理解的“新的抒情”的文体要求。正如前面所说,他称赞了艾青的《吹号者》,肯定了艾青“诗的散文美”的诗学主张。而对卞之琳《慰劳信集》的批评却是:“‘新的抒情’成分太贫乏了。这是一个失败。”“这些诗行是太平静了,它们缺乏伴着那内容所应有的情绪的节奏。”针对这一问题,穆旦提出了他的看法:
这些“机智”仅仅停留在“脑神经的运用”的范围里是不够的,它更应该跳出来,再指向一条感情的洪流里,激荡起人们的血液来。诗人的善于把“机智”放在诗里,也许有时是恰恰麻木了情绪的节奏的,然而也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如此。“机智”可以和感情容受在一起,也有的时候,自然,顶好的节奏可以无须“机智”的渗入,因为这样就表示了感情的完全的抒放。
《<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1]
在对艾青、卞之琳的抗战诗作进行批评并提出“新的抒情”诗学主张的同时,穆旦也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着“新的抒情”论。他在抗战期间特别是1940年前后创作的《漫漫长夜》、《在旷野上》、《出发》、《五月》、《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赞美》等诗章,应视为对“新的抒情”理论的自觉实践。这些作品,有明显的艾青诗风的影响,却又充盈着新鲜的、独创的个人风格。一方面,是对新生的中国充满热情的礼赞;另一方面,这种礼赞又以深厚的理性精神为依托,而不致使这种礼赞流于表面化和庸俗化。理性与情感的深层次的交融使穆旦的抗战诗既富有感情的强度,又富有思想的力度。至于“强烈的律动,洪大的节奏,欢快的调子”,由于题材、情境的不同而在不同诗作中有着不同的表现,通过以上诗作也可以窥见。
综上所述,可以对“新的抒情”诗学主张作如下理解:
一、“新的抒情”论是青年时代的穆旦在特定的抗战背景下提出的诗学主张,具有时代背景的特定性。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下重提“抒情”,目的在于以“抒情”焕发、鼓动国人对民族复兴崇高理想的巨大热情。表达了穆旦对抗战和民族复兴的信念,对抒情主体的新的要求,以及对“抒情”这一传统诗学概念内涵的充实与提升。在中国的抗战时期,正是穆旦“新的抒情”的主张赋予了“抒情”以新的内容,激活了这个被浮浅的浪漫派诗人用滥、几乎成为“感伤”、“风花雪月”代名词的诗学概念。
二、“新的抒情”论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既有对传统诗学的继承又有个人创新性的有机统一理论。它由“鼓舞性”、“理想性”和“理性”三个基本内容构成,前两个内容使“抒情”既承续“抒情”的基本特征,又摆脱了个人性的“感伤”,后一内容使“抒情”增加了思想的力量,显示了穆旦的独创性。穆旦的意图是以理性精神来节制“抒情”,而又使“抒情”建立在理性而非“感伤”的基础上。由此,穆旦的“新的抒情”论实际上开辟了一种“深度抒情”理论,它既不同于某些左翼诗人以概念代替抒情的功利性诗论,也不同于浮浅的浪漫派诗人以个人的“感伤”代替抒情的宣泄性诗论。穆旦所强调的“理性”来自他所接受的欧美现代派“玄学”理论特别是“非个人化”论和“理智”论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简单化移植,而是创造性借用。
三、“新的抒情”论不仅重新肯定了现代诗的抒情功能,重新赋予“抒情”以新的内涵,特别强调了现代诗“抒情”中“理性”成分的重要性,而且还提出了对“新的抒情”论的文体要求,即“强烈的律动,洪大的节奏,欢快的调子”以及“诗的散文美”。同时,穆旦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新的抒情”论提供了具有典型性的文本,其抗战时期创作的《漫漫长夜》、《在旷野上》、《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赞美》等系列作品,不但是穆旦本人的代表作品,而且也是中国最好的抗战史诗。
四、“新的抒情”论是穆旦在评论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特别是艾青、卞之琳的抗战诗时提出的诗论,又是对20世纪英美诗坛“放逐抒情”论以及抗战时期国内诗坛“放逐抒情”论的积极而又辩证的反应。但由于以评论的方式出现,其观点没有得到更充分深入的展开和论述,故“新的抒情”论尚显得单薄、不系统;又由于当时穆旦还是一位知名度不高的诗人,故发表后没有引起诗歌理论界足够的重视。5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格局和文学思潮的变化,“新的抒情”论很快被淹没在历史的阴影里。80年代以后,穆旦诗歌中的现代主义质素备受推崇,而其抗战时期提出的“新的抒情”诗学主张却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和评价。出于对历史和诗人穆旦的尊重,这种现象应当结束了。
2003年4月6日 朝晖楼
收稿日期:2003-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