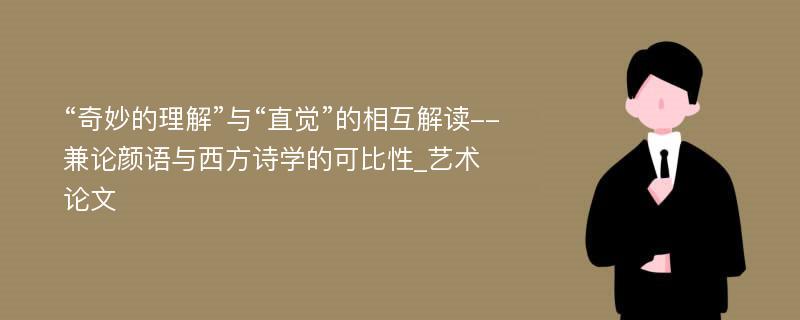
“妙悟”、“直觉”的互释性问题——兼谈严羽与西方诗学的可比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可比性论文,直觉论文,性问题论文,妙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5)06—0089—07
“妙悟”是严羽诗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美学史上禅、艺合流的内在理论基础。“直觉”是克罗齐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西方美学中的一个普泛性概念。虽然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直觉”一词,但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原本就是直觉、印象和感悟,这个传统潜在地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论接受西方直觉说的文化心理基础。本文试图从梳理“妙悟”、“直觉”各自在中西文论中的发展轨迹入手,结合“直觉”这一术语在中国的传译和演化,企图揭示“妙悟”与“直觉”之间所存在的互释性问题。由于这两个概念分别是严羽、克罗齐诗学的核心和基石,比较二者对我们认识严羽、克罗齐诗学的整体意义和具体形态具有积极意义。
一
中国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因此就其词语构成而言无论是“直觉”还是“妙悟”都不是其正传。“觉”尽管在佛教经典中大量存在,但以“直”来修饰“觉”之语词构成,据笔者阅读所及,在古典时期并不多见,至少在古典文论中尚未遇见。但中国古典文论的宝库中却有许多“直”字的出现,如钟嵘“直寻”、司空图“直致所得”,其“直”的理论意旨都指向审美感知的直接性。这些为20世纪文论界在翻译西方“intuition”时挑选“直觉”一词提供了语言、文化上的“既有知识”和“前在视野”。
与“直觉”同为偏正结构的词语构成,“妙悟”尽管在中国古典时期就已广泛流行,但其形成却与佛经传译联系在一起。据史载,“妙悟”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晋僧肇的《涅槃·无名论》里:“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僧肇之前,“妙”、“悟”在古典文论中基本上是以单个字眼出现。作为偏正式的词组,“妙悟”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在“悟”上,然而“妙”也不容忽视。“妙悟”不仅仅是佛教哲学的产物,也是老庄哲学的结晶。“妙”与“悟”的合一,与历史上庄禅的互相影响和融会贯通是相一致的。
在中国哲学史上,“妙”主要出自道家,《老子》第一章就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庄子·寓言》说:“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曰:‘自吾闻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九年而大妙。’”“众妙之门”与“大妙”相得益彰,均是道家求道、体道、悟道的至境。正是如此,我们可以说老庄哲学是“妙”这一范畴的古老源头。由于佛学的中国化,“妙”后来又成为中国佛教哲学的重要范畴。“妙悟”之“妙”因此打上了道、释两重烙印。“妙”的观念,自东汉开始进入美学领域,唐宋以来,“妙”在诗学话语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这恰与中国古代诗歌在庄禅文艺思想的影响下臻入化境的情形相吻合。朱自清先生在《好与妙》一文中列举了大量事实,发现“妙”总与“玄(妙)”、“神(妙)”、“微(妙)”、“妙(不可言)”等联用,它出于自然,归于自然,“不可寻求”、“不可以形诘”。[1] 其意与源于西方的现代概念“直觉”在许多层面上相通。
和“妙”这一深受本土道家学说熏染的范畴相比,“悟”主要渊源于印度佛学及中国化的禅宗。佛教一直有讲“悟”的传统,“悟”是指修行参禅时恍然大悟、洞见真谛的情形。到了中国化佛教禅宗兴起之后,“悟”进一步被推到“顿悟”的极致。“顿悟”说与艺术创造中“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灵感现象有相通之处,所以对中国古典文论影响极为深远。因此,深具直观性、神秘性、体验性的“妙”和指称恍然大悟、洞见真谛的领悟性的“悟”组合成词,本身就是在直觉领悟为主要特征的庄禅合流的产物。何谓“妙悟”?《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2](P12) “妙悟”乃诗的“当行”、“本色”,它与读书穷理做学问是不同的思维方式。“诗道”契于“禅道”,《除盖障菩萨所问经》卷十说:“此法惟内所证,非文字语言而能表达,超越一切语言境界。”就禅道而言,所要妙悟的是“见性成佛”之境,所用方法是“以心印心”。严羽既是诗禅相喻,我们可以禅道之妙悟来诠释诗道之妙悟,即在悟出诗的本质,其方法也应是“以心印心”,不落言筌,不涉理路。在艺术中惟“审美直觉”有此特征,即对诗性不可言传、不涉理路之直觉把握,它是一种审美能力的具体显现,一种经熟参而大彻大悟的境界。可见,严羽的“妙悟”说是其美学理论中突出审美主体、弘扬自我性灵的最具独创性的命题,其实质是突出“心”的作用。严羽最推崇的禅宗“正法眼藏”,就是指心悟心传的大法,他借用来特别强调审美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所谓“妙悟”,是强调心的悟入,“悟”是指心(审美主体)的一种把握美的特殊的直觉体悟或领悟状态。
二
“直觉”即西文“intuition”的中译。 要考察“直觉”与“妙悟”的互释性问题,就得弄清楚“直觉”概念在西方的形成过程及其在中国的传译。
在西方,从柏拉图到普罗提诺,“直觉”概念已经有了雏形。柏拉图认为诗人的艺术状态是凭借天赐的“迷狂”,而普罗提诺把审美感觉从一般感觉活动中区分出来,隐约可见直觉说的滥觞。中世纪文论受基督教哲学的孕育,把关注焦点从外部世界转移到主体内心世界。“这种强调美的感性和直接性的观点在后来康德和克罗齐的主观唯心主义美学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它就是美只关形式不沾概念说与艺术即直觉说的萌芽。”[3](132)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之“美的分析”里,从质、量、关系和方式四方面分析了审美判断的特性,认为美感是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是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这直接开启了克罗齐的审美直觉说。
关于直觉,克罗齐反复宣称:“艺术是什么——我愿意立即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艺术是幻象或直觉。”[4](P209) “简单地把直觉作为艺术的定义,就已经给艺术下了完整的定义。”[4](P229) “我们已经坦白地把直觉的(即表现的)知识和审美的(即艺术的)事实看成统一,用艺术作品作直觉的知识的实例,把直觉的特性都付与艺术作品,也把艺术作品的特性都付与直觉。”[14](P19) 直觉是最单纯的,是在知觉和概念之前的意识的活动,它的对象只是单纯的未经肯定的意象。作为一种心灵活动,直觉是赋予形式于本无形式的物质那种“心灵综合作用”。所谓“直觉即表现”,克罗齐认为,情感或事物在被表现以前,仅是一种感受和自然的事实,尚不具备形式,亦即无形为心灵所认识,只有心灵以主动的姿态去接近、综合、表现,赋予情感以形式,心灵才能对情感起直觉。直觉与表现,从发生角度来讲,是同时的,情感在被表现的同时心灵即已直觉。反过来,心灵在直觉的同时亦完成了表现。“此出现则彼同时出现,因为它们并非二物而是一体。”[4](P15) 形诸符号并不是表现,而只是以物理的操作手段将艺术记录下来而已。
由此可见,以克罗齐为代表的西方直觉主义者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把“直觉”与概念活动区分开来,二是强调直觉活动的“心灵综合作用”,三是主张“直觉”的纯粹审美感知活动,西方的纯艺术精神大多坚持直觉主义。克罗齐及其西方的“直觉”说的上述特征,就与我们前面论述的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讲究“心悟心传”的中国“妙悟”诗学具有较大的相似之处。正是这些相似之处,为我们探究“妙悟”与“直觉”的互释性提供了坚实基础。
一个值得寻味和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西方“直觉”这一概念及其所蕴涵的思想传入中国时,人们最初翻译“intuition”时, 为什么选用了中文“直觉”这一语词!与“悟”主要源于佛教禅学一样,“直觉”之“觉”也主要见于佛教经典,而且“觉”与“悟”意义大体相当,现在流行的“觉悟”一词,有自来焉!而且“妙悟”与“直觉”在语词构成方式上完全一样,都采偏正结构!但与“妙悟”流行于中国古典诗歌批评(尽管也算较晚出)不同的是,“直觉”一词不见用于中国古典诗学。
1905年,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谈到“intuition”的引入情形:“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试以吾心之现象言之,如‘Idea’为‘观念’,‘Intuition’之为‘直观’,其以例也。夫‘Intuition’者,谓吾心直觉五官之感觉,故听嗅尝触, 苟于五官之作用外加以心之作用,皆谓之‘Intuition’,不独目之所观而已。”“‘Intuition’之语,源出于拉丁之‘In’及‘tuitus’二语。‘tuitus’者,观之意味也,盖观之作用,于五官中为最要,故悉取由他官之知觉,而以其最要之名名之也。”[5](P102~104)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Intuition”进入中国学术界的时间大约是19、20世纪之交的数年,最初是从日本人的翻译传入的,译为“直观”。但王国维认为译作“直观”并不准确,虽然从词源上看“tuitus”具有观之意味,但“Intuition ”的语义不仅指眼之观看,甚至也不仅指五官之感觉。他明确指出,五官之作用外还要加上心之作用即心的综合,才可谓“Intuition”。
中国文论对“直觉”的接受与传播有其特殊的语境。一方面,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原本就是直觉、印象和感悟,从庄子的“目击道存”到王夫之借用佛教概念而标举的“现量”,从钟嵘的“直寻”到王国维的“不隔”,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凸显出一条重视直接感知、兴会神到的传统美学追求。这个传统潜在地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论接受西方直觉说的文化心理基础。由于受道、佛影响下的文艺批评中的“妙”总与不可穷诘、不可智识、不可言传的直觉领悟联系在一起,现代学者常常以西方“直觉”概念对之进行诠释。如前述朱自清在《好与妙》一文中隐然以直觉观念来解释中国的“妙”,而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在其英文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则以西方“intuition”阐释中国文论的形上传统,把老子的“涤除玄览”、 庄子的“听之以气”解释为清除心灵中的理性知识,而以直觉的方式静观自然与道合一,并译“神思”为“intuitive thinking”。在译“妙契同尘”、“妙造自然”的“妙”时,刘若愚开始选用“wonderfully”,但认真思考则觉得不妥, 最后敲定为“intuitively”,颇为得意。[6](P47) 事实上,从老庄对道本体的体悟到佛禅的反智主义,从刘勰的“神思”到严羽的“妙悟”,都标举直觉领悟的艺术精神。这正是中西文论的某种相通且可彼此解释之处。
三
正如文学批评史家方孝岳先生在三十年代所说,“‘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7](P227) 严羽以“妙悟”为核心的诗学思想本身就是外来佛学与中国本土思想化合后的产物,在中西文化大碰撞、大交融的二十世纪,严羽诗学的阐释与研究自然也就开始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由于严羽诗学的理论重点在于对诗歌的审美活动特殊规律的探讨,在于阐明不同于“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这些沦为“诗道”之“厄”的“别材”“别趣”,[2](P26) 而西方秉持直觉主义的理论家们也在执着地探寻那些使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美之所以为美的因素,并力图把审美活动(包括艺术活动)与人类其他精神活动区分开来。这些构成了严羽诗学和西方一些美学思想具有可比性最深层、最重要的基础。
最早把严羽与西方沟通、对照的是钱钟书先生。他在写于战时、初版于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的《谈艺录》一书中,把法国神秘主义诗论家白瑞蒙等《诗醇》学派与沧浪诗学主张进行沟通,发现二者“盖弘纲细节,不约而同,亦中西文学之奇缘佳遇也哉。”并盛赞“仪卿之书,洵足以放诸四海、俟诸百世者矣。”[8](P276) 50~70年代,在大陆处于对外相对封闭、文化独尊的状态时,台湾学者张健在其著《沧浪诗话研究》以其跨文化的广阔视野将严羽的诗论体系与国外的理论进行多方面的比较阐发:“入神”说与伯格森的“直觉”、“妙悟”说与马拉美的“境界”、“兴趣”说与克罗齐的唯心论美学及海兹立特的“韵味”等等,[9] 尽管其中不少牵强的比附,但却展示了严羽诗学广阔的理解途径和宽广的意蕴。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比较文学、比较诗学在中国的勃兴,加之严羽诗学本身和西方一些美学思想具有可比性的内涵,遂出现了一批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阐释严羽诗学的论家。
八十年代以来较早论及严羽诗学与西方比较的是曹顺庆。他拿来与严氏“妙悟”说进行平行比较的西方理论是柏拉图的“狂迷”说,探讨的是“中西灵感思维的异同”。[10](P157) 早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古代文论研究热潮中, 就有不少人把严羽的“妙悟”解释为艺术灵感,而以“狂迷”与“妙悟”对举,则始于曹氏。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一比较在可比性上留下较大空当,但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而且曹氏在本章最后“特别指出”:“严羽的‘妙悟说’并不完全是论灵感”的,[10](P196) 表明曹顺庆只是就“妙悟”说的某一层面的内涵进行中西诗学的沟通,这体现了他的客观和审慎。略约同时,韩湖初把严羽与康德联系起来作比较,发现他们在纯粹的审美判断上的契合。[11] 之后,陈良运尝试将严羽的“无迹可求”之说与瓦雷里的“纯诗”理论进行比较,认为中国诗人和诗论家在西方文艺复兴初现曙光之时,就有了自己相当成熟的“纯诗”理论和实践,只不过理论术语的表述不同而已。[12]
在以范畴为中心的中西比较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一书,其中一些章节牵涉到严羽诗学。执笔者李春青将严羽的“别材、别趣”说与康德的“美的艺术”说比较,分别从三个方面阐释了他们在文艺审美特征问题上的相近性,即艺术的审美特征与理性知识的关系、对艺术本体的认识、对艺术活动审美直觉性的肯定。而严羽与康德美学思想的差异性在于: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严羽研究诗歌理论,目的在于总结诗歌创作经验和规律,并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康德研究美学问题是为了解决人的认知系统与道德系统的关系问题;研究方法不同,严羽的方法主要是经验归纳,是从形而下的经验上升为形而上的观念,而康德恰好相反,他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哲学思辨;研究的层次不同,康德是从主观角度、在人的审美能力与其他诸种精神活动、心理机能的联系中来考察人的审美心理的。这一点是严羽不能企及的,他只是对诗歌的审美属性和诗歌创作的独特心理进行反思。[13](P395~P415) 另一执笔者陶水平则将严羽的“兴趣”说与20世纪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说进行平行比较,虽然两人所讨论的艺术门类不同,一个讨论的是语言艺术,一个讨论的是视觉艺术,但他们在艺术的审美本质问题上,都主张纯艺术理论。二人在艺术美的根源问题上,又有着实质性的不同,贝尔的学说反映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它与西方形式主义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严羽的“兴趣”说则具有浓厚的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受到中国道家哲学和经过道家改造的禅宗哲学的深刻影响。[13](P417~P431) 九十年代末,陈伟军则撰文全面比较分析了严羽与秉持直觉主义的克罗齐诗学思想的异同。[14] 他的论题与本文较为接近,但主要偏重于两者的平行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严羽与西方比较的学术历史的回顾与考察,我们发现严羽诗学确实具有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互释的宽广意蕴。这些研究坚定了我们在“直觉”与“妙悟”之间进行互释的可行性;而在上述众多的比较中,又总离不开“直觉”、“艺术思维”、“纯诗”、“纯艺术”、“纯粹审美判断”,这些则启示了这一沟通、互释的可能方向。
四
克罗齐的“直觉”说是通过朱光潜介绍到中国来的,朱光潜在接受之初,对直觉的理解是停留在反映论上,直到他进一步熟悉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翻译了克罗齐《美学原理》的部分后,才在中国本土思想与克罗齐美学之间找到沟通的渠道。他说:“诗的境界突现都起于灵感。灵感亦并无若何神秘,它就是直觉,就是‘想象’,也就是禅家所谓‘悟’。”[15](P52) 可见,克罗齐“直觉”理论在中国的传译者朱光潜也隐约把“intuition”与中国的“妙悟”联系起来理解, 这就意味着中西文化和美学相互吸收和交融的可能性,也说明了人类共同的审美心理积淀使得中西方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本原上的一致性。依据上述对“妙悟”、“直觉”说的阐发,我们可以在如下方面对两者进行互释:
一、“妙悟”与“直觉”均揭示了审美和艺术活动不同于其他意识活动的特殊性,强调了艺术的感性功能。整部《沧浪诗话》主要是针对北宋以来诗坛上弥漫的一股“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风气有感而发,其着重区分“妙悟”与“学力”、“别材”“别趣”与“读书穷理”的不同,强调的是一种对意义的直觉领悟,根本不涉及任何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思维形式。与之“貌异心同”,克罗齐的直觉理论也是有感于“在十九世纪的哲学中,谢林和黑格尔把艺术同宗教、哲学等同或混淆起来;泰纳把艺术同自然科学混淆起来;法国真实主义者把艺术同历史证据的研究混淆起来;侯巴特的形式主义则把艺术同数学混淆起来”[4](P218~219) 的倾向而阐发的。克罗齐美学的根基就在于把直觉知识和逻辑知识对立起来,把前者与艺术合为一体,这与严羽“诗道亦在妙悟”的主张是可以并比的。
二、“妙悟”与“直觉”均强调审美和艺术主体在创造中的决定作用,揭示了审美主体在艺术直觉活动中不通过理性、逻辑、认知而洞见本真、直契本原的特征,接触到艺术创造的心理奥妙和美学规律。严羽及其影响所自的佛教禅悟,提出“以心印心”、“心悟心传”,提倡对微言妙谛不可言传、不涉理路之领悟、意会,所成就的是一种审美直觉的具体显现。佛教教义也注重人的悟性,讲究“慧根”、“正法眼藏”,受其影响,严羽重“真识”、“金刚眼睛”,他的“妙悟”说便是其美学理论中突出审美主体、弘扬自我性灵的最具独创性的命题,其实质是突出“心”的作用。
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有这样的结论:“现象之后有一个本体,现象可徒凭感官接受,本体则须凭理智领悟。”[16](P373) 于是就有了现象与本体,感官与理智的区分问题,也就是心物关系的问题。为了打破这一影响长久的心物二元论,克罗齐认为直觉就是对无形式的物质赋形造相,直觉品才是物质,直觉外无物质,这样就把物统一于心,而不存在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克罗齐的直觉说强调以心统物,极力强调人的主体性,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把主体的地位提到了极至。克氏美学中那种赋予物质以情感、形式的“心灵综合作用”,与严羽“妙悟”说提升“心”的作用的思想是可以并比互释的。
尽管“妙悟”与“直觉”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相似之点可以“互释”,见出中西文论共同的美学规律;而不同处则能“互补”,为建设“普遍的文学理论”(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提供启示和参照。
一、克氏的“直觉”说有其泛美学色彩,而严羽的“妙悟”说则主要论述诗的审美特质,这一不同就导致了后者主张悟性因人而异,诗人“悟”的程度如何,直接影响着作品质量的优劣高低;“直觉”说则否认彼此之间存在质的分野。与佛教哲学所说“利根”、“钝根”一样,严羽区分了“悟有分限,有浅深”,“透彻之悟”与“一知半解之悟”甚或“不悟”的高下差异。有人饱学诗书而导致以才学为诗,其创作成就反而不如学力不深的“一味妙悟”者。而克罗齐的“直觉”说则认为每个人都有直觉活动,所以实际上每个人均有几分是艺术家。艺术的活动并不限于号称“艺术家”的人们在“创作”时才进行,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多少都有审美的活动和艺术的活动,只不过普通人未能将心中已经直觉到的艺术以技术或物质手段记录下来而已。大艺术家和我们平常人在这一点上只有量的分别,而没有质的分别。克罗齐曾言:“‘诗人是天生的’一句成语应该改为‘人是天生的诗人’;有些人天生成大诗人,有些人天生成小诗人。天才的崇拜和附带的一些迷信都起于误认为这量的分别为质的分别。”[4](P22) 克氏的这一观点使其“直觉”说带上了浓厚的泛美学和泛艺术论的色彩。[14]
二、“妙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诗人“熟参”前代优秀诗歌,从而领会诗歌创作技巧,把握创作规律,提高艺术修养;而克罗齐则由于其直觉一方面超越了“直觉前”的感受之流的干扰,一方面又超越了“直觉后”的逻辑的、经济的、伦理的、传达技术的约束,因此强调了直觉的绝对纯粹性和艺术家的天生性。
严羽一方面强调了“妙悟”与“学力”、“别材”“别趣”与“读书穷理”的不同,但同时又主张诗人“见诗”要“广”,“参诗”要“熟”。他说:“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之为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2](P1) “熟参”与“妙悟”是两个互相不同而又有联系的过程。“熟参”历代优秀作品从而积累起深厚的艺术经验,这些艺术经验是诗人“妙悟”的重要基础。艺术经验是诗人积淀在心理深层的精神结晶,当“妙悟”展开时,它就作为一种潜意识存在而不自觉地参与艺术思维过程之中。严羽强调“熟参”历代诸家名诗,“酝酿胸中”,其目的即在提高、丰富、加深诗人的艺术经验,为创作之悟的顺利展开创造条件。如果说克罗齐主张“直觉前”、“直觉后”的诸种活动均应排斥在艺术活动之外的话,那么严羽诗学则做足了“悟前”、“悟后”的文章,正所谓“悟外更有事在” 明人胡应麟云:“严氏以禅喻诗,旨哉!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棒喝怒呵,无非至理;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禅必深造而后能悟,诗虽悟后,仍须深造。”[17] 钱钟书先生对此更有会心之阐发,他在《谈艺录》中言:“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并引宋人陆(桴)亭言:“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断,悟头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击不已,火光始现。然得火不难,得火之后,须承之以艾,继之以油,然后火不可灭,故悟亦必继之以躬行力学。”[8](P98~99) 钱氏的这一阐发,被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先生极力称道,认为“此说最为圆通,与一般空言妙悟或怕言妙悟者不同。”[2](P24) 严羽的这一思想及其后来的阐释、发挥,可补克氏理论之偏。
三、二者对于语言文字等传达媒介的态度有重大差异
“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是禅家的宗旨,既然“悟”要超言离象,那么是否是说文字语言对“悟”毫无作用可言呢?我们认为,在“悟”的闪光瞬间,固然没有语言文字横亘于其中,但在它的引发过程里,语言文字起着重要作用。对它的忽略,则导致对严羽“妙悟”说的片面理解。竺道生在《法华注》中说:“夫未见理时,必须言津。即见理乎,何用言为!其犹筌蹄以求鱼兔,鱼兔即获,筌蹄何施?”道生的意思是说,在没有体悟到佛教的真谛之前语言文字是津梁,是媒介物。这个媒介物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需的;而一旦得悟,文字概念又必须抛开,不能掺杂其间,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也。因此,以严羽为代表的中国诗学“妙悟”论者强调“不落言筌”,反对“以文字为诗”而不是不要文字而沦于无字天书,反对“参死句”、死于句下而同时主张“参活句”,使语言文字如盐溶于水,达到“透彻玲珑”、“无迹可求”的浑化境界。
而在克罗齐那里,在内心酝酿成直觉,这种在内心的表现活动,是心灵的艺术活动。但他把艺术活动仅限于内心的直觉活动,仅限于内心的表现,而把实际的表现活动(在纸上写诗,在画布上画画,在乐谱上作曲)看作是“外射”活动,外射活动的目的仅为保留直觉活动以便其重现,外射活动所产生的外射品(诗篇、书画、乐章等)并非艺术品。实际上,克罗齐是把实际表现活动排斥于艺术活动之外,把实际艺术品排斥于艺术之外,这与严羽的“妙悟”说对艺术本质的揭示是有很大不同的。
[收稿日期]2005—03—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