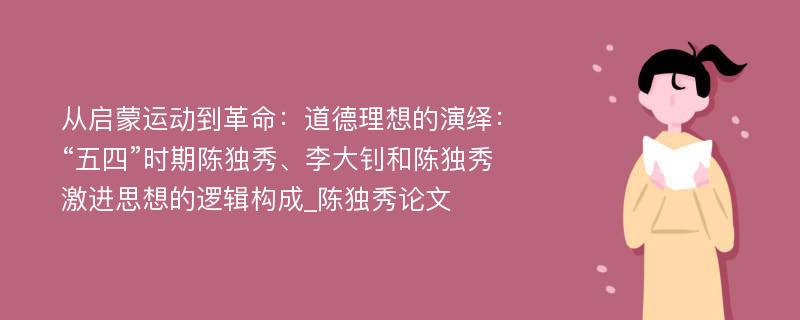
从启蒙到革命:来自道德理想的引渡——“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激进思想的逻辑构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论文,逻辑论文,陈独秀论文,时期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绪论:道德命题在革命中的位置
在进入本文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个看似与本题无关但却不可或缺的结论。因为这是笔者立论的基本前提:作为打过硬仗的“五四”阵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松散的思想“独联体”。在名目繁多的思想割据中有两个思想较为明晰的思想板块,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五四精神”在学术界依然歧义的原因。从胡适将“五四运动”说成是对“整个文化运动的一项历史的政治干扰”的观点来看,他是一位执着的思想解放守成者(注:胡适:《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在胡适看来,这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偏离了原旨。同是当事人的毛泽东之论断在大陆流行了近一个世纪:“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注: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北京〕《人民日报》1985年12月1日。)革命的逸出使“五四”多了一层意念,历史的“安排”也使我们只好历史地将这一精神事件分成真正的启蒙与另一种意义上的“启蒙”。因此,本文所说的启蒙属于立足政治层面的“直接”式启蒙,与立足于文化层面的“间接”式启蒙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里,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在历史学家所谓的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思想机制中,层出不穷的“新道德”为革命的循环与升级补充了足够的营养。
“革命”:来自道德理想“彼岸”的致命诱惑(上)
此岸,一个恶贯满盈的不可爱现实世界;彼岸,一个善意纷飞的理想国度。在中外古今的革命志士那里,带着憧憬、幻想,围绕从此岸走向彼岸进行设计一直是激荡于胸的主旋律。而正是在这样救星般为他人的“设计”中,道德成了“成人之美”的得力中介。可又有谁会想到,看似将人们带向理想国度的美丽天使竟在无情的历史演绎中充当了恶之花?18世纪的法国就有过这样惨痛的一幕,而20世纪的中国也自觉不自觉地复制了那惊魂未定的一页。
血雨腥风的辛亥革命并没有给国人以“代价”的启迪。相反,以《新青年》为大纛揭橥的“五四”却变本加厉地在革命那伤痕累累的伤口上挑“不彻底”的刺儿。陈独秀这位从革命丛林走出的老革命党人在文化的义旗下沉痛忏悔道:“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三次革命虽然流了血,但是还是流得不“充分”。若要将革命更进一步深入,伦理道德的“换血”举足轻重”(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1日。)。
回眸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新旧道德激战,先驱们有着共同的孔教革命之思想平台。而且,他们也都是看透了千年中国特有的伦理道德与政治体制的暧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革命逻辑就不是单纯的“以暴易暴”,同步的还有“以德易德”。在与旧的不道德不理想帝国告别之际,一个新的道德理想共和国已为先驱所沉醉。于是,“以仁易暴”的舆论也纷纷登场。世纪初年,邹容的《革命军》在“去腐败而存良善”、“有野蛮而进文明”的道德理路下不胫而走;陈天华的《猛回头》也是在卢梭那理想国的设计中石破天惊;辛亥革命的理论家也并不例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伴随着“冲决网罗”的道德砥砺,革命家的理论也别出心裁:他们不曾考虑怎样以少的代价获取大的进步,而认为代价与进步之间无条件地成正比。在他们心灵深处,“等价”换取构成了革命的内在逻辑。“五四”之前,这种以血洗污、购取进步的典型当推“为民变法,必先流血”的谭嗣同(注:《清国殉难六士传》,《知新报》第75册。)。这位热血汉子的殉道逻辑即是以血换得民族的生存。而当辛亥无量鲜血“购得伪共和”的代价已经成为事实后,激进的先驱们不但没有半点为自己“议价”的意思,反而仍在自我“代价”付出上再加一码——这是“货物买卖”式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注:李大钊:《东西文明之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这种“漫天要价”其实是对自我的“漫天加价”,其结果必然是在“舍得一身剐”的口号下连自由的依托都一同埋没与葬送。
从《新青年》主编那文乎其文、诗意浪漫的个性、自由等充满奶油味道的字眼中我们也不难咀嚼到其中潜在的“血雨腥风”。这是一块散发着奶酪香味的夹心“三明治”:“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幸福事功,莫由悻致。”(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1卷4号,1915年12月15日。)这就是幸福的来源之所在,为此我们看到的文化运动的“思想界明星”又是一个尚武意识十足的铁血之战的推崇者:“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以鲜血争自由,吾料其人之国终不沦亡。”(注:李大钊:《东西文明之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光荣革命”与温和的“忠告”都不在“话下”。只是在铁血与自由之间,陈独秀几乎划了一个等号。带着这种启蒙视角所启蒙起来的国民不可能不是一个混沌的群体。恰恰是在这方面,李大钊以及后起之秀毛泽东比陈独秀发挥得更充分。当李大钊的“调和”法则失效与毛泽东的温和之“无血革命”不达之际(注: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他们都在尚武而不“弃文”的政治启蒙中走向了“社会”。
在“西学”众多的资源宝库中,法兰西成为激进人士注视的焦点。迈过谭嗣同《仁学》中对“法人之改民主”的赞叹以及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对法国革命“民权主义”胜利的认同,陈独秀在“五四”初期对法兰西文明的顶礼膜拜态度已经足以让人警觉:“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注: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新青年》1卷1号,1915年9月15日。)在政治哲学意义上,这是一个先验论唯理主义传统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歧义。在胡适那里,他以导师身份指导的学生留学深造多选英国与美国,而陈独秀与李大钊的学生则是法国与俄国的居多。以本文我们选取的三位个案而言,他们在思想渊源上统属“血气方刚”一脉,行动特征则是师法宗俄。就思想的敏感程度而言,三人还呈现出接力棒式的“传承”色彩。从陈独秀的“唯法独尊”,到李大钊的“法俄综合”,再到毛泽东的“中国道路”,这是一个渐渐明朗与成熟的过程。在陈独秀那里,法兰西的文明无非是“人权”、“社会主义”、“生物进化”。在李大钊的意识里,俄法革命的不同则是“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不同。在对俄国表示了极大的欣喜与热望的同时,李大钊也没有忘记两种革命在不同世纪对世界所起的巨大作用,只是他认为在社会革命意义上说,俄罗斯的革命觉悟比前者单纯的政治革命更人道,更富有道德的普遍性。从他具有历史感的比较评论中,我们能充分感觉到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桐叶惊秋”的政治敏感:“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的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今之为俄国革命抱悲观者,得毋与在法国革命之当日为法国抱悲观者相类欤。”(注: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文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2页。)如果说孙中山从“自由、平等、博爱”的福音中找到了道德知音,那么陈独秀的感悟则在“自由、平等”之外添加了“独立”,而且将这一“伦理的觉悟”视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就在李大钊“漫卷诗书喜欲狂”之后:“人道的警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注: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03页。)年轻的毛泽东很快拥抱起留学法国的同乡蔡和森漂洋过海转来的“俄国方式的革命”。反观当年毛泽东为“当今之世”开出的救世良方:“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改变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注: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他从社会主义的空想到脚踏实地地“科学”实行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因为他心理清楚:“用和平的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注:毛泽东1920年2月日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于是,无论是陈独秀的道德论,还是李大钊的人道说,抑或毛泽东的伦理学原理,它们都在诱惑中发挥了强大的内驱力。
“道德”:“此岸”与“彼岸”的逻辑贯通(中)
以道德的旗号进行流血,这在伦理学上是不是道德的悖论呢?如果是,“五四”先驱又是这样进行逻辑贯通的呢?
众所周知,在《新青年》的前几卷里,除了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名分,道德的地位就是最显赫的了。问题是,“五四”的道德言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着超负荷的文化承诺,也正是这么个特征使它十分容易打通“仁”与“暴”之间的阻隔。
这是一种与理想结合得极为紧密的新道德。当初《新青年》的创刊宗旨就是为了能够塑造出具有新型觉悟的“新青年”。在创刊号上,主编开诚布公:“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国人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注:陈独秀:《答王庸工》,《新青年》创刊号,1915年9月15日。)青年的“修养”是新型的道德修养,国人的“根本之觉悟”是伦理的觉悟,也即是根本性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在陈独秀看来,“文明大进时代有文明大进时代之道德”:“愚固信道德为人类之最高精神作用,维持群益之最大利器,顺进化之潮流,革故更新之则可,根本取消之则不可也。”新的道德就是“平等、博爱、公共心”为代表的新觉悟,而故旧的道德则是“忠、孝、节、义”为代表的愚昧意识(注:陈独秀:《答淮山逸民》,《新青年》3卷1号,1917年3月1日。)。这样两种道德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以陈独秀为先驱的“五四”人士在新旧道德之间极尽挑拨之能事,在唤起它们之间的深沉怨恨之后,对两种道德作了“水火不容”、“取一去一”的“抽刀断水”式处理。本来,新旧道德之间的创造性转换可以说是一个社会良性循环的基本规律。而陈独秀对道德的“革故更新”完全是一种“大换血”式思路。
道德的地位决定了其在民主与科学之后成为重要的“第三者”。而道德的“大换血”又令人不禁要问:即使是在旧道德与新道德大换血的瞬间,会不会出现赖以维系社会的真空道德状态?按照如此绝对化的逻辑,道德真空的出现是不言而喻的。若是,“平等、博爱、公共心”等觉悟何以让先驱激情飞跃呢?这就要从“新”意丛生的“理想”寻找答案了。“新青年”是已经觉悟、文武双全的社会栋梁,旧青年则是不可理喻、不屑一顾的社会蛀虫。事实上,“新青年”觉悟的内容以及完全式的判断带有极其浪漫的乌托邦色彩。唯其如此,理想也才更容易在混沌模糊的无限膨胀中走向幻想的彼岸。道德理想的璀璨星空令先驱眼花缭乱,由此在新型的内圣式道德律令下结束了世俗与宗教、此岸与彼岸的冲突和对抗。这一逻辑的实行者在面对劣迹斑斑的不道德现实时,他们将本应“普度”的东西“引渡”到了“此岸”。在近代思想史上,借助道德的无限“心力”而“人定胜天”者不胜枚举。谭嗣同、章太炎的道德“心力”说如此,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的”理想国度充满向往的陈独秀不断质问匮乏理想的国人:“理想家那里去了?”(注:陈独秀:《理想家那里去了?》,《每周评论》第10号,1919年2月23日。)对罪恶已经被清扫得“干干净净”社会的想往的李大钊坚信未来“必是赤旗的世界”。在毛泽东,问题的根本即是怎样将一个“必是”世界改造出来。
由此,这就论述到了我们进一步要问的问题:为什么引发流血的暴力手段反倒冠冕堂皇地成为“仁道”的理论构架。对此,三位先驱的内在逻辑构成不谋而合,尤以李大钊“前后”阶段式的划分富有城府。在一篇专为暴力革命辩护的文章里,他以“欲扬先抑”的手法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作了铺垫。这一切都是在对“协和、友谊、互助、博爱”的褒扬中落定的:“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疑的道理。”既然是确信无疑的道理,那阶级竞争岂不就是一截多余的盲肠?其实,从笔锋的转变已经不难窥见一斑:“与这‘互助论’仿佛相反的,还有那‘阶级竞争’(Class Struggle)说。”注意,是“仿佛”而非“确信不疑”。为此,已经是“必然”肯定式判断的“阶级竞争”不但不是作孽的乱源,反而成了开满仁道花朵生命之树上不可或缺的绿叶。李大钊热衷革命的性情终于在1919年“爆发”:“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注: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第3卷,1919年1月5日。)他还表达了“互助的一半是阶级竞争”的判断:“这个大变化,就是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免的。”(注:在《阶级竞争与互助》这篇文章里,他还说:“竞争的法则,常是死亡的法则。协和的法则,常是生存的法则。”“有友谊是天堂,没有友谊是地狱。”而且,“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和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这时的李大钊已经“社会主义的道义”扛在了自己的“铁肩”上。他的理论武器也由过去的对抗“进化”论转化为“阶级”争斗论。不是为争斗而生存,而是为生存而争斗。李大钊革命逻辑中手段与目的清晰可见。在这样的思路里,革命焉有非仁道之理?
这,也与“我们的血不会白流”的“代价论”一脉相承。陈独秀、毛泽东等革命者的逻辑世界如出一辙。应该说,这是一个颇富激情的理性设计,问题在于“为生存而争斗”与“为争斗而生存”之间的意义界域在哪里。从“五四”的思想源头上说,这两种理路的混沌还是从“人”的混沌认同开始的。
“自由”:在此岸道德泛化中无地彷徨(下)
在新型的道德理想国出现之前,革命发生的逻辑告诉我们,革命不但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换来无穷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它本身过度理性化的同时就潜存着一个非理性的因子。这是革命自身难以避免的两难与症结。因此,对一个革命者来说,读懂革命的限度、歧义以及怎样限制可能发生的滑坡,则成了走向现代的另一个逻辑起点。
对希望“立等可取”的革命者来说,他们首先要面临的思想吊诡就是个性自由与共性互助之间的紧张。而这一紧张的根本还在于带有个性色彩的自我独立意志与被道德色彩染浓的公众意志的一致性问题。对另一种启蒙路径的先驱而言,这样的“兼融”简直就是“炼狱”。当年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在潜意识意义说上无非还是“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对抗。李大钊坦言道:“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这个“满意不满意”的尺度是“理想、主义”,而这一“理想、主义”的实质也就是一种意念中的道德理想王国标准。拿过度高远的彼岸理想尺度衡量此岸现实的“问题”自然不会得出别的结论。至于“设法”使之成为“多数人共同的问题”的“所设之法”也离不开道德理想的诱惑、政治启蒙的觉悟。当年马克思所批判的“个别的或个人的意志应该是毫无地位的”、“公意或者主权的意志永远应该是主导的”卢梭式波拿巴政体,讲求的就是一种意志的合力,这恰似平行四边形那条对角线的方向。值得说明的是,公众意志并不是公众意志的简单相加:“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0页。)如此理论模式下理想国之国民人格无不是道德型的人格。陈独秀的“个人本位”可以暂时与传统脱节,但是他的道德理想策划出的“人生真义”还是要设法将个人的痛苦以及其他一切置之度外,以努力给他人和后世“造成幸福”(注: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4卷2号,1918年2月15日。)。
揭示“五四”道德泛化潜存的可能性以及可能由此爆发出巨大威力的历史真实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论旨的核心应是:“公意”在不断升级过程中如何将东方旭日般的生命个体置换成了消失殆尽的夕阳晚霞?如所周知,“五四”文化营垒的两种启蒙格局在化大众与大众化的走向中由歧义而分道扬镳。一个在“提高”宗旨里转向“象牙之塔”,一个在“普及”意向里奔向“十字街头”。对这两条线索,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算是较为典型的“说法”。
悬挂在头顶上的理想从来没有与道德结合得那样紧,不遗余力地为伦理道德立命的原由也正在这里。据上所论,这里的道德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而是一种用诸激活民意或民力的人化甚至神化“生命”现象。在李大钊看来,如果这种伦理道德不与民众结合起来,那它就是一个没有着落的虚设。所以他说:“我们今日所需要的道德,……乃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注: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2卷2号,1939年12月1日。)究竟是什么一种道德呢?原来,他讲的是普遍的、动力的、实践的道德。一言以蔽之,是要转换成有能量的道德。先哲们并不是不知道,靠一个两个人的道德并不足以解决问题。那只能是“独善其身”的自我设计。于是,将道德“普度”,辐射到人人身上就可以在强大的民意中实现自我的意志。说穿了,道德泛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自我膨胀的过程。人人的善,积聚成为一个无限的大善,连成浑圆的一体。这就不是“人人皆可为尧舜”的问题,而是“人人必须为尧舜”的问题。既然道德不振是社会罪恶的根源,那就有必要从道德振作开始。
我们发现,出于本能的“牺牲自己爱他人”的道德心去传播散射福音,非常容易在“回天”的过程中将“自我”消融在混沌的宇宙与灿烂的蓝天里。李大钊《青春》中“宇宙即我,我即宇宙”(注:李大钊:《青春》,《新青年》2卷1号,1916年9月1日。)的生命主题在革命的前夜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神秘的色彩几乎可以说与佛法相近了。但其中的关键或说主题词还在于“无限的青春”之运用。无始无终、无限无极的思路已经将自我膨胀到了“宇宙即我”、“我即宇宙”的无以复加地步。从个体的有限走到全体的无限,这个过程模糊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个体—投入整体的洪流就会力大无比、气魄无限。就这样,个人“心力”(心理能量)的神化在向下寻求道德力量的三位先驱身上得到了同样的表现。
来自道德理想对自由天平形成威胁的另一个砝码是“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位置协调命题。那就是他文中的“物心两面的改造”之说。
关于“心的改造”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在李大钊早期的文章里诸如“精神”、“意志”、“意念”、“悔改”等方面的论述即是他的心力意志的表现。“互助的原理”也正是他以往心力思想顺理成章的发展。而“物的改造”则是新的历史进程中的新学说。这即是以阶级斗争的方法实现经济利益分配的合理化。在李大钊那里,“物心两面的改造”即是客观世界的改造与自我心性的改造。不过,在提倡并驾齐驱之共同“改造”的同时,先驱还是倾向于“经济”范畴争斗优先的原则。这在哲学上也非常符合物质与意识关系之辩证法。后来,李大钊的这一两面改造思想被他的追随者毛泽东所接受并发展,毛泽东在不同文章中反复述说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说法与李大钊的思路如出一辙(注: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前辈的李大钊率先遇到了毛后来也遇到的问题。这就是,从他接受的唯物史观来看,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不足支持他的“经济变动”论点。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里已经强烈地感受到经济条件的特殊性,于是他便开始用拔高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的办法来弥补“物的改造”的局限性——把有限、被动甚至看似“怯懦无能的人生观”转化为无限的、主动的“发奋有为的人生观”。在这里,包括在此之前的谭嗣同等先辈的心力“艺术”也无不频频传递出这一信息。
“物质”总是有限的,而且条件是具体可见的;而“心力”则是“无限”的,而且在理论上是可以不受时空限制的。在“心力”的作用下,什么权威、实际都将化作乌有。“心力”的理想负荷已经使道德的越位承诺不堪其苦,加之“物质变动”条件的不成熟或说匮乏又无条件让道德负担社会革命所需要的代价。于是“自由”只能在具有神性的彼岸向我们招手,而实际的现实“自我”之自由则已经在“我与世界”的阻隔打通后逃之夭夭:“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障碍,应该逐渐废除。”(注:李大钊:《我与世界》,《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
结语:道德理想主义的再造
当朝阳般鲜活的生命个性消失在灰暗混沌的意志世界之际,由于他们心力意义上的“道德”逻辑各有不同,因此在公意倾向的一致外还有不同的归宿。
就这一命题,我们在“民粹”意义上发现了“微言”机关。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三位早期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身上,民粹主义特征有着鲜明的接力递增色彩。在政治道德启蒙意义上,陈独秀相信民众合力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但是他的理论明显建立在国民道德素质与觉悟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早在《新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就认为尽管国民身上有积淀很深的劣根性,但目前较民国以来已经有很大发展,后来在指导“国民社”成员向外转的讲话里也在不够“尽善尽美”的标准上判定“国人及今已至觉悟之期”(注:陈独秀:《在〈国民〉杂志成立周年大会上的致词》,《国民》2卷1期,1919年10月12日。)。似乎,陈独秀的“绅士”风情难以割舍。他在“神圣事业”领域不适应的感觉充分体现在他的道德感悟上,在他心目中“革命与作乱”不可模糊,因此拥有道德与道德不足的分子在革命阵营里就不可鱼目混珠。陈独秀在“随感录之九十九”所感悟出的革命动力的困惑也正是他1927年下野的前兆(注:他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新青年》第8第4号,1920年12月1日。)。正是陈独秀饱蘸书生意气的“真理”祈求态度给他在通向道德理想国的路上带来了无穷的困惑。与陈独秀的化大众与大众化的两难与困窘相比较,李大钊在民粹主义的道路上则“技高一筹”,他在革命主体力量上的道德认同使他坚信:“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注: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晨报》,1919年2月20-23日。)思想的“悔改”改出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这预示着意志论影响下的唯民主义时代的来临。质而言之,李大钊淳厚的道德理想在其思想过度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暗合了中国革命里的内在混沌力量的利用。更为直接的还是毛泽东的公然声明:英雄离不开“小人”的“援手”,圣贤成事要与“小人”“共跻圣域”。即是说,道德理想王国的实现必须依靠革命阵营里的混沌力量(注: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毛泽东对长沙抢米风潮“主人公”的同情、对会党起义的认同,对被诬蔑为“痞子运动”的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的赞赏十分清晰地说明了他对工农革命队伍中混沌力量的器重。以阿Q的形象来说明问题,在陈独秀,阿Q绝对不可以“做”;在李大钊,阿Q本来就不是那个样子;在毛泽东,阿Q“做”,而且必须“做”。
在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中,启蒙必须导致革命的应然逻辑根源于至高无上的道德理想。在今天我们反思启蒙如何保持其独立性——不一定必然导致革命——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理想,只要焕发得当,同样是牵引我们前行的动力;革命,只要因地制宜,同样是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
标签:陈独秀论文; 李大钊论文; 新青年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毛泽东论文; 道德论文; 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理想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每周评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