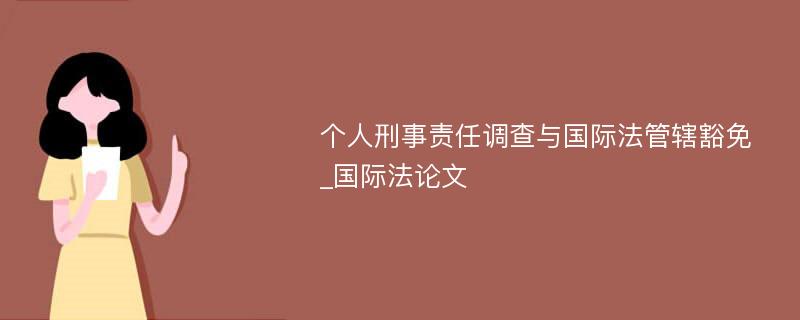
国际法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与管辖豁免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法论文,刑事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里所说的管辖豁免,是指司法管辖豁免;追究个人刑事责任,是指通过起诉和审理来惩治犯有国际罪行的个人;管辖豁免则是指某些人因为特权而免受他国的司法管辖。管辖豁免是国际法一项非常古老的原则。外国国家元首、国家代表及其该国位于外国境内的财产豁免于当地法律的原则,也许是整个国际法中最为古老的部分。管辖豁免的理论根据是“主权平等”原则。管辖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主权是平等的,“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Par in parem non habet jurisdictionem)。因此,一个国家的主权不能凌驾于另一个国家主权之上,从而排除了一个国家从属于另一个国家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国家间相互管辖或支配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国际刑法的发展,使得原来传统国际法上管辖豁免问题在理论或实践方面都需要在新形势下重新审议。
国际刑法上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与国际法有着直接内在的联系。国家责任的理论与实践是传统国际法的重要部分之一。根据国家责任原则,一个作为国家机关或政府的代理人,如果犯有国际不法行为,就会产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相对由于国家代理人而使国家承担国际法上“国家责任”之说,现代国际法上开始强调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也就是说,任何个人(自然人)犯有国际罪行,就必须为此承担个人刑事责任。
刑事法律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惩治来预防和打击国际犯罪,以维护世界正常的和平秩序。国际刑法中的人权保障机制,就是通过设立对犯有国际不法行为的人予以起诉和惩治的机制,来达到保障整个国际社会基本人权不受伤害的目的。所以,国际刑法的发展势必对传统国际法上豁免原则会产生影响和冲击。
一、追究个人刑事责任对管辖豁免概念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国家官员之所以享有豁免权,是因为这些官员的官方地位和对外交往的需要。只要他们拥有某些官职,就会享有此种身份豁免权(personal immunity)。传统国际法上,这些官员首先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① 同时也包括外交官和其他在国外执行国家特殊使命的官员。② 从逻辑上讲,这些在国际交往中担负主要职责的国家官员享有这些豁免权,是国际关系和国际合作的平稳发展的需要,是国家相互之间进行有效交往与沟通的需要。因此,这种豁免权的存在对于保持国家间的合作与和平共处是十分必要的。正如国际法院在1980年美国诉伊朗的“绑架案”判决中所声明的那样:“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编纂了外交关系与领事关系的法律,明确了维护国家之间和平关系的主要原则,并被世界各国所接受,而不管这些国家在宗教、文化以及政治立场方面有如何的不同。”③ 所以从传统国际法的角度讲,由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结果,国家及其代表在国际上就自然享有免受其他国家司法管辖豁免的权利,目的是确保国家不会受到他国不正当的干涉。然而,随着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发展,现在又产生了一些较新的国际法原则。它们以人道价值为基础,并把某些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利益的行为界定为国际法罪行,并要求对那些犯了国际罪行的个人追究刑事责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为了惩治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而成立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清算他们在战争中的暴行。通过对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的审判,国际法上开始出现“官方身份无关性”(irrelevance of official position)的原则,即:不管担任国家或政府怎样的官职,只要犯有国际法上的罪行,就都要被惩处。例如,《纽伦堡法庭宪章》第7条就明确规定:“被告之官职上地位,无论系国家之元首或政府各部之负责官吏,均不得为免除责任或减轻刑罚之理由。”
联合国大会在1946年12月11日的95(1)号决议中肯定了国家元首犯有国际罪行不能适用豁免权。后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1950年也确认了由《纽伦堡法庭宪章》和法庭审判所确立的国际法原则:犯有国际法下严重罪行的人在犯罪行为发生时其作为国家元首或负责的政府官员的事实不能免除其在国际法下的刑事责任。这个国际法豁免权的例外可能扩大到国际和国内的刑事管辖范围中,这样,犯罪官员非国籍所属国就可以依赖这个例外并运用普遍管辖的原则在本国国内法院起诉这些人。④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编纂1954年《惩治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时坚持了“与官职地位无关”原则,不仅适用于一般的官员也包括国家元首;在1996年的《治罪法草案》中国际法委员会同样坚持了这个原则。另外,根据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4条、1973年《种族隔离法案》第3条和1984年《酷刑公约》第2条与第12条的规定,国家元首和其他官员如果犯有这些国际条约的规定,也都不能享有不被刑事起诉的豁免权。因此,对于他们的这些行为,不论国内还是国际司法机构都可以予以起诉。
国际法以上这些关于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规定和规则表明,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是从法律意义上讲(de jure)、还是从事实上(de facto)讲,即使是因为代表国家利益犯有国际罪行,那也不能享有司法豁免权,也要被追究其个人在国际刑法上的刑事责任。
二、关于不予豁免的国际实践
对国家和政府官员所犯国际罪行不予豁免的规定,在国际法上有一个实践的过程。它随着国际刑法的发展以及国际社会要惩治国际犯罪行为呼声的提高、为了防止出现导致犯罪人逃脱惩罚的情况下才开始强调对所有的人都要追究个人刑事责任,⑤ 并开始对怀疑犯有国际罪行的国家领导人予以追究刑事责任的实践。在传统国际法上,没有关于对国家要加以刑事制裁的规则。事实上,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不可能将国家作为一个集体来实施刑事方面的制裁;另外,传统国际法对那些被怀疑实施国际罪行的国家领导人或其他负责人,也没有要追究其个人刑事责任的规定。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一般认为是代表国家的行为,个人不应负刑事责任。⑥ 传统的国际法文件,如1917年《海牙关于陆战规例公约》第3条规定,交战国(也就是国家)对于它的军队所属个人的一切行为负责任。换句话说,在传统国际法上个人对国家行为是不需承担个人刑事责任的。
然而,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发生的关于国际刑法有关实践则清楚地表明:关于国际法上的国家刑事责任和实践起了变化。国家官员以官方身份为的行为不由本人负责而是仅由国家负责的这条普遍规则不再适用于导致国际犯罪的行为,行为时具有的官方身份不能成为免除他(或她)应对其犯下的国际罪行负个人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这是二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确定的原则。以后的一些案例里,例如在皮诺切特一案中,英国最高法院(House of Lords)也都坚持与纽伦堡、远东国际审判相同的立场和观点。⑦ 由此,国际刑法对传统国际法上的管辖豁免原则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1.《1919年凡尔赛条约》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刚结束时,在国际法上出现一种比较新的观念,即:国家的一些行为,特别是与侵略战争有关的行为也可以构成刑事责任。理论上讲,虽然不可能对犯有国际罪行的那个集体实施刑事制裁,但对于具体犯有国际罪行的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负责人,仍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制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实质上也就是对这种行为实际负责的个人的国际犯罪行为。因此,应该要有刑事制裁。
纵览国际刑法的发展历史,第一次要起诉和审判政府高级负责人的尝试正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由于那次世界大战的空前规模以及它给人们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痛苦和牺牲,使得整个国际社会对于大战的发动者德皇和德政府领导人怀有深深的仇恨,认为必须对他们予以严厉惩罚。
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署的《1919年凡尔赛条约》明确规定,同盟国及协约国将组织特别法庭审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并治之以“破坏国际道德和条约尊严的最大罪状”(第227条)。然而,由于威廉二世在战争时期就已逃到荷兰,当协约国及其联系国向荷兰政府提出引渡战犯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请求时,荷兰却以违反本国《宪法》与历史传统为由拒绝引渡。这里,《宪法》当然是指荷兰的《宪法》;“历史传统”则是指国际法上关于国家元首享有司法豁免权的习惯和原则。所以,荷兰拒绝引渡使得协议国要对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审判没有成功。虽然威廉二世由于荷兰的庇护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但《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订立则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了要惩办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和国际不法行为的负责人的努力,并开始了初步的尝试。
2.纽伦堡和东京国际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轴心国的失败而告终。对于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战胜的同盟国在德、日投降后,就先后在德国纽伦堡和日本东京设立了两个国际军事法庭。这两个国际刑事法庭虽在机构的组织上略有不同,但它们的任务和目的却是一样的:把轴心国对侵略和其他国际不法行为负责任的领导人当作首要的战争罪犯加以起诉和审判。⑧
针对与身份有关的豁免权的适用问题,建立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律文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就明确规定,被告的官职地位不得成为其免除责任或减轻刑罚之理由。从而明确消除了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享有的不被刑事起诉的豁免特权。被纽伦堡审判的有22名甲级战犯,他们都是纳粹德国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果希特勒不自杀也一定会被列为受审者之列),其中被判处绞刑的有1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4人、无罪释放的3人。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6条是关于“被告之责任”的规定,虽然它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避开明确“国家元首”的提法,但在该条款中还是明确规定:“被告在任何时期所曾任之官职,以及……,均不足以免除其被控所犯罪行之责任。如法庭认为符合公正审判之需要时,此种情况于刑罚之减轻上得加以考虑。”所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于政治考虑没有起诉日本天皇,但还是起诉并审判了前日本政府其他军政首脑和内阁官员共28人,这些人都被证明有罪并得到判决,其中判处绞刑的有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16人、判处有期徒刑的2人。⑩
以后,对德国实施占领的同盟国在其制订的“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第10号法案”里对追究个人刑事责任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该法案的第2条第4款第1 项与《纽伦堡法庭宪章》第7条的规定只是措辞略有不同,实质完全相同。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纽伦堡原则》第3条中去掉了“减轻刑罚”,它规定:“被告人以国家元首或者政府负责官员的身份实施了国际法上罪行的事实,不能免除其根据国际法应当承担的责任。”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如此规模浩大的审判和极其严厉的惩罚,是以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通过这两个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审判,在国际法上确立了“个人刑事责任原则”以及“个人官职地位不能成为其开脱罪责之理由”的原则。
3.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国际政治、或者说是由于东西方对立的实际状况,使得国际法上极具制裁力的国际刑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什么发展,也一直没有对被怀疑犯有国际罪行的领导人进行过实际的刑事审判。然而,这个状态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和新的国际刑事法庭的设立而被打破。
在1993年和1994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分别建立了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这是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以后第一次用设立国际司法机构的形式,以求达到恢复并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目的。由于人员资源受到限制的原因,这两个国际刑事法庭自然而然地把起诉对象的重点放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高级官员方面。(11)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7条第2款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2条第2款分别规定了国家元首豁免权的不适用性。这两个法庭分别起诉了前任国家元首:前南斯拉夫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Melosevic)和卢旺达总理冈比达(Kambanda)。冈比达前总理因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道罪和战争罪被起诉,尽管他在法庭主动认罪,但因罪行严重,仍被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2) 米洛舍维奇总统于2006年3月11日在法庭拘留所(detention unit)去世。根据刑法“无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的基本原则,米洛舍维奇总统一案在去世时还没审理完毕,所以,不管历史学者根据史料作如何评论,从法律上讲,米洛舍维奇总统就是一个无辜和清白之人。尽管如此,米洛舍维奇于1999年5 月就任南斯拉夫联盟总统时被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从而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起诉的在位的国家元首。这件事本身清楚地说明了国际法追究个人刑事责任对管辖豁免原则的影响和冲击。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在其刚成立的时候,曾担心因没有被告、而不能成功地履行国际社会所委托的惩治国际犯罪行为的任务,因而在调查和收集一定证据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颁布了起诉书。但出人意料的是,由于西方国家及北约军事组织的合作与配合,很快就有不少被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被告被抓获并移送到法庭来。在这一背景情况下,根据国际刑事法庭资源有限的条件,加拿大籍的检察长路易丝·阿赫布(Louise Arbour)就重新调整起诉政策,果断地撤销了前检察长对一些人的起诉,从而把力量集中放在那些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犯罪负责任的政治家和军队的高级将领的起诉方面。这个事例典型地说明了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对根据传统国际法本应享有豁免权的人的起诉态度和立场,也表明国际刑法实践对国际法豁免原则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冲击。
4.“皮诺切特”案
通过本国国内法来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最为典型的案例,是1998至1999年间基于国际法被动“属人管辖”原则理论基础上的“皮诺切特”案。这也是近年来对传统国际法豁免理论影响较大的一个案例。
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原是智利总统。1973年9月,皮诺切特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发动了军事政变,杀害了当时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于1974年12月自任总统。皮诺切特统治智利长达17年,一直到1990年3月。但即便下台后,他根据智利1980年宪法规定,仍继续担任陆军总司令,直到1998年3月。那时他才彻底交出军权,成为一个终身参议员,法律上享有完全的刑事豁免特权。在皮诺切特统治期间,智利有许多人被杀害,或失踪。由于这中间有不少受害人是西班牙人,所以西班牙多年来一直在调查皮诺切特担任智利总统期间所犯下的罪行,并试图就这些罪行对他进行起诉。
1998年10月,西班牙趁皮诺切特来英国治病时以皮诺切特犯有国际罪行为由,要求英国拘留皮诺切特并提出引渡请求。(13) 于是,英国司法部门在西班牙的请求下将皮诺切特拘捕,皮诺切特的律师则自然地以传统国际法豁免理论为基础,提出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英国没有权利拘留皮诺切特,更没有权利将他引渡给西班牙。在皮诺切特于英国拘捕以前,欧洲有些国家法院已经基于普遍管辖权对那些被指控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犯有严重罪行的人进行了审理。(14) 从那以后类似案件接连不断,最后终于因为比利时国内法庭对卢旺达国内武装冲突中的四个犯罪嫌疑人在卢旺达所犯的战争罪行的审判,使得“普遍管辖权”从理论转为实践,从而使传统国际法的豁免原则发生了变化。
对皮诺切特进行起诉和审判,首先是由西班牙国内法庭作出的决定。根据西班牙的“国家听证”(Audiencia's National)裁决,“西班牙可以就在智利发生的严重罪行进行调查,国内法庭可以就此对那些在西班牙领土之外的非西班牙国民行使普遍管辖权”(15),这一决定为西班牙在1998年提出将皮诺切特引渡到西班牙的正式请求提供了基础。
从该案的案由来看,西班牙是以保护管辖原则为根据向英国提出引渡请求,英国只是根据本国1978年《国家豁免法》来审查它是否符合向西班牙引渡的条件。然而,由于这种审查本身涉及到皮诺切特作为一个前国家元首所享有的国际法豁免权能否阻止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因此,该案也就成了涉及国际法上管辖豁免原则的一个重要问题。
皮诺切特一案经过英国上议院上诉法庭的审理,最后是以六比一的投票结果在1999年3月24日通过裁定,决定将皮诺切特引渡到西班牙。然而,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重要的还不仅仅是结果,主要是在于为什么同意或者反对引渡的理由。
在案件审理中,布朗尼·威金森(Browne Wilkinson)议员认为,国家豁免的适用是有限制的,它只限于国家元首等人在位期间代表国家实施的职能性行为,而实施《酷刑公约》规定的酷刑罪行则不属于执行一个国家功能的范畴。另外,他还认为,酷刑罪行与国际法相违背。这种酷刑即便是发生在智利,其他国家也有权管辖这种官方的酷刑罪行。克雷格德(Craighead)议员认为,国际法豁免理论原则是为了在一个国家元首行使其政府职能时对他进行保护。但它有两个例外:一是该国家元首以行使政府职权为幌子而实施其个人利益行为;二是实施国际强行法禁止的行为,因为强行法要求所有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实施这类行为,并要求所有国家对这些行为予以惩罚。所以,在皮诺切特被指控的犯罪中,酷刑罪属于国际法上可引渡的罪行。(16) 切维利(Chieveley)议员则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仅仅是行为构成犯罪这个事实,并不能排除国家豁免的适用。一个国家元首的职能是政府性的,而不是私人行为;如果一个国家元首实施了一个非私人行为,并且构成犯罪,但这仍然不失去其政府行为的性质。对于严重的犯罪,例如谋杀或者酷刑,或者对于较轻的犯罪,都是如此。因此,切维利议员认为应当驳回西班牙的引渡请求。
尽管英国上议院上诉法庭裁定,要将皮诺切特引渡到西班牙。但2000年3月,英国则以皮诺切特的健康状况不适宜接受审判为由,仍拒绝了西班牙的引渡请求。但在皮诺切特回国以后,智利圣地亚哥上诉法院于2000年6月5日取消了皮诺切特终身议员的司法豁免特权。2005年1月4日,智利最高法院以3票对2票的表决结果维持该裁定。(17) 所以,英国的司法程序对智利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英国的裁决使得皮诺切特作为议员而享有的豁免特权被取消,也使得智利的国内司法程序也能适用皮诺切特。
在皮诺切特一案审理时,英国还认为,所有1984年《反酷刑公约》的缔约国都有义务(18) 对国际罪行采取必要措施,其中包括对正在其国家领土范围内的罪犯行使管辖权,或者将其起诉,或者将其引渡。它们也强调,一个国家的前元首犯有酷刑罪或者是犯有此罪的通谋不能要求享有豁免特权而免于引渡或被起诉。
三、国际法院坚持传统管辖豁免原则的意见
关于国际刑法上被怀疑犯有国际罪行的人原来所享有的外交豁免权归于无效的规定的理论和实践,在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之一、也是国际法最权威的机构——国际法院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国际法院在“逮捕令”的诉讼案中管辖豁免问题上的裁决,与其他国际刑事法庭的也截然不同。
2002年,国际法院受理了对刚果诉比利时关于“逮捕令”的诉讼案。在该案中,刚果反对比利时法院对被指控犯下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时任刚果外交部长阿普杜拉耶·耶罗迪亚·努道姆巴西(Abdulaye Yerodia Ndombasi)发放国际逮捕令,认为外交部长在国际外交法上享有不受起诉的豁免权。
案由与比利时关于惩治战争罪行的国内立法和发生在卢旺达的大屠杀有关。比利时于1993年已制订了关于惩处严重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法,(19) 里面明确规定:“比利时法院对于本法规定的罪行有管辖权,无论该行为发生于何处。”以及“因官方身份而享有的豁免权不妨碍本法的适用。”所以,比利时国内法院对种族灭绝罪、战争罪以及反人道罪行都可以使管辖权,即使犯罪嫌疑人当时并不在比利时的领土范围之内。
1994年4月至7月,卢旺达国内爆发了种族大屠杀,它是占卢旺达人口多数的胡图族(Hutu)对图西族(Tutsi)的屠杀。所以,该屠杀引起大量的图西族人涌入邻国的刚果,并在刚果形成严重的难民问题。1998年8月,刚果境内又发生了刚果政府与图西族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当时,努道姆巴西任刚果总统私人秘书,他多次在公开场所煽动对图西族人的种族仇恨。所以,2000年4月,比利时布鲁塞尔法院的冯德迈斯(Vandermeersch)法官对已经担任刚果外交部长的努道姆巴西发出了国际逮捕令(an international arrest warrant)。但刚果民主共和国认为它违反国际法外交豁免原则,所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国际法院撤销这一逮捕令。
刚果在国际法院审理阶段认为,一个国家外交部长在其任职期间享有不可侵犯、绝对的管辖豁免权,这是国际法的一项原则,没有任何例外。因此,外国法院不能对其进行任何刑事诉讼和刑事判决,否则就违反了管辖豁免原则。这种管辖豁免是纯粹从其职能上考虑,是习惯国际法能够保证其无障碍地行使职权的保障。
比利时则认为,外交部长在国外所享有的豁免权只能基于其行使官方职能的行为,豁免权本身并不保护该人的私人行为或者非行使职能的其他行为。而在“逮捕令”案中,努道姆巴西被指控行为发生时,并不享有豁免权,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那些行为是他以官方身份实施的。换句话说,逮捕令是针对努道姆巴西个人行为、而不是国际法上管辖豁免所要保护的国家行为。(20)
国际法院在该案中认为,根据国际法,外交部长在其任职期间在外国享有完全的管辖豁免权和不可侵犯权,这些权利可以保护其不受外国有关当局对其行使职权进行妨碍: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区分外交部长以官方身份实施的行为与其以所谓私人身份实施的行为,也不能区分该人在担任外交部长之前的行为与其任职期间的行为。因此,如果一位外交部长在另一国由于刑事指控而被捕,显然妨碍了其行使职权。当其被逮捕时,无论该外交部长是以官方身份进行访问还是以私人身份进行访问,也无论其被逮捕的原因是与其担任外交部长之前的行为有关还是与其担任外交部长期间的行为有关,也无论其被指控的行为是以官方身份实施还是以私人身份实施,这种妨碍其行使职权的逮捕所产生的后果,其严重性都是一样的。”
对于比利时发布的逮捕令的背景情况以及该命令的内容,国际法院也进行了仔细地研究和考察。从其背景来看,毫无疑问,比利时的司法当局希望能够逮捕这位被指控实施了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刚果外交部长。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比利时的司法当局才颁发了逮捕令。从法律上讲,该逮捕令在比利时具有执行力,因为它“命令所有能够执行本逮捕令的司法官及公共当局的代表执行本逮捕令,并且将嫌疑人送到位于福雷斯特(Forest)拘禁中心”,并且认为“该嫌疑人现在的外交部长职位并不能赋予其在管辖和执行方面的豁免权”。(21)
鉴于此,国际法院认为,比利时将逮捕令在全世界范围公布,就是想“在国外奠定一种法律基础,以便逮捕努道姆巴西并将其引渡到比利时”。然而,国际法院认为,这一逮捕令的国际性质在客观上侵犯了努道姆巴西作为刚果外交部长的豁免权,并且会进一步影响刚果在国际社会交往中的行为,因为只要努道姆巴西一出国就有可能被捕。所以,国际法院认为,比利时公布逮捕令的行为违反了比利时对于刚果的国际法义务,它没能尊重刚果外交部长的豁免权,即他作为刚果外交部长根据国际法应当享有的刑事管辖豁免权和不可侵犯权。由于那些被赋予这类豁免权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官和其他官员若在外国遭到逮捕或拘留则必然会阻止他们履行职务,所以这些官员对他国的刑事管辖享有绝对的豁免权。这种豁免权不仅适用于这些官员的职务行为,也同样适用于他们的私人行为。并且无论他们被怀疑的犯罪行为(包括极其严重的国际犯罪行为)发生在他们任职期间还是发生在任职之前,这些官员一概可以用这种豁免权作为抗辩。(22)
刚果在2000年11月进行了政府改组,努道姆巴西改任教育部长。不过,他在2001年4月中旬又停止担任该项职务。尽管如此, 国际法院认为:“尽管努道姆巴西先生不再是外交部长,但是逮捕令依然还在,并且其非法性也还在持续。本院因此认为,比利时必须自己采用适当的方法,撤销该逮捕令,并且告知被送达的有关当局。”(23)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国际法院根据条约法和国际习惯法,认为对于高级官员享有不被外国国内法院刑事起诉的外交豁免权这一普遍规则不存在例外的情况,即使这些高官被控告犯有战争罪或其他危害人类罪时,他们也同样享有这样的豁免权。这个判决明确地包括了在位的外交部长,并且国际法院对这种官员在一国外交关系中的特别职责与活动作出了特殊解释。(24)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国际法院在这一“逮捕令”案中,判决比利时败诉。 (25) 同时,国际法院强调,国际法上授予豁免权的目的是允许外交功能能得到充分发挥,正如《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在其序言中所表述的:“特权与豁免……目的并非有益于个人,而是确保代表国家的外交使团职责的履行。”(26)
国际法院在刚果诉比利时一案的判决中坚持了传统国际法上国家政府官员享有外交特权的原则,但在整个国际刑法领域里的实践来看,从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到塞拉里昂特别法庭、东帝汶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国际刑事法院这些所有国际司法机构的《规约》全都明确地规定要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
四、塞拉利昂特别法庭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是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刑事法庭。虽然它也是一个国际刑事法庭,但其成立的途径与联合国两个特设国际刑事法庭却完全不同。联合国前南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则是根据2002年1月16日联合国和塞拉利昂政府之间达成的协定而设立的。(27) 在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迄今为止的审判中,对利比里亚前总统泰勒管辖豁免问题的决定也是反映了国际刑法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决定。
利比里亚邻国塞拉利昂于1991年爆发内战,战争持续了10多年,造成20多万人死亡,被称为非洲现代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之一。泰勒被怀疑武装并培训了塞拉利昂当时的反政府武装革命联合阵线,并犯有国际罪行。2003年3月7日,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汤姆泊森(Bankole Thompson)法官同意(confirm)对泰勒的起诉书,里面有17项指控。与此同时,法庭还签发了逮捕令。2003年7月23日泰勒的律师向法庭提出管辖豁免的申请,认为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国际刑事法庭对一个国家元首不具有管辖权。2003年10月30日和11月1日,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就这一问题举行了听证会。
泰勒的律师提出了管辖豁免动议,要求法庭撤销对泰勒的指控和逮捕令以及其他一切命令。为支持这一动议,该律师援引了两个案例:一个是国际法院的“刚果诉比利时案”;另一个是常设国际法院的“荷花号案”。
在“刚果诉比利时案”里,如前所述,国际法院认为比利时国内法庭公布逮捕令违反比利时所承担的国际法义务,也违反了国际法上的管辖原则,因为根据这一原则,刚果外交部长应当享有刑事管辖豁免权和不可侵犯权。根据国际法院的裁决,所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官和其他官员都因为履行职务的需要而享有对他国刑事管辖的绝对豁免权。(28)
常设国际法院“荷花号案”清楚地表明,国际法上的主权平等原则禁止一国在另一国行使主权。根据这一原则,一国只有当犯罪人出现在该国的领域内时,才能对其发生在外国的罪行进行起诉。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向加纳送达逮捕泰勒的起诉书和逮捕令也都违反了主权平等原则。
对于泰勒律师的论理,法庭检察官则认为,国际法院审理的“刚果诉比利时案”,其实是一个关于国家现任外交部长是否应在另一个国家法院享有豁免权的问题,这与当前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是根据国际法建立的国际刑事法庭,习惯国际法允许国际刑庭起诉在任的国家元首。起诉泰勒的根据是《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规约》,泰勒被起诉的罪行是在塞拉利昂实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进行的。(29)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上诉庭在听取了当事方的理由后作了裁决。在法庭辩论中,检方认为管辖权与豁免之间存在有区别,认为即便有豁免权,管辖权不能被行使,但它仍然存在,所以被告方提出关于豁免问题动议并不影响法庭行使管辖权。对于检方这一观点,法庭不同意。法庭认为,既然管辖豁免原则意味着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阻止法庭行使管辖权,申请人就豁免问题提出动议还是与管辖权有紧密的联系。
但上诉庭同时还认为,法庭是由塞拉利昂政府与安理会通过签订协议而成立的,代表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所以,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与其他国际刑事法庭,如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及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基本一样,《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规约》第6条关于官方身份既不影响定罪也不影响量刑的规定与任何习惯国际法的规定,其中也包括管辖豁免原则的规定并不矛盾,因此,法庭也就没有必要去讨论被告人提出的关于他在其他国家是否享有管辖豁免问题。据此,法庭拒绝了被告人关于享有管辖豁免的动议。(30)
当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就泰勒总统管辖豁免问题进行法庭辩论时,泰勒本人还没有被逮捕或移送到法庭。2003年8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安排时任利比里亚总统的泰勒流亡尼日利亚,以结束利比里亚多年的内战。然而,当利比里亚新任女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于2005年3月当选后,就表达了要追究泰勒刑事责任的希望,同时也向尼日利亚方面提出引渡要求。(31) 之后,在尼日利亚的协助下,泰勒最后被移送到了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准备接受审理。(32) 我国国内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曾有一篇文章以《泰勒:从总统到囚犯》为标题。(33) 这个标题特别生动和形象地说明了国际刑法发展对管辖豁免问题的影响和冲击。
五、国际刑事法院关于管辖豁免的规定
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社会为惩治国际犯罪而成立的一个常设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于2002年因为国际刑事法院成立而正式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在许多方面沿袭了这些年国际刑法实践中反映出来的规则和原则,其中也包括司法管辖豁免问题。
联合国为成立国际刑事法院而成立筹备委员会在其1996年报告中,就开始使用“官方身份无关论”(irrelevance of official position)的术语,并将它作为一个“实质性问题”提出以供讨论。筹备委员会1996年报告认为:
“考虑到纽伦堡、东京、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法庭的先例,有人支持规约应驳回作为国家或政府首脑或负责的政府官员的官方立场的任何抗辩;这种官方立场不应免除刑事责任。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与‘辩护’一起编入。有人也认为,关于外交或其他逮捕豁免问题和关于法院或以法院的名义采取的其他程序措施的豁免问题的进一步审议将是有益的。”(34)
1998年联合国成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在荷兰聚特芬举行的会议报告第18条(官方身份无关性)规定:“(1)本规约应绝无任何歧视地适用于所有人:任何人不得因其官方身份,无论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政府成员或国会成员、民选代表,或政府官员而免除其根据本规约所负的刑事责任,也不得(仅仅)以其官方身份构成判刑理由。(2)不得援用国内法或国际法的规定而对任何人的官方身份适用的任何豁免或特别程序规则,使法院无法对该人行使其管辖权。”(35)
在1998年为成立国际刑事法院在罗马召开的外交大会上,与会国家代表们就管辖豁免问题进行了最后的全方位的讨论,并最终通过了《罗马规约》第27条的规定,明确规定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不能适用于传统国际法上的管辖豁免。
《罗马规约》第27条第1款规定:“本规约对任何人(all persons)一律平等适用,不得因官方身份而差别适用。特别是作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a head of state or government)或议会议员的官方身份,在任何情况下(in no case)都不得免除个人根据本规约所负的刑事责任,其本身也不得构成减轻刑罚的理由。”
此条款用绝对性的语言排除了行为具有官方性质而享有的豁免权,确立了即使这些行为是以官方身份所为,这些官员也要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第27条第2 款进一步规定:“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法可能赋予某人官方身份的豁免权或特别程序规则,不得妨碍(shall not bar)本法院对该人行使管辖权。”
所以,第27条第2款作为程序法上的规范进一步表明国际刑事法院拒绝适用国际法及国内法豁免权的坚定性,以此强调在国际刑事法院进行的诉讼中彻底消除了行为人依赖豁免权以逃避个人刑事责任的可能性,同时确保了第27条第1款承认的结果不被豁免权或其他程序所阻碍。
《罗马规约》第27条明确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对任何个人具有管辖权,不论其是否拥有官方身份或任何国内或国际法可能赋予的豁免权或特别程序规则。因此根据这条规定,所有被指控犯有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范围内罪行的国家官员,都不能享有外交豁免权。
国际刑事法院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不同,它不是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建立,因此没有《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赋予的权威性的支持。但它仍然对所有参加国际刑事法院的国家具有拘束力。国家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就意味着接受了《罗马规约》第27条的规定,即放弃本国外交官和其他官员在国际法本应享有的基于官方身份而产生的豁免权。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关于管辖豁免的规定,相对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以及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规约》来说,显得更为明确,它不仅确定犯下国际罪行的国家官员都要在国际法上承担个人刑事责任,同时它还意味着,《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放弃了自己本国国家官员本应享有的豁免权。
当然,那些还没有放弃国家或外交豁免权的国际刑事法院非缔约国,能够利用国际法提供的在被外国法院起诉时所享有的保护措施。尽管国际刑事法院有权对其非缔约国的公民行使管辖权,(35) 但《罗马规约》却没有相关条款规定可以消除非缔约国官员在国际法下正常拥有的豁免权。从《罗马规约》的序言和第27条所明示的目标中,可以推断出,国际刑事法院有权对任何被怀疑犯有法院《规约》中所规定罪行的嫌疑者进行起诉,即使最高级别国家官员也不能被排除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之外。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被批准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就意味着存在把本国官员交由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和审判的可能性,并且按照《罗马规约》第27条的规定明确消除本国高级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的国际法豁免权。缔约国不仅同意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官员进行起诉,而且还同意这些高级官员可以被其他国家逮捕并移交到国际刑事法院,这是国际刑法上的一个重要发展。
六、结论
管辖豁免是国际法的重要部分之一。自从国际法产生以来,某些人、物或事件有权免受一国的司法管辖就一直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管辖豁免,简单地讲,就是指一国的行为及其财产不受另一国的司法管辖。其内容包括对国家行为和对国家财产的豁免,当然,也包括对他国国家元首、外交人员的刑事管辖豁免。
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国家主权是平等的。国际法豁免权则是国家主权的产物。根据国家相互间达成的国际条约,主权国家的代表人享有不受其他国家司法管辖的豁免权,包括民事和刑事豁免权。(36) 这是传统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规定。
然而,通过以上对国际刑法近年来发展所作的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国际刑法的发展,现代国际法上也开始强调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主张任何个人(自然人)如果犯有国际法罪行都必须承担个人刑事责任。这对传统国际法上豁免原则势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冲击。
注释:
① See Judgment of Case Concerning Arrest Warrant,(Congo v.Belgium),ICJ,2002,para.47.
② 参见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9和31条;1969年《联合国特别使团公约》。
③ Bruce Broomhall,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Between Sovereignty and the Rule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New York,2003,at 12.
④ See M.Cherif Bassiouni,An Introd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Ardsley,N.Y.Transnational Publishers,2003,at 75.
⑤ Se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Final Report on the Exercise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 in Respect of Gross Human Rights Offences,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Practice,London Conference,2000,p.2.
⑥ 中国受害者就日本在侵华期间因为日军使用细菌化学武器所受到的伤害,曾多次在日本法庭要求追究其责任、并予以赔偿。但所有这些申诉基本都被驳回。其驳回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日本法律中“国家无答责”,认为国家的行为(日本军队所为)不需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⑦ 英国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认为:智利前军政府领导人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被指控的罪名是“酷刑罪”(torture),它不属于官方行为(official act),或者说不属于国家领导人的职责范围。See John R.W.D.Jones,Immunity and Double Criminality:General Augusto Pinochet Before the House of Lords,in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Essays in Memory of Li Haopei,Eidited by Sienho Yee and Wang Tieya,London:Routledge,2001,at 261.
⑧ 参见《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1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1条。
⑨ 参见纽伦堡审判宣判书,转引自[德]P.A.施泰尼格尔:《纽伦堡审判》(上卷),王昭仁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25页。
⑩ 王铁崖等编:《战争法文献集》,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199页。
(11) See M.Cherif Bassiouni,An Introd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Ardsley,N.Y.Transnational Publishers,2003,at 707.
(12) See The Prosecutor v.Kambanda,available at http://www.un.org.ictr.
(13) 西班牙在引渡请求中对皮诺切特的指控有32项,主要涉及到酷刑、绑架、谋杀等罪行。See Opinions of the Lords of Appeal for Judgment in the Cause,Regina v.Bartle and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for the Metropolis and Others (Appellants) and Ex Parte Pinochet (Respondent),24 March 1999.
(14)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Final Report on the Exercise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 in Respect of Gross Human Rights Offences,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Practice,London Conference,2000.附件中回顾了皮诺切特案之前在奥地利、丹麦、法国、德国以及荷兰的各种援引普遍管辖权的案件。
(15) Mary Griffin,Ending the Impunity of Perptrators of Human Rights Atrocities:A Major Challenge for Internaitonal Law in the 21st Century,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No.838,June 2000,p.382.
(16) See Opinions of the Lords of Appeal for Judgment in the Cause,Regina v.Bartle and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for the Metropolis and Others (Appellants) and Ex Parte Pinochet (Respondent),24 March 1999.
(17) 参见《人民法院报》2005年1月7日。
(18) 参见《反酷刑公约》第4、5、7条。
(19) 惩治严重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其1977年第一、第二附加议定书的罪行的法律,参见《比利时观察报》1993年8月5日。
(20)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Judgment of Case Concerning the Arrest Warrant of 11 April 2000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Belgium),14 February 2002,paras.47—50.
(21) Ibid,para.55.
(22) Ibid,paras.70—71.
(23)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Judgment of Case Concerning the Arrest Warrant of 11 April 2000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Belgium),14 February 2002,para.76.
(24) See Judgment of Case Concerning Arrest Warrant (Congo v.Belgium),ICJ,2002,para.51.
(25) 比利时国内法庭于2000年4月11日发布了针对刚果外交部长的一个国际逮捕令。刚果认为这是对国际法的违反,于是2000年10月17日在联合国的国际法院起诉比利时。2002年2月14日,国际法院作出判决,裁定比利时的这一逮捕令违反了国际法上的特权豁免原则,并要求比利时收回这一逮捕令。有关情况参见:Judgement of Case Concerning Arrest Warrant (Congo v.Belgium),ICJ,2002,available at http://www.icj.org.
(26) 参见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序言第四段。
(27) Se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of Sierra Leon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Annex to th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UN Doc.S/2000/915,4 October 2000.
(28) Se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Judgment of Case Concerning the Arrest Warrant of 11 April 2000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Belgium),14 February 2002,paras.70—71.
(29) See Decision on Immunity from Jurisdiction,Prosecutor Against Charles Ghankay Taylor,the Appeals Chamber,Case Number SCSL—2003—1,31 May 2004,paras.6—10.
(30) Ibid,paras.31—42.
(31) 参见马震:《尼日利亚同意将泰勒引渡回利比里亚》,《北京晚报》2006年3月26日。
(32) 参见《非洲审判将引向何方?》,美国《洛杉矶时报》2005年4月2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年4月4日。
(33) 参见《北京晚报》2006年4月4日。
(34) Report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U.N.GAOR,51st Sess.,Supp.No.10,U.N.Doc.A/51/10,Volume Ⅰ,March-April and August 1996,para.193.
(35) Report of the Inter-Sessional Meeting from 19 to 30 January 1998 in Zutphen,the Netherlands,U.N.Doc.A/CONF.183/2/Add.1(14 April 1998),pp.54—55.
(36) 如果犯罪发生地国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则不论犯罪人的国籍所属国是否是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均可以行使管辖权。参见《罗马规约》第12条的有关规定。
(37) 参见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9、31、23条的有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