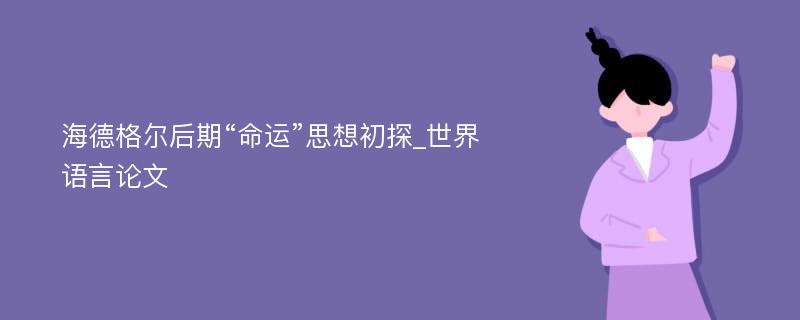
后期海德格尔的“命运”思想初探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后期论文,命运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1-0051-05
一、存在与命运:命运之思的“转折”
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转折”,他对“命运”和“天命”进行了深入探讨。
海德格尔断言:西方的命运就系于对“存在”一词的翻译[1] (P556),因此要把握西方的命运就必须明了“存在”的历史。为此又必须回探古希腊早期思想,因为那里有本真可能性的源泉。经过对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三位早期希腊思想家的独特考察后,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原始意义集中体现在Physis、Aletheia、Logos、Eris、En、Moira这几个希腊思想的基本词语上。Physis、Aletheia、Logos和Eris(斗争)是同一的,它们都是指存在本身既遮蔽又澄明的双重运作。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Moira。
Moira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命运女神。海德格尔利用“命运”和“派遣”、“发送”(beschicken,Schickung)之间的字面联系表明,Moira就实质而言乃是一种“分派”(Zuteilung)。在这种命运的分派中,存在本身蔽而不显而存在者得以澄明。所以,海德格尔说:“从存在之本质经验方面得到思考的命运相应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2] (P583)显然,它也相应于其它早期希腊思想的基本词语。比梅尔就曾指出:“真理作为无蔽状态,就是人按照他经验存在者的方式承受并保持的命运”[3] (P135)。
总而言之,在此时的海德格尔眼里,Moira取得了同Physis、Logos、Aletheia、Eris、En相等的地位,而且都与存在同义,即既遮蔽又澄明的双重运作。所以,波格勒说:“海德格尔把在其中遮蔽和揭蔽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发生(occurring)称为‘天命’”[4] (P203)。
然而,命中注定的不幸之事还是发生了: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思想开始了其堕落的行程。于是,存在成了持续的在场,Physis成了“自然”(物理),Aletheia成了主客体或知物符合一致意义上的“真理”,Logos则成了“逻辑”;中经笛卡尔的“意识”至尼采的“强力意志”,“存在者之存在聚集自身入于存在之命运的终极之中”[2] (P537),“而思之沉沦为科学和信仰,乃是存在的恶劣的命运”[2] (P565)。至此,思之堕落达到了顶点,哲学也即形而上学终结了。不过,这却并不意味着存在历史的终结,而是预示着存在历史的另一个新的开端。在这个开端里另一种存在之天命被唤起了。
为什么会有这一思的堕落?海德格尔解释说,“存在之命运始于差异之被遗忘状态”。这也就是说,思的堕落是由于人们只关注存在者而遗忘了使得存在者得以存在的存在本身。然而,存在的遗忘却并非人为所致,而是出于存在本身既遮蔽又澄明的双重运作。所以,海德格尔说存在之被遗忘“如此本质性地归属于存在之命运”[2] (P578),以至于思之堕落乃是存在本身所必致的。
所以,海德格尔把存在的历史就叫做“存在的天命”。在这个词语中,“存在”成了一个起辅助作用的限定词,而其重心则落在了“天命”上。因此我们说,此时的海德格尔试图直接与命运、天命对接,这也是他重返早期希腊思想之源头的根本动因。简单地回顾一下哲学史我们就会明了,在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作品中始终含有着命运一维。而海德格尔在早期希腊思想家中尤为看中的恰恰就是这三人。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出在他们之间默契于心的就是这无尽的命运之思。对此黄克剑先生颇有卓见,他说:“海德格尔之‘思’未必全然步前哲后尘,但‘命运’在他们那里却是相承于一脉的”[5] (P161)。
二、遮蔽与澄明:天命的双重运作
综观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既遮蔽又澄明的“命运”和“天命”展现于艺术、科技和语言之中。
1.艺术:天命得以展示之所
为了探讨艺术的本质,海德格尔首先进行的是物之物性(die Dingheit)的分析。他指出哲学史上主要有三种对物的规定方式,即或把物理解为特性的载体,或理解为多样性的统一体,或理解为具有形式的质料。在他眼里,“这一历史就是命运。西方的思想至今仍在此命运的支配之下去思考存在者之存在”[2] (P252)。这也就是说,这三种理解的出现和存在是必然的。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恰当的。海德格尔通过对凡·高所画的一双农鞋的描绘最后得出的结论说:是艺术作品才让我们懂得了真正的器具是什么,只有在艺术作品里才有真理的发生。所以他把艺术的本质规定为“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2] (P256),这里的“真理”也即无蔽状态。
然而,这种本质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海德格尔说是由于在作品中发生了两件事:制造大地(Erde)和建立世界。“世界是在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命运中单纯而本质性的决断的宽阔道路的自行公开的敞开状态(Offenheit)。”[2] (P269)因而,只要一个世界开启出来,“世界就对一个历史性的人类提出胜利与失败、祈祷与亵渎、主人与奴隶的决断”[2] (P283-284)。关于大地和世界的关系,海德格尔说:“世界不能飘然飞离大地,因为世界是一切根本命运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境地和道路,它把自身建基于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2] (P270)这即是说,世界离不开大地,大地是它的根基,但世界总是想出离大地而显现;另一方面,大地也离不开世界,否则自身锁闭着的它也无从显现,但大地却总想把世界扣留住。因而我们可以说,大地乃被扣留的命运,而世界则是显现出来的命运,二者处于一种相依而“为命”的争执(Streit)状态之中。
设置入艺术作品中的真理则冲开了阴森惊人的东西,同时冲倒了寻常的和我们认之为寻常的东西,从而使人们可以借作品看到大地和世界的原始争执。所以,通过艺术作品人们就能看清其中展现出来的本真的命运。海德格尔所举希腊神庙的例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在对神庙描绘一番后说:“正是神庙作品才嵌和那些道路和关联的统一体,同时使整个统一体聚集于自身周围;在这些道路和关联中,诞生和死亡,灾祸和福祉,胜利和耻辱,丑恶和堕落——从人类存在那里获得了人类命运的形态”[2] (P262)。
总之,大地的扣留、世界的显现展现着命运本身既遮蔽又澄明的双重运作。在艺术作品中命运展示着自身。
2.科技:解蔽的天命
海德格尔指出,传统观念把技术视为工具和人的行为。然而,要弄清被视为工具的技术是什么就必须追溯到四重因果性。在进行了一番词源学的考察后,海德格尔指出“原因”建基于解蔽(das Entbergen)。所以,他最终得出结论说,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然而,统治着现代技术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Herausforden)。这种促逼促使人专注于把一切现实事物定造为“持存物”(Bestand)。他把这种促逼着的要求命名为“座架”(Ge-stell),并将之看作现代技术的本质。
可见,“座架”指点给人们的是一条解蔽的道路。然而,“给……指点道路”在德语中就叫做“遣送”(schicken)。利用schicken与Schicksal和Geschick在词源学上的关联,海德格尔指出:“我们以‘命运’一词来命名那种聚集着的遣送,此种遣送才给人指点一条解蔽的道路”,而且“一切历史的本质也都由此而得到规定”。可见,他对命运的理解又前进了一步。此时“命运”指的是聚集着的遣送,它不再像《存在与时间》中那样等同于历史,而是历史要由命运来支配和决定了。所以,“人类行为唯作为一种命运性的行为才是历史性的”,“而且唯有进入对象化的表象活动中的命运才使得历史性的东西作为一个对象而能为历史学(也即一门科学)所表达”[2] (P942)。
既然座架是一种解蔽方式,而又只有命运的聚集着的遣送才能指点一条解蔽的道路,所以,“座架就像任何一种解蔽方式一样,是命运的一种遣送”[2] (P942),“座架归属于解蔽之命运”[2] (P943)。因而,海德格尔的结论是:“技术之本质居于座架中,座架的支配作用归属于命运”[2] (P944),也即是说,支配着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归根结底乃是“命运”。然而,“由于命运一向为人指点一条解蔽的道路,所以人往往走向(即在途中)一种可能的边缘”。也就是说,命运每次只为人们指引唯一的一条解蔽之路,于是人们就会执迷地忘记解蔽的方式并非只此一种。因而“解蔽之命运作为这样一种命运,在其所有方式中都是危险,因而必然是危险”[2] (P944)。而“如果命运以座架方式运作,那么命运就是最高的危险了”,因为“作为命运,座架指引着那种具有定造方式的解蔽……它便驱除任何一种解蔽的可能性”[2] (P945)。
综上所述,虽然“技术之趋于到场,若无人的本质之趋于到场的协助,便不能被引入其天命的变化”[6] (P145),但是,现代科技的产生和存在归根结底取决于解蔽的天命,“存在者是否显现以及如何显现,上帝与诸神,历史与自然是否进入以及怎样进入存在的澄明,是否以及怎样在场与不在场,都是人所不能决定的。存在者的到来在于存在的天命”[2] (P374),而“技术在其本质中实为一种付诸遗忘的存在的真理之存在的历史的天命”[2] (P384)。
具体说来,这乃是因为正是在这一天命的统治与支配下人们对存在和命运的理解发生了一个堕落的过程。“在西方命运的发端处,各种艺术在希腊登上了允诺给它们的最高峰。它们使诸神现身当前,把神性的命运与人类命运的对话灼灼生辉。”[2] (P952)然而,时至现代,人们把存在只是理解成为作为主体的人所支配的客体和对象,人成了存在的主人。现代科技就由此而开始产生。于是,对于已被吹得无比膨胀的现代人来说,命运简直成了无稽之谈。当然命运之运作的微妙和威力也就无从被体验了。
总而言之,对于后期海德格尔来说,现代科技乃是解蔽的天命,乃是作为既遮蔽又澄明的天命的现实运作的必然产物。
3.语言:带来天命的消息
在后期海德格尔看来,“人之说作为终有一死者的说并不是以自身为本根的。终有一死者的说植根于它与语言之说的关系中”[2] (P1002)。所以,语言(Sprache)对人来说是命定的,它就像无所不在的磁场一样弥漫于人的周遭。不论是在大声地喧哗还是在沉默地行动,人们总是不断地以某种方式而在说,“这乃是命运的法则/一切自行体验/即便寂静返归/也有一种语言存在”[2] (P1085)。
海德格尔指出,语言在允诺(Zusprache)中以独白的方式而自身“道说”(Sage),即显示(zeigen),让显现,让看和听。道说在既遮蔽又澄明之际向人们允诺一个世界,否则一切都将陷入暗冥之中。因而,“语言乃存在的家”。也正因此他认为语言并非属于“存在”(ist)的东西,对于语言来说我们只能说“它给出”(Es gibt)。给出什么呢?就是“存在”。因而,关键问题在于:这个“Es”(“它”)又是什么呢?
对于Es gibt中的这个“Es”,海德格尔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Ereignis,并说它是在道说之显示中的活动者和允诺者。又说对于这个在道说中运作的Ereignis我们只能这样命名:它——Ereignis——成其本身。这又怎么理解呢?也许下面这句话透露了真情:Ereignis“乃是一切关系的关系”[2] (P1148),这不能不让我们想起一个词:“凭空缘起”。因为这“凭空缘起”就是指无根无据地形成一张无穷无尽的关系之网。海德格尔的这个玄之又玄的Eregnis,实际上指的就是决定宇宙万有之间能否形成关系以及形成何种关系的东西。而且按照海德格尔对其动词意义的强调,我们也可直接把Ereignis理解为一切关系的形成运作。
然而,Ereignis一方面使在场者得以出场而存在,但另一方面它又听之不闻视之不见,即总是遮蔽着自身。Ereignis就是这既遮蔽又澄明的双重运作。但它何时、怎样遮蔽又何时、怎样澄明,却非人力所及,乃取决于天命。如张祥龙先生指出的,“缘(分)才是根本的命运”[7] (P88)。海德格尔自己也说,“干脆,我们从属于‘它’的给出的特点出发去思‘它’”。
“从作为天命的给出,作为澄明着的到达的给出出发去思‘它’,而就天命植根于澄明着的到达而言,这两者又是共属一体的。”[2] (P681)于是,我们有理由说,Ereignis即天命(刘放桐先生已将之译为“天命”了[8] (P353)。另外,此时海德格尔一再强调,Ereignis并非“存在”的一个名称,而是从根本上不同于“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是由Ereignis派生出来的。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海德格尔的“命运”、“天命”再次“升级”,它不再归属于存在,当然也更不归属于历史。相反现在存在和历史都归属于天命,是天命派遣和发送出了存在和历史。所以,波格勒指出:“海德格尔后来关于天命(destiny)和居有事件(appropriative event)的谈论,不可以再用历史来理解了”[4] (PXV)。
海德格尔说,“任何一种本真的语言都是命运性的(geschicklich),因为它是通过道说之开辟道路才被指派、发送给人的”,“决没有一种自然语言是那种无命运的、现成自在的人类自然(Menschenatur)的语言”[2] (P1145)。而斯退芬·格奥尔格诗中的那位会命名的远古女神就是这一事实的象征。
所以,语言必然能带来天命的消息。人与语言的关系的转变,只有通过应和于道说带来的天命的消息才会出现。然而归根结底这一转换也非人力所能左右,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只有作为Ereignis的天命。所以,海德格尔说:“转换触及我们与语言的关系。此种关系取决于天命,即我们是否和如何被作为Ereignis之原始消息(Ur-kunde)的语言本质扣留到大道中”[2] (P1148)。
总而言之,后期海德格尔所谓的语言即是天命自身的显示,从而能为人带来天命的消息,而天命则在语言中给出自身。
三、人与天命:人乃澄明的天命
关于人的本质,海德格尔指出“存在是天命善于投的,此在就是作为天命善于投者的存在之抛中成其本质的”[2] (P371),所以,“生存只有就人的本质才说得上……因为就我们所知看来,只有人堕入了生存之天命”。所以说“生存是称呼人在真理的天命中所是的东西的规定”[2] (P371)。这里所谓的真理无蔽或澄明状态。所以,缘在乃天命的澄明之所。然而,“这个澄明作为存在本身的真理而出现,这件事本身就是存在本身的天命。这就是澄明的天命”[2] (P380)。所以,归根结底,缘在作为存在的澄明之所乃是基于澄明的天命,作为缘在的人就是澄明的天命。
然而不幸的是,自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都在歪曲地理解着人的本质。不过这并非人为,而是基于天命而致的存在的遗忘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诸神逃遁,大地消隐,于是人失去了“家园”。所以海德格尔说:“家的内在本质是一种天命或如我们现今所说的历史。然而,由于天意安排,此本质仍未完全被给出来。它仍保留着。因此,那唯一符合天命即恰当的东西也仍未被发现。”[8] (P227-228)在海德格尔眼里这无家可归状态成了整个世界的命运。但是,“命运决不是一种强制的厄运。因为,人恰恰是就他归属于命运领域从而成为一个倾听者而又不是一个奴隶而言,才成为自由的”[2] (P943)。因此人需要做的不是去对抗天命,而是倾听天命的消息。谁能做到?诗人与思者。
海德格尔指出,在我们这个处于无家可归状态中的时代里,诗人通过与诸神的对话能在与诸神的相互需要中直接截获“神圣”所赠与的暗示。在这种对话中诗人倾听并应答诸神的要求,为诸神及存在者命名,从而为人营造栖居的家园。所以海德格尔说,只有做诗才首先让一种栖居成为栖居。而“栖居”的基本特征则是守护,即“留神关注,关注曾在的和将到来的存在之天命”[2] (P1185)。就在这种对存在天命的守护中作为天、地、神、人四方的纯粹性的四重整体(das Geviert)发生了。在其中天地神人相互发出召唤的声音,“在此四种声音中,命运聚集了整个非有限的关系”[10] (P134)。在此关系中它们相互缘起成为一相互映射的游戏。这游戏也即Ereignis,也即天命。也就是说,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运作就是天命。在这运作中,人被天命纳入了本己的命运中。唯有如此才有人的本真的生存。所以,海德格尔说:“此游戏作为命运给我们传递了存在和根据”[10] (P78)。
海德格尔认为,诗人通过做诗探听到天命的消息,并转达给人类,这乃是诗人的责任,“源出于一种天命的责任”[2] (P316)。这也是海德格尔极力推崇真正的诗人的根本原因。如他自己所说:“那自身属于存在命运和那出自存在命运的显明是为诗人准备着的。”[11] (P86)而且这也是海德格尔说诗思同源的根本原因,即二者都源出于天命。
思者的情形又如何?海德格尔说,“虽然世界天命在其本质来历的各基本点上都还是被欧洲规定着的”,但是“没有一种形而上学……还能够追上这个天命”[2] (P384)。这就是说,实质上现代人并不思。而这乃是因为现代人的思是一种计算性思维,它唆使人逃避真正的思,即沉思之思。
那么,如何才能追上远逝的世界天命呢?通过“返回步伐”,“即从形而上学而来返回到形而上学之本质中,从差异之为差异的被遗忘状态而返回到自行隐匿着的分解之解蔽的命运之中”[2] (P842),也即去重新领会命运的原始本真的可能性。所以他说:“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那个充满迷雾的返回步伐,即返回到一种思索,这种思索关注着那个存在之天命中预先确定的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转向(Kehre)。”[2] (P1186)而存在之被遗忘乃是人无家可归的最终根源,所以,沉思之思所要追赶的天命就是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因此,海德格尔说:“思从事于存在的家之建立,存在的家起存在的组合的作用,存在的组合总是按照天命把人的本质处理到在存在的真理中的居住中去。”[2] (P400)也正因此,“把存在作为真理的天命来说,而且要说得适合天命,这就是思的第一规律”[2] (P405)。沉思之思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通过采取一种态度,即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性的虚怀敞开,也就是应和天命之召唤而去思。
另外,海德格尔还指出,真正的思并非与行动截然对立,它“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自己在自身中行动,这种行动是处于与世界命运的对话中”[2] (P131)。所以,思者通过沉思之思能够倾听到天命的消息。然而,思之作用也仅止于此而已,因为“现代的主体性之自由完全消融于与主体性相应的客体性之中了。人不能凭自力离开现代本质的这一命运,或者用一个绝对命令中断这一命运”[2] (P921-922)。
总而言之,海德格尔关于人的本质之思表明:人乃澄明的天命。然而,只有诗人和思者才能像赫尔墨斯那样成为诸神的信使“带来天命的消息”[2] (P1033),从而使人守护住它的这一本质。
注释:
①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命运”一词用在作为个体的“缘在”(Dasein)身上,而把共同体和民族的演历(Geschen)称为“天命”(参见中译第二版,第435页)。在后期,海德格尔将这两个词混用,二者的含义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不过,后期海德格尔还是偏向于多用“天命”这个词。本文对这两个词的含义也不做区分。所以,为了简便起见,本文的题目以人们更常用的“命运”来概称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