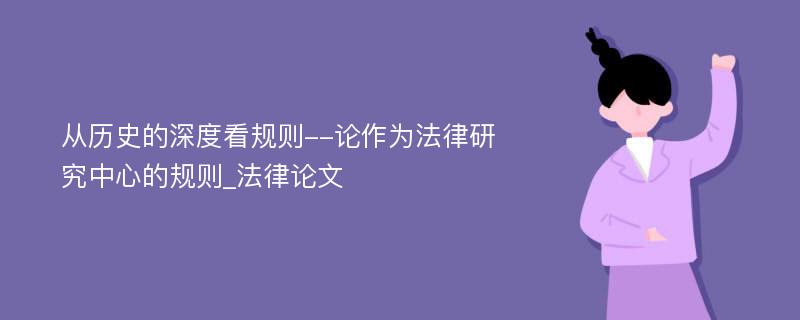
历史深处看规则——论规则作为法学研究的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则论文,深处论文,法学研究论文,历史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28(2008)01-0035-12
一、法律史研究的可能视角
如果法律史只研究朝廷或国家颁布的律、例、令、章程等,那么,这门学科几乎快要走到了它的尽头。以近代法律史研究为例,这一时期留下来的法律文献较多,大约20年前,学界对它的重视还远不如今天,但现在,如果把公开和未公开发表的研究生论文加在一起,可以说,这一时期各种重要的部门法都被梳理了一遍。而且,不同学校的研究生论文之间出现重复选题的已不少。我们不是要否定国家法的重要性,但现状是只把国家法当成法律史的研究对象,甚而有认为,只要把立法过程、法典内容讲述一遍,就算大功告成,连司法的情况都很少顾及。这种研究很可能会将法律史的研究带入死胡同。因为,一开始可能发现领域很广,可以信马由缰,跑马圈地,到处找那些尚未发现的法律文献,不久,当出现了上面说的所有领域都被写过的局面后,研究生就只好重复作业了。于是学科研究陷入僵化和萎缩的状态。只把国家法作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态度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法的理论之上的,这将在后文讨论。现在需要来看看在法的历史中,哪些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先来看看外国法律史的研究状况,我们知道,如果仅把国家法放在中心,而不去了解那些实际运作的规则或制度,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律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
比如古希腊的法律。倒不是说古希腊城邦没有国家法,但即使有,也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目前能看到的古希腊时期较为完整的法律只有《格尔蒂法典》,是19世纪中后期(1854-1887年)逐渐发现的,即使这部法典也只是克里特人的法。古希腊世界中,城邦林立,希腊民族之内又有三个大的种族,即爱奥利亚人、伊奥利亚人和多利安人,克里特人的法律最多只能代表多利安人的法。那么,难道没有这部法律,古希腊的法就不能研究了吗?当然不是,从学术著作、演说词、碑文、文学著作等非国家法文献中,人们仍然能够了解古希腊的法和法观念。在这一点上,古罗马的情况也大致相通,在《十二铜表法》之前,罗马人没有自己统一的法典,但这不能阻碍人们研究古罗马王政时期的法律状况。显然,对于国家法文献未能流传下来的时代,法史学者毫不犹豫地采用了非国家法的文献去阐述古代法,这时,作者和读者都不会问:“它们是法吗?”实际上,不会有人在此时想起“法必须是国家法”的观念。
让我们举例说明这个问题。从现有的资料看,当古希腊进入到有国家法的时代之后,仍有许多重要的法律规则不是成文的。比如,有学者考察古希腊的审讯规则后指出,古希腊在审讯时虽然采用刑讯,但刑讯仅适用于奴隶,且奴隶的证言只有在司法刑讯下才是有效的。[1](P7)而自由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或公民是禁止提交司法刑讯的。他们只要通过誓言就可取得信任。其原因在于:古希腊人认为,自由人若发伪誓,“将使他的子孙在将来承受严重的惩罚”,而“一个奴隶不能充分的预期自己的未来的后果,他只关心他当下身体的舒适感。”[2](P66)可以发现,这一规则与古希腊的社会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如果不理解古希腊人关于神、家庭和盟誓的观念,是无法理解这一规则的。盟誓的观念在不同民族社会的早期都曾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古罗马,同样有“逼供的刑罚只用于奴隶”这样的规则,[3](P136)就是因为奴隶没有资格盟誓。在古罗马王政时期,私人之间的契约无法请求国家的保护,也是因为私人契约除了诺言之外,还常常加上盟誓,而“背誓者害怕神诛,所以畏惧神诛也是债主的一种保障。”[3](P138)对于审讯、盟誓等规则,以及相关的家族延续、神的惩罚、奴隶与自由人的区别等观念,都没有出现在古希腊的国家法中,但在法律史研究时是否可以弃之不顾呢?当然不是。所以,关键是如何看待“法”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法”等同于国家法,那么,法的历史就成了国家法的历史。法律史研究也就庸俗化为国家法历史的研究。而如果我们的理解不是这么狭隘,那么,国家法则可成为我们认识和接近古代法的线索。
为什么说国家法只是为我们提供线索呢?因为,国家法并不能反映我们所要认识的古代法的全貌。让我们用中国清代的立嗣规则来继续说明。研究中国法律史的学者都知道,立嗣或立继是古代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最容易引起纠纷或诉讼的一种社会关系。在我们能看到的各朝律典中,均有关于立嗣的规定。明清两代引例入律,关于立嗣的国家法规定更加详细。大部分关于“立嗣法”的研究,都要引用《大清律例》中的“立嫡子违法”这一律条及附例。因为该条正面交待立嗣的顺序:“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这一规定成了后人确认古代立嗣顺位的重要依据。按照这一规定,亲兄弟的儿子即胞侄处于继子的第一顺位,有胞侄可以立继时,堂侄、从堂侄、族侄等无从置喙。没有胞侄,再以服制远近逐次择立。但事实上,当没有胞侄的时候,一般来说当然选堂侄,没有胞侄和堂侄时,一般来说当然选从堂侄。真正引起大量立继纠纷或诉讼的,是因为同时有几个胞侄;或者没有胞侄时,同时有几个堂侄等情况。也就是说,在服制相同的情况下,该如何选择嗣子?关于这一问题,答案在国家法中是找不到的。但通过其他材料却可以知道,有一项规则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这项规则的名称叫“长房次子”①。意思是说,在服制相同的情况下,立继应从长房开始排序,但长房长子不能出继他房,所以,就从长房次子开始往后排,长房无子可继,往后为次房次子,次房无子可继,则往后为三房次子,依此类推。这个规则,在古代又称“挨继”或“序立”。违反“挨继”或“序立”的,则被斥为“搀继”或“挜继”。
要是不懂这项规则,好多古代立继方面的案例都看不懂。比如,徐士林审理过一个案件。孀妇吴阿王是吴章斌之妾,曾生子吴习科,习科已亡。因近支无孙辈可继,族内公议以旁支之孙继习科。但吴阿王不愿,认为习科未婚而亡,不如取亲支之侄继章斌。官司打到了徐士林那里,徐赞成吴阿王的意见,接着问她喜爱亲支内的哪个侄儿?徐士林的判词中记载了吴阿王的选择:
随谕吴章鳌等开具亲支诸子名呈阅。面讯阿王所爱,立答以愿立章鳌次子名端者。查章斌同曾祖弟,首章浣,浣仅一子,不便承继。次则章鳌,鳌五子,择立其次以继章斌,论序论爱,均属相宜。[4](P601-602)
注意判词中的记载,徐士林问吴阿王的是“所爱”。“爱”即“爱继”。按清例的规定,只要昭穆相当,父母可择立自己喜爱者为子。但吴阿王是妾,能否“爱继”在两可之间。徐士林这样问,明是要为吴阿王作主,使其可以任择一位自己喜爱的房侄为继子。但徐士林一查族谱,发现吴阿王“愿立”之侄是次房次子。又发现长房为独子,不能出继。次房长子要承重本房,也不应出继。因此,吴阿王所谓“愿立者”,正是按照“挨继”顺序应继之人。对此选择,徐士林大加赞赏,说:“论序论爱,均属相宜”。所谓“论序”,就是指的“挨继”或“序立”,但整个判词中并未提到“长房次子”或“挨继”等字眼,如果不懂得“挨继”规则,对徐士林的赞赏肯定会莫名其妙。
规则并不是国家法,在有的案件中,官府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突破这些规则。如果不小心引用了这些案件,再加上过度诠释,就会使结论出现舛误。例如,《樊山判牍》是后人较为推崇的清代案牍,研究清代法律和社会时,往往会引用这一文献。但却应该很小心,因为樊樊山判案之所以为人称道,是因为他使“良善者有所劝,而无情者不得尽其辞”。[5](序言)
我们来看这个案件:史家兄弟三人,史念南是老三,有子三人。二兄在战乱中殒命,绝后无子。长兄有子二,长子史垂青,次子史继青。史垂青作为长门长子,不与胞叔史念南商量,也未写立立嗣文书,即以史继青入继二房。将二房遗产分为三份,大房得2/3,三房得1/3。官司打到樊樊山那里,樊樊山批评史垂青“藐尊霸产”。[5](P145)
我们说过,看樊樊山的批词,一定要分清谁是“良善者”,谁是“无情者”。这个案件中,史垂青乃长门长子,是为大宗。史念南虽居三房,却有史垂青胞叔的名分。史垂青以胞弟出继二房,是按“长房次子”的规则办理。但在樊樊山看来,史垂青却是“无情者”。说他“藐尊”,是指这么大的事情不和胞叔商量,目无尊长;说他“霸产”,是说他不立继书,不商同亲族,立嗣手续不全。
樊樊山要教训“无情者”,但史垂青在“长房次子”这一点上没有错。而如果承认史垂青是对的,就不能替“良善者”找回“面子”。要作好这篇批词着实不易。樊樊山是这样决定的:
查二门既已过绝,所有家产,应令长三两门,各得一半。二门禋祀,亦应令长三两门,各出一子承继。方昭公允。而本县留尔体面,不加惩责,仅照史念良(二房已故叔名)原管,将二门之业,作为三七劈开。长门得其七,三门得其三。[5](P145)
这个批词下了一个多月,史垂青“抗不遵断劈分”。后来,樊樊山不知用了什么强硬手段,才让史继青“畏罪改过”,“向其叔承情服礼”,算是为史念南找回了“面子”。不过,如果知道“长房次子”的规则,对这个批词,就有诸多可议之处。其一,一般来说,只要族中有子可继,就不采用“并继”。徐士林曾论道:“夫继定于一,争端乃息,间有朋继者,乃斟酌于爱、序之间,不容偏废。故以人情通理法之穷耳。”[4](P536)所谓“朋继”,即指多人入继,是“并继”的别称。这段话是说,“序立”和“爱立”是正常情况,“并继”只在特殊情况下通融人情时偶尔为之。但即使“并继”,也必须以“序”和“爱”为基础,不能违背“序立”和“爱立”原则。②樊樊山硬让两房并继也罢了,但他又不指定出继的适当人选,只是将二房产业作三七开。这使史姓族人无论如何都难以办理。因为,不为二房立继,就无人有资格承受二房产业。如果为二房立两个继子,那么,两个继子的身份就是平等的,该平分二房产业,岂能多少不均?这就是乱命了。其二,既然樊樊山要为史念南找回“面子”,就该让三房多得些产业。先前按史垂青的分法,三房得二房家产的三分之一,就是得了约33.33%。现在按樊樊山的分法,三房得二房家产的十之三,只有30%。这不但没帮着三房,反而让三房吃亏,真是乱中有乱了。有此乱命,难怪史姓族人无法执行。
樊樊山的本意是想助史念南找回尊长的“面子”,这个出发点在当时看来是好的。由于“长房次子”不是国家法,对于案件审理来说缺乏刚性的约束力,樊樊山要自立规矩也不能算是违法。然而,立继规则是在长期实践中沉淀而成。一项规则与其他规则相互牵连,“长子次房”就是为了解决服制相同时的立继次序问题,同时与限制“并继”相联系。樊樊山要撇开这个规则,必须解决谁应入继的问题,否则,服制相同的族侄就全都可以入继。然而,大家都入继到一户人家,其他族内人家绝户又由谁继?且入继为争财,一股脑地入继一家,家产难免分割细碎。没多少利益谁还愿意入继?
这个案件对我们认识规则的地位、国家法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关系都有启发。但这里只想说一点,就是规则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了解“挨继”或“长房次子”的规则,在阅读这些案例时可能会犯不必要的错误,比如,会认为樊樊山是在按照陕西当地的立继习惯法判案,并可能以此支持“在清代社会中,不同地方有不同习惯法”等结论。
总之,要研究国家法,却不可迷信国家法。认识古代法需要联系古代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需要联系国家法之外的规则或制度。国家法往往是粗线条的,它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却不能提供完整或真实的画面。当我们真的要接近古代法时,就会发现很多时候需要跳出国家法,此时,所有的历史文献都向法律史敞开,而法律史研究又何必把自己框死在国家法的圈圈里呢?
进而言之,有时候,国家法不但不能为我们提供真实的全貌,反而会阻碍我们认识古代法。很多人知道古罗马社会中的“家父权”极为强大,是因为在《十二铜表法》中第四表有明确规定:“家属终身在家长权的支配下。家长得监禁之、殴打之、使作苦役,甚至出卖之或杀死之。”此规定,使人产生了不必要的联想,仿佛古罗马的家长极为蛮横,并经常任意处置家庭成员和家庭财产。但这很可能混淆了极端情况和正常情况之间的区别。事实是,一方面,罗马法承认家长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父亲不能擅自剥夺子女的继承权,因为他既不能取消父权,又不能立一个经过整个民社许可的遗嘱,因为这一许可也会遭到拒绝,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常常遭到拒绝。”[3](P137)古罗马的父亲不但不能取消子女的继承权,甚至不能以自己的意思出卖祖产。因为在古罗马社会中存在着两个相对立的原则,“一是产业主有无限的支配权,二是家产应保全不散”。[3](P138)由此,如不了解古罗马的家产规则,仅凭《十二铜表法》的规定,不可能正确理解古罗马的法律与社会。
以上这些例子足以说明:第一,在法律史研究中,不能仅以国家法为据。国家法是为了规范社会关系,如果没有意识形态作怪,一般来说,国家法一定是确有所指的。因此,法律史研究必不能脱离社会史研究而进行。同时,国家法也会反映政治体制或政治格局,因此,法律史研究必不能脱离政治史研究而进行。当然,如果涉及某种专门的制度,如货币、财政、人口等方面,则必不能脱离金融史、经济史、人口史等研究。而且这种对社会、政治或其他领域的研究,必不能泛泛而为。否则,法律史研究就会深陷于“就事论事”的泥潭中。而如果法律史能够抛弃门户之见,国家法中一条一款,均可发现有深意所在,则将来之研究,或有别开生面的气象。第二,法律史研究必须重视各种规则的研究。无论中外,国家法的条款都既有简明的优点,又有粗阔的缺陷,社会或政治生活的运作,必不能仅凭国家法而有效。这就势必要求在研究中深入到社会规则和政治规则中去。国家法之于规则,就像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不清楚规则的状况,也就不清楚法的整体形象。实际上,我认为,法律史以至于整个法学的研究,均应从以国家法转移到以规则为中心(论述详后)。在法律史研究中,国家法虽可提供线索,但还需要循此线索,顺藤摸瓜,找出支撑国家法的规则体系,才算有所小成。
二、法律史研究对法学基础理论的要求
很大程度上,国内法律史研究中出现的以国家法为中心的问题,是由我国的法学基础理论引起的,确切地说,是由我国正统的法的定义引起的,因为在我国关于法的基本定义中,已经对法学和法律史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定位。法律史不过是按照这个定位发展下去,最后发现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横向地看,在法学的各个学科中,也正是法律史学科对这一问题最为敏感。当法律史学者可以跳出所处时代的限制,去讨论古代法时,他最关心的是那些实际有效的规则,因此,如果国家法是有效的,它当然在法律史的研究范围之内。然而,如果在国家法之外另有有效的规则,它也当然会引起法律史学者的浓厚兴趣。因此,法律史学者本来就不应该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拘囿于国家法之内。关于这一点,在以往的讨论中往往是忽略的。比如,国外有学者在讨论法学史家和法律学家的关系时,曾对二者的基本差别有过这样论述:
法律学家是从现存的情况出发并且是为了这种现存的情况而理解法律的意义。反之,法学史家没有任何他要从之出发的现存情况,他只是想通过建设性地考虑法律的全部应用范围去规定法律的意义。法律的意义只有在所有这些应用中才能成为具体的。所以法史学家不能满足于用法律的原本应用去规定该法律的原本意义。作为历史学家他将公正地对待法律所经历的全部历史变迁,他将必须借助于法律的现代应用去理解法律的原本应用。③
我不认为这一论述可以涵括了法史学与法学之间的所有差别,因为它过多地考虑了“法律的原本应用”或“法律的现代应用”,它所讨论的“法律”就是“国家法”,不过,它强调国家法在不同学者的眼中所看到的不同意义,对我们是有启发的。然而,这还只是法史学不同于部门法研究的一个方面。的确,法史学者在国家法的理解上不同于部门法学者,是因为他必须考虑法的时间性。在一个法史学者看来,没有一种法律是当然地可以一直存续下去,它总有发生、兴盛、衰亡、转变等过程,这些过程又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等各种因素相联系,所以,在法史学看来,即使是在文字上毫无变动的法律条文,它的理解与应用也在时间变迁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上引论述所要表达的主要含义。然而,从更基础的层面上去看,法史学和法学在关注的对象上还存在极大差别。只要注意观察,就会发现很多法史学者在讨论古代法时,不会把自己限制在“国家法”这个概念中。因此,回过头来,清理法的概念和定义,对法史研究也极为必要。
任何一个现代学科都有自己核心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最重要的内容,一般来说,某一学科的名称即由它的研究对象而来。比如,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这些学科名称都是以研究对象来标志的。某种程度上,研究对象的定位与定性,决定着这门学科是否成为一门科学。一门学科是否可以定位为科学,我的理解,可以用两个条件去衡量:(1)它的研究对象是否为具有实在性;(2)核心的研究方法是否为实证的,且这一方法能否帮助研究者有效地认知研究对象。乍一看这两点,立刻会有人批评我陷入了实证主义的陷阱。实证主义在当代哲学中身价大跌,现在国内学界如果要讨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或方法论,总是会以现象学、哲学解释学或语言哲学等流派中的理论为依据。我并不反对这种谈论,只是这些流派并不拒绝讨论对象,而是注重讨论对象的合法性。以语言哲学为例,逻辑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的区别,是究竟以逻辑语言还是以日常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但它们之所以都在语言哲学的范畴内,是因为,在必须将语言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上,其观点是一致的。而这种将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观点,是以承认语言更具有实证性为基础的。在这一意义上,现代哲学只是超越了古典哲学中那种经验的、“表象的”实证性,因此,在现代哲学体系中已经不再出现“实证性”或“实在性”一类的古典哲学概念。④然而,从更加深广的意义上看,这些哲学体系是在扬弃古典哲学关于实证性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提出对实证性的新的理解,也是在这一意义上,现代哲学继续承担着论证哲学的科学性的任务。
另外,把“实证性”或“实在性”作为衡量某一学科的科学性的标准,并非贬低非实证的方法。任何学科和方法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科学也不例外。实证性只是针对科学范畴下的各学科而言,文学、哲学、史学、神学、伦理学等学科,其核心领域或主要领域虽不具有实证性,却不因此动摇它们在人类知识中的重要地位,适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这些学科是无知的表现。因此,这里强调的只是,如果一门学科要具有科学的品质,或者,一门学科中具有科学性的那一部分,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实证性。
按照加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观点,科学的致知方法是说明,哲学的致知方法是认识,史学的致知方法是理解。即与一般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不同,在哲学和史学中,体验、领悟、审美、整体的理解,以至于主体与对象的互动交流(哲学诠释学)、“对现象的凝视”(现象学)等,甚至道家所谓的“玄览”或“玄鉴”,都比实证性的说明更加重要。“哲学”的古希腊单词是“亲近智慧”的意思,⑤所以,在柏拉图对话录中,既有分析性的《普罗泰戈拉篇》,又有沉思性的《斐多篇》、审美性的《会饮篇》,这些综合性的观照与思索,都不是仅仅用“科学”二字所能概括的。而史学,当希罗多德用“历史”这个希腊单词来为他的巨著命名时,就是希望人们不要把他的书误解为仅仅是众多事件的记录文本,因为这个单词的核心涵义为“研究”和“探索”。[6](出版说明P3)也就是说,除了考虑真实性之外,史学还应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但很清楚,这些方法的运用,与说明性的研究是不矛盾的,或者说,把说明性的研究作为这些学科的基础,应该是妥当的。
同样,在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中,也少不了整体的理解、领悟等,也就是说,少不了哲学和史学的成分。但这不能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可以不顾自己的科学任务的借口。因此,我们的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尽管法学一直划入“社会科学”的范畴,但法学可否冠以科学的称号?或者说,法学是否僭用了科学的称号?这是我们在研究法和法的历史时,常常会碰到的。
我国的经典的“法”的定义是这样的:法是统治者⑥意志的表现,由国家强制力⑦保障的社会规范。关于法属于“社会规范”这个范畴,虽然并不准确,但一般来说是没有异议的。至少,“社会规范”是一种实在的现象,并可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记录或证实。问题在于,这个定义对“社会规范”有一个限定,即法学所研究的是表现统治者意志的社会规范。而这一限定制造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联系。它反映在,根据这一定义,人们可以获得两个不同性质的解释:
解释Ⅰ、法是现存的社会规范中,统治者宣示或承认的那一部分。
解释Ⅱ、只有统治者宣示的才是“法”,(由于法必定包含在社会规范的范畴之中),从而这种“法”也当然的就是社会规范。
我们之所以认为以上两种解释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其标准即是实证性。对于解释Ⅰ,可以发现它一定是实证的,因为它必定存在于已知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实之中。对于解释Ⅱ,可以发现它可能是实证的,也可能是无法实证的。因为统治者的宣示不一定是一种社会事实,更不一定是一种社会规范。它很可能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对应的现象,也就既不可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也不可能适用一种说明性的研究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表面上,现有的法的定义采取了限定语的方式,使人们对它的科学性产生了信赖。而实际上,这个定义中的核心概念如“统治者意志”、“法”、“社会规范”等,它们之间的关系未曾限定,从而为扩张解释打开了缺口。因此,我们认为,关于现有的法的概念的非科学性或伪科学性,主要表现为核心概念之间的意义关联具有不确定性。
事实上,对这个定义的理解不可能采取解释Ⅰ,因为解释Ⅰ过分限制了法的外延。现实中的法律,显然不只是社会规范的一部分,它既与社会规范相重合,又有溢出社会规范之外者。比如,公法中规定的很多行政关系或权力关系,就是统治者创设的后果。因此,如果采用这个法的定义,则不可避免地会采用解释Ⅱ。而这种解释,不过是使人们对法的理解倒回到了先秦法家那里。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韩非子·难三》)其意即为,法只是国家或统治者所编辑和颁布的那些律令。但是,我们知道,先秦法家谈“法”的时候,还强调法应合乎时代与“人情”。如商鞅所谓:“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商君书·壹言》)又如慎到所谓:“法者,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慎子·佚文》)即使是韩非,也说:“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韩非子·八经》)我们知道,先秦法家的“法”的概念与先秦黄老有极大的渊源,而先秦黄老谈论的“法”是在“道”之下的,因此,黄老的“法”是离不开规律性与合理性的。[7]法家的“法”概念将黄老的“法”庸俗化了,但即使如此,也还未见得把“法”的合理性完全抛置不顾,在法家的“法”概念中,多少还有合理性的影子。而按照解释Ⅱ所理解的“法”,是更加庸俗化的定义,因为,按照解释Ⅱ,对法的讨论基本上可以不考虑法的合理性问题。
或者说,这个定义的目的,就是要为“口含天宪”争取地位。它的言下之意是,法就是我们说的,好坏你都得服从。因此,这个定义实际上是要为法的不合理性寻找借口,并由此排除了讨论的余地。当然,很多学者都意识到这个定义不妥,他们为这个定义曲为解释,希望能修正这个定义中的谬误,比如,将统治者的意志解释为能够反映社会利益,或多或少的具有某种客观性的东西。然而,这并不能掩盖这个定义的专断和野蛮。
科学是文明的象征。文明意味着优雅、宽容、合理性,意味着追求进步、独立见解、自由讨论、相互理解等等,同时反对专断和野蛮。这些均无需申说。需要明确的是,这个定义使得法学虽然一直僭用着“社会科学”的名号,却不能让人信服。理由很简单:(1)它宣称,自己的研究对象不是一种实体或实在。法学把某人或某些人的意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意志虽然可以间接地反映社会利益或利益格局冲突的结果,但“意志”自身是偶然的和主观的。无论辩护者如何打扮“意志”这个概念,都不能抹去“意志”的偶然性和主观性这两个特性。其中,偶然性又是其基本属性。把一种具有偶然性的事物作为学科的研究对象,很难说这个学科中还能为独立见解、自由讨论以及相互理解留下多少空间。(2)无法用实证的方法去研究意志。物理学家用实验去分析某一事物及其结构;数学家用演算去验证某一定理;地理学家通过实地勘测去确认某种地质地貌;历史学家用搜集文献、查阅档案等方法去复原历史;社会学家用田野调查去认识某种社会现象。这些实证的方法,虽不能一举解决所有的科学问题,但每一步工作都是有成效的,它们可以被证实或证伪,从而形成有效积累。在这些科学方法的指导下,人们才有信心在认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时不断获得进步。但“意志”,除了自己以外,他人无法用科学方法得到。关于意志的研究,只有一种是有意义的,那就是“神的意志”。但那已不属于科学的范畴。既然意志本身是偶然的和主观的,且无法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而法又被说成是一种意志的表现,那么,法学还在多大层面上可以自称是一种科学?从这一意义上说,在现代学科中,法学既是最古老的一种,又是迄今为止仍不具有科学品质的学科。而这种现象,正是由研究对象的定位偏差造成的。由于这种偏差,法学只能充当统治者的跟屁虫的角色,把解释统治者颁布的法律或法令作为自己唯一目的和工作。
但我这样说,并不是主张,国家法不能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或者主张,国家法不可能通过实证的方法去研究,更不是要否定所有关于国家法的研究成果。我的意思是,应该斩断法学研究与现有的法的定义之间的联系。正如上文所提到了,如果不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家法必然会面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同时,即使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⑧大多数法律条文仍然需要客观地反映社会和政治现实。而且,只要意识形态与社会观念不是分离的,即当意识形态也是一般公众认识和解释世界的观念时,那么,意识形态同样也具有客观性。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宗教观念虽然不一定全都是科学的,但某一宗教在信奉它的社会中,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有意识形态并不为社会中大多数人所相信时,我们才可以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为虚伪的意识形态。也只有在具有虚伪性的意识形态下制定的法律,才不具有客观性。实际上,任何统治者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即不依赖于法的传统或知识积累,不依赖于社会现状和政治生态,凭空创造出体系性的国家法。而法只要具有客观性,它就可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它不但必须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但当我们在社会科学的层面上讨论它的重要性时,必须抛弃“国家法”这个概念,把“规则”或“制度”放在核心的地位。这样就能发现,规则或制度不但是法学研究的核心,而且也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核心。⑨也正因此,必须抛弃现有的关于法的定义,这个定义突出了法的随意性、偶然性和主观性,没有也不能概括大多数法律条文的高度客观性。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定义一直严重地阻碍法学各学科及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阻碍了公众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阻碍了人们在立法和司法中保持平和、中立和客观的立场。关于这一点,相信任何法学工作者都心知肚明。但是,只要仍保留法的这一定义,无论怎样为它曲为解释,都不能剥离它的非科学性。因此,重新界定法学的研究对象,并重新定义这些对象,已显得极为必要。
三、把“规则”作为法学的研究中心
关于“法”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狭义的解释,上引我国通行的法的定义,即属其中之一。另一种是广义的解释。所谓广义解释,是把一切成文法和不成文的规则均视为法。广义解释是一种接近实质性的观点,而它的缺陷在于无法保证逻辑自恰。它当然无法保持逻辑自恰,因为它是一种向狭义解释进行妥协的学说。广义解释的目的,只是畏缩地想把“不成文的规则”塞进法的范畴中,如果有人同意了这点微薄的要求,它就心满意足了。它不敢否认狭义解释中的谬误,在它骨子里,同样承认“统治者的意志”一定是法律,它无法想象如何可以否认这一点。它和狭义解释的实质,都是把法的表象和法的现象不加区分地合煮在一锅,只是浓度不同而已。因此,和狭义解释一样,法的广义解释同样是表象主义的。要刺穿法学表象主义的迷雾,不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检讨,而且要在学术语言或学术概念上进行创新。
新的概念必须满足如下条件:(1)它必须与实在相对应。按照“奥卡姆剃刀”:“若无必要,毋增实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如果要增加某一概念,它必须对应实在。没有对应的实在,不必增加概念;反之,存在某种实在,却没有对应的概念,同样会导致理论表达的模糊性。(2)它必须符合本民族的语言习惯。如它不符合日常语言的习惯,它就只会在学术表达和日常生活中带来混乱。以往用“不成文法”所表达的某些事物,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当某人的行为不符合某种交易习惯时,人们会批评他“违反规矩”或“不懂规矩”,而不会说“你违反了不成文法”。说某人违反“不成文法”,他会跳起来问道:“我违反了什么法?哪里有法?”并且轻蔑地反问:“不成文的也叫法?!”在生活中批评别人“违反了不成文法”,这违反日常语言的习惯。如果希望别人接受,被批评的人一定要是学法律的。当然,这个概念除了违反汉语的语言习惯和语言传统外,还因为它不能表达许多真正需要呈现的研究对象。(3)与前面两个条件相联系的,它必须具备足够的概括力或抽象性。也就是说,它能同时将需要表达的不同对象概括起来,当使用它们的时候,不会让人有突兀、生疏或“两码事”的感觉。而这又同时需要我们回到语言习惯中去,因为当我们在激动时脱口而出的那些词汇,才是最具概括力的词汇,同时,这些词汇一定满足与实在相对应的条件。
“规则”、“规矩”等词汇,正是我能想到的较合适的汉语词汇。先来看两个日常语言中的例句。
例句1:“你不守规矩”!
例句2:“你不按规则办事”!
这两个例句可以在许多类似的日常语境中出现。其出现时,意味着在某个领域中的确存在着一种有拘束力的事物,但这些“规矩”、“规则”究竟是什么,一时又难以表达。只有当人被反问“那是什么规则(或规矩)”时,才会逼使表达者逐渐将那一“规则”或“规矩”清晰地陈述出来。让我们接着考虑,当表达者被反问“那是什么规则(或规矩)”时,他会怎么说。他惯常是如此回答:“我们一贯是这样做的……。”或者说:“我们都是这样做的……。”或者说:“我们总是这样做的……”等等。联接在“一贯是……”、“都是……”、“总是……”之后的话可以有很多。比如,“一贯是三分的月息”(借贷方面的);“都是先交房屋一段时间后,再付尾款”(二手房买卖方面的);“总是由领导指定候选人”(选举方面的);等等。我们可以把“一贯是……”、“都是……”、“总是……”之后的话视为对某一规则的具体分析和陈述。在日常言语中,它们因不同的人而有不同的陈述方式,可能是简洁的,也可能是拉杂的。但只要得到旁人的认同,且能让不了解规则的人懂得该怎么做,就不会影响这一规则的实质内容。而且,最重要的是,关于规则的表达句不是应然句或祈使句,而是陈述句。其区别在于,当我们用应然句或祈使句时,我们表达的是想象的或可能的事物。而当我们用陈述句时,我们表达的是一直存在的事物。后者对我们来说,是“一直在那里”,是“从来如此”。它是可以观察的,可感受的,可用实证的方式记录并验证的。
无可否认的是,在今天,大量的规则约束和规范着人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人们无时不在确认规则、承认规则、澄清规则,人们利用规则肯定或否定他人的行为。大多数时候,法律离我们很远,而规则无处不在。一个人从生到死,可以不了解法律或只了解很少一些法律,但他却必得了解大量的规则。家庭、学校和社会,都无时无刻不在向个人灌输规则的知识,一个人可以一生都是文盲,但他却不得不学习各种规则。是否掌握了各种规则是衡量一个人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社会化”的重要标志。正如日常语言所反映的,当一个人能够基本上按照社会规则的要求去行动时,人们才称他“长大了”、“懂事了”;相反,当他不能够领会或掌握社会规则时,人们就叫他“不懂事”、“拎不清”。而当一个人明知道规则如何,却要反着规则而行动,人们就会认为他是“反社会的”、“有个性的”或“特立独行的”等。社会的或公众的评价显然具有一种强制的力量,很少有人能够长时期地超越时代或社会的限制,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均实施“反规则”的行为。但有些人可以在某个领域中总是采取“反规则”的行动,但他能否改变规则仍是未知数。也就是说,“反规则”的行动与规则可以同时存在。规则还在那里,大多数人按照社会规则生活,冷眼看待少数违规者,既不阻挠,也不支持。如果少数人通过“反违规”的行动获得了好处,那么,或许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反规则”行动中,并且,或许有一天会让所有的人参与进来。这意味着,原有的规则消灭,新的规则产生。然而,如果“反规则”的行动者处处碰壁,那不需要人劝说,“反规则”者终会返回到原有的规则世界中,至少,不会有人再加入到“反规则”的行动中。可见,与利益相关是规则的另一种强制力。大多数时候,“反规则”或违规行为意味着利益受损,而守规则是正常情况下维护现存利益的最佳策略。同时,如果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反规则”或违规行为也可能获取利益,这将成为规则发生变革的前提。社会评价和利益衡量是保证规则自我运行的基础,二者类似某种“自然力量”,由于它们的存在,很多时候无需警察、法庭等出面。
如果我们承认以上这些事实,那么,同时就需承认,规则具有一种实在性或实体性。如果一项规则在那里,那么,无论你喜欢与否,它都存在。对于一项规则,你可以说它是好的或者坏的,但却不能说它不存在。而用类似“不成文法”的概念,会造成一种误解,似乎“不成文的”即是非实在的或非实体的。实际上,“不成文”仅仅意味着不是文字记录的,并不意味着非实在。判断“实在”与否,最起码应以是否具有语言性为标准。规则当然是语言性的。传授和学习规则、解释和澄清规则、利用规则肯定或否定他人的行为,无不依托着语言,或者说,规则唯有获得语言的帮助才能成立和澄清。规则与法律在形式结构上只差文字这一形式,但这不是缺憾或疏忽,而是因为:(1)复杂和庞大的规则世界令文字难以应付;(2)很多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规则的价值和地位,也未将规则研究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来看待。就这一意义而言,以“成文与否”作为判断法的性质的标准,是一个肤浅的学说,它试图迎合人们的感觉经验,却屏蔽了需要认识的现象。对这一概念及相应的类型学说,亟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象学还原”。
因此,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断然拒绝将“成文性”和“不成文性”作为判断法的性质的依据。我们主张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即“成文性”和“不成文性”对于认识法的性质是毫无意义的,在今后关于法的认识中,应该打破这种以感觉经验为依据而形成的“自然拘囿”,不能突破“成文性”和“不成文性”的观念,就无法理解“规则”概念。因为,人们很容易将“规则”与“国家法”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而在这一对立中又隐含了“成文性”和“不成文性”的圈套。我们说过,应该彻底抛弃“成文与否”的观念,“规则”的判断标准不依赖“成文性”和“不成文性”。如果说“规则”也有对立面,那么,它的对立面只有一种,即“伪规则”。值得注意的是,规则的对立面不是“非规则”,因为“非规则”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世界。而所谓“伪规则”,是那些具有规则的形式,却不具有规则的实质的事物。“伪规则”对我们来说是耳熟能详的,不需要过多的举例。最典型的是一些国家法或具有国家法性质的文献,它们虽然创设或规定各种权力结构、行为规范等,但实际上并不具有其所宣示的效力。相反,真正的权力机构的等级关系和运行惯例或许是不能通过任何文献查到的,但它们才是规则,是法史和法学共同的研究对象。至于那些有文字记录的“伪规则”,即使有意义,也更多是作为规则揭示前的障碍而存在的。规则与伪规则在形式上的区别仅仅在于,规则可能是成文的,也可能是不成文的,但伪规则一定是成文的。显然,如果一百年后(相信到时候学术研究已经少了很多精神束缚),某个法律史家要阐述今天的法律体系,他会破除伪规则布下的迷阵,把揭示规则体系作为自己的任务,如果做到这一点,他就是成功的。相反,如果他把“伪规则”和“规则”掺杂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拿去给百年后的人看,他就是失败的法律史家。
我们所谓的规则,不仅是指那些有约束力的社会规则,它既包括各种有实际约束力的国家法,也包括各种实际有效的权力结构和行政程序、行政惯例等。但它不包括:没有效力或效力并不如它所宣示那样的各种国家法,即“伪规则”。这些伪规则的产生有着各种各样的情况:(1)它们或许来源于已经过时的规则,这些规则在过去的时间里有效,现在因各种原因被保留下来,当然,它们仍可作为法律史家的研究对象。(2)它们或许来源于人们对未来的构想,因此迫不及待地将其写入法典,但事实上由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条件不成熟,导致其无法具有拘束力。这种情况在较多地移植外国法,以及受宗教或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笼罩的国家法体系中很容易出现。(3)它们或许由于区域性发展不平衡,导致在统一国家内,某些地区有效力,某些地区没有效力。(4)它们或许由于阶层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社会条件的约束,导致在某些人口中有效力,而在某些人口中受到抵制。(5)最后,它们的无效或失效,或许仅仅因为违背了少数能够操纵规则的人的利益,这些人在某一领域或社会关系中,通过实际行动创设了新的规则,导致国家宣示的规则被废弃或搁置。
无论如何,最应该将规则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学科是法学,而且,也只有法学最适合这一对象。而法学如果要把规则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必须首先学会如何自觉地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区分规则和伪规则。但是,法学由于视野狭窄,却从不敢越过“成文法”的边界。因此,到现在为止,如果说法学研究还具有某种合理性,不过是因为现有的“成文法”中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社会和政治现实,这使得法学也不得不间接地关注和解释社会和政治现实,从而间接地将实在的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并把实证的方法部分地注入到它的以往研究中。但无论如何,法学不能证明它在自觉地、主动地研究那些需要研究的对象,到目前为止,法学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古典经学式的学问,当然,经学式的学问也可以是实证性的,因为通过阅读大量的历史和社会调查文献同样可以了解部分社会关系或规则。不过,另一个矛盾也存在于法学中,就是法学研究者本身是轻视历史学的,同时,他们也并不重视搜集社会调查文献。以法学中较为成熟的民法学研究为例,我们的民法学家,大多喜欢谈论“一说”、“二说”,直至“N说”。在法史学者看来,这种讨论更多的属于法律史的工作范畴。因为,这些不同的“某说”,大多是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再到近代社会以来,在民法学中层积下来的各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则的反映,以及不同时代的法学家在思考同时代出现的社会问题时,在自身所处的时代局限中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或解释。因此,问题就在于,(1)如果某一社会关系仍然存在于当下的中国社会,那么,在新的社会条件里,它是否有新的现象,以及能否有新的解释?(2)如果某一社会关系已经不存在于当下的中国社会,那么,是否有新的社会关系代替它,并且在这一社会关系中的规则体系如何?(3)除了这些社会关系之外,我们还面临哪些无法在“书斋里”看到的新的社会现象(包括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则)。唯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讨论“某说”对于法学才是有意义。就此而言,尽管一些法学家瞧不起案例分析的研究方式,但在我看来,迄今为止,追踪司法案件,并将案件中反映的新情况与现有理论相结合的解释,或许是法学研究中最具实证性的方法。
关于“规则”的基础性的讨论,在本文中仍然只能点到为止。但我想,一些基本的意思已经比较清楚了,它包括两个方面:
(一)法学应该把“规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中心。与“成文法”相比,规则才是一种实在。法学首先应该讨论实在的现象,然后才去讨论“应当如何”和“可能如何”。顺便说一句,我不反对在法学中讨论“应当”和“可能”这两个问题,任何学科在理论深处所隐含的思辩的和伦理的关怀都是正当的,更何况法律与正义本是一体之两面。我的意思仅仅是,在我们讨论深层次问题之前,首先应完成基础工作。
(二)法学只有把“规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中心,才能培养出自己的方法论或解释学。关于这一点,加达默尔早有清醒的认识,在他关于“法学诠释学”的讨论中,曾经明确地指出这一方法论的限制性:
所以法学诠释学可能性的本质条件是,法律对于法律共同体的一切成员都具有同样的约束力。凡在不是这种情况的地方,例如在一个专制统治者的意志高于法律的专制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存在任何诠释学,“因为专制统治者可以违反一般解释规则去解释他的话”(原著引瓦尔希语)。因为在这里,任务根本不是这样来解释法律,以使具体的事例能按照法律的法权意义得到公正的判定。情况正相反,君主那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意志能够无需考虑法律——也就是不受解释的影响——而实现任何他认为公正的事情。只有在某物是这样被制定,以致它作为被制定的东西是不可取消的并有约束力的地方,才能存在理解和解释的任务。[8](P423)
需要注意的是,加达默尔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即绝对专制主义(Absolutism),来说明解释学对“伪规则”的无效性。但绝对专制政府(Absolute government)真正存在于历史中的实例是极少的,[9](P1-3)伪规则并不一定以绝对专制主义为必要条件,这在前面已有分析。所以这个例子既能帮助我们理解,又可能局限我们的理解。加达默尔的真实意图是想说明:只有“被制定的东西是不可取消的并有约束力的地方,才能存在理解和解释”。
收稿日期:2007-10-23
注释:
①如在明末的《盟水斋存牍》中记载了不少运用此规则进行判决的案件。如“审得冯公珮祖兄弟七房,其第五房故绝,应长房次子公绰承继,此不易之例也。”(“搀继冯公珮等杖”审语)“但二房绝,则长房次子承继。长房次子又绝,三房廷钦以次男亚三入继,亦自成说。”(“争继陈廉等杖”审语)“陈明厚、陈明宜亲兄弟也。明宜以长房次子先承嗣于次房,理也。及明宜绝嗣,而以明厚之次子陈廉入继,亦理也。”(“争继陈廉等杖”布政司批语)参见[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542、543页。
②在《徐公谳词》中还有一件较为复杂的争继案件,是同时为婆媳二人立继。“断令两立,黄朝继忠宜,为阿查子,序也;黄二继登彝,为阿徐子,爱也。所有忠宜产业,二人均分,昭穆相当,情理两得,庶可相安于无事矣。”但实际上,这个案件是因为没有亲支子孙可以立继,较为特殊,不能算是规则。参见[清]徐士林:《徐公谳词》,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173页。
③参见[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18页。注意,这段论述是加达默尔引述德国学者贝蒂的论述,并不代表加达默尔关于法学诠释学的全部观点。但可以发现,在加达默尔以后的论述中,他和贝蒂一样,在讨论法学诠释学的时候,仅仅考虑了“法律”这个概念,并基本上把“法律”等同于“国家法”作为讨论的前提。这与我们在本文中涉及的“法”概念有很大的区别。
④除了语言哲学外,现象学呈现相同的特征。现象学的流派及采用的概念和论证路径较为复杂,不可能在三言两语中讲清楚,但在扬弃心理主义和主观主义方面,它和语言哲学是相通的。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体系中极为重要的“明证性”概念为例,这个概念就是要批判和扬弃心理主义的关于“自然条件”的重视。胡塞尔认为:“就明证性而言,心理学的任务仅仅在于探讨在明证性标题下所包含的体验的自然条件,即探讨那些根据我们的经验的证明,明证性在其中产生并消失的实在情况。……对它们的研究不会导致对精确内容的认识,不会导致真正的规律特征的明确普遍性,而只会导致模糊的经验普遍性。”参见[德]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163页。这段论述很能说明胡塞尔对于以往哲学的不满原因。他批判的是“心理主义”关于实在性的肤浅理解,而不是要抛弃实在性。但是,在进一步的论述中,胡塞尔引入了“观念”这个概念:“判断的明证性也服从于观念的条件。任何一个真理都是那些具有同样形式和质料的正确陈述在可能性上无穷和无限的多样性的一个观念统一。”“……作为观念的规律性条件却对任何可能的意识完全有效。”这导致后人动辄给他贴上主观主义的标签,这是对胡塞尔的最大误读。事实上,胡塞尔的“观念”概念同样具有实在性,但它也同样超越了以往关于实在性的理解。限于本文的目的,这些问题不再展开。
⑤希腊语的“哲学”(ΦιλοσοΦια)一般又译为“爱智慧”,但我认为“亲近”更恰当。其词根Φιλο来源于中Φιλικοσ(“友爱”、“友好”、“友谊”等意),做词根时可以连接动词和名词,派生出“喜欢狩猎”、“爱喝酒或嗜酒”、“好斗的”、“爱好喜剧的”、“爱农村生活的”,等等。可见,这种“爱好”或“喜欢”和非理智的、狂热的“爱”有区别。另外,ΦιλοσοΦια还有“有系统的钻研”、“科学的钻研”的含义,也可证该词的理性色彩。关于古希腊文“哲学”的翻译以及中Φιλο这一词根和派生词,参见罗念生、水建馥:《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57-961页。对古希腊文“哲学”一词的来源,参见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⑥或“统治阶级”。但“统治阶级”这个词在现在的大多数教科书中已不用或少用了。
⑦类似表达为:具有约束力、拘束力、强制力的。
⑧在任何历史时期,法律都难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也是社会事实的某种反映,在这一意义上,“意识形态”本身也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⑨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例,社会学研究者都知道,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应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但他所谓的“社会事实”,在很大程度就是我们所谓的“规则”或“制度”概念。当然,“社会事实”概念在涂尔干的理论中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比较成熟的表述是他在1899年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作二版序时的表述,在这段文字中,他直接将“社会事实”理解为“制度”:“有一个词只要把它的一般含义稍微扩大,就可以确切表达这个极其特殊的存在方式(指“社会事实”概念),这就是‘institution(制度)’一词。实际上,我们可以不曲解这个词的原意,而把一切由集体所确定的信仰和行为方式称为institution。这样就可以把社会学界定为关于制度及其产生与功能的科学”。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页。那些争论“社会事实”概念的学者,应该认真体会涂尔干的这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