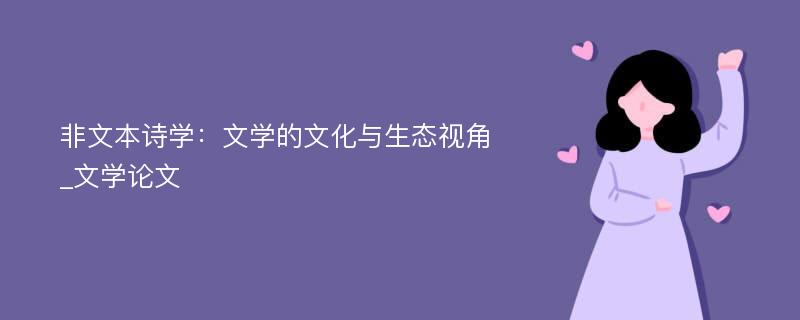
非文本诗学:文学的文化生态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视野论文,文本论文,生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伊始,中国文艺学界曾讨论文艺学的边界问题。这场讨论所针对的是90年代中期以来文艺学研究的泛化或“泛文化化”①倾向,即研究对象离开了传统的文学,扩展到杂文学、边缘文学、广义文学乃至非文学的娱乐和消费文化领域如广告、时装、房地产等等。人们觉得文学研究的领域未免拓展得太宽了,因此又提出回到经典的口号,希望重新找到文学研究的真正价值。其实,文艺学是否“越界”可能不是问题的关键。过去的文艺学,只要拿着“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把卡尺便可为千古文章定谳;如今的文化研究用“文化霸权”、“消费主义”、“话语狂欢”等几个标签就差不多可以打遍天下了。总结几条规律、贴上几个概念,似乎是文学研究的永恒法则。但问题是:除了这些法则,文学和文学研究就一无所有了吗?文学理论的创新只有炮制新词和扩大领地这两招吗?
也许我们需要退出传统的文学研究的理论起点,重新思考文艺学基本观念的合理性。所谓理论起点,就是在研究中不作为问题,而是作为自明的前提的基本观念。
基本观念之一就是关于文学研究对象的观念。虽然如今的文化研究已使研究对象大大泛化了,但仍然可以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文本”。从先秦散文到当代小说都是文学“文本”,这没有什么问题。而对于文化研究者来说,一则广告、一场角斗(罗兰·巴特例)乃至脱衣秀和恐怖袭击,都可以视为文本。当然,把《离骚》与超女选秀的文本并置在一起会令人觉得不伦不类。但当我们说它们都是文本的时候,其实已承认了它们之间的确有某些共同的东西。作为文学研究对象的文本尽管可以千差万别,但都会具有的基本属性首先是固化性质: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并且可以释读意义的对象。所谓文学研究,就是对某个客观存在物(文本)的研究。
基本观念之二是研究目的问题。传统的文学研究,直接目的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做出评判,而最终目的就是通过批评而确立文学的价值标准。无论是“历史的与美学的观点”,还是“现代性”与“被压抑的现代性”之争,都是试图把文学纳入某种评价体系中。确立价值标准的结果就是产生合乎标准的文学作品,即文学经典。
基本观念之三是研究的范式。传统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范式主要是归纳、概括和演绎,通过这些研究范式来发现和总结具有普适性的规律。
基本观念之四是研究的方法,既然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文本,也就意味着它的意义就蕴含在文本中,所以研究就是对文本的阐释、分析和评价。
上述四个方面的核心就是文本,文学研究就是研究文学文本的意义。这些观点之所以被称为基本观念,是因为它们很少被当作理论研究所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似乎具有理所当然的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文学研究归根到底都是研究文本的诗学。问题在于:文本的意义是否最重要?文学研究是否必然要以文本为中心?
丹纳曾经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出:“在翻阅一份手稿——一首诗、一部法典、一份信仰声明——的泛黄的纸张时,你首先注意到的是什么呢?你会说,这并不是孤立造成的。它只不过是一个铸型,就像一个化石外壳、一个印记,就像是那些在石头上浮现出一个曾经活过而又死去的动物化石。在这外壳下有着一个动物,而在那文件背后则有着一个人。”这段文字曾经被当代德国学者卡西尔在《人论》特别引用来阐释他的学术研究观念,即“把所有单纯的事实都归溯到它们的生成,把所有的结果都归溯到过程,把所有静态的事物或制度都归溯到它们的创造性活力”。也就是说,从文本的背后去寻找活的过程。
怎样理解这种研究思路呢?这里举一个清代学者方玉润研究《诗经》的例子。在《诗经原始》这部书中,方玉润在分析《芣苢》一诗时涉及关于解读和研究《诗经》意义的方式问题,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赖,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接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唐人《竹枝》、《柳枝》、《棹歌》等词,类多以方言入韵语,自觉其愈俗愈雅,愈无故实而愈可咏歌。即《汉府·江南曲》一首“鱼戏莲叶”数语,初读之亦毫无意义,然不害其为千古绝唱,情真景真故也。知乎此,则可以与论是诗之止矣。②
方玉润在这里提到的解诗之法所针对的正是无法以字句解读的民歌。他所谓“平心静气,涵泳此诗”,“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云云,就是主张不要拘泥于文本字句的阐释,而要运用想象,以设身处地体验的感觉来把握民歌韵味。
《诗经》虽被当作文学经典,但其中有许多诗类似《芣苢》,文本自身的意义简单到近乎空洞,使多数经学家和研究者除了穿凿附会几无计可施。而方氏的解读则是穿过文本去追溯和还原这首诗作为文学活动的原始过程,从而在对过程的想象体验中重构出诗的原始意义。关于方氏的解读是否属文人的臆解问题尚有争议,但《芣苢》的例子至少说明,把文学文本自身蕴含固定意义的想法作为预设前提而进行意义阐释和研究,这种传统的做法可能是靠不住的。方玉润的解读启示了一种超越文本意义的研究思路。
《芣苢》只是文本研究困境的一个方面例子。后代的文学发展历史中还存在着固化的文本与活态的过程之间的冲突问题。金圣叹在《西厢记》评点中说:“《西厢记》乃是如此神理,旧时见人教诸忤奴于红氍毹上扮演之,此大过也。”③在他心目中,案头化、经典化了的《西厢记》与舞台演出是不相容的。另外一个可以与金圣叹参照的例子是孔尚任为自己创作的《桃花扇》写的“凡例”,其中有几条是专门写给演出者的:
各本填词,每一长折,例用十曲;短折例用八曲。优人删繁就简,只歌五六曲。往往去留弗当,辜作者之苦心。今于长折,词填八曲,短折或六或四,不令再删故也。
旧本说白,止作三分;优人登场,自增七分。俗态恶谑,往往点金成铁,为文笔之累。今说白详备,不容再添一字。④
从孔尚任刻意安排的一番苦心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对舞台演出提出种种限制和要求,是因为优人会在演出中随意作一些即兴的改动,“点金成铁”,破坏了案头文本的完美性。这和金圣叹反对舞台表演的意思是一致的。
《西厢记》本来就是供演出的戏剧,金圣叹的反对似无道理。实际上他的态度反映的是明代文学的一种变化趋势;原来以活动的形态存在于民间的文学艺术如说话、戏曲等,经过文人的加工整理而逐渐成为更加完美成熟的文学文本。这个完美化的趋势使作品越来越符合经典的文学标准,也就是意味着越来越固化,而不再是活态的、即兴的活动过程,因而与原生态的、活的民间文学趣味之间产生了冲突。
金圣叹的经典观念至今仍然为人们所接受。关于对文学作品意义的阐释,习惯上人们相信意义是文学文本自身固有的,阐释和评价中的分歧源于评价者自己视野的片面,“知多偏好,人莫圆该”。如果能够做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自然也就可以获得文本的真正意义了。这种观念以文本的客观意义为理解的前提,因而也就预设了意义阐释普适性的可能。
然而《芣苢》的例子已表明,文学的意义并非仅由文本自身给出。经典化的文本代替不了活的发展需要。鲁迅曾经在《谈金圣叹》一文中批评金圣叹修改《水浒传》,说“《水浒传》纵然成了断尾巴蜻蜓,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从这段话的上下文来看,鲁迅的原意只是不满金圣叹删去了《水浒传》第71回以后的情节,似乎是因为金圣叹的删改而使得《水浒传》少了“武松独手擒方腊”的故事。其实这段故事即使在未经金圣叹删改的100回和120回的《水浒传》中同样找不到。这段故事不属于经典化了的《水浒传》,而是存活在经典之外的讲唱、传说和杂剧《水浒》故事系统中的一部分。这样一来,鲁迅举的例子就有了另外一种解释的可能性:老百姓真正感兴趣的或许不是经典,而是民间文学。
为什么“乡下人”非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不可?这段故事从经典艺术的角度来讲可能并不出色,但它属于“乡下人”所熟悉的另外一个《水浒》故事叙述系统。这个故事系统并没有因为经典化文本的出现而消亡,恰恰相反,它一直在经典之外生存和发展着。直到20世纪,《水浒传》的经典文本即使在金圣叹删改之后也已经固化了300年,而民间的叙述系统仍然存在而且还在生长,从中产生了像扬州评话大师王少堂的《水浒》评话那样精彩的作品。拿王少堂的《水浒》和经典化的《水浒传》作一比较就可看出,故事内容已经相差很远了。评话不是另一种固化了的经典,而是在一代代传人的即兴表演过程中不断变化、不断生长、不断丰富的叙述活动。它永远是叙述者和接受者直接交流的活动,是现场的、即兴的、互动的,是“活的”文学。金批《水浒》和《西厢记》虽然公认是最精彩的经典文本,却没有、也不可能阻止经典之外的文学活动。如果文学研究永远以金圣叹的尺度画地为牢,可能会遮蔽掉一大半活生生的文学经验。
如果离开了文本,文学研究还能够做些什么?所谓文本背后的“活的过程”究竟是什么?简言之,就是从文化生态的视野审视和研究文学。所谓文化生态,通常是指一定的文化形态与特定自然、历史和种种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学的文化生态,就是指与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具体存在形态相关的各种自然与文化环境,正是这些环境关系构成了文学存在的根据和文学意义的深层蕴涵。
文学的文化生态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首先,或者说最直接的就是文学文本与文学活动的关系。上面提到的丹纳和卡西尔的观点,就是认为文学文本的意义要从文本产生的文化活动过程中寻找。丹纳对希腊古典时期雕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以及英国文学史的研究,都是这种研究的例子。当人们谈到丹纳的实证主义艺术史观时,都会简单地理解为他本人概括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决定论。对实证主义的批评也是针对“三要素”说,认为这是一种外部条件决定论,否定或忽视了文学艺术的创造个性或主体性。卡西尔却注意到丹纳研究方法的另一个层面意义,即把文本回溯到活动过程这样一种从具体语境理解文本的思想,而这恰恰是丹纳之后20世纪学术思想进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批评者很容易从怀疑论的角度质疑:古典文本的具体发生语境早已消失,如何保证这种回溯活动语境的研究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确,像方玉润那样仅凭想象回溯《芣苢》的发生语境,其正确性是难以证实的。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却可以展开我们考察和理解文本意义的视野,使更多的文本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尤其是这种研究观念的自觉,将使我们得以保存许多尚未完全消失的活态历史语境的记忆;这对文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可能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其次,是经典文本与民间文化的关系。传统的文学史观只承认经典文学从最初的起源上讲来自民间文化,但很少真正关注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民间文化对经典化了的文学是否起着作用。然而如果把文学纳入文化生态视野,就应当注意民间文化对经典文学发展持续发生的影响问题。民间文化中的文学活动与经典化、文本化的文学之间存在着对立、差异和张力,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关系范畴:
就创作活动特征而言,是书写作品与口头创作的对立。前者是通过书写构造起完成的、固化的客观作品,而后者则是在口头传承中即兴发挥和不断演变中的叙述活动。
就文学接受活动特征而言,是文本阅读与表演观赏的对立。也就是金圣叹所主张的案头文学与他所排斥的“红氍毹”上表演的文学之间的差异。前者在叙述活动中叙述者与接受者是相互分离的,接受者是在独立语境中接受和理解作品意义的;后者的叙述中叙述者与接受者是共同在场的,文学的接受是一种现场互动的行为。
就作品性质而言,是固化的整体与变化着的母题的差异。经典文学的文本最基本的特征是完成了的整体性。而民间文学只有核心母题是通过传承而持续存在的,由母题扩展形成的作品整体其实是在传承过程中不断重复生成的。当学者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时,他心目中所谓的“一千个哈姆雷特”其实就作品而言只是莎士比亚写的那一个,其余的只是读者的想象造成的差异。但如果谈的是民间传说中的丹麦王子复仇故事,那就可能有不止一千个不同的故事版本了。
上述几个关系范畴的对立或差异并不意味着经典文学与民间文化是排斥或隔膜的。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对立或差异造成了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可能。如果从宏观的文学发展史来看就可以看出,民间说话艺人不断发展演变的叙述特色对现当代文学的叙述形态其实是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从50年代前后产生的“红色经典”如《暴风骤雨》、《林海雪原》,到后来高度繁荣的新武侠小说如金庸的作品,都可以找到这种影响的影子。可以说正是民间文化对经典化文学的影响,促成了现当代文学形态的多样化生态特征。经典作品常常从民间文化中寻找素材和原型,莎士比亚就是这样的代表。其实即使像曹雪芹闭门泣血创作的《红楼梦》,其中同样包含着许多民间文化的原型和因子。反之,经典文学也对民间文化发生着影响,如在文学文本中经典化了的《三国演义》中人物关羽,就在经典的接受中向民间文化扩散和再生成,逐渐发展出来后代民间文化中生生不息的关公崇拜。
文化生态的第三个方面是文学与文化空间的关系。所谓文化空间,是指某种文学活动得以存在、传承和发展的特定客观环境——地域、族群、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体系等等的总和。这也是一个与经典研究方式有差异的观念。在对经典文本进行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时,文本是被孤立地释读的。就是说,人们相信文本的意义是存在于文本内部的。西方的形式主义批评认为,作品一旦创作出来,作者就死了。中国传统批评虽然讲“知人论世”,但多半是从“言为心声”的意义上理解作者,仍然是在文本的内部寻找作者的存在;即使有考据作者生平人品者,同样是以先定的文本理解为前提,再来考察作者究竟属“言为心声”还是“心声心画总失真”之类,并非研究作品是如何从作者的生活活动中发生的。“人”既不外于文,更遑论“世”。所谓“文变染乎世情”,亦只是因“文”之变而联系“世情”解释其理,并非具体考察“文”如何从“世情”中发生的过程。
传统的文学史观是以经典作品为线索沿着时间轴串联起来的逻辑过程,即所谓“作品链”的历史。⑤在这样的历史观中,文学活动的空间意义当然被删略了。删略的结果是使得文学文本因脱离了具体空间而获得更加普适化的意义与价值,从而成为经典。然而,脱离了特定文化空间的文学,却可能同时也脱离了更丰富的意义内涵。有学者提出,这种只有时间维度而缺少了空间维度的研究,可能因为以文学上的进化论代替具体而丰富的文学研究却遮蔽了文学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因此而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思路:“‘文学地理学’是一种有体温的地理学。这种有体温的‘文学地理学’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地域文化。中国的地域文化几起几落,战国之后的具体地理文化板块埋下了地理文化的基因,几经变迁,产生了文学地理。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第二是家族文化。可以说不研究家族文化就研究不清楚文学问题。很多家学、家教、家风都是通过家族传承下来的。……第三个问题是作家的人生轨迹问题。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北关文化’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北关’是作家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之地,也是‘文学地理学’中非常重要的地理概念……另一个是文化中心转移的问题。……文化中心的转移实际上是以空间的形式显示了历史的变化。我们研究文学,应十分重视文化中心的转移这一事实对文学深层结构的影响。”⑥
其实,丹纳的实证主义艺术史观其实也可以说成是一种艺术地理学,但他的决定论倾向使后来的学者不能完全接受他的理论。文学与文化空间的关系的确不能简单地表达为地理决定论或空间决定论。事实上,文学活动与这些活动所依存的文化空间之间的关系应当被理解为循环互生的动态关系。东晋文学思潮的产生可以认为是中原士大夫衣冠南渡的空间迁移过程造成的结果,同时也是南朝文化空间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至于当代文学,某一文学思潮、流派的发生与传播,更是与当代社会中特定文化群落的形成有密切的互动关系⑦。
对文学与文化生态关系的研究不同于过去的所谓“外部规律”研究,即文艺社会学研究。文化生态视野的意义在于,以活态文学的观念审视文本意义的生成条件,从而为文本研究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文学研究的文化生态视野并非简单地在研究中增加社会文化和地理环境要素,而是展开另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文本中心研究理念,也可以说是一种“非文本诗学”研究理念。
所谓“非文本诗学”,并非不要研究文学文本,亦非否定或颠覆传统研究。这种研究理念的实质是超越文本中心观念,是对传统研究理念的丰富和拓展。非文本研究理念的主要内涵可以在与传统研究观念的对比中发现和展开。根据上面论及的文化生态观念,可以相应的勾勒出非文本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
从研究对象而言,非文本诗学研究是从文本向活动的扩展。以活动为对象,是为了还原文学文本发生和传播的活态过程,以认识文学意义生成的生态根据。就拿中国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经典——唐代以后的古典诗歌而论,人们相信这些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就蕴涵在文本中。然而奇怪的是,许多在我们看来妇孺可颂的清浅绝句,却给学习中国文学的外国人带来很大的困扰。显然,这些清浅诗句的意义并非如字面所表达的那样显豁,有一些字句之外的东西影响着读者的理解。从《文镜秘府论》可知,唐人的诗歌并非都是独立创作的,按照诗格、诗评、诗镜、诗式之类现成的写作指南模仿写作倒是一时风气。许多诗句的意义与其说是作者创作出来的,毋宁说是在学习和模仿活动中公共化、程式化了的表达套路。宋代之后,围绕着诗歌的种种闲谈裒集成的“诗话”——如欧阳修“集以资闲谈”的《六一诗话》——成为新的诗文化现象。当代人对古典诗歌的读解其实大多就是来自这一代代文人的诗话闲谈活动。当代接受美学的效果史观念实际上就是对文本意义增殖现象的一种解释,而要真正学术地剖析接受效果的发生,就得回到文学的创作、传播和接受活动过程中去。
从研究视野而言,这是从经典向民间的扩展。贯穿了两千多年文学发展史的以经典为标志的古典艺术精神,对于文学审美理想和文艺价值观念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但对经典的尊崇也压抑着不符合古典艺术理想的文学活动,因此而造成了文学发展史上一再出现的复古与革新、经典与奇变、精英与民间的冲突。比如,明清时代提倡复古和效法经典的文学门派林立、学说纷呈,而经典文学的创作却缺乏生气和创造性。从整个文艺活动潮流来看,这个时期真正有生命力的是各种民间文学形态——戏曲、白话小说、山歌、笔记小品、曲艺等等。文艺观念和文艺活动的现实发展趋势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冲突。明代的李梦阳等倡导效法经典文学的人后来都不得不承认“真诗乃在民间”,实际上表明他们意识到经典文学观念影响下的文艺创作在衰落,并且开始注意到民间文艺活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尽管在文学史的总体描述中也会提及民间文化的影响,但基本上是作为文学的低级形态看待,多多少少忽视了民间文艺活动的多样性和原生态活力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因此,研究视野向民间的扩展并非简单地进行民间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早已存在了),而是把不同时代、地域、族群的民间文学活动纳入到文学发展的宏观过程中,考察经典的文学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影响与共生关系,建立起文学发展研究中的多层次文化生态意识。
从研究的理论范式而言,非文本诗学的研究范式是从规律到特殊,即从追求具有普适性的认识(“规律”)扩展到发现活态的多样性(“特殊”)。经典的学术研究范式是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归纳和演绎,抽象出普适性的概念和规律;在这种学术观念看来,不具有普遍性品格的现象是没有研究价值的偶然现象。而文化生态视野的研究则关注的是现实的多样性,认为正是背离普遍性和典范性的特殊现象才深刻地体现了生命的多样性本质。比如在江苏靖江至今流传着一种介乎变文与说话之间的宝卷讲唱活动,因形态的古老粗朴而被称为文学的“活化石”。按照经典的艺术标准,这种文学只有民俗研究价值而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然而,研究这种“原生态”的文学对于全面地认识文学的意义是重要的。宝卷讲唱在当地称作“做会讲经”,最初产生时所依附的文化环境是传统的宗教文化生活;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演变为民间的一种公众娱乐活动。早期这种活动的宗教教育功能在发展过程中渐渐淡化,而以方言和区域生活习惯相关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语言幽默感等因素则成为凝聚参与群体的核心要素,通过做会讲经的特定仪式组织起来。这种活动是靖江地方民间文化情趣的和群体认同感的表现,它的存在是文化多样性的证明。当今的许多表现地域、族群特征和认同感的文学,如东北二人转、深圳打工文学等等,存在的价值并不在于合乎普遍的审美标准,而在于表现了文化的多样性。非文本的生态研究所关注的就是对多样性文化的认识、理解和沟通。
从研究方法而言,非文本的研究观念是从书斋到田野。所谓书斋是指以阅读阐释文本为中心的传统研究方法,也可以称之为经学方法。而田野则是以参与、同情、体验和对话为方式的研究文化差异的方法,也可以借用社会学术语称为“民族志诗学”(Ethnographical Poetics)方法。当研究的视线从经典文学转到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中时,对文化差异的“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就显得非常重要。而要获得了解之同情,就需要对文化差异的体验和沟通。这就是田野研究方法的要义。比如临夏有一首著名的叙事民歌《马五阿哥和尕豆妹》,唱的是一个根据真事编成的凄婉爱情故事:一对有情人被有钱人活活拆散,为了爱情他们不得不杀了人,结果是双双被斩首。就这个故事梗概而言,与历史上许多民族和地区流传的爱情悲剧故事没有太大不同。但仔细了解故事的叙述内容后就会发现很多与人们熟知的爱情悲剧不大相同的细节:尕豆妹被恶霸马七五抢去当童养媳,这个马七五俨然就是黄世仁。但在尕豆妹进了马家后哀诉不幸遭遇时却说“人家的女婿是十七八,我配的女婿是尕娃娃……女婿尕者上不去炕,一把揪到者炕沿上。女婿尕者贪瞌睡,孤单单身子靠给谁?”似乎没有出现黄世仁霸占喜儿那样的情况。两人幽会的时候“花花的枕头我两人枕,女婿娃枕给个木墩墩。花花的被儿我两人盖,女婿娃盖给个破口袋。”老财的儿子竟变成了受虐待的可怜虫。更奇特的是当马五杀人被捕后的遭遇:“马五阿哥抓给者城里了,大老爷阴子里说通了。亲戚朋友把银钱凑,给老爷背给了半背头。几十个元宝喂上了,大老爷一见心软了。大老爷见钱者心变了,命案问者不算了。不是官司也罢了,马五哥出来者话大了。气得马七五浑身抖,要和马五哥作对头。”马五的亲戚朋友花钱通关节居然可以使官府徇私放掉杀人犯,而且马五出来后还向马七五炫耀示威。故事讲到这里,给人的感觉马五不像被官府、有钱人或封建礼教害死,倒有几分像咎由自取。这使得习惯于读解“孔雀东南飞”、“梁祝”一类殉情故事的读者很难产生共鸣体验。要真正理解《马五阿哥与尕豆妹》故事的意味,必须进入到产生这个叙事的文化环境,感受和了解这个族群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性格特征。作家雷达评价说:“这故事中‘生’的描写极为大胆野气,其反叛性的异乎寻常的决绝,中原文化恐不可能有此胆魄。但我又觉得,它的反叛精神是非理性的,自在的,原始的,带有一种可悲的封闭色彩。”⑧雷达是甘肃人,多年生活在省会兰州,而这个故事的最后地点就在兰州。他自己对故事流传的地域、族群文化有亲身的体验和深刻的理解。这个故事看起来像是个奇特的文化个案,其实也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独特离奇。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民间文学已经被历代文化人有意无意地筛选、修改和雅化了,与真正乡土的文学往往有差异,有时候还是较大的差异。因此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要获得对乡土文化的真正理解就需要田野研究的方法作补充。
总之,从文化生态的视野重新审视和研究文学,这种“非文本诗学”研究观念对于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创新来说应当是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上,自19世纪的实证主义史观以来,语言学的语境理论、结构主义文化理论、接受美学、文化诗学、口头诗学、民族志诗学、新历史主义诗学乃至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和文化生态学等等,无数创新理论和研究实践已经在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文学的文化生态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所以“非文本诗学”的意义其实是把这些成果引进文艺学的传统研究视野中来,通过借鉴和融合来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注释:
①姚朝文:《文学观念泛文化化与立场迁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4期。
②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5页。
③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之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孔尚任:《桃花扇·凡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⑤参阅拙文《作品链与活动史——对文学史观的重新审视》,《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⑥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学术研究》2007年第9期。
⑦参看拙文《从意识形态到群落意象》,《文艺争鸣》2004年第4期。
⑧引自雷达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60ad6010009cj.html
标签:文学论文; 金圣叹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水浒传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西厢记论文; 芣苢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