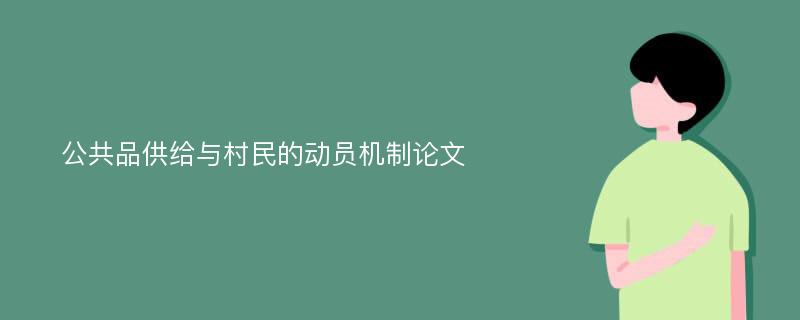
公共品供给与村民的动员机制
陈义媛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以三个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案例为分析对象,考察了在国家资源输入背景下,当村社作为资源支配的主体时,村级组织如何通过公共品供给来实现对村民的政治动员。研究发现,当村级组织可自主支配资源时,利益博弈逻辑会主导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村民动员具有自发性;如果国家在输入资源的同时也输入了科层制的资源使用程序,村庄的公共品供给就会显示出较高的程序正义逻辑,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也具有制度性的特征;与之对比,如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获取与村干部个人能力高度相关,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主要依靠村干部的长官权威,这种动员形式可能是不稳定的。因此,村社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可以重建利益博弈的政治空间,为村干部和村民打交道创造制度性的条件,避免政权的“悬浮”,同时可以激活村庄社会中的非正式权威,达成治理有效的目标。
关键词: 公共品供给; 村民动员; 村社组织; 村民自治; 国家资源
一、项目制下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研究
税费改革以来,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税费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取消农业税费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使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汲取型”向“服务型”转变。不过,在这一转变中出现了一些意外后果,突出地表现为以乡镇政府为中心的基层政府难以回应农民的诉求,“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1]。在资源输入背景下,国家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如何与“治理有效”的目标相结合,如何能重建与农民的紧密联系,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以农村公共品供给为切入点,讨论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何在提供公共品的过程中激活村民的政治参与,推动村民自治,增强治理能力。
关于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研究主要关注资源输入背景下,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出现的问题。尽管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投入,但供给的效率却比较低[2],不少研究讨论了公共品供给中出现的问题。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借助于“囚徒困境”“公地悲剧”和“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逻辑”等理论展开,这些理论的核心都是对“搭便车”问题的治理[3]。不过,国内的相关研究发现,尽管“搭便车”问题的确存在[4],但它只是公共品供给困境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在项目制的资源输入方式下,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不能被调动起来解决项目实施中出现的治理问题,容易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最后一公里问题”[5]。还有研究者发现,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国家难以通过项目制对接农民多样化的公共品需求,难以协调公共品供给中涉及的多主体利益[6]。此外,乡村组织的自利性和村庄内部整合能力的弱化,也容易导致公共品供给中的组织困境[7]。
第二类研究主要从乡村治理的角度讨论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作用。这类研究强调,集体土地是村民自治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强化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权利有利于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8-9]。同时,有研究者指出,政府通过提供政策激励,将村级组织作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可以提高公共品供给的效率[10]。此外,还有一类研究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考察了村庄选举与公共品供给的关系,发现村民会出于对公共品的需求而参与选举,通过村级公共资源分配和公共品供给,可以激发村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11],在村集体经济水平提高的情况下,规范的选举也有助于提高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数量[12]。
与真实石头相比,仿石热惯量较小,一天中温度变化幅度较大,需要调节仿石辐射温度变化速率,而相变材料应用是一种有效手段[6-9]。相变材料是指随温度变化而改变形态并能提供潜热的物质,在其吸热或放热过程中,温度变化缓慢,这一特性与大热惯量物质相似,故在仿石中添加相变材料可以提高其热惯量,促使其与真实地物热红外特征匹配。
第三类研究主要考察了村庄社会的力量如何影响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这类研究强调,要实现农村公共品供需的均衡,除了需要国家的资源输入外,还要撬动农村社会的内生力量,提升村社承接外来资源的能力[13-14]。通过激活熟人社会内部的规则,村级组织可以动员村庄社会力量解决公共品供给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利益纠纷,发挥村民的主体性[15],宗族的存在加强了村民集体行动的能力,从而促使村干部在公共品供给中更多地考虑村民的意愿[16]。
上述研究对于理解项目制背景下的村庄公共品供给有诸多启发,本研究是在第二类和第三类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探讨。不过,不同于上述研究,本文讨论的是项目制之外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国家对农村的资源输入并非只通过项目制方式进行,村集体经济组织可能会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得到国家资源。本文将通过展示不同的案例,探讨在“悬浮型”政权下国家如何通过资源输入来激活村民的公共参与,加强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互动。具体而言,本文讨论的是当村社作为资源支配的主体时,村级组织如何通过公共品供给来实现村庄内部的政治动员,提高治理能力。在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村资源输入的背景下,这些案例为思考资源输入的多样化方式提供了参考。本文的案例资料来源于笔者2017年3月、2018年3月和2018年7月分别于广西贺州、山东青岛和四川成都的实地调研。
二、村社主导的公共品供给与不同的村庄动员类型
除了项目资源外,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可能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获得资金资源,例如国家提供的补贴收入,或地方政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专款专用资金等。本研究展示的3个案例中,广西贺州、四川成都的案例展现的是村集体获得国家资源的特殊形式;山东青岛的案例是作为对比案例呈现的,这一案例中村集体获得的是集体土地的租金收益,而非国家输入的资源。不过,在3个案例中,村集体都因掌握了可支配的资金资源而成为公共品供给的主体,且都在提供公共品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村民的政治动员,但3个村庄在公共品供给中的逻辑却各不相同。
(一)公共品供给的机制差异
由于资金来源的不同,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对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上也存在差异,因此3个案例中的公共品供给逻辑各异。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关注的农村公共品,既包括农田水利设施、道路等基础设施,也包括村庄内部的纠纷调解、公序良俗的维护等[13]。
1.利益博弈逻辑下的公共品供给
3. As to the dispositions of a qualified mathematics teacher in community college,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core components? Please make a list and explain it briefly.
Y村的集体收入主要用于自然村内的公共设施建设。例如,2010年(当时还没有一事一议项目)Y村用集体收入重修了村内全长3公里的主干道,共花费40多万;2013年Y村投入10万元左右建了一座牌坊;2017年Y村投入20万,重修了被洪水冲毁的旧桥(重修这座桥的总投入是43.78万元,该村通过争取“两筹两补”项目获得了一部分资金支持);此外,Y村从2011年开始还每年投入8万元左右进行水利设施建设和维护。每一项重大支出的决定都是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形成的,这些决策的过程本身也是利益博弈的结果,村民代表需要反映民意,共同商讨兴办这些公共事业的先后顺序。更重要的是,Y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利益博弈逻辑还体现在对“钉子户”的抑制和对“搭便车”问题的化解上。
在对钉子户的抑制上,村集体一方面通过发挥村民代表的上传下达作用来获得村民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通过利用地方社会规范来给“钉子户”施压。事实上,在项目制的运作中,修路、建渠时因为少数钉子户的阻挠而使整个工程难以开展的案例并不少见[19-20]。在Y村的公共设施建设中,也涉及到了占用村民土地的问题,但很少出现钉子户。Y村村主任介绍,每一次实施大工程前,村委会都会组织村民代表大会。村民代表是在各村民小组中推选出来的,对本组内村民的意愿也很熟悉,由他们进行讨论提议,并在村民代表都同意的情况下,项目实施的方案才会得到通过。在会后,村民代表负责在各自的小组内进行宣传,保持信息透明。村民代表所发挥的上传下达作用,使村内的公共事业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可以减少“钉子户”出现的可能性。
即便真的出现了“钉子户”,村集体也可以利用地方性规范进行约束。2014年,Y村修环村路时出现过一个“钉子户”。修路前开村民代表大会时,大家共同商议的补偿标准是水田20000元/亩,旱地、沙地5000元/亩,但有一户不同意,提出了高额补偿的要求。在村民代表和村干部都无法劝服他的情况下,村里的一位老党员主动提出,可以绕路,占自己家的地修环村路。这样就把“钉子户”的问题解决了。Y村村主任谈到,现在这个“钉子户”受到了极大的舆论压力,因为每个人走过那段路的时候,都会因为要绕路而抱怨他。这一事件对之后的潜在“钉子户”也是一种震慑,想要当“钉子户”的人也需要慎重考虑后果。舆论之所以对当地村民有约束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在生活中有很多合作需求。例如,在当地,老人过世后需要合众人之力抬上山安葬,这需要多位同村村民的帮助。村干部通常会劝“钉子户”说,“你横,你家老人过世了,别人都不帮你,你一个人背上山?”正是彼此长期交往、长期合作的需求,使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会轻易走极端[21]。
除了对“钉子户”的抑制,村集体还可以利用村庄社会舆论来解决“搭便车”问题。因旧水坝被洪水冲毁,Y村的一个村民小组2015年曾对其进行过一次重修。Y村用集体收入为该村民小组购买了所需的材料,该村民小组组织在村的村民出义务工进行修建,在外打工的农户则以现金方式对出了义务工的村民进行补偿。但也有村民既不愿出钱,也不愿出力,企图“搭便车”。该村民小组组长和村民代表指责他们,“你明明在家,但不出力,以后讨媳妇都讨不到!”“讨不到媳妇”在当地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惩罚,一旦形成了不利的社会舆论,这些农户的确有可能在儿子娶妻时遇到麻烦。因此,这些不肯出义务工的村民最终支付了补偿金。事实上,对“搭便车”村民的约束体现的是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博弈,村庄社会舆论也是这一博弈中的工具。
Results from this study may help surgeons to appreciate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ESD, which has not yet been widely adopted by surgical societies outside of Japan for the treatment of early colorectal epithelial neoplasms.
不过,在集体收入的分配上,Y村内部也仍然时常出现分歧。在集体收入增多的最初两年,Y村根据各村民小组人数的多少,将集体收入分配给了各小组。这种分配方式下,始终有群众不满,认为分配不公。此后,Y村放弃了这种分配模式,决定将资金积累下来以便将来做一些大的建设项目。在村集体收入的分配和使用上,村庄内部的博弈一直存在,村级组织也在自我纠偏中不断探讨更合适的方式,在利益博弈中达成村庄秩序的均衡。
继电保护装置在内的相关二次系统发生回路断线、硬件失效、方向元件输出错误等而使跳闸信号不能正确产生、传输,或断路器机构故障导致不能跳闸,称其为第一类拒动,以指数分布模型表示其概率:
不过,程序正义基础上的公共品供给模式也有一些不足。一方面,标准化的程序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治”的发挥空间。以G村所在的乡镇为例,该镇是全县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在成都市的试点乡镇,该镇各村从2016年开始,每年所得的村公资金数额是其余村庄的两倍,各村的资金数额均在80万以上。但由于村公资金的使用范围是有明确规定的,在进行村民意见征集时,村民小组议事会也提供了村公资金可支出项目的类别,村民在已有的类别下进行提议。其结果是,该镇各村的村公资金开支结构高度相似:环境卫生、村庄巡逻队(包括对村庄安全、秸秆禁烧等各方面的巡逻)、村民事务代办员补贴、路灯照明这四项支出,占了各村每年村公资金开支的一半以上。尽管这些支出改善了村庄环境,但也限制了村公资金回应村民诉求的能力。
注释应在正文中以上标序号形式标注(例:①),并列于所在页的下方。参考文献一律采用实引制,引文需以(作者,发表年份)形式在正文中标注,如(张三,2015),并在文后按作者姓氏首字母顺序排列,英文文献在前,中文文献在后。具体参考文献格式见本刊网站。
2.程序正义逻辑下的公共品供给
2009年,国务院批复了成都市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方案,成都市成为试点城市。这项改革的其中之一就是建立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分类供给机制,由市、县两级政府安排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专项资金(以下按照当地人的习惯,简称为“村公资金”)给村级组织。成都市政府对资金管理和使用作出了详细规定,要求严格按照“六步工作法” 进行。从“六步工作法”的要求中可以发现,成都市在向村庄输入资源的同时也输入了科层制的资源使用的规范。从调研情况来看,各村级组织在提供公共品时也是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的。这些程序中已经包含了对村民的广泛动员,例如,在“入户收集意见”环节,成都市对于民意调查表的填写数量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填写数量不能低于本组村民的90%。在实际操作中,基层政府有更严格的要求,成都市G村会计提到,村组干部在进行任何一项入户工作时,如意见收集等,都需要拍照留存,并将照片打印出来与材料一同上交。这些严格的程序决定了村级组织只有在动员村民参与的基础上才能提供公共品。
这种建立在程序正义逻辑上的公共品供给模式有不少优势。除了能推动村组干部对村民进行动员外,这种严格的资金使用程序也极大地限制了村干部徇私的空间,并防止了资金滥用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在程序正义的基础上,村庄内部容易形成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均衡。因为村集体的每个决议都由村民小组议事会征集过村民的意见,所以形成的决议也具有了公共性。G村村支书说,“(村民小组)议事会就是挡箭牌。”正因为村庄公共事务的决议并不是由几个村干部决定,而是经由村民小组议事会讨论通过的,所以即便出现了“钉子户”,村组干部也比较容易以理服人。
认知行为护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以患者为中心,对患者的日常行为进行评估,针对患者的饮食和生活行为进行纠正和干预。进而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保障治疗效果,降低疾病进展风险。同时通过改变患者错误理念,纠正负面情绪,医患间建立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良好关系,提高协作有效性,让患者在心理上对健康的生活方式加以肯定。
总体而言,在贺州的案例中,地方性规范和村庄社会舆论形成强大的约束力,能解决村庄内部利益博弈过程中形成的“钉子户”和“搭便车”问题,这与当地的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有关村庄社会结构的讨论将在后文进一步展开。Y村的案例所展现的是利益博弈逻辑下的公共品供给机制,无论是对“钉子户”的抑制,还是对“搭便车”行为的负面舆论,实质上都体现了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博弈。利益博弈正是村庄政治的关键侧面,通过利益博弈而形成均衡的秩序,是“治理有效”的一种重要体现。
尽管当地也实行村财镇管的财务管理政策,L村的钱、物、帐都由其所在的街道办代管,村集体的每一笔支出都要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不过,村级组织在集体收入的使用上仍然占主导。以L村为例,该村每年的集体收入中80%左右都用于给村民发放福利。平均计算,每位有资格享受福利待遇的村民每年从村集体领取的各类福利金有5000元左右。除了给村民发放福利金外,L村也用集体收入进行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修路、铺设沥青路面、建数字影院等。不过,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主要由村两委决定,村民的参与并不太多。
与广西贺州Y村的案例相比,成都的村庄在公共品供给中更多地遵循着程序正义的逻辑,村民之间利益博弈的逻辑并不突出。不过,总体而言,在成都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的背景下,以公共品供给为中介,村干部与村民打交道的机会大大增加了。
3.福利发放逻辑下的公共品供给
山东青岛L村与前两个案例有所差异,该村由于距县政府只有2公里左右,距青岛市区也不过40公里,随着青岛市的开发,该村因为被征地而获得了不菲的集体经济收入。L村的公共品供给主要依托于村集体经济收入,与前两个依托于国家资源输入的案例有所不同。
2006年,L村所在县的县政府迁到了离该村大约2公里的地方,村干部认为这是L村今后的发展机遇,因此在同年将全村土地全部返租回村集体[注] 村集体之所以能顺利地将所有土地全部返租回来,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该村人均耕地只有0.4亩,土地上的收益少,降低了村民对土地的依赖;二是由于该村离青岛市区只有不到40公里,当地的非农就业机会很多,也减少了村集体返租土地的阻碍。 。自2004年前后开始,青岛市政府在征地后,会将土地增值收益返还一部分给村集体,返还数额的多少根据被征地村庄的区位而定。L村在二类地范围内,自2008年起,地方政府每从L村征1亩地,即给该村返还10万元。征地返还款是近年来当地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到2018年,L村每年的村集体收入已达到1300多万元。
另一方面,严格的程序规范也导致了公共品供给成本的上升。G村会计谈到,村内的路灯维护及电费每年的开支大约是10万元。原本由村集体去缴纳电费,并由电力部门开具发票就可以了,但按照村公资金的支出程序,G村必须通过招标,找第三方来运营路灯,且必须有3家单位竞标。在招标过程中会因法律程序而产生成本,且第三方也要有利润空间,因此找第三方运营的结果就是村集体要多付出30%的成本。G村会计对此十分惋惜,表示这30%的钱本来可以用来为村民做更多的事。更让村级组织为难的是,运营路灯这样的项目资金太少,企业往往不愿意来竞标,村干部为了找到足够的竞标企业也得花费不少人力。
L村为村民提供的公共品除了道路、娱乐设施等硬件设施外,更重要的是村庄内部的秩序。L村公共秩序的达成与该村村规民约的强约束力密切相关,因为其中详细写明了违反村规民约的惩罚措施,最主要的惩罚就是对福利的扣减。例如,L村村规民约明确表示,“凡在本村出现打架斗殴、辱骂他人、酗酒滋事、造谣惑众、扰乱村庄正常秩序,损害公共财物及个人财产的,除赔偿经济损失外,村两委会将减去当年本村对该村民各项福利、补贴的50%,情节严重的减去当年补贴的100%……”又如,“子女应……及时交纳父母的口粮、养老费,不得无故拖延。不得虐待老人,更不得打骂老人。如有发生,父母可报告村委会或老年人协会进行调解,对调解无效或不听调解者,村委会按规定采取处罚措施并扣除本户当年的全部福利待遇及补贴……”除此之外,还有对于不按规范建房、不按规范停放车辆、乱丢垃圾、自来水费缴纳不及时等问题的福利扣除规定。
从村集体经济组织所获得资源的角度来说,本文的3个案例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3个案例的共性在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资源使用和分配中都发挥着主导作用。对比而言,当国家以项目制的方式向乡村输入资源时,村级组织往往是被动的配合者。在本文的案例中,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导下,集体资源都用在了村庄公共品供给中,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对村民的政治动员,达成了村庄内部均衡的政治秩序。这种治理秩序的达成背后有三种重要机制。
(二)不同类型的村民政治动员
以公共品供给中的村民参与为切入点,可以考察不同的公共品供给机制下村集体对村民的动员方式。村民的公共参与与社会结构有密切关联。贺雪峰将中国不同区域的村庄划分为团结型、分散型和分裂型村庄。团结型村庄多在华南地区,村民以聚居为主,村庄相对封闭,多强宗大族,地方性规范强,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强;分散型村庄多在长江流域,村民以散居为主,村庄相对开放,村内只有小的同族集团,无大宗族,地方性规范较弱,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弱;分裂型村庄多在华北地区,村民以聚居为主,村庄相对封闭,村内有小的血缘集团,无大宗族,地方性规范也较强,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较强[22]。在本文的3个案例中,广西贺州的W村属于典型的团结型村庄,血缘和地缘的重合使宗族组织在村庄社会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四川成都的G村和山东青岛的L村均为城郊村,更具有分散型村庄的特征。村庄社会结构影响着村民的公共参与,在有宗族组织的地区,村庄社会的自发动员能力往往很强。不过,在分散型村庄,村民也可能在一些特殊机制下被动员起来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但动员机制会有所不同。
广西贺州市W村地处南岭山地丘陵区,村域范围内有大量的生态林。2009年林权改革时,W村下辖的两个自然村Y村和H村出于对村民集体意愿的尊重[注] 村民之所以不同意将生态林承包到户,是因为Y村和G村将此前所得到的生态林补贴都“用之于民”了。在当地,村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需要缴纳150元/人/年作为个人自筹资金。在2009年前,生态林补贴标准较低,Y村和G村的集体生态林补贴在替村民缴纳这部分费用后,也所剩无几了。 ,没有将各自的18000亩和9000亩生态林承包到户,因此这两个自然村的生态林收益权仍归自然村集体享有。近年来,由于中央财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不断加大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投入,生态林补贴逐渐成为Y村和H村集体收入的重要来源。2001—2009年,生态林补偿标准为5元/亩,2010年提高到10元/亩,2013年进一步提高到15元/亩[17]。因此,自2013年以来,Y村和H村集体每年所得生态林补贴分别为27万元和13.5万元。到2017年,Y村的集体收入已经累计到100多万元。由于这两个村庄的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国家提供的生态林补偿,因此本文也将之看作国家资源输入的一种形式。不同于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方式[18],在使用集体生态林补贴收入时,Y村和H村有充分的自主权。因为没有将生态林承包到户的自然村极少,所以Y村和H村的情况即使在当地也是特殊案例。在对集体收入的支出和管理方面,两个自然村的情况非常相似,因此本文仅以Y村为例进行剖析。
1.自发性动员
在广西贺州Y村的基础建设中,村民自发形成了“清账小组”,对村集体经济的支出和账目进行监管,并每季度向整个自然村公示一次。在对村集体经济收入监管过程中,一批有声望的村民被动员进来,参与村庄财务监管的村民都是村庄中有声望、有社会基础的,而且村民对公共活动的参与有很强的自发性,因此本文将这种动员类型称为“自发性动员”。
也就能够得出教师的相关评价数值,根据每个教师所得出的数值的不同对教师加以判断和评价。而这一过程在具体计算的时候相对比较复杂,这就需要将这些程序能够和计算机相互配合使用,使得数据输入之后,计算机能够在经过其中具体程序计算之后,得出必要的数据结果,根据相关结果内容对教师群体加以评价,使得教师们能够对自身的评价更加公平公正对待,促使教师的综合素质不断加以提升。
Y村共有8个村民小组,各村民小组以同姓村民为主,村民之间有紧密的血缘关系。各组均有一个代表进入清账小组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均衡的“代表制结构”,这种结构与村庄社会结构高度同构。清账小组作为村庄内部的非正式组织,其成员并没有固定工资,只在每次清查账目当天会得到100元/人的误工补贴。清账小组的成员是各村民小组推选出来的代表。Y村村支书谈到,能进入清账小组的人都是深得村民信任的人,而且是热心、正直的人,“修路的时候让你捐点钱你都不捐,哪个服你?”他们对村庄的每一笔开支都了然于心,如果有村民对账目存疑,则由代表该组的清账小组成员负责向其解释。
在Y村这样的团结型村庄,基于宗族血缘的长老式权威是普遍存在的。这些非正式权威人物在村庄治理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村庄内部的纠纷调解方面[23],但要让这种非正式社会力量发挥更大作用,则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来激活他们。在Y村的案例中,意外积累的集体经济收入激活了这种力量。由于生态林补贴是村社内部的共同财产,每个村民都认为与自己有关,因此也都积极关注着这笔收入的分配和使用情况。在推选清账小组成员时,也必然会选出能服众的代表人物,在这个过程中,宗族结构中的内生权威自然地浮现出来。村社内部的非正式权威被动员进村庄公共事务中,这个过程正是村庄内部自发性动员的过程。
2.制度性动员
将上述两个村庄与青岛L村对比,可以发现,后者无论在公共品供给中,还是在村民动员中,都有较强的长官主导特征。尽管村规民约在L村有实质的约束力,村庄内部也形成了均衡的秩序,但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比Y村和G村低。更重要的是,当村庄所获取的资源与村干部的个人能力高度相关时,这种权威服从的逻辑就会十分突出。其风险在于,村庄治理的有效性和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高度取决于村干部的公心和能力,因此更具不稳定性。
村民小组议事会成员与普通的村民代表不同,前者会更深度地参与公共事务。如前文所述,村公资金的各类开支都需要议事会来讨论,除此之外,议事会还有提议的权力,因此是村庄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主体。G村共14个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推选出5位村民代表,各组的村民代表加上村支书,共同构成全体村民代表;议事会成员则是由各村民小组从本组的5名村民代表中推选出2名,一共28人,加上村支书,共同组成议事会。需要说明的是,由于G村距离其所属的县城仅4公里,距离成都市区也只有40多公里,所以外出务工的村民很少,绝大部分村民都可以就近务工,在村庄中生活,因此村庄能人的流失并不严重。议事会的成员基本都是在小组内部有公心的村民,且通常也是村庄中的能人。村公资金的使用和监管成为一种制度性的渠道,使村中的能人被动员起来,为村庄公共建设出谋划策。
此外,由于村公资金的使用程序之一就是提前征集民意,且每一项支出都需要收集村民的满意度评价,所以村公资金的输入很大程度上激活了村民的民主参与。正因为有程序上的要求,所以在成都的村公资金使用中,参与决策和监督的不仅有村民代表,更包括了绝大多数的村民。无论是民意调查表的填写,还是项目实施后的满意度测评,都需要村干部不断与村民打交道,这一过程客观上强化了村干部与村民的联结。其意义在于,基层组织不再悬浮于村庄社会之上,在这种程序性地打交道过程中,村民就不断有机会向村干部反映情况,将一些潜在的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当然,非要在拥堵的路况中驾驶这辆特殊的保时捷911也无可厚非,毕竟每个人有权利在吃饺子时候选择蘸酱油、醋或者番茄酱。
3.权威型动员
作为对比案例的山东青岛L村,在村民动员方式上更具有权威长官主导的特征。由于L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的征地返还款,而征地又与村干部招商引资的能力直接相关,因此村干部在村集体经济收入的获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L村村民对于能人村干部的权威是认同的。村干部对村民的动员主要表现为使村民遵守村规民约的规定,从而维持村庄内部的公义和秩序。从村庄治理的效果来看,这种权威型动员也能够在村庄内部达成均衡的秩序。相较于同乡镇的其他村庄而言,L村的邻里纠纷、养老纠纷、违建等问题都更少,村庄内部的公共秩序和公共设施建设也都更好。
在全国大多数村庄,村规民约很难真正对村民形成约束,因为村庄缺乏实质的约束措施。在L村,在正式启用村规民约的惩罚措施之前,村级组织专门召开村民会议对村规民约的细则进行讨论。此后,村规民约仍时有更新,但每次更新也需要通过村两委、村民代表大会和党员大会讨论通过。事实上,对村规民约的讨论,也是村庄内部公共性的体现。村规民约本质上只是一种自治手段,并不具有正式的法律效力,是非正式治理的一种形式。村民被动员起来讨论村规民约的细则,也是村民自治的一种体现。更重要的是,正因为村规民约的执行与村民福利的发放挂钩,村民才能被动员起来进行讨论,村民对村规民约的遵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村干部权威的服从。这种权威服从下的政治动员有较高的风险,因为它高度依赖权威型村干部的公心和个人能力。如果村干部缺乏公心,那么这样的村庄中由于利益分配不均所产生的矛盾会远远多于其他村庄。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到,尽管广西贺州Y村和四川成都G村的集体资源都来自国家的资源输入,但由于资源输入的形式不同,两个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方式和村民动员方式也不同。在成都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中,市政府在向村庄输入资源的同时,也输入了资源的使用程序,因此G村是在资源使用时是严格依照程序进行的,该村的公共品供给具有很强的程序正义逻辑。Y村在资源使用上则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Y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本身就是国家提供的补贴性收入,村集体经济组织有充分的自主权,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村民之间的利益博弈也更充分。尽管两个村庄都进行了较充分的政治动员,但相较而言,G村在严格的程序约束下,自治空间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Y村在公共品供给中则表现出更高的自治能力。
在成都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中,村公资金的使用和监管成为村级组织动员村民的一种制度性的渠道,其中有两个关键的动员机制:一是村民小组议事机构(在G村被称为“村民小组议事会”,简称“议事会”)被组建起来,在组建议事机构的过程中,各村民小组有声望、有公心的村民代表被发掘出来,他们成为联结村级组织与村民的中介;二是在村公资金的使用中,村民也被不断动员起来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监督。
三、村民动员背后的治理机制分析
可以看到,L村村规民约中的规定大多是针对村庄治理中最常出现的纠纷,例如打架斗殴、邻里矛盾、不赡养老人、违规建房、环境卫生等问题。在缺乏治理资源的村庄,上述问题往往成为村庄治理中的难题。但L村以福利发放为中介,将村规民约激活,使之有了正式的约束力。相比于缺乏村集体收入的村庄,L村的治理状况的确更好。村庄秩序、公序良俗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品,L村的集体收入成为村级组织供应这类公共品的重要基础。
第一,通过公共品供给,村集体经济组织重建了利益博弈的政治空间,只有充分的利益博弈后达成的妥协才能形成均衡的秩序。利益博弈的逻辑尽管在广西贺州Y村的案例中体现得最充分,但在另外两个案例中也有呈现。在Y村的案例中,对“钉子户”的治理和对“搭便车”行为的约束,都是村民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在四川成都G村的案例中,民意调查的过程也体现了村民之间的利益博弈,每个村民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公共品诉求,在村民小组议事会上的排序和筛选则呈现了利益博弈的最终结果。在山东青岛L村的案例中,村规民约的细则讨论,奖惩措施、奖惩程度的确定,也是一场博弈。只有公共利益才能产生公共政治,村民能被动员起来,根本原因是公共利益与每个人都有关。村级组织在对集体资源进行分配的过程中,重塑了公共治理的空间。
第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村干部和村民创造了打交道的制度性渠道,避免了“悬浮型”政权的问题。在三个案例中,村集体都利用集体资源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占用村民土地问题,因此在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村干部需要频繁与各类村民打交道。这个过程事实上提供了一个梳理村内矛盾的机会。在村庄公共建设中出现的“钉子户”,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为了索要高额赔偿,而是因为有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借此机会发泄。只有解决了之前的问题,公共设施建设才可能继续。因此,村庄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村干部解决村庄内部积累的矛盾提供了一个渠道。事实上,这一渠道在有关土地调整的研究中也有论及,在土地调整中,不配合的村民往往并非真的不愿意退出土地,而是因为此前遭遇过不公正的待遇。只有梳理清楚了这些矛盾,土地调整才能顺利进行[24-25]。只有当村集体经济组织有可支配的资源,能够不断为村民提供公共品,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联结渠道才能持续存在。村庄内部的矛盾是不断产生,又不断被解决的,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因此只有形成制度性的渠道,村庄治理的有效性才能持续。
第三,对村庄社会非正式权威力量的激活,也是形成有效治理的一个重要助力。在贺州和成都的案例中都出现了“代表制”:Y村的“清账小组”是各个村民小组推举的代表所组成,G村的“村民小组议事会”也是在村民小组代表中产生的。这些“代表”并不是正式的村组干部,而往往是乡村社会中有威望、有公心的能人或非正式权威。他们是村庄治理中的沉寂资源,但在村庄公共资源的分配和监管中,这些非正式的社会力量被激活了。村庄社会中的非正式权威是村庄治理中重要的辅助力量,他们有助于在村庄中形成低成本的“简约治理”结构[26]。
为此我们成立了“日日顺智慧物流研究院”。在大件运输领域,不管物流怎么运作,最核心的是一定要解决两端的问题。用户端:用户体验一定要最好。否则它没有价值,用户体验决定知名度,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还要得到更多的认可;企业端:企业竞争力一定要提升。日日顺物流现在除了服务海尔,还有3000多个品牌商,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大的研究院来提升日日顺物流的整体服务和商业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村庄中一旦形成了公共参与的空间,往往会产生良性的政治惯性。这种惯性的形成表现在,在公共品供给之外的村庄事务中,村民也有积极参与的动力。这一点在成都G村的案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村公资金的运作程序要求村干部不断征求村民意见,村民被不断卷入村庄建设中,村庄内部也形成了通畅的意见表达渠道。
对于学生而言,管弦乐的欣赏并不陌生,但打字机对于学生而言就是陌生的。如果没有视频的辅助,学生很难把音乐中的节奏和打字机工作时发出的节奏及各种音响结合起来进行想象。视频在音乐课中的使用是很普遍的,这里凸显的是多媒体技术对帮助学生加深音乐文化理解的作用。那么,音乐教学中有哪些文化需要借助媒体技术来实现呢?
四、小结
本文的核心关注点是在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国家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如何达成“治理有效”的目标。国家资源并非只通过项目制的形式向乡村输入,本文呈现的案例中,四川成都的村公资金、广西贺州的生态林补贴,都是国家资源输入的不同形式。作为对比案例的青岛L村,其集体经济收入并不是国家资源输入,而是基于村庄自身的土地资源和区位优势所获得的收入。本文的三个案例中,集体资源都是以村社为主导进行分配和使用的,这与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方式有很大差异。本文讨论了当村社作为资源支配的主体时,村级组织如何通过公共品供给来实现村庄内部的政治动员,提高治理能力。
研究发现,村集体的资金来源形塑了不同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和村民动员机制。以广西贺州Y村为例,当国家输入的资源直接成为村集体经济组织可自主支配的资源时,村庄内部可以进行更充分的利益博弈,在公共品供给中利益博弈逻辑占主导,村民动员具有较高的自发性。在四川成都G村的案例中,国家在输入资源的同时也输入了科层制的资源使用规范,因此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显示出高度的程序正义逻辑;在严格的程序执行中,绝大部分村民也会被动员起来,但这种动员是在制度性的安排下实现的。与这两个案例对比,在山东青岛L村的案例中,村集体经济收入的获得不是依靠国家资源输入,而是依靠该村自身的土地资源和村干部个人能力。该村供给的公共品除了基础设施外,更重要的是村庄内部的公序良俗。村干部以村规民约为中介,通过福利扣减来约束村民的行为。在这种福利发放逻辑下的公共品供给中,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主要依靠的是村干部的长官权威。尽管L村维持了良好的秩序,但这种形式的村民动员有较高的风险,因为村庄治理的有效性和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高度取决于村干部的公心和能力。
如本文案例所示,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利用集体资源提供公共品时,都达成了村庄内部均衡的政治秩序。这种治理秩序的达成背后有三种重要机制。第一,通过公共品供给,村集体经济组织重建了利益博弈的政治空间,只有充分的利益博弈后达成的妥协才能形成均衡的秩序;第二,由于村集体主导着公共资源的使用,因此能持续进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一过程为村干部和村民创造了打交道的制度性渠道,避免了“悬浮型”政权的问题;第三,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村级组织激活了村庄社会非正式的权威力量,他们也是有效治理的重要助力。
(1)存在精神和(或)听力、语言障碍者;(2)低位复杂性肛瘘或高位肛瘘;(3)晚期肿瘤、躯体残疾者或伴有心、肝、肾等器官障碍者;(4)治疗前2周使用过影响治疗效果的药物者;(5)无自知力,不能配合者。
本文认为,国家在向村庄输入资源时,有必要在项目制之外多开拓其他形式。同时,在国家输入资源的过程中,应当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性。国家固然应当对村级组织的资金使用进行监管,但也需要给村民自治留下足够的空间,不能让监管程序消解了村民自治。党的十九大以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已经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如何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如何使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增加与“治理有效”的政治目标相结合,本文的案例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参考。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教授赵荣光提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是食材、食品与饮食文化之路,是人类饮食文明之路,而当前的“一带一路”也是“舌尖上”的“一带一路”。我国食谱因此更加丰富多样,既有土耳其的无花果干、越南的咖啡、斯里兰卡的红茶,也有意大利的葡萄酒、奶酪等。
参考文献:
[1]周飞舟. 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J]. 社会学研究, 2006(3): 1-38.
[2]罗兴佐.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模式与效率[M]. 北京: 学林出版社, 2013.
[3]刘燕舞, 毛刚强. 农村公共品研究的现状与前瞻[J]. 学习与实践, 2010(8): 106-112.
[4]陈柏峰. 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好混混”[J]. 青年研究, 2011(3): 48-54.
[5]桂华. 项目制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分析——以农地整治为例[J]. 政治学研究, 2014(4): 50-62.
[6]王海娟. 项目制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 62-67.
[7]李祖佩. 论农村项目化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困境及其逻辑[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 8-16.
[8]贺雪峰. 土地与农村公共品供给[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1): 19-24.
[9]桂华. 产权秩序与农村基层治理:类型与比较[J]. 开放时代, 2019(2): 36-52.
[10]王奎泉, 赵玲玲. 村级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研究[J]. 财经论坛, 2014(10): 17-21.
[11]卫龙宝, 朱西湖, 徐广彤. 公共品供给满意度对村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1): 81-90.
[12]王海员, 陈东平. 村庄民主化治理与农村公共品供给[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6): 72-84.
[13]董磊明.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内生性机制分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5): 69-75.
[14]孔卫拿, 肖唐镖. 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治理结构与中国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质量[J]. 人文杂志, 2013(12): 110-118.
[15]高万芹, 龙斧. 村民自治与公共品供给的权利义务均衡机制——以Z县G乡L村为个案[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 38-45.
[16]齐秀琳, 伍骏骞. 宗族、集体行动与村庄公共品供给——基于全国“十县百村”的调研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 2015(12): 117-125.
[17]陈静. 广西公益林补偿标准提到每亩15元[N/OL]. 广西日报,2013-12-18 [2019-03-35].http://www.forestry.gov.cn/main/72/content-647592.html.
[18]折晓叶, 陈婴婴. 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11(4): 126-148.
[19]李祖佩. 乡村治理领域中的“内卷化”问题省思[J]. 中国农村观察, 2017(6): 116-129.
[20]贺雪峰. 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6-7.
[21]陈柏峰. 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22]贺雪峰. 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J]. 开放时代, 2012(10): 108-129.
[23]桂华, 贺雪峰. 再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一个农村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J]. 开放时代, 2013(4): 157-171.
[24]杜鹏. 土地调整与村庄政治的演化逻辑[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24-36.
[25]陈义媛, 甘颖. 土地调整的政治逻辑: 对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再思考[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102-111.
[26]黄宗智.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J]. 开放时代, 2008(2):10-29.
Rur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and the Public Mobilization Mechanisms
CHEN Yi-y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
Abstract : Based on the rur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cases in three villag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ublic mobilization mechanisms within a village when the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 dominates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vides public good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when a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 has the autonomy in 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this village c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logic of interest game, whereas the public mobilization could happen spontaneously. If the national resource input comes along with the input of bureaucratic procedures, the public goods provision might be characterized with the logic of procedural justice, and the public mobilization might be institutionalized. In contrast, if the collective income of a village is highly depended on the village cadres’ personal ability, rather than the national resource input, the public mobilization could be subordinated to the bureaucratic authority, which might be risky. The village-dominated rur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could re-shape the public political space and re-activate the informal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governance, while avoiding the ‘floating’ of local government.
Key Words : rur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public mobilization;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 villager autonomy; national resource input
中图分类号: D03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 2019) 04-0101-10
收稿日期: 2019-03-30
DOI: 10.7671/ j.issn.1672-0202.2019.04.0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CSH071)
作者简介: 陈义媛(1988—),女,湖北荆州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E-mail: chenyiyuan1988@163.com
标签:公共品供给论文; 村民动员论文; 村社组织论文; 村民自治论文; 国家资源论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