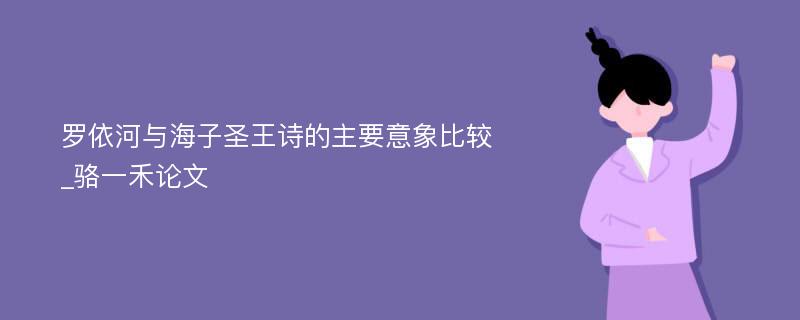
圣与王:骆一禾、海子诗歌主体形象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子论文,诗歌论文,主体论文,形象论文,骆一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34X(2013)02-0041-09
骆一禾、海子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孪生的麦地之子”。由于海子之死的神话效应,在这一“孪生”的视野中,骆一禾的创作往往被视为海子的回声而受到忽视。事实上,骆一禾和海子的诗歌写作虽然在精神方面存在广泛的共源、共振和共鸣,文本上也存在多重的呼应、互通以至互文的现象,但在精神构造、情感和价值取向、诗歌心象、写作方法论诸方面都存在深刻差异。骆一禾、海子心灵构造和诗歌境界的差异集中反映在他们诗中的主体形象中。当然,两位诗人的主体形象并不是单一的,在不同的作品中,它们通常由不同的形象来承担。但如果我们要从两位诗人的作品中分别拣选出一个最突出的形象来代表他们各自的主体形象,那么在骆一禾的诗中非“圣”莫属;在海子的诗中,则非“王”莫属。“圣”是骆一禾的自我期许,它是骆一禾的诗歌抱负、人文关怀、人格理想的象征;“王”则是海子的自我镜像,代表了海子对诗歌成就的最高渴望——“诗歌之王”正是海子全心的向往。可以说,“圣”与“王”两个形象分别代表了两位诗人的心灵原型。
一、圣:骆一禾诗歌的主体形象
早在1981年的《桨,有一位圣者》中,骆一禾以“圣”为归宿的人格理想就已经在觉醒的曙光里透露了端倪:
有一个神圣的人/用一只桨拨动了海洋/蒙昧的美景/就充满了灵光/天明的退潮遗下了彩霞/夜里闪光的菌类、贝壳、石英/宛如醒来时旋流的思想/成串的追忆/和细碎而坚硬的希望/那位灯塔一样/神圣的人/鼓起我张满的帆/引导我认识并且启示海洋/像他手中的船桨
某种程度上,这首小诗可以看作骆一禾诗歌世界的全息微缩:它是骆一禾常青的诗歌大树得以发生的种子,包含了其诗歌和人格理想的基本要素。在这首诗中,有两个意象值得特别关注,一个是“灯塔”,另一个是“桨”。诗中那位“灯塔一样神圣的人”,以一只桨拨动海洋,而使蒙昧的美景充满灵光。这里的“灯塔”可以说寄托了骆一禾的价值理想,同时又表征着诗人所念兹在兹的智慧之光。“桨”在这里象征着行动,以及体现于行动中的主体意志和力量。也就是说,骆一禾的诗歌抒写和两个东西关系特别密切,一个是智慧,另一个便是行动。对骆一禾来说,诗歌不只是一种审美的满足,更不是单纯的感情抒发,也不仅是一种思想的智慧,而是兼容情感、审美和智性,并在其中寄寓了诗人改变世界、改造世界的理想。在骆一禾那里,诗的歌唱始终是导向行动的一个开口。骆一禾的人格理想乃是要成为一个“神圣的人”,不仅以智慧之光启示读者,同时也以行动改造世界,使蒙昧的世界而变为充满灵光的美景。这样,骆一禾的诗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而是关联于“圣歌”、“圣咏”和“圣诉”。他的写作从始至终笼罩着这样一种“神圣”、“圣洁”、“圣地”的氛围:
但命运压迫得太紧了/当我们睡下/一双手还伸在圣地之外(《爱情(二)》)
生活是我的统治者,庙,和圣殿/……想着这些可怜的苦难的圣者/火舌吐着猩红的穗子/在我们的心中残酷地跳跃(《对话》)
因此圣洁是可以想象的/它没有修筑自己的出路(《音乐》)
修远/这两个圣诉蒙盖在上面(《修远》)
你要记住这庄严的圣地/记住这濒危在嶙峋积雪上站立的身影(《世界的血·飞行》)
在千条火焰下面,澎湃大海/这无尽的火焰照亮了苦难圣者的河流,遗址(《大海·第十四歌》)
……我的心脏:这神圣的容器/正在我胸中怦怦撞动(《大海·第十五歌》)
当然,骆一禾所倾慕、所欲成为的圣者,既不是孟子所谓的“四圣”,①也不是柳宗元所谓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的“大人”。②对骆一禾来说,孟子和柳宗元的“圣人”和“大人”标准无疑是一种不适当的甚至错误的尺度,它们出自一种今日已告衰微的文明,是这一文明的产物,也是这一文明的载体。而实际上这一“圣人”和“大人”的标准应当为这一文明的衰微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它们都把“圣人”和“大人”定位于强者—统治者,甚至把“圣人”作为帝王的专名,所谓“圣人出而四海一”,而把天下苍生视为“圣人”和“大人”们役使、控制、教化的对象,当然也就把绝大多数人排除在“圣人”和“大人”之外,从而压抑、压制了他们个体生命的生成、强大和发扬。在骆一禾看来,这正是华夏文明活力衰退、生机不昌的原因。与之相反,骆一禾把“圣”定位于每一生命个体。他说:“当生命规律、文明的宿命已演为新的活体,或正向活体演化之际,个人生命的自强不息,乃是唯一的‘道’。生命的体力及精神上的挥发、锻造,这便是我们的历史,便是我们真实地负载着的、享受着的、身处其中的历史”。[1]换言之,个体生命的自由发扬足以让每个人成圣。“一面是巨大的死,一面是弱者的生,美从拇指姑娘长成为维纳斯,唯赖心的挣展,舍此别无它途”,[1](P830)而华夏文明的新生所可依赖寄托者全在于此。所以,骆一禾站在弱者一边,其所谓“圣者”,乃是弱者的自强。他说:“生为弱者”(《生为弱者》)。他说:“强者是弱者的升华”(《年华》)。他说:“只有弱者才能献身”(《滔滔北中国》)。他为无名的农人、工匠、兵士、哲人、幻想家、诗人、艺术家、革命者、流浪的舞族祈祷,赞美世上一切从弱者中涌现的智者、勇者、善者、义人、俊杰、英雄、战士、牺牲者,歌颂他们为天下跳动的心、踔厉风发的意志,赞美他们平凡的劳作或不平凡的功业,讴歌他们质朴、高贵、坚韧的品德,颂扬他们的担当、牺牲和受难:
那些智者勇者和善者/身躯平淡如四周/心却为天下跳动过(《瓶画:九影如神》)
义人们衡量心地的车轨/我此去头顶我亲手制作的醴酒和羔羊(《汉诗一束》)
这是一条义人的道路/当脚步证实心脏的时候/这是一种心声/一条博大的道路(《遥忆彩云南》)
你们罗列的是诗人/我所打造的是战士/(《云层》)
长坐山崖英雄故去(《秋水》)
我是一个英雄/因为我爱的是召唤/与人无害。(《最简单纯洁的歌曲》)
短促地就使义人栽倒。可是好呵……你这/白石的坚贞,你这黄昏里银色的一地麦捆。(《太阳》)
假道于义人的道路:头顶着羔羊的/我的道路/素朴加于其间/投掷阳光的实体(《素朴:语言和海》)
英雄的故事便是一个人所成就的(《世界的血·航海纪:俄底修斯与珀涅罗珀》)
跋涉着那些敲响木头/或投石问路的智者……(《海·第二歌》)
我见到新月干燥,义人皎洁/飞行使我的精神长醒/那是我思沃泉,兹之永叹,风骨长明(《大海·第十四歌》)
在骆一禾看来,正是这些无名的“义人”背负着生活的重负,承载着岁月的涵容,在创造自身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民族和文明的未来。因此,华夏文明的新生只有寄托于无数无名的个人为生存所进行的壮烈斗争中。
早在骆一禾诗歌写作的起步阶段,诗人就对“无名”怀有特别的深情:“心爱的/永远是心爱/无名的/永远是无名。”(《无名的深情》1982)他在诗论中说:“我默颂这淹没在丛林中无名的墓址,我赞美这人的名字,‘太初有为’”。[2]这里,人的名字是以他的行动来命名的(人=行动):“太初有为”。这就是平凡人的事业,是平凡人所成就的:“这正是无名者里的大劳作/此时③我所面对的/正是唱诗的人/登山寻火的人施洗者”,“作为舞蹈的族/无名者随身带走的/只有自己的舞”(《舞族》)。正是这些无名者的劳作、行动,成就了生命巨流奔集的历史,荡涤了由于苟且停滞所积聚的污物和渣滓,而使生命常往常新:“最伟大的劳动者/通过人体穿行在与幻想同等的天空上/也穿过了寄居的生物和渣滓”(《舞族》)。诗人的职责就在彰显这些无名者的劳作及其所成就的:“我青莲变幻,彰显无名的事物”(《世界的血·生存之地》)。骆一禾也把自己视为这些无名者中的一员:“做无名的生者/你要善恶分明”(《爆炸》)。他认为,“无名”既是一切劳作者的共名,也是艺术家和诗人的本名:“因为诗的美是一首诗一首诗的生命形成的美,它不受自我的操纵;由是艺术家其实是无名的,当我在创造活动中时,我才是艺术家,一旦停止创造,我便不是,而并不比别的工匠们重要什么或多损失了什么。才能也只是一种天分和天分的砥砺,若它即有,实由生命的滋长,命运的导向天赋,它是用来创造而此外无它。”[3]在他眼中,无论李白、陶渊明,还是叶芝、惠特曼、瓦雷里,都把自己作为“无名”注入诗章,最终成就一首由中外古今的诗人、无名的歌者以及被歌唱的无名者共同完成的大诗。作为个体的诗人,通过与这一大诗的联系而获其本质,他从它而来,并为它所规定,因此他必以谦卑的姿态面对它:“我想成的乃是诗歌”,“我怎能阻挡在歌的前面/这诗歌不是比你我更大么/我是诗歌之后,那泥土粗糙、口含虎穴/它是我心头的太阳/哪一个诗人为了自己会把太阳忘记?”(《大海·第一歌》)
这些无名的“圣者”在投往世界的途中所倾心的不是王者、官吏和市井社会所梦寐以求的生杀予夺的威权、显赫的声名、夸耀于市场的财富,甚至也不是今日小资们所向往的幸福,更不是“高帅富”之类等而下之的目标,而是灵魂的砥砺与熔炼。磅礴的灵魂,就是他们所成就的,是他们随身携带,永不会失去的财富。由是,他们于天路上的道是一赤子之道,也是成为超乎个体之上的大生命之道:“我能,我做,我熔炼/这是我所行的/为我成为一个赤子/也是一个与我无关的人”(《漫游时代》)。——成为“一个与我无关的人”,就是从自我走向他人和世界,让自我向世界和他人敞亮和敞开。他们以良知和同情为立足:“只有良心上/很快地/涌起了一大块发光的液体”(《归鸟》),“万念俱灰而空余天良未泯”(《大海·第十五歌》);以质朴无畏为盾:“热爱生命并且质朴无畏”(《黄昏(二)》);牺牲为斧钺:“他离开了我们/证明了/我们没有坚持的朴素信念/自由/原来就是/鲜红的血液”(《殉道者》),“世界说需要燃烧/他燃烧着/像导火的绒绳”(《先锋》),“冲破剑拔弩张的密林/群星已经聚集/是时候了/歇一歇你撕成碎片的躯体”(《春之祭》),“我们活着不过在殉葬/他们死了却是去牺牲”(《舞族》),“这纯黄而暖热的浆汁/饱含着希望失地和回声/在跨度上酿造/依然地影着完美和牺牲”(《世界的血·蜜——献给太阳和灿烂的液体》)。正是从这无名者的牺牲中,熔炼了一种血性的、源于生命根柢的高贵:“这就是说我的头颅是高贵的/我的产物也应该高贵”(《和平神祇》),“高贵勇敢的头颅在太阳里精美绝伦/高贵勇敢的头颅在太阳里易于粉碎”(《世界的血·日和夜》)“他的泰然/他的质地/他的至大/是那么有为而高贵”(《大海·第十三歌》)这一高贵的性质及其纯度,在骆一禾那里,是依其与生命本质的联系来决定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在骆一禾看来,生命的本质从生命的全体而来,并为它所规定(也是成为“一个与我无关的人”):生命只有在与生命之全体的联系中成其本质,而孤立的生命就是自绝于这一本质。海德格尔对于诗人有两个关系其本质的命题:一是,忧心是诗人的天职;[4]另一是,诗人的天命是为他的民族谋求真理。[5]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那么现代。真正的诗人从远古就已承担了这一忧心和为民族谋求真理的使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西周这位如此道说的诗人也不是第一个如此忧心的诗人。当曹操作为一个诗人,他也是忧心的化身,“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其所忧者不是一己之私,而是天下,或者说是处于崩坏中的文明。其实,海德格尔的两个命题在不同的称谓下,言说着同一个真理:诗人与生命本质的亲密关联。真正的诗人所忧心的就是这个生命的本质,他所为他的民族谋求的也是这个生命的本质——作为人民的灵魂的历史实现。而在骆一禾看来,这一灵魂在中国迄今为止从未完全实现。骆一禾说:“在中国大地和俄罗斯大地一样,生长着同样厚实而沉重的人民,在此,人民不是一个抽象至上的观念,他不是受到时代风云人物策动起来的民众,而是一个历史地发展的灵魂。这个灵魂经历了频繁的战争与革命,从未完全兑现,成为人生的一个神秘的场所,动力即为他的深翻,他洗礼了我的灵魂,并且呼唤着更为智慧的生活。”[3](P833)与生命本质也即人民的灵魂联系的方式包括歌唱与行动。歌唱是对生命本质的召唤,并在自身中为生命本质的到来准备处所;行动则是生命的本质的兑现,并为这一本质的持存提供血的动力。就两者的关系而言,歌唱是人向着行动的开口,它为着行动并在行动中达到圆满和实现自身。里尔克的诗道:“歌唱即实存。”海德格尔对此阐释说:“吟唱,真正去道说世界实存,是从整体牵引的美妙方面去道说,而且只是道说这种美妙。吟唱意味着:归属到存在者本身的区域中去。”因此,这种歌唱始终是艰难的,“其艰难不仅在于难以构成语言作品,而且也在于,难以从对事物的一味贪婪地观看的言说作品,从视觉作品,转向‘心灵的作品’”。[6]骆一禾对于诗歌歌唱性的探索,正是相关于海德格尔所说的这个“心灵的转向”,用他自己的话说乃是对于“人民的灵魂”的深翻。这个灵魂作为心脏向行动者泵送着“世界的血”,并从根源和根基的意义上承担着世界。活生生的世界就是在血中运行着的:“这时候,让泥土随身而起/把整个深渊提起来/并不是一切都要放在地面/提起伟大的青春、海拔和盐/从永昼里提起光明来/并不是一切都要放在地面”(《世界的血·世界的血》)。这是关于伟大的憧憬,也是从伟大而来:“当脚掌证实心脏的时候/那是一条伟大的道路/一种新生”(《长征》),“伟大是超出寻常的规模和气象/也是莫大的/震动了本能的深度和悲痛”(《大海·第八歌》),“为生命的伟大,请扩张你的心脏”(《大海·第十六歌》)。
在如此憧憬中,一种浩然的辽阔胸怀腾起。诗人说:“修远,这两个圣诉蒙盖在上面”(《修远》)。诗人说:“谁不能长驻辽阔胸怀/如黄钟大吕,巍峨的塔顶/火光终将熄灭,只剩下洞中毒气/使穷兄弟发疯”(《辽阔胸怀》)。在赋有如此胸怀者的眼中,所见的乃是使个人消失的事物:“星座闪闪发光/棋局和长空在苍天底下放慢/只见心脏,只见青花/稻麦。这是使我们消失的事物”(《壮烈风景》)。这般忧心的、为民族谋求真理的心灵,是站在通向伟大的起点上,也就是站在诗人所谓“天路”的起点上。由此而往,通过行动、受难和牺牲,通过胼手胝足的劳作、跋涉、奔波,最终在本于自性的灵魂本质——它从未脱离与人民的灵魂也即生命的本质的联系——中熔炼出“伟大”的钻石:
我撕开空气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伟大的艺术家们别有人间/而永生为什么不出现在这座城里/终生穷困只是因为精神缭绕(《乐》)
每一个奔波了一生的劳动者/都用一部伟大戏剧,一部伟大音乐/一部伟大的诗歌/总结了我们的一生(《一块大陆的五座北方》)
这时人也就有了神性。骆一禾不仅一直深信而且一直从其血的本质中体验着人和神这种神秘的、互相分享的关系。在骆一禾看来,真正的人都必然有神性(荷尔德林的诗“神乃人之尺度”),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而神就是人的升华,是人向着天空之物的归向。这是他的根本信仰,也是他的属“圣”的心灵属性决定的。早在1985年,他就写出了这样的诗句:“人/到了这时候/就该长成神明了”(《祖国》)。以后,这一主题不断回响在骆一禾的诗中:“神的灵依附于我的身体”(《世界的血·雪景:写给世代相失的农民和他们的女儿》),“人的一半/是神的一半”(《大海·第四歌》),“在诗歌深处我送走人心/这大地上流浪的,脆弱的神明”(《大海·第十六歌》),“我在神的心里走着”(《大海·第十六歌》)。
这一人神共居的主题也回响在其家园主题的咏歌中,寻找家园,也就是为心灵找到向神性的归宿,回乡也就是回到神的故乡:“埃斯库罗斯,远在他乡的悲剧之父/我的诸般神圣的对话者/你所有的神都像人,你所有的人都像是神/……/就像神来到人的家乡,人来到/神的家乡”(骆一禾《素朴:语言和海》)。这是他的血中之歌,也是他灵魂中最深沉的歌:“哦我那长长的长长的/我那长长的回故乡之路”(《生存》),“我渴望家园”(《翼之上》)。不同于物质的、人世的家园,心愿之乡以空白显现自身,因为它就是我们自身中那没有实现的(神性):“或许只是我们心里那块凄怆的空白/我们望它就如望乡”(《生存》)。然而,真正的居住就是居住于心愿之乡,只有这种居住才能实现人在自身本质中的永久栖居,只有这种居住能够改变人所深深感受到的“万物之逆旅,百代之过客”(李白语)的暂栖性。那么,诗人所行的就是那通往神的家乡之路:“伟大的舞族踉踉跄跄地走着快乐的乐曲/涂满白垩似的道路/两侧燃烧着荆棘/照出了他们最后的舞蹈”(《世界的血·舞族》)。可以肯定的,正是脆弱的、必死的个人向着家园回归之途成就了“伟大”:“伟大的幻想伟大的激情/都只属于个人/随生而来随生而去/每一个世纪都有人摸索它由此竭尽”(《世界的血·女神》)。
不难看出,“圣”正是骆一禾诗歌主体的精神原型——它从本源的、属水的爱和良知出发,经由行动、受难和牺牲,最终走向了信仰和神性。在这一路途中,诗人改变了他最初关于美、艺术和人生的设定。在美与善的关系上,骆一禾从最初以美为核心,到成熟时期走向了善对美的全面覆盖。骆一禾早期的诗具有唯美色彩,以他自己的一行诗来概括,那就是“少年歌唱少女的美丽”(《海滩》)。写于1987年的《美丽(一)》最能代表其早期诗作的这种唯美气息:“又闻雨声/那水里的浪花盛开/你那葱青的小屋顶依旧//阳光晒暖后背/飘着春雪/一种早早的感受/使我期待你/你是才惠的青草/初通人性”。然而,这个美的歌者,这个“为美而想”的沉思者,不久却转向了善,而把诗人视为“冒险行善的人”。他说:“这歌中的美人人懂得/这善却只有等到我抵家园”(《修远》二稿)。在《大海·第十三歌》中,他甚至说“美”只是次要的、无足轻重的东西:“在漆黑的深海/美观是非常无足轻重的一端/……/在这深海/古风可以是不美观的而是一种至美”。这就是说,相对于“善”所建立和成就的,“美”只是附属的,而“至美”在性质上可能正是与“美”背反的。当然,这并“不美观”的至善正是建基于此前的“少年”对于美的敏感心性上的,没有这个少年心性,所谓的善就会失去自己的根基。实际上,少年心性的美就是自性的善。而诗人成熟时期的“至善”,是从自性走向作为灵魂和本质的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这就是骆一禾在《世界的血·蜜:献给太阳和灿烂的液体》里所写的:“居天下之 正行天下之志 处天下之危”。这也是骆一禾为新文化型态下的“圣”所下的定义。
骆一禾也写到“王”。但在多数的情形中,“王”在骆一禾的诗里,是作为一个负面形象出现的。在《大海·第十二歌》中,“王”完全是反面形象。骆一禾在这一歌里写到了“万王之战”,但无论万里吞云、一世横行的“天下之王”,还是引吭高歌、仪态万方的“谎言之王”,抑或执着于迷狂和探险的“酒神之王”,居中苦练、全盘忍受的“僧侣之王”,还是“旋转着望向未来”的“虚构之王”,以及“抽象之王”、“变体之王”、“玄机之王”、“滚石的废王”等等,在骆一禾看来,他们所占有的只有灰烬,他们的结局都只是“惨灭和悲悯”。就是说,他们都处于骆一禾诗中“圣”的对立面。这和海子以“王”作为主体形象的象征完全不同。
二、王:海子诗歌的主体形象
如果说骆一禾的精神原型是“圣”,那么海子的精神原型就是“王”。“王”是海子诗歌中出现频度最高的词之一。粗略统计,“王”字在《海子诗全编》中出现500多次,“帝”字出现近百次,两者合计达600多次。也就是说,在《海子诗全编》中隔不一页,就会出现一个“王”字或“帝”字。这两个词某种程度上成了海子的心魔。在骆一禾的“圣者”形象的周围,是智者、勇者、义人、俊杰、战士等亲和性形象,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精神结构相近的诗歌意象系列。在海子这里,则是“国王”、“帝王”、“歌王”、“皇帝”、“王子”、“王后”、“王冠”、“王座”、“王位”这些以“王”和“帝”为词根的词汇,它们构成了海子诗歌心象的词汇学基础。这一事实暴露了海子内心的秘密——对诗歌荣誉的珍爱和追逐,以及由此而来的殚精竭虑。海子确乎是为诗歌而生,为诗歌而死。骆一禾说,“这就是他的一门心思”。[7]
如果我们不考虑海子诗歌学徒期间的习作,而以海子正式进入自我抒写阶段的1983年以后的诗作作为研究的起点,我们会饶有意味地发现,海子第一个以“王”为词根的词汇(“王冠”)出现在1983年写的《农耕民族》中。在这首里,它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在发蓝的河水里/洗洗双手/洗洗参加过古代战争的双手/围猎已是很遥远的事/不再适合/我的血/把我的宝剑/盔甲/以至王冠/都埋进四周高高的山上/北方马车/在黄土的情意中住了下来”。这首诗写到了一个由狩猎、战争走向农耕的文明化过程。但海子本人后来走过的诗歌道路正好与这首诗写到的过程相反,呈现了一个反文明的“野蛮化”过程:它从农耕颂歌出发,逐步退向更原始的狩猎之歌,最终结束于对原始暴力的赞美。在这一过程中,诗人把他曾经埋进高高山上的宝剑、盔甲、王冠统统挖了出来,已经在黄土的情意中平静下来的血也重新沸腾,暴力对人再次变得充满诱惑和魅惑,而诗人最终在一种针对自身的暴力中摧毁了自己。写于1985年《打钟》,以二十三行的篇幅集中了海子诗歌中几对重要的对立主题,因而特别值得引起注意。这几对主题包括:爱与死,爱与疾病,柔情与暴力,孤独与众人。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抒情主体的自我形象:皇帝。这个形象,毋庸讳言,正是诗人自我的一个镜像。它可能受到张枣早年的名作《镜中》的启发。但是,张枣《镜中》充满青春气息的唯美,在这里被一种暴力、颓废和孤寂的氛围所代替。这个“恋爱的皇帝”形象折射了海子心灵的某些基本倾向:自恋,爱的渴望与爱的恐惧,自我神化的冲动。这里,爱人也是敌人和对手,爱情也是火灾和战争:
我是你爱人/我是你敌人的女儿/我是义军的女首领/对着铜镜/反复梦见火焰
在海子笔下,对爱情的追求,是类似飞蛾扑火的举动:“恋爱,印满了红铜兵器的/神秘山谷/又有大鸟扑钟/三丈三尺翅膀/三丈三尺火焰”。海子的自恋冲动,从他诗中不断自呼其名中多少可以窥见消息。“王”的形象、“皇帝”的形象是他这一自恋心性的象征化表达,它们充斥海子各个时期的诗:
骨头之中/楚国的歌声四起/我是楚国的歌王(《但是水、水》)
诗集,我嘴唇吹响的村庄/王的嘴唇做成的村庄(《诗集》)
我来到玫瑰花园/脱下诗歌的王冠(《玫瑰花园》)
秋天深了,王在写诗(《秋》)
两半血红的月亮抱在一起/那是诗人孤独的王座(《黎明和黄昏》)
盐田上坐着痴呆的我——走投无路的诗人之王(《土地》)
诗歌生涯本是受难王子乘负的马(《土地》)
我从原始的王中涌起涌现/在幻象和流放中创造了伟大的诗歌(《土地》)
我像一个诗歌皇帝披挂着饥饿/披挂着上帝的羊毛/如魂中之魂手执火把(《土地》)
太阳中盲目的荷马/土地中盲目的荷马/他二人在我内心绞杀/争夺王位与诗歌(《土地》)
在夜色中/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夜色》)
我是擦亮灯火的第一位诗歌皇帝(《太阳·诗剧》)
作为国王我不能忍受/我在这遥远的路程上/我自己的牺牲(《月全食》)
“王”、“国王”、“王子”和“皇帝”的意象系列在海子诗歌中贯穿始终。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推断出诗人膜拜权力的结论。实际上,海子的“王者”形象和世俗权力无关,在海子那里,它们完全是诗歌荣誉的象征。海子最终成为了一个“在死亡中高叫自我疯狂掠夺/难以生存的走投无路的诗人之王”(《太阳·土地篇》)。在这里,“王”的形象一方面联系着诗人基于自恋的自我夸张,另一方面又总是和海子心仪的诗歌事业分不开。在《以梦为马》一诗中,海子说:“我选择永恒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他从古到今——‘日’——他无比辉煌无比光明/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对海子来说,诗歌就是“永恒的事业”,而且是唯一的。如果说骆一禾认为艺术家是无名的,那么海子对艺术家之名、诗人之名不但珍视,而且极为敏感。[8]在同一首诗中,海子虽然也有“我必将失败/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的表白,似乎他也愿意像骆一禾一样,把诗歌看成无名者的事业。然而,事实上对海子来说,诗人的事业和诗人之名是分不开的。而且,在海子看来,诗人之名还存在界限分明的等级差别。在海子那里,诗人、诗歌王子、诗歌之王(或诗歌皇帝),这是一条严格的等级性链条。海子把自己看作诗歌王子中的一员,但内心里却渴望成为诗歌之王。他说:“做地上的王者——这也是我和一切诗人的事业。”[9]他从自己的才华,某种程度上,也是从自己预感的命运,认同他所谓的“浪漫主义诗歌王子们”。他说:“我更珍惜的是那些没有成为王的王子。……他们是同一个王子的不同化身、不同肉体、不同文字的呈现、不同的面目而已。他们是同一个王子,诗歌王子,太阳王子。对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与这些抒情主体的王子们已经融为一体”,“有时,我甚至在一刹那间,觉得雪莱和叶赛宁的某些诗是我写的”。[10]然而,他对于成为诗歌之王还是抱着热烈的期待:“当然,还有一些终于为王的少数。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就是。命运为他们安排了流放,勤奋或别的命运,他们是幸运的。我敬佩他们。他们是伟大的峰顶,是我们这些诗歌王子角逐的王座。对,是王座,可望而不可即。……但丁啊,总有一天,我要像你抛开维吉尔那样抛开你的陪伴,由我心中的诗神或女神陪伴升上诗歌的天堂,但现在你仍然是王和我的老师。……”[10](P896-897)正是由于这种诗人等级制的存在,成为诗歌之王、争夺诗歌王位的过程就演变成了一场残酷甚至惨烈的竞争和角逐:“自从人类摆脱了集体回忆的创作(如印度史诗、旧约、荷马史诗)之后,就一直由自由的个体为诗的王位而进行血的角逐。”[10](P896)在《诗学:一份提纲》中,海子抄录了未写出的《太阳·地狱篇》的写作提纲,其中赫然有“诗歌始皇帝”的标题——他渴望成为中国的诗歌始皇帝,而这个“成为”的过程,也如秦灭六国一样血腥而酷烈。
在海子那里,诗歌的意义有一个无限放大的趋势,它甚至覆盖了生活和生存本身,而成为唯一的实存。在骆一禾那里,诗歌的意义根源于生活,诗歌行动的目的在于重建生活,或者创造生活的可能。对于海子,这一关系似乎是颠倒的,诗歌成了生活意义的根源,而且它似乎总是野心勃勃地渴望取代生活。海子也强调诗歌要成为行动(在《太阳·断头篇》中,海子甚至不断发出“行动第一”的呼吁,其后记更直名之曰“动作”),但是海子的行动也被限定在文本之内。在海子的文本中,到处是血腥的征逐杀伐,然而这些行动却是不及物的,对现实无所触动,海子也并不想有所触动——它们仅仅是诗人的诗歌幻象。海子的一个未完成的写作计划正透露着这样的信息:“我一直想写这么一首大型叙事诗:两大民族的代表诗人(也是王)代表各自民族以生命为代价进行诗歌竞赛,得胜的民族在歌上失败了,他的王(诗人)在竞赛中头颅落地。失败的民族的王(诗人)胜利了——整个民族惨灭了、灭绝了,只剩他一人,或者说仅仅剩下他的诗。”[9](P904)也就是说,生活的胜利和诗歌的胜利不可兼而有之。而在海子看来,诗歌的胜利已经足够:只要诗歌之王的诗万世长存,哪怕整个民族因此惨遭灭绝。
诗剧《太阳·弑》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海子的上述构思,当然情节更复杂,涉及的主题也更丰富(除了诗歌主题,它还涉及权力与阴谋、革命与背叛、爱情与友谊、青春与死亡等多对互相对立、对峙的主题),但仍然可以看作一个关于诗歌王子竞逐诗歌王位的隐喻。剧中年老无子的巴比伦王用诗歌竞赛的方式来确立王位继承者,胜利者被选为王子,失败者人头落地,“让一个人踏着另一个的头颅走向王座/用理想和诗这心中之剑互相屠杀”。剧中的吉卜赛成了最终的胜利者,赢得了王位的继承权,然而却以兄弟的头颅为代价。这是他赢得胜利之时的独白:“我以诗歌为武器,杀死了我的同胞兄弟。我现在已成了王子。(疯狂大笑)这是暴君的王子。现在都是没头的王子。我一定要完成无头王子的使命。”也许,在海子看来,为诗歌的王位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而这正是海子在他的生活里所行的,他把生活的全部砝码押上了诗歌的天平。说海子的诗歌行动是不及物的,那是因为他的诗歌行动不针对外部世界,也没有改变外部生活的企图。然而,就他自己而言,这一行动却是高度及物的,真正做到了“像自己写的那样生活”。[11]
海子的这种诗歌形而上学,秉自尼采将艺术视为“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12]的审美人生观。骆一禾也以此尼采的酒神精神来阐释海子的基本精神构造。他说:“(海子)处于梵高、尼采、荷尔德林式的精神境地:原始力量核心和垂直蒸晒。”[11](P871)写于1987年的《尼采,你使我想起悲伤的热带》,是海子向尼采致敬的诗。在诗里,海子把自己和尼采的关系比作鱼头和鱼尾的关系:“一只陶罐上/镌刻一尾鱼/我住在鱼头/你住在鱼尾”。在海子看来,尼采的疯狂正是酒神精神在现实生活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你踏上雇佣军向南进军的大道/走出战俘营代价昂贵/辉煌的十年疯狂之门/一眼望见天堂里诗人歌唱的梨花朵朵。”诗中的“向南进军”,显然是指由理性走向酒神式的沉醉所经之道。海子把南方视为原始生命力的泉源所在,而把北方视为冷漠的理性的位置所在。在海子看来,所谓“文明的生存”,不过意味着生机的衰退和活力的丧失。在《太阳·诗剧》中,海子沿着这个向南的方向,一路来到了太阳焚烧的赤道,从一个诗人变成了一只猿,从一支歌变成了一把剑。海子的不能酒而沉溺于酒,显然也与他对酒神精神的认同有关。“酒”和“醉”也因此处于海子诗歌中另一重要意象系列的核心位置。他把酒视为“血中之血”、“人类的皇后”、“内心的谷仓”。在《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中,海子充满激情地描写了酒徒的拼酒、酗酒以及醉后的幻觉。小说中的叙述者逃出牢狱,撞进了一家酒馆,又一次闻到了酒的气息。接下来,他叙述道:“我接过一位有刀子一样眼光的人递过来的液体一饮而尽。酒,啊那是酒。是酒。……我必须用一坛子一坛子酒把我这条在地牢在荒芜的山上丢失的命捡回来。我知道。这是我的命定之星,酒,每当我大醉或十分饥饿后,呕吐了一地,我又能在这呕吐的滋味中十分地痛饮一次,大醉一次。我的呕吐,恢复和再生功能之胃十分完善,哪怕我全身已十分瘫了。我仍是酒神,大风和火速运行的雨阵雷鸣之神,我更是酗神”,“在众人狂饮中我最狂。全身抖颤像沙漠上披头散发的呓语的神,坐在一面古老又大的鼓上。全身是火药硫黄味,羊骚马尿味,和化为青草野花的阵阵香气”。海子大概是中国现代诗人中最深情地描绘酒和醉,并赋予其形而上意义的诗人。他写出过最美妙的关于酒与醉的诗句。1987年8月30日醉后早晨所书的这首《日出》,最能表现那种着魔一般的、欣喜若狂的酒神状态:
在黑暗的尽头/太阳,扶着我站起来/我的身体像一个亲爱的祖国,血液流遍/我是一个完全幸福的人/我再也不会否认/我是一个完全的人我是一个无比幸福的人/我全身的黑暗因太阳升起而解除/我再也不会否认天堂和国家的壮丽景色/和她的存在……在黑暗的尽头!
酒精的作用强化了自我的迷恋,放大了自我的幻觉。响彻《祖国或以梦为马》中的那个高亢的声音:“太阳是我的名字/太阳是我的一生”,表明海子已经在幻觉中将自己与笔下的太阳合为一体。在《太阳·诗剧》中,海子的口吻俨如神明:“我夺取了你们所有的一切。/我答应了王者们的请求。赦免了他们的死。/我把你们全部降为子民。/我决定独自度过一生。/……/你们或者尽快地成长,成为我/或者隶属于我。/隶属于我的光明/隶属于我的力量。”在主体的无限膨胀中,诗人仿佛接近了尼采所描绘的人神合一状态:“此刻他觉得自己就是神,他如此欣喜若狂、居高临下地变幻,正如他梦见的众神的变幻一样。”[12](P61)然而,这也是一个黑暗而空虚的王。诗人自己说,“走过全部天堂和沙漠的人必是一个黑暗而空虚的王”。其实,黑暗和空虚的原因并不在于他是否走过了全部天堂和沙漠,而在于一个唯我主义的“王”所能收获的一定只有黑暗和空虚。因为,对一个“在这一千年里我只热爱我自己”(《西藏》)的人,王座、王位和王冠都不能有所安慰,相反,他的内心将因王座、王位和王冠而更加荒凉空虚:“作为国王我不能忍受/我在这遥远的路程上/我自己的牺牲”(《月全食》)。
海子的人神一体状态是超善恶、非伦理的,与骆一禾对“歌中的善”的追求正好南辕北辙。实际上,海子几乎从不为“善”而歌。虽然他说过,“在所有的人中/只有我粗笨/善良只有我④/熟悉身边的木头/瓦片和一代代/诚实的婚姻”(《门关户闭》),但以“善”为词根的词汇在海子诗中出现的频率很低,而且多是作为修饰性的用法出现,几乎不构成实质意义。显然,“善”对海子缺乏吸引力。海子也不为真实和真理而歌。虽然他喜欢谈论真实和真理,但他的结论是真实和真理对人类根本不可能存在。海子魂牵梦萦的只有一样,那就是美。在《海子诗全编》不算“美”的众多同义、近义词,光以“美”为词根的词汇就出现近250处,频度之高仅次于“王”为词根的词汇。对海子来说,流水美丽,风美丽,云美丽,阳光美丽,月光美丽,闪电美丽,火美丽,早晨的星美丽;草叶美丽,树枝美丽,果实美丽,杜鹃美丽,山楂美丽,五谷美丽,白杨树美丽,戈壁美丽,肮脏的大地美丽;灯美丽,井美丽,塔美丽,房子美丽,村庄美丽,小镇美丽,家园美丽,远方也美丽;鸽子美丽,奶牛美丽,马匹美丽,狮子美丽,豹子和老虎美丽;少女美丽,肉体美丽,骨头美丽,头发美丽,脚趾美丽,血污美丽,晨光中的情人浑身美丽,故乡打麦场上的女俘虏美丽,甚至凋零的棺木也美丽;早晨美丽,黄昏美丽,夜晚美丽,春天美丽,夏天美丽,秋天美丽,冬天也美丽;微笑美丽,飞行美丽,行走美丽,虫鸣美丽,软体动物的爬行美丽,生育美丽……在海子眼里,美丽无往而不在:美丽在春天,美丽在天上,美丽在水里,美丽在草原上……这众多的、不胜数的“美丽”,甚至让人感到海子诗歌词汇的单调,却足以证明美在海子心目中的地位。对海子来说,一方面,美对他具有最大的吸引力,正如他自己说的:“美丽总是使我沉醉”(《跳伞塔》);另一方面,他的诗包括他的人生都是“为了美丽”(《为了美丽》)。显然,这种“唯美”的态度与后期骆一禾认为“美观是非常无足轻重的一端”的态度也大异其趣。
注释:
①《孟子·万章下》列举了圣人的四种类型:“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②柳宗元在《箕子碑》中提出了伟大人物的三个标准:“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
③“此时”,《骆一禾诗全编》作“此是”,据《花城》1988年第4期发表稿改。
④此行《海子诗全编》作“善良的只有我”。根据原诗断行法,“善良”在语法上应接上行,“只有我”则接下一行“熟悉身边的木头”据笔者大学时候的手抄稿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