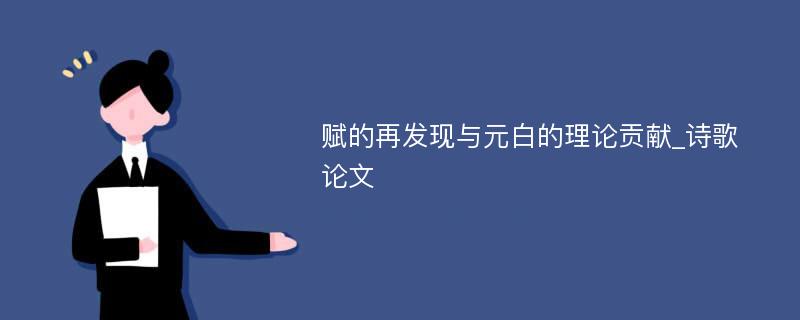
赋之再发现暨元白的理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发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现暨元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6)02—0035—06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倡言:“元和、长庆的时代,真是中国文学史一个很光荣灿烂的时代。这时代的几个领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动,都下了决心要创造一种新文学。”这是一个“有意的、自觉的文学革新时代”[1](P366)。而元稹、白居易则是这“几个领袖文人”中的佼佼者,其巨大的创作成就给予诗坛以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元、白在中国文学史、批评史上,更是以其所倡导的对诗歌艺术功能的重视而名重一时。元、白论诗,大抵主张诗须有为而作。元稹《乐府古题序》倡言:“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寓意古题刺美见事”,赞扬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2](P255) 之新题乐府,并以之作为模范。在《叙事寄乐天书》中又申明此义:“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2](P352) 受元微之影响,白居易《与元九书》作了更为深入详尽的解说,从文之本体论来探讨文之本源,标举“六义”,在对以“六义”为绳衡的诗歌发展史的追述中,批评“六义”之缺失——“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对于杜甫则肯定其“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的杰出创作才能,又遗憾于其“六义”充沛的作品数量不多,未能形成蔚然成风的创作气象,因此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3](P2790),要求诗歌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元白对诗歌社会功能的重视,实源自“六义”,要求诗歌以情而感人,达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目的。就其形式而言,实乃一种复古的文学主张。故而陈寅恪说:“二公新乐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篇之乐府如《兵车行》者为其具体之模楷,固可推见也。”[4](P123) 以复古之名而行创新之实,乃元白诗歌理论及其实践所取得巨大成就之关键。
对于“六义”,孔颖达的解释可以代表唐人的普遍意见,《毛诗正义》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5](PP.12—13) 那么,风、雅、颂是诗之体裁,赋、比、兴是诗之表现方法。
作为表现方法的赋、比、兴,郑玄《周礼·春官·大师》注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并引郑众之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物于事也。”[5](P11) 相较而言,尤其重视比、兴。因为,比、兴或借外物起兴,或通过比喻来表现作者的思想情感,探讨的是此二种表现方法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涉及到了如何进行形象创造的问题,揭示出诗歌创作是通过具体的物象来抒发情感、表现现实生活的。在实际创作中,比、兴是不同的,《文心雕龙·比兴》以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6](P601) 对此,刘永济分析得比较精到:
比者,著者先有此情,亟思倾泻,或嫌于迳处,乃索物比方言之。兴者,作者虽先有此情,但蕴而未发,偶触事物,与本情相符,因而兴起本情。前者属有意,后者出无心。有意者比附分明故显,无心者无端流露故隐。《困学纪闻》载李仲蒙《释赋比兴义》……曰:“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记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7](P142)
并进一步指出“兴之为义,虽精于比,而其为用,则狭于比”[7](P142),遂造成了后世兴义销亡,比兴连类,其意则侧重于比。其实清人黄叔琳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指出后代诗歌“非特兴义销亡,即比体亦与《三百篇》中之比差别;大抵是赋中之比,循声逐影,拟诸形容,如《鹤鸣》之陈诲,《鸱鸮》之讽谕也。”[8](P215) 黄侃说得更为明确:“自汉以来,词人鲜用兴义,固缘诗道下衰,亦由文词之作,趣以喻人,苟览者恍惚难明,则感动之功不显。用比忘兴,势使之然,虽相如、子云未如之何也。”由于比、兴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用比者历久而不伤晦昧,用兴者说绝而立致辨争”[9](P220),兴之销亡,实在是无可如何之事。应该说,兴者,称名小而取类大,其要在于揭示形象所涵蕴的现实意蕴;比则拟容取心,求其神似,其要在于展现形象的形似及神似。赋比兴乃体用(诗体与诗法)问题,即体即用,诗体与诗法相兼,不可截然割裂。因此,在兴义销亡、比兴之义混淆难明之时,比兴的即体即用则简化了,所谓比兴则仅仅成为蕴含了某种比喻、寄托的意义的代名词——不是作为一种表现手法而要求辞句的炼饰;而是重在要求表现寄兴讽谕的内容,重视篇章的寄托寓意。
这一理念,在唐人诗论中比较突出。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倡诗歌在内容上要有“兴寄”、在艺术风貌上要有“风骨”、要“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所谓“兴寄”,强调的是诗歌内容的丰富深厚、情感的强烈深沉,而非“采丽竞繁”式的浮靡浅薄。陈氏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正是其丰富深厚内容、强烈深沉情感的体现,乃其“兴寄”理论的最好实践。李白主张“寄兴深微”[10](P17),倡言“《大雅》久不作,吾衰竞谁陈”[11](P91)、“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11](P156),重视继承《诗经》美刺比兴的传统,要求诗歌具有关注现实的精神,李阳冰《草堂集序》称其“凡所著述,言多讽兴”[11](P1789),吴融称其“气骨高举,不失颂咏风刺之道”[12](P364)。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则在赞美元结的《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二诗“道州忧黎元,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之时,直接提出了“比兴体制”,并要求艺术创造上的“微婉顿挫”。考察元结二诗,并非运用比兴手法,而是赋体,那么,所谓“比兴体制”则是对诗歌思想内容的丰富深厚、情感的充沛强烈之要求,也就是要求诗歌要发挥社会功能、具有关注现实的精神。受此理念的影响,白居易、元稹虽然陈义甚高,要复归“六义”,实际上对“六义”是有所取舍的,不能达到《诗三百》或者汉儒的要求,最终也只是将“风雅比兴”作为一种思想内容的标准,要求诗歌有所寄托寓意,能够关注现实民生而已。“风雅比兴”在元白的思想中,实在只是一种关注现实的理念而已,因此,比兴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创作手法的意义,那么,“六义”中最具有“体”“用”意义的只有“赋”了。
作为一种艺术方法,“赋”最初大多作为一种“用”诗的方法,属于所谓“借诗赋命”、“借诗言志”[13](P207);作为“六义”之“赋”,按郑玄的意见,比、兴是用一种委婉含蓄的方法来表达其意旨,而赋则是直接铺陈、不借助比喻和起兴的方法,意在直露明白地表述意旨,所以孔颖达《正义》云:“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赋之所铺陈,在于对政教之善恶表述意见,实际上已经寓有了警戒、劝谏之意,正如朱自清所说:“赋比兴的‘赋’多少也带上了政治意味,郑氏所注‘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便不是全面凿空立说了。”[13](P263)
“六义”之“赋”发展衍变,并与《楚辞》相互影响,遂由创作方法之一种而演变成文体之一。《汉书·艺文志》指出春秋之后,采诗制度消亡,然《诗》之精神未失,“学诗之士,逸在布衣”,秉承《诗》之关注现实的精神、美刺讽谕之旨,“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至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竞为侈丽闳演之词,没其风谕之义”[14](P1756),“赋”遂由“六义”之创作方法而衍成文体之一种。所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乃“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成为与诗不同的一种文体,即所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从创作方法衍变为一种文体,“赋”本身所蕴含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即所谓“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6](P134) ——由“直陈”衍为“铺叙”,重在铺张辞采而为文、体察物象以抒情,突出了叙述描写的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委婉详备,曲尽事情,以求穷形尽象且追求文采的夸饰。故纪昀评曰:“铺采摛文,尽赋之体;体物写志,尽赋之旨。”[8](P85) 确为知言之论。刘熙载也说:“诗为赋心,赋为诗体。诗言持,赋言铺,‘持’约而‘铺’博也。古诗人本合二义为一,至西汉以来,诗、赋始各有专家。”[15](P117) 皆揭示了赋之内容蕴含与艺术形式上的特点。
早在刘勰之前,挚虞《文章流别论》就认识到作为文体的赋,其特点是“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并且区分了作为创作方法的“赋”(古诗之赋)与作为文体的“赋”(今之赋)的不同:
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主,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疑作“富”)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选辞过壮,则与事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16](P191)
在探求赋之本义、考察创作实践、品评鉴赏等全面论析的基础上,刘勰建构了这一文体的根本原则:“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要求事义文采的相称,目的亦在避免挚虞所谓的“四过”。因此,刘勰赞扬“依《诗》兴《骚》,讽兼比兴”的屈原,批评两汉辞赋家徒具形式之美的作品:“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讽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沓,倍旧章矣。”[6](P602) 在刘勰的理论视野中,“蔚为大国”的文体之赋,大大强化了“体兼比兴”的诗法特色。
作为文体的“赋”的基本特点是铺叙,而在创作实践中,正如陆机《文赋》所说“选义按部,考辞就班”[16](P171),已经昭示了其谋篇布局的过程,并形成一定的格式,为后人所遵循。因此,“赋”也具有了篇章建构的意义。在“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形成“客主以首引”的格式——以主客问答开端,“极声貌以穷文”。而汉大赋之基本格式是“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至于小赋则是“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6](P135)。故纪昀评曰:“分别体裁, 经纬秩然,虽义可并存,而体不相假。盖齐梁之际,小赋为多,故判其区畛,以明本末。”[8](P87) 又,《诠赋》所论十家之赋,“并辞赋之英杰也”,选文以定篇,实乃昭示不同类别的赋所体现的篇章结构特点,亦具有“构篇”的意义[7](PP.24—28)。
要而言之,由“六义”发展而来、作为文体的“赋”,本身则蕴含了铺叙与构篇的意义,重在讲求文章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和文体的谋篇布局。受此影响,作为创作方法,“赋”不仅仅是“直陈”,重在铺叙,讲求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叙述描写,委婉详备曲尽事情以求穷形尽相;亦需讲求谋篇布局、叙述描写的步骤井然,以便更好地“体物写志”,描摹物象,表达作者的情感、意旨,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可见,发展至后代,“六义”之中,唯“赋”最具有体用相兼的特色,而这正是元白能够发扬光大的原因。
元白所倡导的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论诗则本于“六义”,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求诗歌“孕大含深,贯微洞密”,起到“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3](P2789) 的社会作用。白氏认为,其诗歌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3](P136), 是直接秉承了《诗三百》之义的。早在永贞二年二月,白居易所作《策林》之《采诗》、《议文章》,要求文章“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3](P3547),发挥劝善惩恶的作用,从考虑国家大政的高度,来认识诗赋文章巨大的社会功能。此外,从总结他人及自身的创作实践中,白居易也更为深切地体认到了诗歌的社会意义,《读张籍古乐府》曰:“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3](P5) 《寄唐生》曰:“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3](P43) 强调诗歌的社会功利性,注重其社会作用的发挥。元稹要求诗歌“雅有所谓,不虚为文”[2](P278)、“感物寓意”[2](P632)、“凡所为文,多因感激……稍存寄兴,颇近讴谣,虽无作者之风,粗中遒人之采”[2](P406),具有深刻的现实内容,“美刺见事”,能够关注社会民生,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
这一功利主义文学观要求,诗歌要发挥其社会功能,产生广泛的社会效果,就不能生涩隐奥,而要通俗易懂、明白晓畅;因此,白居易《新乐府序》说其诗“不为文而作”,采取最为简洁晓畅的艺术形式:“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3](P136) 并且要求诗歌语言质朴明快、晓畅通俗,使读者能够容易了解、接受,因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追求诗歌的通俗晓畅方面,元稹亦勇于探索,所谓“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予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2](P278)、“其间感物寓意,可备蒙瞽之讽者有之,词直气粗”[2](P632),实际上是为更好地发挥诗歌社会功能而追求艺术的通俗晓畅的一种委婉说法而已。
当然,元白诗歌亦有文辞繁冗、缺少含蕴的缺点。这一方面是由于元白出于“救济人病,裨补时政”的热切愿望,而追求诗歌的通俗易懂、叙事说理的周详所导致的。《和答诗十首序》曰:“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3](P105) 另一方面,是由于元白比较普遍地使用了“赋”这一即体即用的形式。 如前所论,元白虽倡导复归“六义”,向《诗三百》学习,然“风雅比兴”只具有思想内容之标准的意义,要求诗歌有寄托寓意,能够关注现实民生而已,已不具有艺术方法的实际效果。作为“六义”之一的“赋”,汲取了作为文体的“赋”的成就,体用相兼,由原本所具有的“直陈”而兼有了“铺叙”与“构篇”的功能,使得这一方法的创作能力大大加强:原本诗不能很好地表现杂沓情事,现在却能够游刃有余、穷形尽象,“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吐无不畅,畅无可竭”[15](P117),其委婉详备足以曲尽事情、细腻深入,产生动人的艺术感染力。实际上白居易对赋的理解,是汲取创作方法的“六义”之“赋”和文体的“赋”的创作特性的,《赋赋》承袭“赋者古诗之流”的观念,来阐述对“赋”的理解。白氏认为,赋乃秉承古诗之精神而进行创作的——“四始尽在,六义无遗”,就其实质而言,诗、赋则融为一体——“全取其名,则号之为赋;杂用其体,亦不出乎诗”,因此,诗、赋在艺术上是交融会通的,“信可以凌砾《风》、《骚》,超轶今古”[3](P2622)。此种观点,实受南北朝以来赋的“诗化”观念的影响,而出现了诗的“赋化”倾向,在元白的诗歌创作中有着明显的表现。对赋之“义兼比兴”、体用相通,《师友诗传录》论曰:
赋也者,因物造端,敷弘而体理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是赋者古诗之流也。雅颂之则,于是乎托;比兴之音,于是乎俪。故讽谕抑扬之音以寓,涵蓄渊停之义以存,是真风雅之正则也。流极其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辞,博诞绝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纤毫之内。祖构之士,雷同附和,罔知所终。至杜少陵乃大惩厥弊,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直纾鸿文,而新体立焉。较之白太傅讽谕诗、《秦中吟》之属,及王建、张籍新乐府,倍觉高浑典厚,苍凉悲壮。此正一主于赋,而兼比兴之旨者也。[17](P143)
虽扬杜抑白,但指出赋能够表达“讽谕抑扬之音”、“涵蓄渊停之义”,具有内容的现实丰富性和艺术的委婉含蓄,乃“风雅之正则”,则是中肯的。而且,如果赋法运用得比较恰切,可以取得“高浑典厚,苍凉悲壮”的艺术效果,发挥诗歌所具有的社会作用。
元白重新发现了“赋”的艺术价值,并从理论上阐释其体用相兼的特色。作为一种古老而有生命力的创作方法,“赋”长于叙事,深切著明;说理议论,畅其所欲;建构篇章,章法井然,颇有助于诗歌的通俗化。朱熹说:“简严者,似于事理有所未尽;而重复者,乃能见其曲折之详。”[18](P151) 信然,元白诗之深切入情亦正在于此。《滹南诗话》卷一云:“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捻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19](P511)
实际上,元白之重视赋体,乃受赋及传统乐府文学的影响,也与中唐叙事文学的兴起相关。萧涤非指出:
有唐一代,实为一切文学之复古时期,惟复古之中,往往寓创作与改进精神……所谓新乐府者,“因意命题,无所倚傍”,受命于两汉,取足于当时,以耳目当朝廷之采诗,以纸笔代百姓之喉舌者也。杜甫开其端,白居易总其成,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乐府至此,遂举一切六朝以来风云月露、绮罗香泽之体,一扫而空之。与汉之“缘事而发”者盖异代同负。实为乐府之写实主义时期,此又一变也。[20](P26)
所谓乐府传统之影响,一方面指写实精神,一方面指乐府诗常用的白描、对话、独白、铺陈等表现手法。在题材、语言方面,得益于古乐府也不少。徐祯卿称:“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盖叙事辞缓,则冗不精。”[2](P769) 其影响于诗歌,则不仅在于乐府体,而且及于其他诗歌体类。这一影响,杜甫开其端,至元白而发扬光大,使得赋法普遍、娴熟地运用于许多诗体。除乐府而外,杜甫“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2](P601)、“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3](P2790) 之作,亦深得赋法之精髓。元白正是由此勘破少陵之成就处,遂发扬光大,终自成一家面目。就诗歌艺术成就而言,元白讽谕诗而外的作品是颇值得珍视的,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曰:元相作《杜公墓系》有“铺陈排比,藩翰堂奥”之说,盖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之中,有藩篱焉,有堂奥焉……然而微之之论,有未可厚非者。诗家之难,转不难于妙悟,而实难于铺陈终始、排比声律,此非有兼人之力、万夫之勇者,弗能当也。但元白以下,何尝非铺陈排比,而杜公所以为高曾规矩者,又别有在耳。此乃是妙悟之说也。(元)遗山之妙悟,不减杜、苏,而所作或转未能肩视元白,则铺陈排比之论,未易轻视矣……元白之铺陈排比,尚不可跻攀若此,而况杜之铺陈排比乎。微之之语,乃真阅历之言也。[22](P39)
肯定元白诗歌“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之巨大成就,乃洞见诗歌创作奥秘之论,而非胶着于宗唐宗宋藩篱之识见。
而中唐叙事文学的兴起,为元白诗歌叙事及重视赋法提供了大的背景,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夫当时叙写人生之文衰弊至极,欲事改进,一应革去不适描写人生之已腐化之骈文,二当改用便于创造之非公式化之古文,则其初必须尝试为之。”“是故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本与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体制也……此文体之兴起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其优点在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备具众体也。”[4](P4) 秉承此文体革新之精神,且预此叙事文学兴起之风会,元白遂肆力于诗文之改造。
“文备众体”之传奇,其本义乃在于叙述故事描写情节、在于展示客观场景,叙述、描写之委婉曲折、旖旎多姿,也不妨碍含蓄而巧妙地抒情,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使得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故其感人也深。不但如此,传奇以其匠心独具之谋篇布局、篇章建构,而使得故事波澜层深,引人入胜,感动激发人意。而此二者均与赋法之铺陈、构篇有极相通处。诗歌长于抒情,而其短处则在于难以详尽地叙事及刻画人物,所叙事情因过于简略而徒具梗概,不能引人入胜。元白乃中唐传奇创作之健者,自应熟谙叙事之技巧及构篇之章法,并在诗歌创作中自觉抑或不自觉地加以运用,则合于杜甫诗歌所昭示的“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之一途,周详而委婉,散散诞诞,往复回环,情深意足,详而不觉其繁,曲尽事情,如对面话语,从而赋予了赋新的艺术生命力[23]。而且,元白诗歌将内在的心灵视角,转向了外在的人世,以其杰出的艺术思维,将人世物情及心灵感受外化为内蕴丰富的诗歌,叙事、抒情,描写日常生活琐事,皆委婉周详,曲尽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一意百折,往复缠绵,极平极曲,愈浅愈深,亲切感人,故能盛行于一时,为人赏爱且当时及后世模范者甚众,良有以也。
在中国古代文学、文论发展史上,许多概念与范畴的提出,往往具有丰富的意蕴,并随着后人的踵事增华,使其内涵更为丰富多彩,且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因此,理解这一概念、范畴的最初意蕴,进而探讨其踵事增华、与时俱进的内涵,对于研究理解艺术创作的相关专题,阐释复杂丰富的艺术创作实践颇有裨益。[24] 要而言之,赋本为《诗》之“六义”之一,乃一种表现手法,衍变而为文体之一种。在此表现手法与文体之彼此消长融会之中,受赋体文学之影响,赋法具有了直陈、铺叙、构篇的功能。赋的诗化与诗的赋化,相互作用,遂使得赋法的内涵越来越丰富。至中唐,元白受传统乐府及新兴叙事文学——传奇之刺激,由杜甫转向写实而开其端的赋法,被元白重新发现,“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不但作为创作手法,亦运用于篇章建构,在各体诗歌中都有表现。其委婉周详,曲尽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使诗歌的叙事功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诗歌的叙事说理、谈性论道开辟了途径,使得唐诗通俗化有了长足的进展,并在极盛难继之盛唐诗歌之后,别创一新局面,乃对于盛唐情韵浑融之诗境的反动;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则强化了诗歌的散文化倾向,同时也相对削弱了诗歌的抒情性和形象性。赋之再发现,其影响所及,遂开宋人诗风之先声。
[收稿日期]2005—12—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3BZW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