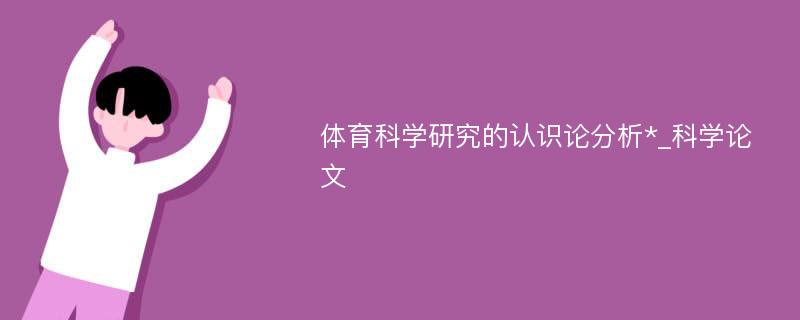
体育科学研究认识论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探析论文,科学研究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体育科技成果的获得及其对体育发展作用的大小与科研方法的选择、运用密切相关。认真检阅我国的体育科研成果,不难发现:有的论文貌似宏观,内容涉及体育路线、思想和方针政策,但觉失之笼统,缺少耐心细致、冷静求证的科学分析而擅作主观定性肯定或否定;有的论文貌似精细,仪器检验、数理统计兼备,推敲之下,又感与解决体育工作实际问题的期望相距甚远。体育科研应该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逻辑思辩与数理统计相结合,但哪些研究需要运用思辩、定性方法,哪些需要运用数理定量方法,或者多种方法相结合运用,很值得研究。必须看到,在大科学中体育科学只是一个较小分支,科研人员少,经费不足,知识更新相对较慢,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应注意防止以固有的、其中甚至有一些已落后的知识去研究体育问题,以固化的思维方式认识、观察体育现象,从而影响体育的发展。
关于体育科研仪器的悖论。几百年来,科研人员甚至包括许多哲学家已经习惯把仪器看成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延伸。例如,有了望远镜,伽利略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有了显微镜胡克看见植物有细胞。这些仪器的作用是辅助人类自然感觉能力(如目力)的不足,即把眼睛的能力直接扩大。体育科研领域盼望着科学家们带着更加精密的仪器来到运动现场。的确,科学研究仪器的更新使生物学研究进入分子水平,使物理学研究向基本粒子(微观)领域挺进。前美国奥委会运动医学委员会主席达迪克(Dardik)说:“一旦把运动与科学结合起来,就会取得成就。”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发展对体育科学的研究工作,特别是竞技技术的科学研究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因如此,我们要对这些学科(特别是物理学)的研究进展状况有大概的了解,否则,体育科学研究的进展将受到影响。由于体育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还要受到他本身认识和思考方式的影响。因此,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进行一些反思也是必要的。
20世纪量子力学观测仪器问题的出现,给传统认识论方法提出了挑战。原子科学所用的仪器不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延伸,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超越。观测仪器在此的作用不是直接扩大可知觉的世界,而是间接展现不可直接感知的世界,其作用与望远镜和显微镜相比并不仅是微小与宏大的问题,而是本质上的区别,这种由本质差别所引起的问题,不能够通过改进仪器(如复杂化、精密化)的方式来解决。如果说直接观测仪器仍然受传统认识论的局限,那么,用于原子科学(微观世界)研究的间接观测仪器却不得不超越传统认识论。间接观测仪器的诞生使科研人员、仪器和微观世界之间出现了新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就带来了传统认识论所未遇到的新问题。其实,即使是在使用传统观测仪器的体育科学研究中也出现了间接观测的问题。以运动选材为例,人们采用体重计来称量体重就是一种间接观测。轻重本来是皮肤和肌肉的感觉,但却以人眼可观察到的刻度来表示;再如,确定骨龄的X光照射。尽管X光本身至今仍是一种不可见的神秘射线,我们却相信由它所产生的某种效应(如由X光片所显示的人体器官和骨骼的形态特性)。 好在拍摄目的是为了观测运动员的器官和骨骼之类的宏观对象。但是,对于从事原子科学研究来说,X光射线的不可复原问题就成了重大障碍。 这种不可复原的信号转化说明基本粒子永远看不见、摸不着、嗅不到。体育科学研究达到今天这个水平,与我们体育科研人员对物理学、生物学成果的借鉴是分不开的。科研仪器的“共有性”和科研成果的“信息共享”还会使体育科研人员继续从相关学科的发展中吸取大量营养,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当我们冷静地从哲学认识论视角出发去考虑一些问题时,对传统宏观认识论的某些观点以及对由这种认识论出发而去类推微观世界的某些做法进行反思,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否则,当体育科学研究在“借鉴惯性”的推动下而撞墙的时候,就不仅仅是一个是否死心的问题了。因为,“借鉴惯性”极有可能封杀体育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和反思能力。量子力学间接观测仪器的出现,致使我们必须对仪器的某些悖论进行认识论上的反思:(1)仪器性质的悖论。 科研仪器是观测工具还是观测对象?如果把仪器当作观测工具,那么,我们却只能观测仪器中展示的图像而无法观测原子(微观)事件本身;如果把仪器当作观测对象原子的地位又被消掉。(2)仪器地位的悖论。 在科研人员(主体)和研究对象(客体)之间,仪器属于哪一方面:如果是作为主体的一部分(如传统认识论所认为的“人体感觉器官的延伸”)那么,科研人员其实也在观测着仪器;如果是作为客体一方,那么仪器本身就不是观测工具。(3)科研仪器作用的悖论。 仪器作用于微观粒子是否意味着科研人员的主观介入?如果不是,我们就解释不清科研人员对被观测对象的巨大干扰的原因,也不能说观察者是在有目的地使用观测仪器;如果是,被观测对象(如粒子)的客观实在性就讲不清楚。
微观不只是一个“细小”的问题。以当代物理学为先锋的科学研究进入微观(基本粒子)领域之后,一些传统的认识论观念与新领域的研究成果格格不入。微观物体无非是小一些,它们在本质上是宏观物体的缩影。于是,一种普遍的“宏观类推”式的思维模式深深嵌入科研人员(包括体育科研人员)的观念中。许多科学家设想,永久粒子(牛顿式的)和沙粒相比无非是极微极小和无比坚硬而已。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利用宏观经验的外推来想象微观世界的做法。既然微观世界仅仅是宏观世界的缩影,那就的确没有必要让哲学家去建立不同的认识论体系。外部世界的许多信号是人类的感官所不能直接感受的,它起因于信号本身的质与量的特征。科学研究观测仪器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服务的。信号量的大小可求助于信号扩大,例如:运动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使用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其作用主要表现为信号扩大。而解决信号的质的问题需要的是信号转化,例如:看不见的X 射线照在荧光屏上产生暗绿色的可见光,或者照在感光底片上,使银盐分解成为黑色化合物(此时,研究人员通过某种可见的效应来感知X射线的存在的)。 观察基本粒子的主要方法是信号转化而不是信号扩大。体育科研人员的一个常识是:微就是微小,微生物就小生物。观察微生物只需依靠信号扩大,现代科学却证明,到了一定的空间尺度(在微观尺度方面,迄今为止,科学家的观测可达10[-13]厘米的水平), 微就不仅是量的大小问题,而且还涉及质的差别问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许多量的单位都是人类自行制定的,而量子引进各门学科后,传统的量的观念,传统的量和质的关系,都会在根本上发生变化。
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生质变,这是经典哲学的一条认识论原理。但在微观领域里,这条原理却不灵。中国现代哲学家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一书中以雷锋塔倒塌为例来形象地说明由量变的积累所引起的质变。雷锋塔与白蛇娘娘的故事相牵连。作为镇邪之用,常有人偷拆砖块拿回家。当砖一块又一块被偷走时,塔还是塔,并未发生质变。经历了几百年,积累了一定数量,塔身无法支撑时,才突然哗啦一声倒塌。金观涛等在“质变方式新探讨”这篇文章中,对艾思奇的这种突变事例作了补充。金认为量变引起质变不一定非经过“哗啦一下”这一突变过程,假如人们从塔顶开始从上到下地偷砖,就不会有突变。其实,早在两千年前,古希腊人就已经以堆谷为例探讨过金观涛式的质变方式。然而,微观领域的质变方式却是真正的新探讨。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命题“数是万物的本源”意味着“数的本质就是万物的本源”。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都重视数在构成万物中的作用和地位,但俩人的观点却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把数看成是万物的本源;后者把数看成是万物的关系。在古希腊还没有澄清这两种不同看法的迫切需要。到了20世纪,情况就不同了。古代许多部落把某些物件作为图腾;在现代科研工作中有人把数学符号作为图腾。语言和数学符号都是人类创造的,数学符号何以能在语言束手无策的微观领域逞能?揭露数的神秘性的一个好办法是归真返璞。华罗庚在“数学的用场与发展”一文中有段很通俗的话:“数是各种各样不同量的共性,必须通过它才能说明量的变化。……凡是要研究量、量的关系、量的变化、量的关系的变化、量的变化的关系的时候就少不了数学。”微观现象是转化为宏观现象之后呈现在人类面前的。这样的(信号)转化把原子世界原来的图景完全改造了。原子世界的图景本身具有超越直观感觉的特性,所以人们难以使用日常语言进行描述。但是,微观世界各种现象之间的量的关系可以从宏观效应中间接反映出来(核弹的制成就是一个证明)。对数来说,有这样的信息就有了“英雄用武之地”。剩下来的问题就是科学家们寻求合适的方程,以便通过量的关系获得明确结果。
数并不是有什么神秘的性质,仅仅是由于人类的其它认识手段在微观领域受困时,数凭其特点可扬其所长罢了。语言有语言的魅力,数有数的特长。一个人吃了没有成熟的葡萄,只需一个词“酸”就可以描述了,然而任何复杂的数学方程对于描述此种感受不仅没必要而且不可能。在描述人类复杂的情感动机、价值观念等方面,数学是很难描述的。众所周知,自然科学在接受自然检验时所用的工具主要是数学,那么,数学要不要接受自然检验呢?如果需要又是以什么为工具呢?数学家高斯为了检验三角形的各内角之和等于180°, 曾对三个山头构成的三角形进行大地测量,但并没有获得决定性的结论,其原因是高斯的测量仍未摆脱欧几里德几何的羁绊。爱因斯坦发现,欧几里德几何的基本概念(点、直线、线段等等)与现代物理学经验格格不入,这是使他在建立相对论的过程中采用非欧几何的重要原因。可见,数学也是要接受自然检验的,其方法不是通过个别实验的裁决,而是和人类日益发展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然观相对照。在原子科学中数学越来越抽象,但一个关键问题是:量子论中数学公式不能总是去描写我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而是要描写自然本身。因为如果把自然界本身和人类自然界的知识完全等同起来,即使在宏观领域也是不正确的。
当代体育科学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强调定量化,强调以数表示的精确性,但是,体育科研人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数非万能,数的用途和范围是有限制的。血乳酸浓度以及无氧阈值的计算自然可以向精确化发展,而复杂的战术思维,变化着的体育价值观念,错综的运动情感等等并非是数称雄的地方。体育科研人员还必须认识到,许多体育科研成果之所以不实用,原因之一是我们常过分注重于对人类关于体育运动规律的认识的描述,而忽略了体育运动规律本身。长此以往我们的许多貌似精确的科研成果都有可能成为“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体育科研的一般状况表明,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偏重于宏观的逻辑思辩,体育自然科学研究偏重于微观的实验与数理分析,这是学科的性质所决定。但因此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要注意防止过于偏重某一类研究方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应适当注意数理统计方法的运用,防止以讨论、结论代替必要的调查统计;体育自然科学研究应适当注意逻辑思辩方法的运用,防止以调查实验结果代替分析、讨论和结论。
注释:
* 国家教委优秀年轻教师基金资助课题。
1997—0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