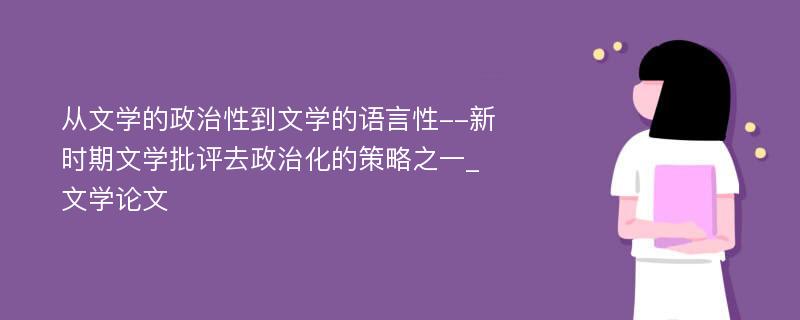
从文学的政治性到文学的语言性——新时期文学批评去政治化策略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政治性论文,文学论文,新时期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1)04-0002-07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力争摆脱“文革”时期阶级分析和政治批判的批评模式,探索更为宽广的批评空间。其中的途径之一就是从“语言转向”来探索文学的形式美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始摆脱“政治标准第一”,逐渐认可“艺术标准”;将批评焦点落实在文学语言上,但仍然将文学语言作为文学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将语言视为文学的本体,转向语言本体论的语言审美批评。这一批评上的“语言转向”,其实也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去政治诉求,从而完成了从文学的政治性到文学的语言性的根本转变。
一、从政治标准向艺术标准的转变(1977-1979)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语言转向”正式启动于1985年左右,从外在原因来看,得益于西方语言学批评的引进,但从内部原因来看,新时期文学批评从政治批评转向语言批评有其合理的内在趋向。从“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检索1977年的文章,可以发现为数不多的文学批评类文章在分析时仍以阶级立场为基础,执行的是“政治标准第一”甚至“唯一”的批评原则。如王阳松指出:“我们评价一部作品的好坏,首先要看作者站在什么立场上,以什么思想作指导来反映什么样的生活。茅盾的《白杨礼赞》之所以思想性高,艺术性强,是因为作者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歌颂了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华北人民。”作者认为《白杨礼赞》“是一篇战斗性强烈的抒情散文”。[1]田绘蓝在评价茅盾的《子夜》时认为:“分析任何一部作品,都应该首先弄清楚它的历史背景,才能确定它的阶级实质和它所代表的路线实质,从而才能给它以正确的评价。”[2]不仅如此,文中还有很多地方引用毛泽东语录,并用黑体标识。贾佑吉认为:“贺敬之同志的《西去列车的窗口》是一首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激情的时代精神的颂歌,它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时代永葆青春的老干部和朝气蓬勃的一代新人。”[3]查国华、蒋心焕认为鲁迅的《朝花夕拾》“尽管它以回忆作为素材的,但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立足于现实战斗的需要,以战斗为目的,这就是《朝花夕拾》的基本特色。”[4]在这些文章中,“时代性、阶级性、革命性、战斗性”是最为突出的字眼,是文学批评的标准。
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打破“两个凡是”,执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带来的不仅是社会经济领域的变革,更是思想观念的变革。对比1977年和1978年的文学批评,可以发现批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1977年的文学批评中很难看到以“艺术”作为篇名的关键词,即使在文章中涉及“艺术”方面的内容也大都放在文章的末尾或者几笔轻轻带过,而1978年的文学批评中以“艺术特色”、“艺术风格”、“艺术形式”、“艺术结构”等作为篇名的文章开始涌现,如辛宇的《要按艺术规律办事》(《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谭绍凯的《高尔基〈母亲〉的艺术特色》(《贵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阎纲的《〈创业史〉艺术谈——在“对立”中刻画人物》(《上海文学》1978年第7期)、郭在贻的《试论李贺诗的语言艺术》(《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李朝正的《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特色》(《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杨建文的《诗歌的艺术形式与小说的人物塑造——〈李自成〉的民族风格管窥》(《湖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等等。虽然这些对作品艺术特色的分析多是泛泛而谈,还很简单和粗糙,有些还是从语文教学的角度出发的,但它们的出现至少表明政治意识形态开始松动,原先“政治标准第一”的批评准则开始向“艺术标准”转换。
1978年文学批评从政治意识形态分析向艺术特色分析的转变不仅有赖于思想解放运动,而且还得益于“为文艺正名”的大讨论。《戏剧艺术》于1979年1月在显要位置发表了陈恭敏的文章《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提出质疑。不久,《上海文学》在1979年第4期发表了“本刊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旗帜鲜明地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进行驳斥,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口号歪曲了文艺的定义和全部本质,从根本上取消了文学艺术的特征;狭隘地理解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忽视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把文艺变成单纯的政治传声筒,“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文艺观”。在作者看来,文艺的功能应该在真善美的统一中来理解,文艺的政治作用虽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文艺还有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可见,作者之所以要为文艺正名,就是因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口号将文艺与政治等同起来,忽视了文艺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殊性。
鉴于有反驳者,从1979年到1980年,《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山东文学》等刊物为此开展过专题讨论,检索“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1979-1980)”,仅以“文艺与政治”、“文学和政治”作为篇名的文章就达50多篇。这场讨论从“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文艺是否为政治服务”等问题逐渐深入到“文艺是否属于上层建筑”、文艺的本质以及如何理解“政治”的含义等问题。在讨论中,由于争辩双方对“政治”这一概念的理解差异很大,“所以当时的讨论真如‘盲人摸象’,交集点很少,当然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5]因此,如何正确理解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成为“第四次文代会”的中心问题,成为能否召开好这次会议的关键。在广泛征求意见、几易其稿后,周扬在报告中指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并明确指出:“政治不能代替艺术。政治不等于艺术。”[6]307报告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在其表述中实际上已经纠正了“从属说”和“服务说”,对两者的关系作了重新界定。这一界定与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的提法相呼应,邓小平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半年之后,邓小平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中再次强调:“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作为回应,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口号取代了过去的“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至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终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场波及甚广的大讨论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舍弃了两个不科学的口号,还在于它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使文学创作观、文学批评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场讨论解除了文学和政治之间长达几十年的绑定关系,把文学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战车上拉了下来,使文学获得了禁锢已久的自由。在文学批评领域,政治标准占主导的局面逐渐改观,艺术标准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两者由过去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主次关系逐渐转变为平分秋色的平等关系。批评方式也由过去的“内容(主)+形式(次)”这种机械的、生硬的叠加模式逐渐转变为两者相互融合的模式,使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
但另一场发生在语言学研究内部的讨论,则非常智慧地将上述为文艺正名,转变成了为语言正名,重新思考语言的本质问题,对“语言的阶级性”及“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观点提出质疑,成为文学批评最终能够出现语言批评的内应力。徐荣强率先批判了“文革”时期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语言的错误做法,主张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来指导语言研究;并认为应该借鉴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观念建立符号语言学体系。[7]对“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批判得最为彻底的是李行健,他认为新时期虽然某些报刊已经痛击“语言具有阶级性”的谬论,但力度和深度还不够,还未触及“语言具有阶级性”这一谬论的基础——即“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因为“阶级斗争工具论”是“语言无阶级性”到“语言有阶级性”的桥梁,因此需要对“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进行彻底清理,以正本清源。[8]文章从阶级斗争的工具的特点和语言自身的特点两大方面论证了语言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交际的工具,社会性、全民性才是语言的本质属性。虽然将“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还原为“语言是人类交际和思维的工具”,并没有改变语言的工具属性,但对新时期的语言学研究和文学研究来说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它从根本上斩断了阶级分析对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干预和钳制,使两者获得了学科的独立和自由。
通过为文艺正名,再到为语言正名,既蕴含了强化形式批评的可能性,也蕴含了建构语言批评的可能性,为将文学语言分析作为批评的基本任务之一,提供了理论的空间与依据。此后,随着对于文学语言理解的深化,又经历了由工具论语言观向本体论语言观的转变,摆脱了文学政治性的干扰,确立了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
二、以工具论语言观为基础的语言批评(1980-1984)
从1979年开始,分析作家作品的语言特色、语言艺术、语言风格成为一大特征。检索“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1979-1984)”,以“语言艺术”、“语言特色”、“语言分析”、“语言风格”作为篇名的文章就达190篇(这里仅以篇名统计,有些文章虽没有以这些关键词作为篇名,但内容也涉及语言特色,这样的文章也很多)。细察这些文章,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第一,重视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在新时期以前的文学批评中,语言问题难以获得重视。正如滕云所言:“尽管人们惯于援引高尔基的说法‘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但在文学研究、批评文章和文学史专著中,这个‘文学的第一要素’却往往只能排到附于作家作品研究骥尾的地位。真的,我们对作家作品的文学语言的研究,与文学语言在作家、作品艺术生命中所占有的特殊重要地位颇不相称。”[9]至1980年代初,这一局面有所改观,文学批评在分析作家作品时大多注意到了语言特色和成就。如孙宜君认为:“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之所以赢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赞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要的位置,与它的语言成就是分不开的。”[10]李保均认为:“研究一部作品的文学语言,是研究作家的艺术风格和该作品的艺术性的一个重要方面。”[11]庄森认为:“茅盾是中国现代一位伟大的语言艺术大师,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这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理应得到重视和研究。”[12]郑春元认为:“《聊斋》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珍品,在语言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13]
第二,重视文学语言的特点。文学语言不同于科学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它是对日常生活语言的提炼和加工,因此具有自身的特点。在1980年代初的文学批评中专门探讨文学语言特点的文章并不多,大多数是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语言特色的分析来展示文学语言的特别之处。如孙宜君认为《骆驼祥子》的语言具有四大特色:一是通俗、明白、新鲜、活泼、口语化;二是遣词造句严格,用字精当传神;三是平易、幽默、轻松、诙谐;四是人物语言个性鲜明独特。[10]熊宪光认为《战国策》的语言有三个特色:生动形象、敷张扬厉、明畅通俗。[14]李保均认为:“《红旗谱》在语言艺术方面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它的人物语言极富个性色彩。”[11]庄森认为茅盾小说的描写语言生动形象、富含感情色彩,叙述语言冷静中透射着鲜明的褒贬感情,人物语言高度个性化。[12]综合这些观点,可以看出文学语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生动形象,(2)准确传神,(3)简洁凝练,(4)通俗畅达,等。这些特征较少涉及文学语言本身的形式美,主要还是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的,将文学语言作为叙事写人、写景状物、传情达意的工具。虽然有的评论者认为文学语言具有形式美,但语言形式的美必须要服从于思想内容的真。如王畅认为文学语言是艺术的语言,美的语言,是一种形式的美,“但这种形式的美必须服从于内容的真,只有当形式的美与内容的真有机结合起来,成为统一体的时候,这种形式美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才具有艺术美”[15]。这里依据的基本理论是形式为内容服务,这与当时文论界对文学语言功能的界定是一致的。
第三,重视文学语言的功能。高尔基曾指出:“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象和思维过程。”[16]294这段话在新时期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分析中被援引的频率相当高。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文学语言的功能有描写功能、塑造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功能、反映现实的功能、传情达意的功能等。在这些功能中,文学语言是被动的,它必须根据人物、情节、环境以及作品思想情感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表面上文学语言与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完美契合,实际上两者仍有主从之分,即思想内容的变化决定语言形式的变化。正如涂一程在论述《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时所说的那样:“一定的语言是为一定的内容服务的,《红楼梦》高度的语言艺术,只是作者赖以表达其政治主题的手段和工具。”[17]但既然突出了文学的语言功能,用之于批评实践,也能强化对语言作用的认识,从而丰富对作品的理解与欣赏。如薛瑞生在分析《红楼梦》中的人物对话时就通过引用语言功能深化了对作品的认识,“《红楼梦》中的人物对话,不仅具有刻画人物的功能,而且具有叙述功能,揭示主题的功能,概括人物性格的功能,等等”。“人物语言的多功能表现,这是曹雪芹对小说语言的突破。文学上的创新,总是自由与规律的结合。原先那种只用人物语言表现人物性格的作法,显然束缚了生活,也影响了作家更加灵活地结构作品。”[18]
整体地看,1980年代初的文学语言分析并没有向美学和文艺学延伸,基本上还是在语言学领域内打转,这从上面对文学语言特征和功能的分析不难看出。对此,傅继馥曾有所反思,他说:“怎样分析文学作品的语言才比较科学呢?用对非文学语言的要求作为评论文学语言的标准,会忽略后者的特点;把语言的形式和它所反映的内容混淆在一起,又会忽略语言作为艺术形式的特点;单纯罗列一些形容词,会缺少内在联系,而再任意摘引一些例句,又缺少代表性。这样恐怕很难获得科学的认识。”[1 9]因此,他试图从遣词造句、感情色彩、意趣、形象描写的特点来探索《儒林外史》语言艺术的风格。傅继馥提出的问题很有价值,但他并没有提出一种新的方法,这说明1980年代初的语言批评,只能处于这样的一个过渡地带,只有等到新的理论引进,并且受到创作界的巨大挑战,才有可能发生从理论到实践的变革要求,指向一种本体论的语言批评。所以,1980年代初期出现的对于文学语言的审美分析,如许卫强调语言的相对独立性,“在文学作品中,语言应当与其他构成因素相得益彰,但并不是说,语言只是被动地适应,在更多的时候,它是积极地参与着整体构思的实现。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语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20],就代表了这种征象,但整体局面的改观要到1985年以后。
三、以本体论语言观为基础的语言批评(1985-1990)
“语言本体论”包含三层意思:语言是人类的本体;语言是世界的本体;语言是文学的本体。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维特根斯坦认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俄国形式主义学派认为:“文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21]102。而“文学性”就是文学的语言形式。结构主义批评用“文本”取代“作品”,使“文本”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它是语词的编织物,与作者无关。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将语言形式奉为文学的本体,并对其进行精细的科学化分析,这是以本体论语言观为基础的语言批评。这种文学语言观和批评观在1980年代中期引入中国,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与文论发展。
1985年,以刘索拉“黑色幽默”小说《你别无选择》为代表的一批小说因在语言方式上极具创新力而吸引了文坛的关注,马原、王安忆、莫言、徐星、韩少功、残雪等作家脱颖而出,他们的小说以形式的创新和语言的怪诞为文学创作开启了崭新的空间。1987年以后创作界“第三代小说家正在进行一场语言的战争”[22],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以更加反叛的姿态痴迷于小说叙述方式的革新;以于坚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也打出了“诗到语言止”的旗号。作家们不仅在文学创作时醉心于语言的创新实验,而且也从理论上阐发他们对语言的理解。张承志指出:“叙述语言连同整篇小说的思想、结构,应该是一个美的叙述。小说应当是一首音乐。小说应当是一幅画。小说应当是一首诗。而全部的感受、目的、结构、音乐和图画,全部诗都要依仗语言的叙述来表达和表现。”[23]27何立伟同样赋予语言以显要地位:“一个作者或读者,若完全属于审美型的,于他的第一要义,我想应该是语言,一部作品失去了语言的魅力,则正如同一朵花失去了清香,它的审美价值就真正是值得怀疑了。”[24]39汪曾祺的一段剖白很能说明当时创作界对语言的重视以及语言观念的转变,他说:“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25]1-2从上述创作感言中可以看出,作家所秉持的已经是本体论的语言观,其表现在:一、语言不再是表达思想内容的工具,语言是文学的本体,本身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二、语言与内容是融为一体的,不可分割,两者不存在主次之分,先后之别;三、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从而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内容决定一切”的创作观。
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也将焦点对准语言,形成了一股强劲的语言热潮,首先从关注文学语言开始,继而扩展到文体、结构及叙事方面。与创作界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相呼应,理论批评界也在“语言——小说的一切”[26]的启示下“由语言而悟小说”[27]。1985年,黄子平率先对传统理论命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进行重新审读,对“得意忘言”式的文学批评进行批判。他指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却是忘却语言的艺术。语言被当作文学创作的‘副产品’放到‘最后’来说,更多的时候连这‘最后’也没有。”黄子平认为文学评论走出内容与形式二分法窘境的出路只有一条:“即在于对作品语言作透彻的、有机的结构分析。”“把诗(文学作品)看作自足的符号体系。诗的审美价值是以其自身的语言结构来实现的。”基于此,黄子平倡导建立“文学语言学”,“不仅研究‘语言的文学性’,更注重研究‘文学的语言性’”[28](着重号为原文所有)。紧随其后,吴方从文体学的角度阐述了文学语言的意义,传达出相同的意向,即“文体——文学语言本身也不再仅仅具有修辞意义,它成为艺术生命的活力源泉之一”,并预言“文学语言学的研究将日益受到重视”[29]。对于文学语言的本体价值,李劼曾指出:“如果人们能够承认文学作品如同人一样是一个自我生成的自足体的话,那么我就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这种生成在其本质上是文学语言的生成,或者说,所谓文学,在其本体意义上,首先是文学语言的创作,然后才可能带来其他别的什么。由于文学语言之于文学的这种本质性,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换言之,“文学形式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而在作品中产生了自身的本体意味”[30]。可见,李劼把语言与形式看成是二而一的东西,形式是内容化了的形式,内容消失或融合在形式之中,与形式水乳交融在一起,这是语言形式本体论的要旨所在。
以本体论语言观为基础的语言批评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关注文学语言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如程德培探索语言背后的深层内涵,认为在何立伟、贾平凹、阿城等作家那里,“语言不仅只是一种表达的‘符号’”,“而且还是结合着个人乃至地区、民族历史及其思维方式的”[31]。周源发现,在工具论语言观下,文学批评“对文学语言政治寓属功能的强调致使作家的语言追求被限制在对文件、政策以及领袖著作的阐释上,而放逐了作家主观情思对语言的灌注和加工”,而“1985年以后的小说语言革命首先是一种文本语言的体验性密集。无论是刘索拉的荒谬嬉戏,还是残雪的意象重叠与抽象再现,无论是孙甘露的似梦非梦及语言隔阂,还是莫言感觉分解与复合,都实际地表现为作者对语言的主观加工,意在通过语句、语段参差错落的排列达到与人类生命的同构效应。他们淡忘了语言的普遍原则和规律,凸现着的正是语言符号对于人类本体生存的意味。”而寻根派作家的语言追求则“致力于通过语言来破译文化密码”[32]。这里揭示的是语言与人类生存以及人类文化之间的共生关系,突破了语言单纯作为表达工具的符号性。
其二,探索文学语言的多功能性。文学语言不再只是单纯的表现工具,而具有其他的功能。在唐跃、谭学纯看来,文学语言不是载体而是本体,具有表现性价值,但这种表现价值与传统的“表现工具”有本质区别。他们认为:“就‘表现工具’这个偏正词组而言,由于中心词‘工具’的机械意义,修饰语‘表现’便失去活力,呈现为中心词和修饰语在内涵上不相容的尴尬局面。语言是‘工具’,表明它是具有载体性质的实用传达手段,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只是具体言语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固定对应关系。而‘表现’意在强调语言的本体价值的表现效果,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则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语言的丰富属性。”[33]正如日本符号学家池上嘉彦所说:“实用功能,认为语言作为‘手段’只有对某种目的起作用时才有其价值,而‘美学功能,是从语言本身所固有的价值角度来理解的。”[34]11除了表现功能外,谭学纯、唐跃认为文学语言还具有呈现和发现功能,这是因为文学创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以文学语言论,它在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同的用途,也就理所当然地具有不同的功能。在作者的创作阶段,文学语言被用来表现作者的意图,因之具有表现功能;在文本的实现阶段,文学语言被用来呈现文本的意义,因之具有呈现功能;在读者的接受阶段,文学语言被用来发现读者的意味,因之具有发现功能。”[33]文学语言参与了文学创作活动的全过程。
此外,在工具论意义上,文学语言主要的功能是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但在本体论意义上,文学语言本身就具有造型功能。夏中义认为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分界线在于它具有语象造型功能。“语言作为传达媒介只有在文本结构中才能获得其美学生命,这一美学生命集中体现在它的语象造型功能上。”[35]正是这一功能将文学的虚构世界与日常的现实世界区分开来,使文学进入了自由的审美天地,而摆脱了日常语言的现实指称性。就诗歌来说,其语言造型主要有两种:一是以象形图形直接表意,即把文字和诗行排列成某种图案或形状来表达某种意义,图案或形状与所要表达的意义相吻合。如周振中的《英雄纪念碑》把诗句“一尊巨大的磨刀石砥砺着民族的意志”造型为纪念碑形状,给人强烈鲜明的视觉效果,使诗的形式与诗的内容融为一体。二是通过意象组合来表达意义。在组合策略上,可以通过并置式组合、重叠式组合、承接式组合以及向心式组合等方式来获得。[36]182-197不同的组合方式虽然带来的诗意效果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诗歌的语义。
其三,更新文学语言的研究方法。在本体论视域下,文学语言的研究方法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其中语言学与文艺美学的结合最为突出,它既突破了语言学方法,同时又以语言分析为基础,但又不止于语言学,而向文艺美学层面提升,关注语言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正如谭学纯所说:“我所理解的小说语言研究,起点在语言,但落点不能仍然在语言,小说语言研究与纯语言学的语言研究毕竟不同,后者的研究对象在语言自身,前者的研究对象从语言向小说文本延伸,向作家的精神世界延伸。小说语言研究,存在着本自语言学,又超出语言学的双重阐释空间。”“只做语言分析的文学语言研究关注的是一般的修辞技巧,把语言分析纳入文本框架和作家的精神世界,是超越技巧论的修辞诗学。”[37]修辞诗学就是研究作家的修辞行为如何转化为修辞文本的语符化过程。很明显,谭学纯的小说语言观超越了传统语言学意义上的“工具论”而走向了“诗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将语言分析与审美分析结合在一起。
在1980年代中期的文学批评中,文学文体学就是以其对文学语言的审美性研究而引人注目的。如章少泉指出文艺文体学就是从语言学和文艺学结合的角度来研究文学。[38]徐剑艺认为一般语言学是寻找语言本身的规律,而文体学对文学文本语言形式的研究是为了非语言性——“文学性”的表达规律。[39]这里所说的“文学性”其实就是“审美性”。郜元宝也认为:“小说文体学,如果简单定义为对小说文本的语言学研究,那它只是为了语言学的目的,把小说文本当作语言事实着手的一项语用学研究。实际上,我们研究小说文体,是因为我们总想借助语言学的手段解释、探求一些别的东西。”[40]在郜元宝看来,这些“别的东西”就是作品的审美意蕴。徐岱将普通文体学与文艺文体学作比较后,发现“文艺文体学的对象是文学活动中的各种功能性言语事实”,它的研究方法来自语言学,但并不以语言分析为自身目的,而是由此而进,“通过语言学所提供的方法论来深入地探究文学作品的文本的奥秘”[41],揭示其审美特性。这些都说明,文体学的语言研究必须要以语言学做后盾,与语言学结盟,但又不能停留在语言学的层面上,还必须向文艺美学和文化哲学等方面拓展与提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进入文学语言学批评的殿堂。
由上可见,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语言批评,开始关注语言自身的审美价值,文学语言不再是传情达意的工具,而具有表现功能、呈现功能、发现功能、造型功能、文化功能以及审美功能等,语言分析与审美文化分析有机结合在一起。至此,文学批评才完全摆脱了“文革”时期的政治功利和新时期初的社会功利,突破了以工具论语言观为基础的语言分析,走向以本体论语言观为基础的语言审美批评,完成了从文学的政治性向文学的语言性的艰难转变。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本体论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人物分析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