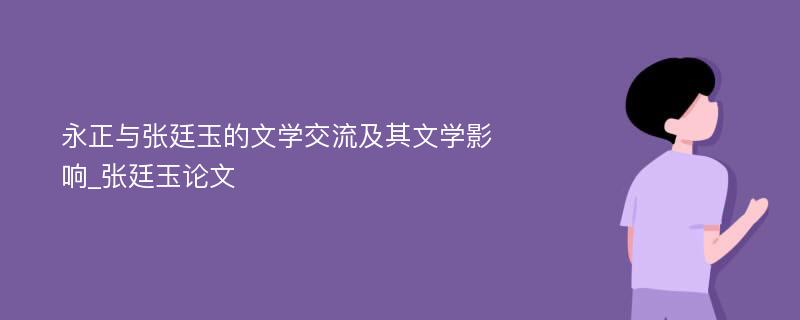
雍正与张廷玉之文笔交往及其文学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雍正论文,文笔论文,张廷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535(2013)-055-05
清代雍正皇帝作为“朝乾夕惕”的君主,能够善用文臣,为奠定本朝官方正统文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雍正本人著有《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三十卷,并撰写了大量的朱批谕旨,这其中有不少与臣工进行文笔交往的资料。张廷玉,字衡臣,又号澄怀主人,为雍正朝重臣,曾在本朝任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文渊阁大学士等职。过去,从史学的角度对两人的关系与影响已有不少论述,但从文学的角度加以考察还鲜有人涉足。本文拟从这一新的角度出发,以时间为序,对两人之间的文笔交往进行考述,从而考察两人的特殊关系,并探讨他们以特殊的身份对代表朝廷的正统文风所产生的影响。所谓“文笔”即文章的泛指,而所谓“交往”有直接的交往,也包括一些间接的交往。
一、雍正赐张廷玉诗文
雍正与张廷玉的文笔交往可追溯到雍正元年(1723)八月初九。雍正帝赐张廷玉翰林院掌院学士,张廷玉以“谫陋不能称职辞”[1](p2)。雍正曰:“汝学问优长,器量雅重,克堪斯任,何以辞焉?”张廷玉奉旨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并充日讲起居注官。初十,雍正御制诗一章,并亲自将诗书写于宫扇之上,颁赐张廷玉。诗云:
峻望三台近,崇班八座尊。
栋梁才不忝,葵霍志常存。
大政资经画,訏谟待讨论。
还期作霖雨,为国沛殊恩。[2]
首联称张廷玉的地位可以接近三公,崇高的身份可与六都尚书一样尊贵,明确指出了自己对张廷玉的信任,要重用他。颔联继续夸赞对方不愧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并且有忠贞不渝的志向。颈联、尾联提出希望,国家的大政等待贤良之臣谋划、讨论,期待他能像甘霖一样使国家得到充沛的滋润,受到恩泽。诗中饱含着对臣子的信任,希望对方能够不负众望,为国效力,不必推辞。此诗写于张廷玉推辞任职之时,殷切之情可见一斑。诗末书“御笔赐尚书张廷玉”八字。张廷玉“拜捧天章,知圣心之期望臣厚矣,感激愧悚,不知所云”[1](p2)。这是雍正赐予张廷玉的唯一一首诗歌。
当年十月二十日,雍正又恩赐御书“世笃纯勤”四大字匾额与张廷玉。以后,雍正赐给张廷玉的文字主要为匾额题词和对联。如雍正六年(1728)六月,御书十体字墨迹赐张廷玉,“文採十条,书备各体。尧章羲画,神运天成。直如化工元气,絪缊融结,而莫能状其妙”[1](卷十);七年,因张廷玉旧居“湫隘”,特赐第宅一区,在西安门外,并赐白金千金,为迁移之费。移居之日,御书“调梅良弼”四大字,遣内侍捧赐,又赐肴馔、饼饵等食物。九年(1731)正月二十五日,御书“赞猷朔辅”四大字,命内廷良工制龙匾以赐。赐御书“不染心”、“含清晖”两块匾额,又赐对联曰“绿荷池畔吟新句,翠竹林中披异书。”仔细考察这些匾额、题字,除十体墨迹具体内容暂无从考证外,其余几处都颇见雍正之良苦用心。“世笃纯勤”即一辈子都笃行纯正勤勉的言行,这一方面是对张廷玉的褒奖,另一方也是对他的鞭策。七年之后所赐“调梅良弼”也多含褒扬之意,其中“调梅”指宰相的职务,“良弼”即好的官吏,称赞张廷玉是调鼎中之味,使国家机构运转协调的辅弼大臣。“赞猷朔辅”中“赞”当为辅佐,“猷”为计谋、计策,此四字意为国君左右出谋划策的良臣。颇为巧合的是“世笃纯勤”与“赞猷朔辅”对仗很是工整,虽为不同时期的赐匾,亦可置于一处。“不染心”与“含清晖”与对联“绿荷池畔吟新句,翠竹林中披异书”形成对应关系,前者既指荷花的清新高洁,又暗喻张廷玉品行高尚,不染尘埃,后者既指翠竹清影,又喻指对方如翠竹一般高洁。雍正皇帝一向以严明著称,能对臣工的品德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实属不易。
雍正赐张廷玉之诗文到张之父张英去世时达到高潮。张英,字敦复,为康熙六年进士,入翰林,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曾任《大清一统志》、《政治典训》总裁,并奉敕编《渊鉴类函》,康熙四十七年(1707)卒,雍正十一年(1732)九月,帝谕贤良祠大学士张英祭于桐城本籍,大学士张廷玉给假数月,于十月十三日启程回家,举行典礼。其子与族中在京子弟为官者均给假同行。张英已死去二十余年,为何要在这时让他的儿子回乡祭祀,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名义上是祭祀张英,实际上是赐予张廷玉殊荣。启程之日,钦选十月十三日午时,又命赐以安车良骑,并谕诏沿途文武官弁护卫送迎,赐内府书籍五十二种,令织造臣用官艘载送。雍正还“手赐玉如意一柄”,谕曰:“尔往来事事如意”[3)(卷十二)。谕祭文曰:
翊熙朝之泰运,端重良臣;稽册府之鸿猷,宜崇元祀。盖成劳懋著,生平之风概如存;斯盛烈昭垂,弈世之宠褒益笃。载申纶綍,式荐牲醪。尔张英端敬居心,冲和成性。三十载趋承禁直,讲帷之启沃弘多;四十年扬历清班,纶阁之赞襄允懋。靖共尔位,忠纯克笃夫小心;垂裕后昆,善庆弥彰夫厚德。於戏!流芬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树范严廊,允矣千秋之茂典。列豆蓬于祠宇,渥泽攸隆;布筵几于里闾,湛恩叠沛。灵其不昧,尚克歆承。[1](P42-43)
这篇祭文并没有收入《世宗先皇御制文集》,而文集中的祭文除了为和硕怡亲王所写之外,其他都不是写与他同时代的人,多半是写给“神”的。皇帝亲自为一位故去多年的前朝臣子写祭文,这恐怕是少有的。祭文开头说明了祭祀张英的原因,是因为他为“端重良臣”,为康熙朝的鸿运昌盛作出了贡献。接着赞美他曾建立伟业,功勋卓著,品行端正,性情平和。然后说他的厚德可以为后世垂范。祭文写得典雅工整,不乏溢美之词,但属于祭文通常的特点。另外还御书祠宇匾额对联。匾额曰:“忠纯诒范”,对联曰:“风度犹存,典礼焕千秋俎豆;师模如在,忠诚垂奕叶箕裘”。上下句分别指明张英对上可于“千秋”万代焕发光彩,对下可为子孙累世垂范。张英确为前朝功臣,帝子师傅,文采卓著,但死后得到如此优待恐怕更多是看在张廷玉的面子,为了笼络本朝重臣。
雍正十一年九月,张廷玉回乡行祭礼之后,向雍正上谢恩奏折,雍正阅后又御批曰:
览卿奏谢,知卿一路如意抵家,深慰朕念。吉人天佑,理所必然。朕即位十一年来,在廷近内大臣一日不曾相离者,惟卿一人,义固君臣,情同契友。今相隔月馀,未免每每思念,然于本分说话又何尝暂离寸步也。俟卿办理祭典毕,明春北来,握手欢会可也。所奏一路地方情形,欣幸览之。都中得雪两次,直省各处奏报大率相同。天恩似普,其内外事宜如卿在京光景,颇觉相安,特谕,以慰卿之系念。[1](p45)
如果说写给张英的祭文还有些夸张不实的“虚情假意”,但这段文字只可谓字字饱含情谊,字里行间所见不仅是君臣之情,更可见挚友之谊,甚至手足之情。雍正对张廷玉的顾盼、想念之情绝非矫揉做作之情。十一月二十八日,张廷玉家人赍捧御书“福”字驰回,一同捧回的还有御书对联及宝胜、绣囊、鲜果等十数种,雍正传旨曰:此赐大学士过节者,务于节前赍送到家。对联如今已不能见到,但从传送的旨意可见,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雍正的遗诏中有一段话是专门写给张廷玉的,可以看作是赐给张的最后文字:“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尊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钜。大学士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洵为不世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2](卷四)后来,张廷玉七十岁时向乾隆皇帝提出“致仕”,乾隆很不情愿,勉强答应以后,又因一些礼节方面的小事而曾经几次“威胁”说要取消他“配享太庙”的资格,但最终还是尊照雍正的遗诏实行,雍正一句“朕可保其始终不渝”,才最终保住了这位汉族大臣成为整个大清朝唯一受此殊荣之人。
以上只是雍正帝御笔钦赐张廷玉的诗文,此外还有大量谕旨、御批并未一一摘录,但雍正对张廷玉的关切已可见一斑,二人之关系正如“天恩春灏荡,文治日光华”①。虽然所赐笔墨不多,但一诗一文,一字一语,皆有所用心,发于关键,隐隐关切之情,微言大义,自在其中。
二、张廷玉纪恩、应制类作品
张廷玉自受到雍正的器重,委以重任,莫不诚惶诚恐。《壬责十一月十八日纪恩诗》当为他与雍正诗文交往之初始②。诗有序云:“上嗣位之处,特降谕旨,念臣父宣力先朝,公忠勤慎……并谕臣曰:‘此体皇考圣心也,应至梓宫前申谢。’臣闻命下,感激涕零,伏地不能起。”其诗有云:“两朝知遇超古今,载拜瑶墀泪满襟。”初次表达了自己受到重用的感激之情。当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张廷玉还写下了《蒙恩擢授礼部尚书恭纪二首》。
雍正元年(1723),张廷玉曾在四月初六写下《奉命主顺天乡试恭纪二首》、四月初八日《锁闱试士蒙恩特遣侍卫颁赐饼饵及龙井新茶恭纪三首》、五月二十一日《室庐不戒于火仰荷圣恩轸念慰谕再三敕赐第宅一区白金千两叨蒙渥泽仍获安居恭纪四首》、二十二日《奉命署左都御史事恭纪》。
最值一提的当为八月初十日,雍正令他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之位,并赐御书诗扇一柄之时,他“惊承异数,感愧并集,不知所云”[4](卷十一),写下的《恩赐御书诗扇恭纪二首》,诗云:
宝翰新承赐,殊荣昔未闻。
自天飞凤藻,入手耀龙文。
笔染三危露,身依五色云。
仁风生扇底,当暑挹清芬。
再拜聆天语,和衷愧转深。
栋梁邀帝奖,葵霍鉴臣心。
谬掌孙通礼,难为傅说霖。
君恩期许意,长奉作官箴。
第一首五律主要奉承雍正所赐诗扇文辞优美如同天飞凤藻,才华出众如耀龙文。雍正帝好祥瑞,《朱批谕旨》卷一百二十五之十二,朱批鄂尔泰奏折,载云南等地出现五色之云上报皇帝。张廷玉此处把五色云用于雍正身上,实乃投其所好。尾联感慨自己获得诗扇即沐仁风,好似酷暑当中吹来的清风。
第二首主要表达自己的谦逊之辞,羞愧难当之情。一方面感激帝王明鉴自己的“葵霍”之心,另一方面也拿自己和前代的先哲贤臣相比,表示差距很远。“孙通礼”是指汉代的叔孙通制订的礼仪,汉初悉去秦仪,群臣争功,醉或妄呼,礼仪尽失,帝忧之,叔孙通破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后人称为叔孙通礼。傅说为殷代名相,苏轼有《喜雨》诗云:“久苦赵盾日,欣逢傅说霖。”“谬掌孙通礼,难为傅说霖”为作者的谦逊之辞,说自己不了解“孙通礼”,也难以像古代的贤相傅说那样。尾联表明自己会将皇上的期许铭记在心,作为自己为官的箴言。
当年还有《八月初十奉命兼摄翰林院学士恭纪二首》、《九月初六日奉命为会试考官恭纪二首》、《九月初七日蒙恩特授户部尚书恭纪》等。十月二十日,当获赐御书“世笃纯勤”四字匾额时,他写道:“珥笔趋丹陛,挥毫锡紫宸。举头光万丈,运肘势千钧。龙凤飞天迹,云烟妙入神。捧归瞻墨宝,斗室耀星辰。”对雍正的书法赞赏有加,并非阿谀奉承之词。雍正自幼学习书法,临帖颇多,善于模仿,曾学习康熙的字体,十分相像,得到父皇嘉奖。雍正的朱批谕旨均为行楷,字迹端庄而不失飘逸流动,书法自成一格。
以上可作为张廷玉与雍正帝诗文交往的第一阶段,主要特征为初受重用,诚惶诚恐,感恩戴德,惭悚交深。
雍正二年(1723)正月十五,雍正于养心殿召王公内大臣三十六人赐食于御座前,赐东珠一颗、紫貂一张,称这些是前一年外蕃所献之贡品。事后,张廷玉有诗恭纪二首写道:“既饱天厨馔,还分内府珍。骊珠光映月,貂珥暖生春”,并称皇上之“恩谊最缠绵”[4](卷十一)。二人亦君臣亦朋友之关系显露无疑。同年七月,张廷玉在《拜大学士谢恩奏》中说:
我皇上绍登大宝,恩眷尤隆。既长仪曹,复领农部,委任信用,直如心膂股肱。训诲提撕,不啻家人父子。……叨渥泽之有加,愧寸长之莫效。今者恭承恩旨,晋陟纶扉,闻命自天,感恩无地,心神俱惕,惭悚交深。伏念政府深严,职任重大,为机务殷繁之地,处人臣极品之荣。
臣躬自知愚分,益深悚惕于兼官。唯有竭力殚心,夙夜供职,勉尽微臣赞襄之愚悃,仰答皇上高厚之鸿慈。
虽有谢恩的客套话语,但雍正“委任信用”确是实情,“职任重大”亦非虚言,“处人臣极品之荣”亦非夸大之词,历史已经做了见证。
雍正三年(1725)暮春时节,雍正召近臣十余人到御苑看牡丹。这时候,“千枝竞放,高下错列,若摛锦布绣”[3](P卷十)。雍正指示擅长绘画的刑部侍郎高其佩把当时园中图景绘制下来。后来,这张图被赐予张廷玉,张亦撰文记载此事,称“我皇上优礼大臣,恩谊稠渥,芳辰令节,宴赏不时。而臣之奉清光,被殊眷,又在诸臣之上”。当年八月,雍正把戚畹旧园赐给张廷玉和大学士朱轼、尚书蔡珽等八人同居。此园在御苑之东半里许,“奇石如林,清溪若带,兰桡桂楫,宛转皆通。而曲榭长廊,凉台燠馆,位置结构,极天然之趣。”“爰赋纪事诗八章,以示同人所以志恩泽之隆,述园林之胜,而庆遭逢之不偶也。”[4](卷十一)这八首五言律诗第一首和第八首总括戚畹名园之胜境,堪比“上林”。第二首至第七首分别从潭水、滩石、树木、曲径、楼阁、花木等角度进行描写,意境清新自然,有唐诗风韵。其中第四首“树杪千寻阁,松阴百步廊。岚生峰滴翠,花落水流香”,第六首“草色澹遥碧,杏烟笼浅红”,第七首“拂地三眠柳,参天百尺梧。棣棠红组绣,芍药玉盘盂”等句属对工稳,风格典雅而无雕琢之痕迹,为写景之佳作,反映出张廷玉当时的愉悦心境。后来,张廷玉以康熙所赐“澄怀”二字名此园,并于三年之后写下《以澄怀名所居之园恭纪二首》,称“身居瑶岛瞻银牓,湛露恩深戴两朝”[4](卷十二)。
雍正六年(1728)六月赐十体字墨迹,张廷玉于墨迹之后作跋,把自己所受恩宠与他人相比较,云:“伏念自古人臣叨受御书之赐,不过幅缣片楮,即已诩为殊荣,传为盛事。况以御屏之郑重,仰天翰之神奇,集书法之成睹,云章之辉映。遐稽简册,洵千载所希闻;叨被恩荣,实百生之厚幸。”并称要把墨迹奉为子孙世世之宝。
以上又可视为张廷玉与雍正诗文交往的第二阶段,主要特征为担当重任,不负圣望,知遇之恩,亦君亦友;身居名园,不染尘滓,洗心浴德,为国尽忠。
张廷玉雍正诗文交往之高潮当在雍正十一年(1733),帝赐假祭其父张英于桐城本籍这件事情之上。可查考的有《赐假纪恩诗六首》并序、《给假举行先臣谕祭典礼谢恩奏》、《谕祭礼成谢恩奏》等诗文均围绕此事而成。表面上看这些诗文是为祭礼而写,实际上也是对于十一年来君臣关系的总结。张廷玉一方面表明自己一直忠心耿耿:“窃念臣十一年来仰沐鸿慈,趋乘禁近,时闻圣训,日觐天颜,未曾一日睽离殿陛……葵向之诚,定蒙睿鉴。”[3](卷二)另一方面,对雍正的感恩之情也再次得到升华:
凡白叟、黄童、绅衿、士庶以及四方观礼者……骈肩累迹,莫不欢欣叹羡,以为恩荣光宠不特耳目所未见闻,亦且史册罕有伦比。盖皇上之施恩于臣家者,实属从古未有之恩礼;而臣家之邀荣于皇上者,实为从古未有之光荣。臣感激微忱,虽累牍连篇,何能宣述万一。[3](卷二)
自古人臣最大的荣耀莫过于光宗耀祖,张家此次所享受到的荣耀为乡人所羡艳,其程度非一般祭祀所能相比,无怪乎张廷玉三番五次、连篇累牍说明自己的荣耀自古未有,甚至没有什么语言能够形容自己的心情。
笔者注意到这中间张廷玉两次提及“乌鸟私情”,一次是在《给假举行先臣谕祭典礼谢恩奏》中,一次是在《赐假纪恩诗六首》其六。诗云:“已酬乌鸟愿,更挈燕雏行。”这是以前的诗文交往中没有过的。
以上可谓张廷玉与雍正文笔交往之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张廷玉宠荣之极,无以复加,位极人臣,古今少有,亦君亦友之情再次升华为乌鸟私情。
三、雍正与张廷玉之文学影响
雍正与张廷玉之文学影响首先是文章的创作观点上的相互影响。历史上,张廷玉是以大学士名世,而非诗文。他之所以受到雍正的倚重,主要是因为能够“详达圣意,缮写上谕”。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说明雍正与张廷玉文风一致,两人之间有着趋同的文章创作思想与趣味。
雍正曾在《谕科甲出身官员》一文中称:“朕嗣统以来,元年、二年内阁面奉之旨,书写时动辄讹舛。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盖记载一事,良非易易,毫厘千里之差,不可不慎。”[2](卷三)这里说明在张廷玉任大学士之前,雍正对他人所写之上谕是很不满意的。而为什么只有张廷玉写的令他满意呢?这里面除了因为张廷玉能够很好地领会雍正的意图外,文风一致也恐怕是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后来张廷玉并不被乾隆看好,要不是因为雍正的遗诏,险些连配享太庙的资格都取消了,难道历事三朝的张廷玉就不能领会乾隆的意图吗?
雍正在此文中还明确谕示科甲出身官员:“尔等翰林自以文章为职业,但须为经世之文、华国之文,一切风云月露之词何所用之……至于赋诗饮酒,自附于晋人风流,此种恶习,所当深戒而痛绝者也。”张廷玉的功劳也就在于“经世文章”,他曾多次在诗文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庚戌年原序》中,他称赞当时还是皇子的乾隆说:“皇四子粹质天禀,明敏博达而功力缜密……有非专攻文学之儒所能希其万一者。”对文学之贬抑,与雍正如出一辙。在他的《澄怀园文存自序》中,他说:“夫以弇鄙无学之人,居殚力服勤之职。则其于文艺也,寻章摘句,不能工大雅,扶轮愧前哲。”此处虽是自谦之词,但亦是实情,一方面的确因为公务繁忙,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文艺”上,所以不能有太高的成就,另一方面恐怕与他的文学观念有关。虽其弟子吴华孙赞美其诗,称:“读其诗不知其为台阁之与山林,将无寄迹轩冕而天怀淡定故耶”,“其诗萧然高致,有出于语言文字之外者,由其澄心而渺虑也。”[4](序)但他的诗名没有得到流传,甚至不如乃父。
雍正与张廷玉文学观点的趋同是一种巧合,还是君臣二人交往磨合的结果?也许二者兼而有之,至少是在频繁的诗文交往中互相达到了认同,形成了默契,于我心有戚戚焉,才会心领神会,配合一致。
其次,雍正与张廷玉以他们的特殊身份对奠定本朝代表官方的正统文风起了十分重要作用。雍正通过规范科举考试来规范士子的文风,而张廷玉就是这其中最得力的执行者。雍正一登基就拜张廷玉为太子师,雍正元年(1723)三月即开恩科顺天乡试,命张廷玉为主考官之一。并面谕张廷玉曰:
科场乃国家抡才大典,而北闱历科以来,每多物议。不但有伤于士习文风,亦大有关于国政、国体。今当雍正开科之始,特简朱轼与汝使主试事。料汝二人必能矢公矢慎,识拔公明,俾士论翕然,群情悦服,不蹈从前覆辙也。[1](p20)
本朝首次恩科乡试,令诸生翘首以待,所命之题事关重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读书人定然趋附之。张廷玉奉命出策问五道,一问《孝经》,二问至圣先师孔子,三问取士之法,四问民风,五问治水。其中第三问直接把雍正的取士标准点明,策问云:
自隋唐以来,士子以文章为先资之献,而文与行违者,往往有之。论者谓行乡举里,选于今日,恐滋矫伪之习。文以载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以此求士,拔十得五,舍是更无良模,其说然欤?抑必学校制备诗儒之教,严使内外交养,本末兼修,而后收制科之实效欤?[3](卷六)
这段话指出,人不如文,文、人不一现象的存在,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同时,希望学校加强诗儒之教,把生员们培养成“本末兼修”之人。所谓“本”当指儒家仁义之本,而“末”当指文辞。为了强调“本”,策问中点明“钦命顺天乡试三题首揭忠敬二字,示士人以立身行道之大端;次明五品人伦而归于立诚,三言稼穑之艰难,以为恒心之本。”为了指出所谓“末”,策问中甚至说:“诸生其何以祗率圣教躬行实践而不徒事文艺之末欤?”而学者所读之书不过“诸经子史”罢了[3](卷六)。策问四还提到:“夏尚忠,商尚质,周监于二代而尚文。文即文此忠、质也,岂忠质之外别有所为文耶?”此处“尚文”之“文”应为名词,指文辞;而“文此忠质”之“文”当为动词,可理解为用文辞表达;最后一个“文”,仍为名词,当指文章或文辞,除了忠、质之外,文章没有别的应当表现。这样的策问已经不仅仅是一张考试卷而已,是向士子们宣告了雍正朝所追求之文风是以忠、质为主要内容的文风,脱离了这个主题,其他一切文字都不会是好文字,都不会受到统治者的青睐。
这次恩科乡试的结果令雍正十分满意,他朱批嘉奖:“十卷皆好,第一名为留心性理之人,必是端方之士。”并下达谕旨,称:“国家大典首重抡才……今顺天主考朱轼、张廷玉公慎自矢……细心搜阅,尽拔佳文……朕心深为嘉悦。其酌加议叙,用示优奖,兼使嗣后考官咸知激励,以副朕兴贤育才之至意。”[1](P21-22)张廷玉与朱轼一起为雍正朝以后的考官做出了榜样,而奉命出策论五道的张廷玉在题目的引导上应该说起了更大的作用。
此后,张廷玉还曾经于雍正元年(1723)雍正二年(1724)两次充当正考官,均出题策问,从询问“天人性命之旨”到“德教”到问礼,问人臣事君之道等“大道”,逐渐过渡到有关历史、农业、仓储、刑法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先立本而后务实,都得到了雍正的肯定。
张廷玉在规范士子文风方面所做的贡献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雍正元年,蔡世远《古文雅正》十四卷付梓,原序正是张廷玉所作。蔡世远(1628-1733),字闻之,福建漳浦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雍正元年(1723)被召入京师,授编修,值上书房,侍诸皇子读共八年,累迁侍讲学士、少詹士、礼部左侍郎。“其学博通今古,尤以程、朱理学名家。”②纪昀也称其“理醇词正,具有本原”[5](p842)。蔡世远所编《古文雅正》选自汉至元上下二千年中历代古文仅二百三十余篇,其自序曰:雅正者,其词雅,其理正也。
张廷玉在这个时候以他的身份、地位为这样一本文选作序,其意义自非一般。序言开篇明义:“文辞之兴非偶然也,发天地之精华,而根之性命。”“故夫性命之文约而达、赡而精、奥博而有体。要他若俶诡幻怪,卮词蔓衍,与夫月露风云,连篇累牍,大雅弗尚也。”③言下之意,性命之文才是大雅之文。接着,他强调了当今皇上“以崇实学、敦名教为先务,凡以期海内文学之士不鹜声华,而衷诸性命也。”这实际上是为雍正代言,呼吁普天之下的读书人读书作文都要以性命为本,而不要以文辞形式之美超越于对性命的追求。他还进一步批评有些选家“往往漫无主见,是非纯驳,鲜所抉择。徒取词句之赡美,为学者讽诵之资,不几判文章之学与性命之学为两途,使习其事者何所取以为束身检行之归欤?”他赞扬蔡所选之文“有奇醇正典则悉合六经之旨,而俶诡幻怪、风云月露之词无一焉。”最后归纳此本所选之文“其秩简,其义精,而崇实学以黜浮华,明理义以祛放诞”[3](卷七),评价可谓极高。《四库总目提要》称《古文雅正》“数十年传诵艺林不虚也”,可见此书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终雍正一朝,除了在十一年时,方苞替和硕果亲王编《古文约选》外,所编能够代表官方观点的古文选恐怕就只有《古文雅正》,即便雍正皇帝自己所编《悦心集》也只是作为“悦目养心”的工具,离性命之文远矣。这就更可见此书的重要意义,亦可见张廷玉作序之用心和影响。
再次,雍正影响了张廷玉的文章创作思想和趣味,张廷玉又进一步影响周围的人,为雍正朝培养和选拔了更多的人才。除了在担任考官时能够公正地选拔出符合雍正人才标准的士子之外,张廷玉的兄弟、子侄也多在本朝科考中名列前茅,所撰考试之文受到雍正的青睐,这恐怕并非偶然现象,与他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有密切关系。
比较典型的是其弟张廷珩与其子张若霭。雍正元年(1723)十月,张廷玉任殿试读卷官,与诸大臣“秉公校阅,取定甲乙,照例以前十卷进呈御览”。雍正读到第五卷,大为嘉赏,说:“此卷应置第一,奈何拟为第五?”这时,张廷玉禀报,此卷为其弟张廷珩所作。雍正就想要把他的卷子拔置一甲。后来,由于张廷玉以自己为阅卷官要避嫌为由不赞同雍正的做法,最后列为二甲第一。[1](p24)
事隔十年,相似的事情又发生在张廷玉的儿子张若霭身上。雍正十一年张若霭以会试第三十名参加了殿试。四月初一,雍正在懋勤殿阅卷,对阅卷官说:“尔等所拟名次,未为允协,中拟第五名卷,策语恳挚,识见老成,非经生家可比,字画亦端楷。尔等须再加详阅商定之。”后经重省,将原来的第五名列为第三名。等到启封一看,原来第三名就是张若霭。张若霭的策论得到了雍正的高度评价。策内“公忠体国”一条云:“僚采之际,善则相劝,过则相规,无诈无虞,必诚必信,则同官一体也,内外一体也,文武亦一体也。广而至于百司庶职,何莫非臂指手足之相关也。此则纯臣之居心,可以不负千载一时之遭逢,而赞襄太和之上理。”[1](P39-40)对于这段策论,雍正的评语是:“数语极为恳挚,颇得古大臣之风。”并称:“盖大臣子弟能知忠君爱国之心,异日必为国家宣力。”[1](p40)雍正认为这正是张廷玉家教影响的结果。谕曰:
策内议论,确有识见,想其习睹习闻,秉承家训,得大臣忠君爱国之意,是以敷陈之言,切当恳挚如此。张廷玉佐朕多年,居心行事,比诸古人皋、夔、稷、契,信可无愧。且自伊父张英累世厚德,绳绳相继,宜其后人克肖,贤才蔚起,以副国家之用。[1](p38)
后来张廷玉坚辞,执意要将一甲的名次让于天下寒士,张若霭最终名列二甲第一。后授为翰林院编修,值南书房。后来,张廷玉、鄂尔泰二家子弟多受拔擢,为了避嫌,雍正还专为此降谕:
如伊两家子弟才具平庸,未克胜任,而朕必欲逾量擢用,是非所以爱之而实以害之,岂朕所以待两大学士者耶……一以两家之先人培植深远,方获生此贤者,为国家之股肱心膂,而绩厚者流光,谅不仅钟秀于两大学士之一身而已。[1](p48)
雍正的反复强调说明任用张若霭等张家子弟确因他们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总之,雍正与张廷玉的文笔交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人的创作情况,显示了二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君臣情谊的实录。雍正非常重视张廷玉正是因为其文笔能够为自己代言,能为雍正朝的政治服务。张廷玉的文章创作思想和趣味与雍正趋同,他在担任科举考官的过程中很好地代表帝王贯彻了文学思想,为培养符合帝王要求的文人作出了贡献。他们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对当时官方正统文风的把控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