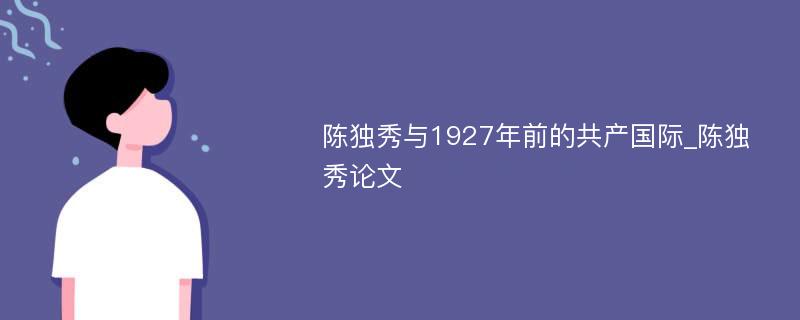
1927年以前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气势磅礴的中国历史画卷中,20世纪无疑是最为生动精彩的一页。在这个重大而又关键的历史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叱咤风云的弄潮儿,陈独秀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以纵横家的政治气度,与共产国际反复探索,设计了医治百孔千疮的中国社会的种种方案。然而,从1920年8月始,直到1927年春夏之交,七年的风风雨雨、屡起屡扑,又使他感到十分的疑虑和忧伤……
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在马列主义传入伊始,除李大钊等个别人外,新文化运动的其他领袖们对此尚未表现出多大兴趣。尤其是主帅陈独秀,他仍坚持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为利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而思想革新、而文学革命、而伦理革命,而教育革新、而基督教救国,可谓狂飙突进、日新月异。只是在这一系列的启蒙手段的尝试收效甚微乃至事实上宣告失败之后,陈独秀才转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手段,以工农劳苦大众为启蒙的对象。对于陈独秀来说,这个转变既有无可奈何的被迫色彩,又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一次转变。陈独秀一旦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以其一往无前的气概,积极开展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宣传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工作。
毫无疑问,最早主张在中国建党并着手建党的,是李大钊与陈独秀。首先,以陈独秀为“总司令”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使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方面、干部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①;其次,李大钊、陈独秀最早在中国酝酿建党:1920年2月中旬,当李大钊第二次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之时,两人曾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②。当时虽未作详细讨论,但两人心心相印,决心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再次,陈独秀等人在天津时就曾进行过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只是因为形势的紧迫而不得不中止活动,而转赴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去开展活动③;陈独秀南下上海后,确实加强了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研究,并筹办工人刊物,组织工会,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些活动,都是在共产国际代表首次来华之前开展的,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独立自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新尝试,是自觉的要求与行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拉开了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幕。那种主张“中国共产党外来论”的观点,实在是荒诞的臆言,根本不堪一驳。
但是,共产国际所给予的协助,又大大加快了陈独秀建党的进程。虽然第一个担负着指导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建立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维经斯基一行的首次来华,并非受共产国际直接派遣,但毕竟是受命于俄共(布)远东地区的党组织,他们在上海帮助陈独秀创建了中共上海发起组,还创办了外文学社,培养革命干部和进步青年,设立了华俄通讯社,翻译和报道来自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大量材料,对于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建党工作,起了积极作用。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马林来华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党在成立初期的工作,更是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国际主义的援助。应该说,这些援助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程,然而没有这些援助,中国共产党也将产生,只是时间上的早晚问题。
二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国共两党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后达成的共识,既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可能性。共产国际起了关键作用,大大加速了国共合作的进程;但在推动过程中,又犯了不少大的错误。
共产国际成立之时,正是苏俄处境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列宁主义的要求,面对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苏俄迫切需要缓和某些次要矛盾,团结那些可以利用的力量,以对付主要的敌人。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则是其争取联合的最佳对象。从自身的安全考虑,苏俄迫切需要打开对华关系,争取中国的同情和中立立场,以求在苏俄与东方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建立起一个广阔的战略缓冲地等。因此,苏俄不惜以放弃帝俄时代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为钓饵,以换取中国政府的谅解和中国人民的感激。同时,苏俄又与中国各派政治势力进行了广泛联系并探讨合作。时而张作霖、时而段祺瑞政府、时而吴佩孚、时而孙中山,但最终选定了孙中山作为合作对象。这是正确的、明智的选择。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选定孙中山并推动国共合作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最早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在取得共产国际支持并被委以全权后,在杭州西湖会议上他以国际命令和纪律压服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促使中共中央大多数同志转变态度。他还为营救陈独秀出狱伤精费神且花钱不少,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④。马林还做过其他不少有益于国共合作的事。此外,维经斯基、加拉罕、达林、越飞等来华的国际代表和苏俄特使以及后来来华工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他们同陈独秀一起,对于转变中共中央其他同志和一般党员的思想认识,尤其是对国共党内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认识,对推动国共合作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陈独秀思想认识的转变,带动了一大批共产党人的转变;陈独秀等率先加入国民党,更是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
但是,共产国际在指导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右倾错误观点,违背列宁主义原则。尤其是列宁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这种右倾错误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压制了陈独秀原本正确的一些思想观点。
第一,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众所周知,陈独秀在1919-1922年间曾“看重过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⑤,并提出:“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指有产阶级政治之下的全力造成的政党——引者),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⑥。即使是1923年4月,陈独秀仍然坚信:“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这体现了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的思想发展,与国际代表马林明显贬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观点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的雏型,后者则是不折不扣的右倾投降主义观点。但是,马林的意见却能为共产国际所支持。《真理报》1922年7月27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当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在陈独秀参加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国际执委会书记拉狄克当面批评中共代表的发言,坚持认为:在目前的中国,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实现的条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还为时尚早⑦。1923年1月26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更是开宗明义:“共产党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应用于中国”。苏俄政府与共产国际低估中国无产阶级和贬低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为其右倾错误政策的出台做好了准备。
第二,关于中国农民阶级的革命性。陈独秀对中国农民阶级力量和革命性的判断是比较客观的。他多次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半数,农业是国民经济之真正的基础,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在势力,国民运动不可漠视农民问题⑧。他又批判了所谓“农村立国”的口号,提出“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⑨,因此,不经过一次革命的洗礼给农民带来土地等实际利益,农民是难以立刻投身国民革命的。这个看法虽然对农民革命性认识不足,但却看到了农民阶级的巨大革命潜力。然而,国际代表马林却说中国农民阶级对革命漠不关心,《真理报》也认为中国农民“落后、愚昧、保守、消极”,革命运动“在农民中得不到任何响应”。这显然是否定农民阶级的革命性,把农民阶级排斥在革命运动之外。因而中国农民运动在建党初期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影响到党在以后的农村工作。应该说,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农民政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和危害,比陈独秀要严重得多。
第三,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地位和作用,西湖会议前,陈独秀一直认为国民党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组织涣散,作风腐败。虽然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提倡“劳工运动”,但其阶级性质未有改变,西湖会议后也有保留。但马林却说国民党是一个中国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论断虽对促进国共党内合作有推动作用,但却容易导致一个错误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国民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⑩。拉狄克在国际“四大”上指示中共“一、组织青年的工人阶级,二、使它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采取明智的态度”(11),即让中国工人阶级追随资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这是明显的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观点。《真理报》更是公开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政党,首先是最激进的、人数最多的国民党,它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它所吸收的主要是中间的小资产阶级成份,知识分子和激进的工人(12),而将中国共产党看成是“小团体”、“小组织”,甚至认为“诞生过早”,“本来不应该产生”等等。苏俄政府和联共(布)中央派来的鲍罗廷顾问初来乍到就对中共中央说:我们应该“努力使国民党真正成为民族革命运动的首领,切实地发展它,赋予它斗争的意义和口号,促使它达到最终目的。国民党作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代表,应该掌握政权(13)。”可见,上起联共(布)中央、苏俄政府、共产国际,下至苏联顾问、苏俄特使、国际代表,其右倾错误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第四,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问题。如前所述,“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的萌芽最早是陈独秀提出的。早在1920年,陈独秀就公开宣称:“在社会党(即共产党——引者)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之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敌人(14)。”显然,这两个革命之间并无过渡阶段。这是陈独秀“两步革命”思想的最初说法。“两步革命”与“两次革命”仅一字之差,实质迥异,关键就在于两个革命中间有无过渡阶段和由哪个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1923年,陈独秀改变了说法,提出了“二次革命”论。对于一个年轻的党的领袖来说,这种改变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两论”形式上太相似了。然而,这样的错误发生在列宁主义的故乡,就难以令人信服了。从国际“四大”上拉狄克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断言:“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议事日程;遗憾的是,在中国甚至连全国统一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共和国问题,都没有提上历史的日程”(15),到《孙文越飞宣言》对孙中山提出的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错误观点的完全赞同,这充分说明: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还相当严重,甚至暴露出一些取消中国共产党、取消中国革命的严重错误立场。这些错误观点和消极情绪,对陈独秀“二次革命”思想的形成并逐渐产生严重的危害,提供了发育的温床。
三
在巩固统一战线、发展革命力量的斗争中,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做了一些努力,但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着右倾错误观点,压制了陈独秀等的正确主张,又刺激了他的错误观点,实际上包办了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工作。
第一,关于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在这个最重大的问题上,陈独秀的内心世界是相当复杂的。如果仍旧放弃领导权,他担心会被“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16)。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革命斗争形势的高涨,使他受到了鼓舞。他认识到:中国革命若没有劳动阶级“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革命“是不能成功的”(17)。中国工人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天然的农民同盟者”;而资产阶级当中,有些是帮助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反革命者,有些是非革命的中立分子,有些是偶然倾向革命而易于妥协者;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的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18)。此外,党的“四大”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五卅运动中陈独秀用自指挥上海各界的反帝爱国运动,而陈独秀亲自组织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更是中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这些宝贵的思想行动,都是在没有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的参与下提出和进行的。
中共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提出和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展,引起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恐慌。他们从组织上弹劾共产党,不惜分裂国民党;从行动上则暗杀支持国共合作的著名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面对此种甚嚣尘上的反共气焰,共产国际虽制定了打击右派、扩大左派、团结中派的政策,采取了揭露甚至清除右派的措施;但是,国际更多的却是压制中共向国民党“作某些让步”,以消除右派的反共宣传的影响。苏联顾问鲍罗廷企图以放弃中共在国民党决策机关中的地位来换取统一战线的巩固(19),这恰恰是在断送统一战线的前途。基于此,共产国际对中共作出的争取领导权的任何努力和斗争,都一概加以压制和阻挠。这种一味妥协以求得团结的做法是幼稚而荒唐的,在实践中则必然是失败。
第二,关于革命武装力量的建立。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对此,陈独秀是有所认识的。早在青年时代,陈独秀就学过军事知识,还报名参加过反对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的“拒俄义勇队”,重建的岳王会组织也主要是在安徽的新军中开展活动,成为军界革命运动的先锋(20)。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曾多次“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并数度向国际代表提出,但均遭拒绝。仅1926年,苏联政府给国民党援助枪支18000多枝,给冯玉祥国民军的援助达35000枝,子弹更是不计其数,陈独秀曾要求国际把援助蒋介石、李济深的枪械匀出5000枝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以“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为借口严辞拒绝(21)。共产国际过高估计了党代表在军队中的作用,以为只要把政治工作做好了,就可以控制军队;这实际上是放弃了革命武装的建立。本来完全可能建立一支由中共直接掌握的强大的军队,由于共产国际的放弃而付之东流,因而当蒋介石、李济深、冯玉祥、汪精卫等相继叛变革命,屠杀工农之时,我党不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第三,关于反击国民党新右派的进攻。面对戴季陶反苏分共小册子的发表和蒋介石反共夺权的反革命行动,陈独秀对前者给予了大力的批判和揭露,态度是坚决的,斗争是有力的。而对于后者,陈独秀就不敢贸然直言了。因为面对着的是共产国际的红人、国民党的军事领袖蒋介石。共产国际认定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把蒋介石的军队当作革命的中心力量,因而大力扶植蒋介石,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进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军事上给以大量的军火援助,使蒋介石逐步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促使了蒋介石反动野心的膨涨和反革命势力的增强。尤其是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两大事件中蒋介石反动面目暴露无遗之时,共产国际仍然姑息、迁就,鲍罗廷与蒋介石的三项君子协定内容一直没有告诉上海的陈独秀。共产国际更不惜以压制陈独秀等的正确主张(明确指示共产党人不应在国民党内谋取领导权,但又不准退出国民党)和国民党的反蒋势力(22),反而接纳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其报刊仍不惜版面用肉麻的语言吹捧蒋介石。直到蒋介石明显地成为新右派时,仍把他说成是中派,一味强调对他的团结和争取。尽管陈独秀多次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并派人去汉口向国际代表陈述意见和决定反对蒋介石的计划,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仍不觉悟,却连电陈独秀去武汉,企图依赖武汉国民政府解决问题(23),国际报刊仍连篇累牍地吹捧蒋介石、驳斥蒋要政变的宣传,从而抑制了陈独秀对蒋介石反革命阴谋的揭露,迷惑了年轻的共产党人,放弃了对蒋介石应有的警惕和提防,致使蒋介石顺利地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措手中及,组织不起有效的力量予以反击。
第四,武汉时期关于中国革命的扩大和深入问题。有人把1926年12月在汉口举行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会议通过的一系列议决案说成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标志,是完全违反了几乎与此会同时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精神。但是,这次会议恰恰又是在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亲临指导下召开的,而且会议最后,由中央政治局与维、鲍两人召开的联席会议又确认了此次特别会议的精神,并在一些重大问题的把握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尚且违反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精神,还能苟求陈独秀等中国同志吗?
又有人说,1927年4月陈独秀与汪精卫的“联合声明”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麻痹了革命群众、松懈了革命斗志并助长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气焰。然而,这个声明的内容恰恰是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最新政策而制定的,而且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这个宣言十分器重,曾在多种场合和报刊上引用了宣言的全文和某些段落。陈独秀后来回顾说:“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命令,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而且根据国际对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汪精卫联合发表那样可耻的宣言”(24)。悔恨和无可奈何之心情由此可见。
陈独秀奉国际电令来到武汉之时,形势已相当危急:一方面两湖地区农民运动迅速发展,但地主豪绅和反动军官也在密谋组织反扑;另一方面南京蒋介石、广州李济深、重庆杨森等新旧军阀封锁武汉,企图拖垮国民政府;还有北方的吴佩孚、张作霖盘踞河南、河北,伺机南下扑灭革命。因此,革命势力面临着三种选择:东征讨蒋、土地革命和继续北伐,即革命的扩大与深入的关系问题。陈独秀先是赞成周恩来等提出的东征讨蒋,但由于苏联顾问鲍罗廷热衷于实践他的“西北理论”,主张继续北伐,于是陈独秀又转向继续北伐。先扩大尔后深入,致使蔡和森、毛泽东等提出的先深入后扩大,即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两湖地区开展农民运动,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和周恩来等东征讨蒋的正确主张没能到采纳。当时政治局内部争论激烈,国际代表罗易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更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陈独秀徘徊于两人之间,不知所从,最终服从了鲍罗廷。实际上,此时的陈独秀已经象一只迷途的羔羊,陷入了无限的怅惘与苦闷之中。
有人提出,陈独秀拒绝执行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是丧失了挽救革命的最后良机,这种说法实在是言过其实。应当承认,这个指示强调了自下而上的没收土地、充实国民党政权,并首次提出了中共建立军队的任务,这比以往任何一个指示都有较大的发展和进步,是共产国际挽救中国革命的一次重要努力。然而,这个指示来得太晚了,当时建立军队的大好时机已经丧失;而且指示本身也包含有明显的矛盾,即既要坚持与武汉国民党合作,又要改造他的中央领导机关,使其执行规定,这简直是与虎谋皮的幻想、空谈,即使是俄国人自己也感叹无法执行。关键时刻,国际代表罗易又自作聪明,把指示交给汪精卫看,干了一件大蠢事,为汪精卫“分共”提供了口实。
郑州会议,尤其是徐州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陈独秀先扩大后深入的革命意图化为泡影,但鲍罗廷的西北学说更是流为笑料。此时,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既无力进行东征讨蒋,又不愿深入两湖,发动农民,建立两湖革命根据地,只是恪守共产国际“决不退出国民党”的指示精神,因而不惜以解散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承认国民党处于当然的领导地位、退出武汉政府中的共产党员以及承认工农团体归国民党的领导与监督(25)。全面放弃领导权的目的是在于“推迟”武汉国民党的叛变,其结果只能更加助长其叛变革命的反动气焰。
本来,武汉时期的陈独秀是紧跟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的,革命失败关头向共产国际承担责任的应该是处于决策和督促执行地位的这些代表和顾问们。然而,鲍罗廷却提议要陈独秀“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26),并另行指定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这实际上是剥夺了陈独秀的领导权。陈独秀无法领导下去,因而向中央提出辞职,其主要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27)。但陈独秀并未去莫斯科,而是继续留在武汉并隐蔽起来,以后又去了上海。陈独秀开始独立思考了。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660页。
②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传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25日。
③详见任武雄《从社会主义者同盟到社会共产党到共产党——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④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三),第2页。
⑤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1931年9月。
⑥⑧⑨(14)(15)(17)《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5、312、367、12、259、519页。
⑦(11)《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64、65、65页。
⑩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8年6月21日。
(12)(13)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内部出版,第72、85页。
(1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内部版,第331页。
(18)《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第11-12页。
(19)乌里扬诺夫斯基:《共产国际与东方》,第281页。
(20)参见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
(21)(23)(24)(27)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22)详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中山舰事件前后》,《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2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256页。
(26)《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8页。
标签:陈独秀论文; 鲍罗廷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蒋介石论文; 真理报论文; 国民党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