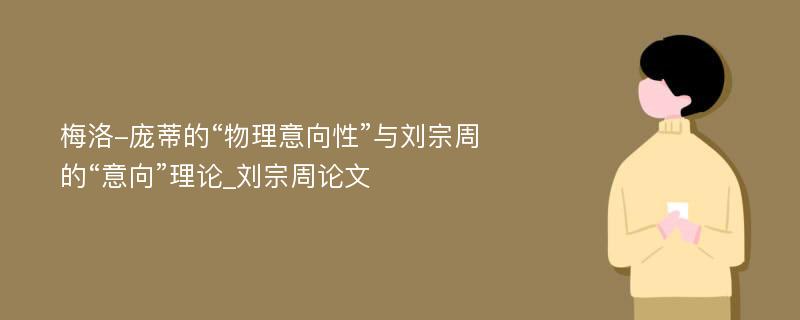
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性”与刘宗周的“意”的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向性论文,学说论文,身体论文,梅洛论文,刘宗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法国现象学哲学家梅洛-庞蒂以其思想的独创和自成一体,堪称身体哲学理论的真正翘楚。一种深入的研究将使我们发现,梅氏的身体哲学理论的奠定,又是与该理论的一个至为核心的概念、一个决定了身体之所以为身体的概念——“身体意向性”的天才发现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故为了真正地跻身于梅氏为我们所构造的身体的殿堂,我们就不得不追溯他思的足迹,对“身体意向性”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确切的内涵给予深入的梳理、分析,尽管由于诸如其著作中实证语言与哲学的混用,其不同语境下的表述的多义性等种种原因,在一般人心目中,该概念是如此的扑朔迷离,如此的不无诡谲,以至于对它真实面目的破译实属不易。 “身体意向性”的概念,在梅洛-庞蒂的早期开山之作《行为的结构》一书中已初现端倪。当梅洛-庞蒂沿着前人的步伐,试图对有机体的行为,尤其是人类的行为之谜给予探秘时,他发现自己面对着西方两大理论遗产:一为传统的经验主义,一为批判哲学。一方面,传统经验主义学说从原子主义出发,以“刺激—反应”为解释图式,把行为视为自然界的实在事物;另一方面,批判哲学则从反思的角度切入,以“意识之构成”为解释图式,把行为视为纯粹人为的产品。这样,无论是传统经验主义的学说,还是批判哲学,以其各执一端的致思取向,同样都错失了对行为之为行为的洞识,同样都与行为自身性质的解释失之交臂。相反,与这两种学说不同,梅洛-庞蒂借助于格式塔心理学的“心物同型”之“完形”思想,在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中为行为的解释另辟蹊径。在他看来,正是在此互动中,不仅作为一种“肉身化的辩证法”为我们克服了传统行为理论的自在和自为、物理与心灵、机械论与活力论之间的选择上的两难,不仅使我们从二者的“线性因果”走向了“循环因果”,同时从中也使一种作为“意向性的行为主义”这一行为理论的“第三条道路”得以豁然朗现。 关于这种“意向性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e inentionnel),梅洛-庞蒂写道,“那些严格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如言谈行为、劳动行为、穿衣行为,并不具有固定的意义;我们只有参照各种生命意向才能够理解它们”①。在《行为的结构》一书中,这种行为的“生命意向”还被称为有机体置身于环境中的“身势”、“姿态”:“现象身体的各种身势和姿态应当有一种特定的结构,一种内在的意义,它一开始就应当成为向某个‘环境’衍射的各种活动的中心,成为一种物理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轮廓,成为一种特定的行为类型。”②此外,在《行为的结构》一书中,在某些场合下,这种行为的“生命意向”还与“前意识”的我们的“各种需要”、“各种注意”这类概念相提并论③。然而,表述各异,其指却一。虽然能指在不同的语境中不断地变换,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这里的种种所指都为我们指向了作为行为的“初始动作”,也即行为固有“行为结构”的“身体意向”(即“生命意向”)。同时,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其早期处女作《行为的结构》里,还是其早期代表作《知觉现象学》里,乃至在代表其晚期成熟思想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当中,这种“身体意向”都一以贯之地贯彻其中,成为梅洛-庞蒂“现象学”身体哲学整个理论为之运转的中轴,赖以成之和构造的坚实基石。 那么,到底什么是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呢?若深入地加以分析,我们可为它概括出以下几点重要的属性。 1.身体行为的朝向属性 顾名思义,“身体意向”即身体行为的意图和取向,故“朝向”属性当属“身体意向”的第一义。因此,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身体意向”与其说是一个“行为”,不如说“是一个朝向……的存在”④。这里的“朝向……”的“……”与其说是胡塞尔式的“意识意向性”朝向其“意识对象”的,不如说是实践论的“行为意向性”朝向“它的任务的”⑤。正是这种之于“它的任务”的朝向,使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性在打上鲜明的价值上的“目的论”而非学理上“认识论”的烙印的同时,使他从身体“需要论”走向身体“功能论”,并断言我们的身体功能丧失的疾病的产生乃是意向弧“变得松弛”所致⑥。也正是这种之于“它的任务”的朝向,使梅洛-庞蒂把这种朝向不是理解为向自在的自然的指向,而是理解为向人化的自然即有机体的生存环境的“敞开”,理解为人的生命意义向其“情景场”的“投射”,并像有些心理学家所认识到的那样,把人的“天赋性”不是界定为“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界定为“主体从其自身的内在深处抽引出来并向外投射的东西”⑦。在这里,正如梅洛-庞蒂所说,“从内部把握,我的行为呈现为有方向的,具有某种意向(intention)和某种意义”⑧,即对梅氏来说,具有“意向”的与具有“意义”的二者实质上异名同谓,身体的意向活动也即身体的“指意”(Signifaction)活动。 这种之于身体意向性的“朝向”属性的强调,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格式塔心理学的“图形—背景”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恰恰是对该原则进一步的理论重申和提升。正如在格式塔心理学的“鲁宾瓶”这一著名的示例中所看到的那样,由于知觉注意的定向不同,对同一知觉对象我们或可视为人脸,或可将其视为瓶。这种“横看成岭侧成峰”不正是对梅氏的身体意向的“朝向”性质的不无实证而生动的说明吗?所不同的是,如果说格式塔心理学的“图形—背景”原则以其“看”的“透视主义”的性质,而使这种“朝向”仅仅停留在意识认知论的水平的话,那么梅氏身体意向的“朝向”则由于与生命的内在目的直接连接,而使自身最终与身体的生存论之旨息息相通。这就把我们引向了身体意向性的另一属性,即可能性属性。 2.身体行为的可能属性 “身体意向”,既就其对一定目的朝向而言而为既定性的,又由于该朝向作为一种生命自身运动的朝向,即作为所谓的生命自身“运动的机能”而为可能性的。故梅洛-庞蒂在把这种“运动的机能”理解为“最初的意向性”的同时,不仅坚持真正的意识实际上是一种动态的“身体意识”,而且明确宣称:“我的身体运动和我的身体运动揭示的物体‘属性’之间的关系,是‘我能’及其产生的奇迹的关系”⑨,宣称“意识最初并不是‘我思……’。而是‘我能……’”⑩。这里的“我能”即我的潜在性、我的可能性。故在《知觉现象学》里,基于“身体意向”,梅洛-庞蒂提出了所谓“潜在运动”的概念(11),提出所谓“作为在一切决定性思维之前也不停地呈现的我们的体验的潜在界域的世界”(12)。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一书中,基于“身体意向”,他除了提出“潜在的意向性”的概念外,还指出“它(世界的肉身)是可能的完形,是世界的可能性”(13),并且径直断言:“这种可能就是我,我就是这种可能性”(14),以一种堪称“我能故我在”命题的推出,而代表了对西方传统的长盛不衰、不可易移的“我思故我在”命题的彻底颠覆。 不难得出的结论是,可能性之为可能性,可能之区别于既定性,恰恰在于它是对一切既有规定性的超越,用萨特的表述来说,它“不是其所是”,“是其所不是”。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和一种萨特式的“虚无”联系在一起。故在《知觉现象学》里,梅洛-庞蒂指出,“身体的生存不是基于生存本身,它始终受到一种活跃的虚无的影响”(15)。在其后期《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一书中,这种对“身体意向”的“虚无”之旨更是被多次提及和极力标举。梅洛-庞蒂写道“我的意向本身是空无的”,“我作为虚无的呈现”(16),提出“如果能够有多少存在,那么就会有多少虚无”(17),提出“人是每次进入新的开放维度的空白中的附属物”(18),以至于他宣称“我是乌有”(19),“我是虚无”(20),以其对身体意向的无比空灵的“我能”性质的无上强调,恰恰在身体这一切身可感、实实在在的血肉之躯中,为我们宣布了西方“实有论”、“实体论”哲学传统的寿终正寝。 3.身体行为的激活属性 身体行为的可能属性既是一种之于既有规定性的超越属性,同时又是一种通向日新又日新世界的属性。这使身体意向成为事物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故梅洛-庞蒂写道:“身体本身在世界中,就像心脏在机体中:身体不断地使可见的景象保持活力,内在地赋予它生命和供给它养料,与之一起形成一个系统。”(21)与这种作为“世界的心脏”的“身体意向”观点相应,在另一处,梅洛-庞蒂还写道:“当某一广延片段通过它的运动安排,通过它的每一运动对所有其他运动的暗示而返回到它自身,开始表达某东西,开始把其内在存在向外显示出来时,生命现象就出现了。”(22)这一切,使梅洛-庞蒂为我们谈到了身体意向作为“更加根本的可能性”的“激活”的可能性:“作用于我们的经验,将我的经验向世界和存在开放的那种可能性,以及肯定不把世界和存在当作它之前的事实来发现,而是激活和组织它们的事实性(facticité)的可能性。”(23) 这样,正如胡塞尔、海德格尔基于我的可能性而为我们隆重地推出了一个“生活世界”那样,梅洛-庞蒂也不例外。他不仅提出“现象的身体”的知觉乃为“活生生的身体”(24),不仅提出“我能”乃为一种“生命的一种原则的可能性”(25),不仅提出“身体意向”乃为“生命意向”,“内在于我们存在的生存过程的一个生命事件”(26),而且还把我们的也即以身体体验的世界视为一个生动的、鲜活的世界。故他写道:“感觉体验是一种生命过程,也是生殖、呼吸或成长”(27),并且把格式塔的“完形”视为一种所谓的“爆发的能力,生产能力,繁殖能力”(28)。此外,他还援引生命哲学家柏格森的观点,指出“活的存在在世界构成了‘不确定的中心’”(29),并且宣称“必须重新回到生命冲动的观念中去”(30),以至于与柏格森思想完全殊途而同归,断言世界的经验乃是一条不舍昼夜、川流不息的“生活之流”(31)。 4.身体行为的整合作用 如前所述,身体意向之于事物的“激活”属性已为梅洛-庞蒂所力挺、力揭。其实,不特如此,对于梅洛-庞蒂来说,除了该属性之外,身体意向之于事物还有“组织”、也即“整合”这一重要属性。也就是说,在事物经由身体意向的活动一跃成为活的生命有机体的同时,它们也经由身体意向的意旨被综合、统摄为意义的统一体。故梅洛-庞蒂指出:“正是这个意向弧造成了感官的统一性,感官和智力的统一性,感受性和运动机能的统一性。”(32)而这种统一性与单纯的物理系统的统一是迥然异趣的,“各种物理系统的统一是一种关系的统一,各个机体的统一则是一种意义的统一”(33)。换言之,“如果没有把一个身势从各种运动的总和中区别开来的这种内在的意义统一体,活的身体之自然在我们看来早就是难以想象的了”(34)。在此,梅洛-庞蒂明确告诉我们,身体意向(即身势)之所以获得内在的意义并成为“内在的意义统一体”,就在于身体是一种“活的身体”。我们看到,正是身体意向的这种“意义的统一”,才使梅洛-庞蒂的身体思想和弗洛伊德的身体动力学思想殊途同归却与弗洛伊德纯粹生物化的“生命能量”的概念保持着距离(35)。也正是基于身体意向的这种“意义的统一”,才使梅洛-庞蒂把人的存在与符号象征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宣称在人那里,“身体机能被整合到了一种比生命层次更高的层次,于是身体真正成为了人的身体”(36)。 在梅洛-庞蒂的学说里,这种“意义的统一”,就认识论而言,也即其所谓的知觉和认识。故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康德式的“统觉”(apperception)又一次复活了。正如康德宣称旨在能动地整合、综合事物的统觉功能即知性自身那样,梅洛-庞蒂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所不同的是,如果说康德的统觉是基于自我意识的一种统觉的话,那么,梅洛-庞蒂的统觉则为基于自身意向的一种统觉。进而,如果说康德的统觉所导致的是一种思之知的话,那么,梅洛-庞蒂的统觉所导致的则为一种前思之知。这种前思之知不是像康德那样,认为认知不过是意识之于意识对象的逻辑地构造和统辖,而是以一种“实践”、“实现”的方式坚持“当我的运动意向在展开时从世界得到所期待的反应时,我的身体就能把握世界”(37),坚持“理解,就是体验到我们指向的东西和呈现出来的东西,意向和实现之间的一致”(38)。乃至对于梅洛-庞蒂来说,实际上,我们不是用意识来理解,用意识来知道,而是“用身体来理解”,“用身体来知道”。易言之,在梅洛-庞蒂那里,一种“不虑而知”的“体知”,使行为的身体成为一种无所不知的我们真正的大脑。 5.身体行为与体现属性 这种所谓的“用身体来理解”,“用身体来知道”,与其说意味着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的属性,不如说就其“意向和实现之间的一致”,为我们指向了一种呈现论意义上的“体现”的属性。这种“体现”的属性,用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话来表述,它与“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海德格尔语)这一显体即本体的一致,是指“意识本身是一种为己的原呈现,这种原呈现被呈现为为他的非原始呈现”(39)。在梅洛-庞蒂的话语体系里,这种为己的原呈现与为他的非原始呈现,又分别对应于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不可见的与可见的、自为与自在、虚无与存在等等范畴,而“为己的原呈现被呈现为为他的非原始呈现”,则意味着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不可见的与可见的、自为与自在、虚无与存在等等二者之间的无间彼此的统一。故梅洛-庞蒂提出“生命是某一‘内在’在某一‘外在’中的呈现”(40),提出“‘不能客观化的活动’是根据‘能客观化的活动’构成的”(41),“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广延和思想的直接的和二元论的区别被放弃”(42),提出“萨特在解释这一点时说,自为必然被一个想象的为己的自在所纠缠。我们仅仅说,为己的自在不只是一个想象物”(43),提出“我拥有一个用存在填满的虚无,和一个被虚无掏空的存在”(44),“如果能够有多少存在,那么就会有多少虚无”(45)。 诸如此类的这些统一,不仅意味着对传统哲学中的主客二元论根本的消解,使哲学从主客对立走向了“对‘客体’范畴和‘主体’范畴的双重归属”(46),同时还意味着冥顽不化的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也随之作古,使作为“我能”的潜在而抽象的“心”完完全全体现在现实而具体的“身”之中,以至于我们的身是“走向世界之身”,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身”也在哪里,以至于就“心”的无限性、无边际性而言,“我的身体一直可达到星星”(柏格森语)(47)。在梅洛-庞蒂那里,身已不再囿于人的七尺之躯,而是被扩展到了无穷无尽的宇宙。于是梅洛-庞蒂宣称,“身体通过自身的本体发生将我们与事物直接联合,就像将两块陶泥像两片嘴唇那样贴合起来”(48),“这两组形象构成了一对夫妻般的东西”(49)。此即梅洛-庞蒂在其《行为的结构》中所指出的意向行为所具有的“向一个内在于它们环境扩散”的所谓的“肉身化的辩证法”(50),也即梅洛-庞蒂在其多部著作中一再重申的具有“能受一体”特征的意向行为的“身体间性”。 走笔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梅洛-庞蒂学说的终极皈依,即作为身体哲学核心概念的身体之为自身的“身体意向”的提出,并非仅仅停留在一种以身体为中心的彻底经验主义、彻底直觉主义的认识论,而是雄心勃勃地旨在“解构”笛卡尔的客观主义本体论(51)。梅洛-庞蒂在把肉身视为所谓“普遍性的存在”(52)、“普遍的存在的元素”(53)、“终极的观念”(54)的同时,也“使身体有了本体论的意义”(55),从而以一种对身体的前所未有的高标特立,实现了从西方传统的意识本体论、心灵本体论向“身体本体论”的战略性的转移,并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赋予了卑下而沉重的身体以下学上达、超越一切的“形而上”的意义。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诚如《易传》所言,中西文化、中西思想虽然天悬地隔、相距甚远,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决定了二者却以其“心一而道同”而可以互发和对接。法国现代哲学家梅洛-庞蒂的学说与明儒刘宗周的学说二者之间的关系即其一例。 谈到刘宗周,就不能不涉及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突出地位。这位以其说为理论结穴的宋明理学的“殿军”,这位被牟宗三先生视为其绝食而死意味着中华文化命脉之危机的中国明季最后一位伟大思想家,其之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如此非凡和独特的学术地位,与其说是他的学说发前人所未发地以“慎独”之旨为宗,不如说是他的学说独辟蹊径地对“诚意”之旨给予了独到而深切的发明,从而在他的学说里以其“意”的破译,既使中国哲学以一种“归显于密”(牟宗三语)的方式而揭示出其内蕴的真正隐秘,又使中国哲学秘响旁通地可在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说中找到其理论上深度的默契,而以其思想的民族性适成其普世性之理。 在刘宗周的学说里,其“意”的概念与梅氏的“身体意向”的理论上深深的默契,可一一对应地从刘氏的“意”的如下定义中得出。 1.作为“定盘针”的“意” 刘宗周之于“意”的隆崇,是对阳明基于古本《大学》解读的“诚意说”的进一步的深化和发明。关于这一点,他写道:“古本圣经而后,首传诚意,前不及先致知,后不及欲正心,直是单提直指,以一义总摄诸义。至末又云‘故君子必诚其意’,何等郑重?故阳明先生《古本序》曰:‘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56)并曰:“《大学》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57),“乃知诚意一关,为《大学》全经枢纽”(58)。进而,关于这种“诚意”之意,他指出“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止言心,则心只径寸虚体耳。著个意字,方见下了定盘针,有子午可指”(59)。类似的表述还有,“‘心如舟,意如舵’。又曰:‘心意如指南车’”(60)。 再联系《增韵》“意,心所向也”,以及《说文》注释中“心有所之”这些对意的解读,这种之于“意”的“定盘针”属性的一再强调,不正可以看作是对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之“朝向”属性的又一申明吗?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正如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的“朝向”具有鲜明的价值上的“目的论”的倾向那样,刘宗周的“意”亦不例外。故他就《大学》的“好好色,恶恶臭”指点“意”,把“意”视为“好恶之情”而非“是非之心”。他提出“好恶意之情,生而有此好恶之谓意之性”(61),提出“好恶者,此心最初之机,即四者之所自来,所谓意也”(62)。除此之外,他还提出“意之好恶,与起念之好恶不同。意之好恶,一机而互见;起念之好恶,两在而异情。以念为意,何啻千里”(63)。在这里,针对阳明心学,他指出“自心学不明,学者往往以想为思,因以念为意”(64),由此造成了把先天前意识的目的论的“意”与后天意识的认识论的“念”混为一谈的现象。在他看来,二者实际上是迥然异趣的:一为未发,一为已发,一无起灭,一有起灭,一无迁,一有迁。就此而言,“意”以其“无意之意”,它即古人所谓的“惟精惟一”的“道心”,而非随遇而起、思虑纷纭而作为种种想法和念头的“人心”。或者说,如果我们坚持要把“念”与“意”联系在一起,那么,在刘宗周那里,他所谓的“意”不过就是禅宗所谓的“但念无常,慎勿放逸”的“正念”之念。 既然刘宗周的“意”就其“好恶”而言实际上为价值上的“目的论”概念,同时,既然刘宗周进而宣称“意者,至善之所止也”,乃至提出“乃若其意,则可以为善矣,乃所以为善也”(65),这不仅意味着“意”属行为践履的伦理学的范畴,而且还意味着,正如王阳明将“好好色”属行,而将“见好色”属知那样,在刘宗周那里,作为“好恶”的“意”与其说是意识范畴的“心”之“意”,不如更确切地说,它不过是“行为结构”的“身”之“意”,也即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是也。无怪乎刘宗周谓“诚意之后,更无正心工夫”(66),谓“其实诚意则无意,无意则无心”(67),在这里,刘宗周的“在心为意”的“心”之“意”竟然一变为“无心”之“意”! 2.作为“几微”的“意” 当现代哲学家梅洛-庞蒂把潜在的“可能性”作为其“身体意向”的根本属性时,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该属性亦为中国古代哲学家刘宗周的“意”的学说所极力推重尊崇。刘宗周对“意”之“几”、“意”之“微”的强调即其明证。这里所谓的“几”即“动而未形”的“几”,这里所谓的“微”即“隐而未彰”的“微”,故二者均可视为是对潜在的而非现实的“可能性”概念的中国式表述。关于“意”之“几”,除了可见之于刘宗周提出“意之好恶,一机而可见”(68),提出“好恶者,此心最初之机”(69)外,他还写道,“未有是事,先有是理,曰‘事几’,未有是心,先有是意,曰‘心几’”(70)。此外,他不仅宣称“授之诚意以谨其几”(71),也即“诚意”即诚其“几”;并且宣称“慎则无所不慎矣,始求于好恶之几”(72),也即,“慎独”即慎其“几”。又,关于“意”之“微”,刘宗周的论述更是俯拾即是。例如,他谓“就心中指出端倪来,曰意,即微之体也”(73),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全是指点微体”(74),谓“动之微而有主者,意也”(75),谓“人心之有意也,即虞延所谓‘道心惟微’也”(76),以及谓“意根最微”(77),如此等等。同时,正如他把“诚意”与诚其“几”、“慎独”与慎其“几”联系在一起那样,在他那里,“诚意”与诚其“微”、“慎独”与慎其“微”亦成为异名同谓的东西。故他提出“知几故通微,通微故无不通,无不通故可以尽神,可以体诚”(78),提出“其为己也隐且微矣。隐微之地,是名曰独”(79),“慎独之功,亦只于微处下一著子”(80)。 我们看到,在梅洛-庞蒂的学说里,其对“身体意向”的“可能性”的揭示导致了其对超越一切既有规定性的“虚无”概念的发现,无独有偶,类似的情况亦在刘宗周的“隐乎微乎穆穆乎不已者”的“意”的观点中得以体现。故刘宗周写道,“人心径寸耳,而空中四达,有太虚之象。虚故生灵,灵生觉,觉有主,是曰意”(81),写道“以虚灵而言谓之心,以虚灵之主宰而言谓之意”(82),写道“惟天太虚,万物皆受铸于虚,故皆有虚体。非虚则无以行气,非虚则无以藏神,非虚则无以通精。即一草一木皆然,而人心为甚”(83)。写道“心与理一,则心无形;理与事一,则理无形;事与境一,则事无形;境与时一,则境无形。无形之道至矣乎,吾强而名之,曰‘太虚’”(84),写道“钟,虚也而鸣;心,虚也而灵;耳,虚也而听;目,虚也而视;四支百骸,虚也而运掉”(85)。除此之外,他还把这种“虚无”、“虚灵”理所当然地归之于“不囿于形”的形上之“道”(86)。凡此种种,使刘宗周对“虚无”的理解,以其之于“意”的可能性的发明,以其这种可能性直切身心之“我能”,不仅超越了“有无之辩”的老庄、魏晋玄学家之思,就是以张载“太虚论”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理论也难以与之比肩。 3.作为“生意”的“意” 正如梅洛-庞蒂坚持“身体意向”的“我能”乃为一种“生命的一种原则的可能性”,从而“身体意向”也即“生命意向”那样,刘宗周从“意”的“几微”出发,亦为我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故他指出,“只此一点微几,为生生立命之本。俄而根荄矣,俄而干矣,俄而枝矣,俄而叶矣,俄而花果矣。果复藏仁,仁复藏果。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尾。是故知死生之说,是故知无死无生之说”(87),在另一处他还指出,“曷为天下《易》,曰‘心’。心,生而已矣。心生而为阳,生生为阴,生生不已,为四端,为万善。始于几微,究于广大”(88)。这样,在刘宗周的学说里,其“心意”之“意”已不啻为“生意”之“意”。故他称“心如谷种,仁乃其生意,生意之意,即是心之意,意本生生,非由外烁我也”(89),称“人心如谷种,满腔都是生意,物欲锢之而滞矣。然而生意未尝不在也,疏之而已耳”(90),称“当其(指怵惕恻隐之心)未感之先,一团生意原是活泼泼地也”(91),称“满腔子生意流行,自有火燃泉达而不容己者,又何患天地万物不归吾一体乎?此古人务本之说也”(92),并言“观春夏秋冬,而知天之一元生意,周流而无间也。观喜怒哀乐,而知人之一元生意,周流而无间也”(93)。 这种以“生”训“意”,不仅以其作为《易传》的“言不尽意”和“立象尽意”意象之“意”的概念的理解,可视为是对中国古老的大易的“生生”之旨的重揭,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以《大学》的“诚意”说为思想桥引,为我们实现了宋明时期的新儒学学说与大易之道的真正的理论对接。因此,随着刘宗周对“生意”之“意”的发明,在他那里,正如其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94),人性已成为生之性;“生机之自然不容己者,欲也”(95),人欲已成为生之欲;“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96),恻隐之心已成为生之心;“浩然之气,即天地生生之气”(97),浩然之气已成为生之气;“诚则通,诚则复,即天命之不已也”(98),诚之道已成为生之道;“父母虽不在,吾身即父母之身,身在即父母在”(99),我的身已成为生之身。于是,“吾这里纯是生生不已之机”(100),故刘宗周的“生意”之“意”的推出,带给我们的与其说是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孟子式、明道式的“以心著性”,不如说是对佛释的“死寂”之说的力辟,不如说是“援易于儒”,使沉睡千年的大易的“生生”之旨再次复明于世,并贯彻于宋明新儒学的一切论域,而成为该学说真正的不二之谛。 4.作为“不贰”的“意” 一旦我们把“意”视为一种“始于几微,究于广大”的“生意”之“意”,那么,这不仅意味着“生生”成为意之所以为意的东西,而且还意味着“为物不贰”,整个世界都一统于“意”,一统于“生意”之“意”。正是在此意义上,刘宗周宣称“意者心之主宰”(101),宣称“物有本末,惟意该之;事有终始,为诚意一关该之”(102)。在他看来,这种“为物不贰”,一如米粒为根芽,为苗叶,为结实,虽形态各异,却始终生意不改、生意一以贯之那样(103)。同时,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他明确提出“意”是“即主宰即流行”(104),“言所发而所存在其中”(105),也即其以“意”为中枢、中介,为我们彻底消解了中国哲学论域中形上与形下、未发与已发坚执的二元,使宋明理学所力倡的中国古老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思想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这样,在刘宗周的“意”的学说里,我们同样看到了一种梅洛-庞蒂式的“意义的统一”,这种“意义的统一”使刘宗周发现儒家《大学》的“意”,乃至与释氏的“佛法大意”不期而遇了,尽管他不否认释氏的“唯心主义”使二者的宗旨最终判若云泥。故他写道:“释氏视意为粗根,然根尘相合,以意合法,可知佛法都括在意中,故曰‘佛法大意’。但佛氏推宗于觉,故尊视其心而遁于空,以意夷之六根。岂知离意无法,离法亦无心无觉。”(106) 我们看到,刘宗周的“意”的这种不贰之谛不仅使整个世界归于一统,也使势如水火的“理学”与“心学”之争成为地地道道的“伪问题”。一方面,“理学”代表的朱子以“道问学”为宗,“表章《大学》,于格致之说最为吃紧,而于诚意反草草”(107),另一方面,“心学”代表的阳明则以“尊德性”为宗,虽于《大学》的“诚意”之旨大力提撕,却“将意字认坏,故不得不进而求良于知。仍将知字认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于心”(108)。故无论是“重知轻意”的朱子,还是“重意轻知”的阳明,他们都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他们都远离了作为“一贯底血脉”的《大学》的真理。因为作为“一贯底血脉”的《大学》告诉我们:“好即是知好,恶即是知恶,非谓既知了善,方去好善,既知了恶,方去恶恶。审如此,亦安见其所谓良者?乃知知之与意,只是一合相,分不得精粗动静”(109),换言之,“《大学》曰诚意,曰致知,其旨一也。要之,明善之善,不外一诚,明之所以诚之也;致知之知,不离此意,致之所以诚之也。本体工夫,委是打合”(110)。如此,基于这种“意”的一元论,刘宗周在使中国古老的不虑而知的“良知”得以真正深入发明的同时,也为我们推出了超越“理学”与“心学”、朱子与阳明的宋明新儒学的“第三条道路”,“阳明以朱子为支离,后人又以阳明之徒为佛、老,两者交讥而相矫之,不相为病。入《大学》之道者,宜折衷于斯”(111)。而究其故端,这种“第三条道路”之得以推出,与其说一如牟宗三指出的那样在于所谓“以心著性”,不如更确切地说,恰恰在于宗周学说之为宗周学说的所谓的“以意著性”。惟有“意”,才是宗周学说之既有别于朱子学又相异于阳明学的东西。 5.作为“大身子”的“意” 刘宗周“意”的这种“不贰之谛”,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它既以其即显即微,为我们导向了“心”与“物”、“心”与“理”的统一;另一方面,它又以其“诚于中,形于外”,使“心”与“身”的二元论得以真正的消弭。关于后者,他指出“如内有阳舒之心,为喜为乐,外即有阳舒之色,动作态度,无不阳舒者。内有阴惨之心,为怒为哀,外即有阴惨之色,动作态度,无不阴惨者。推之一动一静,一语一默,莫不皆然”(112)。指出“无形之名,从有形而起”(113),指出“由此仁义礼智根于心,自然有生色之妙”(114),并指出“道体本无内外,而学者自以所向分内外。所向在内,愈寻求,愈归宿,亦愈发皇。故曰:‘君子之道,圈然而日章’。所向在外,愈寻求,愈决裂,亦愈消亡。故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115)。在他看来,这种合内外之道也即古人的“诚意”的“诚”之道,“诚则必形。有诚者,天道之形。有诚之者,人道之形。天道之形,见乎蓍龟,动乎四体是也。人道之形,睟面盎背,施于四体是也”(116)。对于刘宗周来说,这种“诚则必形”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反身而诚”,也即惟有身的体现才是“诚”的体现,还有身的“动与万物共见”,身成为梅洛-庞蒂式的“走向世界之身”,也即刘宗周所谓的“大身子”之身,“自圣学不明,学者每从形器起见,看得一身生死事极大,将天地万物都置之膜外,此心生生之机,早已断灭种子了。故其工夫颛究到无生一路,只留个觉性不坏,再做后来人,依旧只是贪生怕死而已。吾儒之学,直从天地万物一体处看出大身子。天地万物之始,即吾之始;天地万物之终,即吾之终。终终始始,无有穷尽,只此是生死之说,原来生死只是寻常事。程伯子曰:‘人将此身放在天地间,大小一例看,是甚快活。’予谓生死之说正当放在天地间,大小一例看也。于此有知,方是穷理尽性至命之学”(117)。 正是这种“大身子”,才使刘宗周与他的“心包天地万物之外,非一膜之能囿”这一命题一致,提出“身在天地万物之中,非有我之得私”(118)。也正是这种“大身子”,才使刘宗周把家国天下的兴亡视为个体生命的兴亡,抱着“吾与汝偕亡”的决心,用自己的绝食而死为明的国之殇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生命之绝响。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刘宗周的“始于几微,究于广大”的“心”,与他的“与天地万物共始终”的“身”其称虽异,其指却一。而这种“一”也即其“诚意”的“意”。无怪乎他就阳明的《大学》之解的支离之失指出:“岂知诚意章言‘德润身,心广体胖’,将身心二字一齐俱到乎?”(119)并在另一处地方径直宣称:“修身为本,正是诚意为本也。”(120)这一切不正表明了,如前文业已点出的那样,刘宗周的“诚意”之“意”既是所谓的“心意”之“意”,又不失为所谓的“身意”之“意”,而与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之“意”几乎别无二趣吗?值得一提的是,囿于王学的“心学”传统和当时的谈辩语境,在刘宗周的学说里,这种“身意”之“身”的思想并未得以真正充分的表述,只是殆至后理学的王夫之的学说的兴起,随着其对“心学”的彻底清算,随着其从现象学式的“天有显道”到“即身而道在”的命题的标举,该思想才在中国哲学史大张旗鼓地被正式祭出,尽管不无遗憾的是,王氏的学说对“意”的概念本身并未像宗周那样,给予足够的论及和关注。 这样,正如《大学》以“诚于中,形于外”喻指“慎独”那样,这种作为“大身子”的“意”也恰恰是刘宗周极力推重的“慎独”之“独”。在刘宗周的学说里,“慎独”之“独”之为“慎独”之“独”,不仅在于它是为物不二的一,还在于独乃宇宙不可诘致之究极,“独便是太极”(121),而这种“太极”,也即他在《读易图说》里所谓的“始于几微,究于广大。出入无垠,超然独存,不与众缘伍,为凡圣统宗。以建天地,天地是仪;以类万物,万物是宥。其斯以为天下极”(122)。于是,在刘宗周那里,随着把“意”与“太极”联系在一起,一种终极性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意”即顺理成章地推出了。无疑,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深入而准确地为刘宗周学说属性和宗旨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就理论的纵向发展而言,它意味着刘宗周的学说的兴起,实际上代表了宋明新儒学从“理”本论向“心”本论,再向“意”本论的战略性转移,并标志着至此一种牟宗三所谓的不无圆融的儒家“道德形上学”体系的真正确立。另一方面,就理论的横向比较而言,它意味着,刘宗周从“意”走向“大身子”的“身”恰如梅洛-庞蒂从“意”走向“普遍性的存在”的“身”,以对“身本论”的共同归依,二者在理论上再次深深地相契了。 如前所述,我们已经探讨了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与刘宗周的“意”的学说二者之间理论的一致性,一种几乎妙合无间的一致性。但意犹未尽的是,一种真正的中西哲学的比较不仅要论及二者之间理论上的“同”,还要不忽视二者之间理论上的“异”。而后一点正是我们文章即将收笔之际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法国哲学史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曾提醒我们,在研究哲学思想史时,应意识到作为哲学论述(discourse)的哲学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之间的差别。如果说前者更多涉及“世界是什么”这一思辨的学问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多涉及“我应该如何做”这一修身的工夫。这一差别,既对阿多所关注的以抽象的本体理论为旨的西方一般哲学与以切身的精神修炼为旨的希腊化时期哲学二者之区分通用,也对我们所涉及的传统的中西哲学二者之对比成立。换言之,较之传统的西方哲学,就其主导的取向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与其说是长于思辨的学问的话,不如说是以修身的工夫而取胜。这一点,无疑也在宋明新儒家之代表的刘宗周的学说里打下了深深的理论烙印。 也就是说,刘宗周的“意”的学说实际上是一种亦本体亦工夫的学说。一方面,作为“大身子”的“意”,既使“意”作为“独体”而成为宇宙至真的“太极”,又“惟人有极”(123)地使“意”作为“独体”而成为人之至善的“人极”。故宗周反对阳明“四句教”中“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认为这种“意”决定了人性有善无恶,其是至善的滥觞和栖居之地。但另一方面,作为“大身子”的“意”同时又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以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方式使我们置身于整个大千世界尘世之中的同时,又使我们不得不置身于种种社会历史的习染里。而这种“迁于习”决定了“性相近,习相远”,决定了我们“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斯日远于性矣”(124)。此即刘宗周所说的“人生有此形骸,便有此气质”(125),并由此就不能不使他在坚持“性善”论的同时,把“变化气质”的修身工夫提到了议事日程,并且与“诚意”之“诚”一致,把“慎独”之“慎”这一道德修为作为修身的不二法门。 为刘宗周本人所推重的其《人谱》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他称“总题之曰《人谱》,以为谱人者莫近于是”(126),也即“人谱”之为“人谱”,旨在于“从深根宁极中证人”,教人如何成为一个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人。故《人谱》开篇的《人谱正篇》里,在“人极图”的名下,他告诉我们的是,就本体而言,真正的人如何从“意”之“独体”的人极出发,以一种“分为二五,散为万善”方式,其本身乃为“大身子”的人。继而,在《人谱续篇》里,他告诉我们的是,在现实的语境下,为了成就为这种“大身子”的人,就工夫而言,我们应该采用哪些具体的方法和手段。由此就有了“续篇一”中“证人要旨”的“六旨”(一、凛闲居以体独,二、卜动念以知几,三、谨威仪以定命,四、敦大伦以凝道,五、备百行以考旋,六、迁善改过以作圣),就有了“续篇二”中“纪过格”的“六过”(一、微过,二、隐过,三、显过,四、大过,五、丛过,六、成过),以及“讼过法”和“改过三说”。 在这里,我们既看到了做人的依据,又看到了做人的途径,并且二者是如此的协调一致,以至于正如在“证人要旨”和“纪过格”那里所表明的那样,随着无极而太极→动静→五行→物物→无咎的依次展开,它使宗周的工夫论完全与他的“人极图”同构同步,以其逻辑上的一一对应和层层递进,而与本体论成为“天生人成”的毫无滹缝、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正是基于这种本体与工夫完全的合一,我们在看到了刘宗周对先天人性之善的坚信的同时,也看到了刘宗周对后天人性之扭曲、人之过恶的正视。也正是基于这种本体与工夫完全的合一,使刘宗周不无理由地得出,虽然世风日下,人心浇漓,虽然人兽几希,但是每一个人心中的“独体”却是永存不泯的,只要我们立足于斯,并坚持在迁善改过上做功课、下工夫,我们就可以循序渐进一步步地成就为人,甚至可直跻那种为横渠所指向的民胞物与的圣域。 这也即是《人谱》中刘宗周为我们推出的“慎独”说。由于本体与工夫的并重,由于将本体与工夫彻底打并归一,这使“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黄宗羲语),使儒教的内圣之学、成德之教,“至蕺山而为更深度更完备地完成”(牟宗三语),也使宗周学说上宗《论》、《孟》、《易》、《庸》,中接濂溪、横渠、明道,标志着中国式的学、教合一“圆教下的道德形上学”的正式奠定。实际上,这种“真功夫”的“慎独”说的推出,乃是对王学后学所流于的工夫论的缺失乘弊而起、奋力纠拨的产物。正如他在《人谱》的“自序”中指出的那样,“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沦于虚无,以为语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于功利,以为语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则皆远人以为道者也”(127)。此即其所谓的“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虚玄而夷良于贼”。不难看出的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都是将王学一味禅学化的结果,一者“情炽而肆”地极倡“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而悬崖撒手、收拾不住地流于人所侧目的狂禅;一者则一如我们在龙溪之学中所看到的那样,貌似玄妙高洁,却以“不思善”、“不思恶”的无念为宗,坚持“良知”乃“自见天则,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以一切笃信谨守,照管安排之事皆为犯手做作,从而同样遁入那种“心性本净,见性成佛”、“道是平常心”的禅门之说。 无独有偶的是,这种对工夫论的无视,既为中国明代的王学后学学说所特有,也在现代梅洛-庞蒂的学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就是说,在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学说里,一种以“意”为宇宙之本的“意本论”思想的确立,虽然使人自身的先天的自足性在哲学史上得到空前的彰显和标举,从而使梅氏对人自身的“良知良能”是如此坚信不疑,以至于他不仅提出我可以自发地“用身体知道”而使身体实际上成为“沉默”的,而且提出我可以自发地“用身体行动”而使身体实际上成为“跛足”的,但和王学后学一样,这种对人自身的自足性的高度肯定,同时却是以对人自身的后天的非自足性置若罔闻、视而不见为补足、为牺牲的。这使他虽然也承认和强调“习惯”的力量,并把其理应如此地视为我们自身“良知良能”得以成立的基础和前提,却认识不到“性相近,习相远”这一事实,认识不到好的积习可以通向人的真知善行,而坏的积习则使我们对谬误和恶迹亦步亦趋,并最终将使他苦心孤诣所发掘出的那种本体论的至真至善的“身体意向”的存在沦为乌有的虚无。 这一切告诉我们,一如西方一般的传统哲学,在梅氏的学说里,由于仅仅停留于纯粹理论的慧观,东方式的强调身体修为的工夫论思想实际上同样是毫无立足之地的,从而它也使我们意识到,虽然梅洛-庞蒂学说与刘宗周学说同样以“意”为本体,但二者看似近在毫厘却难掩其真正宗旨之失之千里,并从中以一种典型的理论个案反映出中西哲学之间固有的深层差异。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现代西方身体哲学阵营中有同室操戈的舒斯特曼学说异军突起,明白了为什么舒斯特曼对梅洛-庞蒂的“沉默的”和“跛足的”哲学的力辟,以及其从身体的理论思考义无反顾地走向身体行为训练和修习。一方面,既是对西方希腊化时期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的积极复兴;另一方面,一如他自己所坦诚告白的那样,是对以“修身为本”的中国古老哲学传统的忠实皈依(128)。 注释: ①②③⑦⑧(22)(24)(30)(33)(34)(35)(36)(40)(50)莫里斯·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杨大春、张尧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44、236、247、248、19、242、235、233、234、242、266、297、243、242页。 ④(13)(14)(16)(17)(18)(19)(20)(23)(25)(28)(29)(31)(39)(42)(43)(44)(45)(46)(47)(48)(49)(51)(52)(53)(54)(55)莫里斯·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18、379、74、83~85、78、339、75、78、137、74、263、320、50、304、188、108、97、78、169、75、168、172、229、184、182、174、326页。 ⑤⑥⑩(11)(12)(15)(21)(26)(27)(32)(37)(38)(41)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8、181、183、299、129、218、261、124、31、181、319、191、373页。 ⑨莫里斯·梅洛-庞蒂:《符号》,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6页。 (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3)(74)(75)(76)(77)(78)(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1)(122)(123)(124)(125)(126)(127)《刘宗周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390、451、337、517~518、344、389、412、280、443、347、347、412、389、434、341、447、279、337、453、469、387、409、517、410、425、462、462、471、136、468、429、341、488、518、178、279、182、314、523~524、536、536、447、468、468~469、442、442、344、451、318、444~445、453、415~416、514、375、309、402、323、394、347、481、136、137、311、310、2、1页。 (71)(72)(79)(111)(120)《刘宗周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52、49、649、648~649、617页。 (128)关于舒斯特曼对中国古老大哲学传统的积极评价,可参看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表现》,王辉译,《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4期。以及Richard Shusterman,"Body Consciousness and Performance:Somaesthetics East and West",Thinking through the Body:Essays in Somaesthe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