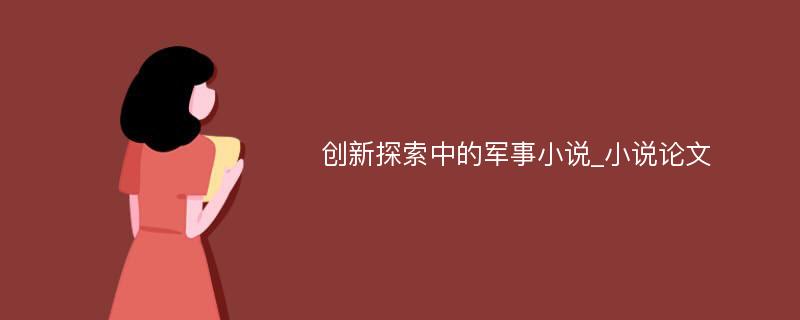
创新和探索中的军旅长篇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旅论文,长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多年里,军旅长篇小说创作有了较快发展,无论数量和质 量都有了可观的提升,虽然在同期的国内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内,军旅长篇小说与我们的 期望尚有距离,但是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毕竟迈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梯。我的这一看 法的主要依据在于,已有不少军旅作家对于长篇小说这种文体的认识、把握及开拓性探 索,与以往相比已经初步拥有了自觉的意识,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势。
长篇小说这种文体在人类社会中产生已有数百年,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化的形成阶 段,到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进入了一个鼎盛期,在中国和西方出现了一批被后人称 为“经典”的优秀作品。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人类生存世界的剧变,人们的生活形 态与思维形态日益繁复驳杂,长篇小说的内涵和形式自然也会发生许多时代性变化。但 作为一种走向成熟的文体,长篇小说业已形成的文体特征,它的一些区别于他类文体的 质的规定性,却是大致稳定、明晰的。比如说,长篇小说这种大型叙事文体与中小型叙 事文体之区别,并不单纯在于篇幅和文字的扩张,更在于它应当能涵括远为丰厚的艺术 内容,且往往可以从某些方面展示出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的时代变迁与历史命运。又如 ,长篇小说应当能创造出鲜活、饱满而多样的人物形象和生活景象,以承担其丰实的艺 术内容的充分表达与诠释,却不像中小型叙事文体那样只能选取有限的人物之有限的侧 面去进行艺术描写,只能展示社会与人生的截面或轮廓。再如长篇小说的艺术结构,更 是中小型叙事文体的较为单纯的建构样式所不可比拟的,它更像是一种由许多具体构造 有机地整合而成的精密严谨、浑然一体的建筑艺术。所以,对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特性 的认识和把握,应当是进入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作家所必备的前提条件。事实证明,能 够画好中短篇小说或其他文学样式者,却不一定能写好长篇小说,原因可能正在于尚不 具备此种文体意识。
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就曾显露出活跃状态,产生过一批较有生 气的作品,其中有些还是出自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成就显著的军旅作家之手。但是,这 个阶段的一些作品显然欠缺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必备要素,有的甚至是以写作中短篇的 习惯方式用于长篇创作,有的则是将有限的艺术内容抻长或膨化。这表明,不少军旅作 家在进入长篇小说创作之前的准备不足,尤其是对于长篇这类文体的认识和把握尚未到 位。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视野的开阔和实践的积累,上述状况才逐步有所改观。军旅 长篇小说创作在近些年来的明显长进,除去诸种客观因素之外,确实与军旅作家对于长 篇小说这一文体的认识与把握的增强密切相关,而军旅长篇小说的进一步提升和跨越性 发展,则有待于继续深化对这一文体的认识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开拓性探索。这 里,不妨联系一下近些年军旅长篇小说的创作实践,就上述话题作一个考察和表述。
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宏大叙事文体,其大容量、高密度以及较为宽广的时空领域,为作 家表达他所认识的社会生活和人生经验提供了较之中小型叙事文体远为开阔的天地,同 时也为作家充分抒写自己对生存世界的思考和展现自由创造精神提供了更大的艺术空间 。长篇小说的较大容量,包括其涵纳的生活容量和思想容量,应当是这种文体的要素之 一。以往有些军旅长篇小说之所以看起来不似长篇,却像是拉长了的中短篇,正是由于 欠缺这种文体所应有的较大容量。近些年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随着文体意识的增强, 对于长篇的容量这一要素的把握作出了努力。可以看到,不少作品的艺术构想力图拉开 较大的时空距离,以铺展人物与故事的从容叙述,并在这种叙述中融入较多社会的历史 的和人性的内容。有些叙写老军人传奇故事的作品,并不着意于其戎马生涯的传奇色彩 的渲染,而是在社会历史的剧烈动荡中展示其生活命运与精神操守,或是在战争与和平 的不同环境下,揭示人际关系中人格与情操的对峙与冲撞,使得较为单纯的传奇故事获 得了更为丰盈的社会生活容量。也有些作品尝试采取家族故事模式,由同一家族中祖孙 、父子之间的隔膜、认同或悖反的情感纠葛的描绘,展现几代人的生活道路与人生追求 在社会历史变动中发生的差别与变异,使得家族故事的叙述中涵括了更多的时代历史内 容和生活的思考。
长篇小说的容量自然不是可以自由扩充、随意添加的东西,而应由作品的创作意蕴和 艺术主旨所决定,为其所需要所能包容的东西,它必须是为着丰富和深化作品的艺术主 旨而精心选择制作的有意义的艺术内容。否则,就可能成为艺术的赘疣。况且,一部作 品容量的大小,不仅在于文本中呈现出的东西,还在于文本中潜在的容量,即作品的具 象化内容和艺术概括力如何。一部优秀的作品,往往能够透过其展示出来的艺术内容, 概括地反映出一个时代或一段历史的某些带有普遍性或本质性的社会特征与生活走向。 此种艺术概括力,正是使作品的容量和艺术价值得以延伸扩展放大的一种艺术能量。近 些年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在注重把握作品的容量、以不同类型的叙事方式呈现较为丰 盈的艺术内容方面,确有明显长进。不仅如此,有的作品还通过一群当代军人面对军队 建设新课题所产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冲突,力求揭示时代现实中有变革意义的生 活脉动,对于某种昭示着生活走向的事物作出锐敏的艺术概括。不过,从整体来看,这 一时期的军旅长篇小说由于受到作家的生活视野与生存经验的限制,大多仍欠厚重与繁 富。有的只能在故事框架设定的范围内展开特定的生活描写,而难以容纳军旅和社会的 更为深广的生活内涵;有的则较为靠近以往同类作品曾涉及的生活层面,虽可见角度和 侧重的差异,却未能对历史与现实的军旅生活内涵作出更有深度的多层面的开掘。而追 求作品内蕴之较大的艺术概括力,使作品的艺术内容和艺术形象能够超越题材范围的限 定,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尚有待于军旅作家们韧性地努力。
人物形象的艺术创造不只是长篇小说这类文体的一大要素,甚至可称作长篇小说具有 的全部思想艺术含量的一个支点。人们熟知的经典性长篇小说,从《三国演义》到《红 楼梦》,从《堂·吉诃德》到《复活》,无一不是由于人物形象的成功创造而使作品长 久流传下来的。长篇小说的人物形象创造,显然不同于中小型作品里的人物描写,它并 不限于人物生活历史的一个片断或人物性格的某种侧面,却应展示人物性格与生活命运 的发展历程,要在时间和空间的延展变换中从诸多层面上去塑造人物形象。一部有价值 的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但可以涵括较为丰富的社会历史生活的内容和形态,甚至 能呈现出一定时代的某些特征性的东西。近些年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在人物形象的创 造上取得了应予称道的成果,比如,单是老一代军人的艺术形象就有关山林、方英达、 梁必达、周汉以及那个无名的地下工作者“爷爷”等,此外还有一些各具特点的少壮军 人形象。从对于这些军人形象、特别是几个老军人形象的塑造中,可以看出与以往的军 旅长篇小说有许多不同之处。首先是作者们大都与其所写人物存在着年代相隔的距离, 但是这种距离也会产生美感,容易将人物原有的色彩层次看得分明,且能采取冷静平视 的叙写姿态。因此,在小说中不仅有对人物最具特征的个性化描写,同时又呈现出人物 性格面貌的多种色调,人物描写的本色和多彩,反而拉近了与当代读者的距离。其次, 这类老军人形象虽然不少具有传奇色彩,但却并不对此刻意渲染,而是注重从人物生活 历程的描叙中展示社会历史的变迁和人物命运的沉浮,并融入较多的人生思考。关山林 等老军人形象的出新之处,正在于写出了这种颇具沧桑感的人生命运以及蕴含其中的某 些历史生活况味。此外,对于一些少壮军人形象的刻画,则较为注意把握这一代军人身 上的某些时代性变化,往往通过少壮军人之间的价值理念、人格追求乃至社会身份意识 的对比与冲撞,展现这一代军人不同类型的性格面貌。
对于近些年军旅长篇小说在人物形象创造方面的成绩,既应充分估价,又须估价适度 。因为,这是不少新一代军旅作家开始有意识地操练长篇小说这种文体的起跑阶段,其 准备和经验毕竟不足。事实上,不少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创造尚带着各自的弱点和缺欠。 比如,有些作品偏重于人物外在性格的描绘,而较少对人物精神内质的揭示,有些作品 则专注于人物在特定场合、特定事件中的思想情感、行为方式的刻写,或某种心理重负 的反复渲染,却忽略了在日常生活里对人物原本丰厚的思想性格面貌作多方面的纵深刻 画,不少作品的人物描写尚未能由个性化层次进入到心灵化层次,等等。这自然有艺术 经验不足的原因,但与作家对于所写人物的深度认识和把握尚欠功夫,与作家自身的此 种生命体验不够饱满甚为相关。
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在时代发展中不断产生新的艺术表达方式和形式因素,变换和充实 着它的形式面貌。近些年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较为重视吸取这些新的艺术养料,在艺术 表达方式上进行某些探索和创新尝试。有些作品对于艺术视角和结构方式的择取与构建 ,力求冲破以往那种拘谨的单一选择惯性和线性叙述样式,而采取新的视角或多种视角 的交错转换,以切割和拼接时空的结构样式将漫长的历史生活压缩于简约的故事叙述之 中。有些作品还能自如地运用潜意识、幻觉等表现手段,来刻画人物在特定状态下的心 理动势。不少军旅作家在坚持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同时,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某些 有效的表现方式融汇起来,以扩展自己的艺术表达能力,丰富作品的艺术面貌。从近些 年看得到的军旅长篇小说中,确能让人感到其艺术面貌正在不断更新。
不久前,有的学者在研究分析90年代以来国内长篇小说的现实状态时,曾指出其在艺 术探索上有超越发展,而在精神探索上却普遍不足,欠缺相应的精神含量,存在着艺术 探索与精神探索不平衡的现象。这种看法大体是准确的,因为有许多文学事实可以佐证 。不过,就近些年的军旅长篇小说而言,似乎尚不存在这种不平衡的明显迹象。也许是 由于在艺术探索或精神探索方面,近些年的军旅长篇小说均未能出现远胜于另一方的超 越性发展,或者可以说,在这两种探索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力度。既然军旅长篇小 说创作已经进入了起跑阶段,必定会有加速跑和冲刺阶段的来临。期待着军旅作家们再 积蓄力量,争取在下个阶段跑出更好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