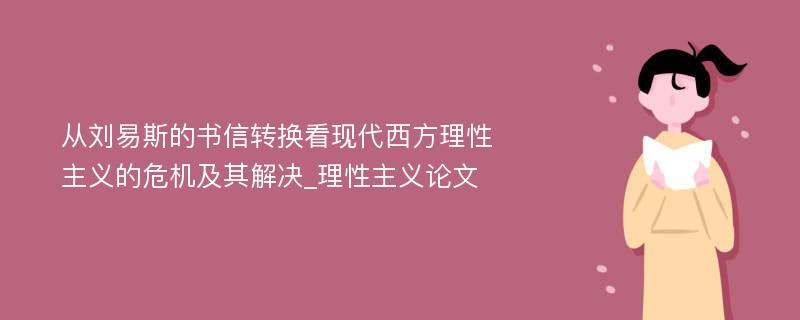
刘易斯转信事件折射出的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危机及其解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主义论文,折射出论文,刘易斯论文,危机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英国当代学者,写作了许多的文学评论和许多反映其精神变迁的著作,创作了大量蕴含基督教思想的文学作品。刘易斯是一位学者,一位思想家,一位文学家。刘易斯在语言学研究领域的著作有七部,代表作为《牛津16世纪英语文学史(不含戏剧)》(1954),《语词研究》(1960);在现代语境中阐述基督教教义的护教作品近二十部,代表作为《地狱来鸿》(1942),《圣诗撷思》(1958),《四种爱》(1960)等;文学著作近二十部,代表作为星际三部曲和纳尼亚系列。本文以刘易斯转信这一个案为基础,来解读西方社会的民众对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重新认识。通过解读,作者认为透过刘易斯转信体现出来的西方社会反理性思潮的升温是20世纪西方社会对理性主义思潮进行“社会反动”的外化表现。
一、刘易斯重新建立宗教信仰的历程
刘易斯于1898年11月29日出生在爱尔兰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家庭,刘易斯的父亲阿尔伯特(Albert)与母亲弗罗拉(Flora)都有着在当时普通人看来较为渊博的知识,这使得刘易斯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柯克(William Thompson Kirkpatrick),刘易斯亦称其为了不起的诺克(the Great Knock),是另一位在刘易斯的青少年时期对其产生过重要作用的人。刘易斯从父母和柯克那里不仅打下了自己在古典主义研究方面的坚实基础,而且还充分地发展了具有高度逻辑性的理性思考能力,成为了一个理性主义者。
1917年,刘易斯离开柯克来到牛津求学。此后刘易斯的一生基本在牛津度过。①
在牛津,刘易斯完成了自己从无神论者向基督教信仰者的转变。最初来到牛津的刘易斯仍然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一位无神论者。这一点可以从他这一时期关注的学术思想的范围和他讲给阿瑟(Arthur Greeves)的一个故事中看出。
在1919年3月2日写给阿瑟的信中,刘易斯讲道:
“我依然在读哲学著作,已经快完了。斯宾塞、威廉·詹姆斯等人的作品远没有洛克和巴利(Paley)的作品好懂。”②
在1920年2月3日写给阿瑟的信中,刘易斯讲了这么一个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
“谈话主要在我与贝克之间进行的。我们主要谈论了鬼、精灵以及神的问题。……我有了一种自童年以来从未有过对神灵存在的恐惧感和因此产生的厌恶感。他可能有点神经不正常。”③
从信件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刘易斯在这一时期感兴趣的依然是将理性主义在英国推向极致的思想大师,如斯宾塞。刘易斯在这一时期对于宗教信仰所采取的方法是依据自己从理性主义思想家那里获得的知识将其处理为对神灵的崇拜。他的这种认识与19世纪理性主义思想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他采取排斥宗教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到了1931年刘易斯就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基督教信徒。
总体而言,刘易斯在1919年至1931年期间发生的信仰转变是他在20世纪中前期西方社会理性主义思潮与后理性主义思潮的斗争中自主抉择形成的。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刘易斯从理性主义向后理性主义的认识转变呢?莱莉·多塞特认为,转信基督教对刘易斯最大的帮助在于给他的写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从此刘易斯写出了众多的学术以及文学作品,成为一名成功的学者。④
莱莉的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看是对的。转信之前刘易斯仅仅出版过两本著作:《精神的结合》(Spirits in Bondage)和《戴玛》(Dymer)。转信之后,如果从反映其转信思想历程的寓言式自传《朝圣者的回归》算起,一直到他最后一部著作《给马尔柯姆的信:关于祈祷者》为止,刘易斯在30年中出版了37部著作。我们从数据对比可以看出转信前的刘易斯创作的作品是远远低于转信后的。但是莱莉的这种认识只是一种表层的认识。因为刘易斯不是为创作而转信的,而是因为转信而改变创作。创作上认识角度的变化带来的论著丰产是转信带来的后果而不是转信的目的。
二、对刘易斯转信所折射出的西方信仰复兴思潮的探析
刘易斯的转信意味着什么呢?毫无疑问,20世纪西方社会的民众对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了重新认识,而他的转信正是这种重新认识的外化。
刘易斯的转信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历史事件。
首先,作为个人的认识行为,刘易斯对上帝信仰的重新建立使自己认为通过皈依上帝已经正确处理了永恒与断裂的关系,从而获得了自己心灵的平静,走到了自己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从这种意义出发,在1931年9月28日确立对上帝的信仰之后,刘易斯认为自己得到了上帝的拯救。
刘易斯转信事件的第二个层面在于其社会行为层面。
20世纪的西方,理性主义在思想界的高峰在现代社会对宗教的认识上可以得到体现:19世纪以来,理性主义者对宗教的认识是,现代宗教问题事实上是由神的存在问题向神的观念问题转变的问题;宗教只不过是社会的异化,是人的观念产生的而且成为了压迫人的工具。19世纪以来,理性主义者还认为:历史不是宗教的,而宗教却是历史的,宗教是一个存在于历史环境中的概念,不是一个普适的概念;并认为人的解放是政教分离,即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使人摆脱宗教成为社会的主体,这种真正的解放只有在未来社会中才能实现。
当然,在理性主义高唱凯歌的同时,许多学者已经开始举起了自己的旗帜,以怀疑的眼光去观察理性主义者过度拔高理性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引导作用的做法。⑤ 例如,舍勒在宗教哲学方面强调宗教关爱对社会的作用;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卡西勒、克罗奇以及克林武德等在历史学、历史哲学领域内开始清点实证主义过度强调理性主义这一做法对历史学造成的不良影响;俄国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就以日记体小说的形式向世人揭示了理性控制人类所造成的恐怖。
但是在当时,这种疑虑相对于理性主义者强大的呼声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得理性主义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精确预言成为了社会认识的主流。这些理论的提出使当时的学者陶醉在人类已经能够通过理性全面把握社会,设计未来发展的迷梦中。人类似乎已经能够摆脱上帝。于是思想家们宣判了上帝的死刑。而由科学带来了物质高度丰富的社会也默默接受了这种对上帝的宣判。
可是上帝缺席之后,20世纪的人类社会发生了什么巨大的变化呢?20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并未向充满理性且又美好的方向发展,反而使西方争夺主导世界控制权的野心膨胀了,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战争对欧洲来说是巨大的灾难。
灾难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大战的悲惨后果使得西方充分认识到理性主义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还给人类带来了毁灭社会的能力。理性主义者的乐观理念被打破,社会开始了反思。人们记起了舍勒、狄尔泰、卡西勒、克罗奇、扎米亚京等思想家的预言。于是人们开始对认为社会可以按照类似自然科学规律的调节实现数字式精确发展的理性主义思想产生了怀疑。这一点被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妙新世界》这类的文学作品的广泛流行所证实。西方社会在精神方面也出现了社会整体认知从理性主义向后理性主义的发展。
后理性主义思潮的社会物质基础的成熟把后理性主义者的活动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此,后理性主义者拥有了实现其思想的社会阵地,不再仅仅局限于19、20世纪之交时后理性主义思想家的超前认识中。西方社会也开始正面回应后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挑战。
刘易斯正是通过他的著作,通过他于“二战”期间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系列演讲,通过他的精神世界向基督教回归的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理性主义者当年宣判上帝死刑是错误的,宣判上帝死刑的人必须收回自己的宣判,让上帝涅槃重生。刘易斯通过他的作品帮助许多同时代的人重新认识了上帝,走出了生活完全由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笼罩的阴影。由此,刘易斯转信事件实现了它作为群体认识行为的目标。
我们可以由此作进一步的探究,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刘易斯转信还是西方现代社会思想发展里程中的一道风景。存在两种社会思想之间的斗争,一种是反对将理性与科学理念贯穿于人类社会治理的社会思想,一种是承袭了启蒙运动传统、试图以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理念治理社会的社会思想,刘易斯的转信代表着前一种思想在这一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证明社会发展在理性之外还需要人的关怀,后理性主义者的质疑因此而逐渐成熟。
注释:
① 刘易斯的家位于牛津的东部。刘易斯称其为The Kilns。刘易斯自1933年秋季学期起经常在家中与具有相同信仰和爱好的朋友讨论宗教、学术以及文学等问题。后来的研究者们将经常在星期四晚上参加刘易斯家庭学术聚会,和星期一或者星期五的午餐前在鹰与儿童俱乐部(The Eagle and Child)的一间屋子中参加学术聚会的具有相近学术思想的学者们,诸如托尔金(J.R.R.Tolkein)、雨果·戴森(Hugo Dyson)、沃伦、查尔斯·威廉姆斯(Charles Williams)、罗伯特·哈佛(Dr.Robert Havard)、维威勒(Weville Coghill)以及欧文·巴费尔德(Owen Barfield)等称为启示学派(the Inklings)。启示学派的这种学术交流一直持续到1949年。
② Walter Hooper,ed.,C.S.Lewis:Collected Letters,Volume 1,Family Letters 1905-1931,p.440.
③ Ibid.,p.473.
④ 详细论述可见于Lyle W.Dorsett,ed.,The Essential C.S.Lewispp.7.-9.
⑤ “格奥尔格·卢卡契曾经说过,1848年是一个转折点,在它之后,西方资产阶级趋向反动衰落,西方文化也随之由理性转向‘理性的毁灭’”。相关论述可见于卞谦:《理性与狂迷:二十世纪德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