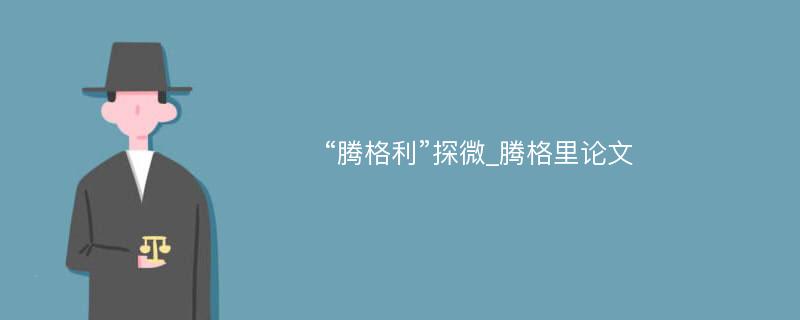
关于“腾格里”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腾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蒙古语“腾格里”,意思为“天”。关于这个词,学术界一般认为是经过畏吾尔人进入蒙古的突厥语词。我们目前还不太清楚蒙古人开始使用这个书写与发音并不一致的词以前究竟是用什么词来表述“天”的。蒙古语中“阿噶尔”、“噢格特日贵”之类的词有时虽也能表示“天”,但是多数情况下前者指“气候”,后者指“虚空”,其意不像“腾格里”那样专一。“腾格里”一词变复数时指的不是“天”,而指“众神”。“阿噶尔”、“噢格特日贵”均无此功能。因而,在过去人们信奉诸多天神的年代,“腾格里”一词不但出现频率高,而且还增加了几分神秘色彩。诸如鄂尔多斯人的“十三阿塔腾格里”、布里雅特人的“西方五十五腾格里”和“东方四十四腾格里”,每每有非同寻常的本事而受人崇敬。尽管如此,从文献记载和信仰崇拜发展轨迹来断定,蒙古人对“天”的崇敬是从单一到众多、从自然到神灵逐渐演变而成的。换句话说,就是物质的客观的天常被精神的主观的天所取代。当然,问题也并非如此简单,特别是现在当我们回首审视那些众多“腾格里”时,会发现自然意义的天与萨满教和佛教中的天搅在一起,致概念混乱,难以辨别。本文就其中的几个代表者试为疏理。
一、关于“孟克腾格里”
蒙古族是一个崇敬上天的民族,这一点早被初次踏入幅员辽阔蒙古境内的西方使者和传教士注意到,如约韩·普兰诺·加宾尼在他的《蒙古史》中写到:“他们相信只有一个神,他们相信他是一切可见和不可见事物的创造者,他是世界上的美好事物也是种种艰难困苦的赐予者。然而,他们并不用祈祷或赞颂或任何种类的形式来崇拜他。”[①]又如鲁卜鲁乞在《东游记》中和蒙哥汗的对话那样,汗说:“我们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个上帝,在他保佑下我们生活,在他保佑下我们死亡,对于他我们怀着一颗正直的心。”我说:“这是上帝本人的恩赐,因为,如果不是上帝的恩赐,那就不能有这样的情况。”蒙哥汗继续说:“我的话对你是不适用的。像我刚才说的,上帝赐给你们《圣经》,你们并不遵守它们。另一方面,他们赐给我们占卜者,我们按照他们告诉我们的行事,平平安安地过日子。”[②]上述引文中的“一个神”、“一个上帝”实际指的是一个意思,即“腾格里”。加宾尼和鲁卜鲁乞试图以为蒙古人相信的“腾格里”就是他们所相信的上帝,其实不然,蒙哥汗说得很明确,他们对保佑自己生存与生活的上帝是坚信不移的,这个上帝便是“长生天”——“呼和腾格里”(蓝天)或“孟克腾格里”(永恒的天即长生天)。我们从蒙古人的早期文献、碑铭、公文中常常读到的“长生天底气力”指的就是那个上帝。蒙哥汗送给路易国王的信中就写到:“这是长生天的命令。天上只有一长生天,地上只有一个君主成吉思汗——天子,”[③]这些叙述也吻合初到蒙古的汉族使者对他们的描述:“其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著。无一事不归之天,自大鞑主至其民无不然”[④]。在此必须重复的是,蒙古人平常对天冠以“呼和”、“孟克”、“德都”等字眼,纯属自然的客观的描述,强调了它的颜色是蓝的、性质是永恒的、位置是无上的,没有多少宗教色彩。人们也喜欢用这些词来给自己家乡的山水或子孙起名,但他们绝不因这些字眼而变得神秘。
对人类生存与生活乃至对他们整个生命起着直接、决定影响的客观条件莫过于天地,童年时代的人类还没有足够能力认识自己所处大自然瞬息万变的情况,无法弄清日月更替、天昏地暗、山崩地裂、风卷海啸等究竟出于何因,就以为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力量在操纵这一切,而这神秘力量又被一位超凡脱俗的主人主宰。在为生存而与大自然的长期拼搏中,逐步意识到顺自然者存逆自然者亡的道理,毁灭、死亡使人俱怕,兴旺生存使人喜悦,人们对大自然对天地的认识就是从如此盲目恐惧与崇敬的复杂心态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对周围环境天地、山川、河流、树林、飞禽、走兽以及人间万物的来龙去脉给予非常朴素、幼稚、可笑甚至唯心的解说,我们可以从不同种族与不同民族的神话传说中窥视这一人类认识活动进程的脉络。有的认为动物创造天地,有的认为半人半神的生物创造天地,有的认为神创造天地,有的认为妖怪创造天地,这种种说法就是人们对大自然进行探索的初始。中国最普遍的说法是浑沌生盘古,盘古开天地,女娲以土为人。[⑤]蒙古人的祖先没有留下有关开辟天地的清晰完整的神话。但是,他们却有把祖先的来历和上天连接一起的记载。众所周知,《蒙古秘史》开篇第一句便是:“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度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⑥]从《蒙古秘史》中的另外记载来看,不但蒙古祖先来自苍天,就是他们的猎物也来自苍天,如:“斡歌歹皇帝说。自坐我父亲大位之后。添了四件勾当……一件将天生的野兽。恐走入兄弟之国。筑墙寨栏住。致有怨言。”[⑦]世间万物中只有人和动物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生命,蒙古人以为他们(它们)的命运是由苍天来主宰和左右的,那么,对它产生恐惧和崇敬也就不奇怪了。蒙古人时时处处把自己言论和行动的结果用天意来审核,对了、成功了以为苍天给予恩赐,错了、失败了认为是长生天的惩罚。同时,还把那些奇特的梦幻、意外的征兆也归天意,倍加相信。一旦有限的生命结束,蒙古人称之为“腾格里宝勒宝”(变成天)、“欧德宝勒宝”(升上天)、“布而罕宝勒宝”(变成神了,产生这种说法较晚)等。当然,这里所说的“腾格里”和“布而罕”,与其本意完全不同,但是,也正因为这种人为“腾格里”不断增多使原来唯一“腾格里”的数量发生了变化。“布而罕”也如此。世间万物包括人的生命不断发生变化,生长与死亡,兴旺与毁灭无时无处不在。与此相比,唯一长生不变的便是苍天——“孟克腾格里”,这正是蒙古人崇敬它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蒙古人和“孟克腾格里”以及代表它的永恒颜色产生了不解之缘。“呼和”指的是蓝色,即天的永恒颜色,从前,蒙古人喜欢自称为“呼和蒙古勒”,此称里多少包含着他们崇敬苍天的余韵。总之,蒙古人起先时而认为那浑沌的“腾格里”是世间万物的主宰者,并把他人格化(叫天为父,叫地为母),时而又把它当做诸多神灵栖息的场所。但到后来“腾格里”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被人为宗教的领袖所代替,他们敢以“腾格里”称名便是例证。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腾格里”的神秘色彩不断减弱,渐渐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因而其受崇敬的程度也远不如从前了。
二、关于“胡日穆斯塔腾格里”
蒙古语中“胡日穆斯塔腾格里”的使用率曾经一度超过了“孟克腾格里”,萨满教和佛教信奉的万神殿里均有它的尊名,并常以“罕胡日穆斯塔”、“固沁固日班腾格仍额巾”(三十三天之主)、“胡日穆斯塔义日义孙腾格里”(九十九个胡日穆斯塔天)等形式出现。有辞书解释胡日穆斯塔为:“玉皇、上帝。胡日穆斯塔腾格里为玉皇帝”。[⑧]另外一部辞书除了上述解释外,还对其词源略有说明:“三十三天的最高天名,也称额色润腾格里。该词是经粟特借用的,据说有布而罕或真理之意。”[⑨]关于“胡日穆斯塔腾格里”的来源,诸学者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蒙古学者达木丁苏荣认为它是维语借词。[⑩]日本学者羽田亨认为回鹘人使用的“胡日穆斯塔”是借自伊朗,他写到“回鹘人西迁后不久就从摩尼教改宗佛教,他们在这种改宗中把摩尼教的思想带入佛教中,从而使人可看到这种混和合成之迹。如回鹘佛教中用摩尼教诸神之名来称诸天和恶魔之名,如梵天(Brahma)称(Azrua),帝释(indra)称(khormuzta)等。Azrua,是伊朗神Zerwan之音转,Khormuzta是ormuzd之音转。”(11)布里雅特学者班扎若夫认为胡日穆斯塔“这一观念是借鉴于伊朗的阿胡拉,马兹达”(12)。综上所述,可以断定两点:其一,胡日穆斯塔一词在蒙古语中的含义并非严明、固定、一贯,显然是外来词。其二,它很可能是经过突厥、回鹘进入蒙古的伊朗语即波斯语词。
蒙古早期文献中表示天、神这类观念时使用的大都是“腾格里”、“孟克腾格里”、“德都腾格里”、“苏勒得腾格里”等字眼,而没有或很少使用“胡日穆斯塔腾格里”。这表明它在蒙古语词汇中尚未占居适当的位置。实例为证:一、有人统计过《蒙古秘史》中出现的“腾格里”一词多达69次。(13)然而这些“腾格里”分别是自然天体、神秘天神和人员称谓。它们常被“德日”(上)、“孟克”(生长、永恒)、“敖都太”(有星星的)“特卜”(健壮、穿通)等字眼来修饰,但从未冠用“胡日穆斯塔”一词。换句话说,《蒙古秘史》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胡日穆斯塔腾格里”这一称谓形式。二、元明时期蒙古统治者所颁布的回鹘式蒙古文指令、公文、碑文、印玺文等历史文献中(14),“腾格里”一词同样频繁出现,但仍不见“胡日穆斯塔腾格里”。三、元明时期编纂刊行的几部“译语”如《至元译语》(元泰定乙丑1225年)、《华夷译语》(洪武22年即1389年)、《登坛必安究》(1589年)、《庐龙塞略》(1610年)、《武备志》(1621年)等书籍中搜集的常用蒙语词汇里均有“腾格里”一词,有“腾吉里”、“腾革力”、“腾克力”三种汉字注音形式,但却不见“胡日穆斯塔”的影子。四、早期翻译文献如汉译蒙《孝经》和藏译蒙《入菩提行》中“腾格里”也不断出现,但没有出现“胡日穆斯塔”。无需再举例子,足以说明“胡日穆斯塔”一词,当时尚未进入蒙古语常用基本词汇之库。当然,通过上述例子不能得出“胡日穆斯塔”一词直到元明时期还没有进入蒙古语的结论,因为我们发现元代藏译蒙的另一部著作《萨迦格言》里就有“胡日穆斯塔腾格里”这一名称。它与藏文表示帝释、天王的brgya byin一词同值。
帝释在藏传佛教中被称之为帝释天,33天神之主,常住在须弥山顶之善见城。33天神分别为:8个财神、12个日神、11个威猛天、娄宿2子。(15)财神包括:水神、北极星、月亮、太阳、风、火、天明时、黄金;12日神包括:帝释、大梵、火天、大自在、日天、非青、青胜、毗沙门、遍入、罗刹、水天、焰摩;11威猛天是:未生、三足、安止、威猛、勤奋、能夺、乐生、三眼、胜他、得自在、三地;娄宿2子为:娄宿天和鸠摩罗天。(16)佛典认为33天居住的须弥山顶是个分界线,它往下依靠大地,往上脱离大地进入空间。自33天界以上虽无日月运行,但有昼夜之分,以花谢、鸟不鸣、困睡、身体不发光之刻为夜。(17)
藏传佛教中的帝释天即brgya byin并非藏族崇信的古老天神。它是随着印度佛教的传播而进入藏区后才渐渐成为人人供奉的众所周知的天神。而帝释天在印度古代即其神话传说中叫做因陀罗(indra)。关于因陀罗,我们借用金克木先生的描述来简略说明:“…《梨俱吠陀》歌唱得最多的是天神因陀罗,……因陀罗是主要的神,它的最重要的事迹是战胜敌人,破除障碍,取得了水……”;“因陀罗又是火的创造者。他用两块石头生出了火。因此火神是他紧密的伴侣”;“因陀罗的另一个著名称号是‘破坏城堡者’。他破了许许多多城堡,其中属于弗栗多的就有九十九座”;“因陀罗还杀死了许多敌人,其中有三头六眼或则九十九臂的妖魔等等”;“因陀罗手持雷杵(金刚杵),成群的风神是他的部队,又以解放水为勋绩,印度传统后来把他算做雷雨之神,西方学者更多以为他只是雷雨的人格化。”(18)从上述种种不难看出因陀罗原本是个印度神话中的天神,他与水和火有着密切关系。水与火不仅对印度人而且对整个人类的童年生活有着特殊的意义,因陀罗既然是它们的创造者,深受人们崇敬和歌颂是无可非议的。这样一个重要角色逐渐被印度佛教纳入其万神殿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印度佛教万神殿里因陀罗的地位并没有象梵天、毗沙纽、湿婆、黑天那么显赫,自然受崇的程度也逊色多了。
在西藏以及甘、青、滇、川藏族地区人们崇拜的众多天神中,因陀罗的名称似乎没有“白哈尔”叫得响亮和知晓广泛。关于“白哈尔”,其名称写法不统一,学者对他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据奥地利学者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的力著《西藏的神灵和鬼怪》中的“白哈尔及其伴神”一章看,西方著名藏学家图齐、石泰安、托马斯、霍夫曼、乔玛、罗列赫等对“白哈尔”神的起源、流传、名称、地位等诸多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但他们所利用的资料和研究角度不同,因而很难把众人的观点统一起来。对此,奥地利学者写道:“白哈尔被西藏佛教万神殿接纳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关于雪域之地何时开始崇拜白哈尔神,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显然缺乏根据的说法是,白哈尔最初居于孟加拉——传说中莲花生的出生地——后由孟加拉赴西藏。另一份文献说,白哈尔由最初居住的孟加拉,将其法座移到了位于裕固境巴达霍尔的修习禅院。更有价值的资料说白哈尔在北木雅的神院,如同时代石泰安在他最近发表的有价值的关于木雅和西夏历史的著作中表述的那样。”(19)作者稍后接着写道:“在讨论这位重要的护法神及其伴神的造象之前,我们先应该说几句有关‘白哈尔’这个词的意义的论述。根据最近得到的有价值的西藏文献所述,‘白哈尔’名称的来源问题似乎被解决了,指出,‘白哈尔’一词等于‘比哈尔(王)’(bi har rgyal po),源于梵语的Vihara,意即‘寺庙’。在本书引证的藏文文献中,‘比哈尔王’和‘白哈拉’的形式也经常出现。很显然,在担任了桑耶寺护法神的职能之后,这位源于国外的神灵才用了‘白哈尔’这一名称。虽然,白哈尔一名的来源问题还没有被真正的解决,但值得一提的是,人们试图证明,‘白哈尔’一词来源于突厥语的bag,还有汉语的‘白’;或者如布莱彻斯特耐尔最近所做的研究那样,认为‘白哈尔’Pebahr一词源于波斯语的Paihar(图画、偶像)(中世纪波斯语作Pabhar,粟特语作Patkrg,阿维斯塔语作Paitikara);或者说源于波斯语的Paikar(战斗)(中世纪波斯语作Patkar,阿维斯塔语作Paitikara)。”(20)我们从以上引文中至少可以肯定两点:一、“白哈尔”是外来的神;二、关于“白哈尔”的来源众说不一。这两点为弄清“白哈尔”的本来面目提供了一个范围,我们顺着前人的研究再往前走,距离达到胜利的彼岸并不遥远了。
“白哈尔”在藏文文献中有种种拼写法,这也足以说明他不是土生土长的神。那么,他究竟是什么神,说法也不一。“我们在这里再列举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一种说白哈尔原是梵天的一种形式;另一种根据他曾被称作帝释天的事实,认为白哈尔就是帝释天。”(21)藏文是用brgya byin两个词来表示帝释天的,这一点上面已经提及。倘若“白哈尔”也是帝释天,那么他与因陀罗即Indra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了。或许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同样用藏文brgya byin来表示帝释天的“因陀罗”和“白哈尔”实际上是一回事,是外来的神。但是,这两种称谓进入藏区的时间和路线不同,因而造成了一些误会。笔者以为:“因陀罗”很可能是带着本意直接进入藏语的梵语词,而“白哈尔”是经历过不同语言的国家带着不同文化色彩步入藏区的外来语,很可能是波斯语。“白哈尔”被藏族接受的时间大概比“因陀罗”要早,所以才出现了“白哈尔”比“因陀罗”知名度高的现象。这么看来,藏语brgya byin、梵语Indra、蒙语Hormosta便是一回事,指的都是帝释天。
三、关于“额色润腾格里”
《本义必用经》对天有如下概括:所谓天是以欲界6天、色界17天和无色界4天而成的。(22)根据该经的解说,欲界天有父母,自然也有男女之分,但是另外两界天则不然。不同天所居住的位置也各异。所谓6欲天的位置分别为:四大天王居住在须弥山第四层,周围有他们部下众天围绕;33天居住在须弥山顶;然后顺着往上有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和他化自在天。色界17天内分四禅定,第一禅定有: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第二禅定有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第三禅定有: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第四禅定有:无云天、福生天、广果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观天、善见天、色究竟天,共17天。空无遍处、识无遍处、无所有处和非想非非想处为无色界4天。(23)这是佛教经典中宇宙形成学说的一部分,它曾深刻地影响了蒙古族佛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思想。在他们的著书立说中那些宇宙观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予以转述,不提任何异议。这种情形延续了几个世纪。此外,蒙古社会中流传至今的诸多佛教经典、神眝、寺庙、法器等在很大程度上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想探讨的“额色润腾格里”也不例外。
蒙古语里的“额色润”(Eseron\Esero-e)是个外来词,通常只与“腾格里”搭配,以“额色润腾格里”形式出现。它的出现率没有“胡日穆斯塔腾格里”那么高。除了佛教翻译作品外,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中很少用及。
在一般藏蒙对照辞书中藏文“tshang pa”与蒙文“额色润”对应,但“额色润”这个词不属于纯粹的蒙古词而不收入蒙文辞书,因而人们对它的真正含义并不十分清楚。这大概是该词使用率不高并使用不规范的原因之一。现在我们通过藏文“tshang pa”(梵天)的解释弄清了“额色润腾格里”就是上面提及的色界17天中所指第一禅定三个天即梵中天、梵辅天、大梵天的总称或叫初禅之王。如同“额色润腾格里”不是蒙古族传统崇拜的神眝那样,“梵天”也不是藏族崇信的传统的土著的天神。它来自印度,其故地称谓为Brahma\Brahme,“是最高无上的神,唯一永远的神,是世界的大原与本体,万物从他流出并以他为归宿。和梵天融为一体产生摩刹(Mokcha),意即解脱肉体的桎梏,此后,灵魂即脱免一切轮回,并入神体。最后解脱被看作是无上幸福,是一切虔诚的印度人愿望的归宿。”(34)从前人的研究成果看来,“梵天”是在印度早期宗教兴盛时期即佛教形成以前就被印度人崇信的一个重要神眝。“它是唯一自在的、无所不在、超人的神,一切事物从它而生,并将返回其中。这一概念的形成,是印度神学最原始的特色,它倾向于认为梵不仅存在于一切事务中,而且认为梵即是一切事物,所以摆脱了幻觉的灵魂能够觉察到它和梵本是一体,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存在。”(25)“梵天”与印度婆罗门教有密切关系。“梵文婆罗门(Brahman)一词在初期吠陀中表示圣典,具有伟大优越的涵义。后来当保拉法时代婆罗门这个词人格化了,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或上帝,一般被译为梵天,它是最原始的实体,宇宙即由它而化成。有时梵天一词颇为哲学化抽象化,被理解为非人格的绝对存在,可是仍然具有生命。从梵文梵天(Brahman)又派生出婆罗摩那(Brahmana)一语,义为掌握圣典的教士,后来又变成上帝的教士。”(26)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关于“梵天”的一些本质特征即至高无上的、创造万物而存在于万物中的印度古老神眝。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身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并增加了一些新的色彩。其中较突出的一点就是与湿婆和毗沙奴相比没有那么高的威望,因而失去了一些崇信者,这与他创造善神的同时创造了妖魔和灾难有关。当佛教把他吸收为护法神之后,其名声逐渐从印度向外传播到其他的雪山、草地,他是在藏区以“tshang pa”或“tshangpa dkhar po”,在蒙区以“Eseron Tegri”或偶尔以“Barman Tegri”形式出现的。在人类童年时期被幼稚人们所创造的具有不同功能的无数善恶神眝随着人们的文化活动,有的跨出了人种、地域、民族、国家的界限,走到了异国他乡,其中有的保持了本来面目,有的却走了形。无论是土著或外来神,其名声、地位和威力多么不可一世,但随着人们对自身和大自然的不断认识,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诸神及其主要神眝便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在蒙古族中,“孟克腾格里”、“胡日穆斯塔腾格里”和“额色润腾格里”的命运也都是如此。
四、并非最终的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已经基本上弄清了:“孟克腾格里”这个概念是指蒙古人最古老最受崇敬的天,他有天和天神两个基本含义。“胡日穆斯塔腾格里”是蒙古人崇敬的仅次于“孟克腾格里”的天,但是个外来者,与藏语的“brgya byin”(百给者)和梵文“Indra”(帝师)意义相同。“额色润腾格里”是蒙古人崇敬的另一个重要天,也是来自异国他乡者,他与藏语的“tshang pa”、梵文的“Brahma”意义相同。可是,如果我们审查一下这三个天的在蒙古书面和口碑文献中的具体应用,就会发现他们并不规范,而且还很混乱。通常是把“孟克腾格里”和“胡日斯塔腾格里”等同或相混,把“胡日穆斯塔腾格里”和“额色润腾格里”等同或相混。让我们举几个简单例子:如上所述,在《蒙古秘史》中称成吉思汗的祖先是“上天处生有的”,他们常把自己的所有行为与“长生天的恩赐”联系起来思考,这里的“长生天”和“上天”无疑是“孟克腾格里”。此处的“长生天”后裔成吉思汗,在十六七世纪的著名翻译家席热图固实却尔济的笔下却成了“诸天之汗大自在胡日穆斯塔,变成了无与伦比的成吉思汗。”(27)在一本《世界雄狮子格萨尔王传》蒙译本中的藏文“tshang pa bkarpo”一词有“胡日穆斯塔”和“额色润胡日穆斯塔”等两种翻译。(28)前者是在书面语中混淆“孟克腾格里”与“胡日穆斯塔腾格里”,后者是在口碑文献中混淆“胡日穆斯塔腾格里”与“额色润腾格里”的例子。显而易见,“胡日穆斯塔天之主”形象的随意性尤为突出。如经过后人整理的蒙古史诗中就有把“三十三天之首胡日穆斯塔”叫做“三下三个胡日穆斯塔”的说法;也有把“西部五十五天之首胡日穆斯塔”叫做“胡日穆斯塔之九十九个天”或“上九十九天之汗胡日穆斯塔”等等。甚至使其人格化,成为食人间烟火娶亲生儿育女的“胡日穆斯塔”。这些腾格里在文献中的如此不规范的称呼造成了后人对他们进行解释和研究时顾此失彼或张冠李戴。又比如有人解释“胡日穆斯塔”为“玉皇,额色润腾格里”;(29)有人解释“阿修罗”为“一种天神,也叫额色润腾格里”(30)等等。这些解说,现在回过头来看,显然是不确切的。我们知道,“玉皇”也叫玉帝,是道教对天上最高神的称呼。“阿修罗”原为古印度神话中的一种恶神,常与天神战斗,有时翻译成“不端正”或“非天”等。除此之外,常见的另一个现象是把“胡日穆斯塔”等佛教的天神硬拽入蒙古萨满教诸多天神的行列。如《蒙古萨教事略》中的“比斯曼腾格里”;《哈腾根十三家神祭祀》和《蒙古宗教概论》中提及西部55天和东部44天时把“胡日穆斯腾格里”和“阿修罗腾格里”分别归入东西部天列便是明例。
蒙古族的萨满教和藏族的苯教是他们的原始宗教,均有其崇信的众多神眝,其中当然包括一些天神。后来这两个民族先后信奉了佛教。佛教也有自己崇敬的神灵。不同时期的宗教为不同时期的统治者所利用和重视的程度不同,不愿轻易让位的萨满教和苯教曾与佛教进行过长期抗衡,局部地区甚至并行到近代。在这个复杂的进程中佛教的万神殿里纳入原始宗教的个别神眝的象现是有的。相反,在局部地区盛行的原始宗教是否也接纳了佛教个别神眝?笔者以为,在佛教界赫赫有名并较为规范而定型化了的天神被原始宗教接纳的可能性很少。
总之,“腾格里”——天,很早就是人类探索的重要课题之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民根据自己传统文化对他进行了不同阐释。以往的结论大都把自然天与人为天混为一谈,对认识造成了一定障碍。现在看来,所谓自然天就是宇宙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人类而言,他是地球之外的笼罩物,其容无量,日月、星宿都在其中。没有科学的时代,人们给所谓的“万能的主宰者”和“神灵”寻找生存和栖息的空间也是这个天,久而久之成了天的化身,这就是人为天。在蒙古,天的数量不断发生变化,是与“神灵”上天的数量有着密切关系的。尽管如此,我们对蒙古的万神殿仍知之甚少。
注释:
①《出使蒙古记》,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②参见注①214-215页。
③参见注①222页;
④参见注①72页;
④参阅茅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⑤《蒙古秘史》校勘本,91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⑥参见注⑤1055页。
⑦《蒙汉词典》68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⑧斯琴朝克图:《蒙古语根词典》1146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⑨《首届国际蒙古学会文件汇编》第一册,57-85页,乌兰巴托1961年。
⑩《西域文化史》8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西藏和蒙古的宗教》416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
(12)额尔德木图:《论“蒙古秘史”中的天》;见《内蒙古社会科学》(蒙)1986年2期29-42页。
(13)道布:《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14)《本义必用经》(蒙)34页。
(15)《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85年。
(16)《水晶鉴》,民族出版社1984年,30页。
(17)《梵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19-26页。
(18)《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15页。
(19)见注(18)128页。
(20)见注(18)118页。
(21)见注(14)31页。
(22)见注(14)59页。
(23)《摩奴法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22页。
(24)《印度教与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148页。
(25)《印度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26页。
(26)《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乌兰巴托1959年版,292页。
(27)《滋穆林森沁那木塔》,乌兰巴托1959年版,2-3页。
(28)见注⑦ ⑧。
(29)优·其木德道尔吉:《格斯尔可汗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