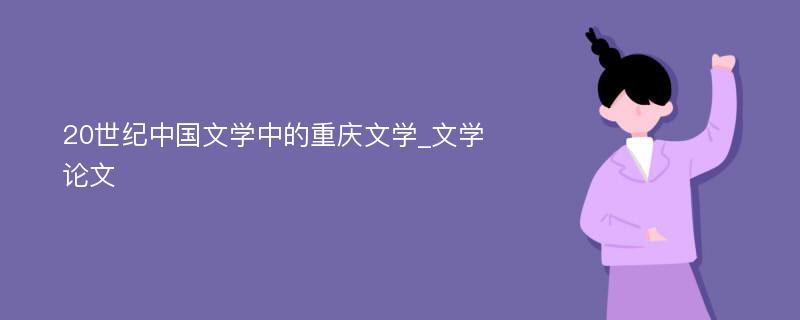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的重庆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庆论文,版图论文,中国文学论文,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09.9
临近世纪之交,各种各样的“回顾”与“总结”构成一种亢奋的世纪末文化心态。与之同时,当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数番转折之后,正在寻找新的视角和方法,以期构成新的知识增长点。这为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回顾和总结象重庆文学这样的地域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发展走向提供了可能。诚然,那些急于作出总结性发言的亢奋的世纪末情绪固然有其浮躁的一面,但也并非毫无道理可言。一如区域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研究既是对于当今全球化(或后殖民)时代文学话语的一种应对,同时也不妨是对于区域文学的一种更为深入的把握一样,均有其历史的和逻辑的合理性。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版图中,重庆文学似乎还是一个至今未被认真提及的话题。这跟重庆文学的实际成就和影响有关,但显然也跟我们对此的认识有关。直到大约80年代中期,才有人提出要为文学上“渝军”的崛起鼓与呼。此前的提法则是巴蜀文学不分家。但事实上,自古以来,巴蜀文化便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这种情况即使到了现代,虽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冲刷,其内在的脉络仍然历历可辨。诚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巴(重庆)文化因“山地的封闭壅塞难免粗粝朴拙,又因有三江(按指重庆境内的长江、嘉陵江和乌江)的疏浚融通而不失滋润清灵,从而有别北国大漠荒原的沉雄枯焦”。另一方面,“三江舟楫与商旅因山地风习的侵染与牵掣,虽然润泽而富赡,而并不流于绵软俗艳,从重庆习尚、乌江文化到大峡(夔万)风情,莫不如是。这种独具的文化特征,在巴蜀文化之内,也应该说是独树一帜。”(注:易光·重庆文学史:一种可能性描述·涪陵师专学报,1999(1 ))这种独树一帜的巴文化对于重庆文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甚至进而促进重庆文学形成自己的特殊性。只是在巴蜀文学一体化的语境中,重庆文学的特殊性被认为是一个次要问题,或者说只是四川文学中的一个局部问题。但是当历史出现新的契机(例如重庆从行政区划上脱离四川再次成为直辖市),人们获得一种新的语境,便可能对以前忽略的东西产生新的认识。当重庆文学自身的特殊性被有效放大之后,人们发现,即使把它放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版图之中,重庆文学似乎仍有它不可忽略的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人们还可以从中看到现代重庆文学生成的轨迹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现代重庆文学的发生与重庆作为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先驱也许要追溯到那位写《革命军》檄文的邹容以及白屋诗人吴芳吉等人那里。但20世纪重庆文学的正式崛起则应是从30年代末期伴随着抗战军兴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开始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芦沟桥事变,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迫于形势,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迁都宣言》,宣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1939年 5月,国民政府将重庆由四川省辖市擢升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又宣布将重庆定为中华民国陪都。 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大敌当前的形势,大批工厂、机关和文化教育机构内迁,重庆迎来自1890年开埠以来最为活跃的发展阶段。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37年8月至1939年底,在国民政府组织下, 以工业重镇上海为中心,在北起山东青岛、南迄广东香港的广阔地域上,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工厂内迁的浪潮,先后迁往内地的国营和民营工厂多达数百家,其中多数分布在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这就不仅为处于西南内陆的重庆带来了当时国内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大批产业工人的加入对于改变重庆人口结构和素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从1937年12 月1日起开始在重庆办公,1938年10月各机构陆续迁抵重庆,仅当时国民政府主要办公机构迁来重庆的工作人员就多达数千人。更重要的是,大批文化教育机构也随同内迁,为战时重庆大后方文化事业的勃兴奠定了基础。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抗战中迁到四川的就有48所, 其中有31所分布在重庆,包括著名的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此外,重庆的文化艺术团体和新闻出版机构数量也急剧增加。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波兰、荷兰、比利时、韩国等30多个国家也在重庆设立了使领馆或办事处,使重庆迅速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都市。一时间,大批文化界、艺术界人士云集山城,为重庆大后方文学的勃兴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可能。当然,促使现代重庆文学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形成第一次有相当规模的发展高潮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抗战的需要。抗战的需要从根本上规定了当时重庆大后方文学的题材、主题、人物形象和艺术风格,也决定了它在当时所能达到的规模、水平及其影响。从重庆出版社已经出版的10编20卷本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收录的作品情况看,重庆文学在抗战八年间所发表的作品、培养的作家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都是相当突出的,也是当时大后方其他城市和地区所不可比拟的。我们所熟悉的一大批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都是当时写于重庆或与当时的重庆生活有关。它们包括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腐蚀》、巴金的《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以及艾青、臧克家和“七月派”的诗歌、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等。它们既是20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收获,同时也是现代重庆文学崛起的重要标志。
建国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七年间,从总体上讲,重庆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形象较为暗淡,不再具有40年代大后方文学那样的风采。但仍时有亮点表明它处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之中。这之中,5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批表现西南内陆生活的诗人颇值得注意。他们中的代表有梁上泉、高缨、雁翼、杨山、穆仁、陆棨、孙静轩等人。此外,引人注目的还有一批反映革命斗争历史题材的作品,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者,即是人们熟悉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创作的,以渣滓洞白公馆革命志士的斗争经历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红岩》。就一般情况而言,上述作家作品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并不是特别突出,但仍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某些作品甚至还相当突出。长篇小说《红岩》,1961年出版后不到两年时间就印行了四百万册,创造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从一个侧面表现出该作品所得到的社会的广泛认同。《红岩》几乎是创造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把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文学教化功能与大众审美趣味,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故事与革命者的人格魅力成功地结合起来,其影响不仅超出了文学的革命意义,而且也早已不限于文学本身。然而上述作家作品的地域文学含义则还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发掘。例如,我们注意到50年代中后期重庆文坛那批表现西南内陆生活的诗人群的出现是颇为引人注目的。梁上泉的《高原牧笛》、《红云崖》,高缨的《丁佑君之歌》,雁翼的《大巴山的早晨》,杨山、穆仁的《工厂短歌》以及稍后陆棨的《重返杨柳村》等,都是当时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品。然而这些作家作品产生的条件是什么?对于重庆文学的意义又是什么?在我看来,其中至少有两个因素值得特别注意。一是重庆的政治地位,二是重庆的地理环境。 重庆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一直是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 也是1953年成立的“西南区文学工作者协会”的所在地。当时西南区文学工作者协会的主席是任白戈,副主席是沙汀和艾芜,成员中包括蹇先艾、邵子南、曾克、陈翔鹤、方敬、林如稷、邓均吾、李劼人、李亚群、陈炜谟、李乔等许多著名作家。直到1956年5月, 为了与中国作家协会及各大行政区分会统一名称,才将西南区文学工作者协会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并将原来的协会刊物《西南文艺》改名为《红岩》。后来西南大区撤销,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迁往成都,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原有的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遂不复存在。而前述重庆文坛那批表现西南内陆生活的诗人恰好大都是那时重庆作协的专业作家。重庆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对于这批作家队伍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尤其如此。另一方面,重庆虽然一度是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但它的地理环境毕竟身处西南内陆,交通的不便、经济的不发达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落后等也就在所难免。所有这些地理环境的因素也给这一时期的重庆文学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过,这种效应也应该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重庆文学由于受制于当时环境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和当时的北京、上海等地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地区的文学相比,自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这种差距在文学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作家作品的数量与质量、文学创作在全国所产生的影响等方向都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地缘上的“边缘”与“中心”的差距,又可以看作是政治与文化上的“边缘”与“中心”的差距,并因此而具有了更为复杂的内涵。对于一个喧嚣甚至是荒谬的文学时代而言,这种“边缘”与“中心”的差距反而成为某种积极的因素,使得重庆文学在50年代以后的颂歌与战歌的大潮中没有被完全吞没,从而多少保留了某些自己的特色(例如对于西南内陆生活的动情歌唱)。如果说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学是现代重庆文学的第一次崛起的话,那么它主要还是一种被动的和缺乏特色的过程。建国以后重庆文学在规模和影响上虽然都不及当年的大后方文学,却开始顽强表现出自己的某些特点。这说明地域文学的发展仍有自己内在的动力。
新时期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新时期以来的重庆文学既与此前的重庆文学一脉相连,又表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丰富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首先,我们注意到新时期以来重庆的诗歌一直表现出极为活跃的态势,甚至一度在全国居于领先的地位。重庆诗人傅天琳的诗集《绿色的音符》和李钢的诗集《白玫瑰》先后两届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诗歌作品奖。这在全国其他地区和城市的文学履历上都是罕见的。所谓的“第三代诗”更是以四川和重庆作为重镇,成为继北京作为朦胧诗运动中心以来的又一个现代诗歌运动中心。重庆的诗歌创作具有深厚的基础,诗歌爱好者无计其数。新时期以来有影响的诗人除前面提到的傅天琳、李钢以外,还有冉庄、王川平、李元胜、虹影、廖亦武、李亚伟、何小竹、何培贵、徐国志、杨永年等。吕进先生主持的西南师大中国新诗研究所也为推进重庆诗歌的健康发展作了大量工作。他们共同构成新时期重庆文坛一道耀眼的风景线。但是,也应该看到,重庆这片诗的沃土尚存在种种不容忽视的问题。尤其应该看到,重庆人的那种热辣而执著的诗情既是诗歌不竭的源泉,同时可能又与相对封闭不开化的氛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分析傅天琳和李钢的创作道路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位诗人的成功恰好在于他们既禀承了重庆人的灵气和率真炽热的情感方式,又以不同的方式超越了西南内陆生活的某些局限。傅天琳是一位从果园走向大海后取得成功的诗人,李钢则是从大海回到山城尔后发现了自己和自己的诗。两人适成对照而又颇有相通之处,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认识重庆文学的一面镜子。其次,新时期重庆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新时期以来重庆文学的发展表现出对自己的传统,特别是对抗战以来形成的大后方文学资源的回望和借鉴,从而一改十七年文学中那种对国统区大后方文学传统有意回避的姿态。这突出表现为黄济人的几部作品: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长篇小说《崩溃》、《哀军》、电影剧本《重庆谈判》等。此外,相关的作品还很多,如况浩文的《在茫茫的夜色后面》、杨益言、刘德彬的长篇小说《大后方》、杨益言的《秘密世界》、杨耀健的《宋氏姐妹在重庆》、曾健戎的《郭沫若在重庆》等。重庆是一个充满了雾气和传奇故事的城市。抗战以来所形成的现代重庆文学传统理应成为重庆文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十七年文学对于这一传统的漠视甚至有意回避显然是不明智的。而且,无论是大后方文化、陪都文化甚至更为久远的巴渝文化,都有不少值得重庆作家进一步思考发掘的东西。同时,所有这些对于传统的继承都还应与时代的需要结合起来,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结合起来。不过新时期以来重庆文学在开发利用抗战以来所形成的大后方文学传统资源取得某些成功的同时,也显示出了这样的问题:即重庆文学的主体性尚未得到有效确立的问题。一方面,作家和读者的审美旨趣往往还停留于故事的层面;另一方面,对于题材的深入开掘还明显不足。尤其令人深思的是,新时期重庆文坛其实有几位相当有实力的小说家,如写《忧魂》的余德庄、写《诗礼人家》的莫怀戚和写《一路狂奔》的刘凯娟,以及万州的熊建成、涪陵的朱亚宁和阿多等,但他们似乎在重庆的文学系统中找不到感觉,在全国的文学版图中也就不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或许正好说明了重庆文学的不成熟。相对于那些已有丰硕成果的地域文学而言,现代重庆文学似乎还是正在发育中的少年。这一切都显示了重庆文学在今后的发展中确实还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