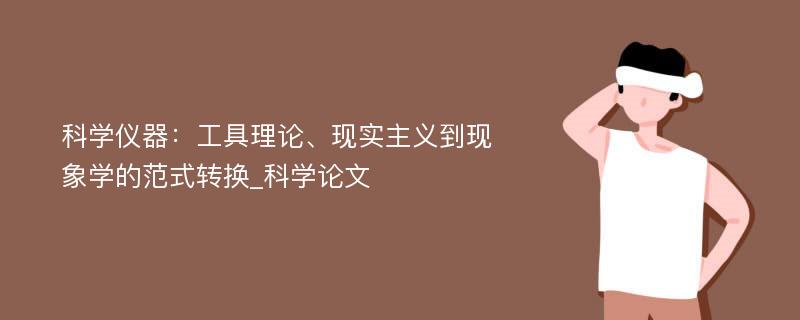
科学仪器:由工具论、实在论到现象学的范式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在论论文,现象学论文,范式论文,科学仪器论文,工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0-0763(2012)02-0018-05
科学仪器是现代科学中主体与客体的中介和工具,这一传统认识正在受到实在论和现象学的挑战。对科学仪器的实在论解析和现象学思考,使其从被动工具和手段成为具有调节与统合作用的“准主体”,并通过干涉与转译过程,同时体现人类和外部世界,在认识论意义上建立起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深刻关联。
一、工具论视域下科学仪器的“表征”作用
传统认识论将科学仪器定位为沟通主体与客观世界的中介,仪器仅仅是器物,只能服从和服务于其它价值实体。这种仪器工具论的观点建立在常识基础上,认为科学仪器的作用仅仅是“表征”(represent)对象。工具论仪器观的主要论点可归纳如下:
1.仪器的设计和选择具有理论负载
工具论认为不渗透理论的仪器是不存在的,仪器是预设理论的实物化。可以说,仪器是假设最终成为科学共同体广为认可的理论的土壤。预设理论决定仪器的内涵和职能,因而仪器完全是被动的。
2.仪器的“中立性”源于看似“理性”的特征
作为“中性的”纯工具和手段,仪器只是偶然地与它所服务的实体和目的相联系,仪器的应用无所谓好坏、真假与善恶,有用、方便和有效才是仪器的属性,因此在一种情境中有效的反映在另一种情境中也同样有效,因为仪器完全以理性的方式呈现现象。
3.仪器与社会因素无关
仪器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情境中都能在本质上保持同样的设计和使用标准,这种普适性意味着同样的衡量标准可以毫不犹豫地应用到不同情境中。一架望远镜就是一架望远镜,一台显微镜就是一台显微镜,这样的仪器在任何社会制度和社会情境中都是有用的。
然而,仪器工具论无法回避一个问题:仪器的两个变量——“表征”的客观性最大化和非理性因素参与度最小化——不可能同时实现最优化。由于仪器在这种辅助位置上是显而易见的,这种通过仪器使客体具体化的关系就相当容易被忽略掉,而只去注重被具体化后了的自在实体是什么,或成为了什么状态。因此,“表征度”是仪器自身固有的却被忽视了。同时,仪器的两个变量也意味着仪器并非只具有单纯的“表征”功能。科学仪器具有历史性、情境性和社会性。问题不在于仪器表征了什么,而在于以何种方式表征以及表征程度如何。当仪器超越了完全的身体展现、当科学超越了纯粹数学的界限、当人类自身超越了单纯数学方法的计算者和仪器的操作者时,仪器对人的认识和世界呈现方式都产生了影响,它不再是被动的“表征”工具,而是主动的“调节”与“统合”实体。
二、实在论视域下科学仪器的“居间调节”与“统合”作用
仪器工具论中的“表征”作用仅属于被动反映,无法解释“表征度”问题,也不能有效解释仪器在主客间的中介机制。笔者认为,仪器的实在性不仅在于解释这种机制,更在于人类和世界均和仪器发生了交互关系。仪器作为技术的人工制品,通过主体和世界的相互作用,客观知识才得以发展,“一个东西同第一世界的相互作用(即使是间接的)乃是称其为‘实在’的决定性论据”[1],即凡是实在的东西都会与世界1和世界2发生相互作用。既然仪器具有历史性、情境性和社会性,那么其本质就是动态的;既然仪器的本质是动态的,那么它就有自身的进化规律,不再是被动的“表征”工具,而变成了有生命的“有机体”。并且,仪器的实在性也体现在人类对其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仪器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工具,而是“隐藏在技术下面的,正在被接受的是一组新的经济关系,并最终将导致一种依赖关系。”[2]
1.作为人类和世界“居间调节者”与“统合者”的仪器
仪器在科学事业中参与了人类思维的形成,建构了世界得以“呈现”的样态。甚至可以说,近现代科学发展史就是仪器应用史。这样,仪器历史、人类历史和世界历史成为一个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整体。马丁·海德格尔也给予仪器以特殊地位,“现代物理学作为实验物理学,依赖于技术设备以及制造设备的进步。”[3]此时的仪器已不再是客体,它不仅为人类“呈现”了世界的样态,而且也决定了样态的“表征度”。
以透镜技术为例,透镜技术产生了一种新的居间调节的人类视觉形式。它使全新的科学知识建构成为可能。无论是伽利略的望远镜还是列文虎克的显微镜,都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呈现”自身的程度,透镜的“居间调节”产生了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没看到也无法看到的影像:月球的山脉和陨石坑、金星的盈亏、太阳黑子、水中的原生物、微血管、骨骼肌中的条纹、神经结构、微生物和血液经过微血管的循环现象等等。如果没有仪器的帮助,人类对科学世界的认识很难想象。因此,新的视觉产生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完全归功于仪器的居间调节。正如怀特海宣称,“令我们出于更高的想象水平之上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精美的想象,而是因为我们拥有更加优良的仪器。”[3]
科学正是通过使用仪器进行观察而得以正常运行的,“如果科学是产生新知识的人类实践,而且这种知识超出了空洞的、没有仪器帮助的感觉,那么只有这种放大了普通能力的仪器体现的科学才是有资格的,并且这就是伽利略用他的望远镜产生的科学。”[4]利用望远镜的伽利略和利用显微镜的列文虎克不仅仅是利用数学方法的计算者,同时也是被现代技术居间调节的、被“仪器化”了的科学世界中的感知者和实践者,其科学也是被仪器“体现”了的科学。至此,仪器已远不再是工具,其作用已远不再是“参与”的初级阶段,而是无时无刻不控制着世界和主体。仪器在主体和世界间的居间调节一方面限制了人对世界的认识,从而“遮蔽”了主观世界;另一方面仪器也限制了客观世界,脱离仪器的世界是不可知的“自在之物”,通过仪器的“过滤”,“筛选”出仪器所“允许”的显现的世界,从而也“遮蔽”了客观世界。望远镜的放大倍数由3X到30X,世界“呈现”给主体的内容决然不同。仪器不仅“表征”了对象,更建构了对象,人类认识世界的范围和程度以及世界可以向人类“呈现”的内容都由仪器来决定。特别是现代科学的发展与仪器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仪器的增值与创新是引起和推动科学发展的前提,仪器使主体只能用这种方法而不能用那种方法“看到”仪器所“允许”显现的世界,使世界通过仪器只能呈现它的这一面而不能呈现它的那一面。于是,仪器的历史、人类历史和世界历史成为了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统一体。正是由于仪器的居间调节与统合,人和世界之间才建立了某种联系,才形成了现代科学。
2.作为“居间调节者”与“统合者”的仪器产生的两个重要后果
伊恩·哈金(Ian Hacking)尤其强调实验的作用,强调对实体进行“工程化”操作。他指出,“对判定一个假设的或推测的实体的实在性的最好证据就是我们能够测量它或者理解它的因果关系,而我们所具有的这种理解的最好证据就是一开始我们就能够利用这个或那个因果关系来建造可靠工作的仪器。因此,证明实体的实在性的最好证据是使之工程化而不是理论化。”[5]哈金还明确表明“实验有自己的生命”。仪器是实验的前提条件,仪器在主体和客体间的调节“统合”机制说明仪器是历史的、情境的、有自己的进化规律,确立了其在认识论中的独立地位,即它不从属于主客体的任何一方,非但不从属还超越了人类和客观世界。仪器作为主体和世界之间的“界面”(interface)对世界的“工程化”操作会产生两个重要后果:第一,可以“制造”其它第三世界的新客体并产生新技术和新知识;第二,人类自身和客观世界均被“仪器化”。正如海森堡(Heisenberg)所言“只有当现象与测量仪器,从而与世界的其余部分发生了相互作用,从‘可能’到‘现实’的转变才能发生。”[6]
仪器的实在性使其能够主动地在主体和世界之间进行调节,这两个重要后果在仪器简单的“表征”功能下是无法产生的,而必须通过仪器对世界的“工程化”操作。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制造现象”,就是仪器主动对实体进行“干涉”而不是被动“表征”。主体和世界在干涉过程造成的现象界中相互“体现”自身,在仪器这一界面中相互交流。
三、现象学视野中科学仪器的“干涉”和“转译”作用
在“人类-仪器(技术)-世界”的经验模式中,存在两个变量:世界的体现和人类的体现;及两个过程:干涉过程(intervening)和转译过程(translation or interpretation)。仪器使现象成为可以获得的乃是通过仪器对对象的“干涉”,使不能被直接经验之物发出的信息成为可感知的。这种干涉产生了两个现象:使“自在实体”变为“现象实体”;使主体不再是自然意义上的主体,而是被仪器所“体现”的“仪器化”了的主体。因为现代科学所触及的范围越来越超出人类的知觉(perception)能力,“人类的体现”必须要被解释到生活世界(life-world)之内,成为人类知觉能够理解的可视化形式,那么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交流就需要以上提到的第二个过程——转译,即将现象转译为一种体现的生活世界的解释学(hermeneutics)转换过程。
1.在仪器干涉造成的现象界中主体和世界间的相互体现
仪器构成了主体和世界之间相互交流的“界面”,这一界面决定了人类和世界“体现”自身的样态。“体现关系”(embodiment)是唐·伊德(Don Ihde)在思考作为工具的技术现象和人的关系时揭示出的人类与技术之间四种关系之一。他认为,通过人造物扩展的身体能力的感觉即是人类与技术之间的“体现关系”。因为人类了解自然的欲望越来越强,而人类自身能力却极其有限,所以这种“体现关系”的重要性随着人类对仪器的依赖程度呈现出了指数型增长的趋势。将望远镜对准月亮时,人感觉“我离月亮更近了”或者“月亮正在逼近我”,这是仪器对人所经验的事物加以空间改变的形式。正是因为望远镜的放大功能,在望远镜干涉人类知觉的过程中,不仅放大了月亮,同时也“放大了”人自己的“身体活动”,这正是使用望远镜的一种现象学的结果。在体现关系中,望远镜展现出透明性,成为“身体体现”的一部分或身体的延伸。在微观世界中,仪器对微观粒子与主体的作用超出了“居间调节与统合”的解释力,此时的仪器更加活跃,因为它已达到了“干涉”微观粒子运动状态的程度。
对仪器本质的分析也必须放置到“意向性”本体论的现象学框架内。这里借用胡塞尔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来表达:主体在从事各种高度复杂的行为时,认为世界的秩序是自然形成的,所以主体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这些高度复杂的行为正在使世界变得有序化。在使世界有序化的过程中,自然就更不会对仪器造就现象界的过程加以关注。那么考察“意向性”过程的任务就由现象学承担起来。对胡塞尔而言,“意向性”始终是对某客体的意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件事物,即“意识不能是空白的,而是根据我们对它们的兴趣和好奇不断地从一个场景转到另一个场景。”[7]那么对仪器的本质所做的“意向性”本体论解析乃是在这种关系中展开的:仪器“干涉”建构了一个主体和世界分别呈现自身的界面,在这一界面中,主体和客体都不再是自然意义上的,而是被“仪器化”了的;伊德认为,“工具具有一种‘意向性’能力,它既可以揭示未知事物,又可以改变现象出现的方式。工具的意向能力表现在工具连续统一体之中,随着工具连续统一体产生的变化,人类-工具-世界的意向弧(intentional arc)发生变化。”[8]也就是说,这种“意向性”不是静态的、内部的,而是“关系性的”,它存在于“人类-仪器-世界”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当中。以下就以仪器对微观体系的“干涉”来说明在仪器造成的现象界中人类、仪器和世界是如何“相互体现”而成为统一体的。
仪器工具论对于说明经典力学中针对宏观、低速对象的仪器应用是充分的,仪器对客体的作用力可忽略不计,测量结果仍可被视为对象本质的反映。仪器对对象的作用仍然是“表征”,未达到“干扰”的程度。然而,量子力学对仪器工具论产生了挑战,仪器的认识论意义因物理系统的差异而发生了改变。量子力学中的体系状态有两种:一种是按方程演进,另一种是仪器改变体系状态的不可逆变化。由于仪器对某些量的干扰,使得共轭量不准确。因此,量子力学对物理量不能给出确定判断(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仪器的干涉不仅在科学意义上对对象产生了“干扰效应”,而且使关于量子力学的解释涉及的许多哲学问题也都显露出来。微观物理系统的性质总是在它们与其它体系——尤其是仪器的相互作用中得到“体现”,成为主体可见的“显现”的世界。而且对微观体系的表述也不同于经典物理学,后者主要表现为波动图像或者粒子行为,而量子力学则用量子态来表征微观系统,量子态分为显态和隐态,显态符合经典物理学的实在,隐态乃是由仪器的“干涉”所体现的状态。
微观物理系统同时具有不可分离性,量子力学把对象及其环境看做整体。在仪器对世界的干涉过程中,主体也被仪器所“干涉”,主体由自在主体变成“仪器化”主体。在这种人与技术强有力的相互关系之中,人类成为被仪器“体现的人类”,这种体现完全是在一个具体的背景中——在这一背景中,“被体现的人类”关注“被体现的世界”并与之相互作用。在人、仪器和世界相互交流的环境中,人类在被仪器体现的那部分世界和仪器的界限间感受着自己。此时,通常意义上的主客体界限越来越被淡化,对微观物理系统的测量已分不清到底是主体通过仪器看到的(或者说是仪器“表征”出来的),还是仪器“干涉”而获得的现象了。仪器与微观物理系统产生了无法分割的相互作用——人类主体、仪器和世界融为一体,形成了“主体-仪器-世界”的连续链条。主体和世界在仪器这一界面中各自“去蔽”,在仪器造成的现象界中相互“敞开自身”。这种相互作用表现在“体现的人类”感受着“体现的世界”,而这一世界又反作用于人类,完成着各自“意向性”的过程。
在仪器“干涉”产生的现象界中,现象的获得是从科学世界中得来的,这一步骤可以说是纯粹的科学事实阶段,而要使现象对人来说有意义,就需要将科学事实“加工”成人类知觉可以实实在在“触摸”到的形式。这就是下文要重点论述的问题。
2.科学世界到生活世界的“转译”机制
胡塞尔后期研究集中于现代科学的危机及其出路,他认为危机源于将科学看做是纯数学化、失去了一切主观价值内容的科学。这种撇开意义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科学使人不再是整体的人,而仅仅是纯科学事实的“片断”。单纯的科学事实无法感受“体现的人类”及其知觉存在,况且现在所感知的世界是人类通过“意向性”活动而形成的对人类有意义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并非外在于一切存在的、由科学事实组成的世界,而是透过人类对科学世界的“意识”才变得有意义。正如唐·伊德所言“可以存在没有科学的生活世界,但却不存在没有生活世界的科学。”[4]科学事业根源于日常经验的世界,“科学不能忘记生活世界,因为它必须找到用身体可以感知的、可以解释的证据。”[9]并且,解释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是伊德所界定的人与技术间的四种关系之一,其结构是人→(技术-世界),人类对世界的知觉需要对技术呈现的数据进行解释。
仪器从科学世界中“发觉”了现象,仪器对观察者来说已经不再意味着工具。仪器不再被感知,人不是通过对象的存在意识到仪器的存在,而是通过仪器意识到对象的存在。在人与技术之间的“交流”中,仪器成为与人类身体感觉的结合物。正是通过对人类知觉的改变,仪器才使新增强的科学世界的维度向生活世界敞开、向知觉身体经验开放。要使科学世界的维度真正进入生活世界,仪器的“转译”过程就必不可少,即,需要有技术做解释学转换。
正如胡塞尔所说,“写作语言的重要功能是它无须即时的、个人的表达,因此使交流成为可能。”[9]写作技术能够改变交流方式,仪器类似于写作。在“转译”过程中,仪器“它所显示出的不是一种躯体的延伸,而像是一种语言的延伸,也就是说,实际上如同一种文献。”[10]正如伊德所说,“如果技术只是复制我们直接的和身体的经验,它们将很少有用并最终使我们失去对它们的兴趣。”[11]“写作沉淀了意义……但是读者可以使其再次自我确证,可以使其重新激活自我证明……这种技术使意义结构成为可以重新激活的、可重复的和主体间的。”[4]在将现象从底片中“转译”成人类视觉的可视化形式时,使从前不可经验的现象变成可以获得的,同样也使影像成为可重复的和主体间的。此过程可由全息技术得到形象说明。全息技术是影像技术的一种形式,伊德认为“影像技术的技术化建构的方法超出了现代认识论的界限,它更加接近于一种现象学的建构。”[2]记录并再现物体三维图像的技术,自然其第一步就是利用干涉原理记录物体的光波信息,即拍摄阶段。信息存储在底片上,经过显影、定影处理成为全息图。第二步就是利用衍射原理再现底片信息,这就是成像过程。通过相干激光的照射,物体的三维图像就呈现出来了,此过程即“转译”。将平面的底片信息转译成具有真实感的视觉效果图。现在广为应用的X光-CT、超声成像、磁共振成像等技术都是成像技术原理的应用。肿瘤患者可以借助X光-CT得到患部断层照片,这个照片同样也是由胶片上的信息通过计算机转换为三维立体图像产生的。计算机就是一部增强了的照相术的“转译仪器”,实现了使数据向影像的转变。
至此,仪器完成了“干涉-转译”的全部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一种解释学过程,将现象解释为生活世界可以理解的形式。这种成像技术不是简单的“表征”,而是一种对仪器的批判的解释学范式。在“人类-仪器-世界”的两个变量中,人类通过“沉淀的”实践与在仪器的干涉与转译的技术中所能够知觉到的东西现实地联系在一起。影像必须通过人类的知觉能力和“体现的技术”转译而呈现出来。这种为“体现的人类”而“仪器化”了的影像正是对科学世界(确切地说是对生活世界)的重新关注。
工具论、实在论和现象学提供了关于科学仪器认识论的三种不同视角。之所以要超越仪器工具论,乃是因为仪器单纯的“表征”作用无法有效解释仪器的历史性、情境性和社会性。仪器的实在性在于它建构了世界得以“呈现”的样态,这种“建构”是在对人与世界的“调节与统合”中完成的。在“调节与统合”构成的人和世界相互交流的“界面”中,仪器始终控制并调节着人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主体认识世界的程度和世界呈现自身的内容都由仪器来决定,即仪器的视阈决定了人类和世界的视阈。主体和世界之所以能够相互“交流”是因为二者能够“交流”的部分乃是被仪器“体现”了的那部分,这就是仪器“干涉”和“转译”造成的结果。仪器干涉了对象使其成为了认识客体,同时仪器也干涉了主体,使其成为了被仪器中介了的主体。由此,“体现的人类”与“呈现的世界”之间才有了“交流”的可能,主体、世界和仪器成为了一个连续的链条,同时,“人类的体现”与“世界的呈现”必须被解释到生活世界之内,成为人类知觉可理解的形式才有意义。仪器成为将现象“转译”为一种体现的生活世界的解释学过程的主体,使科学世界的维度向生活世界敞开。
对科学仪器的实在论和现象学解析,不仅是对传统工具论的批判和超越。仪器的调节、统合、干涉和转译等作用不仅使我们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上重新定位科学仪器,而且也促使我们在本体论上对科学研究进行重新思考,即,科学研究的主体是否是理性主体?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否还是自在对象?对科学仪器的以上思考将可能成为推动科学研究中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
(感谢哈尔滨师范大学孙慕天教授、黑龙江大学周桂林和蒋红雨老师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