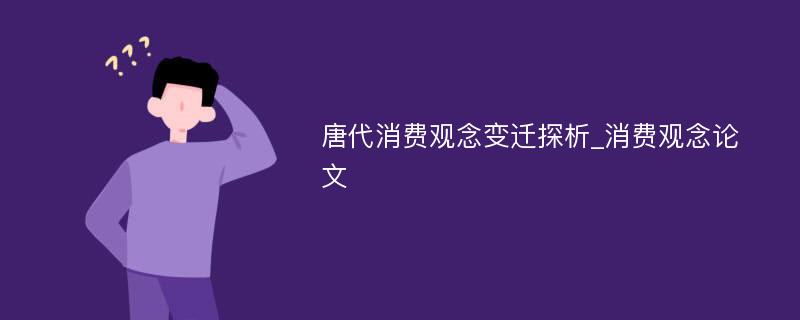
唐代消费观念变化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09)02-0013-05
消费观念是消费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一方面指导着人们的消费实践,另一方面又能动地作用于消费经济乃至社会经济。“由于生产的相对重要性的降低和作为生活方式的消费的重要性的提升,人们的社会角色、认同、态度、价值和日常生活的结构都发生着基本的变化。”[1]110不同的消费观念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同步。唐代是一个生产力不断进步的时代,也是一个兼容并包、易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国度,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们,其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无时不在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研究唐代各种消费观念的形成、变化及其发展,掌握它在特定社会中的作用和变化规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由节俭消费观向奢侈消费观的变化
奢侈消费观是一种与节俭消费观完全对立的消费观,它主张消费者大量地、无节制地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以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价值取向的更替,历朝历代消费观念的变化大都遵循这样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由初期的“尚俭”逐渐向中后期的“崇奢”演变。在这方面,唐代亦不例外。唐代由俭趋奢消费观念的演变过程,大体以开元、天宝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在此之前消费观念以“尚俭”为主流,在此之后消费观念逐渐向“崇奢”转变。
第一阶段:唐初至开元、天宝年间,社会消费观念以“尚俭”为主导。唐朝建立之初,由于隋末大起义的冲击,社会经济凋敝,物资比较缺乏,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在生活消费上大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节俭的原则。唐初的几位帝王也大都反对奢侈铺张,崇尚并推行节俭消费,也颁布过一些在饮食、衣着、器具、祭祀等方面的禁奢政令。
作为贞观之治的奠基人,唐太宗是一个善于纳谏,主张生活勤俭节约的皇帝。他深知稼穑之艰难,深知民以食为天的重要性,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一向坚持抑奢扬俭的指导思想,制定了一系列禁奢的规定。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2]295而他自己在日常消费中也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给臣子们作出了榜样。这种帝王的躬身实践,对俭约社会风气的形成起到了正确的导向作用。时至贞观十六年,当时粟价相当便宜,米斗仅直五钱甚至三钱,为此,唐太宗甚为忧虑,因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2]376他不仅自己努力做到“不听管弦,不从畋猎”,而且经常告诫自己的儿孙,警醒他们不要奢侈。史载太宗谓侍臣曰:“朕自皇太子立也,遇物必诲。见其将饭,告稼穑艰难,不夺农时,乃可常有。”受太宗皇帝的影响,后宫的奢侈消费得到有效节制,许多宫人能做到自觉节俭,如皇后长孙氏“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给而已”。[3]3802,686正是由于太宗皇帝推己及人的尚俭抑奢的努力,在其统治时期,出现了太平盛世“贞观之治”。虽然社会财富日益雄厚,但消费方式以俭为主,奢侈现象并不严重,“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2]295这种说法虽多少有些夸张,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段时期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大都能做到崇尚节俭、抑制奢靡。
在太宗皇帝的倡导下,后代皇帝大都能坚持尚俭抑奢,致力于推行节俭消费、适度消费。在其后第二个盛世的开创者唐玄宗统治前期,亦不仅倡导节俭,而且致力于力挽奢靡风气,出台了诸多革除奢侈弊端的措施。开元二年制曰:“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戊戌又敕:“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4]1701此后,他还下令关闭了两京织锦坊,等等。在宫廷崇俭风气的导向下,唐代前期黎民百姓的消费观念更是以节俭为主。尤其是“贞观之治”时期,民风淳朴俭约,不尚奢华浪费。当然,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有一些权贵、富人或明或暗地推崇奢侈消费,但这只是当时社会的一股潜流,仅在个别的富贵群体中暗暗涌动,不左右当时整个社会的消费观念,总体上仍以“尚俭”为主,不事奢靡。
第二阶段:从开元、天宝年间开始,社会消费观念日趋“崇奢”。经唐初几十年的积淀,至开元、天宝时期,经济发展趋势良好,国力鼎盛,家境殷富,人们的经济收入不同程度地增加。“是时,海内富实,……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5]卷51《食货志一》于是人们的消费欲望大大增强,消费需求不断扩张,消费水平日渐提高,日常生活开始出现奢侈消费现象。自唐玄宗统治中期以降,唐人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较大变化,上层社会开始转向崇尚奢侈靡丽。“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3]1553宫廷消费向来是世俗消费的导向,崇奢风气始自宫廷。对于唐玄宗的奢侈消费行为,史籍记载不绝如缕,如唐玄宗“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沉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在他的纵容下,皇亲国戚更是肆无忌惮地奢侈糜烂,史载“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饰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啻数十万贯”。[6]1818在宫廷奢侈风气的诱导下,世风日下,奢靡趋高。都城长安奢侈之风更是超前于世风:“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7]卷下这说明唐人消费观念由俭趋奢的转变,影响着人们的消费习俗,刺激着消费方式的变革,奢侈性消费遂成为人们仿效、追慕的时尚消费方式。
二、由富足消费观向超前消费观的转变
随着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举国上下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特别是国都长安,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商贾麇集,财富集中,游人如织,消费空前,更有“冠盖满京华”之美誉。这使人们有条件追逐着“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的富足生活方式。章碣的《曲江》诗即描写了人们追逐欢乐生活的情景:“日照香尘逐马蹄,风吹浪溅几回堤。无穷罗绮填花径,大半笙歌占麦畦。”[8]7713特别是在各种节日期间更能显示出一派尽情欢愉、及时行乐的富足景象。以元宵节为例,唐代的元宵节是举国上下全民欢庆的一大盛事,从正月十四开始延续到十五、十六。这几天中人们尽兴观灯,尽情消费,整个城市观者如堵,游人如织,蔚为壮观。张祜《正月十五夜灯》诗曰:“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地京。”李商隐《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也说:“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8]5876,6275在长安的公共园林曲江,天天都是一派娱乐消费景象。王棨《曲江池赋》云:“是日也,樽俎罗星,簪裾比栉。云重阳之赐宴,顾多士以咸秩。”人们对这种繁华富足的生活方式,打心里非常之满足、留恋,希望世世代代都过着这种美好生活。为此人们对富足生活发出“愿千年兮万岁,长若此以无穷”[8]8027的祈愿。
生活的美好,人生的短暂,似乎是人生中最难以调和的两难矛盾,人们想留住青春、留住生命、留住美好的幸福生活,但生老病死的规律却是不可逆转的,由此引发了世人及时行乐的消费观。《太平广记》中的一则记载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消费观:“贞元末,有布衣,于长安中游酒肆,吟咏以求酒饮,至夜,多酣醉而归,旅舍人或以为狂。寄寓半载,时当素秋,风肃气爽,万木凋落,长空寥廓,塞雁连声。布衣忽慨然而四望,泪下沾襟,一老叟怪而问之,布衣曰:‘我来天地间一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见春日煦,春风和,花卉芳菲,鹦歌蝶舞,则不觉喜且乐,及至此秋也,未尝不伤而悲之也。非悲秋也,悲人之生也。韶年即宛若春,及老耄即如秋。’因朗吟曰:‘阳春时节天地和,万物芳盛人如何。素秋时节天地肃,荣秀丛林立衰促。有同人世当少年,壮心仪貌皆俨然。一旦形羸又发白,旧游空使泪连连。’老叟闻吟是诗,亦泣下沾襟。布衣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与秋时。争如且醉长安酒,荣华零悴总奚为。’老叟乃欢笑,与布衣携手同醉于肆。”[6]536日有春夏秋冬,月有阴晴圆缺,这本是天地间的自然现象,然而一旦与人的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规律结合起来,常使那些对人生感悟深刻的人萌发某种难以名状的凄凉,一方面难舍对人世的贪恋与情怀,另一方面悲叹自我生平历程的短暂。这种两难的心境一旦难以自我调适,便会产生无尽的痛苦,所以只有采取某些方式麻醉自己。在这则记载中,酒在被消费的过程中便充当了布衣与老叟自我麻醉的工具。这虽是以一个个案的形式传载于史籍,但反映了那个朝代、那种社会中的人们面对无情人生而去尽情消费的心理状态。
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追求更舒适的享受,乃人之常情,积极的、合理的消费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也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然而,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由富足消费观到“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超前消费观的变化。这种消费观的变化,在中唐以后尤为明显,其中又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政局已经完全不同于开元盛世了,开始走下坡路。各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伴随着时势变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失去了盛唐时期那种积极向上、慷慨昂扬的心态;同时,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局面遭到破坏,朝廷权柄失衡,威信下降,朝臣之间互相勾心斗角,倾轧不断;特别在永贞革新后,受牵连的大臣被杀的杀、贬的贬,这种遭遇使士人感到了报国无门、人生无常;加之政治的腐败,有才之人入仕受阻,社会生活的重大变故与个人理想的无情破灭,使士人产生一种超脱的心态和“沽酒过此生,狂歌眼前乐”的超前消费观。崔敏童的《宴城东庄》云:“一年始有一年春,百岁曾无百岁人。能向花前几回醉,十千沽酒莫辞贫。”[8]4504,2871这正是大多数士人及时行乐消费心态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唐朝后期社会开始迅速衰退,更使一些人产生消极心理,人生如梦,为欢几何,于是迫不及待地及时行乐,甚至不顾后果以声色自娱。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正是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超前消费观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
作为中国历史上三种传统消费观(节俭消费观、适度消费观和奢侈消费观)之一的奢侈消费观,是一种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的消费观,是一种消极因素大于积极因素的消费观。总体上看,当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消费而不是生产的情况下,奢侈消费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反之,它不仅对人们的消费心理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会极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健康发展。唐代亦然。
三、由商品性消费观向“拜物教”消费观的转变
开元、天宝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奢靡消费风气的日盛,商品经济价值与个体价值之间的联系和作用越来越密切和深入,商品性消费观日盛并逐渐让位于拜物教消费观。人的金钱意识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增强起来,对金钱的崇拜和狂热追求直接影响着人情世态,各种人际交往关系越来越服从于金钱关系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具体地、直接地表现为金钱关系。
由于商品经济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冲击,金钱至上的消费观使唐代上层富裕阶层生存取向的多维性渐被物化为单一的占有与消耗,成为官僚贵族、富商大贾等上层社会群体的价值追求。他们普遍认为自我价值只表现于自我的消费与享受之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人的精神向度的价值,使自身成为被动、贪婪的物质占有者和消费者。白居易在《相和歌辞·短歌行二首》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心态的实质:“世人求富贵,多为身嗜欲。”[8]216在物欲横流的上层社会里,金钱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纽带和桥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情感来加深的,而是以金钱的多寡来衡量:“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富贵疏亲聚,只为多钱米。贫贱骨肉离,非关少兄弟”,“本以势利交,势尽交情已”。[8]2027,9170,3114这些都是世人对势利世风的感叹,但感叹无非是一种牢骚,谁也无法凭借个体的力量去遏制、去扭转。
由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使得那些游离于奢侈消费群体之外且具有良知的仁人志士发出怀古的呼声。一生贫困、衣食不足的杜甫对此刻骨铭心:“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边塞诗人高适感叹曰:“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如云屯。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君不见今人交态薄,黄金用尽还疏索。”时人称誉为“郊寒岛瘦”的二君子之一的孟郊也很伤感:“古人结交而重义,今人结交而重利。有财有势即相识,无财无势同路人。”[8]2254,3294,206可见在金钱至上消费观指导下的生活方式,不仅意味着社会财富占有、消费的不公,而且还严重地威胁着社会最基本的消费伦理,使人们在消费心理方面产生巨大差势,迫使芸芸大众不得不放弃自己传统的消费观,转而加入金钱至上的拜物教式的精神信仰。诗人戎昱在他的《相和歌辞·苦辛行》中道出了他所代表的贫寒文人阶层的心声:“如今刀笔士,不及屠酤儿”,“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不只知识分子深深认识到舞文弄墨已经到了“不及屠酤儿”的尴尬处境,农民、手工业者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贫女苦筋力,缲丝夜夜织。万梭为一素,世重韩娥色。五侯初买笑,建章方落籍。一曲古凉州,六亲长血食。劝尔画长眉,学歌饱亲戚。”[8]237,6986文人士子、下层劳动者皆认识到金钱之于人的生活、人生的重要性,至于商人则更不用说了。在名与利之间,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经商牟利,逐利行为的普遍也反映出这个社会金钱至上的世风。
家庭财产的贫富、消费水平的高低是划分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标准,因贫贱而遭人看不起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那些身居陋巷的孤寒志士,虽然有“颜回之乐”作精神支柱,但因缺乏物质生活的支撑,精神支柱未免有些疲软。有诗为证:“陋巷孤寒士,出门苦恓恓。虽云志气高,岂免颜色低。”之所以让这些志气清高的寒士“苦恓恓”、“颜色低”,是因为“昔年洛阳社,贫贱相提携。今日长安道,对面隔云泥”。昔日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故交,早已把“苟富贵,毋相忘”的诺言丢到九霄云外了。可见由于贫贱而被亲朋故旧所遗忘、看不起的滋味是多么的难受了。在这种“笑贫不笑娼”的氛围中,只有想方设法积聚财富才是一个人挤进社会主流的唯一出路,否则连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太婆都笑话你。寒山有首诗云:“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8]4687,9163可见拜物教的金钱观无缝不钻,竟已浸染至老人这种弱势群体。在外面遭到冷落尚可忍受,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因为贫穷不能养家糊口竟然遭到妻儿的鄙视,白居易《读史五首》中描写的季子即是这样一种遭遇。诗云:“季子憔悴时,妇见不下机。买臣负薪日,妻亦弃如遗。一朝黄金多,佩印衣锦归。去妻不敢视,妇嫂强依依。富贵家人重,贫贱妻子欺。”[8]4690这首诗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对于追逐功名的读书人。他们摆脱贫寒的奋斗目标无非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旦这一理想不能实现,别说是外人看不起,就是家人都不拿正眼看。《唐人说荟·玉泉子》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说是当时有一名叫杜羔的寒士累举不中名落孙山,其妻深为不满,寄诗奚落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如此嫌贫爱富,竟然让其夫夜里回家,想必杜羔感受到了奇耻大辱。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杜羔考取进士以后,其妻却一反常态,谄媚地又奉一诗道:“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8]9082落第时,竟让夫君夜里回家;中榜后,关心丈夫的狎妓行程,同出一女之一倨一恭行为,实在是判若两人。所以,在那种金钱至上的社会、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呢?[8]4687
上述这种世风的形成,说明商品经济状态下,商品和金钱较多地与人的物质利益、短期效益和局部利益挂钩,人们追逐的是眼前利益,较少地与人的精神利益、长远效益和整体利益相联系。对于这种不正常却又相当普遍的金钱至上观念浸润下的社会现象,人们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根据生产力判断标准,商品经济是一种先进的社会经济,代表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商品意识和金钱意识是一种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消费观念,应该是一种进步或者说是合理的价值观。特别是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却非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商品与金钱主要发生在消费经济领域,与人的物质生活密切相关。正如白居易所言:“世人求富贵,多为身嗜欲”,而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为的也是“残杯与冷炙”。[8]216,2252他们不是不懂得脸面的重要,而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商品经济状态下的消费活动,人们更多地注重经济行为,对人性伦理则有意无意地或削弱或忽略。
亚当·斯密认为,人们同时拥有贪图享乐与追求进步两种欲望,如果前一种欲望占上风,就会产生奢侈性消费行为;如果后一种欲望占上风,则会产生节俭性消费,而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不断发展、进步,就是因为节俭消费占上风。[10]76中国也有一句古语“成由勤俭败由奢”,体现了国家、社会乃至家庭兴衰成败的历史规律,历朝历代皆视之为修身之至理、齐家之根基、治国之大脉。应该看到的是消费观念在唐中后期以后由“尚俭”向“崇奢”发生变化的同时,“崇俭抑奢”的传统影响并未完全消失。从皇帝到臣民,倡导、实践节俭消费者大有人在,即使在最高统治者当中,也有一部分人依然视节俭为应予发扬光大的美德,仍希望坚持这种优良传统。不少皇帝身体力行倡导节俭。如肃宗皇帝,“帝性俭约,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5]卷51《食货一》一个掌握大唐帝国财富的最高统治者,能够将“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德宗即位后,有一年“蝗旱为灾,年不顺成,人方歉食”,为此他降旨曰:“来年正月一日朝贺宜罢。”[11]卷51《岁歉罢朝贺诏》不仅如此,他还曾下诏“令尚食每日所进膳各减一半,宫人等每月惟供给粮米一千五百硕,其馀悉皆停省。年食支酒料宜减五百硕,飞龙厩马,从今已后至四月三十日已前,并减半料”。[11]卷63《优恤畿内百姓并除十县令诏》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皇帝,能够在大灾之年主动停罢朝贺,折减膳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抑制奢侈性消费的蔓延,缓解消费不公引起的社会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不过,就实践情况而言,戒奢与崇俭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并不能也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个中缘由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一方面在口头上念念不忘崇俭戒奢,另一方面又大都过着骄侈淫逸的糜烂生活;就是一般民众在收入增加、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时,生活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因为不断提高消费水平,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与条件乃人之天性,它必然会影响到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和消费方式的变革。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人群体成为消费水平仅次于官僚贵族士绅的一个富裕阶层,他们在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的变革中也发挥着先导作用,对传统的崇俭戒奢消费观形成了较大的冲击。这也是节俭性消费不能自始至终贯彻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制约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