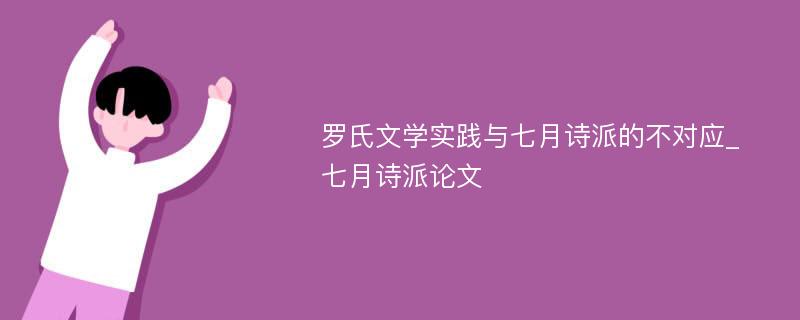
罗洛文学实践的不对应现象与七月诗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I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6)01—0081—09
罗洛(1927—1998),1946年开始进行革命文艺活动,解放后加入华东作家协会,1955年因胡风案受到株连,后在青海工作,1984年后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等职。作为一位诗人、作家、翻译家、文艺评论家,罗洛数十年笔耕不辍,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诗歌、散文、诗论、译诗和文学评论等。从罗洛的文学实践看,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学实践的不对应现象,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诸多特征之一,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一
对相当一部分人而言,认识罗洛的名字是在20世纪80年代。罗洛在80年代出版了3种译诗集:《法国现代诗选》(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魏尔伦诗选》(1987年漓江出版社出版)、《萨福抒情诗集》(198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80年代的诗歌读者,在我们的印象中罗洛仅仅是一个诗歌翻译家而不是一个诗人。罗洛的译诗集确实对当时年轻一代诗人形成自己的诗歌倾向、美学趣味和诗歌感受力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他的翻译体现了对现代汉语表现品质的高度敏觉、特异的节奏把握能力、准确细腻的语感。如,他的译诗中的诗句:
当她们呼吸着夜而灵魂慢慢地/飞向阿弗洛狄忒,/那处女一定坐在静寂中阴影里,/因羞愧而浑身灼热。
她感到惊讶,脸色苍白地把自己归于/那温柔的预示,/它,通过一张年轻面孔而转向未来的/一个现存的肉体”[1]31—32
睫毛敲击出什么样的沉默!/而在黝黑的胸下,什么样的呼吸/爱抚着树木胆怯的影子!/另外的睫毛像雌蕊在闪烁!/“吹哨吧!吹哨!”它对我歌唱!/我感觉到一阵阵的战栗,/我的巧妙的鞭子是那样的长,/在我经受的这一切纷扰里:/它们滚卷着,从我冠上的/绿玉,直到危险地失去控制![1]38
这是瓦雷里《致悬铃木》的两节和《蛇》的一节,译诗的表现力非常生动细腻,读后给人以深切的感触印象,十分难忘。
罗洛从1948年开始学习法语,并开始接触法国现代主义诗人的诗歌,在他的译诗《魏尔伦诗选》中,魏尔伦诗歌所具有的亲切感、飘忽情绪和强有力的敏觉,那种深哀浅貌、短语长情的特点,那种即使在倾诉痛苦和哀伤的时候也使诗句保持着天鹅绒般质感的特征被翻译出来了。如《巴黎速写》的一节和《诗的艺术》的一节:
月亮把她锌制的盘子/斜放在钝角上。/浓黑的烟的尾羽,像一个5 字/从高高的屋顶向上升扬。[1]151
让你的诗在冒险中得到幸运,/在清晨的卷风中瓢散开去,/使百里香和薄荷发出香气……/而其余的一切便都是散文。[1]225
类似的翻译诗句在他的译诗集里非常多,限于篇幅不再举例。这些译诗的中文表达几乎达到了完美无瑕的境地,从而给现代汉语诗歌带来了一种融纤细敏锐的感性和严丝无缝的智性于一体的特殊的精神气质。读者通过阅读可以感受到诗歌通过汉语的表现所产生的巨大魅力。
除了80年代出版的3种译诗集,在《罗洛文集·译诗卷》里, 还收集有罗洛生前翻译的15个国家92位诗人的302篇诗歌作品。同样,在这些诗歌翻译中, 罗洛凭借着自己精通多国外语的有利条件、对不同国家诗人的了解及自己敏感的诗性,熟练地驾驭着汉语语言,他俨然是一位通晓语言秘密的大师,深知用简练的口语表现、调和出完美和谐的语言艺术色彩。罗洛在翻译中表现出的才华在现代诗人当中是为数不多的,他的译诗确实给80年代以后的许多青年走向文学的道路带来了特殊的嘉惠,他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外国诗歌翻译的佼佼者。
在翻译理论上,罗洛自有自己的观点。他不赞成过分自由的“意译”,认为为了保持原貌,译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尽量依从原诗;但也不赞成对原诗每个音节都亦步亦趋,过于拘谨而使译文难读。在《译诗断想》中他认为,“如果原诗是格律体,译诗也应该是格律体。当然不是说要用五字句、七字句等等来译十四行诗或亚历山大体,但字数或顿数应该大体整齐。也可以采用大致相近的韵,但韵脚的排列则应该依从原诗。如果原诗在形式上有独特的处理手法,译诗也应尽可能地表达出来。”[1]318 对罗洛来说,诗人真正的好诗常常可以不受形式的限制束缚,而在格律上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手法。因此,译诗最为重要的是要在译作中表现出原诗的风格、诗意和韵味。许多译诗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常常不是由于形式的缺点,而是失去了原诗的风格和诗味。所以,罗洛在长期的翻译过程中信守着一条原则,就是“译出来的诗必须仍然是诗。读者即使不看原文,也能感到那是诗,而不是别的什么;而且那是某一位诗人的诗,而不是任何其他诗人的诗”。[1]320 要做到这些,罗洛认为翻译国外诗人的作品对翻译家来说是一种创造,这是一项翻译家不能不参与的创造,准确地讲是翻译家参与诗的再创造,再创造出和原作尽量相似的艺术品,从而产生相应的艺术感染力。再创造就是要在译诗中既保持有原诗的形,还要有原诗的神。“就诗而言,形、神是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因而译诗既要神似,也要形似。如果仅取原作的意思重新写一首诗,那就不是翻译而是摹拟原作的创作了。”[1]321 对罗洛来说,诗歌翻译家是不能仅仅维持在“创作”水平的,必须要进行再创造,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感受到诗歌强烈、震撼人心的力量。但同时,罗洛又强调了这种再创造的自由是有限度的,不能因再创造而有损于原作。
敏感性是一个诗人最重要的品质,在译诗中如何表现原作诗人的敏感性,诗人借助这种敏感性可以把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转化为具有诗意的艺术品。在《诗的敏感性》一文里,罗洛认为在译诗中,一定要注意原作诗人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独特感受、独特表现方式,要让译诗的读者能感受到原作诗人所讲的是“活生生的现在”。也就是在译诗中,要“尽力表达出这样一种现代感”。[1]327 如,他翻译惠特曼《你,带着同样的孩子的母亲》的一节:“新世界的首脑,你有何等艰巨的任务,/制定‘现代’——从现代的无比崇高中,/从你自身中,包容着科学,重新塑造诗歌、教堂、艺术,/(重新塑造,也许屏弃它们,结束它们——也许它们的工作已经完成,谁知道?)/通过幻想、手、概念,在已死亡的强大的过去的背景上,/用绝对的忠诚描绘强大的活生生的现在。”[1]630
在罗洛看来,惠特曼的诗是自由、雄辩的,像海浪一样层层相催,具有内在的节奏,在字里行间流动着一种热切的活生生的现在的呼唤。所以他的译诗也尽可能地表达出了强烈的现代感节奏,读者读起来非常富有韵味,似乎感到惠特曼就在我们面前表达着我们自己对现代社会的赞美及对未来乐观昂扬的诗歌调子。
另外,罗洛认为翻译后的诗必须应该是耐读的,是可以嗟叹和咏歌的。“如果一首译诗能够让人反复吟咏,甚至久读不厌,那么也许这就是一篇成功的译作。如果反之:语言是乏味的,意境或结构是破碎的,韵律或节奏是跛脚的,这样的译诗是否可以称之为诗,就值得怀疑了。”[1]321 他所持的这种翻译观念虽然在比较文学、译介学的历史里常常被提及,但是在我们的翻译实际中却往往被忽视,有些诗歌翻译家的译诗也非常注意格律、韵脚、与原作的相似等,但由于忽略了读者普遍不懂外语等文化因素,往往会造成读者对译诗难以理解。而罗洛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的译诗易懂、耐读,给人以强烈的语言感染力。这不能不说是罗洛对中国的新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二
罗洛作为进行革命文艺活动的开始是在1946年,但如果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罗洛决不能算一个成功者。虽然已出版的《罗洛文集·诗歌卷》从量上十分厚重,远远超过了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的新诗创作量。然而,这些诗歌的质量是无法同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等人相比的。在罗洛的文学实践中,他一方面在诗歌翻译上体现出了自己的超卓不凡,另一方面在诗歌创作上又表现出了自己的平庸随俗,罗洛在翻译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的精神敏感性在他的创作里确实看不到丝毫痕迹,对有些人来说,是无法容忍这种精神的敏感性被淹没在庸俗趣味的创作当中。“他在译诗中体现出来的语言敏感、丰富细腻的感受力、严密的思维,好像全部典敏给了翻译。”[2]126
为什么会这样?这似乎构成了一个二元悖反的精神命题,对这种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的不对应现象个案,只有从罗洛的经历进行了解。
从创作的时间看,实际上很难说罗洛属于七月诗派的成员,但他在创作上和诗歌理论上却都深受这个流派的影响。七月诗派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战火声中诞生成长的诗派,这是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时期的一个特殊的时代,是一个全民族共同高唱救亡歌曲的时代,也是诗歌民族化、大众化要求取得对精神和诗歌艺术探索的胜利的时期。七月诗派的成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共同的信仰和向往。在诗歌创作上,诗人们严格遵循着自己创立时形成的诗歌理论。七月诗派的理论基础是胡风的主观性战斗精神。胡风的诗歌观念是一种高扬主观精神的现实主义诗歌观念,他的“主观精神”在当时实际上就是指抗战初期那种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高扬热情。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胡风自觉地继承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实主义诗歌观念。他认为,“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是为人生而文艺,并不是为文艺而人生,……现实主义者底第一的任务是参加战斗,用他的文艺活动,用他的行动全部。”[3]515 在这里,胡风强调的是文学的战斗性,而且十分绝对地要求文学要起到改造社会改造人生的作用。在抗日的民族战争全面展开的时候,作为诗人实际上担负着意识战线领域的任务,也就是“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量”的任务,这时“作家应该去深入或结合的人民,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感性的存在。”[4]189 同时,胡风还高度强调了诗与时代的关系,诗人与生活的关系。他希望诗人扎根现实生活的土壤,面对人生,深入生活,这样的创作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早在艾青的第一部诗集《大堰河》出版时,胡风就认为:“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里,诗应该唱出一代底痛苦、悲哀、愤怒、挣扎和欲求,应该能够丰润地人生养育而且丰润地养育人生。”[3]454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说:“诗人底生命要随着时代底生命前进,时代精神底特质要规定诗的情绪状态和诗的风格……人民在受难,人民在前进。诗,我们这一代真诚的诗,应该是对于这个受难的控诉的声音,应该是对于这个前进的歌颂的声音。诗人,我们这一代底真诚的诗人,应该在受难的人民里面受难,走进历史底深处,应该在前进的人民里面前进,走在历史的前面。”[5]753 七月诗派的诗人们把人民的愿望当作自己的诗歌理想,要反映时代的真实,而时代的真实就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和领导下同国内外敌人进行生死搏斗。这实际上是对文学与时代内容关系较为简单的一种理解,作为文学功用主义倡导在当时具有实际的意义,但作为文学思想,它是一种较为狭隘的诗学观念。七月诗派要求这个诗派的诗人们放弃个人的自我,从而使诗人们自觉退出了个人在精神领域的探求和思考,也使诗人们失去了对诗歌艺术开拓的追求意向,诗歌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
值得注意和肯定的是,七月诗派诗人们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现代社会中充满热情和力量的时代,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氛围把诗人和大众的心联系到了一起。所以,这种现在看来狭隘的诗学观念,并没有完全遮蔽诗人们的艺术生命力,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中华民族普通大众身上所具有的坚忍不拔的意志,也给诗人们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使其很多作品具备了深沉厚重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力量。
胡风的诗歌观念和七月诗派诗人们的创作,在当时对青年显然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作为四十年代的青年学生,罗洛“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不满和反抗,对未来新中国的憧憬和希望”。[6]63 他必然要追求历史的进步,接受共产党的指引。胡风的诗歌观念显然是被罗洛相当全面地接受了。绿原在《罗洛文集·序》中说:“罗洛从青年时期接受了阿垅、胡风等前辈诗人的诗教,对诗的创作过程早有他的原则性的见解。”[7]序6 那么,罗洛的原则性见解是什么呢?罗洛在1947年12月至1948年4月的《信底短片》中他表达了自己对诗歌的理解:“诗是情绪的结果,而情绪又是由生活而来,没有生活内容的诗不是诗;诗歌要从人民中来向人民去。对自己来说就是要“加强了主观战斗和加深了自我改造。在向世界作战之前,必须先向自己战斗,这战斗就是使人成长的力量。”[7]23 后来,罗洛就他第一次以“罗洛”的笔名发表处女作撰写了文章,对他在解放前写诗的情况进行了回顾,“到一九四六年,我对社会、对人生、对诗都有了一点新的认识,对以往写的诗越来越不满意。以往写的诗,大都局限于学校生活,仅仅反映出年轻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光明的朦胧追求,而且常有‘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我已开始认识到:诗应该反映真实的现实人生,应该反映在苦难中挣扎、斗争和前进的人民的生活,不能停留在个人狭小的感情世界里雕琢一些精巧的生活装饰品。从《在悲痛里》开始,我不再在个人灵魂的窗口徘徊,而把目光投向社会现实斗争。此后几年,我写了一系列的政治诗和社会讽刺诗,我认为这是当时斗争所需要的。”[1]293 这些话我们现在看来都应该是真实的。的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一个正直、进步的年青知识分子而言,这种思想和精神的选择是符合逻辑的。
罗洛早期(1946年至1949年)的诗歌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战斗性,显示其深受七月派诗人及诗歌风格的影响。如1946年8 月的《在悲痛里》:“让生的生/让死的/死!意志不结冰呀/战斗的信念/不磨灭!”[7]4
1946年12月的《短歌》:“战斗的道路/沙石磨破脚掌的道路/(一步一滴血啊!)/寒风吹击的道路/(困忧着呼吸和跳荡的脉搏)/从家走向牢狱/从阳光走向墓地的道路/(如果需要牺牲/为什么要吝惜自己呢?)”“路上荆棘丛生么/我们有岩石的意志/路上沙漠绵延么/我们有骆驼的脚步。”[7]6
表现年轻的诗人对旧社会的愤怒和对新生活的向往,诗歌语言的表达是非常直接的。如1948年2月的《出发》:“这街道多苍老啊!/破烂的房屋像披满了灰尘的僵尸一样立着/那边还有一间房子要倒了,用木柱支住/行路的人就在木柱下和木柱旁泰然走过……/啊,这城市该有一场大火了!”“我不是不坚强的,而眼泪竟热得发烫啊!/我的眼圈发红了吧?/二十年了!我生活在这里/行走在这里,拥挤在这里/哭和笑在这里,爱和恨在这里……/今天,再会了!/即使流了泪我还是坚强的!我要毫无顾惜地跨过这古老的城市/我要回来!回来在废墟上重新建设它!”[7]9
1948年3月《旅途》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和人民的关切、热爱, 充满了年轻人的一腔热情:“我沉在情绪的起伏的海里了……/我的周围是陌生的人们,我不会被他们了解/我用双手捧着脸,我不要在他们面前露出/我的激动的面容/而且,风大,沙土也的确多啊!……”[7]11
有表现诗人对新的社会生活的急切的等待盼望心情的,如1948年的《时间》、《我知道风的方向》、《火与歌》等。罗洛早期的诗歌创作也有表现一个年轻人“小资情调”的为数不多的作品,如,《站在这小小的土岗上,我望着》、《时间》、《宙斯》,在这几首诗中,罗洛敏感的诗性火花闪亮了。
可是,对罗洛的文学创作来说却没有那么幸运。当罗洛刚刚开始按照七月诗派的理论进行自己的诗歌创作时,“这个时代就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永远过去了,青年时代的罗洛面对的是一个肤浅的乐观主义的时代。他在七月诗派影响下形成的诗学观念面对这样一个新时代显得手足无措,他所习用的自由诗在‘民歌化运动’的热潮中也显得不合时宜。”[2]127 罗洛的创作的确是如此。刚解放后的诗歌(1950年至1955年)主要表现诗人紧随时代步伐的理想主义和面对新的生活所产生的喜悦心情,格调是清晰、明快的,但内容缺乏作为诗人自己的个性特征,诗人仅仅是一个时代政治的歌手。这时,诗人一方面不能放弃自己的追求和已形成的诗风,一方面又必须检讨自己。诗人在1951年写道:自己解放前写得东西“在今天看来,和这一伟大的时代相比,我底这些情绪表白,是显得有些寒伧了”。[6]25 作者在这一时代的普遍矛盾之中,把诗看作是时代精神的直接呐喊,《黎明》、《我爱》、《春天来了》等皆是。如《我爱》中的诗句:“我爱戎冠秀、郭俊卿/我爱英雄们走过的道路/我爱那路上每一滴血迹/我爱通过痛苦、牺牲的幸福我爱毕加索的鸽子/它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飞翔/我爱母亲的爱抚和婴儿的哭泣/我爱诗歌如同小麦和钢铁一样生长。”[7]34 这里,诗人完全失去了自我,自我如同小麦和钢铁一样是随时代“生长”的,而不再是被表现的。
又如,1954年秋作的《河上》:“绿油油的河水/哗哗地响/年轻的姑娘/划着船桨/船舱里/是新割下的稻米/是期待已久的/希望的果实/船舱外/是漫天的阳光/是富饶的田野/是江南的水乡”[8]51 在这首诗中,诗人想极力使自己的诗歌向民歌靠拢,在语言的表现上非常民歌化,但内容也十分空洞苍白。同时,在这段时期罗洛不多的创作中,还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带有应景性质的诗作,如《致珈丽娜·乌兰诺娃》、《还有什么——给少年舞蹈家们》、《马头琴——听蒙古艺术家演奏》、《波兰》、《蔷薇》等(这类性质诗的风格对他“文革”后作为文化官员的应酬诗的风格是完全一致的)。这些都反映了刚刚开始创作不久的罗洛面对生活的变化既不适应和又极力要去模仿、适应的状态。解放后我们的绝大多数作家们在当时都是如此,年轻的罗洛自然不能幸免,对他来说,七月诗派的诗学观念在当时是胜利者的诗学观念,必须是要紧紧遵循和依赖的。可以说,罗洛在这个时间基本形成了自己的诗歌创作格调和诗学观念。1955年,不幸又对罗洛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沉重的影响,他和七月诗派的诗人们一起牵连进了胡风政治冤案,28岁的他失去了写作的自由。在《罗洛文集·诗歌卷》中,收集有罗洛在1957年至1963年期间创作的10首诗,这些诗的时代性色彩淡化了,其中也有个人的一部分抒情,但表达都较拘谨,缺乏诗性的力量。
三
《罗洛文集·诗歌卷》中,绝大部分诗歌是在“文革”以后完成的。对诗人而言,当他重新焕发精神抄起诗笔进行写作时,历史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0年代是中国20世纪一个思想解放、西方文化思潮被大量引进的时期,整个社会充满了一种蓬勃向上的热情和活力,但是它与40年代的时代气氛又是截然不同的。它有热情,但却是一种个体生命的热情;它也有力量,但却是一种个体意志的力量。40年代那种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的团结一心的热情和力量是这个时代所不具备的,这个时代最为缺乏的就是把诗人和人民群众的心维系在一起的共同的时代精神。在精神文化的领域里,一系列的“伤痕反思”、“文化寻根”等社会文化现象都表明了这非一个团结和显示集体力量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一种现成的价值是可供人和诗的栖息地,每一个体都必须独立地承担起自己的命运。繁荣而多样化的80年代的中国诗歌创作表明,诗歌的价值在这个时代体现为诗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对人类精神价值的维护。但是,重新抄起诗笔的罗洛面对如此的诗歌创作环境和转型的时代精神,他诗学观念并没有发生改变。他仍然坚守着明显已过时的七月诗派的诗学观念,把新诗丰富的传统简化为一个所谓的“战斗传统”。他在1981年谈关于诗与自我的关系时说:“诗人总是借抒‘我’之情,来抒人民之志,来言人民之志。对于一个诗人,情和志总是水乳交融般融合在一起,有机地统一于诗。诗人是人民的歌者,是社会主义的歌者。他决不歌唱‘自我’的喜怒哀乐。一切脱离人民、脱离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对他都是格格不入的。在他血管里流的是血而不是水,更不是污浊的水。”[1]7 由此可见,他的诗歌价值观是长期不变的, 是完全寄托于一些已经与现实生活失去血肉联系的简单粗暴的观念。在罗洛看来,他在青年时期形成的诗歌观念是绝对不可能进行反思的,是不能变动的,他的诗歌生命离不开这些观念。而从文学历史的角度看,罗洛坚持的这种观念与他不得不处身的新时代的奇特的错位造成了一个作为诗人的遗憾。虽然从罗洛的经历看,1980年以后是他的诗歌翻译最为丰富的时期,但是在一种首先是诗人自我大脑中意识形态对创作的体制化控制下,再多的翻译并无助于提高诗人的创作活力。这个时期罗洛的诗歌创作意识与他在1955年以前的青年时代相比没有多大的差异,他的诗歌创作基本上是一个历经磨炼后的胜利者——文化官员,重返故地的抒情诗、应景诗和记游诗。在《罗洛文集·诗歌卷》中,第三辑《雨后》开始的创作占他的诗歌作品数量的绝大多数,但除极少部分的格律体诗外,在这庞大数量的自由体诗里想要挑出几首真正的好诗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对一个诗人来说,写出好诗的生命年代已经过去,罗洛“到1980年平反时已经五十三岁,应该说已跨入老年的门槛了”。[6]121 但对一个真正的诗人而言,年龄并不是唯一。如,同为七月诗派诗人的牛汉在“文革”后至21世纪,用发自生命的体验写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关键是不能失去在精神和艺术上进行探索的勇气,不能割断诗与自己生命的联系,不能放弃诗人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感受力、放弃诗作为对人类本真终极探求的敏锐感和沉重感,如果放弃了诗作为思想精神栖息处的特性,就必然会造成诗人存在的空缺。
罗洛由于不愿意放弃七月诗派狭隘的诗学观念,所以虽然他也讲诗歌艺术的探索创新,但是他把诗歌的探索和创新仅仅局限在艺术的表现手法和诗的形式方面,“为了提高诗的表现力,我不拒绝浪漫派的想象的翅膀,不拒绝现代派的隐喻和变形,象征和意像。在艺术表现方法上,现实主义不是简单划一,而是包容众多。”[2]24 “但是,如果脱离了诗的历史内容和社会内容,单纯地追求艺术表现手法的新奇古怪,我认为是不足取的。”[1]13 历史和社会内容是什么?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他看来,单纯地追求艺术表现手法会强调面向自我、面向个人的内心世界,就会忘记人民和社会主义的需要,诗歌就会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作为1953年加入共产党的党员,正是怀着这种对犯错误的恐惧而不敢在创作上有真正意义的诗歌内容意识的探索和突破。如,1980年的《白色花》,其中有:“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今天/每一个今天都将成为昨天/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痛苦/每一个痛苦都将成为欢乐/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不幸/每一个不幸都将成为幸福/是吗/不是?”[7]549 从诗的立意上讲应该是可以写得很深入、很有沉思性内容的, 当然这首诗也表现了一种思考,但这个极富可拓展的诗性空间的命题却被肤浅的乐观情绪所遮蔽了,形式和表现手法的讲究并不能掩饰思想对人的本真存在探求的贫乏。在罗洛“文革”后的诗歌作品中,虽然有一些形式上的变化,如:增加了许多十四行诗、格律体诗,自由体诗的写作也十分随意,但是由于缺乏心灵和精神的力量,这些变化并不能确立自己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
《罗洛文集·诗歌卷》收集有格律诗147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诗人在1980年前的作品。这些格律体诗大部分读起来可以使人感到诗歌意味的存在,在随意自然、变化自如的形式中感到了诗人真情诗意的流露。格律诗体的短小要求诗人要尽可能地集中表现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要求诗人要放弃更多的其他。所以,格律诗倒突出体现了罗洛的诗歌感受力,而这跟罗洛在翻译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感受力是一致的,我们可以说罗洛的译诗是受他格律体诗创作的影响,他的译诗得益于格律体诗。但是从他大量使用的诗歌形式上看,他使用的是自由体。这是因为罗洛的诗歌观念中,把格律体诗看成是与自由体诗对立的形式,自由体诗表现的是革命的战斗,而格律体诗是无法表现这种战斗的。“诗离不开政治:在革命、建设和人生的斗争中,都包含着政治的内容,最好的诗,不是这些斗争的进行曲,便是凯旋歌。”[1]19 罗洛虽然也在许多文章中强调要继承中国诗歌的传统,但是对他而言首先重要的是:诗是人,是现实的人,“诗就是人,做诗先要做人,做革命的诗先要做革命的人。”[1]214 按照他的思路,诗歌的形式和表现方法“是离不开所要表现的对象和内容的”。[1]304 格律体诗形式的本身只能表现“小我”,而不能表现革命、政治斗争过程中的“大我”,是与自由体诗对立的形式,在革命和政治的斗争中是不能正式使用的。显然,这样的诗学观念是多么偏颇,它对诗人在创作中的诗歌感受力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另外,罗洛文学实践中的不对应,一方面在鉴赏中、西方诗歌时表现出高度的敏锐性,另一方面又在诗歌评论中泛泛而谈。罗洛对20世纪初期法国现代主义、德国表现派及美国、罗马尼亚等国现代主义诗人们的作品评价非常准确,对这些诗人们精神的把握是那样的贴切、到位。如:他评价阿波里奈的诗:“仿佛是自然地融入形象,而他的形象又是明晰的、跳跃而有着内在联系的,有如经过巧手剪接的电影镜头。”[1]8 评价苏佩维埃尔是,“他的诗在令人惊奇的变化着的世界面前显示出一种自然的虔诚。而当他看到死亡不可避免地到来,因而对即将死亡的事物感到怜悯的时候,他的诗便具有一种悲剧的庄严气氛。”[1]8 评价勒韦迪是,“他的诗是玄想的,表达的典型情绪是一种苦恼的、焦虑不安的情绪。……他的诗的想像有如万花筒般的驳杂,他的诗之世界也就有如破碎玻璃构成的光怪陆离世界,其中晃动着一些不幸的、梦幻般的人物的影子。”[1]9 等等。罗洛的这些评语是无可挑剔的,他对诗的敏感可见一斑。同时,在《罗洛文集·诗论卷》第四编里,罗洛在对中国新文学新诗的鉴赏中表现出来的艺术敏感性也是非常准确、细腻的。但是,当罗洛为了要表现出自己强烈的政治思想倾向时,在对一些诗歌的评价上却又有所失态,看不出他是一个对诗的敏感性有深切体验的诗人。如,他在评价德国表现派时说:“表现派强调内在的真实,反对模仿自然,因而常常歪曲客观社会,使之变形。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歪曲的、变形的社会,表现派作家用特殊的艺术手法来表现这个社会时,确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真实。”[1]121 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内涵就如此简单?显然,这样的评价是不够水准和分量的。又如诗人昌耀的诗作《山旅》:“多少年过去了,/我总记得/在紫曦初萌的地平线上/那些美丽的琵笆犁,/有如惊蛰的甲虫,/扒开沃壤/在舂宫里展翅,/而播种者们修长的手臂/向天空划出一个个光的圆弧,/撒出一把把绿的胚胎……”罗洛对此的评价是,“祖国的山河是壮丽的,然而残留的伤痕时隐时现;历史在前进着,虽然也有过曲折和崎岖;人民是勤劳坚强的,虽然曾经历过苦难,正面对着困难。人民的形象,像浮雕一样镂刻在诗人的记忆里,凸现在诗行中”。[1]44 在这几句诗行创造的意象里,意象就等于人民的形象,如此评价简直不像出自一个对诗的敏感性颇有心得的人之口。罗洛在诗歌的鉴赏和评价上的两种不同的姿态,不得不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同时,罗洛一方面认为新诗应该要不断地进行借鉴、探索和创新,他说:“对于一个诗人,不断探索的精神是最最可贵的。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诗人的生命线之所在。”[1]338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诗歌,都各有其特色和优点,都有可供借鉴之处。……在诗歌艺术创造上,我主张古今中外兼收并蓄,对外国诗我赞成‘拿来主义’,不宗一家而博采众家之长。”[1]308 可另一方面他又在对诗歌中精神、意识的自我探索进行限制。在罗洛看来,“创新首先是创立新意,离开内容单纯去追求手法的新奇是不足取的……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下,表现手法的创新和多样化正是艺术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1]83 虽然他承认西方现代派诗歌“也并不全是一堆垃圾”,但他把创新和对西方诗歌的借鉴严格限制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而对其他方面则十分恐惧和戒备,认为只要内容不是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就是格格不入的“污浊的水”。有了这样根深蒂固的意识,就必然把他所翻译的西方现代诗歌中的诗人精神价值淹没了。而西方现代诗歌所表现的艺术手法和技巧,实际上是为了服务于西方人进入现代社会后对人类精神的探索,它是形式服从内容,这是不能分开的。否认其内容中的精神探索价值,也就等于取消了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存在的基础。这种人为的内容和形式的二元悖反说明了罗洛身上体现出的诗歌创作与翻译的不对应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罗洛作为一个诗人由于放弃了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探求,所以他不能从自己的西方诗歌翻译中受益并影响自己的诗歌创作,作为诗人的罗洛是一个失败者。而这或许正是中国20世纪文学中一个带有普遍性意义的现象。
四
罗洛文学实践的不对应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如大的政治环境因素、作家具体的生活环境、作家创作的准备、翻译与创作相互影响的理论总结等等,但笔者认为,主要是流派的原因。
罗洛的诗歌观念主要受七月诗派的影响,这一点在《罗洛文集》中看得非常清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七月派诗人实际上带有明显的传统中国文人的特征倾向,“主观战斗性”一方面是由诗人个体的性情所决定,一方面又由诗人个体的政治抱负和社会责任所决定。这性情是由现实而感悟产生的情,所以性情离不开现实的社会政治,诗是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积极拥抱和大胆投入。由于“主观战斗性”是针对“纯客观主义”提出来的,所以诗不需求探索在这之外的抽象和终极的本真。这个流派由于其成员大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是革命的。革命者在解放后必然是胜利者、得势者,那种由此而来的自信或说自负不仅在胡风身上体现,而且在50年代初年轻的罗洛身上也可看到。虽然七月诗派的领导人胡风在解放前夕就已“失势”,但是随着1955年这个流派的真正“失宠”,直至“文革”结束前,这个文学流派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史后中的地位实际上是处于边缘地位的,没有什么优越感了。可当胡风案平反后,七月派诗人又以重返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文坛上,这一次的胜利者是绝对的,在人们纷纷重新关注和认识这个流派的历史和现实时,更多的是予以肯定和赞誉。但这个流派的大多数诗人也在这时的自我慰藉中忘记了对自己诗学观念的反思。“胡风的主客观化合论由于受到传统思维的影响而表现出某种模糊性和理论的自我循环特点;他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缺少足够的包容性……”[8]552 这些胡风等人诗学观念明显的缺点并不是能被很多人所看到。在罗洛看来,七月派诗人的缺点,就是“题材较狭隘,言词较迂远,感情上的知识分子气息较浓”。[1]76 他对七月诗派的自我评价跟绿原差别不大,其中的一部分讲得也比较客观。可是,他还没有从作家个体生命的价值意义上去探索一个文学流派在文学史中的影响,在这一点上,罗洛明显不如晚年的牛汉。晚年的牛汉不愿把自己归属在七月派门下,其晚年的汉诗歌创作的丰富和变化的根本在于他的诗歌观念发生了变化。事实上,七月诗派是仅仅适宜于那个特定的战争和政治年代的,当社会生活发生变化后,诗歌也应回到它的本来地位,作为诗人的观念也应当发生改变。
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七月派诗人可以说是一个经历了太多苦难的诗人群体。但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在涉及对这个流派的评价时也受到了这个流派悲剧命运及平反昭雪的情绪性影响,缺乏反思的深刻性,没有把七月诗派理论负面影响的辐射强度与5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主导理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从而使“文革”后复归的七月诗派诗人只有慰藉而没有对自我的批判。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社会的文学批评力度贫乏的表现。
收稿日期:2005—06—07
标签:七月诗派论文; 诗歌论文; 胡风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读书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