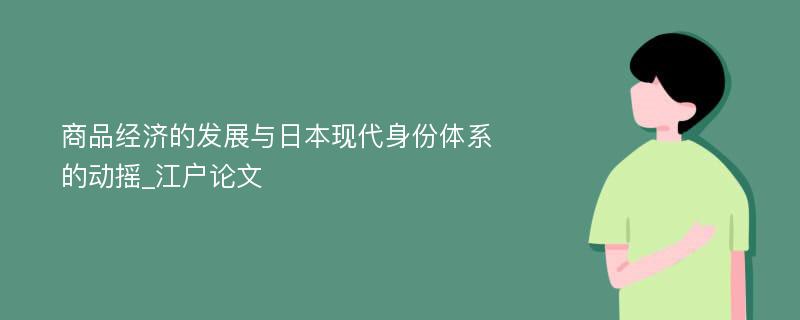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日本近世身份制度的动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世论文,商品经济论文,日本论文,身份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6)02-0029-11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6.02.004 肇建于织丰时代①的身份制度被德川幕府完整地继承下来并日益巩固、完善,一些儒家知识分子站在幕藩国家的立场上力图论证“士农工商”身份制度的合理性,身份制度和身份意识渗透到近世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成为支撑近世日本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要一环。但是,对于这一重要的制度体系,国内的专门研究几乎没有,仅有少量论文在讨论其他问题时涉及到身份制度,这些论文大多关注幕末,缺少对近世日本身份制度的通贯性考察,并且基本上只关注武士或町人,缺少对“士农工商”四民的整体关照,尤其缺少对农民群体的整体考察。此外,还有少量的研究著作涉及到身份制度,这些著作认为近世日本的身份制度存在着以下特征:(1)士农工商四民之间存在着严格的身份和职业区分,并且身份和职业世袭,禁止身份和职业之间的流动;(2)武士作为社会的统治者,其身份地位高于作为庶民的农工商阶层②。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政治权力对身份制度的强制规定性,却没有看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近世日本社会结构的冲击以及因此所导致的身份制度的嬗变。文章试图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身份制度的关系角度出发来通贯性考察近世日本身份制度的嬗变,并关照到“士农工商”四民整体,以期重新认识近世日本身份制度的真实样态。 一、日本近世身份制度的建立及其特征 身份制度是近世日本的基本社会制度之一,对于维持统治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世日本社会正是在身份制度的约束下运转的。在其形成过程中,检地、刀狩发挥了主要作用。 1582年,丰臣秀吉开始实施检地,其目的是为了在其控制的区域内扫除中间性的土地所有者,实现对农民的直接控制,以强化自身权力。太阁检地在制度上确定了拥有主人、负担军役的人及其他的人的区分,持有知行地即为军役负担者,持有耕地即为年贡负担者[1],在土地所有关系上确定了“兵”和“百姓”的身份。此后,武士脱离农村集居城下町,逐渐脱离与农村的政治经济联系,靠领主发放的禄米维持生活。因此,检地在客观上削弱了地方小领主的政治经济实力,防止了“下克上”的发生,对于稳定领主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检地扫除了中间性的剥削阶层,也是领主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的过程,确立起武士对庶民的一元化统治。 1588年秀吉又发布了“刀狩令”,为避免农民拥有武器而导致“年贡难入,发动一揆,对给人不恭”,禁止百姓持有“长刀、短刀、弓、长枪、及其他武具”,让他们“只持有农具,专心耕作,以至子孙长久”[2]83。这条法令使武士成为唯一的武力集团,而百姓则成为负担年贡、专事农业的生产者集团,武士和农民的身份得以确立,通过武士的武力垄断确立起武士对庶民的优位,促使兵农分离彻底化。 通过检地、刀狩,织丰时代已基本实现了兵农分离,武士成为集居城市、专司军事、行政职能、从领主获取禄米的治者集团,农民成为居于农村、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向领主缴纳年贡并承担诸役的生产者集团,町人则成为集居城下町、为封建领主及其家臣提供手工业产品和商品流通服务的流通集团,奠定了德川时代身份制度的基本框架,并规定了近世日本身份制度的基本特征: 第一,近世身份制度是一系列制度、政策的衍生物,是作为结果出现的,而不是作为目的出现的。中外学界颇有论者将1591年丰臣秀吉发布的“定”称之为“身份统制令”③,认为该法令将武士和农工商、农民和町人的身份明确区分开来,禁止各职业阶级之间的相互流动,是近世身份制度确立的基础。然而,该法令是为了“出兵朝鲜、确保兵员、将武士束缚在主从关系中、确保兵粮米而出台的,不是以从法律上确定兵农的身份分离为目的而发出的”,因此,“将该法令称为‘身份法令’、以身份的法制化为目的来解释是不妥当的”[3]。近世身份制度是在织丰时代实施上述制度和政策之后衍生出来的制度,并在德川时代以惯例的形式来加以继承、完善和强化。无论是织丰时代还是德川时代,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法令来规定这种制度。 第二,近世身份制度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军事强制实现的。兵农分离的本质是领主为了加强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贯彻领主权力而进行的,带有鲜明的强制色彩。丰臣秀吉于1590年平定奥州后,命令奉行浅野长政在奥羽地方检地,要求将检地推行至“六十余州,以至出羽奥州”。在刀狩令发布约40天后,加州江沼郡(今石川县西南部加贺市及山中町地区)一郡即收缴刀1073把,胁差1540把,长枪160根,笄④500根,小刀500把[2]84,由此可见刀狩令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这种制度的实施是以强权为后盾的,正因为如此,当幕藩国家的政治权力弱化时,身份制度也必然会走向动摇。 第三,近世身份制度在客观上导致了武士优位、领主优位、德川幕府优位的结果。检地基本扫除了中间剥削阶层,将领主权力直接贯彻到基层,实现了武士对农民的强有力控制,而“刀狩令”则剥夺了农民的武力,使农民在领主的政治经济剥削面前无力反抗,牢固地确立起武士的统治地位。德川幕府建立后,又屡次发布《武家诸法度》《诸士法度》,通过服饰、车马等方面的规定,来加强武士集团内部的等级秩序,还通过参觐交代制加强德川幕府对诸大名的控制。这一系列制度、政策的根本旨归就是为了确保武士对于庶民的优位、领主对于中下级武士的优位、德川幕府对于地方大名的优位。 第四,近世身份制度的稳定与否取决于石高制稳定与否。身份制度虽然确立了武士对于庶民的统治地位,但同时也切断了武士与农村的直接联系,1615年幕府颁布的《武家诸法度》第一条明确规定:“弓马者,武家之要枢也”[4]464,1635年的《诸士法度》还规定武士不得进行“买置商卖之事”[4]465,从而切断了武士与生产、经营的联系,成为社会的寄生阶层。日本近世中前期的思想家室鸠巢也认为“武士之重宝第一为能兵,第二为良马,第三为兵仗,第四为弓箭,第五为甲胄,此外财产器物全非武士之宝”[5]103。在江户时代初期,幕藩领主进行大规模的新田开发,同时,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石高收入不断增长,使武士的统治地位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身份制度也比较稳定。然而,由于幕藩领主生活的奢侈、城市经济的繁荣所带来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参觐交代制带来的物力财力浪费,无不消耗着幕藩领主的财政收入。同时,农民对年贡增征政策的极力反抗以及定免制⑤的普遍实施,使得因生产力的提高所带来的生产剩余脱离了幕藩的掌控而留在了农民手中。町人则利用从事商品流通工作的便利,攫取经济利润,其经济实力更进一步增大。由此,幕藩的石高收入必然受到影响,武士的优越地位也就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作支撑,而农民和町人的经济地位则在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说,近世身份制度本身就蕴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近世日本社会结构的嬗变 德川幕府建立后,实现了社会的和平稳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幕藩领主为了获得更多的年贡,也积极进行新田开发、兴修水利,为农民的农业生产提供物质条件。农民的土地持有权得到了国家的保障,在年贡村请制⑥下,农民向领主交纳一定量的年贡后,其余的产品可供自己支配,从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此外,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品种改良、肥料施用等因素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城市经济的繁荣。兵农分离之后,武士、町人都集居于城下町,1635年幕府开始正式实施参觐交代制,大名及其家臣须一年在江户居住一年在领国居住,其妻、子则作为人质常年居住于江户,因此,在城下町和江户形成了庞大的城市人口。在17世纪中期,江户的武士和町人的总数达到43万,到18世纪中期超过100万人,总的都市人口合计超过250万人,都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5%[6]228。庞大的城市人口必然会促进城市工商业、金融业组织的发展,以经济中心大阪为例,正德年间(1711-1715年)各地设在此地的国问屋⑦共有1851家、船宿⑧316家,专门进行大米、蔬菜、油料交易的专业问屋共有45种、2355家,其他问屋有14种、949家,可见其商贸的繁荣。1724年从大阪运到江户的主要商品有:皮棉103530捆,木棉10471捆,油73651樽,酒265395樽,酱油112196樽,米13278俵,炭251俵,鱼油296樽,盐6780俵[7]110。这些数据说明了城市巨大的消费能力,而且实现了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联系以及货币流通。 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性农业的展开。如前所述,城市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量。1714年进入大阪市场的主要农产品有大米、蔬菜、烟草、菜种、木棉、绢、布等,价值160416贯,占全部商品价值的56%[8]188-191。同时,由于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对衣料、食品的需求量,木棉种植业、蚕桑业发达起来。在木棉种植业方面,1705年摄津国平野乡的木棉种植面积达到水田的52%、旱地的78%[8]193-194;1714年运往大阪的木棉有1722781斤,棉子2187438贯,1736年运往大阪的木棉有1603878斤,价值3597贯[7]107-108。在蚕桑业方面,1715年6月至12月京都的和丝价值8151贯,到1735年前后达到约2万贯,增长了两倍多[8]147-148。 到了十八世纪三四十年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已席卷整个日本,日本近世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太宰春台在成书于1729年的《经济录》中写道:“当代天下之人……万事皆用金银已成风俗,远国殆同然也”[9]107,到了1740年代,他更明白地写道:“当代天下之人,无论贵贱皆集于江户,因为旅客之故,金银足为万事之用,已成风俗,未成为旅客者,如旅客一样,不以米谷布帛为宝而以金银为宝,即便是在山野,有金银即易得米谷布帛,故当今之世只是金银之世界,米谷只不过是满足朝夕饭食,布帛不过仅充衣服,其余无论大事小事皆可用金银办妥,故天下之人贵重金银百倍于往昔。当今之世,即便有米谷布帛而乏金银则难以立于世间,不仅小民之贱者,士大夫以上、诸侯国君皆然”[10]291。值得注意的是,“不以米谷布帛为宝而以金银为宝”说明的是以商品交换为特征的货币经济已经取代以贮藏为特征的自然经济而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即便是在山野,有金银即易得米谷布帛”,“不仅小民之贱者,士大夫以上、诸侯国君皆然”,更说明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社会阶层上都已经实现了全覆盖。这种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无疑会对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町人势力崛起 町人主要从事工商业,在商品流通中攫取利润,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这一群体成为获利最大的群体,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町人的经济实力雄厚。成书于18世纪前期的《町人考见录》记载,町人两替善六盛时是拥有二三十万两的富豪,居宅是一町平方的大宅。另一位町人两替善五郎在17世纪后期成为京都、大阪的第一大两替商,一年间获利上千贯,账面收入接近百万两[11]182、195。近世后期的著名町人三井、鸿池、淀屋家更为豪富:豪商三井家1813年拥有约74万3千两的总资产,1867年增至约94万6千两;在江户大传马町开店的木棉批发商长谷川家在1828年拥有约31万8千两的资产[12]348-349。町人在流通中获得巨大的利润,以至于近世中期的思想家本多利明在《经世秘笈》中指出,“天下之通用金银悉归商贾之手,豪富之名仅归商贾,永禄之长者武家皆贫穷,是故商贾之势逐渐盛而居四民之上。当时商贾之财货,如将日本国当作十六分,则十五分归商贾,其余一分归武家。例如,羽州米泽及秋田仙北郡一带的米,丰收之节,一升值钱五六文,交于商贾之手,运抵江户,不论丰凶即达百文”[13]。 町人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广泛开展金融活动,向全社会扩展势力,町人开展的面向大名的“大名贷”和面向町人的“町人贷”等高利贷业务就是其中的典型。如大阪最大的两替商鸿池家在1673年的町人贷仅占7%,而大名贷却达到了84%,仅1714年就获利2100贯银[14]。京都商人三井家向纪州藩贷款,从1719年的6万贯起逐年增加,到1774年,达到655000贯,年利率最低9.6%,最高达15%[15]。由此可见,町人的经济实力是多么雄厚,几乎控制了各藩的财政命脉及武士的日常生活,太宰春台写道:“诸侯垂首而向町人讨要,凭江户、京都、大阪及此外处处富商以渡世,贡租一至则归商人,收纳之时金主则封粮仓,以贡租偿还犹嫌不足,常常被追债,谢其罪犹不能安心,见金主如畏鬼神,忘却士之身份而俯伏于町人,或典当重代之宝器以救时急,家人忍饥挨饿而飨金主以珍膳”[9]128。生活贫困的下级武士也不得不向町人借钱以维持生计,如近世末期加贺藩下级武士猪山家1842年共负债银6260匁⑨,其中向町人借款3000匁,占到总借款的47.9%。而且,这些借款的利息非常高,最高的是年利18%,一般是15%左右。在最坏的情况下,猪山家一年要支付的利息就超过1000匁,相当于其年收入的1/3左右[16]56-57。 町人还通过完善的商业组织控制市场和物价。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城市中出现了大量从事物资流通中介的“问屋”。町人通过结成大阪“24组问屋仲间”、江户“10组问屋仲间”等批发商公会,对国内特别是各地于三都流通的主要货物实行广泛的垄断经营。通过这种批发商公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国内主要货物的运输、加工、供销关系网络和流通机构,而且具有了左右全国主要商品价格的权力,从而在市场控制和商品流通领域占据了凌驾于领主阶级之上的主导权。以至于荻生徂徕慨叹“商人们联合起来组成‘仲间’,依靠它来管理商业活动,商人个人无需做任何事就能够获利谋生,这样的经营方式成本花销很大,根本无法降低物价”[17]84。 (二)武士贫困化 兵农分离和石高制的实行,切断了武士的经济基础,他们不得不以静态的石高收入应对动态的经济生活,而为维护身份制度的连带制度体系——财税制度、参觐交代制度、等级制度等又束缚了幕藩国家和武士自身,从而使武士深陷贫困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首先,近世日本的财税体制存在先天漏洞,使幕府与各藩无法完全把握农民的生产剩余。在石高制下,幕藩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民交纳的年贡,然而,由于武士集居于城下町,其生活开支必然要受到城市市场经济的制约,从17世纪中期开始,日本的商品经济就不断发展壮大,到天保年间(1830-1844年),周防、长门国(现山口县)生产总值的52%来自农业,48%来自非农业(含林业、海产业),即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产值几乎相当。然而,幕藩国家对农业部分征收的年贡率达到47%,而对非农业部分征收的年贡率却只有2%[18],这也就意味着国家从非农业部分获得的税收收入是极其微小的。即便是农业部门,幕藩国家获得税收收入也与当时农业的实际生产力水平差距甚大,农民依靠自己的努力而增加的收入基本上成为课税之外的无地租负担的纯收入[19]。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彦根藩宇奈根村在正保期(1644-1647年)有旱地54町6反5亩17步,1651年的石高为53石3斗7升7合,到元禄期(1688-1703年)该村实际的石高是169石8斗4升1合,增加了3倍多,但村高依然固定为53石3斗7升7合[20]。这也就意味着,农村耕地面积的增加以及因此而导致的生产物增加并没有被幕藩国家拿去,而是留在了民间,成为事实上的“藏富于民”。 既然幕藩国家从生产发展中拿走的剩余有限,那么,伴随着城市物价的上涨、消费水平的提高、参觐交代的实施、农民对年贡增征政策的抵制,幕藩国家的财政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大名不得不向富于资财的町人贷款,即所谓的“大名贷”,然而,很多大名借款不还致使町人破产,因此,元禄、享保期(1716-1735年)以后,三都商人对此亦加以警戒,不向藩主融资,有的大名因被商人拒绝而坠入窘境[8]209。在这种情况下,幕府不断发布“奢侈禁止令”和“俭约令”,各藩采取的对策中实施得最多的就是家臣的“知行借上”,即实际上的减俸。太宰春台说:“近年来,大小诸侯皆贫穷,因国用不足之故,减少给人之禄,或即便给人死亡亦不补缺,或无罪而给予长假,此类颇多,与三十年前相比……发给给人之米已减少三分之一,大国诸侯如此,新国之小诸侯比比皆然也”[9]125,“近来大小诸侯国用不足甚为贫困,借家臣俸禄,少则十分之一,多则十分之五六,如不足则要求国民出金以救急,犹且不足则借江户、京都、大阪富商大贾之金,年年不已,仅还借款已罕见,况且息又生息,宿债增多不知至于几倍[10]289。在这种情况下,既导致了中下级武士的经济状况恶化,又使町人阶层获得了巨大的金融收益。 其次,“旅宿境遇”将武士全面卷入市场经济生活中。兵农分离后,武士集居城下町,1635年幕府又开始实施参觐交代制,不仅需要往返路途花费,还须在江户营造藩邸,因而耗费了大量财富。例如,1643年长州藩要将年贡米收入的90%以上作为江户入用,18世纪初的加贺藩也要将年贡米的1/3甚至更多作为参觐交代之用[6]229。近世中期的思想家荻生徂徕将武士的这种“只要不是生活在本人自己的知行所内”的生活状况称之为“旅宿境遇”。身处旅宿境遇的武士,在生活方面“哪怕是一根筷子都要花钱买来”,其结果是“当武士们到江户城生活的时候,他们要卖掉自己整年的知行米,用这些钱购置日用。他们殚精竭虑、奉公敬上得来的俸禄全都让住在江户城的町人得了利益。靠这些利润,町人们势力壮大起来,世界逐渐变小,物价不断上升,武士的贫困状况到现在已无药可救”[17]41-42。“武士们靠典当物品维持生活,或是让町人送钱来,自己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他们手中”,“不用现金购置各种物品的话,武士们连一天也生活不下去,以至于离开商人武士就无法生存”[17]82-83。荻生徂徕指出这种“旅宿境遇”是“天下贫困的根源”[17]69。 再次,武士的“身份消费”束缚着武士自身。在武士身份内部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且,武士要在服饰、家居、消费等各个领域表现得与庶民相区别,如1615年的《武家诸法度》就规定,“衣裳之品不可混杂”,“杂人不可乘舆”[4]455,此后颁布的历次《武家诸法度》都强调这一点,以此来维持武士的“格”。“‘格’是从日常举止、服饰、饮食、器物、住宅、佣人的数量、女眷的礼仪、信件往来、对使者的安排、在江户城活动时的随行人数、出行途中的安排,到冠婚丧祭的诸项礼仪等等,人们都要遵循的一套规矩。社会上流行的做法沿用下来,就成为‘格’,大名自己和他们的家臣、佣人们都十分看重这些,甚至认为只要不符合这些‘格’就配不上自己的大名身份”[17]69。日本学者矶田道史将这种消费称之为“身份消费”,这部分消费是很难削减的。以幕末加贺藩下级武士猪山家1843年的身份消费为例,此年猪山家付给家丁的薪资和生活费、交际费、礼仪行事入用、寺社祭祀费共达银800匁,占到了全体消费额度的1/3[16]77,从而给下级武士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这个角度来说,武士相对于庶民的优位反倒束缚了武士自身。 (三)农村阶层分化 17世纪中叶,日本的小农民基本自立,但农民中存在着阶层分化。抗风险能力低的下层农民在天灾人祸之际,不得不抵押土地以获取生活物资和缴纳年贡的资金,这种土地的抵押关系在17世纪后半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当农民无力偿还借款时,抵押的土地就变成“死当”,其土地所有权就转移到抵押主手中。1723年幕府正式承认土地的死当,此后土地的集中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没有了法律上的限制。富农与地主将其部分土地作为佃耕地贷给贫农层,从而形成地主——佃农关系。这种状况在近世后期越来越严重,从1873年发布的《地租改正条例》可以窥见土地集中的状况:全国耕地的佃耕率是27.4%,北陆、东山、东海、近畿、四国、山阴比这个平均数高,最高的是山阴42.7%,其次是四国41%,第三是北陆39.6%。佃农不仅耕作佃耕地,而且多从事雇工和零工活动[12]313。富农与地主同时又从事织机业和其他营业,经营质屋、酒屋、谷屋等,具有半商人的性质,还通过地方金融积累财富。即寄生地主多是兼营地主经营、农业经营、商业、小营业。豪农既从事农业经营,通过出租土地获取佃租收入,又从事商业、金融业获取收入,在经营方式上与町人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契合。 大量农民成为佃农或脱农化,直接造成农村的纳税农民减少,这直接影响到幕藩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幕藩国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又不得不采取年贡增征等措施,从而引起下层农民的反抗,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农村中的豪农地主剥夺了农民的生产剩余,成为幕藩国家和中下层农民之间的新阶层,从而使幕藩国家对农民的一元化支配实际上被架空。这两者都现实地瓦解了幕藩国家的统治基础。 本应享有尊崇社会地位、独享统治特权的武士阶层因其自身经济状况的恶化,成为近世日本社会的“悬浮”阶层。而在近世前期的身份制度设计中居于卑下地位、被剥夺政治权力的农商阶层中的一部分却因经济实力上升,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提高了地位,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可以概括为武士的“下流化”与豪农豪商的“上流化”,换言之,因商品经济对全社会的渗透,近世初期通过政治强制确立起来的身份结构因社会财富的不均衡分布而出现了严重的动摇。 三、商品经济冲击下近世日本身份制度动摇的表现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引起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社会结构因之发生变动,从而导致近世前期通过政治强制建立起来的身份制度走向动摇。 首先,社会的身份意识发生了转变,武士作为近世日本的治者集团,本来居四民之首,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威,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渗透,庶民阶层形成了自己的身份意识,强调自己身份对社会的贡献,武士的独尊地位受到了挑战。 町人思想家西川如见⑩在其著作《町人囊》中比较了武士身份和町人身份的差异,认为“武士卖身于主人,努力军阵,治世不能逞其志,短暂相交不能逞其武,以不辱主人之名为美。即便不愿亦不得惧其死。町人没有主人,只有父母……只有生为町人才是幸运”[11]95,通过这种对比町人发现了自身身份对于武士身份的相对优越性。西川还强调了町人对社会的贡献:“百年以来,天下静谧,儒者、医者、歌道者、茶汤风流诸艺人,多出于町人之中。水居于万物之下而滋养万物,町人位于四民之下而作用于上五等之人伦,生于兹世兹品,幸甚至焉。(町人)位居人下而不凌于上,不羡他人之威势,坚持简略、质素,安于分际,同类相聚,尽一生之乐事”[11]88。正因为町人对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町人对自身身份充满了自豪而不是自卑。室鸠巢(11)也认为,“农人主田地生植之财,开天地布八谷,植桑麻,入山采薪,趋野刈茅,取山野河海之食物,劳天下之衣食;工人掌天地器用之材,接金铁大木之类,用其材出农具,作兵仗,织衣服,营室宅,作万器劳天下之用;商人助天下之偏倚,省有补无,取有余而补不足,遍天下之财,蒙天下之化育”,并强调农工商阶层为了天下的福祉而不惜劳苦、勤勉工作,充分肯定他们的价值和作用[5]67-68。 庶民的崛起和武士的贫苦使武士在庶民群体面前已经无法维持往昔的体面和尊严,为了度过眼前的经济困难不得不向庶民低头以谋取利益:“今之武家,苦于贫穷之故,以至养他人之子必求金银,因此卑贱而富者,乘此时而出金,以其子养于士大夫,以数百金而取田禄之士大夫之家,国初以来军功忠勤而享世禄之家,被无家系之下贱者而取代者不知几百千人也”[9]245。武士甚至通过卑劣的手段来获利:“今之士大夫苦于贫穷,通过娶妻而获数十百两以救当前之急,金尽则虐其妻,妻不堪其苦而求去,幸而妻还而不还金,又另娶富家女,如前者数次[9]248。显然,在这样的经济局面面前武士已经难以维持武士道德了,其相对于庶民的优势地位岌岌可危,其直接表现是,反映武士和庶民身份等级差别的服饰发生了巨大变化:“凡人之衣服,别贵贱上下之标志也,当今之世无士庶衣服之制度,故贵贱无别,士大夫如贫穷则着恶服,庶民如成富豪则着美服”[9]263。事实上,这种尊卑的逆舛并不是因为“无士庶衣服之制度”,而是因为现实社会中各身份群体之间经济地位的升降引起了社会地位的隆污,近世初期所颁布的《武家诸法度》中“衣裳之品不可混杂”的强制规定已经失去了现实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庶民阶层对于武士的威服感也在降低。十八世纪后半期以后,庶民在日常生活中对武士的无礼行为增多,以至于幕藩国家不得不通过强制的行政命令来维持武士的治者地位。如盛冈藩从1696年至1825年先后11次向百姓、町人、职人发布一揆禁令,禁止向武士失礼,其中1780年、1781年连续发布3次[21],由此可见,武士因其经济上的贫穷不再享有制度上应有的尊荣,其社会地位因缺乏坚实的经济力量作保障而受到农民、町人的挑战,从而出现了名实的分离和尊卑的逆舛,武士成为“悬浮”于社会之上的阶层。换言之,在近世日本,固然有重视身份等级的一面,但同时也有重视实力的一面,经济实力雄厚的豪农豪商也会享有尊崇的社会地位,而贫穷的武士则受到鄙视。领主阶级的经济窘迫,以至于没有富裕的地主、町人的援助就不能维持武士的生计,这成为武士在全社会失去权威的直接原因[12]337-338。 其次,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武士集团迫于经济困境,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身份壁垒,有限地向庶民开放武士身份,从而出现了庶民武士化的现象,近世日本因之在严格的身份制度约束下出现了有限的社会流动。 在近世中后期以后,虽然武士的社会地位下降,但这一群体依然作为社会的治者集团高踞于庶民群体之上,依然掌握着巨大的政治权力,因此,作为被统治阶层的农民、町人仍然有着强烈的身份上升欲望,不惜通过献金等方式获得武士身份。在二本松藩,从宝历年间(1751-1763年)开始就可以通过献金获得与力、乡士、町年寄、检断格的武士身份,通过购买获得永代苗字带刀和一代苗字带刀的町人、百姓增多了。这些富裕的町人、百姓愿意通过大量的经济花费取得武士身份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甚至有人借钱购买武士身份而陷入长久的贫困之中。1868年11月,会津藩大沼郡川东组新屋敷村通过献金获得带刀、苗字、裃(12)等身份者达36名[22]。农民和町人通过献金获得武士身份成为身份上升的重要渠道。 此外,近世中后期幕府与各藩都普遍面临着财政困难的问题,不得不通过“卖禄”的方式获得财政收入,从而为下级武士、农民、町人的身份上升提供了可能。以仙台藩为例,1759年的财政收入是76998两,财政支出195003两,赤字约122000两。为了缓解严重的财政危机,仙台藩允许百姓或下级武士通过向藩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便可获得相应的武士待遇,如“百姓带刀许可”50两,“百姓苗字许可”100两,不同级别的武士价格不等。安永年间又将所有的价格减半。1766年仙台城下的木材商人安倍清右卫门通过献金获得“二十人扶持”的番外士身份,为了获得大番士的身份又献金四五百两。1797年安倍清右卫门被任命为“出入司”,给予500石的役料[23]137-142。幕藩国家的这种卖禄政策满足了下级武士和庶民身份上升的欲求,同时也导致了身份制度的松弛,因为兵农分离的目的就是通过身份隔离确立起武士对于庶民的优位,幕府和诸藩的卖禄政策实际上是一定程度的向庶民阶层敞开了进入统治阶层的通道,而其本质则是政治权力向经济权力的部分妥协。 再次,商品经济的渗透使经济规律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发挥了更有力的作用,更多的人力资源向工商业领域倾斜,通过政治强制建立起来的身份制度已经难以使各身份群体“各安其位”。 武士的贫困化迫使武士在体制外寻找生活来源,据1825-1828年作为江户各町情况调查报告而成书的《江户町方书上》记载,即使在幕府将军所在地的江户,“仅在250家商家之中,本人是武士、浪人或者其祖先是武士、浪人、乡士者,就有48家”,约占1/4;再据《郡村徇行记》记载,在“御三家”之一的尾张藩名古屋,“在181家商人中,武士占50家,平民占10家;僧侣1家;其余120家为町家”,武士出身的商人占商家总数的28%,武士町人化的程度可见一斑[24]。 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使农村出现了明显的脱农化现象,更多的农民从事工商业或流入城市。进入18世纪后,商品经济将农村和山村都卷入其中,各地从事商业的人增多了,到了19世纪,从事商业活动的农家更加普遍。位于中山道沿线的上州五料村,1827年220家农家中有72家农户从事饮食业、手工业活动。在武藏野西部的武州多摩郡新町村,从文化文政期(19世纪初)开始,从事农间商业的人增加了,1838年新町村60家中有20家从事酒、谷类、布匹、木材、蔬菜、烟草、鱼等的买卖,到1843年增加到32家[12]361-363。和泉国宇多大津村1840年前后有288户村民,完全从事农业的有197家,兼营农业的有28家,脱离农业的有66家,其中28家是靠工资为生的日雇工[25]。此外,面对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贫穷的水吞层农民更是通过打工、奉公的方式流出农村。以美浓国安八郡西条村(村高700石高,人口400弱)为例,该村在1773-1825年平均有50.3%的男子、62%的女子出外打工,佃农外出打工的比例更高,男子高达63.1%,女子高达74%。去向最多的是名古屋、京都、大阪、大垣、津、堺、江户、彦根、桑名等9都市,1773-1800年、1801-1825年、1826-1850年、1851-1868年男子在这些都市打工的比例分别是61.8%、54.9%、63.5%、58.6%,女子的比例分别是47.4%、55.2%、47%、34.9%[26]。由此可见在近世中后期农民外出务工已是非常普遍的情况。面对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导致城市膨胀、治安恶化的状况,荻生徂徕一再强调要通过户籍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农村和土地上,避免出现“人们在各地混杂游荡的现象”[17]16。农民群体是近世日本身份制度的基石,这一群体大量的脱离农业生产,意味着近世前期通过培植封建小农以夯实身份制度的努力受到了商品经济的挑战,也意味着武士的政治强制难以抵御商品经济的冲击,社会的组织原理从政治强制走向经济规律。 四、结语 近世后期,由于武士的贫困化,封建领主发放的禄米已无法维持生存,因此,中下级武士不得不从事手工业、商业,设塾教书或从事医生、作家等自由职业,部分中下级武士为了谋生,通过参与商品货币经济活动,其利益诉求逐渐与町人、豪农接近,为即将出现的社会改革和新思想的诞生,奠定了新的社会基础[27]。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的社会财富并没有被幕藩国家所掌握,而是被豪农豪商阶层“截留”,这一群体成为游离于传统的“士农工商”身份之外的新阶层,单纯的政治强制已难以将这一群体约束在传统的身份制度框架内,换言之,这一群体的成长壮大实际上是在幕藩权力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潜在的权力系统,它依靠的并不是政治强制,而是其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经济手段向全社会发挥其威力。然而,町人所遵循的资本逻辑和金钱本位价值观,与武士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力本位价值观存在着根本不可能解决的矛盾冲突[28],特别是开港后幕藩国家面对严重的财政困难在领内实施物产专卖政策,勾结特权商人,垄断运输和贸易,采取压制商品生产者的政策,日益威胁豪农豪商的切身利益[29]。因此,在幕末民族危机加剧的历史背景下,存在着共同利害关系和一致政治诉求的下级武士和豪农豪商结成了“草莽集团”,两者结成同盟,由下级武士领导,豪农豪商出资出力,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展开了壮烈的草莽运动[30]。德川幕府正是在这种体制内的反对力量和体制外的反对力量联手打击下迅速走向灭亡的。 注释: ①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掌握中央政权的时代,主要是16世纪后半期。 ②持此观点的著作有:吴廷璆.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224;沈仁安.德川时代史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65-74;李文.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80. ③其主要内容是禁止武士、武家奉公人成为百姓、町人,禁止百姓放弃耕地从事商卖和雇工,禁止别的武家雇用逃亡的奉公人,违者将受到处分。 ④刀鞘的附属具。 ⑤从过去5年、10年或20年的平均收获量中决定年贡率,不管丰凶都交纳固定的年贡,有利于农民生产的稳定,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⑥以村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体小农为单位向幕府或各藩交纳年贡的制度。 ⑦问屋:批发商,批发行。 ⑧船宿:船员旅馆。除为进港船员提供住宿外,还为其提供方便、供应物资等的旅馆。 ⑨匁,日语读作もんめ,是江户时代银币的重量单位,相当于小判的1/60。 ⑩西川如见(1648-1724年),江户中前期的天文学家,生于长崎,著有《华夷通商考》《町人囊》《百姓囊》等著作。 (11)室鸠巢(1658-1734年),江户中前期的儒学家,著有《太极图述》《赤穗义人录》等。 (12)肩衣与和服裙裤配套穿的服装,江户时代武士的公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