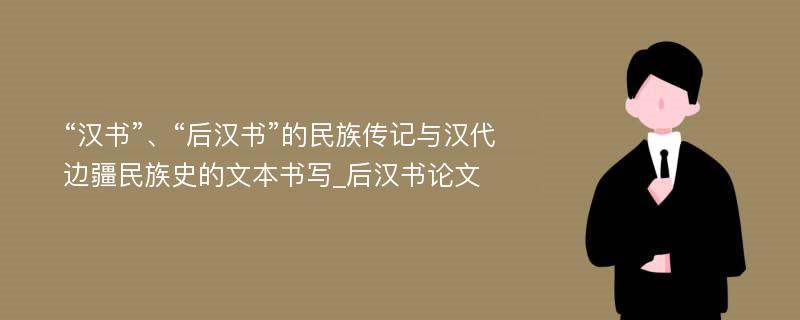
《汉书》、《后汉书》民族列传与汉代边疆民族历史的文本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汉书论文,民族论文,汉书论文,列传论文,边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书》、《后汉书》属于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致认为其史料价值很高,特别是《汉书》、《后汉书》中关于汉代民族历史的记载,几乎是研究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历史必须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成果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论著:沈仁安《〈汉书〉、〈后汉书〉倭人记事考辨》对《汉书》、《后汉书》中有关倭人不足百字的记载进行了考辨;①力之《〈史记〉、〈汉书〉、〈后汉书〉注札记》对《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进行考辨,其中与民族有关的内容不多;②谢晓丹《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探讨两汉时期中印交流》仅仅探讨了两汉时期中国和印度文化交流的问题,没有涉及边疆民族;③舒仁辉《范晔〈后汉书〉史论探讨》主要讨论在《后汉书》的序、论、赞中表现出来的范晔的历史观,与边疆民族历史联系不多;④唐书林《〈后汉书〉研究史概述》主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对《后汉书》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民族历史问题。⑤真正与边疆民族研究有关的研究成果也不多,李珍《范晔的民族思想略论》认为范晔在《后汉书》当中体现了自觉的民族史撰述意识,通过考察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体现突出政治大一统的政治倾向,但是文章并没有对《汉书》、《后汉书》当中的民族列传进行深入评述;⑥汪波《〈后汉书〉与羌族史研究》虽然与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有关,但主要是围绕“西羌传”进行论述,也没有进行综合性的研究;⑦曹德全《〈后汉书〉、〈三国志〉中〈高句丽传〉的比较研究》属于单一性的研究,而且论文主要是考据《后汉书》在引用《三国志》时存在的众多问题。⑧因此,本文从边疆民族历史文本书写的视角进行探讨依然具有积极意义。
班固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对汉武帝之前的历史做了很多补充,从民族史的角度看,《汉书》续写了《史记》所缺汉武帝后期至王莽时代的边疆民族历史。汉武帝中期以前西汉时期的边疆民族历史,《汉书》大量抄录《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班固在向《史记》取材时不是一味照抄,而是在继承中有增补、有调整、有发展。总体而言,《汉书》中所有关于边疆民族历史的记载,比《史记》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和《朝鲜列传》都详尽具体,是今天研究古代中国边疆民族历史以及研究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历史的宝贵文献。《汉书》对民族史的研究,把握住当时社会历史的变化,抓住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进行论述。
《汉书》与《史记》相比较有了许多变化。
其一,从汉与匈奴关系的角度看,《汉书·匈奴传》对《史记·匈奴列传》在继承基础上有一定超越。
由于汉代民族关系和国家战略重点都在北方,汉匈关系是汉王朝民族关系的核心,因此《汉书》对民族史的记述特点更加突出,抓住国家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进行论述,将重点放在匈奴和西域各族上。从数量上来说就是将《匈奴传》增为上、下两卷,除收录了《史记·匈奴列传》的旧文之外,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增加了李广利投降匈奴之后到更始末年的史事,从而使匈奴历史有了完整的记载。此外,《汉书·匈奴传》比《史记·匈奴列传》新增史料五分之三左右,篇幅大大超过《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的历史到公元前98年,而《汉书·匈奴传》则从汉武帝太始元年(前96)起,这一年是匈奴左贤王立为狐鹿姑单于。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仅仅以《史记·匈奴列传》作为研究匈奴的文献,那么只能看到匈奴三分之一的历史,而《汉书·匈奴传》则把匈奴与汉民族的民族关系发展历史较为清晰地展示出来,所以《汉书·匈奴传》的“赞”说:“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拙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而言也。”⑨由此可见《汉书·匈奴传》在研究匈奴历史中的价值。
《汉书·匈奴传》还把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不是十分明确的引用进行了明确,例如《史记·匈奴列传》说:“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⑩而《汉书·匈奴传》则有更为明确的记述:“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曰戎,猃允孔棘’。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11)
其二,从把边疆民族纳入到统一多民族国家郡县统治体系看《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对《史记》相关传的继承、超越。
汉王朝在重点经营北部边疆的同时,积极加强对其他边疆地区的治理,在东南方设置了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在西南方设置了犍为、越巂、牂牁、沈黎、汶山、益州等郡,在东北亚地区设置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等郡,(12)上述地方在汉武帝时都已经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之下,所以《汉书》把《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合并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这样的归并不是简单的归并,而是根据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变化的实际而调整的。在《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班固在继承《史记》各传的基础上也补其遗漏,续其后事,增加了不少珍贵材料,例如汉昭帝到王莽时期西南夷的史事以及汉孝文帝和南越王赵佗之间交往的书信是《史记·南越列传》中所没有的。
其三,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看《汉书·西域传》对《史记·大宛列传》的继承、超越。
由于西域是汉王朝和匈奴争夺的重要战略之地,汉武帝为了实现夹击匈奴的战略目的,建元三年(前138)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希望能够联合西域的力量攻击匈奴,此后汉王朝与匈奴在西域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大宛列传》已经不能涵盖当时西域的历史,所以班固在《汉书》中把《史记·大宛列传》充实修改为《西域传》,记述了西域“城郭诸国”的情况。此外,《汉书·西域传》不仅对《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及的大宛、乌孙等详加叙述,还增加了婼羌、鄯善、精绝等几十个民族的情况,内容比《史记》更加丰富,由于内容涉及了大夏、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等今天的中亚、西亚许多民族的历史,所以《汉书·西域传》不仅是记述中国西北边疆民族史、中亚西亚民族史,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具有世界史意味。
其四,从《史记》中的“太史公日”和《汉书》中的“赞”进行对比看《汉书》对《史记》民族史观的超越。
《史记》中有一个特殊的内容,即“太史公曰”,主要是司马迁个人的观点,就《史记·匈奴列传》而言,司马迁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仅仅认为“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13)其中不乏有对汉武帝的怨言。《汉书》中也有一个类似的内容叫做“赞”,班固在其中不但抒发个人思想,还有许多历史哲学式的思考,例如在《汉书·匈奴传》的“赞”中班固对汉王朝的匈奴政策有深入分析,认为:“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班固“贵华夏,贱四夷”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同时也看到班固强调对待匈奴不能只是用一种策略,应当根据每个时期双方力量的变化,以“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的策略应对。同样,班固在《汉书·西域传》“赞”中也对汉王朝经营西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者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南朝宋人范晔撰写的《后汉书》有120卷。(14)与边疆民族有关的列传是《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羌列传》、《西域列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与《汉书》相比较,增加了《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羌列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这些新增加的列传实际上反映了东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变化。
东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的治理与统治更加深入,众多边疆民族都被纳入了郡县治理,原来的边疆开始成为内地,随之而来的是史家对边疆民族的认识与分类更加细致。在汉文的历史文献中,出现了许多在此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民族名称,说明边疆民族自身在发生着分化与融合,因此《后汉书》在《汉书》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变化,和《史记》、《汉书》相比,《后汉书》没有了《朝鲜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特别是把第一次出现的“南蛮列传”和《史记》、《汉书》中一直存在的“西南夷列传”合在一起,写成了《南蛮西南夷列传》。笔者认为范晔并不是随意进行增减的,列传的增减反映了东汉时期全国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民族关系的变化,反映了东汉王朝对边疆民族的统治更加深入。
从东汉时期全国的政治格局看,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在北方,具体为汉民族与南匈奴、鲜卑、乌桓的矛盾冲突;南方大多数民族因为是农业民族,对土地有很强的依赖性,所以反映在民族关系上,发生战争只在镇压与反镇压的情况下出现,一般不以激烈的矛盾冲突体现,相对来说大的政治事件较少。范晔没有专门为百越族后裔立传,而是将之放在南蛮中交待,这是因为百越民族的后裔到了东汉时期,除了骆越之外,绝大部分已经融入汉族。
现以《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羌列传》、《西域列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为顺序,对《后汉书》和《汉书》、《史记》进行比较,简要论述其对边疆民族研究的意义。
其一,从汉王朝在东北亚地区的发展看《后汉书·东夷列传》对《史记》、《汉书》东北亚地区民族记述的发展。
《史记》、《汉书》的“朝鲜列传”只是记载朝鲜一个民族,而《后汉书·东夷列传》是以东北亚地区主要民族作为对象的区域民族史。在《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范晔不是简单的把《朝鲜列传》换成《东夷列传》,而是更加具体、更加详实地记载了东北亚地区的夫余、挹娄、高句丽、东沃沮、秽貊、三韩、倭等民族,说明史家对东北亚地区的民族有了更多认识。
需要注意的是《后汉书·东夷列传》中提到的东夷,指的是两个对象,在《后汉书·东夷列传》的前半部分,东夷指的是先秦时期分布在今山东、河南的东夷:“《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①由于先秦时期的东夷与华夏族有太多的文化联系,到商朝晚期“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开始与华夏族融合,到了秦朝“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融合到华夏族之中。因此汉代的东夷主要是泛指东北亚地区的民族,是《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的主体,即夫余、挹娄、高句丽、东沃沮、秽貊、三韩、倭等民族。
其二,从汉王朝对西南、中南民族的深入治理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对《史记》、《汉书》的发展。
由于东汉王朝对于西南、中南民族的治理比较深入,所以《后汉书》把西南、中南的民族全部集中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与《史记》、《汉书》的《西南夷列传》相比较,《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的内容更加丰富,记述到的民族种类更多。
先说南蛮。南蛮包括巴郡南郡蛮、板楯蛮等,显然南蛮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民族,而是泛指某个区域的不同民族,所以先需要对《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南蛮进行辨析。第一,南蛮是一个泛称,专指分布在东汉王朝南部,除益州刺史部部分郡县(如牂牁郡、永昌郡、益州郡)外的民族,主要是分布在益州刺史部北部巴郡的民族,和分布在荆州南郡、江夏郡、零陵郡、武陵郡、桂阳郡、长沙郡的民族,以及分布在交州南海郡、苍梧郡、郁林郡、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的民族。第二,由于南蛮分布区广大,所以汉族史家又以行政区名称作为标准,在行政区名称后面加上个“蛮”字来区别南蛮中的各部分,例如澧中蛮、零阳蛮、五里蛮、溇中蛮、长沙蛮、九真蛮、日南蛮、合浦蛮、夜郎蛮、象林蛮、郁林蛮、潳山蛮、巫蛮、江夏蛮。这些蛮都属于南蛮范畴。当然,表面上看似乎只是简单地在行政区名称后加上“蛮”字,但实际上当时汉族史家的分类,是以基本的文化特点作为分类依据的,例如以槃瓠为崇拜对象的武陵蛮,其下又有澧中蛮、零阳蛮、溇中蛮、五里蛮、零陵蛮、长沙蛮等,又如巴郡南郡蛮是指分布在巴郡南郡且崇拜廪君的民族。
再说西南夷。西南夷包括夜郎、滇、哀牢、邛都、莋都、冉駹、白马氐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对于西南夷的记载比南蛮要更加丰富,从文献的字数来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西南夷的部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史记·西南夷列传》有1300多字,《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关于西南夷的内容增加至2300多字,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关于西南夷的内容已经到了4400多字。由此可见其内容大大增加,内容更加丰富。
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还出现了西南边疆民族的神话传说,这是《史记》、《汉书》当中没有的。例如与夜郎国有关的“竹王传说”(16)和与哀牢国有关的“九隆传说”。(17)除了神话传说之外,《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还有民歌民谣的记载:“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18)这是著名越兰津歌,说明随着东汉在西南边疆统治的深入,虽然“行者苦之”,但是对外的交往规模越来越大。
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取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种为臣仆”。(19)所以朱辅上疏给明帝说白狼王慕化归义,作诗三章。希望献给朝廷,明帝十分高兴,“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于是有了《远夷乐德歌诗》、《远夷慕德歌诗》、《远夷怀德歌》,后人将这三首诗歌统称为《白狼王歌》。从《白狼王歌》的产生、传播可以看出边疆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向往,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其三,从汉王朝对羌人的治理看《后汉书·西羌传》对《史记》、《汉书》的发展创新。
羌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代民族,《后汉书》第一次在正史中给羌人立传,因此《后汉书·西羌传》是迄今为止关于羌人最早、最系统、最详实的文献。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关于羌人的民族志记述最有价值:“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20)《西羌传》首先对羌人的民族源流进行记述,然后告诉我们羌人的分布区十分广大,即以黄河上游为中心,“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羌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民俗文化特征为:“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因为游牧经济的原因“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没有成文的法律,因为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劣,所以民族性格十分强悍:“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根据《西羌传》的记载,西羌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民族群体,内部还有诸多的分支,多达150余种,有参狼种羌、牦牛种羌、白马种羌三大派系。因此羌人的民族关系就分为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西羌内部各个分支的关系,二是西羌各分支与汉王朝的关系。在西汉时羌人曾经与匈奴联合对抗汉朝,汉武帝对羌人进行了有效治理,一方面设置郡县,一方面以武力平定,第一次专门设置了治理羌人的护羌校尉:“及武帝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袍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显然羌人与政府的关系已经不是单一的,而是当时以汉匈关系为核心的民族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东汉,羌人不断发动反抗政府的军事行动,东汉花费了巨大人力和财力来镇压西羌,范晔十分客观地认为,羌人的反抗主要是由政府政策出现了失误,再加上用人不当,所以虽然东汉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仍得不到长治久安:“自羌叛十余年闲,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21)可见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之大,
其四,从汉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经营看《后汉书·西域传》对《史记》、《汉书》的继承与超越。
从《史记·大宛列传》开始到《汉书·西域传》,对西域的记载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东汉王朝时对西域的经营仍然在继续深入开展,所以《后汉书·西域传》主要是记载东汉时期对于西域的经营治理,重点是记述西域在东汉时期的重大变化。因此从《后汉书·西域传》可以看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内外民族关系的变化与各民族的分化融合,反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辖区内各民族治理的不断深入。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拘弥、于阗、莎车、疏勒、焉耆、车师等狭义西域的民族或者民族政权,又有广义西域的条枝、安息、大秦、大月氏、天竺等民族国家的风俗人情、地理环境,以及班超、甘英等人在西域的政治活动和影响及佛教传入等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的记述。从世界史的角度看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故《后汉书·西域传》“论曰”有:“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
其五,从统一多民族汉王朝对匈奴的战略变化看《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对《史记》、《汉书》的继承与超越。
匈奴在东汉时期已经分化为南、北两个部分,南匈奴进入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区,开始大量接受汉文化,而北匈奴已经远遁漠北,所以原来的《匈奴列传》变为《南匈奴列传》,对此《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开篇便说:“前书(按,指《汉书》)直言《匈奴传》不言南北,今称南者明其为北生义也。以南单于向化尤深故举其顺者以冠之。”(22)所谓“南单于向化尤深故举其顺者以冠之”指的是南匈奴的汉族化程度已经很深。对于南匈奴为什么要进入黄河流域,与东汉政府放弃了武力征伐,采用和平的招徕的政策有关:“天子总揽群策,和而纳焉。乃诏有司,开北鄙,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驰中郎之使,尽法度以临之。制衣裳,备文物,加玺绂之绶,正单于之名。于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这样一来,东汉政府既分化了匈奴,减少了几百年以来的汉匈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又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南匈奴成为汉王朝的民众之后,帮助东汉守御北方边境,联合鲜卑、丁零,夹击北匈奴,迫使其西迁,结束了匈奴对汉朝的频繁战争。
其六,从匈奴衰亡与乌桓、鲜卑的强盛及其与汉王朝的关系看《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对《史记》、《汉书》的超越与创新。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是在正史当中第一次记载乌桓、鲜卑的历史,所以其史料价值极高。和其他几个传相比较,《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的民族志记述较为丰富,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对乌桓、鲜卑民族源流以及民族名称的由来的记述:“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23)鲜卑“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显然,乌桓、鲜卑都是东胡系统的民族,属于同源异流的关系,民族名称的产生是因为被匈奴灭其国之后“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这种以分布区的地名或者山名作为民族名称的情况在中外历史上是十分常见的。第二,记述乌桓、鲜卑的生产生活方式。乌桓“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鲜卑“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讌毕,然后配合。又禽兽盖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文献从游牧生产方式,主要物产,饮食习俗等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作为游牧民族的乌桓、鲜卑。与农业民族尊老不同,游牧文化认为老年人是整个社会的拖累和负担,所以“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从“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的文化习俗来看,虽然他们已经处在父系社会,但是对于母系仍然崇敬。第三,乌桓与鲜卑的游牧文化使其社会组织与民俗文化不可能同农业民族一样,所以“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是松散社会重大事件发生时的召集人:“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但是在“大人”以下的不同部落政治、经济的联系就十分松散,“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第四,乌桓、鲜卑的婚姻习俗也处处表现出游牧文化特征。婚姻“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聘币。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辨”。从婚姻发展历史看,显然是盛行服役婚。这种服役婚,是男子在婚前或婚后住在妻方劳动一段时间,作为代价偿还妻方劳动力的损失,换娶妻子到本氏族或本家族中来。第五,从宗教信仰上看,乌桓已经有了强烈的灵魂崇拜和祖先崇拜,最突出的是面对死亡自有一套生命观:“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服,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死者魂神归岱山也。敬鬼神,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毕皆烧之。”乌桓社会是以习惯法来控制社会:“其约法:违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贼杀者,令部落自相报,不止,诣大人告之,听出马牛羊以赎死,其自杀父兄则无罪;若亡畔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这些史料都是我们今天研究乌桓、鲜卑的重要参考文献。
对于边疆民族历史的系统研究,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了按地域记载民族历史的少数民族列传,开创了较为系统研究华夏族和汉族以外的民族历史先河,通过《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和《朝鲜列传》,分别记述了中国边疆民族发展历史。《汉书》、《后汉书》的作者基本是仿照司马迁开创的这一范式来进行民族史的记述,但是又根据历史情况的变化有许多超越《史记》的创新,把对汉代边疆民族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历史文本的书写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其一,汉代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的发展紧密相联,所以《汉书》、《后汉书》的民族列传记述了动态变化中的边疆民族,重点以边疆民族的民族关系为主线书写了汉代边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边疆民族也积极参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缔造和建设,对其历史进行充分的记述,可以丰富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其二,《汉书》、《后汉书》的民族列传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宏观视角,紧紧抓住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当中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以匈奴为主的北方民族进行了非常深入详细的记述,真实地反映了汉代民族关系和汉王朝的国家战略重点在中国北方这一历史事实,通过这些真实的历史文本书写,使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北部边疆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北方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其三,《汉书》、《后汉书》民族列传的增减实际上反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变化,例如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发展变化,《史记》中的相关列传在《汉书》、《后汉书》中进行了归并,与此同时新增加了《西羌传》、《乌桓鲜卑列传》等,说明随着汉王朝对相关民族进行有效治理,汉王朝的边疆也在发展变化。
注释:
①沈仁安:《〈汉书〉、〈后汉书〉倭人记事考辨》,《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②力之:《〈史记〉、〈汉书〉、〈后汉书〉注札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③谢晓丹:《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探讨两汉时期中印交流》,《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④舒仁辉:《范晔〈后汉书〉史论探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⑤唐书林:《〈后汉书〉研究史概述》,《唐都学刊》2009年第2期。
⑥李珍:《范晔的民族思想略论》,《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⑦汪波:《〈后汉书〉与羌族史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⑧曹德全:《〈后汉书〉、〈三国志〉中〈高句丽传〉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
⑨《汉书》卷94下《匈奴传》。
⑩《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11)《汉书》卷94上《匈奴传》。
(12)《汉书》卷6《武帝本纪》载,元封二年“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乃募天下死罪击朝鲜”。三年夏,“以其地为乐浪郡、临屯郡、玄菟郡、真番郡”。
(13)《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14)范晔撰写《后汉书》预定是十本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卷,以之和《汉书》相对应,但是十志还没有写完,范晔就被杀害了,所以现在《后汉书》里的《律历》、《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等八志,就由后人从司马彪的《续汉书》当中取出来补到范晔的《后汉书》里面,所以又有人说《后汉书》是范晔和司马彪撰写的。
(15)以下皆见《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
(16)“竹王传说”:“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逐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牂柯太守吴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17)“九隆传说”:“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孕,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着尾。九隆死,世世相继。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18)《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19)《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20)以下皆见《后汉书》卷87《西羌传》。
(21)《后汉书》卷87《西羌传》。
(22)《东观记》称《南匈奴单于列传》范晔去“单于”二字。
(23)以下与乌桓、鲜卑相关者皆见《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
标签:后汉书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汉朝论文; 边疆论文; 大宛列传论文; 朝鲜列传论文; 史记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西汉论文; 西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