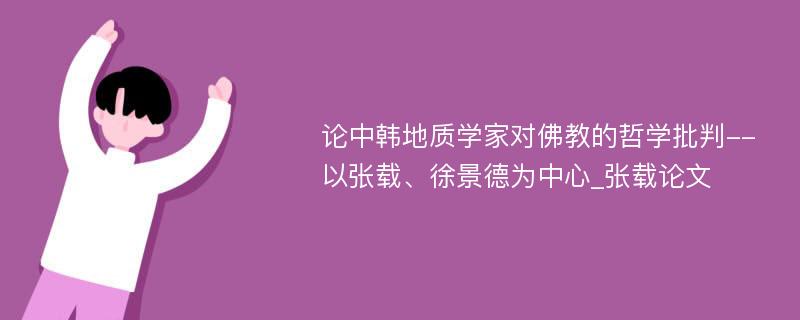
论中韩气学家对佛教的哲学批判——以张载和徐敬德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中韩论文,学家论文,哲学论文,张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载和徐敬德分别是中国和韩国学术思想史上两位颇有影响的“气学派”的重要代表。张载是中国宋明理学中气学思想的奠基者,他提出的一些哲学思想和哲学范畴,对宋明理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且还影响到韩国的徐敬德,而韩国哲人徐敬德的气论思想,成为尔后朝鲜时代显赫一时的“退溪学”和“栗谷学”的先声。徐敬德比张载大约晚400 年,生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有着很大差异,但两人都从儒学中气学一派的立场出发,从哲学高度对佛教作了大体相近的批判。本文试图通过对张载与徐敬德两位气学大师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比较以及他们批判佛教的哲学内容的分析,解读和透视这两个极为相似的哲学事件的文化意义。
一、张载和徐敬德哲学的社会背景
(一)张载哲学的社会背景
印度佛教大约在后汉中叶传入中国,佛教中的大乘空宗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以无为本的玄学思想相通,佛教便依附玄学而传播自己的思想。这样,佛教自然而然地开始在中国传播。与佛教同时发展的道教,到了五胡十六国时代,由于社会更加动荡不安,而进一步得到发展,直至北魏时期达到了宗教化的繁荣时期。这样的社会背景也影响到了思想领域,从而也成为老、庄思想的流行以及清谈思想出现的背景。
唐代实行了与魏晋九品中正制度不同的制度,即通过科举制度来扩大官吏选拔,随之儒学方面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人物。虽然唐初的王通、傅奕及唐中期的韩愈、李翱等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对佛教进行批判的代表人物,但他们只是从“费财”、“伦常”、“夷夏”等方面批判佛教,并没有涉及到哲学的基本问题。柳宗元、刘禹锡虽有所涉及,亦较简略。
宋初的思想家继承唐代朝愈等批判佛道复兴儒学的传统,孙复指出:“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已,若以为心,得不鸣鼓而攻之乎!”(注:《泰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二。)佛教与儒齐驱,对伦理纲常确是很大的冲击,也于仁义礼乐不利,因此主张鸣鼓而攻之。孙复着重从伦理上批佛、老。
张载曾出入道教和佛教,然后又反诸《六经》,他说:“某向时,说以为已成,今观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门庭,知圣人可以学而至。”(注:《经学理窟·自道》,《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89 页。)从而悟到儒学的道。对当时的佛教学家和儒学家迷恋于佛教的态度,张载的弟子范育曾指出:“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而其徒侈其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必取吾书为正。世之儒者亦自许曰:‘吾之《六经》未尝语也,孔孟未尝及也’,从而信其书,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风,无敢置疑于其间,况能奋一朝之辩,而与之较是非曲直乎哉!”(注:《正蒙·范育序》,《张载集》,第4~5页。)释、老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六经》不及释、老,故自诩应以释、老之书为“正”;而儒者亦自愧不如释、老,信其书,宗其道,靡然天下,无敢置疑。在这种情况下,无人奋起争辩,以较是非曲直。唯独张载“以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闵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将灭也,故为此言与浮屠老子辩,夫岂好异乎哉?盖不得已也”(注:《正蒙·范育序》,《张载集》,第4~5页。)。张载从哲学理论上对佛、老进行了批判(注: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第20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二)徐敬德哲学的社会背景
高丽时期,在思想精神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佛教,佛教以“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灵魂不灭”等佛教教理,为高丽王朝的护国护王服务。佛教便得到高丽王朝的重视,高丽太祖王建在《十训要》第一条中说:“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于是王朝借用政治权力,大力扶植佛教,动用大批人力和物力,到处修建佛教寺院,出版佛教经典,提高僧侣地位,王子和国王的亲属出家当僧侣者亦大有人在。
虽然高丽朝亦倡导儒家学说,如《十训要》第十条说“博观经史,鉴古戒今,周公大圣”等,设立国子监进行儒家思想教育,但并未以儒教代替佛教,佛教大僧侣享有与世臣大族同等的社会政治大权,甚至拥有比世臣大族还要大的农庄,他们免除田赋,这就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削弱了国家的物质基础,引起了国贫问题的出现。同时,佛教大僧侣拥有比世臣大族更大的农庄,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加剧了僧侣农庄主与世臣农庄主的冲突,亦加剧了社会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当李代王朝(朝鲜朝)推翻了高丽朝后,为安定政治、经济上的混乱局面,采取了抑制佛教大僧侣土地兼并政策,多次没收清理寺院土地并极力宣扬、推广程朱理学,把它提升为正统的指导思想和“经邦治国”的真理。这样,程朱理学就在“破邪显正”旗帜下,排斥佛教思想。
在这种时代主流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新兴士大夫阶层,儒学也被大大奖励。在儒教至上主义社会中,佛教不得不受到遏制,虽然几次试图再起,但都遭到了失败,佛教便从“国教”的位置上跌落下来,到了朝鲜朝以后,佛教便成为以妇女为主要信仰对象的宗教而流传至今。
尽管在当时形成了遏制佛教、奖励儒教的社会文化的氛围,但作为曾长期支配社会文化和国民精神的佛教来讲,无论是社会影响还是学问上的价值层面都不可能完全被排斥。对此,徐敬德以自己的“宇宙发生论”为根据,批判佛教的虚无主义和空的思想。
二、张载和徐敬德哲学的文化背景
为叙述方便,分为文化背景和学术思想渊源两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文化背景
首先,从相同的方面来考察,张、徐两人虽处不同国家和时代,但都遇到了佛教严峻的挑战,并作出了近似的回应。
宋是经过唐末黄巢起义和五代十国社会大动乱、大破坏后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宋明理学是为了重新建构破坏了的伦理道德和精神家园而产生的。朝鲜前期的性理学亦是在相似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朝鲜建国初期,社会混乱,李氏王朝把性理学作为国教,从而把它“官学化”,其思想和哲学作用均是在适应时代需要的背景下产生的。张载和徐敬德虽然是国籍不同的学者,但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有着相似之处,而两者的理学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孕育并发展起来的。
印度佛教自汉传入中国后,长期与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文化冲突融合。到了北宋时,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并未完成,宋代的儒家哲学家为了抗拒佛教的渗透和影响,便从理论思维层面批判佛教,其代表人物便是张载。张载较之唐代韩愈对佛教采取“人其人,以其书,庐其居”(注:《原道》,《韩昌黎集》卷十一,台北·华正书局,1982年版。)的简单方法,大不相同。这与宋代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历法、地质、医学、生理学、农学等科学技术的繁荣的背景下所产生的对哲学的新的需要是息息相关的。
徐敬德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随着朝鲜的创业,统治者为实施“抑佛兴儒”政策,开始批判佛教的“虚无”、“空”思想,同时奖励儒学,而新的学风也随之形成的时期。在科学技术领域中也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从天文学到农学、印刷术、火器制作、医学等各个领域都迎来了科学的变革。这种学术背景便成了张载和徐敬德形成其独特思想的契机。
其次,从异的角度来分析。宋代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商业发达,城镇繁荣,科技进步,被称作世界三大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已完成。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疑经舍经”的解放思潮,各家各派思想不断涌现,而且北宋各州、县纷纷设立学校以及私人创办书院,也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从而学术思想领域中也出现了新的风气,成了北宋理学形成的契机。这时期的著名理学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以及讲述象数学的邵雍等。到了南宋,朱熹继承周、邵、张、程等人思想,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张载作为理学的奠基者,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徐敬德的境遇则不同。他生活的朝鲜朝前期,是性理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活跃的研究而开始形成朝鲜性理学的时期,即以程朱理学为中心进行众多研究的时期。因此徐敬德与张载不同,他直接接触到程朱理学,并受其影响。换言之,张载是奠定理学基础的人,而徐敬德所接触的是程朱理学集大成的学说,他接受了张载的气学、程朱的理学和邵雍的象数学等丰富的思想,并形成独立的思想。
(二)学术思想渊源
宋明理学家都以极大的兴趣研究六经之首的《周易》,张载也不例外。张载著有《横渠易说》,徐敬德亦著有《卦变解》,又说《周易》是“一部义众理丛”(注:《诗·再次沈教授见赠韵》,《花潭集》,第298页。),由此可见,两者都很重视《周易》的研究。 而且徐敬德的学风与宋儒的学风有着很大关联,因此,张载和徐敬德思想有相似之处。
但张载与徐敬德思想的渊源不同。张载是理学形成时期的学者,对理学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他的思想是独自学习《六经》后体悟了儒学之道,并经过自己的穷究而获得的。当时有人曾认为,张载思想源出于二程,但其与事实不符。《杨龟山集》云:“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故余录此简以示学者,使知横渠虽细务必资于二程,则其他故可知已。”(注:《跋横渠先生及康节先生人贵有精神诗》,《杨龟山集》卷五。)对此,程颐说:“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注:《程氏外书》,《二程集》卷十一。)他的这个解释不是自谦之辞,而是事实。我们从二人的哲学思想体系来看,旨趣大相径庭。朱熹说:“横渠之学,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与伊川异。”(注:《横渠学案下》,《宋元学案》卷十八。)又说:“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注:《伊洛渊源录》卷六。)“自成一家”和“与伊川异”,说明程颐主理与张载主气虽可互补,却确实异趣。张载之学,得力于自己的用功体悟穷究。“学者少有能如横渠辈用功者。近看热得横渠用功最亲切,直是可畏。”(注:《横渠学案下》,《宋元学案》卷十八。)而张载自己也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注:《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第274页。)这是的确之言,张载融会中国古代各家思想,而归于儒, 其儒学已是会通儒、释、道三家之学的新儒学。
徐敬德的思想渊源与张载大不相同:第一,徐敬德是宋代以后的人,他继承、发展了作为当时朝鲜思想史主流的儒学思想。第二,徐敬德的思想受邵雍象数学的影响很大。
首先,我们从徐敬德对朝鲜性理学的继承与展开来考察其思想渊源。有关宋儒对徐敬德的影响,主要指他在自己的论文中提到过的宋五子(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邵雍)(注:徐敬德说:“后学有多得于《系辞传》、周程张朱之说”。(《鬼神死生说》,《花潭集》)“花岩不爱邵吟诗,哈到尧夫极论诗。”(《诗·观易偶得首尾吟以示学易辈诸贤》,《花潭集》))的影响。在李珥的《经筵日记》中载有表现徐敬德与中国新儒学关系的内容:“许晔每尊敬德以为可断箕子之统,闻珥论,敬德之学出于横渠,责珥曰,君言如此,仆所深忧,若曰,花潭之学兼邵、张、程、周,则可矣。君精专读书10余年后,可论花潭地位。珥曰,恐珥读书愈久而愈与公见背驰也。”(注:《经筵日记》,《栗谷全书》;《言行杂录》,《花潭集》,第418~419页。)
由此可见,徐敬德的弟子许晔与李珥之间的论争的焦点就是徐敬德哲学的理论的渊源问题。李珥根据徐敬德的气论这个事实,而作出徐敬德受张载气论影响的结论;许晔认为徐敬德哲学的特点,是受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理论的影响,展开为“无极而太极→太虚之气”、“太极动而生阳→理之时”逻辑过程,并将作为宇宙原理的“无极而太极”解释为“太虚之气”,将宇宙生成原理的“太极动而生阳”转换为生成万物的自律的(自能尔、机自尔)变化运动。这是相对于朱子将“无极而太极”解释为理,将阴阳五行解释为气,把太极的动静解释为天命流行,即“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立场而言的。正如在本太虚、气、物论中所展开的那样,徐敬德受到了张载气论思想的影响,并把它继承、发展为自己思想的主流。
关于邵雍,徐敬德不仅受了他思想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了他甘居林泉生活方式的影响。邵雍在青年时代刻苦读书,一生未做过官,后隐居在洛阳。徐敬德亦是一生未做官,隐居在花潭,与大自然为伴,可见两人的人生哲学有某种共同之处。由此看来,徐敬德或许是因为在与他有类似生活经历的邵雍身上看到了他自己,因而更加崇尚邵雍。他在诗中说:“观物工夫到十分,日星高揭霁披氛。自从浩气胸中养,天放林泉解外纷。”(注:《诗·又一绝》,《花谭集》,第282页。 )又说:“花岩不爱邵冷诗,输得尧夫间静时。道不远人须早复,事皆方物莫教睽。既知性处宜温养,必有事来岂太持。自在工夫曾吃力,花岩不受邵吟诗。”(注:《诗·笑戏》,《花潭集》,第282~283页。)在思想情感上发生了感应,而对邵雍思想更加关心。
他一生研究邵雍之学,撰著了《皇极经世数解》、《六十四卦方圆之图解》、《声音解》、《跋前声音解未尽处》等文,而且在他为数不多的哲学诗中也有模仿邵雍的《观易吟》、《首尾吟》等作品的诗,此外,他也经常谈到邵雍的思想,可见邵雍对徐敬德的影响之大。
徐敬德不仅继承张载的气学,而且融会二程、朱熹等理学大家,在这一点上他与张载不同。徐敬德很重视“理”,在他的著书中有《原理气》、《理气说》等,由此可知徐敬德对“理”范畴的认识,从而也明确了理气关系。综上所述,徐敬德的“一气”思想以张载的气论和二程、朱熹的理论思想为基础,引用邵雍的用语和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综合而再定立了他的“气一原论”思想。
其次,我们从徐敬德的象数学思想来考察其思想渊源。
虽然张载应诏赴京时路过洛阳,二程有信请张载听邵雍讲《易》,但未知去听否?即使去听了,张载在《横渠易说》中也并没有接受邵雍象数学的思想,此与徐氏有异。徐敬德继承了邵雍的象数学,所以后来金用廉赞徐氏“学究天人,实我东之邵尧夫也”(注:《重刊花潭先生文集序》,《花潭集》,第268页。)。徐敬德讲, 道理相混淆时可用数来分辨和理解,而且人的知识可以知道外象和外数,但很难知道内象和内数,以此来表示对数的深深的信赖和理解。徐敬德对象数学的关心和理解,从他为数不多的论文中可以得到印证。他的象数学大多都是对邵雍《皇极经世书》的解释,《声音解》是对《皇极经世书》的《经世四象体用之数图》中有关声音图象的解说。《声音解》是对五行说及阴阳论为基础的邵雍的《图数之学》为根据的声音的解释,他说人的嗓音也是自然现象的一种。韩国的文字是表音文字,而徐敬德的这一思想同时也为我国表音文字的创制和发展提供了哲学的理论依据,其影响尤为远大。
作为对邵雍《皇极经世书》的解说的《皇极经世数解》,李退溪曾评说,《皇极经世数解》为徐花潭先生所撰,先生是在未看解说图的情况下独自穷究而达到的,这是件奇事(注:《言行杂录》,《花潭集》,第414页。)。可见,徐敬德对邵雍图数和象数的悟解之深。 《皇极经世数解》是将宇宙循环以数来系统化了的理论,从理论上讲,这一体系以井然有序的图表或数字通向天地造化。
徐敬德是想通过对这种体系和秩序的追求,寻找天地造化的原理的。也就是说,想利用图表体系,并以逻辑结构方法来解开宇宙的奥秘。徐敬德一生穷究、静思宇宙原理,因此自然而然地对邵雍的图数、象数有很大的关心。对此,后来学者说:“元会的术数无不贯通,可谓是我们东国伟大的邵尧夫。”如上所述,徐敬德有着与张载不同的思想渊源和以象数学为本的自己独特的思想,从这一点来讲,两者的思想渊源有很大的差异。
三、张载徐敬德对佛教思想的哲学批判
张载和徐敬德对佛教的批判大体从两个方面展开:(一)对佛老否定天地万物存在的虚无主义的批判;(二)对生死轮回和鬼神的批判。
(一)对否定天地万物存在的批判
张载首先批判佛教没有认识到万物的本体,而把它视为“幻化”。张载的弟子范育在《正蒙序》中说:“浮屠以心为法,以空为真,故《正蒙》辟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注:《正蒙·范育序》,《张载集》,第4~5页。)在他看来,佛教理论的宗旨是以心为法,以空为真,于是张载立“气”破“空”和“虚”。这就是说,世界万物并不是虚幻的现象,亦非空无所有。即使是所谓的虚空,在张载看来,也无不是“气”,“气”是实存的。虚空虽然看不见,但看不见并不就是虚与空。它是气的一种隐而不可见的状态,而非显现可见的状态。这种隐而不可见的状态便称为“幽”;显现可见状态称为“明”。“明有不尽,则诬世界乾坤为幻化。幽明不能举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注:《正蒙·太和篇》,《张载集》,第8页。)。因此,以天地为幻化,显然是一种“妄意”, 这与夜空中的月亮和星星可显现,白天隐而不见的道理是一样的。
张载批佛亦辟道,范育说:“老子以无为为道,故《正蒙》辟之曰:‘不有两则无一’。”(注:《正蒙·范育序》,《张载集》,第4~5页。)天地万物是“有为”,并非“无为”。
对于张载“虚空即气”的思想,徐敬德加以发挥说:“老氏曰:有生于无,不知虚即气也。又曰虚能生气,非也。若曰虚生气,则方其未生,是无有气,而虚为死也。既无有气,又何自而生气,无始也,无生也。既无始,何所终,既无生,何所见,老氏言虚无,佛氏言寂灭,是不识理气之源,又乌得知道。”(注:《太虚说》,《花潭集》,第340~341页。)徐敬德继承张载“虚即气”的思想,并由此出发批判道家老子“有生于无”、“虚生气”的思想。老氏讲天地万物是虚无、佛教讲寂灭,都是没有认识到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是气这个道理和气是天地万物的本体的缘故,从而他否定了道家的虚无和佛教的寂灭。
张、徐对佛教思想批判的共同之处有以下两点:
第一,张载和徐敬德都是从天地万物实存的本体意义上来批判佛教的。张载说:“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真所谓疑冰者与!”(注:《正蒙·大心篇》,《张载集》,第26页。)由于佛教把“心”作为起灭天地的主宰,把本来为“小”为“末”的“心”,当作天地万物的“大”和“本”,这样便导致本末倒置,大小混淆。佛教用人们肉眼看不到的某种事物的现象,作为论证天地万物虚而不实的根据,犹如《庄子》所说“夏虫不可语于冰者”(注:《秋水》,《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11页。)一样无知。
如果说张载批判整个佛教,以佛教为释教,那么,徐敬德便是主要针对佛教内禅宗的思想。他说:“禅家云,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有日真空顽空者,非知天大无外,非知虚即气者也。空生真顽之云,非知理气之所以为理气者也。安得谓之知性,又安得谓之知道。”(注:《原理气》,《花潭集》,第338~339页。)徐敬德认为,佛教所说的万物皆由心而产生灭亡,以及心理悟到了便成为空的说法,是因为不知阴阳变化运动,不知虚即气的道理。若此天地万物犹如海水的沤发现象,即逝即变,都是空的、虚的。不知理气之所以为理气的道理,怎能知道性和道,亦即不可与之讲形上学问题。
佛教认为现实世界都虚妄不真的,张载批判说:“释氏妄意天性。而不知范围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明不能尽,则诬天地日月为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子虚空之大,所以语大语小,流遁失中。其过于大也,尘芥六合;其蔽于小也,梦幻人世。谓之穷理可乎?……尘芥六合,谓天地为有穷也;梦幻人世,明不能究所从也。”(注:《正蒙·大心篇》,《张载集》,第26页。)由于佛教以天地万物为妄,便错误地把天地日月为虚幻,由此出发,以人世为梦幻,以“六合”为尘芥,他的错误就在于“明不能究所从”,即不能揭示宇宙和人生的所当然的所以然;同时由于“蔽于小”,即把六种微小的感觉作为和合天地的因缘,而以天地万物依赖人的感觉而存在。张、徐批判佛教视虚空为空无状态和以空无状态为万物根源的观念。虚空的观念来自人们的主观的幻想,它是“以心为法”、“万法唯心”为根据的。它否定了万物生死变化的动态性,这是对自然现象的无知,也是对生存自然界的直接的挑战。由此出发,他们进一步追究了万物存在的根源、生灭的变化过程等运动规律。
第二,张载和徐敬德又从事物运动变化意义上批判道佛。张载说:“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圣人之意莫先乎要识造化,既识造化,然后理可穷。彼惟不识造化,以为幻妄也。不见易则何以知天道?不知天道则何以语性?”(注:《横渠易说·系辞上》, 《张载集》, 第206页。)天地万物是在不断运动变易中化生, 佛道不懂得造化的道理,就认为天地万物为幻妄。徐敬德亦说:“易者,阴阳之变。阴阳,二气也。一阴一阳者,太一也。二故化,一故妙,非化之外别有所谓妙者。二气之所以能生生化化而不已者,即其太极之妙。若外化而语妙,非知易者也。”(注:《理气说》,《花潭集》,第340页。 )客观对象事物的变化是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由于阴阳二气的絪缊,才使天地间生生不息。徐敬德认为,变化是事物内在的阴阳二气,而不是外在的力量。
由此,可以看出张徐批判佛教的思想逻辑是从易→天道→性或易→性→天道。如果不知易的造化,即阴阳的变易,而讲天道和性,实是无本之木;只有明白阴阳二气的变化过程之后,才能达到天道和性。
(二)对生死轮回与鬼神的批判
张、徐对佛教所说的生死轮回说和鬼神论进行批判。他们认为人物的生死,都是气的聚散变化。张载说:“易谓‘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者,谓原始而知生,则求其终而知死必矣。”(注:《正蒙·乾称》,《张载集》,第65页。)“浮屠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遂厌苦求免,可谓知鬼乎?以人生为妄(见),可谓知人乎?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孔孟所谓天,彼所谓道。惑者指游魂为变为轮回,未之思也。大学堂先知天德,知天德则知圣人、知鬼神。今浮屠极论要归,必谓死生转流,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悟则有义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昼夜,通阴阳,体之不二。”(注:《正蒙·乾称》,《张载集》,第64页。)
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亦以人生为幻妄。只有这样,才能唤起人们去追求宗教彼岸世界的激情。根据张载对佛教的理解,如果“三世轮回”和人死为鬼说成立,那么必定以承认灵魂不灭为前提,然而按照佛教人的生死都是幻妄的理论,就应该彻底否定灵魂的存在。张载继承中国古代范缜、傅奕等人的神灭论思想,提出人的生死现象都是气的聚散变化,气聚为生,气散为死。张载弟子范育在《正蒙序》中说:“至于谈生死之际,曰:‘轮转不息,能脱是者则无生灭’,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辟之曰:‘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夫为是言者,岂得已哉!。”(注:《正蒙·范育序》,《张载集》,第4~5页。)气聚为人与物,气散为太虚(气)。人的生与死、精神与肉体的关系,就是气的聚与散的关系。人们之所以认为人死有知、灵魂不灭,是因为对自然界的一些怪异现象不理解的缘故。张载说:“范巽之尝言神奸物怪,某以言难之,谓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车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注:《拾遗·性理拾遗》,《张载集》,第373页。)打雷闪电、奇花异木等怪异现象,只要认识它的“定形”,就不会以为怪异,只要人们认识到无鬼,就不会信佛教的人死有知、灵魂不灭了。
徐敬德继承张载的思想,也批判了人死为鬼论。他说:“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此尽之矣。吾亦曰,死生人鬼,只是气之聚散而已。有聚散而无有,无气之本体然矣。”(注:《鬼神死生论》,《花潭集》,第341~342页。)人物的生死是气的聚散变化。气聚而形成人物,这是人物之生;气散便是人物之死亡。气虽然有聚散的变化,但不会消灭。不管是人,还是鬼神,一切万物都由气的聚和散而产生并灭亡。
张、徐认为,事物存在的特性、形态等等的差异,都是由气的聚散来决定的。佛教之所以讲有生死轮回和鬼神,都是没有认识到事物变化的规律性和生死的必然性所导致的,而鬼神只是体现气的运动过程中往来、屈伸等不同的运动形式,并非是什么人格化的神与鬼。他以气伸而为神、气屈而为鬼,来批评佛教错误的生死轮回说和鬼神说。
从社会背景和学术文化背景两方面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张载和徐敬德从哲学上对佛教思想进行批判,既是中韩儒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代表了性理学中的气学派对于佛教思想的清算,也是中韩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要求以进取务实的世风和精神代替佛教尚虚颓废的社会风气和民族精神。张载和徐敬德把对佛教的批判提升到了哲学理论思维的高度,这与以前仅从政治、经济、伦理出发,批判佛教的不忠、不孝、费财等要深刻得多。从世界观高度批判佛教,张、徐两人在各自国家的思想发展史上,都有其重要的贡献。
标签:张载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佛教论文; 皇极经世书论文; 张载集论文; 理学论文; 宋元学案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