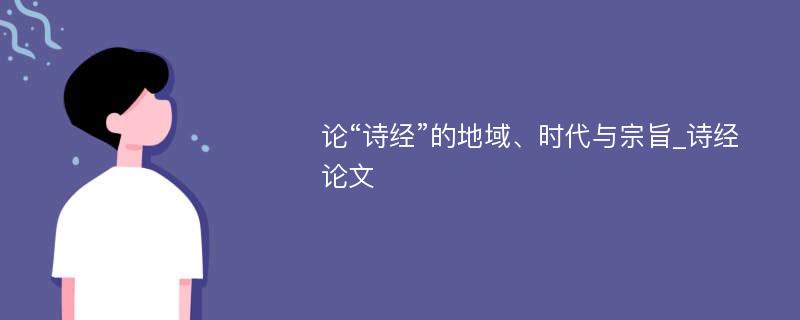
论《诗经#183;王风》的地域、时代与诗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经论文,地域论文,时代论文,王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2)03-0022-06
《诗经·王风》的地域与时代,近年来似乎已成为定论。程俊英教授《诗经译注》说:
“主”即王都的简称。平王东近洛邑,周室衰微,无力驾驭诸侯,其地位等于列国,所以称为“王风”。……《王风》全部都是平王东迁以后的作品。它的产生地,在今河南省洛阳、孟县、沁阳、偃师、鞏县、温县一带。崔述说:“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家室飘荡。”(《读诗偶识》)这正是王风的历史背景。表现在诗中,如《黍离》、《扬之水》、《兔爰》、《葛藟》、《君子于役》等,多带有离乱悲凉的气氛。
陈子展教授的《诗经直解》亦说:“是东周王城诗即称《王风》,以风贬周也。……《王风》兼地理与政治而言之,其义乃全也。”
程俊英、陈子展两位先生本是陈启源的弟子,属师兄妹,都是国内著名的诗经学者,因而程、陈的见解,似已成学界的共识。
程、陈之见之所以能成为学界共识,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此说在东汉末年已成为主流学说,《黍离》之《郑笺》说:“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王城,谓之东周。幽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列于周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郑玄《毛诗谱》又说:“平王以乱故徙居东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为王国之变风。”
郑玄的《笺》说与《毛诗谱》之见,主要又受《毛诗》与司马迁的影响。《毛诗》认为《王风》作于平王、桓王与庄王时期,《王风》的地域自然在东都王城即洛邑一带;而《史记·周本纪》又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司马迁属鲁诗学派,郑玄偏重《毛诗》又兼通三家诗,故有郑《笺》与《毛诗谱》之说。
但就两汉时期或更早时期的一些文献资料来看,有关《王风》地域、时代及诗旨的见解是颇有出入的,《毛诗》与郑玄的见解亦非定论。兹分数点论证如下:
一、三家诗学者认为《王风》是王畿之风。何谓王畿?一般辞书都确认:古代称王城四周的地域谓王畿。《周礼·夏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班固《西都赋》亦称:“封畿之内,厥土千里。”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西周时期周王朝有两个王城,即两个京都,一是西都镐京,一是东都雒(通洛)邑。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最早经营东都洛邑的是周武王,至周成王时期,又特派召公与周公继续经营洛邑,而最终建成洛邑的是周公,所以西汉学者焦延寿《易林·井之升》曰:“营城洛邑,周公所作。世运三十,年历七百。福估丰实,坚固不落。”武王和周王为什么要营筑洛邑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史记·周本纪》说:“(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均。”这是说洛邑的地理位置居于西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位,不仅四方入贡里程较均衡,而且四方诸侯朝见周天子也较为方便,因此东都洛邑成为周王朝与四方诸侯经常联络的一个重要地点。其二、洛邑是周王朝的祭祀中心,这里有祭文王与列祖的清庙,清庙的中央之室称为“太室”,并是三代重宝九鼎的保存之地。据《尚书·洛诰》所载,成王曾多次到过洛邑,不仅在洛邑举行冬祭,并大会四方诸侯。为此成王称“其(指洛邑)作周配”,即洛邑是“周”(镐京)的配匹,故洛邑有“洛师”与“东都”等名称。
由上可见,周王朝的王畿千里是包含西都镐京与东都洛师两个地区的。故齐诗学派的班固,其《汉书·地理志》说:“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郦道元的《水经注》亦沿用班固说,这说明班固的见解是颇有权威性的。无独有偶,班固的父亲班彪(亦宗《齐诗》),在其《北征赋》中写道:“释余马于彭阳兮,且弥节而自思,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痦旷怨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北征赋》作于西汉晚期,班彪为了躲避关中动乱,从长安启程往西北方向的甘肃凉州进发,班彪以上有感而发的一段,是触景生情想起了《王风·君子于役》的诗篇:“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对照曹大家的《东征赋》与潘安仁的《西征赋》,凡触景生情处,均与地理因素及相应的历史故事有一定的关联,因而大体可以认定,齐诗学者班彪认为《王风·君子于役》的地域应在长安以西的地域,而与东都洛邑无涉。由班固与斑彪之见,可知齐诗学派认为《王风》的地域当指“东西长而南北短”的狭长地带,包括西周镐京与东都洛邑东西相通的两个地区,并非只限于东都洛邑。
韩诗学派的观点与齐诗学派也是一致的。如《王风·黍离》,《毛诗序》说:“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宗周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毛序》确认此诗作于东周前期,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诗的地点仍在西都镐京。而韩诗学派认为《黍离》作于西周宣王时期。《太平御览》九百九十三羽族部引陈思王《令禽恶鸟论》曰:“昔伊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胡承珙对韩诗派此见评论说:“尹吉甫在宣王时,尚是西周,不应其诗列于东都。”胡氏之说是囿于《毛诗》与郑玄之见,对韩诗派说法加以责难,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值得深究。按:尹吉甫为周宣王人,是宣王中兴时期文武双全的名臣,据台湾学者李辰冬《尹吉甫的生平事迹与诗经》一文的考证,确认尹吉甫死于周幽王七年(公元前775年)前后,死时已有七十多岁。“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当然是尹吉甫生时所为。故据《韩诗》之说,可确认《黍离》一诗作于西周宣王时期,地点当然在西都镐京。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说苑·奉使篇》所载的一段战国时期的史话:
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使不往来。赵仓唐为太子奉使于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业?”仓唐曰:“业诗文。”侯曰:“于《诗》何好?”仓唐曰:“好《晨风》与《黍离》。”文侯读《黍离》曰:“彼黍离离”云云。文侯曰:“子之君怨乎?”仓唐云:“不敢,时思耳。”
以上记载与《韩诗外传》略同,清代学者王先谦评议这段记载说:“以父子之间其事相类故也。”(见《诗三家义集疏》317页)王氏意谓,据《韩诗》说,《黍离》一诗涉及父子之间的感情问题,伯封因其兄伯奇被父所杀,故作《黍离》以抒怨。太子击因三年之久未能与父王通使,很担心父王魏文侯有废除太子之位的可能,故借用好《黍离》而抒发忧虑。故文侯也因此问仓唐曰:“子之君怨乎?”按:魏文侯是战国前期的贤君,非常精通《诗经》,深晓借诗表情达意的特殊功能。有鉴于此,可以肯定《韩诗》对《黍离》一诗题旨的阐述在战国前期已流传颇广,《韩诗外传》载此,说明曹植的见解乃是对西汉前期《韩诗》学派的沿承;而刘向信奉《鲁诗》,则说明《鲁诗》派的一些学者与《韩诗》派对《黍离》的见解相同。
综上所述,齐、韩、鲁三家诗学者与《毛诗》对《王风》的理解颇有出入。《毛诗》认为《王风》是东都洛邑的风诗,作诗的时间自周平王、周桓王至周庄王。三家诗则认为《王风》为王畿地区的风诗,包含西都镐京与东都洛邑两个都区,《王风》有周宣王西周时期的诗歌,如《黍离》。由此可见,两汉时期对《王风》地域与时代的理解不一,并无定论,因此程、陈之说自然亦非定论。
至于《王风》为什么是风诗而不能属雅诗的问题,郑玄的解释也是缺乏说服力的。郑玄《毛诗谱》云:“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为王国之变风。”这一段话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其一、《郑志》云:“张逸问:平王微弱,其诗不能复雅,厉王流于彘,幽王灭于戏,在雅何?答曰:幽厉元道,酷虐于民,以强暴至于流灭。岂如平王微弱,政在诸侯,威令不加乎百姓乎?”从这一段记载来看,同时代人对郑玄的说法颇有异议,张逸的指责是颇有道理的,周历王周幽王因昏暴无道酷虐于民,历王因而被国人流放于彘地,幽王因而被杀于戏地,厉王、幽王的昏暴酷虐远过于平王,何以厉王、幽王期间的诗歌能称雅诗呢?郑玄的《毛诗谱》确定所谓的变雅与变风,不少归之于厉王、幽王时期,而唯独在《王风》问题上为厉王、幽王开脱,从逻辑上是讲不过去的,《王风》之所以属风诗,与东周的平王无必然的内在联系。
其二,郑玄说:“故贬之为王国之变风。”顾炎武说“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种说法是符合古籍记载的,既然诗经的编辑是太师的职责,他能在编定《王风》时,故意贬低东周平王天子的尊严,把王畿之诗降低为变风吗?周太师能有这种胆量与权力吗?这显然是郑玄想当然的说法,属主观臆测之辞。
既然郑玄以上的见解不能成立,那么陈子展所说的“以风贬周”的说法自然也不能成立。
当然,《王风》的地域与时代问题古无定论,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笔者不是说三家诗对《王风》地域与时代的看法一定是准确的,只是指出沿用《毛诗》与郑玄说的学者,其见解也未必准确无误,不能视作定论。
关于《王风》各诗的诗旨问题,众说纷纭,也很难作出全面而准确的判断,只是对部分诗歌的诗旨逐渐有了一些共识。
《黍离》——《毛诗》与《韩诗》理解不一,不赘叙。著名学者崔述《读诗偶识》说:“此诗乃未乱而预忧之,非已乱而追伤之者也。……《黍离》忧周室之将陨,亦犹《园有桃》忧魏国之将亡耳。”此为折衷之说,诗旨从《毛诗》,而时间在西周末,地域在镐京。现代学者郭沫若认为此诗系旧贵族衰伤自己破产的诗,而余冠英则说此诗是“流浪人诉忧之诗”。此诗迄今无定论。
《君子于役》——《毛序》:“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讽)焉。”班彪《北征赋》确认此诗为“怨旷之伤情”,属思妇念役夫之作,说明《齐诗》对此诗的理解优于《毛诗》。朱子《辨说》:“此国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辞,《序》说误矣。其曰平王,亦未有考。”现代诗经学者均从班彪与朱熹之说,可视作定论。
《君子阳阳》——《毛序》:“闵周也。君子遭乱,相招为禄士,全身远害而已。”王先谦《集疏》曰:“三家无异议。”古今学者对此诗理解颇有分歧,有夫妇相乐说,讽周景王好音说,刺子颓好歌舞说,贤者隐士伶官说,君子贫仕卑官说等等。现代学者对此诗的理解逐渐倾向于一致。高亨《诗经今注》说:“这是写统治阶级奏乐跳舞的诗。”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描写舞师和乐工共同歌舞的诗。”袁梅《诗经译注》说:“这女子看到了身为舞师的爱人,聚首言欢,心花怒放,其乐无极。”总之此诗属于描写歌舞欢乐的情景,这一点较合诗歌的本意,也基本成为诗经学者的共识。
《扬之水》——《毛序》说:“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朱熹《诗集传》对此说也提出疑问,而清代学者姚际恒亦指出,该诗言“戍申”、“戍甫”、“戍许”,只有“申”系周天子母家,甫、许虽亦属姜姓古国,但非周天子母家,何以归之于“刺王”?台湾学者李辰冬在此基础上,经考证,确认此诗为周宣王七年所作,其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据《竹书纪年于宣王七年》载:“王赐申伯命。”申伯是宣王的舅父,《括地志》说:“南阳县北有申城,周宣王舅所封。”周宣王为什么要封申伯于申城呢?其主要意图,就是《大雅·崧高》所说的“南土是保”。当时周宣王派召伯虎南征淮夷,申地正是一个重要的据点。甫地,即河南新蔡县一带;许地,即河南许昌,两地在申的西北,形成一条军事上的防护带,故周宣王必然要派兵戍卫申、甫、许,这是情理之中事。其二,甫,原名吕,到周宣王时才改为甫。《唐书》卷七十五《宰相世系表》说:“其地蔡州新蔡是也。历夏、商,世有国土。……宣王时改吕为甫。”据上述两点,《扬之水》作于周宣王七年,基本可信。
《中谷有蓷》——《毛序》:“闵周也。夫妇日以衰薄,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尔。”《毛序》所释诗旨无误,且亦未确认作于东周何王。朱熹《诗集传》说:“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妇人览物起兴,而自述悲凉之词也。”确认作者为弃妇。此说较切合诗旨,故现当代学者多从此诗,如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描写一位弃妇悲伤无告的诗。”此诗不能明确写作年代。
《兔爰》——《毛序》:“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数败,君子不乐其生焉。”陈子展《诗经直解》说:“自朱子《辨说》疑与桓王时事无关。姜炳璋、范家相、崔述、魏源,皆从诗语推究,谓当作于幽平之际。……朱子(《集传》)云,‘为此诗者盖犹及见西周之盛’”。可谓得其诗旨矣。由此可证,《毛序》作于桓王时说无据,自朱熹始至清代学者,多数确认该诗作于幽王与平王之际,即或作于幽王亡国之际,或作于平王东迁洛阳之时。
《葛藟》——《毛序》:“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但观看原诗:
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终远兄弟,谓他人母;谓他人母,亦莫我有!终远兄弟,谓他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
既于王族无关,亦于平王无涉。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流亡他乡者求助不得的怨诗。”较切合诗旨。诗旨如此,此诗创作年代不可考。
《采葛》——《毛序》:“惧谗也。”但观原诗: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朱熹《诗集传》确认为“淫奔”之诗,现代学者自闻一多始,多确认为恋诗情歌,很切合原诗。因此,该诗亦无法考证年代。
《大车》——《毛序》确认此诗为“礼义陵迟,男女淫奔”之诗。观看原诗:
岂不尔思,畏子不敢。(一章)
岂不尔思,畏子不奔。(二章)
穀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三章)
《毛序》之见无误,当然观点是陈旧的。按现在的见解来看,程俊英的说法当然更确切些:“这是一首女子热恋情人的诗。”(《诗经译注》)诗旨如此,该诗的写作时间当然也无法确定。
《丘中有麻》——《毛序》:“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周人思之而作是诗也。”自闻一多始,确认此诗为恋诗。现当代学者多从闻说。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一位女子叙述她和情人定情过程的诗。”历代学者对这首诗的解释很不相同。有说是思贤之作的,有说是写私奔的,也有说是招贤偕隐的。诸说均未尽妥。”诗旨属恋诗,写作年代亦无法确定。
综上所述,《王风》中《君子于役》、《君子阳阳》、《中谷有蓷》、《葛藟》、《采葛》、《大车》、《丘中有麻》7首诗创作年代难以考证。《黍离》诗,《毛序》以为“闵宗周”之作,时间在周平王东迁洛阳之后。但崔述则认为在西周幽王时期。而韩诗则认为此诗作于周宣王时期,与伊吉甫杀子或放逐其子事有关,此说虽非定论,但据《说苑·奉使篇》与《韩诗外传》所载,战国前期的魏文侯亦以《黍离》表述“父子之间”情事,可证此说较《毛序》说更充分些。《扬之水》诗,李辰冬先生定为周宣王七年之诗,依据较充分,远胜《毛序》之说。《兔爰》诗,自朱熹以来,姜炳璋、范家相、崔述、魏源与陈子展均以为此诗作于幽王与平王之间,即不排斥此诗作于周幽王镐京时期。据此三诗,基本可以证实,《王风》应是王畿之诗,其地域包括西都镐京与东都洛阳两个地区,非仅指王城洛阳。这一点,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得非常明确:“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至襄王以河内赐晋文公,又为诸侯所侵,故其分墜(古地字)小。”由此可见,周王朝封畿的缩小是在周襄王(前65—前619年)之时,距周平王东迁洛阳时已相差一百多年的时间。班固是著名的史学家,其说必有依据,故《王风》指王城洛阳六百里之说无史实依据可言。从《王风》的创作时期而言,应在周宣王至平王之间较为可信。至于东周王朝的地位问题,司马迁《史记》所说的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东周王朝毕竟还有不同于诸侯的一面,班固《汉书·地理志》就强调其另一个侧面说:“平王东居洛邑。其后五伯更师诸侯以尊周室,故周于三代最为长久。八百余年至于赧王,乃为秦所兼。”故郑玄“贬周”之说无据,五伯尚且尊周,而周王朝的太师竟敢贬周吗?
有关《王风》的地域与时代问题,自《毛诗》、郑玄起至陈子展、程俊英,一致认为是东周时期王城洛阳一带的诗歌,积习已久,几成定论。本文则以三家诗的资料为起点,综合古今学者有关研究成果,肯定了《王风》为王畿之风,创作时间为西周宣王至东周平王时期。
收稿日期:2001-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