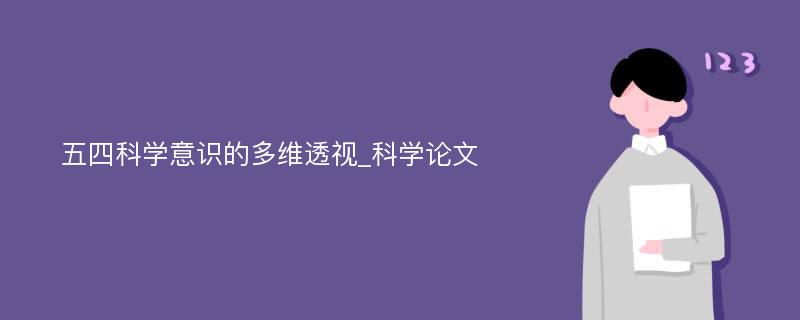
五四先哲对科学的多维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先哲论文,透视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时期国人对科学的认识水平相当悬殊。一方面,有些人乃至饱学之士对科学本身的了解是相当无知或肤浅的,“知科学为何物者,尚如凤毛麟角”。他们或视科学为奇制实业,或视科学为戏法和文章上的一个特别题目。就是略知一二的承学之士,也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太呆子、太窄了、太势利了、太俗了。连大名鼎鼎的玄学派代表人物张君励,也误以为科学是机械的、物质的、向外的、形而下的。
与此相对照的是,五四先哲(我在这里意指五四时期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在西方接受教育且具有广阔视野的科学家和文化人(以中国科学社的先贤和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代表人物为中坚),对科学的多维透视却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和深度,直令今日之学人汗颜不已。这些洞见主要有以下数项。
一、对科学的内涵、外延和特质的认知
五四先哲尝试给科学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以区别于其他学问、知识和技艺。陈独秀写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梁启超从广义上解释,把“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秉志认为,科学“无非将常识而条理之,俾有系统,更由有系统之常识,造其精深,成为专门之知识而已。”
任鸿隽在揭示科学的内涵和特质时表明,科学是自近代以降兴起的“事实之学”和“实验之学”,遂发展为“有条理之学术”。他强调,科学是学问不是技艺,科学的本质是事实不是文字,从而科学是知识而有统系之大名,科学家是讲事实学问以发明未知之理的人。杨诠认为:科学之职务在类分事实,明其关系与比较的重轻;科学的功用,则在能以简确的律例(定律)而驭无涯之经验;科学之目的,在求事物之统系,以简明之律例表其变化。
关于科学的外延和范围,任鸿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科学指自然科学,大体对应于英文词science, 广义的科学指一切有组织的知识, 即科学方法所应用的一切人事、 社会之学, 大体相当于德文词Wissenchaft。王星拱、胡明复也是这样看问题的。 后者借用英国哲人科学家皮尔逊的观点,如下发挥道:“顾科学之范围大矣,若质、若能、若生命;若性;若心理、若社会、若政治、若历史,举凡一切事变,孰非科学应及之范围?虽谓之尽宇宙可也。”
不过,五四先哲在讨论科学的功能、价值、精神、方法和文化意蕴时,主要还是针对自然科学而言的——也许出于有意,也许出于无意。
二、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全面审视:强调其精神价值
五四先哲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审视是全方位的,他们不仅看到科学的物质价值(请读者注意:这种价值并非科学所固有,而是通过其衍生物即技术为中介而导致的),尤其是强调了不甚明显的、易于被人轻视或忽视的科学的精神价值。
任鸿隽论述了科学功能的各个方面。他说,科学施于实用,则为近代工商业之发明;及于行事,则为晚近社会改革之原动;影响于人心,则思想为之易其趋;变化乎物质,则生命为之异其趣。“胡谓科学为近世西方文化之本源,非过语也”。因为科学出现之后,学术上添了许多新科目,社会上添了许多新事业,“世界上人的思想、习惯、行为、动作,皆起了一个大革命,生了一个大进步”。陈独秀也同样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还特别看重科学革除无知、破除迷信的精神价值。
五四先哲清醒地认识到,过分注重科学的应用有失偏颇,乃至造成某种恶果,因此他们十分强调科学的精神层面的价值和意义。黄昌穀以德国为例说明,过分注重科学的应用,其流弊遂至于专尚功利,走到极顶则“质胜文则野”。杨诠认为,科学的应用为枝节,而根株则在理论;使今日束理论于高阁,不特科学无进步之望,后人欲求新发明新应用亦不可得矣。胡明复指出:科学不以实用为始为终,在“求真”而已;真理既明,实用自随,此自然之势;夫科学之最初,莫不始于至微且无关紧要,而其结果则往往为科学界立新纪元,于社会上造一新思潮、新文化。苟令研究者孳孳以实用为主,诚恐其终无所获也。任鸿隽点明:“应用者,科学偶然之结果,而非科学当然之目的”;“故科学者,理智上之事,物质以外之事也。专以应用言科学,小科学矣。”五四先哲就这样以科学的内在结果和研究逻辑的视角着眼,指出不必过分看重科学的实用价值,隐含了科学是“好奇取向”而非“任务取向”的现代观点。
三、对科学精神的深入剖析
五四先哲在揭示和弘扬科学精神方面可谓着眼高远,殚精竭虑。他们把科学精神视为科学之根本和精髓,发表了诸多专门论述科学精神的文章,认为“科学精神之不存,则无科学又不待言矣。”
任鸿隽一言以蔽之:“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即科学“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在他看来,这种“高尚纯洁”的科学精神见于研究与致知之间,一是“崇实”(根据事实),二是“贵确”(分析定量)。黄昌穀认为,科学精神有两项特性:一是须根据事实以求真理,不取虚设玄想为论据,不放言高论为美谈;二是认定求知求用的宗旨,力行无倦。秉志提出,科学精神有五。一曰公:公开结果,大公无私。二曰忠:忠挚忠诚,不存虚伪。三曰信:惟求真理,是非分明。四曰勤:勤苦努力,穷年矻矻。五曰久:锲而不舍,终身不懈。
胡明复等人还持有这样的观点:科学之精神即科学方法之精神,精神为方法之髓,而方法则精神之郛也,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二为一谈。胡明复说:“科学方法之唯一精神,曰‘求真’”;“故习科学而通其精义者,仅知有真理而不肯苟从,非真则不信焉。此种精神,直接影响于人类之思想者,曰排除迷信与妄从”。梁启超也认为:“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科学精神”。
五四先哲关于科学精神的讨论和见解,直接受到批判学派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皮尔逊的影响,尤其是皮尔逊的科学哲学名著《科学的规范》(1892),对中国科学界和思想界的影响甚大。皮尔逊在该书中提出了科学精神(spirit of science,scientific spirit )或科学的心智框架(scientific frame of mind)的概念,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与科学精神相对照,中国学术和学界的拙陋立现。任鸿隽从三个方面揭露神州学风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一好虚诞而忽近理,二重文章轻实学,三笃旧说而贱特思。梁启超坦言,中国学术界因缺乏科学精神,所以生出如下病症: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他认为欲救这病,除提倡科学精神,无第二剂良药。
五四先哲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救国”之根本在于用科学精神救国。胡明复有言:若夫科学之可以富国强兵,则民智民德发育以后之自然结果,不求而自得者也;而惟真理是从的科学精神,最适于教养国民之资格,此科学精神之直接影响于社会国家之安宁与稳固者也。秉志认为:倘人人皆有科学精神,其国家必日臻强盛,其民族必特被光荣焉;而缺乏科学精神,其国家必日见剥削,其种族必不免于沦亡;“救国家者,必以提倡科学精神为先务”。
四、对科学方法的重视与探究
五四先哲特别关注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胡明复表明,科学之所以在事理之繁、变端之奇、种类之多、性质之异的困难面前取其同异,通其变化,溯其通则,全在科学方法,这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之特性。他引用了皮尔逊的名言:“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
关于科学方法的内容,黄昌穀认为,科学的致知方法从F ·培根主张研究自然现象须行观察与试验二法推求真理以后,遂渐成现在所谓的归纳法,与之相对的是演绎法。前者能发明古人所未梦有的新知,后者能推广古人不完全的旧知。杨诠这样回答何为科学方法:征集事变类分之,简析之,律之以假设,证之以实验,假设与实验符合,则律例(定律)成立;科学知识可变,而方法不可变。任鸿隽则从搜集事实、分析、归纳、假设等方面详论了科学方法,并把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的特点、长短加以对照。
胡明复指出:科学之方法,乃兼归纳与演绎二者;先作观测;微有所得,乃设想一理以推演之;然后复作实验,以试其合否;不合则重创一新理,合而不精切则修补之,然后更试一实验,再演绎之,如此往返于归纳演绎之间。丁文江则表示,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事实取出来详细分类,然后求它们的秩序,想一句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它。
在五四时期,也有所谓的“科学万能”或“科学方法万能”论,今人把这作为科学主义的罪状之一大加鞭挞。其实,该论点的代表人物丁文江是这样讲的:“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它的材料,在它的方法”;“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丁文江的这些观点是对皮尔逊思想的过度引申和发挥。不过,丁文江的“科学万能”实则是指“科学方法万能”,而且他在后者之前加有限定语“在知识界内”。况且,丁文江所说的“知识”又是“科学知识”,更何况他认为科学知识本身也不是牢固不拔的、一成不变的、有定论的。因此,今人望文生义,想当然地对丁文江等的科学主义的批判多属无的放矢。更不必说反科学主义在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是有失偏颇的(参见李醒民:“反科学主义思潮评析”,《哲学动态》,1990年第11期)。
五、对科学的文化意蕴和文化影响的探索
五四先哲明确认识到科学是一种文化,是近世西方文化的本源和代表。任鸿隽从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子和态度的定义出发,指出近世文化是科学的,即近代人的生活,无论是思想、行动、社会组织,都含有一个科学在内。这是近世文化的特采,也是科学的最大贡献与价值。
在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上,最能显示科学的文化意蕴和文化影响了。早在科玄论战(1923)之前,五四先哲对此就发表过有启发性的见解。杨诠认为,宗教的、艺术的、竞争的、实利的人生观均有弊病,应以科学的人生观补救;科学的人生观即是客观的、慈祥的、勤劳的、审慎的人生观。杨诠认为科学的人生观与科学精神相通,它有三大特色:颇具德谟克拉西(民主)精神,实事求是,甘于淡泊。任鸿隽也坚持,无科学知识者,必不足解决人生问题。“文学主情,科学主理,情至而理不足则有之,理至而情失其正则吾未见之。”
在科玄论战中,丁文江力主科学与人生观不能分家。王星拱指明:科学凭藉因果和齐一二原理,人生问题也逃不出这两个原理之金刚圈;科学为智慧发达之最高点,智慧之维持生活与改良生活,总要比本能高千万倍。胡适宣布了他的科学的人生观或自然主义的人生观的十大基旨,强调其中“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诗意,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充分运用‘创造的智慧’的机会”。任鸿隽也指出,科学不但借助物质文明间接地把人生观改变,科学自身也可直接发生各种伟大高尚的人生观。
还有一些作者涉及到科学与教育、宗教和伦理的关系,从中也能窥见科学文化的意义和功能。尤其是,唐钺在《科学与德行》中对科学与道德的关系作了十分精彩的论述,从七个方面阐述了“科学之有裨于进德”。
六、对反科学思潮的辩驳
针对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发表后高涨起来的反科学思潮,五四先哲的态度粲然可见。秉志明确表示,今日世界人类,未有不恃科学以图生存者;其有反科学者,毕不能存于天壤之间。诸多人士强调,反科学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杨诠坦言:吾国科学尚无其物,物质文明更梦所未及,居今而言科学之弊与物质文明之流毒,诚太早矣。胡适则明示:中国此时还不曾想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
当时,有人把欧战的责任归咎于科学,并鼓吹“科学破产”。对此,丁文江针锋相对地指出,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战争应负责任的是不科学的政治家和教育家。陈独秀则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欧战是资本家争夺世界市场的战争,它既不是玄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能制造出来的,更不是科学和科学家的罪尤。梁启超则一言中的:社会流弊和科学本身无干。
五四先哲还从学理上驳斥了国外的反科学思潮。例如,杨诠据理反驳托尔斯泰的“玩物丧志”和“为人作嫁”之谬说,批判尼采“科学造成客观之人和无己之人”的偏激之论。杨诠还专撰一文,逐一驳斥托尔斯泰不满科学的四个观点(科学不能解释生命之意旨,科学不以人类幸福为目的,科学与迷信相伯仲,科学既为职业则不得谓为裨益人类)。任鸿隽和唐钺还分别批评了科学损美说和科学败德说。
由于五四先哲能与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潮“接轨”,尤其是从世纪之交科学哲学和科学观的高峰(批判学派)那里汲取了思想营养,因而他们的见解在当时是相当“现代化”的。反观今日之域中,科学在某些人眼中仅仅是生产力(诚然,作为科学衍生物的技术通过诸多中间环节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出金钱和财富,而科学自身宁可说是观念层次而非器物层次的智力结晶和智慧酵素),在平民百姓心内是财神爷;而作为一种文化和智慧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的精神气质(ethos)却被有些人置之脑后,从而消解了科学的本真, 泯灭了科学精神(参见作者的文集《科学的精神与价值》,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面对思想的倒退和历史的中断,国人怎能不感到悲哀,学人怎能不感到耻辱。“五四”80年后的今天,面对如此局面,我们不能不感慨万千,同时又不能不心急如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