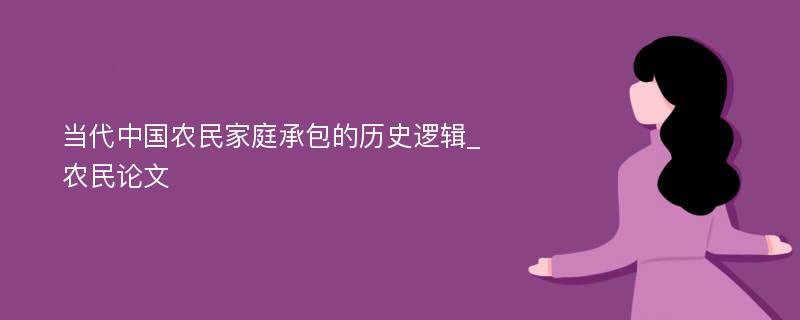
当代中国农民家庭承包的历史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民论文,逻辑论文,当代论文,家庭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27(2016)-01-0001-07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越来越多的农民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明里暗里干起家庭承包,表现出一种不计后果的冲动。这种反复的且愈演愈烈的冲动断断续续,终于在1980年代初取得了合法地位,获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形成了当代中国农村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家庭承包及其原因学术界有很多研究,但其反复冲动现象蕴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却探讨不够。本文愿抛砖引玉,以求教方家。 一、1950年代中后期:家庭承包星星之火 合作化、公社化的快速推进及其遗留问题,是1950年代中后期农民家庭承包兴起的根源。 高级农业合作社建立后,过于强调集中统一,过高提出增产指标,忽视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对社员劳动时间卡得过紧,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1956至1957年浙江、广西、安徽、四川、广东、江苏等地方出现了包产到户。湖南许多合作社推广新技术和新工具急躁简单,将零星的家庭副业和分散的手工业都统一归社经营。有些社员反映“入了社一点自由也没有了”。[1]福建除了渔业、造林以外,对多种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普遍不够注意。有些地区批评搞副业是“资本主义思想”,有的地方甚至把果树、茶树砍掉去种地瓜,把著名的“建莲”莲田改作稻田,该省几项主要山林特产到1956年还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2]农民们说:“共产党领导农民办合作社,增产粮食,什么都好,就是不准搞副业不好”。[3]合作社不能妥善地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收入分配问题,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河南省反映,“从八个社夏季分配的结果看……各社公粮比例很不平衡,最低的占夏季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八,最高的占百分之二十四;在其他税收政策和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的比价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在分配工作中,有些社有平均主义思想。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有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一定的影响。”[4]这些问题在各地农村都有反映,引起一些农村基层干部的思考和探索。 浙江温州专区永嘉县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先驱,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5]温州农业合作化以后,“经营管理体制日趋大与公而广大农民却迫切要求分小生产单位,分田到组、到户,经营体制和管理方法上的分与统的矛盾斗争一直贯穿于合作化、公社化全过程。”[6]永嘉包产到户是农民在县委领导下的有组织的探索行动,虽得到省委领导的支持,但在地委和《人民日报》先后强烈干预下被迫停止。1956年上半年,雄溪乡燎原社在县委干事戴洁天组织下进行责任制试点,形成了“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的做法。这种做法被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称为“包产到户”[7]。9月,李桂茂为书记的县委决定召开全县高级社社长千人大会,介绍燎原社经验,布置“多点实验包产到户”。[8]试验推广工作效果很好。[9]至次年2月,全县255个高级社实行“包产到户”,占高级社数的39%,占农民户数的42%。3月初,浙江省委在压力下改变支持态度。温州地委下令停试包产到户。10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新华社记者的报道《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做法》。同日,该报发表署名“南成”的文章《调动农民什么样的积极性》。文章点了浙江温州、广东顺德、江苏江阴等地的名,认为,这些地方搞包产到户,是“有的人想摆脱社会主义的轨道,重新再走过去的回头路”。1958年2月至6月,省委、地委对永嘉县主张搞包产到户的人员进行了处理。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农户承包情况。1956年春,广西环江县“下南区希远社实行了大宗作物统一经营,小作物(如杂豆、南瓜、番茄、辣椒、火麻、蔬菜等)下放到户,谁种谁收的办法,被群众称为‘大集体下的小自由’,获得较大增产。县委书记王定召开县委会议,决定将社适当划小,山区单家独户则实行‘包产到户’,社队都可推行‘小作物下放到户’。经试点后,逐步在全县推广。”[10]广西平乐专区1957年6月“水田‘三包’到户的有486个生产队……”[11]1957年春,安徽“芜湖宣城县等地开始公开或不公开地实行包产到户。”[12]同年,蚌埠市部分农业社也实行了包产到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35%。”[13]四川江津地区“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包工包产包到了每户社员。生产组承包了一定的土地、一定的产量和一定的成本,又把它分给组里每户社员负责。”[14]江津县龙门区刁家乡“在区委副书记刁有宽主持下,借推行包工为名,把合作社的田土,按各户劳力、人口情况,分到了户;肥料、种子也分了;耕牛不好分,就由各户轮流喂养、轮流使用。生产、收获各户自己负责。各家收的各家得,只按预订产量交纳公粮和部分公积金。很多社员把它叫作‘二道土改’。”[15] 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受到控制。为了争得自主权,家庭承包之火在一些地方“死灰复燃”。1959年5月,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认为,集体对农民卡得过死,剥夺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由。他提出: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把50户以上的生产队分开,按户包给家长。于是,60%的生产队重新丈量土地,出现了“父子田”、“夫妻田”、“姐妹田”。这年,地区“实行包工包产到户的公社175个,占总社数的72.9%;大队2342个,占大队总数的37%;生产队1.2957万个,占生产队总数的29.3%。”[16]同年秋收以后,安徽休宁县一生产队私下里把田分种了。“那是一个小自然村,三四十户,处在丘陵地带,偏僻一点。”[17]甘肃“武都县隆兴公社红石生产队搞包产到户,并且把土地、车马、农具按劳动力固定到户……还有的把全部农活或者大部农活包工到户,取消了或者基本取消了集体劳动,恢复单干。”[18] 反右倾运动开始后,包产到户遭到批判。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8月22日发出的《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揭穿“包产到户”真面目》。浙江永嘉县等地的包产到户虽然先后被迫中断,星火熄灭,但其促进农业增产的甜头永驻农民心田,成为后来家庭承包“规律性冲动”之源。 二、1960年代前期:家庭承包烈火熊熊 1960年代初,经济生活困难严重,全国半数以上的省份先后兴起形式多样、名目各异的家庭承包。1961年8月,中央农村工作部编印的《农村简讯》第175号登载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反映:“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有些地方在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中,把全年一半以上的农活包工到户,结果导致变相的‘包产到户’或‘部分产量包到户’。”[19]这份报告反映的情况有一定的普遍性。杜润生说:1960-1962年,“全国各地陆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单干,据统计约占20%,或曰30%左右。”[20] 安徽在这轮包产到户中最有代表性。1961年2月,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提出“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责任制,并到合肥市郊蜀山公社试点,形成了“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简称“责任田”。3月15日,他在广州向毛泽东汇报,得到可以试验的表态。省委决定全面试行。宿县最为积极,70%的生产队一个多月就实行了“责任田”。年底,全县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98.8%。农民不仅吃饱了肚子,还免费救济了外地来逃荒的农民。[21]滁县地区“仅两、三个月时间,全地区20163个生产队,实行‘责任田’的就有14550个,占72.2%,天长、全椒、嘉山三县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达90%以上。”[22]1961年底,“全省试行‘责任田’的有261294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90.1%。”[23]当年10月,省里对36个县调查,每县各抽2个情况不同的队进行比较,结果:“实行责任田的36个队粮食平均亩产比上年增长38.9%,另外36个条件大致相同但未实行责任田的队,平均亩产只比上年增长12%,责任田对粮食增产的效果极为显著。”[24]天长县98%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在灾情严重的情况下,仍普遍比上年增产,社员食用粮一般达到200公斤。”[25]12月中旬,曾希圣被在无锡的毛泽东喊去劝他把责任田变过来,他没有答应,七千人大会期间被免职。1962年3月,新省委作出《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省委坚决“纠正”责任田。不过,工作并不顺利。“1962年只‘改正’了12%,大部分在1963年完成,1964年搞‘四清’时,还有个别没有‘改正’过来。”[26]宿县到1962年底,“真正由县委领导‘改正’的只有试点的1个大队,下属11个生产队。”[27]岳西县至1963年7月,“尚有85个队明改暗不改,599个队改田不改地,42个队改田不改山,44个队改田不改埂……”[28]安徽宿县、太湖等地一些基层干部还上书中央,举荐或力保包产到户。 家庭承包在其它地区也普遍出现。如东南地区。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凤凰大队1960年“根据农民的要求,把低产田按地定出产量标准,分给社员一家一户去种,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取名曰‘就地分粮’。”[29]1960至1961年,广州从化县江埔、城郊等公社有20个大队试行“户包中耕田间管理的‘超产奖励责任制’”。[30]1961年下半年,潮安县提出在生产队内可划出10%-15%的地包产到户。“全县有45%的生产队实行这种做法。”[31]浙江缙云县“1960年冬,木栗、胡源、溪南等公社部分生产队搞过包产到户。1961年不少社队自发搞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1962年,全县约90%生产队自发实行旱地包产到户”,6月以后,“全县3997个生产队有2820个部分或全部水田包产到户。”[32]同年,龙泉县“全县4049个生产队中有206个队搞包产到户。”[33]1961年,福建省永定县“湖坑、大溪等地有些生产队搞‘定产到田,分户管理’……生产队的土地包给社员耕种,社员向生产队‘包产量,包成本,包工分’。”[34]1962年春夏,龙岩地区按生产队计算,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占68%。[35]同年10月,长汀县委统计,全县3801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2552个队,口粮田、征购田都包到户的698个队,占总队数的85.5%。[36] 中原华北地区。1962年6月,河南省委决定实行田间管理到人、包工到人的责任制,使河南恢复了元气。[37]河北省张家口专区的蔚县、怀安县,沧州专区的河间县、南皮县等地同年实行了“借地”、包产到户等做法。蔚县常宁公社“将95%的耕地按人劳比例或按人口分包到户,社员完成定产任务后,收获全部归己。”[38]同年,山西阳城“全县24个人民公社中,有12个公社的19个生产队作实验。他们共将377亩土地,包给了222户社员耕种。寺头等5个公社的13个生产队,把199亩菜园包给了156户社员管理。”[39] 西南地区。1961年春,湖南浏阳县有58个公社、380个大队、1739个生产队自发地实行“产量责任制”,占全县总耕地面积9.2%。[40]同年冬,湖南将数百万亩冬闲田借给农民(大体每人三至五分),种植冬菜或冬种春收作物,收入全归社员。贵州毕节地区赫章1961年冬至1962年春“全县有180个生产队自发搞包产到户,占总队数7.98%。”[41]1962年2月,广西“有不少生产队已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龙胜县共有1867个生产队,其中790个(占42.3%)已经包产到户;三江县对15个公社的了解,有247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15.3%)实行包产到户……较严重的高明公社有56.2%的生产队已分田单干。”[42]龙胜的情况引起中央关注。4月,邓子恢和张云逸到广西解决包产到户问题。6月上旬,陶铸和王任重也到龙胜调研,研究如何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的问题。 这一轮农民家庭承包时间长、地域广、形式多、影响深,以至于“文革”期间,一些地方仍然在悄悄地实行各种形式的家庭承包。1973年,四川广元县沙河公社桃园大队二四生产队“名为集体经营,暗搞包产到户,又被发现并于当年11月地区在广元召开的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作为‘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典型’公开批判和禁止。”[43]1974年,河南登封县唐庄公社东坡生产队冒着风险实行“以地定产定工”,结果红薯产量倍增。[44]家庭承包的熊熊烈火表明,农民即使是在“文革”极“左”的高压下,也充溢着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三、1970年代后期开始:家庭承包燎原全国 长期“左”的经济政策和政治运动使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生活极度贫穷和困难。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时,“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45]凤阳“一到农闲,全县五六万人外出,在全国各地成群结队地要饭,安徽因此得了个‘雅号’叫做‘叫花子省’。”万里在与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说:“社会主义还要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46] 1977年冬,安徽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省委形成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由于大旱愈益严重,次年9月,省委决定“借地渡荒”,引发了家庭承包的复活。肥西县山南区率先推行包产到户,11月,“已有726个生产队实行了这一办法,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11.29%。”[47]此后逐年增多,1980年春达到97%。1978年10月,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山尧大队前郢生产队“在县委书记王业美的支持下,自发地搞起‘分田单干’。”[48]年底,全县有25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1979年春增加到43个。1979年3月,国家农委在京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的农委负责人)和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村工作座谈会。安徽的包产到户情况引起与会者激烈争论。4月3日,中央批转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虽然允许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但还是认为:它“在否定统一经营这一点上,实质上和分田单干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是一种倒退。”[49]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确认了“两个不”:“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50] 农民的实践走在了政策的前面。1979年2月,安徽凤阳梨园公社小岗、雁塘头两个生产队开始包干到户。两个生产队是全县出名的穷队:“工值一毛九,吃粮一百九”是社员常年的收入水平;粮食总产量由50年代初的近30万斤下降到70年代的不足10万斤;20多年间,两个队共37户社员,净吃国家返销粮35万斤,用国家救济款3万元,有35户社员几乎年年都得靠讨饭来维持大半年的生活。[51]大包干时,小岗全队517亩耕地按人口分包到户,耕牛和大农具作价到户,国家征购任务、还贷资金、公共积累和各负责人员补助款,按承包土地面积分摊到户。[52]在县委书记陈庭元支持和公社领导同意下,包干到户顺利进行。[53]当年,该队粮食总产达到6.62万公斤,是1966年到1970年五年的总和;油料总产达到1.76万公斤,是过去20多年的总和;饲养生猪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该年小岗队粮食征购任务2800斤,实向国家交售1.25万斤;油料统购任务300斤,卖给国家花生、芝麻1.25万公斤,超额完成任务80多倍;归还国家贷款800元,集体留储备粮5000多公斤,公共积累150多元。1980年1月,万里来到小岗,看了以后当即表示:“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并对随行的干部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54] 万里到中央工作以后,安徽农村改革出现了一时的波折。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对家庭承包也想不通,“抵触情绪大,阻力重重。”[55]不过,普通农民对包产到户是“打心眼里高兴”。据安徽省委政研室1980年8月的调查报告,“有的社员说:安徽农村解放后30年社员有三笑,1955年(初级社时期)是微微笑,1961年(搞责任田)是嘻嘻笑,今年(实行包产到户)是哈哈笑。30年有三笑,哪一年的笑声也没有今年高。妇女们更是欢喜,因为包产到户能够自由安排时间,不误生产,多搞家务,还能走亲戚,她们说这是‘第二次解放’。”[56] 1980年5月,邓小平公开支持安徽凤阳大包干。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1号文件,正式将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的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定性为“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57]这以后,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农村改革大潮,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的改革开放。 四、农民家庭承包的历史逻辑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由于合作社、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体制不够灵活等,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村建设长期停滞,农民生活贫穷困难。“据统计,1957年至1977年,我国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从40.5元增加到64.98元,20年间每个农民总共只增加24.48元,即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1.2元。同期,按人口平均占有的粮食产量核算,20年间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0.5公斤。”[58]所以,农民具有强烈的改革意愿和冲劲。浙江一位农村基层干部说:“回想农村几十年工作,农民曾经多次自发地采取包产到户的行动……结果每一次都被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名义打压下去。……现在可以说,包产到户的出现是对原来土地经营制度,特别是对‘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制度的经营体制的冲击。因为长期存在生产上‘单打一’,劳动上‘大呼隆’,财产上‘归大堆’,财务上‘一锅粥’,分配上‘一拉平’。”[59] 家庭承包反复出现的情况表明,农民存在着一种可称之为“规律性冲动”的现象,这是一部生动的农业生产力“暴动”史。农民屡次自发的、私下的,冒着政治风险、甚至生命危险,而又兴奋异常地干起包产到户或大包干,这是一次次的冲动和“暴动”。冲动是相对于理智来说的,它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因为这么干政治上不合法,很容易受到打压。明知道危险,农民为什么还要做呢?因为,家庭承包符合低水平农业生产力基础上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要求,自然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实践证明,家庭承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适合农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种农业生产关系形式,能够促进农业及农副业的发展、农村社会的进步、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符合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因而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和强烈的吸引力。 1956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间,“规律性冲动”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蕴藏着当代中国农民家庭承包的历史逻辑: 第一,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对自主经营的追求是家庭承包反复冲动的历史根源。封建社会制度的废除和土地制度改革的解放,激发了农民久已存在的个体经济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红利”,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具有较长时间的历史合理性,应当与农民的集体经济积极性同样给予充分估计和肯定。 第二,亿万农民摆脱生活困境的强烈意愿是家庭承包反复冲动的历史动因。阻止和压制农民的家庭承包严重地影响和破坏了农业生产力,是农村经济社会不断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生产力面对制约它的生产关系总是要抵制、抗议、甚至“暴动”的。农民是农业生产力的集中代表,他们不愿长期忍受这种生产和生活的极度困难,如1960年代初期那种饥饿。由于曾经有过土地制度改革形成的个体农业经历和集体化初期少数地方包产到户的甜头,所以一些农民总是试图通过家庭承包来摆脱这种困境。 第三,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实干和创造是家庭承包反复冲动的历史主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应该能够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避免两极分化,但其前提是一定要寻找到公有制适合的实现形式,解决体制和机制问题。农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即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应当而且可以是多样的。在人多地少、血缘关系重要的情况下,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仍然有着较大的经济潜力,应当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家庭承包作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之一,是农民和基层干部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的成功创造。 第四,执政党各级领导层对农民创造的逐步理解、默认和肯定是家庭承包反复冲动被短暂允许、并在1980年代初最终取得合法地位和获得历史性突破的历史条件。家庭承包能够反复冲动、愈演愈烈、越来越扩大、最终获得政治认可,是与邓小平、陈云等的领导和各个阶段一大批地县干部敢于试验、敢于思考、敢于肯定、据理力争、坚持真理的实事求是精神和行为分不开的。他们是中国农村改革坚定的政治力量。他们坚信,农民过上美好生活意愿的能否满足是农村改革和发展实践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这些历史逻辑充分表明,以农民为本、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创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发展事业的根本宗旨和根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