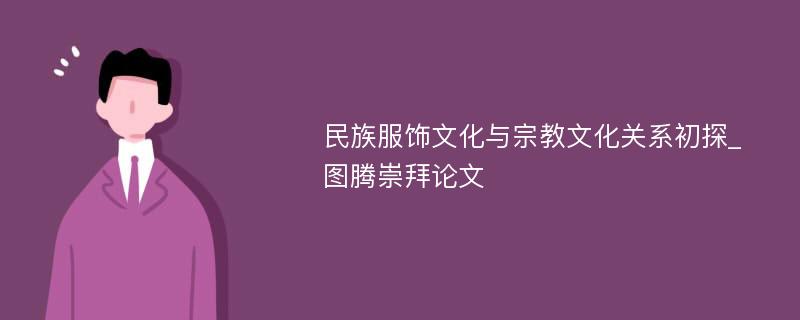
民族服饰文化与宗教文化关系初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宗教论文,关系论文,民族服饰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服饰是人类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为直观的民族文化特征。它包括人们穿戴的衣服和饰物。衣服主要指体衣、头衣、足衣,即人身上穿着的各种衣裳(上衣下裳)、鞋、帽等;饰物是指佩戴在身上起装饰作用的物品,常用的有珠串、刀剑、香袋、荷包、披巾及各种首饰,也包括文身和各种化妆品、涂料等等。服饰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宗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其所包含的信仰系统和仪式系统都具有多变性。因此,宗教作为人的一种精神现象,一种心理需要,一种了解、把握世界的方式,“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是一种形态极为独特的文化现象。”(注:张禹东:“宗教与文化关系的几点思考”,泉州:《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版),1999年第1期,第115页。)。
服饰和民族宗教虽然分属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它们在许多方面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研究为了与民族服饰文化相观照,将宗教文化界定在民族宗教、民族的原始性宗教的范畴内,对其与服饰文化相关的某些方面予以剖析。以下将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宗教文化与服饰文化的相互关联。
一、民族服饰文化对宗教文化的折射
服饰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人们可以通过某一民族外在表征的服饰透视其历史发展、社会习俗、宗教信仰,进而折射出该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如藏族、蒙古族等民族的男子胸前常常佩戴佛像,女子的银饰上往往刻有佛教法轮的图案,他们的衣服上经常编织上各种吉祥结,这是他们信仰喇嘛教的反映,也折射出了其向往平安祥和的民族心理。在此,民族服饰与民族宗教、与民族精神文化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布利亚特蒙古人以帽顶象征太阳,以帽缨象征阳光。元代蒙古人的栖鹰帽、士尔扈特妇女的陶尔其克帽正面都有火形图案,内蒙古博物馆现藏有蒙古族近代妇女所佩戴的银饰上有鸟形、蛇形图案,这都是古老的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图腾崇拜的遗迹。(注:中华孔子编辑委员会编:《中华地域文化集成》,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服饰文化中的纹饰可以反映民族的多神崇拜。民族服饰常用多种花纹图案加以装点,主要有:以诸如山、云、河流、日、月、星斗、雪花等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作纹饰;以植物类的各种树木花草作纹饰;以龙、虎、豹、狮、鱼、凤凰、麒麟、燕子、蜜蜂、鸳鸯、孔雀、喜鹊等等动物作纹饰。这样,不仅具有装饰美化的作用,而且隐含了特定的宗教观念。麦克斯·缪勒认为原始人从三类自然对象形成宗教观念:(1)他们能够把握的石头、甲壳一类的物体;(2)树木、山河一类能够部分把握的物体;(3)苍天、太阳、星辰一类不可触知的物体。(注:纳日碧力戈:“‘民族’的政治文化评析:人类学视野”,北京:《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第58页。)其实,如上所述,人们用以装点服饰的花纹图案并不仅局限于这三类,还经常动用种种动物图案作纹饰。在众多多神崇拜的民族中,这些自然物具有“半神之物”的性质。
民族服饰的更改可以加深或淡化人们的宗教观念。骑射、服饰、语言这三种被直接继承下来的民族传统,成为满族最为直观、最为根本的特性文化。(注:张佳生:“满族文化总论”,沈阳:《满族研究》,1999年第3期,第15页。)为骑射方便和抵御寒冷,满族穿长袍马褂,衣为箭袖,身束腰带。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乾隆皇帝于1747年颁布了《满族跳神祭祀典例》,规定萨满教活动的程序是:只穿神裙,不戴神帽。(注:转引自汪宗猷:“满族宗教信仰浅析”,参加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第七次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原见《满族研究》,1994年第1期,第64页。)汪宗猷先生认为萨满教因此渐为其他宗教所取代。(注:汪宗猷:“满族宗教信仰浅析”,参加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第七次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如果这种论述充分的话,就足以说明服饰在宗教的传播和延续方面的重要作用。
宗教服饰还具有区别宗教与世俗及宗教内部分类的作用。喇嘛教在历史上曾是藏族普遍的宗教信仰。因此,藏民族的服饰与喇嘛教的关系甚为密切。喇嘛的服饰与俗民的服饰不同。喇嘛中不同等级不同教派的僧服各不相同。一般喇嘛穿紫红色长及脚踝的裙子,上身穿一件背心,披紫色袈裟。“宁玛派的僧人戴红色的帽子,格鲁派的僧人戴黄色的帽子。西藏的四品以上僧官穿黄袍,着红云绣靴,四品以下官员则穿紫色或蓝色的长袍,蓝云绣靴。一般的藏民,无论男女老幼,大都身佩‘护身符’,就是佛像,或是经文,或是‘舍利灵丸’,或装进精致的‘宝匣’,或包以珍贵的呢革,或佩带身上或系在颈间,认为可以避灾免祸”。(注:覃光广等编著:《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
各民族绚丽多姿的服饰文化,通过繁多的款式、丰富的面料、鲜艳的色彩、精美的制作、独特的装饰等多个方面,解读其所蕴含的深厚凝重的文化韵味及宗教内涵。
二、宗教文化对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
宗教文化对服饰文化有引导和制约作用。民族服饰带有明显的民族宗教色彩,服饰的灵感常常得源于多神崇拜、图腾崇拜等宗教观念。对于服饰作出直接规定的宗教的影响力更加深远。
(一)图腾崇拜对民族服饰的影响
我国许多民族都有自己所崇拜的图腾,都有图腾信仰。图腾信仰是一个社会中的许多不同的群体各自认定一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其代表,各群体的成员对于代表他们的图腾都经常有认同感,不但认为自己是图腾的子孙,而且觉得自己也具有该动物的各种特质,因此图腾的成员对图腾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并进而产生崇拜以及禁忌杀戮或触摸的心理。(注:李亦园著:《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67页。)瑶族对盘瓠的崇拜具有明显的图腾崇拜的特征。他们崇奉盘瓠图腾,相信狗是氏族的保护物。由这种图腾崇拜而产生的一个禁忌就是禁食狗肉。根据图腾主义同体化的原则,在衣着、饮食方面模拟图腾崇拜物,是图腾崇拜的重要内容。在传说中,盘瓠是一只“五采斑斓”的龙犬,因此,瑶族着衣无论男女,都要在领边、袖口、裤沿和襟两侧绣上花纹图案,有的地方的瑶族还特意把上衣剪得前短后长。妇女(注:根据岑家梧先生的研究,认为戴这种象征狗耳的帽子的只限于已婚妇女。这可能因为图腾民族成员在达到一定年龄时,才行入社仪式。大概瑶族的未婚女子未被承认为图腾成员,也就无须穿戴象征图腾的衣饰了。)将发结梳成角状,再覆上花帕,腰带在臂部掉下一载;男子裤管两侧绣上红线,以象征图腾形象。(注:张有隽:“瑶族原始宗教探源”,宋恩常编:《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页。)对于瑶族婚丧仪式、服饰中的图腾信仰状况,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也有记载:“女初嫁,垂一绣袋。以祖妣高辛氏女配盘瓠,著独立衣,以囊盛盘瓠之足与合,故至今仍其制云。”
畲族的图腾崇拜也是盘瓠信仰,但其因循的神话传说及象征意义则与瑶族不同,因而在服饰上对这种宗教观念的演绎也就有着自己的民族特色。畲族男性的服饰与汉族无异,居住在广东凤凰山区的女性的传统服饰一直是凤凰装。具体装束为:头发梳成凤髻,身着衣领、衣袖、衣边都绣着鲜艳花纹的凤衣,腰间束有向后打结的长长的彩色腰带。凤凰装的来历依然与盘瓠有关。据说这是高辛氏为女儿与盘瓠成婚而精制的嫁衣——镶满宝珠的凤衣和华美的凤冠。后来其女再为自己的女儿做嫁衣时,也按照这种式样缝制,从此代代相传,就成了畲族女性的民族服装。“畲族妇女凤凰装,表现了一种富于神话韵致的飘逸美,而且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畲族人在古代图腾崇拜的原始时代,对大自然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朦胧美的追求。”(注:中华孔子编辑委员会编:《中华地域文化集成》,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第694页。)
宗教图腾对服饰的影响也体现在文身方面。据民族学资料,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文身与宗教信仰,尤其是与图腾崇拜(在躯体上刻划图腾动植物)有关。有时与某种魔法观念有关,如在出征前在身上或脸上画上某种图案,用以壮自己的胆或威吓敌人。(注: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00-401页。)对于文身的起源,甚至有的学者提出了“宗教图腾说”。“刘咸先生在阐述文身有宗教符号意义的基础上,对文身有宗教图腾意义进行了这样阐述:‘文身有宗教图腾之意味。……黎人文身之起源,一说谓生前若不刺涅,特标记号,则死后祖宗不认为子孙,必为野鬼。由此观之,文身实具图腾意味。’(注:陈睿:“论黎族文身与刀耕火种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第50-51页。)不管此说是否可靠,但由此可见宗教对人体装饰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况且还能说明民族的原始宗教对民族服饰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民族宗教中对于服饰的直接规定
在较为成熟的民族宗教中对民族服饰则有直接的规定。如穆斯林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其所信仰的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在服饰方面也作了明确的规范。《古兰经》说:“阿丹的子孙啊!我确已为你们而创造遮盖阴部的衣服与修饰的衣服,敬畏的衣服尤为优美。这是属于睦主的迹象,以便他们觉悟。”(注: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可见,真主所创造的服饰的主要目的是遮盖装饰,并不主张刻意追求华美,只要整洁美观即可,这也体出了伊斯兰教的服饰审美观。伊斯兰教对装饰品也有自己的要求:反对过度装饰,反对纹身、戴假发等改变真主原造的装饰。在具体要求上还有男女之别:伊斯兰教允许妇女穿戴丝织品和金银首饰,对于男子不主张着此类女性服饰,认为这有损于男性的阳刚气概;它还反对妇女穿透明的或不能遮盖大部分肉体的服装,反对男子穿大红大绿的衣服。“在西北地区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穆斯林中,礼拜时身捉黑色长袍,头戴白色无沿帽,既体现肃穆庄重,又不失协调美观。青年妇女披绿纱巾,中年妇女披黑纱巾,老年妇女披白纱巾,衬托不同年龄女性的气质之美。”(注:南文渊著:《伊斯兰教与西北穆斯林社会》,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
三、以萨服饰为例解读民族服饰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共通性
人的宗教经验具有深刻的普遍意义。通过宗教象征来表述人对外在世界的看法并依此演练人界的社会特性,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人文活动。(注:王铭铭著:《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穿衣戴帽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必经历程。因此,服饰与宗教存在着诸多内在统一性。这里,先从二者的功能方面予以简单揭示。
从某种意义上讲,服饰不仅具有基本的御寒、护身、遮羞等基本的实用功能外,还具有与宗教相似的功能,换一角度可以说是有协助宗教发挥作用的功能。现代新功能派的人类学家将宗教仪式的功能综合为三类:生存的功能;适应的功能;整合的功能。(注:即具有帮助个人与自然奋斗并求得生存的功能;有时着重于调适个人心理、适应社会的功能;经常发挥加强社会关系、整合社会群体的作用。)据此分析,二者在功能上看似分立,实则具有一定的相通性。服饰的御寒、护身功能本身就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的。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服装慢慢衍生出了调适心理、适应社会和加强社会关系、整合社会群体的功能。服饰在其演化和发展的历史上,发挥基本的功能的同时,似乎更加强调它在区分民族本身所具有的作用,它逐渐成了民族认同的符号、族群区分的标志,在这一点上,它和宗教一样都具有强化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的作用,能够维持族群认同和共同的民族意识。也是其他族群对其认识的主要依据。两者共同为该民族文化要素。这与宗教的社会功能——传统宗教巩固了群体的规范,给个人的行为提供了道德制裁,为共同体平衡所依赖的共同目的和价值观念提供了基础。(注:王铭铭著:《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存在很大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在上述三类功能中还隐含着宗教的美学价值、娱乐功能。宗教的娱乐要素和审美要素同时具备了内在美感和外在美感。这与服饰所蕴含的艺术美感是相似的。宗教仪典即宗教的表现仪式和集体娱乐很难严格区分开来。在娱乐过程中,很难离开服饰的点缀和烘托,宗教仪式中的人们往往是盛装的。其中,必须由服饰充当外壳和形式来表现内涵。
人类学家所把握的数百个较完整地代表人类文化行为的“全域”的民族文化资料,这当然包括中国的诸民族在内。“因此用这些资料作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如何有力地塑模一个民族的信仰,以及一个民族的信仰如何成为其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而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其他层面,……”(注:李亦园著:《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257页。)宗教自身外现为服饰、建筑、饮食等物质实体。下面将以结合了民族服饰这个物质实体和萨满教的宗教内核的萨满服饰为例解读民族服饰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共通性。
民族间服饰的差别,丰富了跨民族宗教的文化。在我国的众多民族中,有些不同的民族会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如信仰萨满教的主要有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和锡伯族。但因作为宗教活动主持者的萨满在宗教活动中穿戴独具民族特色的服饰,而使其宗教文化又更丰富多彩、更富民族特色。
(一)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和赫哲族的萨满服饰
从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和赫哲族的服饰来看,他们主要有较为复杂的神帽、神衣,及相对简单的刺绣上蝇、蛙等爬虫小兽的神鞋、神袜和手套等物。下面以其繁复的神衣为例介绍其宗教活动中所反映出的精致的服饰文化。萨满的神衣是用兽皮制成的无领对襟长袍。领口到下摆,均匀对称地钉着8个大铜扣;前方左右襟上,各钉小铜镜30个,并有一个大护心镜;背部钉有铜镜5个,其中一个大的是护背镜。长袍前方左右下摆及袖口,横缝上刺绣花样的黑绒各3条(袖口一条),每条钉有小铜铃10个。神衣上加套披肩,其领围和胸襟两边均匀地缝上海贝360枚,象征一年360天。两肩处饰以彩飘带若干,并缝有布制禽一雌一雄,它们象征着萨满的使者。腰臂部系有神裙,由兽皮或布制的二十四条飘带组成。神裙的腰和飘带上,用彩色丝线刺绣出日月、松树、花草、飞禽、鹿、蛇、蜥蜴和狐狸等物,显示出这些自然神灵同萨满的亲密关系。神裙和披肩的飘带还象征飞翔的羽毛。整个神衣装饰,象是在众神庇护下的一座威风凛凛的不可攻克的城堡。(注:蔡家麒:“中国北方民族的萨满教”,宋恩常编:《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二)满族萨满服饰
神帽:野萨满(或称大萨满)戴神帽,家萨满一般不戴神帽。神帽是判断萨满神系的重要标志,也是判断一个萨满的神力、资格的标志。满族及其先世女真诸部萨满多以神鸟通领神系,神帽上神鸟的数量的多少,标志着萨满资历和神力的高低。
萨满神帽由帽托、帽架和各种帽饰组成。帽托多为红色棉制品,形似“瓜皮帽”,萨满戴神帽时,要先戴帽托,帽架置其上,以护头。帽架为铜制或铁制。三面小铜镜分别安缀在帽前脸正中和左右两侧。数量不等的铜铃挂缀在帽沿上方左右两侧的铜(铁)架上,帽顶则多为昂首翘立的神鸟,神鸟的数量,各姓氏不等,吉林满族石姓、杨姓萨满神帽上是三只鸟。萨满正是凭借神鸟的翔天能力来实现沟通人神之境界。帽后缀有4-5尺长的彩色飘带,多为红、黄、蓝三色,彩带象征着神鸟飞翔有双翅。神帽前脸的边沿下,挂着质料不同的条穗。
神衣神裙:与其他萨满教民族相比,满族萨满神服较为简单。神服主要由上衣和神裙两部分组成。个别保留野神祭的家族,萨满穿七星衫,一般是红色、对襟、无袖棉布衫,七星衫象征星辰。也有仍行野神祭的家族,萨满上身着满族白汗衫,与家萨满服饰无异。不同地区、不同姓氏、不同性别、不同类型的萨满神衣各不相同。
和上衣相比,满族萨满神裙显得重要得多,在他们的观念中,神裙代表云涛。无论野神祭萨满和家神祭萨满,下身均穿裙子,但质地、色调不同,做工精粗、镶嵌花边图案也有别。有的用天蓝色、绿色、深蓝色等布制作布裙,也有用粉、深绿等艳丽的绸锻制作神裙者。裙底边一般镶上一圈黑布边或剪有各种图案的花边,亦有在神裙下部镶上彩色绦子或镶上一条彩布者。
饰物:满族萨满跳神时会披挂七彩石坠、灰鼠和香鼠、貂、貉等毛尾、桦皮和藤条、黄柏、蒲苇、冻青等雕成的各种形态怪物、鱼皮和兽牙兽骨、禽羽禽爪、黄羊蹄角等物,有的披全身数百件之多,它们代表了宇宙间的各种生命与物质,萨满借用来为自己添加威力。
民族服饰的装点更突出了宗教的神秘性,它们在宗教活动中可以充当神圣象征符号的意义,因而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能够诱发信徒产生响应宗教活动的意见。“如果象征符号因其内含的意义而具有影响人的力量,那么操纵这些符号的宗教仪式的执行者更能够增强这种力量。”(注:童恩正著:《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页。)如人们认为萨满所佩带的饰品在神事活动中沾染了神力,希望萨满赏赐给自己作护宅神和守护神。如果萨满着常人服饰,那他(她)所从事的宗教活动就减少了神秘性,宗教的表现力和影响力也会大大下降。民族宗教通过作为外在因素的民族服饰得以强化。
四、结论与讨论
总而言之,民族服饰文化与宗教文化是民族文化中相互联合的两个重要方面。民族服饰文化对宗教文化有折射作用。宗教文化对民族服饰文化有引导和制约作用。二者在功能上存在诸多共通性,借助萨满服饰可以进一步揭示出这种特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传统的民族特征也在改变形式或增加新的内容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民族服饰同民族宗教文化一样,都改变了最初的样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如今的民族服饰很多时候只是呈现于民族节日和宗教节日中。因现代民族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民族服饰也大为改观,如旗袍已改变了原有的式样,且不仅是满族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服装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宗教的世俗化进程。现代的宗教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了人们的娱乐、集会活动。正是由于服饰文化和宗教文化之间存在许多相通之处,才使他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关照,在统一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自身,为人类文明增加新的活力。
标签:图腾崇拜论文; 满族论文; 民族服饰论文; 文化论文; 满族文化论文; 满族服饰论文; 中国服饰论文; 中国传统服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