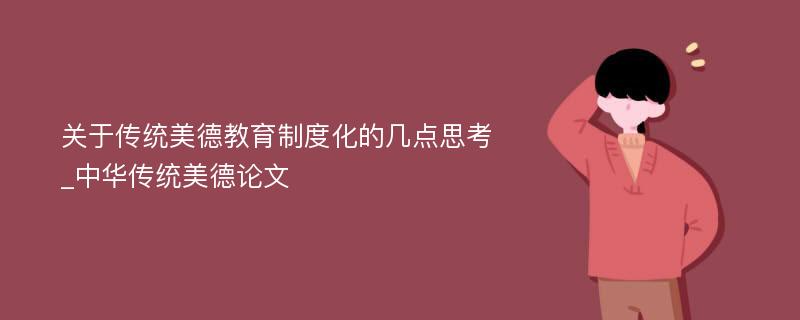
关于传统美德教育制度化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美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4)05-0018-0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对于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国家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作用。2013年12月30日,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1]这意味着党和国家对于传统美德与文化软实力关系的认识已经跃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离不开本民族文化的“根”和“魂”。中华传统美德就是“根”和“魂”之所在。笔者以为,对于当今久违了传统又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心无定所的中国人而言,传统美德教育无疑是提升民族素质、振奋民族精神的一剂良药。传统美德教育应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中返本开新的理性选择。这种教育不仅要着力进行,而且应当纳入制度化的轨道。 一、传统美德教育制度化的涵义 传统美德教育的制度化,就是国家运用公共资源和行政规制、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对公民施加传统美德的教育和影响,使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获得最广泛的民族认同。在此的“传统美德”,其内涵是指在对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经过现代转换,被赋予时代新意的道德精华。 如果说全球化背景下重视传统美德教育已然获得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的话,但对于“传统美德教育制度化”的提法或许就不能完全认同了。人们或许担心传统美德教育一旦制度化,就是搞“文化保守主义”,就可能是复辟倒退。而笔者认为,传统美德教育制度化,其特点与优势就在于能够借助组织资源和手段,使传统美德教育落在实处、落在细处,让传统美德真正成为国人的精神滋养。 “制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其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这就是说,“制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规则、规范、习俗,而是依一定程序由社会性组织来颁布和实施的一整套社会规范体系和运行机制。通常,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但从核心内涵来看,主要是指正式制度。传统美德教育的制度化,就是要通过政府及各种社会组织的一系列运作,有意识地调动各种公共资源,直接或间接地对公民进行传统美德教育并使之常态化。 传统美德教育制度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制度化并不相悖。一个国家的教育战略体系有不同层次之分,随之也就有不同的教育制度化形态。那些直接体现统治阶级或集团利益和意志的意识形态居于教育内容的最高层次,其他的教育内容均从属于这一层次。现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内容,居于教育的最高层次。制度化地保障这一教育的实施不仅毋庸置疑,而且是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特点和优点。传统美德教育,在教育层次上虽然低于前者,但却是“寻根”的教育,是中华文化精髓、中华民族精神的教育,它理应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得以传播和弘扬。 二、传统美德教育制度化的价值旨归 1.传统美德教育制度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国人精神家园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在国人中广为热议。尽管其内涵和价值共识还需要进一步明晰与规定,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追求,就其主要价值构成而言,不外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诚如《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古代中国这一“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就是华夏儿女的“中国梦”。作为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它激励着世世代代优秀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为之奋斗。大同理想也因此成为国人心中的精神家园和价值航标。当代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高速度,但也付出了高代价。经济理性的观念不断侵袭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左右人们判断、选择和决定的基本依据。“人类文化价值生活的可能性空间被大大压缩和挤占,现实或物化了的实在被理想化,而理想和信仰则被现实化和功利化。”[2]人们的精神家园迷失了,社会信仰体系呈现解构的状态。“中国梦”的提出,就是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航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振国人的精神家园。然而,这一宏大的目标将如何实现?它需要13亿中国人凝心聚力、励精图治,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有效整合社会意识,使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习近平同志最近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就是这个道理。 中华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习近平同志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3]以中华传统美德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具中国国情、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东西,是我们增强价值观自信的前提。党的十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进行概括的。个体层面所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德目早已存在于我国优秀的美德传统中。以诚信为例,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认识到它的价值,历代贤人圣哲对此的阐述不绝于史。例如,“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礼诚信,国之大纲”(《贞观政要·诚信》),“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诚善于心之谓信,充内形外之谓美,塞乎天地之谓大”(《正蒙·中正》)。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一文中,把“信”作为中华传统美德加以颂扬:“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可见,今日的诚信道德是对传统的扬弃。中华传统美德,既重视个人道德品质的锤炼,又重视社会道德规范的践行和整体利益价值的追求,是我们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传统美德,在当今依然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当前开展传统美德教育,有利于人们从情感上拉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距离,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 或许有人质疑,在当今社会信仰体系处于解构的状态下,传统美德教育是否管用?笔者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最适合国人的道德信仰体系和文化根基,是我们民族不可多得的道德资源。陈立夫曾经盛赞儒学的精神价值,认为就其对于人们的影响而言,它是一种精神信仰的东西。它似如宗教但深刻于宗教:“中国本身无宗教,有之,均自外来。中国人自来所崇奉者,为一非神之至圣先师——孔子。何以中国人民之道德水准一向不亚于有宗教国家之人民,或竟胜之?宗教者,教之所宗,所以教人如何去私心存公道,以合乎为人之道。更进而教人如何牺牲一己之利益甚或生命,以达致爱人助人之目的,而成为不移之信仰,以求合乎天命之所昭示。至于天堂地狱之说,不过用以鼓励人为善,劝告人不为恶而已。”[4]在当今权威弱化、信仰出现危机的社会转型期,以中华传统美德来凝聚国人,至少与国人的民族心理相契合,也有益于增强民族自信心。中华民族历来有崇先敬祖的传统,这种天然的文化联系使得国人在感情上难以拒斥这份道德资源。若教育得当,定会发挥良好的作用。 2.传统美德教育制度化是整肃党风政风民风家风、提升国家文明程度的需要 中华传统美德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宝藏,它既是国人安身立命、齐家处世、成就事业的品德基础,又是家庭和睦、社会发展、国家稳定的精神支柱。《礼记·学记》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中国古代统治者极端重视道德教化对于治国安邦、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认为仁义兴则道德昌,道德昌则政化明。今天我们在剥离其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及传统美德自身的相对性后,不妨借鉴传统美德在修身齐家、敦化民众、治国为政等方面的思想智慧和行为准则,以整肃党风政风民风家风,彰显社会正能量。在传统道德思维中,有两条相互映衬的逻辑主线是十分鲜明的:其一,良好政风民风的形成是以家庭为起点、为本位,由家及国,由家庭至社会;其二,良好民风及社会风气的确立依赖清明政风的带动,即为政者的表率示范。正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从前者看,良好的家教土壤必将培育出品学兼优的国家栋梁;从后者看,作为国家栋梁的为政者应成为社会道德的脊梁与样板。传统道德这种相辅相成的思维逻辑无疑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历史的沧桑巨变,传统美德与我们渐行渐远。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批判了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儒家学说,呼唤民主与科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立了思想文化基础。但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却否定多于扬弃。“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对于中华民族是个空前的灾难。传统文化遭遇灭顶之灾,传统美德被践踏。走过这场浩劫的中国人,承载着太多的精神迷茫和创伤,他们中留下的道德虚无正在产生着代际的影响。加之社会转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多元化和趋利动机的过度激发,以及对文化和道德价值体系建构的预设不足、判断不清、定位不准、行动不力,社会生活的道德底线被一再冲破。倘若我们再听之任之,再不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强化传统美德教育,那么诸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丰厚的传统美德遗产就要被断送。 2014年伊始,国内主流媒体开展了“家风是什么”的讨论,掀起一场重拾家风的热潮。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是传统美德重要的载体,蕴含着深厚的道德根基。它往往以小见大、由浅入深、由家至国。不孝敬父母又怎能尽忠国家?一屋不扫又何以扫天下?千百年来,传统美德首先透过家风家训及长辈的身教,在代际间传递着平实的生活哲理。百善孝为先,忠厚传家久。今天,当我们重拾家风的时候,有理由相信它将成为正能量,助推社会风气的良性运转。而当党风政风民风家风风正气顺之日,便是国家软实力和文明程度提升之时。 3.传统美德教育制度化是实现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需要 如果说以上的论述是着眼于当前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话,那么这一层意义则是关平中华优秀文化自身的未来。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两个相互依存、彼此呼应的理念。前者是要立足于当今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以扬弃的态度认真汲取传统美德精髓,挖掘和阐发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即古为今用。后者是要在前者的基础上,以传播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为目的,创造性地融传统美德精髓与时代美德于一体,将中华美德推向未来,即推陈出新。中华传统美德源远流长,对待这一道德智慧长河,我们不仅应当珍惜过去,而且还要创造未来。返本开新,这是一个民族有自信、有远见的表现。对待我国道德遗产,“五四”以来就存在不同的态度和主张。其中复古派唯道德遗产是尊,主张“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看不到旧道德的阶级性和历史性,以为返本就可以开新。这是对道德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清的幼稚表现。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上层建筑一样,是服务于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等的变革必将带来道德的更新。因此,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历史之必然。它既是对历史的尊重,又是对未来的担当。 无论是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还是创新性发展,都离不开制度化地加强对国人的传统美德教育这一前提。这是因为:第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项需要广大群众参与的伟大事业。若是国人陷于对传统美德的盲区或空白,是难以完成这一使命的。第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需要培养国人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习惯,积极引导人们追求和向往道德生活。而这些都将使传统美德教育制度化成为必要。 三、关于传统美德教育制度化的若干建议 综上所述,传统美德教育制度化势在必行。那么,究竟如何运行、如何操作才能收获实效?对此,笔者有三点建议: 1.在国民教育体系中适度增设传统美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课程,推进传统美德入耳入脑、深入人心 课程学习是教育的主要渠道,它的形式有两类,即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它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传递教育信息,对国民施加教育影响。对于教人立身处事的传统美德教育而言,两种课程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同样重要。将传统美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这是其制度化的重要举措。亚洲一些国家如新加坡、韩国、日本等,长期以来坚持将儒家道德观念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植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其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这些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当前,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增设传统美德教育课程,一是要处理好传统美德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大中小学美德教育一体化的关系。从前者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我们的指导思想,理应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并贯穿始终。而传统美德教育是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彰显本国资源优势、强调民族特色、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手段。二者相辅相成,却不能相互取代。当前,我们要着重防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取代传统美德教育的认识偏向和制度偏向。从后者看,国民教育体系的课程建设要形成大中小学美德教育一体化的有序局面。比如,小学教育阶段,以实践课程为主,重在学生良好品德习惯的养成。高中、大学教育阶段,以理论课程为主,重在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品德修养的提升。朱熹在描述唐虞三代官学盛景时就指出:“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可见,美德教育规律古今共理。 2.加大社会公共体系宣传和践履传统美德的力度,纠正传统美德教育中的各种偏向 除了国民教育体系的课程主渠道,传统美德教育制度化还要依靠其他社会渠道,营造良好的美德氛围。其中,公共媒体等舆论体系及各种社会组织宣传和践履传统美德的状况,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当前在加大传统美德宣传力度的同时,要注意克服两种偏向:一是形式主义偏向,即传统美德教育过分倚重学习古代的文饰礼仪而忽略了精神实质,搞复古主义。一些公共媒体热衷于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追求卖点,借传统美德教育之名大肆渲染作揖、行礼等形式化的外壳,将传统美德内蕴的实质精神搁置一边。二是庸俗、媚俗、低俗偏向。一些公共媒体或社会组织为迎合某些受众的低级趣味,以“搞笑”的心态贬损、丑化传统美德及其典范人物。这种偏向必须得到有效遏制。传统美德教育制度化,除了制度化地加大其宣传和践履的力度外,还应制度化地规范其运作的导向和水平。 3.在道德典范的选树上,积极挖掘其传统美德内涵,实现公民道德与传统美德的有机契合 典范教育或曰榜样教育历来都是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通常“道德典范”指的是堪称道德楷模的典型个人或团体,是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具体、生动、形象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道德典范就是模范地践履这种价值观并在此过程中表现出崇高的道德境界的人。在社会转型期,越是价值多元化,就越需要主流价值观的坚持和引领,代表主流价值导向的典范效应就要愈加彰显。近些年,党和政府在树立道德典范方面不遗余力。杨善洲、郭明义、任长霞等新时期的道德典范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等层出不穷。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廉洁奉公、敬业奉献、乐于助人、无私无畏等精神,既是当代社会理想人格的化身,又是中华民族优秀品德的缩影。今后在道德典范的选树与宣传上,除了彰显其时代精神外,还应充分挖掘典范人物精神中的传统美德内涵,突出其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美德特质,将公民道德的培育与传统美德的弘扬有机契合在一起,体现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充分张力。标签:中华传统美德论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 社会主义道德论文; 道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