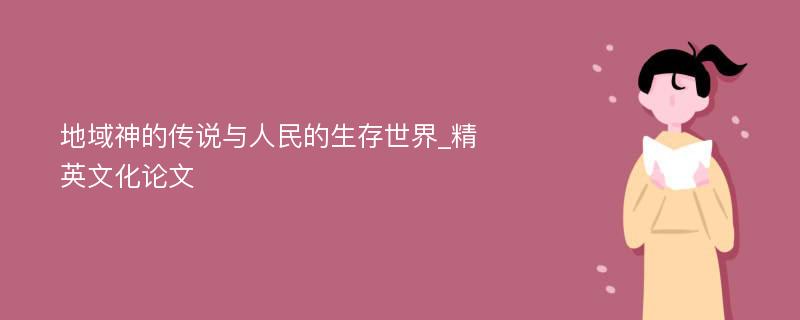
一个地域神的传说和民众生活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众论文,地域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中国民间传说的研究,学者多从文献材料出发,考察传说的起源、播布及其文化内涵。由于缺少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因此也就无法深刻理解民间传说与民众及其生活世界之间的互动。本文试图就一个客家村落的神庙信仰的历史进行民族志的重建,分析一个地域神传说的演变与民众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为民众如何对民间传说进行动态的创造提供一个个案,引起学者对民间传说与具体时空坐落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予以关注。
一、神庙的区位
作为神庙的“白石仙”,位于江西省宁都县东山坝乡富东村境内,是宁都北部具有区域影响的民间神庙。庙内供奉的是一块巨大的白石。“白石仙”的区域影响覆盖了整个东山坝乡以及宁都县“上三乡”的洛口、东韶、肖田、琳池、黄陂,以及临近的于都、会昌、广昌、兴国等县。
富东村,位于宁都县北部偏东,行政上现有24个村民小组。明清时期属于太平乡十二都,为“上三乡”。全村有人口4427人(1996年统计数字),主要由罗、李二姓组成,另外还有少量的张姓,其中罗、李二姓各占2000人左右。罗姓主要居住在柞树、前门、和里(旧称窝里)等自然村,李姓则主要居住在塘边、塘角、垅田及冷田等自然村。自古至今有“富东五坊”(柞树坊、前门、和里、塘角和塘边)和“罗李两姓三族”的说法,即李姓为一族,前门罗姓为一族,和里罗姓与柞树罗姓为一族。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以前,柞树罗氏和前门罗氏还存在着血缘和仪式上的认同。从康熙三十二年柞树罗氏开始独立修谱以来,前门罗氏和柞树罗氏基本走上了家族独立发展的道路。三族均有自己的庙宇,柞树坊、和里为“白石仙”,前门为“新华山”,李氏为“明华山”。
二、传说的形态
1、原生形态
“白石仙”首先是作为柞树坊、和里家族的信仰中心,为区域的民众所认识。其庵堂位于富东的后龙山,地名为燕子岩。关于其来历,民间的说法是:在很久以前,罗姓有一小孩每天都在燕子岩附近的稻田里放养鸭子,等傍晚回家时总要少一只鸭子,他感到很奇怪,可又没有办法,他便对着天天坐的那块白石说:“石头,你要是能保护我的鸭子不会少,我就象敬菩萨一样天天敬你。”果然从第二天开始鸭子便不少了。那小孩将白石灵验的奇事告诉村子里的人,慢慢的人们有事情就求白石保佑,而且那块石头也越长越大,人们便为白石修建了一座寺庙,加以供奉。白石仙崇拜实际上是民众对自然物——一块巨大的白石的崇拜。民间对石头的崇拜:“一是某种石有功于人,人们感激它、崇拜它;二是某石与众不同,使人感到神秘,于是人们神化它,奉之为神。”(注: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第350页,上海三联书店。)人们对其外表的奇异和神秘性的敬畏而崇拜它,进而上升为神。清代,柞树坊罗氏在白石上修建仙庵,永赡香灯执管,标志白石仙为仕荣祖派下族众所有。一般村民都认为白石仙只是一块具有神性的白石而已,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对柞树坊6位崇拜“白石仙”的家庭妇女作过访谈,问她们是否知道“白石仙”是怎样的一位神仙,大多数回答不出其中的所以然,有的只知道其神迹的片段,能比较完整地讲述的几乎没有,基本上只知道一块白石为牧鸭孩童所朝之后逐渐为富东民众所朝拜的发展过程。这说明白石仙作为仕荣祖派下族众的家族神明的人格化时间并不遥远,以至于它的人格化之后的神迹未能在民间流传。
2、人格化形态
清末民初时期,“白石仙”的传说发展进入了人格化的阶段。
“白石仙”的人格化与天花坛(又称崇善堂)的倡建有直接的关系,天花坛正是仕荣祖派下的家族精英出于家族的利益所倡建的。罗仲篪为清末民初作树坊罗氏之族长,族谱中有这样的记载:
甲寅岁,天花盛行,先生邀集同人鼎力倡办,坛中各善举也已次第办理,所建仙坛一座,……(注:《柞树坊罗氏十五修族谱·启用房重棣罗公星海先生墓志铭》。)
至民国三年甲寅十月恭奉天极上相孚佑帝君命大开天化敕命本境白石灵王圭石为监政座主,次年乙卯二月择地造化坛为开化地,……(注:《柞树坊罗氏十五修族谱·仕荣祖助建崇善堂志》。)
天花坛于1987年倒塌,据柞树坊村民罗涛琳回忆,天花坛共有三层,第一层安放孔夫子像,第二层为玉皇大帝,第三层为地母娘娘。从天花坛所祀神来看,主要为道教神。所谓孚佑帝君即吕祖吕洞宾,而罗仲篪则为道教弟子。如此看来,白石仙人格化的直接原因是罗仲篪出于为崇善堂设立座主的需要。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罗仲篪为白石灵王撰写的墓志铭把白石仙人格化的原因表达得非常明白,这就是要为“白石仙”创造一个有显赫身份的神仙。至此,白石仙的姓名、生平,葬在何处及其子嗣都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注:详见《柞树坊罗氏十五修族谱·白石灵王墓志铭》。)
如果说罗仲篪为白石灵王撰写墓志铭里的创造只是简单粗略的描述,那么民国八年创造的“白大师行述”则是完成了对白石仙神性的系统创造:
大明嘉靖我初生,虔化县中认旧城,
卜处朱源岭背地,西阳旧族起家声,
父字尊荣母氏孟,好行阴鸷多方便,
积功累德法燕山,自此天心常默眷,
我父登科始发祥,萍乡作宰姓名香,
十年任满归桑梓,猴岭吹笙还上苍,
所生四子予居长,小字万兴蒙上选,
十五游庠初夺魁,二十得中探花榜,
旋迁内阁侍郎官,走马长安人尽欢,
可恨严嵩怀僭窃,桂冠远隐乐盘桓,
居家学得歧黄术,救世功宏难尽述,
不可良相便为医,赤子苍生归抚恤,
贤哉内助李夫人,举案齐眉敬若宾,
俭效马妃常练服,宛然巾帼作针神,
我身不幸家多难,折翼分飞形似燕,
仲氏先亡季被虏,惟余叔子同忧虑,
有子七人慰我心,箕裘克绍守良箴,
半耕半读承先志,清白传家众所钦,
长子不才学稼圃,三男四子营商贾,
五郎夺得锦标归,六七黉宫称博古,
无何饥谨遇天灾,蒿目时艰泪满腮,
只效尧夫当锄麦,稍苏涸鲋罄资财,
凶荒既遇流瘟起,环顾遍氓忧未已,
采药炼丹妙剂成,死中得活全乡里,
家忧国难历何多,君弱臣强损大和,
因此上苍施劫运,下民无辜受灾魔,
崇祯七载天书召,身赴玉楼膺检校,
寿享期颐余二春,英灵化石彰神效,
牧竖鸭夫向我朝,曾将幻术化尘嚣,
至今佳话传千古,宫殿巍峨气象超,
一卷石子争趋拜,讵科历年形渐大,
变化无穷人不晓,小之无内大无小,
数百年来血食登,牺牲供给众钦承,
自从天化大开后,不忍伤生学老僧,
师遇纯阳学一贯,命予监政封天相,
全球善恶掌稽查,受命以来无稍旷,
迄今善举若完全,差幸功圆果亦圆,
一片苦心谁共谅,麟经补缺活连篇,
磨残木笔说干口,沥胆批肝为众剖,
好把前言剖在心,莫忘我这叮咛叟。(注:《柞树坊罗氏十五修族谱·白大师行述》。)
关于这篇行述的来源,族谱中的记载是于民国八年十一月十二日白石仙显灵降于崇善堂(即天花坛)。实际上,它是由罗仲篪撰写的。
3、衍生形态
作为柞树坊罗氏家族庙宇和区域信仰中心的“白石仙”,在改革开放后富东民间信仰复兴的运动中,关于“白石仙”的传说,除了家族与村落流传的传说与家族精英们所创造的神话之外,在村落中有增无减。据说在此之前,富东民间不能为“白石仙”做戏。毛泽东去世后,柞树坊罗氏便开始修庙,恢复每年一度的唱戏酬神活动。在破“四旧”时,原公社人武部长王×带人拆庙,将瓦、树木等搬到公社,不久他便得肝炎去世,当时参与拆除“白石仙”的其他人,其家庭或本人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不同的灾祸。原公社党委书记章某,其母为神婆,他向富东大队书记罗兰荣建议,将庙卖给私人,就没有人敢拆庙了。柞树坊罗氏便将庙卖给前门一罗姓,庙因此得以幸存。不久,章某便升任某县县委组织部长。1996年6月,黄陂罗姓有20多人来向“白石仙”进香,开车的是一个小伙子,不信神,第二天他们要返回时,汽车无论如何也无法启动,朝仙队伍中有一神婆便点香烧纸,向“白石仙”方向唱揖,请求“白石仙”恕罪,汽车果然启动。广昌一老太婆,其媳妇无生养,富东一罗姓到广昌割松油寄住在她家,得知这一事情后告诉她,“白石仙”很灵,可以求他保佑,不久其媳妇果真生了一个儿子。
三、传说与民众生活世界
1、神庙创建与家族认同
“白石仙”神迹的原生形态,实际上与柞树坊罗氏的家族独立运动和家族认同有密切的联系。柞树罗氏、前门罗氏和塘角罗氏实际上是同一个开基祖发展下来的。据《富东柞树罗氏十三修族谱》载,其开基祖为三十八世祖重三郎,名权,大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丙子七月初十日午时生。从权公开始,罗姓便从前门而柞树坊,至和里,发展成为富东乃至宁都北部的一个著姓。权公定居前门后不久,到四十三世祖元杰生有四个儿子,家庭便开始了析分乃至迁徙的过程。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以前柞树罗氏和前门罗氏还存在着血缘和仪式上的认同。从康熙三十二年柞树罗氏开始独立修谱以来,前门罗氏和柞树罗氏开始走上了家族独立发展的道路。此时,柞树坊罗氏的人口已经发展到了近千人,而且分成了兴大、兴和、兴作三房,并且为“开基祖”仕荣祖以及三位支房建造了祠堂,家族有了祭祀和仪式的中心。
正是在这一段时期,柞树坊罗氏家族集资建庙,为白石建一庙宇。《宁都直隶州志》卷30有载:“白石仙,太平乡十三都富东。顺治中罗仕荣建,置田,永赡香灯。”另外,据《柞树坊罗氏白石仙〈青山寺〉暨白石大仙传志》记载,“柞树坊罗仕荣祖位下裔孙,集资建庙,于清顺治三年把简陋的茅房改为普通的白石庙,清乾隆二十年在各方信士的援助下,又建起一座三宝殿。”直至现在,每年的清明节,柞树罗氏都组织族人前往东韶的南团醮地,祭拜白石仙和仕荣祖。
再从富东罗氏近年的修谱情况来看,有可能从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发现神庙创建与家族独立之间的关系。1995年,柞树罗氏和前门罗氏都续修了族谱。鉴于富东罗李二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罗氏有人提议柞树罗氏和前门罗氏联修族谱,希望通过联修族谱,强化富东罗氏的“一家人”意识,凝聚罗氏的力量,共同对抗外界,维护家族的利益。但是有人提出异议,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柞树罗氏在每年的八月都要为“白石仙”举行斋会,为柞树罗氏带来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收入。一旦族谱联修,意味着仪式的共享,势必会使柞树罗氏损失一部分经济利益,联修族谱的计划未果。富东罗氏因此失去了再次重新联合的机会。
实际上,富东各个家族都各自有其长期以来形成的家族庙宇认同。庙的创建为各个家族在祠堂之外,又确立了一个家族认同的象征。
2、神的人格化与庙会制度化
家族的士绅可以说为民众创造了一个具备忠臣、隐士、救世主形象的神明。白圭石可以说是比较典型地符合儒家传统的士大夫形象。神的人格化过程为神庙信仰提供了正统文化的支持。富东民间关于“白石仙”的神庙信仰可以说是结合了民间自有的地方性文化资源而最终形成的区域性信仰崇拜。
首先,民间赋予“白石仙”神奇灵验,能够化解民间的诸多苦难,民众向“白石仙”祈祷、祭拜能够满足自身的需求,从而被民间加以神化;其次,民间精英完成了对“白石仙”的人格化与神圣化过程,罗仲篪以家族族长的身分,有其固有的文化优势,作为民间精英阶层的一分子,自然掌握着比其他家族成员更多的社会和文化资源,他在这一场造神运动中,充当着民间文化诠释者的身份,依靠其在家族中的权威、地位和声望,创造了家族信仰神明的一系列神迹;再次,由于天花坛的建造,富东民间为各路神祗建构了一个体系,也就意味为社区的神祗体系作了一次安排。在民国三年,“白石仙”被天极上相孚佑帝君敕命为监政座主,稽查人间善恶,正式地纳入到天花坛的道教神仙体系中。
所以,一方面,神庙祭祀仪式具有巫术性质、偏重于人与神之间交流沟通;另一方面,受国家正统思想影响的家族精英,希望建立村落的信仰和道德秩序,两者之间达到了巧妙的结合。地方精英对乡土神祗有意识地摒弃其“朴野”、巫术性的一面,极力对自己社区中的乡土性神明进行帝国化的模仿,使其正统化。在家族精英看来,毫无系统的、带有明显巫术意义的民间信仰难以确立其正统的地位,因为“外神之祭,非士庶所有”,(注:《宁都直隶州志》卷11。)只要有机会,便有可能对其进行改造,削弱其“朴野”的一面。然而,家族精英将“白石仙”纳入到社区神祗体系之中,其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削弱其“朴野”的成分,更重要的是,将其纳入至家族精英安排的社区神祗的等级体系中。“社区神祗与国家神祗、官方宗教间接相关,它是传播正统思想的一条重要途径。”(注: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12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而在这一过程中,正如杨庆堃所说:在宗教意识上,士大夫和普通大众之间有一个稳定的交融。(注:C.K.Yang,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A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Functionsof Religion and Someof Thei-rHistorical Factor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267.)也就是说,家族精英包括那些未取得功名的乡绅等受儒教正统思想影响深刻的人,对民间的宗教生活的正统化和等级化产生影响。
但是,“白石仙”从“朴野”的泛灵崇拜到人格化的完成,也不仅仅只是对帝国官僚体系的简单的模仿。这一过程的完成,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民间神明崇拜与村落文化的结合,家族精英充分地利用了地方性资源与国家资源确立家族神明的正统地位。天花坛是由富东罗李两姓在罗仲篪的主持下建造的,前门罗氏的“新华山”与李氏的“明华山”并不具备如“白石仙”那样的条件,因为它们一开始就是作为佛教的庵堂而设立的家族庙宇,并非属于神庙,它无须完成纳入到官方承认的三教体系之中的过程,而不至于被官方视为“淫妃”之类。实际上,据老人回忆,“白石仙”的香火历来都比“新华山”和“明华山”旺盛。在民国时期,富东民间大量的放养鱼苗,村民希望“白石仙”保佑他们的鱼塘不为洪水冲决,鱼苗不为强盗所掠,能卖好价钱,使白石仙成为宁都北部的主要神明,声名远扬,播及临近的于都、会昌、广昌、兴国等地。他们对“白石仙”的许诺与酬谢都特别慷慨,每年的“白石仙”神诞日所举行的迎神赛会为柞树坊罗氏带来相当大的经济收入,客观上为“白石仙”人格化过程的完成提出了要求。同时,“白石仙”的人格化过程的完成也是家族争夺村落信仰空间的需要。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为了巩固家族在村落和区域中的社会地位、政治、经济的实力固然是首要的,然而在相当意义上,利用宗教信仰的力量也是必须的,其目的无非是借助神的力量维护家族的安全、利益,维系家族内部的团结,扩大家族在村落和区域中的影响。
另外,“神庙要成为民众信仰的文化中心,最少应该具有两种文化功能,即神圣功能和教化功能。”(注:郑志明《台湾神庙的信仰文化初论——神庙发展的危机与转机》,《寺庙与民间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汉学研究中心。)在村民看来,白石仙并不缺乏超自然的神灵力量,但是由于其来历不明,其神性无法为村民所认识,因此,家族精英试图通过为其建构人格化的神性而对村民具有道德的感召力,“行述”中为村民塑的是一位符合儒家思想的人物形象。然而,由于其神迹人为创造的时间并不远久,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迷信”的禁锢无疑遏制了“白石仙”神迹的传播。但是,村民对神的信仰更多的关注于神是否灵验,能否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苦难,能否满足村民的乞求,相对来说,神的出身和具有道德教化作用并不十分重要。
作为神庙的“白石仙”,其之所以能够成为村落和区域中民众的信仰中心,不仅仅是因为其具有村民所信服的神奇灵验,也是因为信仰中心的确立,是一个与家族、村落、区域文化互动的过程。
“白石仙”人格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家族与神之间互动的结束,而是标志着家族与神之间的互动更为深刻、更为制度化,其中更多的体现家族在利益上的统一。家族的利益,一是白石仙的灵验为罗仕荣派下族众带来的是家族的经济利益以及在村落中文化资源的占有上所处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是通过家族神明之神话的创造凝聚家族的力量。在罗仲篪为白石仙撰写的另一篇“白石大仙传”里,记载了柞树坊罗氏家族完成了“白石仙”庙会的制度化过程:
(白圭石)化石在罗氏柞树坊显为神圣,因此白石庙所在地永远是罗氏柞树坊处敬处礼子姓所有……于是仕荣祖子姓集资为其立庙装塑其金像,并每年六月间批唱神戏一月,以报鸿庥。各方信士前来朝谒完愿者络绎不绝。所助戏捐,缴销戏价及开支外,如有剩余,均已立众,为常年醮祭香火及修整庙宇之用。现已买获田租数百担,其众以八房进出均共有份,轮流管理,或推公正廉明辈亦可。八房轮管即兴太、育逊、育顺、兴作、育政、育治六房是也,其余仕、锦、华、苑四柱合为一房,民、贵、璋三柱合为一房,为此敬祖子姓占三分之二,处礼祖子姓占三分之一也。(注:《柞树坊罗氏十五修族谱·白石大仙传》。)
3、传说的衍生与庙会的复兴
1988年,柞树坊罗氏家族恢复了中断三十多年的“白石仙”庙会活动。“白石仙”斋会一年一届,演戏酬神活动原先是在每年的农历六月间举行,从1989年开始改为农历八月间举行,每隔十年还将为“白石仙”塑一次金身,为其举行开光仪式。在其他年份,则一般举行庙会,时间15-30天不等,视捐写乐助的情况而定,因为求神还愿的为多生子、考学、祛病之类。传统时期,多请湖南的戏班来演唱,村民称之为“演大戏”;现在则请附近的广昌、宁都和兴国等地的戏团。演出的剧目有《满堂福》、《珍珠塔》、《红绫袄》、《结彩楼》,多表现喜庆团圆、多子多福、高中榜首等内容,演唱时间每晚二、三个小时,观戏者远至赣州、广昌、兴国、瑞金、石城、于都等地。在庙会期间,卖有各种食品,香烛、纸钱等,传统时期,庙会期间还有富东的流浪头子开设的赌场。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神在柞树坊罗氏家族的家族认同与凝聚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每年清明节举行的家族集体醮祭中,人们对醮祭白石仙的重视程度要大于对仕荣祖坟茔的醮祭(注:据罗涛琳介绍,每年清明到东韶醮地的柞树坊族众是以祭扫白圭石之墓为主。)。清明节举行的祭祖醮地仪式,罗仕荣派下所有族众均到东韶的南团醮祭罗仕荣和白石仙的坟墓,而最主要的醮祭对象已经是“白石仙”而非罗仕荣,此时,罗仕荣更多的是作为一群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人群自我认同的象征,每年神诞日举行的迎神赛会则已经成为富东民间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当代,柞树坊罗氏更多的表现为以罗仕荣为象征的血缘群体,进而在神的力量维系下实现家族最大程度的凝聚。
这一现象,笔者以为涉及了神、祖先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村民看来,虽然同一祖先的族众之间在血缘上是平等的,但是由于家族内部力量的不平稳,民间总是以为祖宗对某一房份特别关照,而忽略对另外一些房份的庇荫,甚至根本就未能给某些房份带来一点利益,这种观念明显地反映在村民关于祖先风水的理解上。村民认为:兴仁房的人丁不旺,有两个原因,一是造谱,另一个就是处敬的坟茔风水只照顾老三,因为兴和房的人丁最多,而且势力也大。神则不同,只要村民信它,经常向它敬奉,为的是得到神的同情和帮助,而且还可以向神讨价还价,在村民看来,神对于每一个虔诚信仰它,并且经常贿赂它的人都一视同仁;而人们与祖先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作为继承人和后代的义务。”(注:Arthur P.Wolf,"Gods,Ghosts,and Ancestors",Study InChinese Society,Arthur P.Wolfe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160)另外一个原因是,村民认为家族的祖先对后代的庇护并不总是具有威力,富东村民认为一个风水至多只能管三至四代,而神则具有更大的威力。
再一个原因是:祖先的威力只有家族效应,而神的威力则有社区效应。祖先崇拜只能为本家族的成员带来庇荫,对于在同一个村落的其他家族来说,某一家族的祖先崇拜只是区别不同家族的一个仪式与象征而已;而神则不同,尽管神有区域与家族的所有之区别,但是,“天下菩萨天下敬”,只有该神有灵,谁都可以来参拜,谁都可以向它企求帮助。家族所有的神在区域中所具有的声誉,给家庭带来的不仅是家族神明的香火旺盛,家族的公益事业具有一定的经济支持,更重要的是使家族在一定区域文化资源的占有上具有支配的地位。柞树坊罗氏家族每年一度的迎神赛会,以及六月的白石公公生日,与之具有经济联系和婚姻联系的远近不同的其他家族都来加入到柞树坊罗氏家族的仪式庆典之中,在一定区域中为民间文化娱乐的所作的安排与调节因此也抹上了浓郁的炫耀家族力量的色彩。
村民对于作为神庙的“白石仙”之态度,大多关切的是神明能否满足自己的要求,能否保佑自己以及家人的平安和福寿。民间对神明的出身并不太注意,注意的是神明是否灵验,灵验与否是决定神庙香火是否旺盛的主要原因。因此,柞树坊家族成员向外来人介绍关于“白石仙”的情况时,总是极力渲染其家族神明多么灵验,几乎有求必应。而他们只有遇到某些非自己能力所能把握的现实时候,他们才可能会向“白石仙”许愿,乞求神的帮助,向神讨价还价。据“白石仙”主持的介绍,每年十月份举行迎神赛会时还愿的主要有生子、升学、发财、祛病消灾等,其中主要以前两者为最,这与富东的经济形态基本上是传统的农耕经济有关,村民关注的仍然是传统的光宗耀祖和传宗接代。两者的还愿明显的具有竞赛与炫耀的意识,家族意义体现得非常重要,在演戏中,人们关注的是哪一姓、哪一族、哪一房的信士许愿了多少本戏,在电视等传播媒体几乎普及富东乡间的今天,人们对于演唱的内容等兴趣并不很大,需要的是那种特殊情景下的狂欢氛围。因此,村民的许愿和还愿的仪式所维系的是“白石仙”的灵验性格,神庙的信仰也就成了一种巫术化的金钱游戏。从这一角度理解,许愿是人与神之间的个体性交易,人只须向神许诺一定的财物,便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而每年的迎神赛会则是集体性的还愿行为,人们举行仪式的同时,神明的力量得到了认同和肯定,在人与神明的交易过程中,神明的灵验当成了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商品,人与神明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缺乏神圣意义,逐渐成为一种交换行为,而这种交换行为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之上。
因此,民间关于“白石仙”神迹的种种传说,与世俗性的神庙信仰是相契合的。人们关注的是神的灵验,包括神对人们许愿的保佑和对人们不恭的惩罚。所以,“白石仙”的传说进入了一个体系萎缩的时代,但以“白石仙”为中心的各种神迹的衍生却极其繁盛,在日益功利的乡间广为传场。
四、结语
“白石仙”的传说经历了原生形态、人格化形态和衍生形态的发展过程。原生形态体现了民间原创的原汁原味,全然是底层民俗的观念表现,传说的播布过程实际上是民间赋予白石神性的过程;白石神性的确立,为庙宇的创建提供了民间的观念支持,进而成为家族认同的另外一个象征。人格化形态的完成,实际上是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互动的过程,互动的中介是民间的精英分子,他们将民间的原创形态与地方的文化资源以及对正统儒家观念的理解巧妙地结合起来,为社区塑了一个符合正统观念、能够满足民众需求的神的形象,“白石仙”的人格化使家族在村落和区域的文化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庙会的制度化为家族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在村落和区域中所具有的家族实力。改革之后的时代发展,庙会的复兴,民间的功利需求,民众发展了“白石仙”的神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民间传说的活态发展与民众对传统的再造之间的传承。“白石仙”传说的活态发展与民众生活之间的关系,真实地体现了民众对民俗的创造、传承和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