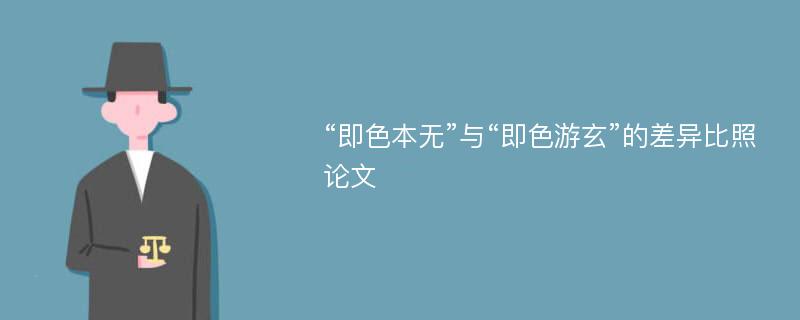
【文化哲学】
“即色本无”与“即色游玄”的差异比照
刘真睿
摘 要 本文的分析对象是魏晋后期佛教初传的本土化产物,即“六家七宗”中的支遁即色宗。理解即色宗倡导的特定概念“即色”时,难免会涉及对“即色本无”与“即色游玄”的解读。以此视角来考察“即色”会发现,在“性空”理论的内部中支遁(道林)即色宗的“即色”概念往往表现出差异性。事实上,“即色本无”即是从作为客体存在的共同特征(“色之为色”的共有属性)来辨究“本无”与“即色”的抽象关系;“即色游玄”则相比“本无”更加侧重其之于“即色”的形象关系,即本文所论述的审美特质。这种差异性虽然影响到了对“即色”本义的中性理解,但也正由于这种差异的比照,才使得我们不断将“即色”推向对其属性问题(共有与个体、抽象与形象)的探讨上,如此方能真正达成对即色宗特定的“即色”概念的进一步认识。
关键词 即色本无;即色游玄;即色;必要主体;属性问题
一、即色宗之所谓“即色”概念
东晋僧肇[1]在其《不真空论》中对时下“六家七宗”(1) “六家七宗”提法主要出自南朝宋庄严寺僧昙济所著《六家七宗论》以及东晋僧肇所著《肇论·不真空论》,其中对罗什来华前的中国本土佛教思想的概况有过总结,即“本无宗”、“本无异宗”(“本无”之支派)、“心无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缘会宗”七宗。此七宗都各自或直接或婉曲地对《放光经》等早期传译经书中所体现的佛教般若思想加以义理上的阐释,从而从各具特色的思考角度出发以形成各自的派别。僧肇在《肇论》中只对本无、心无、即色三宗进行了批判,此后南朝陈僧人慧达所作《肇论序》及唐代元康所著的《肇论疏》也接续此论断,可见此三宗是具有七家的典型性与代表性的。 之支遁“即色宗”本义有过如下批评:“‘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虽色而非色也。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
通过僧肇对“即色宗”之“即色”义的描述可以知道,其本义是“色不自色,虽色而非色”的,旨在说明“色”(客观事物及所产生的现象)不能自我生成,是需要借助主观力量实现的,所以现存的能感知到的“色”并非真正是其本身。对于此点,僧肇则认为即色宗所言之“色”是单方面的,是孤立的。其并没有认识到“色”本就是“非色”(空),“色”在根本上也是“假有”(2) 关于僧肇“假有”概念的提出与阐释,详见其《肇论》中的《不真空论》与《般若无知论》。僧肇认为,如果现实事物“真有”,那么将永无消亡之时,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故现实事物“假有”,也始终保持其自身“假有态”,即“如其真有,有则无灭”。而又因万物皆“缘会而生,缘离则灭”,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所以,在认识论层面上,我们应该承认客体的“假有”属性。 的。故当然可以“非色”,而并不是某种主体的赋予结果。即色宗之“色”“直语色不自色”,而未能发觉“色”的“非色”一面(属性)。
这里,僧肇对即色宗的批判自然是导源于其空观思想的,是在承认事物“假有”,即“色本是非色”事实的基础上来对“色”概念进行认识的。当然,此处我们说这种“非色”不应作“色”的简单对立面去分别“色”,而应归属于“色”的范畴整体之中,并作为其自身的条件性存在而存在。从僧肇处,我们是务必要去空“色”的,不能就“色”谈“色”,否则就是犯了“待色色而后为色”的弊病。但问题是,倘使“即色”范畴成立,也就是说“色”是可以“即”的话,再将即色宗之“即色”置于僧肇所谓“色空”处加以分析,就必然会消解其“即”意之于“色”意的概念主导性,而这或许恰恰才是把握即色宗之“即色”范畴的关键所在。吕澄[2]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评析道:“僧肇批评支道林的片面,仅仅是因为他从认识论上论证空性,没有配合缘起法来理解吗?事实上,支道林是否只有这样表面上的缺点,还是值得研究的。”基于此点,我们把握“即色”含义时就有必要先行对“即色本无”加以辨究了。
又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虽然确诊是牙了,但却由于时间过长,息肉几乎已经把牙包住了,怎么也拿不出来,最终,段主任决定放弃手术。就在那一刹,我和老婆顿觉坠入了冰窖里。
赣南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原中央苏区核心区,是全国较大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贫困范围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十二五”期间,江西省赣州市仍有11个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其中8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932个贫困村、70.24万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人口均占全省的1/3左右,贫困发生率达9.3%,为全国的1.63倍,因病因残致贫比例合计达53.7%,是全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实然,“即色”之空是“虽色而空”(慧达《肇论疏》语)的,且“即色”也因无法“自色”而终致其“空化”。这种“空化”实质上是有别于般若之性空的,乃是“色之性”使然,是在强调“空”的属性特征而不在“究其本”,故石峻[5]先生称其所谓“现象上说‘空’(无)的名‘即色空’”。并且这种旨在说明“物无”的“即色”,实际上是对客观现象中所体现出的“空性”(作为空的属性,非“性空”)在加以着“色”,使之“以色性是空为空,色体是有为有”[6]。进而在支遁的逻辑范畴内,僧肇的色之为色的“假有”本质是不能确证“色”作为非本质一面(“色不自色”)的存在的,即从个体角度的现象存在是难以推出共性本质的“事实存在”的。后者是本体意义的,所以其所得结论具有“事实性”;前者则是属性意义(后文将以此为审美特质)的,所以所得结论只能停留在“空化”(即色本无或即色空)阶段而终究入不了真“空”(“空无”或性空),因为没有“色色”者即不可“自色”。也就是说,“即色”的存在是以色无法自色为前提的。如令色存,则必先令其“真有”;而如何令其“真有”,就须取决于“色”成立所不可或缺的“必要主体”的绝对作用了。
《大乘起信论》有云:“毕竟无得,亦无色相可见。而有见色相者,唯是随染业幻所作,非是智色不空之性,以智相无可见故。言异相者,如种种瓦器,各各不同。”[13]
汤用彤[3]先生在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对即色宗之“即色本无”义有过表述:“支法师即色空理,盖为《般若》‘本无’下一注解,以即色证明其本无之旨。盖支公宗旨所在,固为本无也。”由此可知,支遁即色宗是旨在辨究般若的空义的;且即便是“即色”的存在保有目的性,也是首要服务于“本无”(3) “本无”在魏晋时期,即罗什来华传译大乘佛义前,是一种对印度佛学般若性空(大智)的中国化表述,罗什后称译为“真如”。另外,此“本无”在对“性空”的范畴探讨中是不能等同于正始玄学之“贵无”的,因为王弼的“贵无”更侧重于“无”的本(位),重在“无”的本体论;而佛教性空观中之“本无”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范畴,强调“空”的“本无”属性。 的。故而在支遁处,引述“即色”只是为了说明以至证明“本无”的“事实存在”。如同慧达所言:“所谓色不自色者,即明一切诸法无有自性。”[4]且这种“无有其自体”的“色”由于是因缘假有的施事对象,即获得了色之为色的“空、无”本性。经过上述论断可以发现,支遁的“即色”显然是一种孤立“色”,是始终不能缺少某一“主体”的“必要参与”的,甚至是主导,只能停留在个体层(“色即为空,色复异空”)而不能成为色之为色的“共有”事实(即“色空”),这样的“即色”是需要“待色色而后为色”的。而为了探寻某种“真有”空,经由“即色”作用之后的空就势必不可为“假有空”,而只能是“色不自有”的假象结果;因不能证其“真有”(事实)属性,故这种“即色”之空也将永远成为色本身的一种抽象存在,“假有空”也将被理解为是色之为色的共有属性必然所致,故由此色所得出的空义就会不可避免地脱离其本体问题而投向某种有关空(“本无”)的属性问题之上,即将“色”不断推至与空的“事实存在”相被动的假象存在当中。
二、“即色”得以成立的主体必要性
“夫至人也,览通群妙,凝神玄冥。灵虚响应,感通无方。神何动哉?以之不动,故应变无穷。”[8]支遁所表述之“至人”显然是受时下玄学思潮的深入影响的,当然其本人本就甚爱“玄谈妙美,养马放鹤,优游山水”[9],颇具玄士之风。但究此本义,恐是在为“即色”得以成立寻求一“不动”之“因”,即“至人”(“神”)之使然。而至于“至人”得以成为“即色”之“因”,则应在于支遁意图用以解空,即“固为本无”[10]。前文已论支遁的“本无”有别于“空无”(“性空”),实乃一种“即色本无”(“即色空”),所以这种“即色本无”不像“性空无”可以“假有”,可以“事实存在”;相反,其必须经由“至人”的绝对作用,经由“情所计”,方可得以成立。“至人”之于这种“不可自色之色”则被突出表现为一种“必要主体”之于受造物之状,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恐怕支遁之所以立一“至人”形象,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更好地解释“色不自色”之缘由,使其呈现具象化态势。吕澄[11]先生也谈到:“支遁所说的色,是指‘共相’的认识,是指与非色相区别的‘共相’,而不是指色的‘自相’。”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样的结果便会使得“色”即便在范畴层面,也将只获得共性而失掉个性,并且在对“即色本无”的进一步诠释当中显得尤为被动与不完整。至于“本无”的空性,也不再是独立的“性空”,只可依附于某种“必要主体”的介入(绝对作用)上,以成其为所谓“即色本空”[12]。
也正因由“至人”作为“必要主体”(“必要主体”从认识论意义上也是一种个体存在,此点后文有涉及)的赋予,才使得“虽色”(没有主体化过的“色”)能成为“自色之色”。而这种“自色之色”已然不再“非色”,是为“大种所造之色”,为“情所计之色”。如若我们可以将此“情”同作“即色本无”来理解,那么如其所计而出的“色”是否又有着相对于“本无”之“色”所不同的“色”的表征?前文提到,支遁所论之“即色”是认识论意义的,且并非“空之色”,只是“色不自色”,是一种“空化”的体现。而“即色”目的终究在于解空,“即色本无”作为一种共性范畴(一般性),也始终需要由“必要主体”(可为“至人”亦可为“大种”)所赋予成立。这种“即色”显然是不足以完满回应“本无”作为其共有属性的个体存在“事实”的,所以就必然需要将“即色”尽可能地玄化以致审美化,进而弥补个体表达的不足,即让“即色游玄”的形象属性来自然审美化“即色本无”的抽象属性,从而让“即色”在属性角度上真正达到解空的目的。在“必要主体”的必然赋予下,“游玄”的出现则将“本无”作为“即色”的共有属性一面带有了可审美的特质。而“即色”审美特质的被发觉,也正是“如情所计”、为“大种所造”后的“色”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那么,这种“即色”既不可“自色”却已然“成色”的产生缘由究竟为何?熊十力[7]先生在其《佛家名相通释》中对色义有如此说明:“色者何?《论》云谓四大种(亦称大种),及四大种所造(省称造色),皆名为色。……如情所计,应是大种先起,造色后依之而生。称理不谈,则造色为宇宙灵窍开启,大种之成,正为造色,不得谓大种现起以后,造色乃偶然发生也。是恶可妄计先后耶?……总之,说大种为造色之因者,只明物界乃相依相缘而有,不可于此纷纷起执而更求其生起之时序。”
第二种方法是做点手脚,在Photoshop中使用动感模糊工具。这张照片我们用的是第二种方法,然后给画面右侧的小码头制造出明显的重影效果,这样多少可以让人认出拍摄地。最后的效果看起来相当不错。
“色”是被造的。而何者造“色”?“大种”所造。“大种”为何?可为宇宙灵窍开启所致,亦可专为“造色”而起、而成。在这里,对于“大种”的理解就大有模糊之势了。若说其先起,则先不过“宇宙灵窍”;若称其为后,则“造色”行为实非偶然。尤其在“情所计”的基础上,“大种”之于“造色”显然已经不能简单地次序化了。但应当承认的是,除却先后之别,“大种”的产生实质上是存在目的性的,即是为了“造色”,这一点在“因缘”处也会得到证明。这样一来不难看出,“色”是可以“如情所计”的,这种“情化”后的“色”(“大种”无先后地、非偶然地所造之色)则同支遁即色宗之“即色”似有不谋之和。“大种之成,正为造色”,“情计”之“大种”对于“色”本身来说,是“因”,是其发生之所“依”。这种必然需要的根本主体,则或许在支遁《大小品对比要钞序》之中被描述为了某种理想之“至人”形象。
三、对“即色游玄”问题的思考
离开医院时,英突然想到入院时离去的那个病人。她被推出病房那一刻,深深地停留在英的脑海里,成为挥之不去的画面。在亲人号啕大哭之际,她终将化为灰烬,与大地融为一体,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必然的归宿吗?但是,英一点都不觉得悲伤,也不感到丝毫害怕,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英,对死亡不再畏惧。
《大乘起信论》从“色自在”的角度认为“色相”是无可见的。因其“无得”,故无可见的“色相”也是所谓“智色”的空性的结果呈现。但问题是,为何又会出现“有见”的“事实存在”?这里对“色”本身而言,就开始有了“智色之色”(色共性)与“异相之色”[14](色个体)之别了。确切地说,是“色”在本质与现象、共有属性(共相)与个体属性(殊相)方面产生了“分别”,才致使原同之瓦器各为不同。将“智色”推至“本无”,则“智色之相”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理解成“即色本无”的“事实存在”了。可这样一来,即便是“智色”也会产生“可见”情况,所以对于“即色”来讲,就更需要一种与之对应的“异色”(支遁所谓本无之色的差别状态)了。其通过形容“本无”作为“即色”共有本质的个体(自有)属性、具象属性,从而使“即色之色”本身得到完全。“游玄”的提出恐即在这种需要下被支遁予以呈现。
“支道林著《即色游玄论》云,夫色之性,色不自色。不自,虽色而空。如知不自知,虽知而寂也。”[15]在支遁处,“色”之为空乃在于其“不自”之性。在认识上,我们始终也无法获得“真知”,这样的结果会模糊化我们对“即色本空”(色的共有属性)的有效理解,所以就必须要解决“色”“不自”的“性因”问题(色的个体属性),即“即色游玄”之于“即色本无”的关系存在。通过前文所论可以知道,在“即色本无”的角度上,对“色”的理解是多元的。一方面“色”有其共性,皆“本无”;另一方面,“色”的个体属性也允许其存有差异(“色复异空”),并能逾“空”之外得以留存。而按吕澄先生说法,认识上的色既是非色、假象、空,也就这样来说空之外还有色,即由色的概念而成其为色。故这种“逾外”的“不自色”则必须卸去色之为色的“空性”特征(共有属性),并被置于某种个体存在(即所谓“必要主体”或其他对于“色”而言的个体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色”本身)的差异性之中,才能使“本无”得以“即色”。而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显然将证明“游玄”之于“即色”的属性化的成立,也是“即色”之“未与佛同”的一面。那么,支遁所谓的“游玄之色”在“色”的个体属性上又有着怎样的表现?且又因何这种“游玄之色”于空之外可以“未与佛同”[16]?
《世说新语·文学篇注》有载支遁《逍遥论》:“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17]支遁已然借助对庄子“逍遥”的个人发挥来为其“游玄”之义作以说明。这里的“逍遥”在支遁处,明显是可以代表“至人”形象(所谓“必要主体”)的。具体来说,如何达成“逍遥”?支遁认为,须“至足”,而不可“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如何达成“至足”?则由“至人”“放浪、高兴”的结果产生。而为何这里的“逍遥”是可“不疾而速”的?是因为“玄感”的“不为”。这种“不为之玄感”所体现出的“至人”个性(作为“至人”的个体属性)当然是有别于“天真”(一般“所足”的共有属性)的。其在“色色”的同时在令“色”本身不断玄化、形象化、审美化,以配合回应“即色”的空性、“本无”性以及其共有本质的属性要求,而在这点上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支道林之即色游玄义,与道安之本性空义无异”[18]。“游玄”的属性化来源过程即“‘必要主体’(“色色”)→即色(本无)—(属性化或审美化)→‘游玄’”。
也正因其“不为”,“游玄”的个体属性之于“即色”,才愈发显露其审美特质。也只有通过揭示“即色游玄”的审美特质(即对色的抽象共性予以适当消解)一面,才能补足“即色本无”的“所足”,进而使之“至足”,达成逍遥。故汤用彤[19]先生才称此“无”乃是“亦无心忘怀,逍遥至足,如支氏所写之至人之心”。而通过“游玄”这一审美特质的生发,也在认识论意义上将“本无”与“即色”联系得更为紧密;同时,在属性角度,也将“即色”的共有属性与其个体属性作以差别,从而使得“即色”得以从“本无”中自然分化出“游玄”;而“游玄”作为“即色”的一种个体属性存在,也让“本无”得到了审美化,进而“逍遥”、解空。而这又何尝不是在“关系”中显现出一种“倒流”(4) 此处“倒流”含义详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季羡林著《季羡林全集》:卷15第336页。 之态?这样来看,支遁即色宗的“游玄”问题,实质上则是“即色”如何能够真正实现“本无”的属性问题。
参考文献
[1]僧肇.肇论校释[M].张春波,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40.
[2][11]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M].北京:中华书局,1979.51.51.
[3][4][8][9][15][1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81.180.181.125.180.181.
[5]石峻.石峻文存[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80.
[6]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增订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84.
[7]熊十力.佛家名相通释[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7.
[10]方立天.方立天文集·第5卷: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06.
[12]谢无量.佛学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13.
[13]大乘起信论校释[M].真谛,译.高振农,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52.
[14]欧阳渐.欧阳渐内学集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413.
[16]僧祐.弘明集校笺[M].李小荣,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64.
[17]刘义庆.世说新语[M].刘孝标,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5.
[18]黄忏华.中国佛教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58.
中图分类号 B9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7725( 2019) 12-0057-05
作者简介 刘真睿(1992-),男,内蒙古赤峰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主要从事中国美学研究。
【责任编辑:周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