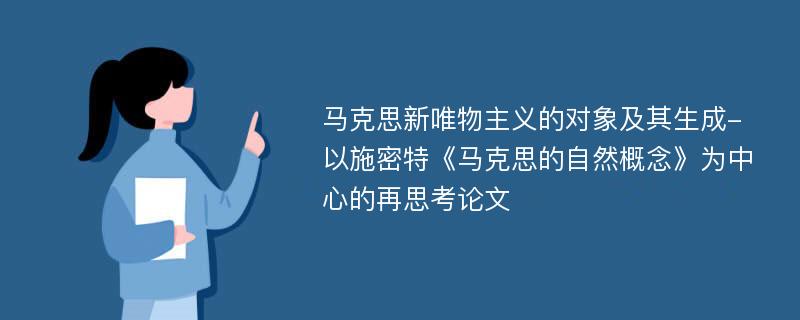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对象及其生成
——以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为中心的再思考
王玉珏
[摘 要] 在施密特看来,理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哲学唯物主义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为了凸显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前提,施密特必将清理历史上的一般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贡献,这其中法国启蒙主义所包含的唯物主义思想、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直观唯物主义)都对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不同于以往各种唯物主义的地方在于其对象的非本体论性质,即对象的历史实践中介性。在阐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关系时,施密特援引了“社会”、“实践”、“社会实践的具体性”以及“劳动的必然性”、“社会劳动的各种形式”等概念范畴,在向我们展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真正对象是如何生成的同时,进一步将理论视野导向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似自然性”问题的分析,从而揭示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意义与革命旨趣。
[关键词] 新唯物主义;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似自然性”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左翼代表,施密特在其博士论文《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与自然双向互为中介的思想。遗憾的是,由于施密特相关文本所依据的思想背景较为复杂,而国内对其主要的文献基础——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有关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发展逐渐遭遇其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发展瓶颈,生态与自然的问题日渐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生态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流派也应运而生。并且,生态文明已是新时代中国道路实践与理论发展的重要维度。在这样的情境下,以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为中心,重新审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逻辑及其对于自然与生态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不失为一种新的理论需求。
诚如该书的标题所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施密特所要重点论述的主题。该书在梳理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过程中,施密特实际上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开战,他既不愿意像卢卡奇那样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完全社会历史化,进而消解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唯物主义前提;也不愿意遵循传统唯物主义的旧路,对唯心主义的命题进行简单的颠倒,或将自然与历史二元对立,或将历史划归为自然的历史,以至遮蔽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人化自然与历史自然的问题,进而陷于物质与精神到底谁是第一性的形而上学式的探讨思路,最终窒息了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实践的历史性、具体性和革命性的灵魂。就后者而言,立足于马克思成熟时期经济研究硕果的研究平台上的施密特,已经深刻的意识到,面对资本主义的复杂社会机体,构成马克思视野中的真正的理论对象绝不是简单的物质第一性问题,而是更为复杂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似自然性”问题。关于这一层,受其理论对象所限,马克思之前的各种唯物主义包括机械唯物主义和哲学唯物主义无论如何是看不到的。
一、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哲学唯物主义的关系
在施密特看来,理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哲学唯物主义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他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开篇即在脚注里批判了第二国际主要的理论家对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忽视或误读。施密特认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的解释者之所以不能全面理解马克思,是因“不理解哲学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所致”。[1]5他指出,梅林等人效仿新康德学派的方式,把马克思思想中的自然与历史二分了,视为构成马克思理论的两个组成部分,即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部分和关于社会的历史科学部分。而新近的许多相关研究也仍然坚持着将自然的理论和历史的理论分离开来的做法。[1]5施密特不满于以往的研究仅从讨论域的差异来仅仅关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各种唯物主义的质的区别。在施密特看来,他们无疑都忽视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古代唯物主义之间的共性。[1]6因而,在施密特的分析思路中,他为了避免将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命题等同起来,他不得不强调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前提,并将清理历史上的一般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贡献视为己任。由此开启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寻根之旅。细细探究,施密特实际上是在一般哲学认识论层面上探究这个问题的,因而,在一般唯物主义中挖掘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唯物前提是否必要以及是否合理,仍是值得细细推敲的问题。无论如何,施密特至少为我们呈现了唯物主义的家族共性,并以时间为线索,以理论对象和表述形式为区分标准,描绘了唯物主义的家谱。这其中,法国启蒙主义所包含的唯物主义思想、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直观唯物主义)都对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对称小四极法:在露头、探槽或坑道的岩矿石表面上,采用对称小四极装置测定自然条件下的电阻率和极化率,供电电极和测量电极要采用不极化电极。
施密特首先指出,“认为决定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因素乃是人类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方式这理论,是以哲学唯物主义为前提的。”[1]6对此,施密特主要援引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的有关论述加以论证。施密特援引马克思对法国启蒙主义者以及他们所孕育的空想社会主义内部各派别的评价,指出在《神圣家族》中,唯物主义被明确地视为“现实的人道主义的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2]167-168此外,施密特还注意到了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自然唯物主义的肯定性评价。在该书中,马克思认为自然唯物主义是构成一个正确的社会理论的潜在前提。[2]191据此施密特指出,马克思在此不仅仅批判黑格尔左派错误的唯心史观,而且试图揭示出该唯心史观产生的机制:“把思维同感觉、灵魂同肉体分开来,是不能把握文化内容和物质生产领域间的联系的。”[1]8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密特还特别肯定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论调帮助马克思形成了其历史理论的“基础”,并且对唯物辩证法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1]8-9“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并不是以原子的机械运动为课题,而是以自然地质的多样性和作为感性的客观存在的人作为课题。这就帮助了马克思形成他的历史理论的‘基础’概念。”[1]8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施密特试图重新审理费尔巴哈在唯物史观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尤其是要重思费尔巴哈对机械唯物主义的超越。虽然施密特并未展开,但在该书第9页的脚注中,他对恩斯特·布洛赫有关费尔巴哈思想的评述可见一斑。施密特注意到,布洛赫肯定了费尔巴哈对于辨证唯物主义的创建,评价了费尔巴哈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建所起到的作用,并特别阐明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理论的要素及其对机械唯物主义的超越。[1]9施密特肯定了费尔巴哈从自然概念出发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认为费尔巴哈“这种不应从绝对精神出发而应从肉体的人出发的思想,对于马克思的主体性理论也具有重大的意义”。[1]13
当然,施密特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哲学唯物主义的关系探讨并不仅仅止步于分析后者对前者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指出它们之间实质性的差异。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施密特关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自然观的超越问题上。
我们知道,费尔巴哈是把自然和对象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诉诸于感性。施密特指出,“马克思比费尔巴哈前进了一步,不仅把感性直观,而且还把整个人类实践导入作为认识过程的一个构成环节中去,……只有费尔巴哈那里的作为权威的人与自然,开始被证明为是实践的辩证要素时,它们才达到了具体性。像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也讲到‘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虽然,他那时加了这样一个批判性的保留:一切这种优先地位只能存在于中介之中”。[1]14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把自然界定为人之外的实在,但绝非无中介的客观实在,亦非本体论意义上的人之外的客观实在。“马克思把自然——人的活动的材料——规定为并非主观所固有的、并非依赖人的占有方式出现的、并非和人直接同一的东西。但他绝不是在无中介的客观主义的意义上,即绝不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这种人之外的实在。”[1]14
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一种革命的解放理论,它的真正关心的不是这个世界的物质性本源到底是什么,因为“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从凡是物质的东西都是实在的和凡是实在的东西都是物质的这种观点,并不直接产生任何道德准则”。[1]30马克思真正关心的问题是“至今人们在历史中仍被贬低成一种经济的动力性对象,这种经济在盲目地机械进展着”。[1]32因此,在施密特的解读思路中,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真正的理论对象是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由隶属自然的依附性存在迈向通过生产劳动创造出的“第二自然”并沦为经济必然性的奴役的历史过程与动力机制。换句话说,马克思之所以超越哲学唯物主义的关键之处在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现实立脚点在于“社会实践的具体性”,在于以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沦为经济力量的奴隶的客观事实和形成机制为自己真正的理论探究对象,并以“把人从自己构筑的、无法预测的经济决定这牢笼中解放出来”为理论的实践旨趣。[1]32由此,我们更能体会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十一条的含义。然而,所有这些是马克思之前的所有唯物主义形态所无法达及的。遗憾的是,马克思之后的唯物主义,从第二国际到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和真理性,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包装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普遍的世界观,将其世界的物质性树立为核心的理论对象而丢失了马克思“社会实践的具体性”这一真正的理论对象和出发点。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现实批判性维度都被抽象的物质本体窒息了,“这一来它就和那种低劣的唯心主义毫无二致了”。[1]31
诚如上文所述,施密特在阐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关系时,他援引了“社会”、“实践”、“社会实践的具体性”以及“劳动的必然性”、“社会劳动的各种形式”等概念范畴。借助这些概念范畴,施密特在向我们展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真正对象是如何生成的同时,也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逻辑混乱。施密特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过,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该书的思路来看,这些概念的依次登场似乎存在着一个由抽象逐渐具体化的过程。尤其是,当施密特强调,马克思视域中的“关于人和自然的‘生成’的问题,与其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历史的社会的问题”[1]29时,当施密特对马克思的自然观与启蒙主义的自然观进行比较并凸显出马克思“物质变换”概念背后的社会生活过程的分析时,当施密特强调“自然只有通过社会劳动的各种形式才显现出来”时,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区别于以往各种唯物主义的另一层面的内涵就逐渐清晰了。此即,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现实落脚点问题。
施密特提醒我们,马克思并非仅仅依据现代科学的成果,也非依据意识形态的批判来捍卫其唯物主义的彻底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所以拒斥任何从本体论意义上提出的关于人与自然的最初的创生问题,拒绝以新旧本体论的思路去探究“世界之谜”,其原因在于,“和萨特尔一样,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创造意义’的上帝不存在,才能保证人的自由的可能性”。[1]28施密特其实想告诉我们,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始终是以思索“人的自由的可能性”为核心旨归。施密特分析道:“在具有‘史前史’特征的人类以往的历史中,由于人并不支配自己相对于自然的各种能力,因而人的本质就残酷地完全隶属于维持其生存的物质条件。人类当前只有首先从理论上把自己作为自身的原因来看待的时候,才能达到其本质和实存的现实统一”。[1]28施密特此处所说的“本质与实存的现实统一”实质上正是历代思想家所苦苦追思的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问题。在这里,施密特其实暗示了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不同于以往的唯心主义,而是从社会生产的历史性视角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中介关系入手的。这其中,前工业文明时代,人的本质及其自由完全隶属于自然,这是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和直观唯物主义所止步的领域。而人类步入工业文明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原先对人类生存条件起完全制约性作用的自然成为了人类生产实践的要素和构成环节,以资本关系为内核的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后,自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地成为了被加工和改造的对象,而人类在冲破自然的宰制的同时,也形成了另一种新的宰制关系,此即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自发)过程。这个过程对于经济活动主体而言同样是一种客观的、盲目的、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过程”,因而类似于前工业文明中的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宰制关系,但二者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即工业文明中的“第二自然”是人类自己生产活动的产物。如此一来,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以往各种唯物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差异性渐渐地显露出来了。
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对象的生成与施密特的“中介”范畴
如果说,上面只是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非本体论性质来看其与以往所有唯物主义的本质界划,那么,唯物主义对象如何生成或如何呈现的问题则是更为质性的区分。施密特区分了唯物主义阵营中的两种“物质”概念。“虽然十七和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的唯物主义,把物理学或生理学的规定性上的物质作为中心课题,但在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本质内容的唯物主义之一的形态中,物质必然是作为最广义的社会范畴出现的。”[1]22-23在这里,施密特实际上从对象的质性差异出发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之前的唯物主义进行了严格的界划。构成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研究主题的“物质”实际上是打上了社会范畴的烙印。施密特进而指出:“不是所谓物质这抽象体,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1]31从一般的抽象“物质”到“最广义的社会范畴”和“社会实践的具体性”,这里的逻辑跳跃确实有点费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楚抽象的“物质”和“社会实践的具体性”之间的逻辑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第2页关于“纯粹自然”的一个脚注当中,施密特援引了列斐伏尔发表于1955年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关于自然观的论述。在其中,列斐伏尔分析道:“因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一种神话,即基于纯粹的自然。对他来说,在人和自然的神秘调和中——只是哲学家感到的调和——发现自然和对象是‘永恒的过去所给予的’,对象是作为直观的对象来设定的,而不是作为社会活动即实践的产物来设定的。费尔巴哈的自然是原始森林的自然,或是近来在太平洋出现的珊瑚礁的自然。”并且,“……自然本身对我们来说,只是作为一种内容存在于人的经验和实践之中”。[1]15-16在引述列斐伏尔的自然观之后,施密特认为,对于费尔巴哈的“纯粹自然”的批判还可以更进一步,他指出:“自然不仅像列斐伏尔正确论述的那样,总是已被人加过工的东西,而且,尚未纳入人类生产的自然领域——列斐伏尔的原始森林或太平洋的珊瑚礁——也只是用关于已被占有的自然的范畴加以直观和理解的。和黑格尔美学一样,与通常的观点相反,对自然美的知觉已经是以艺术美为前提的。即使在马克思那里,还未被社会中介过的自然,只有在将来能予以加工时,才是有意义的。”[1]16
以小区平均数为基础,利用DPS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对组合间差异显著的性状,利用不完全双列杂交模型进行配合力分析[5-6]。
因此,构成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真正对象的不是实体性的物性存在,从一般历史认识的层面上来说,而是以人类实践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历史生成问题;而具体的社会历史层面来说,是工业文明以来人类自我构建的“第二自然”问题。[4]93-96
在施密特看来,以往的唯物主义,由于没有找到真正的对象,而实质上陷入形而上学的逻辑窠臼。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真正对象与出发点不是抽象的“物质”,不是要试图找到精神或物质的本性问题,而是关心如何从这个世界上消除饥饿和痛苦的可能性问题。对于这种可能性的分析,不是有关世界终极性本源的探讨能解决的,而是必须具体到历史进程中,对历史中“物质变换”形式的历史变迁及其背后的社会生活过程和“社会劳动的各种形式”展开具体的分析,才能找到历史前进的动力和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进而找到消除饥饿和痛苦的可能路径。具体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思路中,此即揭示经济决定的“似自然性”牢笼的产生与运行的动力机制,寻找其内在的矛盾与界限,进而将人从这一牢笼中解救出来的道路。而传统的物质主义思路根本就无法生发出这种解放政治学或伦理的诉求,因为“从凡是物质的东西都是实在的和凡是实在的东西都是物质的这种观点,并不直接产生任何道德准则”。[1]30也就是说,按照这种本体论的思维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物”简单地锚定为抽象的“物质”,那么这种抽象的、无中介的“物质”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分析和批判以及由此生发的阶级革命理论之间无疑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逻辑沟壑。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当施密特试图将沟通抽象“物质”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物”之间的中介范畴进一步具体化时,“中介”这一漂浮的能指所包含的内涵逐渐由“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滑向了“劳动的必然性”。我们知道,施密特实际上要告诉我们,在马克思的思路中,构成了我们认识的对象并非直接给定的或直接向我们显现,而是必须通过社会实践中介的。正因如此,我们不能依据形而上学的思路来追寻世界的本源问题,而必须意识到,构成我们真正要去把握的是认识对象的历史生成的动力机制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停留在古希腊哲学时期的朴素实在论阶段,也不能诉诸中世纪经院哲学中超自然存在的神或上帝,也不能返归自我的内在心灵或抽象的不可怀疑的先验自我,更不能迷失在经验感性世界的无穷尽的实证路途中。这些思路其实都导向了一种方法论的二元对立,既是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亦是历史与自然的二元对立。那么,我们该如何才能避免这种主客二元分立的逻辑陷阱呢?对此,施密特有句精彩的概括:“诚然,物质世界概念既包括客体也包括主体,然而,从本质上讲,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还有不调和性,但毕竟是劳动的必然性把它们历史地贯串在一起。”[1]19-20也就是说,作为沟通主体与客体、历史与自然的中介是“劳动的必然性”。那么,这里被施密特委以“中介”重任的“劳动必然性”又该如何理解呢?这其实涉及到施密特在阐发社会的自然中介性思想时所援引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即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
施密特围绕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及其所包含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理解,对培根以来的启蒙主义的自然观与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深入的比较。施密特指出,二者虽然同样是从对人的效用性观念来考察自然,但由于欠缺了马克思的社会生活过程这一中介,启蒙主义将自然视为直接向人呈现的、随手可得的现成物,因而他们“不能把劳动作为占有自然的手段来进行分析,不能从劳动上升到分工的必然性,以及上升到随之规定的阶级分化的必然性,因此就不能揭露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性,……从而,真正立足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后面的东西,更完全不能进入启蒙主义的视野”。[1]78很显然,施密特此处所言及的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背后的东西无疑是指马克思对社会生活过程的分析。对此,施密特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句话加以确认:“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3]209此外,在探讨世界的物质性命题和自然存在的时空性命题时,施密特指出:“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也只有通过社会劳动的各种形式才显现出来。”[1]54
三、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现实落脚点:历史发展“似自然性”的破解之谜
那么,这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之所以能超越费尔巴哈的原因在于他把自己的理论之锚仅仅锚定在工业文明之中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便可轻松地在思想史的变迁与时代的变迁之间直接划个等号了。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把自然和一切关于自然的意识都同社会的生活过程联系起来,由此克服了这种一元论的抽象的本体论性质。因为,人作为中介的主体,作为从有限时空上规定了的人,他们本身也是那以他们为中介的实在事物的组成部分”。[1]17马克思并不是要否定自然直接性,恰恰相反,马克思的自然直接性不同于费尔巴哈,前者是打上社会烙印的,是以有限时空的人为中介的,对于人及其意识而言,仍保持着产生上的优先性。也就是说,同样是对“自然直接性”的肯定,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简单地说,区别的依据在于对象是否经由社会实践中介。换句话说,马克思正是借由“社会的生活过程”这一“中介”,告别了任何形而上学式的研究思路,也同时告别了哲学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诉求。固然,施密特所极力强调的马克思自然概念的中介性是一个令人伤脑筋的问题,但也是施密特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哲学变革意义的关键所在。那么,这里的中介是什么意义上的中介呢?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实现自我的逻辑环节意义上的“中介”么?施密特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马克思意义上的“中介”是一种实践的社会历史性与具体性,而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中介。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引出了施密特眼中的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哲学唯物主义的根本界划,此即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及其生成的问题。
施密特以上的相关言论实际上为我们在抽象“物质”对象和“社会实践的具体性”之间架起了逻辑桥梁。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真正对象的呈现绝非是直接和现成在手的,须借由人们在其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中所居有的概念范畴才可理解。当然,能被援以界定对象的概念范畴并非康德意义上的先验自我,而是人们在其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历史的形成的。而这也正是施密特所倚重的“中介”概念的内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施密特的如下论断:“只有在以有意识的主体创造的人类历史为前提的时候,才能谈得上自然历史。自然历史是人类历史溯往的延长。人用一些打上社会烙印的范畴,去把握以往的再也不能拢近的自然;人也不得不用同一范畴去把握还没有作为为我之物所占有的自然领域。”[1]39
无独有偶,在分析马克思 “巴黎手稿”中把从本体论角度提出的关于最初的人和自然的创生问题视为一种“抽象的产物”加以拒斥的过程中,施密特指出,关于“先于人类和社会的自然的存在的问题”不是被抽象地提出来的,“它们总是已经以对自然作理论的和实践的把握之一定阶段为前提的。在被称之为绝对第一的基质之中,一切都已经同在理论的、实践的活动中产生的东西交织在一起,所以它们绝不是绝对第一的东西。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关于人和自然的‘生成’的问题,与其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历史的社会的问题”。[1]29
(2)印发心理健康教育小册子。让家长以高度认真的态度看待此事,真正从身心上关注下一代,并向家长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操作性强的可行性建议。取得家长的支持,共同关注寄宿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在施密特看来,正是由于费尔巴哈立足于这种非中介的感性存在,费尔巴哈对人和自然以及此二者相互关系的理解都止步于前工业文明的历史阶段。“费尔巴哈的人,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力出现的,而是和人类以前的自然密切相关。”“费尔巴哈所说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只同把人是自然所孕育的这一点神秘主义地神化了有关,而与在工业中以社会、历史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无关。”[1]15可见,费尔巴哈的“纯粹自然”是一种朴素的实在论,其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命题只是停留在前工业社会中。马克思批判的实质则在于将费尔巴哈视为整体的、非历史的、均质的基质消融在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之中,并且将客观世界的创造者界定为人类社会历史的生活过程,而不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随着人类历史步入工业社会,人类外部的自然存在越来越纳入到人类社会中去,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要素和环节。而这一事实在哲学上的反思是“客观性的种种规定越来越纳入主观之中,以至在康德之后所完成的思辨中,被全部吸收到主观性中去了”。[1]16
如今医院的传统治疗在不断发生变化,医院的妇产科也在健康指导下,不断寻找新的护理方法。使母婴获得更好的服务。在医院期间,除了为母婴提供平常的护理活动外,主要工作是提供更多的母婴护理知识和向母婴提供服务,向幼儿家长指导相关的知识,以帮助他们尽快接受婴儿,使他们熟悉家庭的新成员。母婴护理不同于以前传统的模式,它主张把母婴作为中心,把孕妇作为核心的妇幼保健理念。[1]对30例母婴进行床边护理,与传统的模式进行比较。结果报告如下。
四、结语与进一步的思考
在第二国际和苏联、东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与其革命的学说在逻辑上实际上是脱节的,这也表现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与其唯物主义哲学之间似乎在内在逻辑上并无太大的关联。从认识论意义上来看,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唯物主义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施密特正是看清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以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为焦点,就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何以超越哲学唯物主义这一问题展开的分析是深刻的,为我们摆脱本体论式的研究思路并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及其与资本主义批判的内在关联开启了方向。因此,施密特的努力值得高度肯定,但也存在着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地方。
在施密特的解读思路中,为了凸显马克思自然概念的非本体论性质,而强调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的实践中介性。但由于对于“中介”的泛化理解,实际上却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化了。这一点,在施密特分析马克思何以超越费尔巴哈时暴露无遗。比如,施密特明确指出,“马克思比费尔巴哈前进了一步,不仅把感性直观,而且还把整个人类实践导入作为认识过程的一个构成环节中去”[1]14。事实上,从西方哲学传统的内在理路来看,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不在于把实践引入认识过程,而是把认识视为实践的环节与结果。关于这一点,我们应回到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加以透视。在这个被恩格斯誉为“天才世界观萌芽”的著名文献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和以往的一切旧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其批判的核心要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要点:其一,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停留在事物的对象性和外在性并诉诸直观,抛弃了历史过程(主体的感性活动才是真正的理论对象与实践活动的历史性)。“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提纲》第一条)其二,人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进行,历史形成的社会形式是人的活动的既定条件和媒介,因而感性实践活动和活动主体总是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发展的社会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提纲》第六条)“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提纲》第七条)“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提纲》第九条)“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提纲》第十条)[5]54-57
“别想那些了”,竹韵抚摸着他的双肩,“只要你安然无恙,比什么都好。今后你要有火就朝我发,千万别干傻事。”
可见,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分野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理论对象的差别上,在理论对象的生成这一问题上,也不是单一的实践中介的问题。诚然,如施密特所析,我们的认识对象都是由实践中介的,但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以及此二者之间的关系都是由人们的感性实践活动历史地生成的,并且,理论对象的历史生成过程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始终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展开,并且这种历史性的社会形式也不是先天给定的,是由无数的有限时空中的有限个体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历史地塑造而成的。这是一种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内在具有的深刻的历史辩证法,这种历史的唯物辩证法是在马克思推进和深化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依据这种历史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不是抽象的物性质体,也不是单个有血有肉的感性个人,而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马克思意识到,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不可能停留在哲学逻辑上的运演,并须借由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批判,深入历史进程中以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核心焦点展开具体而科学的研究,从而建立一门真正的“历史的科学”。也正因如此,马克思在《提纲》中所倚重的“实践”概念便很快具体化、历史化为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由此生发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化过程中,马克思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进一步将新唯物主义的“物”锚定为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为一种人被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经济结构奴役的“似自然性”状态。然而这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被视为自然而永恒的客观现实其实也只是暂时的历史必然性。如此,我们来反观施密特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解读。由于未能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思想历程,即从“实践”向“物质生产”再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步步推进过程,在面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物”的概念上,只能借助一种泛化了的“中介”概念来加以阐发。由此,施密特自然无法理解《提纲》当中“实践”概念的哲学变革性和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过渡意义,更无法区分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中介性思想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人与自然关系被资本这一“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中介的思想的根本异质性。
(2)加强国内外机构在绿色金融控制方面的合作。 在“一带一路”的大环境下,我们有着很多的机会,利用与国际相关机构合作,以国际金融风险控制的高标准。通过不断学习国内外绿色金融发展的新成果、新思路和新理念。根据雄安的产业特征,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则与标准制定绿色金融法律制度,对于金融监管部分评估与测度,达成金融环境风险评级能够规范操作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93-96.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57.
Object and Its Formation of Marx ’s New Materialism ——Rereading on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from Perspective of Schimidt
Wang Yujue
(School of Marxism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China )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himidt,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s new materialism and philosophical materialism in general.To highlight the material premise of Marx’s new materialism,Schimidt have to explore the contribution of general materialism in history to Marx’s new materialism,in which the materialistic ideas contained in French Enlightenment and Feuerbach’s naturalist materialism (intuitive materialism)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for Marx’s new materialism.But the difference of Marx’s new materialism from the previous materialism is its non-ontological character of object,that is,the historicity and practicality of object.While explaining the intermedi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society,Schimidt cited many conceptual categories such as “society”,“practice”,“specificity of social practice”,“necessity of labor”,“the various forms of social labor” and so on.While showing us how the real object of Marx’s new materialism is generated,it further directs the theoretical vision to the Marx’s analysis of “simulating nature” of capitalist economic life,and thus reveal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revolutionary purport of Marx’s new materialism.
Key words :New materialism;Schimidt;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Simulating nature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19)03-0069-08
[收稿日期] 2019-03-05
[DOI] 10. 19669/ j. issn. 1009-5101. 2019. 03. 011
[基金项目] 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计划资助项目“社会关系再生产视阈下的性别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当代批判” (JYJQ2017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玉珏,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性别与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研究。(厦门 361021)
【责任编辑 于蓬蓬】
标签:新唯物主义论文; 施密特论文;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论文; “似自然性”论文; 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