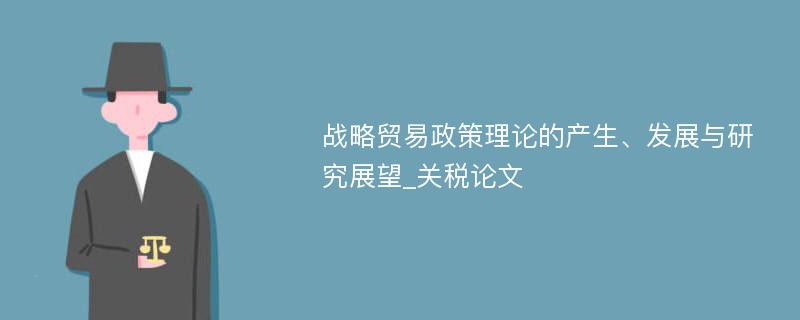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产生、发展及研究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9)04-0012-(07)
1981年,两位加拿大经济学家Brander和Spencer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潜在进入条件下的关税问题及垄断租金的抽取》,提出以下论点:在面临外国寡头垄断的条件下,进口国政府可以利用征收关税从国外出口寡头那里抽取部分垄断租金。这一论点的提出引起了贸易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从而拉开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论争的帷幕。
在Brander和Spencer论点的启示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的发展,西方一批经济学家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理论纳入规范的贸易理论分析之中,建立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模型,创立了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 Trade Policy)理论”。20多年来,许多学者涉足于这一研究领域,形成了众多的研究文献。本文试图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加以总结和归纳,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作一大胆展望。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内容
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涵,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侧重点有不同的理解。按照Brander(1995)的定义,战略性贸易政策是能够影响或改变厂商间战略关系的贸易政策;而战略关系是指厂商间存在的一种相互依赖性,一个厂商的获利受其他厂商战略选择的直接影响。换言之,战略性贸易政策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政府率先采取行动(贸易政策干预),导致厂商作出与无政策干预时不同的战略选择,从而使竞争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通过抽取外国垄断厂商的垄断租金或转移他们的利润,使本国厂商获得规模经济,最终提高本国国民福利,而这一提高足以抵消政策本身的无效性。
就其内容而言,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上述所谓的“利润转移”(Profit Shifting)理论,主要包括三种观点:战略性出口政策、战略性进口政策和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广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除了包含上述“利润转移”的论点外,还包括“外部经济”理论。由于外部经济理论并不属于单纯的贸易政策范畴,有些学者对于将其列为贸易政策有所争议,因而实际上狭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观点代表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战略性出口政策
战略性出口政策的创始人是Brander和Spencer,他们最早提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一国政府总有使用研究开发(R&D)补贴或出口补贴进行干预、帮助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获取更多“租金”份额的动机(Brander and Spencer,1983)。补贴能够提高本国厂商在与外国厂商非合作竞争中的地位,使其扩大出口市场份额并增加利润。尽管补贴国的贸易条件有可能恶化,但其总体福利仍有可能增加,因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使出口价格超过了边际成本,出口市场存在超额的垄断租金(Brander and Spencer,1985)。上述思想被称为战略性出口政策(Helpman and Krugman,1989)。
战略性出口政策模型是一个“第三国市场”模型。假定国内国外双头垄断厂商以产量为战略变量在第三国市场上采取古诺(Cournot)方式竞争,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厂商间会达成一个古诺—纳什均衡。如果一国政府在厂商作出产量决策前宣布给予本国厂商一定的出口补贴,则会使本国厂商生产或出口比古诺均衡时更大的产量。因此,对本国厂商的适当补贴(R&D补贴或出口补贴)可以提高本国厂商在共同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和利润,而使国外厂商的份额和利润减少,从而使本国的国民福利提高。
(二)战略性进口政策
战略性进口政策的创始人仍是Brander和Spencer,与战略性出口政策的“第三国市场”模型不同,战略性进口政策模型是一个“相互倾销”模型。模型假定只有两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厂商同时在本国和对手国市场上销售他们的产品,两个市场是彼此分割的,即垄断厂商分别就本国与国外市场进行生产决策,这意味着本国与国外市场上的价格就像在价格歧视的情形下一样,成为相互独立的变量。
Brander与Spencer(1984a,b)证明,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存在着一国政府利用关税从国外垄断厂商抽取租金或向本国厂商转移利润的可能性。如果寡头垄断厂商采取古诺竞争模式,那么本国政府对外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将通过贸易条件效应、利润转移效应、资源配置效应等三个途径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三)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
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以Krugman(1984)提出的基于“学习效应”的新幼稚产业模型为代表。该模型证明,在国内市场存在扭曲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行动可以使幼稚产业获得“学习效应”以及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成本曲线,使本国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扩展,增加本国产业的竞争力,提高国际市场份额,进而提高本国的整体福利水平。
Krugman的理论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寡头垄断、市场分割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具体地说,假定一个寡占行业存在国内国外两个厂商,他们生产相似的替代品,每个厂商都在包括两个生产国在内的多个市场上销售,而这些市场是相互分割的。关于规模经济,Krugman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形式:静态规模经济、学习曲线形式的动态规模经济以及研究开发带来的成本下降。虽然一个寡占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但模型的结果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可以保证本国厂商在国内市场上的稳固地位,使其获得一种相对于外国厂商的规模优势,这种规模优势又可以转化为更低的边际生产成本,从而使本国厂商在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得以提高。
二、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扩展、反驳和修正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模型在对现实做了极大的简化条件下,精巧地论证了在不完全竞争(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下,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贸易政策干预来抽取和转移国外垄断厂商的利润或租金,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该理论提出以后,引发了理论界的极大兴趣,许多学者对其基本模型做了多方面的扩展。另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提出了严厉的挑战,因而也引发了贸易自由主义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反驳和修正。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基本模型的扩展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基本模型的扩展大体可以归为三类:
1.一般均衡分析的尝试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模型是一个局部均衡模型,模型的基础是Cournot竞争,厂商的数量是外生给定且固定不变的。Dixit(1984)研究了外生地增加厂商数目对第三国市场模型结果的影响。他发现,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取决于国内外厂商数量的对比,当国内厂商数目大于1时,补贴使全部的国内厂商都竞争性地提高产量扩大出口,这样势必恶化本国的贸易条件并使每个厂商的利润降低,从而补贴的效果减弱。
Brander和Spencer(1984b)发现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独立于厂商数目,但厂商数目的增加会降低最优政策的水平。总体来说,其它厂商的进入减弱了政策实施的效果。因此一定的进入壁垒对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来说是必要的。Eaton和Grossman(1986)的研究也发现只有当本国的厂商数目不太大时,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
Dixit和Grossman(1986)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考虑了贸易政策的效果。他们的研究放弃了经济中只有一个寡头垄断行业的假定,讨论了多个寡头垄断行业同时利用相同的稀缺资源的情况。结果表明,政府对一个行业的补贴造成的该行业寡头厂商的扩张和利润转移必然伴随着其它行业厂商的收缩和利润损失。一般而言,当考虑一般均衡的情况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果被削弱了。
2.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引入
基本模型假定政府掌握有关行业成本、市场需求和厂商行为等方面的信息,但事实上,政府可能比厂商掌握的更少。
Brainard和Martimort(1992)的分析假定外国厂商对本国厂商的成本很了解,而本国政府对本国厂商的成本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补贴向外国厂商揭示本国成本状况的作用就不存在,因而在非完全信息下,政府使用补贴的动机就会减弱。
然而Brainard和Martimort(1997)则指出,即使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使得政府收集信息的能力和掌握信息的数量弱于私人部门,政府在某些领域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政府并不会因为在有关战争和武器成本等方面的信息十分有限而放弃国防政策,让军队和军事工业自行发展。
Creane(1998)通过建立一系列的模型指出,即使在各种经济主题都面临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完全的约束下,政府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比完全的自由放任要好。
3.厂商或政府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
基本模型考虑的是单边干预、一次博弈的情况,研究双边或多边同时干预、重复多次博弈的情况也是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扩展。
Davidson(1984)考察了政府采取单一的一次政策以后厂商之间重复多次博弈的情况,他分析了在无限多次博弈中关税怎样使国内外厂商以“触发战略”(Trigger Strategies)维持部分勾结的局面。Brander和Spencer(1985)在考察两国政府同时实施出口补贴时得到了一个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均衡。对于两国政府来说,同时对出口施加补贴只能使双方的福利恶化。Collie(1991)指出,如果一国预期对手国将进行报复,其利用贸易干预转移租金的动机就会减弱。同样的情况在战略性进口政策的模型中也会发生,两国政府单边干预的动机如果导致关税战的爆发,就会造成对两国都不利的结果。
Bagwell和Staiger(2000)从政府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动机的角度研究了国际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与协调的形成机制,指出该机制是多边贸易体系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战略性贸易政策也为使用多边贸易谈判的方法解决贸易自由化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反驳和修正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反驳和修正主要关注了Brander和Spencer(1984、1985)的战略性出口和进口贸易政策、Krugman(1984)的新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等三方面。
1、对战略性出口和进口政策的反驳和修正
如前所述,Brander和Spencer的战略性出口和进口政策的基本思想都在于证明一国可以通过贸易干预来影响本国厂商及其国外竞争对手的行为,改变竞争格局,实现“租金抽取”和“利润转移”。这不仅与自由贸易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冲突,而且与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进程相悖,直接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对该结论的质疑。
Dixit(1989)和Krugman(1990)从一般均衡、动态、更广泛的策略性行为的角度对Brander-Spencer模型进行了分析,认为战略性出口政策理论并不成立:出口补贴虽然导致出口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但出口产业规模的扩大是以其它行业资源转移为前提的,在共有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出口补贴在降低补贴产业边际成本的同时提高了其它产业的边际成本,从而造成产业扭曲。
Horstman和Markusen(1986)的研究对战略性进口政策的效果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通过征收关税带来的“利润转移”和超额利润将会导致本国新厂商的大量进入,而新厂商的进入将会大幅度地压缩行业的利润空间,并最终导致行业利润为零。因此,对于大部分行业而言,采取战略性进口关税保护政策并不能改善社会福利水平,反而会使之恶化。
Streit(1987)从政府失灵的角度证明,即使Brander-Spencer模型成立,政府也不一定能够成功地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因为政府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必须要在事先确定战略性产业。但事实上,政府在获取相关信息以确定战略性产业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游说(Lobbying)和寻租(Rent-Seeking)行为的存在更是有意识地妨碍了政府获取正确的信息,如果政府并不具备成功判断行业结构的能力,则错误的政策将会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
2、对新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反驳和修正
Krugman新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提出为政府在新形式下干预经济、采取保护贸易政策提供了似乎合理的理论依据,也引起了贸易经济学家对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新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和传统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反思。
Corden(1986)指出,新幼稚产业理论和传统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本质上它们都是建立在现实世界各种扭曲基础之上的。即本质上都是在试图用“制造新的扭曲”来纠正“旧的扭曲”,对于幼稚性产业而言,一国的贷款计划、金融市场的深化、人力资源的培训、研究与开发补贴等措施都要比贸易保护政策更好。
Stegemann(1996)则指出,新旧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是有区别的,区别的关键在于新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改变了传统幼稚产业分析中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假设以及外国先进厂商已经完成学习过程的假设,而假定存在卖方的国际垄断和规模经济,由此得出结论:通过保护幼稚产业可以使国内生产者获得比国外竞争者更好的规模优势,并能够将这种规模优势在没有保护的市场上转化为较低的边际成本和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Stegemann认为Krugman对现实世界的修正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修正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卖方垄断的世界市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同时,由于技术创新外国竞争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具有比采取幼稚产业保护的国家更好的学习效应,因此,从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本身难以得到合理的幼稚产业保护结论。
Kaneda(2003)通过建立一个动态模型得出结论: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实施是否有效取决于政府和受保护企业的互动反应,即便政府能够始终如一地实施它所宣布的政策,幼稚产业部门调整的速度、产业的规模以及政策的实施期限都将在政府幼稚产业保护政策设计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在实施产业保护条件下,幼稚产业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
3、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展中国家适用性的争论
20世纪末以来,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引起了贸易经济学家的关注。
Miravete(2003)建立了一个分析幼稚产业动态学习效应的动态均衡模型,结果显示,幼稚产业中的国内价格和关税会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不断下降。Miravete的结论为发展中国家幼稚产业保护后的未来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支持。Greenwald和Stiglitz(2006)研究发现,实施战略性贸易限制的动态收益也许要大于它们的静态成本。这种分析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幼稚经济体(而不仅仅是幼稚产业)提供了贸易保护的依据,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比较广泛的贸易保护而发展起来。
然而新近的研究似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Saure(2007)的研究认为,在贸易保护下,发展中国家具有正外部效应的现代部门将不会得到发展,相反国内传统的产业部门将得到扩张,其结果是传统产业结构得以继续维持,经济增长趋于停滞,其原因在于幼稚产业保护阻断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需要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实证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中,以下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
(一)Dixit(1988)对美国汽车产业的分析
Dixit的研究直接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汽车大量进入美国市场、导致美国在1981年对日本进口汽车施加自愿出口限制(VER)的实际。Dixit的模型是一个相互市场模型,即美国和日本均存在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并假定一国内部生产的汽车是完全相同的,而两国的产品之间存在差异,互为非完全的替代品。Dixit考察了1979、1980和1983三年的情况,以分析不同贸易政策的结果。
Dixit考虑了关税是唯一政策工具和对进口征收关税的同时对本国企业给予生产补贴两种情况。他发现,无论是否存在生产补贴,美国最佳关税的数值均应高于对日本进口实际施加的关税;而当生产补贴存在时,最佳关税小于没有生产补贴时的数值。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当关税是唯一的政策工具时,美国的最优关税率为8%-17%,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论基本成立;关税与补贴并用时福利水平的提高要高于单独使用关税或补贴时的福利,但提高的程度不大。
(二)Baldwin和Krugman(1988)对日本16K RAM的分析
Baldwin和Krugman以世界半导体行业的一种产品16K RAM(Random Access Memory,动态随即存储器)为例,考察了日本的贸易保护政策对市场结果和贸易福利的影响。这一研究的背景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半导体产业的世界市场几乎由美国独占,相比之下,日本才刚刚起步。到1979年,日本占了世界16KRAM市场42%的份额,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
半导体行业具有极强的“干中学”(Learning-By-Doing)效应,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和规模的扩大,生产成本和价格会大幅度地下降,在这种显著的动态规模收益递增的行业,政府使用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干预的动机大大地增强。
Baldwin和Krugman分析了两种政策的效果:一是日美双边自由贸易的情况;二是贸易战发生的情况,即双方都对对方进口施加100%的关税(此时双边贸易不存在)。实证结果表明,在日本政府不对国内市场采取保护政策的情况下,没有日本企业能够成功的存在,更不用说占领美国市场。日本政府的贸易政策确实对保护和促进本国行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进口保护的确起到了促进出口的作用。但从福利分析来看,贸易保护对日本和美国都是负面的,日本消费者的损失多于生产者所得。如果两国发生贸易战,则两国的福利会进一步下降。
(三)Smith和Venables(1988,1994)对欧盟主要产业的分析
Smith和Venables对欧盟主要产业特别是汽车产业的贸易政策效果进行了系统的量化分析,其研究非常引人注目。他们的分析假定厂商的生产既存在规模经济,又存在范围经济,将产品的同质性和差异性一起纳入模型的分析之中;同时他们的模型是市场分割的模型,厂商可在不同的市场上索要不同的价格。
他们的结论与Dixit的结论相似,即一定程度的保护比自由贸易更有利,但是最佳保护关税的数值并不大,从关税中的潜在获利也较小。但与Dixit模型不同的是,在他们的模型中,即使行业的自由进入消除了既有厂商的利润,施加关税仍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可以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
Smith和Venables的一系列文章分析了在多个行业应用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的政策效果,考虑了价格与数量竞争、分割与一体化市场等几种不同假定下的情况,试图对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贸易政策实施及其效果得出较为普遍的结论。其一般性的结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下总有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可能性,只有在极为巧合的情况下,一国的最佳政策才有可能是自由贸易;第二,政府的贸易政策对贸易和生产量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对福利的影响却很小;第三,贸易政策的效果依赖于模型的假定。
(四)Ohyama等(2004)对日本棉纺产业的检验
Ohyama等用日本棉纺产业的发展来检验贸易保护的有效性。在Ohyama等看来,日本的棉纺产业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在政府扶持下棉纺产业在日本建立,政府支持下的企业开始生产并供应日本市场;第二,该产业发展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许多没有政府支持的新企业也开始大量进入。Ohyama等认为,幼稚产业的保护是一个学习过程,其学习的速度依赖于企业家的创造力,而产业的规模则是次要的。
Ohyama等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幼稚产业保护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以及早期受政府保护企业的探索,后期企业也许不会拥有进入市场的机会。因此在产业发展的初期,政府的适度保护是必要的。
四、未来的研究展望
战略性贸易政策从提出至今已有20多年的发展,它为政府干预贸易提供了新的依据。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并不为贸易保护提供支持,它要说明的恰恰是由于各国存在单边贸易倾向,必须用多边的方法来解决贸易自由化问题,从政府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动机的角度来审视国际双边或多边的贸易谈判与协调。总之,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它开拓了人们对贸易政策研究的新领域,扩展了政府使用贸易政策的视野。以下的领域或许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证的丰富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一个没有经验分析基础的理论体系,在考虑报复和一般均衡等条件下,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缺少完整的理论基础,同时也缺少经验数据支持。在最近几年里,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研究相当大的努力转向了实证研究领域。但是目前实证检验相对落后于理论的发展,已有的检验结果也因为方法的不足而众说不一。
因此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计量工具的发展、新的估计方法的出现以及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数据可获得性的增加,在战略性贸易政策领域必将产生丰富的实证文献,以检验理论是否依赖于某一特定的假设条件,是否依赖于某一特定的参考值,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事实上,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一些新的实证文献出现。如Hamilton和Stiegert(2002)利用非参数估计的方法实证检验加拿大小麦委员会(CWB)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国际硬粒小麦市场上实现租金转移的机制等。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
一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变量,也依赖于政府政策的影响。贸易政策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内容。人们已经发现,当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模型从静态一次博弈扩展到动态多次博弈、从局部均衡分析扩展到一般均衡分析,结论将更加的复杂和不确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有可能减轻了垄断扭曲,但却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速度(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以往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都过窄地关注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特定的方面(比如关注于某一特定产业等),这种研究未必能得到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领域仍然有大量的问题值得去研究。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环境问题更多的具有全球性的特点,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的关系更加紧密,贸易与环境的问题也成了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模型排除了环境的因素,在未来关于实际贸易政策的研究中,应该将资源和环境作为一种投入要素纳入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的分析框架之内。最近的研究包括Greaker(2003)、Hamilton和Requate(2004)、Levinson和Taylor(2006)等,但显然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与贸易自由化的趋势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人们对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研究已经大大深化,但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环境。一方面贸易经济学家为战略性贸易保护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却在强劲发展。WTO等国际组织日益趋向于贸易自由化的国际规则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策制定的空间,在这些规则的约束下,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护战略性的幼稚产业、如何制定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已经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如宋泓(2007)等。但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9-0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