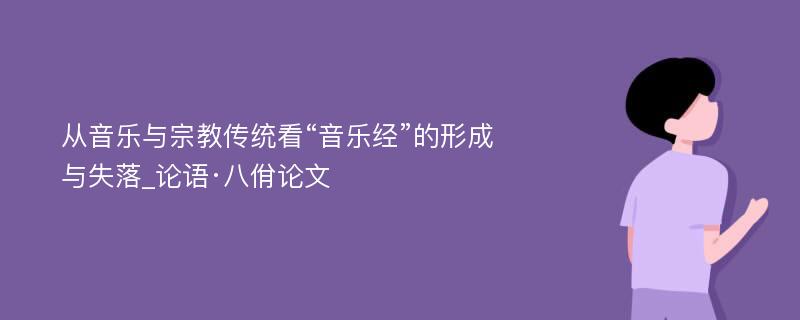
从乐教传统论《乐经》之形成与残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乐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0.01.018
文章编号:1003-7721(2010)01-0141-06
《乐经》作为六经之一,对先秦贵族子弟的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流传过程中,《乐经》并没有保存下来。对此,学界有着不同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先秦实止五经而无《乐经》;[1]而多数学者认为《乐经》确实存在过,如罗艺峰先生从古代学术传统上以纬证经的思路出发,通过对《乐记》和《乐纬》的研究,论证了《乐经》存在的可能性。[2]项阳先生也对《乐经》的失传问题做了详细的研究。[3]不过,要想弄清楚这一问题,还需要将《乐经》文献的形成放到先秦乐教传统的背景下进行讨论。《乐经》后残佚,其对雅乐义理的论述则保存在《乐记》之中。《乐记》在继承《乐经》音乐思想的过程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乐教体系与《乐经》的性质
《乐经》之佚失,为学术史上之一大公案。有人以为《乐经》亡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如宋徐坚《初学记》卷21说:“古者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经。至秦焚书,《乐经》亡,今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乐类》也说:“沈约称:《乐经》亡于秦。”有人则以为春秋之时礼崩乐坏,以六代古乐为代表的雅乐系统受到“郑卫之音”的冲击,而导致雅乐不再被人喜爱而丢失,如清朱彝尊《经义考》:“朱载堉曰:古乐绝传率归罪于秦火,殆不然也。古乐使人收敛,俗乐使人放肆,放肆人自好之,收敛人自恶之,是以听古乐惟恐卧,听俗乐不知倦,俗乐兴则古乐亡,与秦火不相干也。”更有人以为本没有《乐经》,《乐经》在《诗》和《礼》中。如清邵懿辰《礼经通论》云:“乐本无经也。……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对此,周予同先生总结说:“依今文学说,《乐》本无经,乐即在《诗》与《礼》之中。依古文学说,《乐》本有经,因秦焚书而亡失。”[4]两说论点不同,但今文家说虽新而失之于妄,古文家说虽旧却较为稳妥。对邵懿辰之说,夏传才先生已辩其非。另外,他还认为《乐经》并不是只有乐谱而没有文字。[5]夏先生持论言之有据,足以发前人之诬。笔者赞同夏先生观点,以为《乐经》确实是存在的,只不过在流传的过程中失传了。其失传原因详见下文。
《乐经》的编纂,当是伴随雅乐观念之形成,对上古三代乐教经验的总结。《礼记·文王世子》云;“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早在舜时,即有乐官夔负责“胄子”的音乐教育。《尚书·舜典》中记舜之言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的这番话,涉及的乐教内容有乐德:“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乐语:“诗言志,歌永言”;乐律:“声依永,律和声”;乐用:“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另外还有乐舞,即夔所言之“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与《周礼·春官宗伯》所载之负责国学教育的大司乐的职责相类似:“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另有乐师所掌之乐仪,即“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教乐仪,行以《肆夏》,趋以《采荠》,车亦如之。……”乐师也是负责教导国子的,只不过所掌均为“国之小事用乐者”(《周礼·春官宗伯·乐师》),当为大司乐之属官。朱熹也有类似的意见,认为大司乐之教是夔典乐事的遗留,《历代职官表》卷十:“朱子谓大司乐之教即是夔典乐事。今故录舜典,系之《周官·大司乐》前,以明三代相承,实本虞廷旧制也。”由此可知,由舜时至于西周,贵族子弟的音乐教育有其相似性和传承性。只不过西周时的教学内容大大增加了而已。仅以乐舞为例,西周时就将自黄帝而来的六代乐舞(即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作为“国子”教育的必备科目。
说西周有一套完备的音乐教育体系,还可从国子教育不同阶段所传授的内容不同看出。当时贵族子弟的教育内容有“大学”、“小学”之分,按《大戴礼记·保博篇》云:“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其中就外舍所学的“小艺”即“六艺”,按“六艺”之说,即《周礼·地官·大司徒》所云:“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保氏》也曰:“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可知贵族子弟束发之前的学习当偏重于技术层面,属于基础性教育。这里的“乐”也当偏重于对音乐技巧的学习和训练。而束发之后,进入“大学”所学的“大艺”当为“四术”,即《礼记·王制》所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这里的“乐”的学习就与“大司乐”所教的内容相似,更偏重于文化层面,即对音乐知识和音乐思想的学习。这点在《礼记》中也能找到证据,《礼记·内则》说:“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韶。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十几岁时,所学的是与射、御等相类似的技术和技巧;二十岁之后,所进行的则是与“礼”相同的文化层面的学习。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西周之时即使没有一部标准的音乐教科书——《乐经》,也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乐教体系。这个完整的体系就是《乐经》所形成的现实基础。《乐经》的现实基础还立足于当时的用乐实践。通过对先秦典籍的梳理,我们会发现孔子以前对雅乐的演奏、学习和阐释都有着某些约定俗成的规范。传说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导致了雅乐观念的成型,《尚书大传·嘉禾传》说:“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洛诰传》也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尚书大传》所载虽不完全可信,但至少说明了周公在西周雅乐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周公在“制礼作乐”过程中广泛吸收了上古三代的文化资源,即所谓“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同样,周乐的成型也借鉴了前代的音乐理论和音乐资源。后来周成王也正过礼乐,《史记·周本纪》:“成王……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此时的工作与周公不同,以“正”为主,即制定了某些规范。①这些规范指导着周乐的演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札出使鲁国时,曾被“请观于周乐”,他对这些“周乐”的评价显示一个受过国子教育的贵族,对某些雅乐的感性认知。与此相似,在孔子之前,各家对雅乐的阐释有着趋同的标准,如虢文公的“省风说”、史伯的“和同说”、众仲对“羽数”(即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等的区别)的讨论、郤缺的“无礼不乐”说、医和的“中声”说、晏婴的“和同说”等再加上季札对“周乐”的评价,②显示了时人强调音乐与政教合一的道德追求及重视中和之乐的审美旨趣,与《周礼·春官宗伯》中所提到“乐德”内容相类似。这些人大概都受过正规的“国子教育”或者本人就是乐官,他们对雅乐的阐释应当符合《乐经》中的用乐规范。
这些用乐规范和雅乐阐释为孔子后来的“正乐”工作奠定了基础,正如皮锡瑞所言:“孔子之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6]马宗霍也说:“古之六艺,自孔子修订,已成为孔门之六艺矣。未修订以前,六艺但为政典,已修订以后六艺乃有义例。政典备,可见一王之法;义例定,遂成一家之学。法仅效绩于当时,学斯垂教于万祀。”[7]故由二说可知,《乐经》中所保存的当是在西周被奉为政典的、以六代雅乐为核心的音乐内容,至少包括对乐德、乐语、乐用、乐舞等各类知识的总结,它用以培养贵族子弟的音乐演奏技巧和人格素养。而在经过孔子的整理之后,它成为一门反映西周雅乐教育的专门之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孔子之前《乐经》的内容是以非实体的状态——演奏为主的。
二、孔子教乐与《乐经》的存佚
上引皮、马二说,均以孔子对六经的撰述有所贡献。然皮氏为今文学家,更加注重孔子的“删定”之功;马氏为章太炎高足,当属古文学派,更加注重的是孔子的“修订”之劳。但二人认识之共同点,即孔子之六经是在前代文献基础上整理而来。夏传才先生也说:“六经本来是古老的文献,……由于孔子的搜集整理和传授,这些古老而珍贵的文学才不至于湮没。”[8]
以乐为例,有一点疑问。孔子幼年贫困,自云“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孟子云其曾为委吏、乘田(《孟子·万章章句》),未曾入仕于东周王朝,如何获得整理编订《乐经》的材料?其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孔子虽未入仕于周,但曾到过周之国都雒邑,其目的很可能是学习周礼和访求古文献。《史记·孔子世家》曾记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之事。尽管钱穆先生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地无据,其人无征,其事不信。”[9]但钱穆怀疑的是老聃其人和孔子曾问礼于他的事,对于孔子适周,却只存其疑,未敢全面否定。《孔子家语·观周》也云:“敬叔与(孔子)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孔子家语》虽传为魏王肃所伪造,但所载事亦非全伪。因为《乐记·宾牟贾篇》也说:“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史记·乐书》所载亦同。或许此说亦有所据,也未可知。
第二、春秋之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对于乐师的失官情况,《论语·微子篇》中有详细记载:“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这些乐师流入各地,大概也将周朝教育贵族子弟的材料和经验带了出来。对于当时“文献不足征”的情况,孔子尤其注意对文献的访求。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郯子为鲁之附属小国郯国之人,孔子闻其名后就跑去向他学习。这正可见其对文献搜集的热忱。那么,对于这些流散各地的乐官传下的知识,孔子自没有不访求之理。这些知识大概就成为了孔子编纂《乐经》的文献基础。
第三、孔子为鲁国人,鲁国完整地保存了西周的礼乐制度。鲁国与其他国家不同,据传其开国之主周公曾为周王朝制礼作乐,为表彰其功德。“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国不仅有诸侯之礼乐,亦有周天子之礼乐,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可知,正因为鲁国完整保存了周代礼乐,所以吴公子札一到鲁国,就要求观赏周乐。这为孔子能全面地了解西周雅乐制度提供了便利条件。
而且孔子还深通雅乐,《乐记》记载了他对宾牟贾讲《大武》的演奏情况,说是从周太师苌弘那里听来。杨荫浏先生正是根据这段记载,还原出《大武》舞的真实演奏情况。[10]而《大武》是西周雅乐的代表作,原由大司乐执掌。他又曾给鲁国太师讲过乐理,按《论语·八佾》:“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此论与上文乐师所掌之乐仪相类似。可知,孔子对西周雅乐理论是十分稔熟的。孔子还有很好的音乐素养,特别留意对“乐”的学习,《史记·孔子世家》记其跟鲁国乐官师襄学鼓琴,其学习的中心也不仅是对弹琴技巧的掌握,而更多的是“得其志”和“得其人”。③这是着重对乐德的把握,是符合“大司乐”教导国子的首要标准。他在欣赏雅乐时,也首重“乐德”,如“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又“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以“美”“善”等品德作为评价雅乐的标准。
正因为有此便利条件和音乐造诣,才使孔子整理《乐经》的可能大大增加。他确实做过一番正乐的工作:“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正乐是有一定标准的,即是上文所说的雅乐用乐规范。如他批评违反规范的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三家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体现了他对雅乐体制的自觉维护。而他将这些规范加以总结,“以备王道,成六艺”,完成《乐经》文本的整理,也不是没有可能。孔子虽通雅乐之理,却无资格演奏雅乐,故其对《乐经》的阐释更偏重于义理的层面,与西周时将其作为实践之乐已有不同。
“自卫反鲁”是孔子晚年之事,这与孔子整理《六经》、教育弟子的时间相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育弟子,史有明载,如《论语·泰伯》引孔子言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又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礼记·经解》引孔子言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广博易良,《乐》教也。”这里孔子看重的还是乐教的道德作用。孔子对弟子的教育,还吸收了西周雅乐教育的经验。皮锡瑞就说:“则孔门设教,犹乐正四术之遗。”[11]
但行文至此,如果没有新的材料出现,我们实在难以准确推断《乐经》的文本是否由孔子所手定,故只好借本田成之的话做一总结,他说:“此二者(礼、乐)实是孔子之道,经书虽然没有,实是一种活的经书,由孔子的一言一行以及其教门人的微言大义,实在此礼、乐的活用。……总之,经书的基础,在孔子之时,《诗》、《书》、《礼》、《乐》是已经成立的了。”[12]余敦康先生也说:“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列国纷争,‘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以六经为载体的经典处于转型的过程之中,尚未写成定本,但是作为历史文化价值本原的权威地位业已确立,得到普遍的尊奉。”[13]对《乐经》而言,“作为历史文化价值本原的权威地位”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雅乐用乐规范的确立。孔子正处于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雅乐渐趋衰微,周礼亦遭到破坏,他却仍然将周礼和雅乐作为弟子的教育内容。而此时他的乐教思想,正符合了《乐经》代表的雅乐文化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逐渐将《乐经》的实践之乐转变为义理之乐,即更强调“乐德”思想和“乐制”所体现的等级关系。
三、孔门传乐与《乐记》的形成
孔子之学,传于弟子,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既“身通六艺”,当也通“乐”。七十子中较有名的是子夏,东汉徐防曾言:“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后汉书·徐防传》)可知,子夏对《乐》或有所发明。马宗霍以为子夏于孔门四科中以文学著称,所以徐防之言当为可据。[14]刘师培亦曰:“《礼》、《乐》二经,孔门传其学者,尤不乏其人。如子夏、子贡皆深于《乐》。”[15]另据《乐记·宾牟贾篇》载有宾牟贾向孔子请教《大武》之乐事,虽没有直接证据说宾牟贾是孔子弟子,但从其“侍座”之举,可推知其不是孔子弟子就是孔子后学,所以孔子对其有传乐之举。
刘师培又说:“至战国之时,治《乐经》者遂鲜。”[16]确实,孔门治《乐经》者没有明确谱系可传。但《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有“仲良氏之儒”。据陶潜《圣贤群辅录》云:“仲梁氏传《乐》为道,以和阴阳,为移风易俗之儒。”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圣贤群辅录》为后世伪书,不是陶渊明所作。袁行霈先生却认为“未可轻易断定其为伪作”,并有详细考辨。[17]我们大概可知,孔门传“乐”虽没有明确的谱系,但并不表示没有继承这一传统之人。故及至荀子之时,仍有《乐论》之作。马宗霍认为荀子兼传孔门六艺,即“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18]故其《乐论》一篇,虽为驳墨子“非乐”主张之作,但也正好传播了孔门的音乐主张。
《乐经》亡佚后,集儒家音乐理论之大成者是《乐记》。关于《乐记》的作者,学界存在着不同的争论。郭沫若、吕骥等人认为战国时的公孙尼子是《乐记》的作者;蔡仲德等人则认为《乐记》是河间献王刘德及其门人所作。[19]但不管如何,《乐记》确为总结先秦儒家的音乐思想而来。且不说公孙尼子为儒家的嫡传正宗——“七十子之弟子”,即使是刘德所作,按《汉书·艺文志》所言:“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这里所谓诸子,当也是七十子之后学,即《汉书·河间献王传》所言:“献王所得,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可见,不管《乐记》作者是谁,其思想之来源均为孔门七十子之所传。
“记”在汉代是作为解经的体裁而存在的。④《乐记》本为解释《乐经》所作。前文已言,《乐经》至少应当由“乐德”、“乐语”、“乐舞”三方面组成,另外也许还有对礼乐关系的探讨及对上古音乐知识的普及等内容。若按朱载堉的意见,《乐经》失传为“俗乐兴”“古乐亡”的缘故。那么,当时失传最多的应为“乐语”和“乐舞”,因为音乐曲调和演唱舞蹈的技巧很难形诸文字,容易丢失。而“乐德”,即音乐知识和音乐思想却容易被保存下来。这些音乐知识和音乐思想后来被儒家学派给传承下来,很大程度地被保存在了《乐记》之中,《乐记》可视为是儒家学者对先秦雅乐思想体系的一次系统总结。若按沈约的意见,《乐经》亡于秦火,《乐记》中的音乐思想则是免于秦火而流传下来的“七十子”的论乐内容。而“乐语”和“乐舞”部分也不可能完全丢失,当也有乐官能凭借记诵使其得以保存,如汉初乐家之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鎗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汉书·礼乐志》)制氏对如何演奏雅乐还能凭家族相传勉强熟习,但对雅乐的“乐德”部分则不能明了。制氏所代表的不一定是孔子整理的《乐经》,但代表的却是朝廷雅乐。这从侧面也能为《乐经》的失传情况提供佐证。“乐舞”部分,至汉初仍有部分六代雅乐流传下来,如汉初之《文始舞》、《五行舞》,就是上古六代乐舞的遗留。《汉书·艺文志》云:“《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也。”这些“乐舞”和制氏所保存的“乐语”的部分恐怕不是秦火所能毁掉的。这与《诗经》的流传情况有相类似之处,《汉书·艺文志》说:“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说明《诗经》之所以免于秦火,是依靠记诵保存了下来。所以对于《乐经》的消失,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俗乐”大兴使音调迟缓、节奏僵化的“乐语”、“乐舞”大量丢失;秦火之厄又使大量“乐德”内容丢失,仅流传下“七十子之徒”的部分论乐内容。
与汉代其他解经的“记”有所不同,《乐记》在《乐经》失传之后上升到“经”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易》《书》《诗》《礼》《春秋》都有经书存留,而独《乐》无经文,而代之以《乐记》二十三篇。此后的各代书目类典籍像《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文献通考·经籍志》、《宋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都将《乐记》收入经部,由此就可看出《乐记》的重要地位。熊十力先生则直接将《乐记》视为《乐经》,他说:“愚谓《礼记》中有《乐记》一篇,即是《乐经》。……其文当是七十子后学所记述。”[20]
而且通过《乐记》的篇目问题,我们也可看出《乐记》对先秦雅乐教育理论的继承之处。《汉书·艺文志》著录《乐记》篇目为二十三篇,但现存《乐记》仅有十一篇,即《乐本》、《乐论》、《乐礼》、《乐施》、《乐言》、《乐象》、《乐情》、《乐化》、《魏文侯》、《宾牟贾》、《师乙》。另据孔颖达《礼记正义》,刘向《别录》存有《乐记》后十二篇之名,按顺序是《奏乐》、《乐器》、《乐作》、《意始》、《乐穆》、《说律》、《季札》、《乐道》、《乐义》、《昭本》、《窦公》。这比《大司乐》“乐德”、“乐语”、“乐舞”的分类更为细致和条理。《乐记》的内容亦完全以义理为出发点,更重视的是其对《乐经》精神实质的阐发。即便有对乐器及乐舞的介绍,也更注重对“乐情”中所蕴含的道德内涵,如《乐论篇》说:“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乐情篇》:“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这种思想与孔子“‘乐云乐乐’,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宾牟贾篇》对《大武》记载,更重视的也是音乐演奏过程中每一细节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如宾牟贾问舞蹈间歇为何会有长时间的等待,孔子回答说:“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是说长时间等待代表了周王朝的德化和礼乐传播四方,取得人心。
战国时期,伴随雅乐衰微,西周实践层面的用乐规范完全受到破坏,六代古乐开始丢失,按《宋书·乐志》:“周存六代之乐,至秦唯余《韶》、《武》而已。”孔子后学对乐的阐发已经完全归结到义理层面。《乐记》的形成就代表了西周雅乐从实践之乐到义理之乐的转变。至此,《乐经》已成为一种文化象征,代表着后人对西周礼乐文明的向往之情。
综上所述,通过对先秦雅乐教育的梳理,我们可以明了《乐经》形成的可能性,以及孔子对先秦雅乐的整理和改造。而在传承《乐经》过程中,孔门弟子也发展了以《乐经》为代表的音乐理论。在《乐经》亡佚之后,《乐记》全面总结了孔门七十子弟子的音乐理论,使之成为中国古代最系统之音乐理论著作。
收稿日期:2009-11-05
注释:
①赵敏俐先生认为雅乐是指在周代的各种礼乐礼仪上所演奏的正乐,在这些仪式中,正乐的演奏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如金奏、升歌、笙奏、下管、间歇、合乐、无算乐等,多见于《周礼》、《仪礼》、《左传》等典籍中。该观点可参见赵敏俐等:《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78页)。
②可参见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之第一章《孔子前的音乐美学思想》(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
③《史记》卷47《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25页)曰:“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④周予同先生(《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说:“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孔子以后的著作,也不得冒称为经。他们以为经、传、记、说四者的区别,由于著作者身份的不同;就是孔子所作的叫做经,弟子所述的叫做传或叫做记,弟子后学辗转口传的叫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