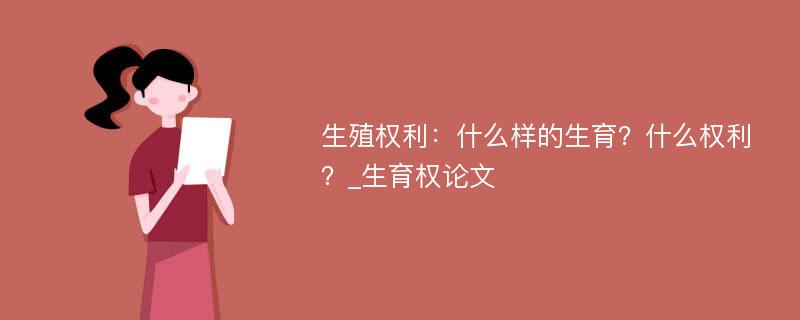
生育权利:什么生育?什么权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育权利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在我们上承祖先下传后世的生育活动中,无论是重视或漠视,都昭示着一种最基本的人生态度。200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中国人的生育权利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前所未有的关注。随后各省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更将大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不断细化和深化,各种具体而微的规定引发了传媒热烈的讨论并最终导致了学界的关注。因为,问题升温的时候最有助益的往往是冷静的思考。
首先要讨论的是“两性生育权”问题。由于女性地位的逐渐提高,女性在行使自己独立生育权的时候很自然就提出了一个与男性生育权的对接问题。男性与女性生育权的两分法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女性已经开始摆脱在生育问题上“听俺掌柜的”这种依附的角色。生育决策上的两性平等问题由来已久,如今却有了新的内涵。倘若两性在生育问题上的认知有冲突,那么到底我们该尊重谁的生育权?是男性还是女性?这显然是两难之择。尊重了男性的生育权就可能剥夺了女性的生育权,反之亦然。
两性拥有独立、对等、协商的生育权应该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两性生育权的基点有三:其一是独立性,即两性生育权相对独立;其二是对等性,即两性的生育权同等重要;其三是协商性,即两性生育权的实现需要两性的对接和配合。只有将两性的生育权整合在一起,才可能在一个共享的架构里完满实现。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讲的“中和位育”之道了。《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近代学人的解释为: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安所遂生,就是生物体和环境之间的调协,就是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潘光旦先生所说的“位育”。(注:潘光旦.潘光旦文选——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2)独立意味着差异,对等期待着协商,而协商则促进了合作。这恐怕也是我们理解人类婚内生育权的基本准则。
女性有了独立的生育权,意味着女性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赞同男性却不必像过去那样附和男性,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必臣服于男权中心的文化。相反地,男性也不能依仗文化的优势和生理的优势来强制实现自己的生育权。如果两性的生育权无法实现对接——譬如,一个想生另一个不想生,那最好是各留天地、彼此尊重;再退一步,爱意全消,婚姻解体,走彼此无涉的路也还不错。但无论如何,两性生育权的讨论都应该在一夫一妻的制度框架里进行。从古到今,没有哪一个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但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还是一个迄今最文明的制度。文明的实质是通过对人类行为的规范和人性中动物性的约束来完善人类的心灵。如果没有婚姻制度的约束,人类的道德危机同时就预示了人类的生存危机。所以,我们需要对婚姻制度有起码的尊重。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人类婚姻和生育制度的基本伦理是责任伦理。婚内生育是最合伦理的生育。
我们需要认真思量的“生育权利”是父亲、母亲、孩子和社会共享共济的权利。忽视孩子的生育权,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进化最大的缺陷之一。他们之所以处在劣势,是因为孩子是被决定、被选择的。他们没有原生生育权——生育的主权,但不等于他们没有次生生育权——生育的知情权、被爱权以及生育之后的个体生存权和发展权。遗憾的是,少数已经考虑到“孩子生育权”的觉者还不足以形成新文明的浪潮。
其次要讨论的是“个体生育权”问题。一个没有结婚的女性或者男性有无生育权?这是一个因为2002年11月1日起开始正式施行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的新条款所引发的新话题。《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0条第2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生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个体生育权”的享受者是终身不婚并无孩子但又想要孩子的妇女。生育的途径是技术的而非自然的。
由此,我们不难想到若干可以讨论的有趣问题。譬如,符合同样条件的男性如果想要个孩子,他们的个体生育权如何体现?是不是也像那些不结婚但要孩子的女性一样去购买“卵子”来满足自己的生育需求?社会出于对男性生育权的保护、出于两性平等的社会需要,是否也要建若干个美女卵子库供那些想做父亲的男子们挑挑拣拣?
从技术手段来说,试管婴儿的做法比较符合男性生理特点,现实可行。也许有人会说,哪有不婚的男性想要孩子的?即便真是“零需求”的假设,作为法律却不能不一碗水端平。何况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已经提出婚内男性生育权的保护问题了,婚外的生育权在理论上同样存在。逻辑至此,也许已经不是好笑了,而是让我们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此其一。
其二,无论生育通过何种技术手段来实现,其实质都不该出伦理的规章。任何有悖伦理的技术化生育只会将人类引向困惑丛生的歧路。需要“技术生育”的人群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无生育能力但试图通过生育技术的辅助来实现生育的梦想;另一类是有生育能力但没有合法的婚姻却要婚外生育。本文要讨论的是婚外生育的技术实现所遭遇的伦理困境。根据吉林省的经验,独身妈妈生育有两种辅助生育技术可选择:一种是人工授精方法,每次费用大约需要1000多元,成功率在20%左右;另一种是试管婴儿技术,每次大约1.5万元左右,成功率一般为30%左右。对于健康的独身女性来说,运用人工授精的方法就可以了,试管婴儿技术通常是因为女方的输卵管阻塞等原因不得已才实施的。
完整的生育权利是家庭利益、个人利益、孩子利益和社会利益整合的结果。1968年,在德黑兰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人权会议上,人类首次将“自由地、负责地决定生育孩子的人数和生育间隔的权利”宣布为一种“人权”(生育权)。《德黑兰宣言》第16条明确宣布:“父母享有自由地、负责地决定子女数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有获得有关教育和信息的权利”。1974年,布加勒斯特首次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提出了“生育权利”。《世界人口行动计划》是这么表达的:“所有夫妇和个人都有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生育孩子的数量和生育间隔并为此而获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夫妇和个人在行使这种权利时有责任考虑他们现有子女和将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外事司编.人口与发展国际文献汇编.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9)这里的责任除了对家庭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考虑外,还包括了对孩子的责任和对社会的责任。从个人理性的普适性假定出发,夫妇或个人的生育决策也许可以无视社会利益的存在和社会诉求的急迫(譬如,一个人口严重过剩的国度对控制人口的积极性),在道义上却不应忽视孩子的生育权——这种关怀体现了父母之爱的博大和无私。对孩子事后权利的确认和尊重闪耀着人类血亲之爱的强烈光芒。
其三,孩子也有生育权?这当然不是一个玩笑,而是对人类社会基本伦理的建构和尊重。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们无妨用一个反问来完成——当孩子长大懂事后,是否乐意出生在一个没有父亲(或者没有母亲)的家庭呢?婚外的技术化生育不仅彻底剥夺了孩子的知情权和父爱权,而且损害了孩子未来的发展权和婚育权。留下的只有尴尬的自言自语和永难消失的心灵创痛。
换言之,职能部门沾沾自喜的双盲原则隐伏着三大危机,即“血缘不清”状况下的自我认知危机、“父爱(或母爱)短缺”状况下的人格发展危机和“信息残缺”状况下的婚姻生育危机。所谓双盲原则,是说合法的医学辅助生殖单位对于精子的使用要按照国家卫生部的严格规定,采取双盲的办法,即捐精者不知精子将被何人采用,受孕者不知用的是何人的精子,医学辅助生殖机构的人员对精子的来源要做到严格保密,否则将被视为违法行为。
“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是人类永恒的追问。倘若父亲(或母亲)是客观存在的,却不知其人其名其事,这该是多大的折磨?父亲(或母亲)是确实存在的,却遥在“天边”,因为信息双盲此等社会性契约的事先约定而不得相见。这里,我们看见的只是冰凉的理性却找不到温暖的情怀。“我是谁?”没有答案,只有风声雨声读书声……。无根的人必有漂泊的心。在孩子社会化的进程中,这种“血缘不清”的困扰会伴随终身。旁人任何一点关于身世的疑问都会在其内心掀起难以平息的风浪。“另类”的字眼从一开始就烙在了这些孩子的人生履历上,成为一个绝不光华的“污点”,想擦也擦不掉。站在孩子生命周期的角度,我们还会简单地认可类似于吉林《条例》这样的做法吗?说穿了,婚外技术生育的做法在本质上与克隆人类的做法一样都存在着人类自我认知不清的潜在危机。
毫无疑问,婚外技术生育的做法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所以在捐精者与受精者的“结合”并不是爱的结合,而完全是商业运作的产物,一个买精,另一个卖精,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但彼此的价值取向与婚内生育却截然不同。至少对卖精者来说,他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生育,而是为了利润。锁定在资源商品化的角度,那么卖精和卖血或者卖肾等能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无非是在出售人体资源或者说生命的生物资源而已。
一个焦点问题是,在婚外技术生育的框架里,孩子对生父是没有知情权的,更不可能享受到慈父之爱。这不是一个无情的剥夺吗?这不是一个人为的歧视吗?这不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吗?所以说,假定真有通过不知名的捐精者的“帮助”来实现自身生育梦想的女性,那么在满足了自私欲求的同时却极可能伤了孩子、毁了孩子,最终是有了孩子反为其累。因为他(或她)并不是“父亲”与“母亲”爱的结晶,只能在苦恼中幻化出一个“影子父亲”。在某种意义上,他(或她)是买来的并带有婚外生育的怪异色彩。这样的情形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会有多大的阴影、又有多大的压力?谁能为孩子社会化过程中不得不承担的巨大心理成本负责?
如果我们能够认可生育权是关系到了主体和客体、家庭和社会、个人和环境、生育和成长等诸多维度的复杂范畴,那么就不难从孩子的角度来理解孩子的生育权的内核——最重要的就是对父爱(或母爱)的渴望。费孝通先生早年提出了家庭三角形理论,至少告诉我们一点,没有父母的爱,没有孩子的爱,都无法成就一个健全的家庭。费孝通先生在著名的《乡土中国》中提到:“家庭这概念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的界说: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亲子是双系的,兼指父母双方;子女限于配偶所生出的孩子。这社群的结合是为了子女的生和育”。(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8)孩子如果能得到充沛的父爱和母爱并且使爱有所附丽,随时可转化为具像的关怀;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孩子的生育权得到了尊重。这样的家庭是健全的,这样的生育也是合乎伦理的。“血浓于水”,是因为我们对血脉亲情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密感,从中我们获得了起码的安全感、情感的慰藉和奋进的力量。
然而,在一个特定法律的框架里,独身女子的技术化生育却无可挽回地使父爱失落了。父爱在哪里?只在少年的幻想和午夜的惊梦里。人格是爱一手制造的。不健全的爱必然导向人格发展的缺陷。孩子只为充满爱心的父母感到骄傲。孩子期望的与其说是物质上的需求,不如说是健全、持久的父母之爱。
技术生育固然开辟了人类生育的新格局,但操作不当,也可能因为越来越远离生育的伦理规则而使我们的心灵蒙羞并成孤魂。婚外生育权技术实现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伦理虚无。技术生育是无爱生育。社会学中所讲的“同类相聚”说明了没有生父的孩子只能被同类视为“另类”。他们在心灵上是被排斥和自我放逐的。他们不仅是另类的小众,而且是孤独和愤怒的,他们一定会求证母亲:为什么没有父亲?为什么没有父爱?为什么要生下“我”?
越接近自然状态的生育,我们就越贴近了生育伦理的本质——责任和关爱。新生命的哺育从头到尾都是“责任伦理”的次第展现。当一个女性为了精神寄托和养老需求通过商业机制和技术手段人为制造出一个婴孩的时候,暂时的喜悦却掩盖不了一个必将逐渐明朗的事实:她实现的残缺不全的生育权利,她给孩子的爱无论多么丰润,也是残缺的,即便她找一个代理父亲,也改变不了孩子没有生父的事实。生父是一个社会学的范畴,或者说父亲是家庭中的角色,但首先要在婚姻中确立这个父亲作为丈夫的角色。卖精者貌似“父亲”,实为“商人”。责任伦理的道德指向提醒我们,生育权利的归依是孩子的生育权,对这一点的关注才能凸现出人类生育活动的崇高性和伦理性。
放远眼光的话,技术化生育还会带来孩子的婚育危机。万一与同父异母的孩子相爱并结婚和生育的话,就有近亲结合的风险。因为一个供精者可能有许多个受精者,但他们之间却信息不明。谁能保证避免同父异母孩子之间的相识甚至相爱?这说明前述的“双盲原则”实际上是将这些来历不明的孩子置于某种恐惧和不安中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案例并非鲜见。
这样的技术化生育突破了生育的底线伦理,可以休也。因为孩子的权利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尊重。孩子被置于不清不白的位置上,从结果上讲,甚至比“私生子”的社会待遇更为恶劣。后者好歹还可能是爱的结晶,可以找到生父甚至沐浴到充沛的父爱。说穿了,“技术生育”无疑是在为借种网开一面,事实上是在挑战甚至在某一小众中颠覆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但一夫一妻制却是人类摆脱动物性的必要约束。无爱的生育的确伤害了无辜的孩子。孩子不是爱的结晶,这难道是有道德基础的生育吗?技术生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
生育主体与生育客体之间选择和被选择的关系注定了生育伦理是最典型的“责任伦理”,必须考虑到孩子的权利。总之,生育的权利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利,不仅仅是生育主体的权利,这是我们生育权利立法时最必要的反思。那种将生育权利只赋予生育主体的做法不仅是偏颇的,而且是有害的。生育权利的实现有其必要的婚姻制度前提和道德伦理基础,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出发,则更要考虑孩子的生育权,考虑到代际之间的权利协商,这一代人权利的实现不能危害到下一代人权利的实现。如此看来,在备受国人关注的生育立法和生育决策问题上,的确需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和视野。
标签:生育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