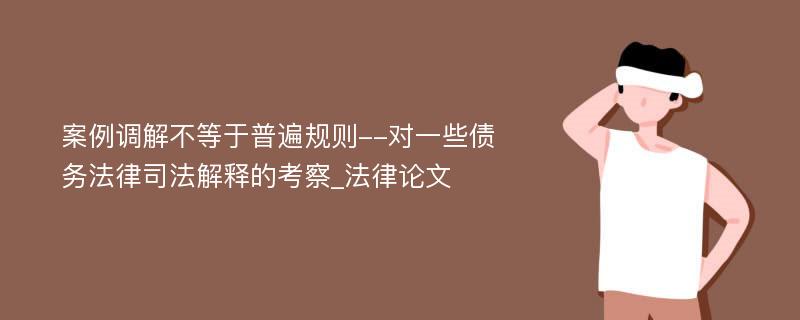
个案调处不等于普适性规则——关于若干债法司法解释的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司法解释论文,不等于论文,规则论文,普适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4)05-0237-09 一、引言 债权,作为与物权相对的范畴和制度,有着自己的本质属性。债法,作为财产流转的基本法律,在世界范围内,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众多的共同规则。它们是历经碰撞、磨砺所产生并存续的,已被证明是符合社会生活要求的,是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规则。因而,尽管它们的绝大多数均非发端于中国,但中国债法仍不可将之拒之门外,而是应当借鉴。当然,债法应当也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而有适当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为《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为《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为《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为《侵权责任法》)等法律中的债法规范,都既吸取了人类共同的智慧,借鉴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债法规则,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某些债法规则,值得肯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债法所作的司法解释,也基本上如此。 毋庸讳言,某些债法的司法解释却没有遵循债权的本质属性,绕开了债法的共同规则,效果不佳。其中,相当一些是将个案的调处方案上升为普适性规则,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弊多利少,应予修正。本文即为此而作,就教于大家。 二、关于一物数卖司法解释的评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法释[2012]8号)第9条第2项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普通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数个买受人均未受领交付,先行支付价款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9条第3项规定,均未受领交付,也未支付价款,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如果其他类型的债也照此规则确定实际履行及其法律效果,那么,法释[2012]8号第9条第2项和第3项的规定就变成了债的实际履行的规则。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如此解释买卖合同乃至整个债的实际履行规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物数卖的案件时,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出卖人与第一个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后,发现价格低了,便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又以较高的价格与第二个或第三个甚至更多的买受人签订第二个或第三个甚至更多的买卖合同,获取不当利益。更有甚者,有些买卖合同的签订是出卖人与第二个买受人或第三个买受人恶意串通的结果。针对这样的案情,为了保护诚实信用的第一个买受人,应当责令出卖人向第一个买受人实际履行。于是,法释[2012]8号第9条第2项和第3项之类的司法解释应运而生。 可不是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法释[2005]5号)早就开了先河,其第10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作为转让方就同一出让土地使用权订立数个转让合同,在转让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受让方均要求履行合同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履行交付土地等合同义务的,应予支持;(二)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已先行合法占有投资开发土地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履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合同义务的,应予支持;(三)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又未合法占有投资开发土地,先行支付土地转让款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履行交付土地和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合同义务的,应予支持;(四)合同均未履行,依法成立在先的合同受让方请求履行合同的,应予支持”(第1款),“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受让方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第2款)。其中的第3项与法释[2012]8号第9条第2项如出一辙,第4项与法释[2012]8号第9条第3项完全一致。 前引法释[2012]8号第9条第2项的规定,改变了传统民法奉行的债务人任意履行(自主履行)的规则,体现了效率原则和优惠保护完全履行义务者的精神,具有正当性。该种创新符合赖泽尔教授关于“所有权阶段性移转,从而当事人依时间先后共有所有权”的观点。①它被形象地称为“削梨说”,日本的铃木弥录教授和几代通教授也持此种观点。②按照“削梨说”,买卖物的所有权随着价款的逐渐支付而逐渐移转,已经付清价款的买受人在普通人的眼里应为买卖物的所有权人。在这个意义上说,法释[2012]8号第9条第2项的规定可以接受。 与此不同,前引法释[2012]8号第9条第3项的规定,确立了依法成立在先的债权优先于成立在后的债权的规则,剥夺了其他已经主张自己权利的债权人取得标的物权利的资格,破坏了债权平等原则。而破坏的唯一根据就是合同成立在先,其正当性显然严重不足。因为债权平等原则是由债权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是立法者权衡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基于民事权利体系的合理设置(尤其是物权与债权的区分)而确立的,轻易不许破坏。所以,法释[2012]8号第9条第3项的规定实在不足取,此其一。该项规定有损交易安全,因为第一份买卖合同不具有公示性,第二买受人、第三买受人等不知买卖物已经成为他人债权的对象,且无重大过失,时常是根本没有过失。在这种情况下,剥夺第二买受人、第三买受人取得买卖物所有权的机会,不符合交易安全原则,此其二。为了避免出现无法取得买卖物所有权的现象,第二买受人、第三买受人等需要花费人力、物力调查买卖物是否亦为他人债权的对象,增加交易成本,也迟滞了交易的进程,此其三。在只有第二买受人或第三买受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裁判机构误将第二买受人作为第一买受人,从而确定第二买受人将取得买卖物的占有和所有权。但于该裁判文书生效后,实际上的第一买受人起诉到该裁判机构,并且援用法释[2012]8号第9条第3项的规定,主张取得买卖物的占有和所有权,该裁判机构该如何处理?显然,陷入困境,此其四。③ 三、关于放弃“入库规则”是否妥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法释[1999]19号)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其本意确实是赋予债权人优先受偿权,其目的在于鼓励债权人积极而主动地行使债权人代位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实务中,如果沿用传统民商法的“入库规则”(次债务人给付的财产归属于债务人,债权人再请求债务人以此类财产向债权人履行其债务),则其他共同债权人“搭便车”,行使债权人代位权的债权人可能不能完全实现其债权,因而挫伤其行使债权人代位权的积极性。 这种基于个案而形成普遍性规则的司法解释的路径及方法,早在法释[1999]19号草案的研讨会上,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就一再反对,认为在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中,赋予债权人优先受偿权,存在如下弊端:(1)违反债权平等原则。各个债权人的债权一律平等,这是原则。拟打破这种平等,得有相当的理由,如为设立抵押权等。债权人主张了代位权,本已扩张了债权的效力,实属优惠,再赋予其债权优先受偿的效力,更是厚此薄彼。这里出现的局面是,债权人对债务人提起普通诉讼,法律不赋予该债权优先受偿的效力,债权人提起了代位权诉讼,反倒赋予债权优先受偿的效力,这不禁使人要问:同样是提起诉讼,为何效果的差距如此巨大?根据何在?(2)违反共同担保原则。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全部债权人的债权的一般担保,债务人对于第三人的债权属于责任财产的范畴,其实现而转化的有形财产应当作为共同担保的责任财产,而不宜直接归行使代位权诉讼的债权人独有。赋予债权人的债权优先受偿的效力,是对共同担保原则的破坏。 笔者认为,赋予债权人的债权优先受偿的效力,还有如下不足或与有关制度及规则相抵触:(1)赋予债权人的债权优先受偿的效力,虽有利于鼓励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但与它给整个民法制度及其理论造成的破坏相比,此种优点微不足道。(2)不赋予债权人的债权优先受偿的效力,奉行“入库规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赋予债权人的债权优先受偿效力的结果相同。例如,第一,在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其他债权人没有向债务人主张其债权、没有向次债务人主张代位权的情况下,次债务人的清偿虽然名义上归属于债务人,但也不影响债权人债权的自然实现。第二,在次债务人向债务人清偿的场合,债权人请求债务人清偿,债务人无权拒绝,债权人没有义务留着财产等待着睡眠的其他共同债权人醒来共沾利益。第三,在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履行的场合,按照“入库规则”,给付物虽然交付给了债权人,但债权人并不能取得给付物的所有权,因债权人对该给付物所有权的取得尚无合法根据,所以,该给付物对于债权人来说属于不当得利,债权人负有向债务人返还不当得利的债务。不过,该返还债务与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若表现为金钱债务或其他类型的同种类债务,符合抵销权的要件,则债权人可主张抵销,无需实际返还不当得利。④这在客观上使得债权“优先实现”。(3)在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其他债权人也提起此类诉讼的情况下,合并审理(法释[1999]19号第16条第2款),首先提起诉讼的债权人无权优先受偿。(4)在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其他债权人向债务人提起普通诉讼的场合,代位权诉讼得中止(法释[1999]19号第15条第2款),债权人的债权也无法优先受偿。这是因为,按照债法原理,法律应当尽量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而非轻易突破之,尽可能地由债权人直接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而非轻易允许债权人越过债务人而直接向次债务人请求清偿,债权人仅为一人时如此,为数人即共同债权人时亦然。(5)中国民法通说认为,债权人撤销权兼具形成权和请求权的性质,其行使一方面使债务人和第三人实施的法律行为归于无效,另一方面又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回复至行为前的状态。⑤所谓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回复至行为前的状态,就是“入库规则”。于此场合,债权人无需再行提起代位权之诉即可请求债务人为清偿。就是说,债权人就债务人的财产没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法释[1999]19号没有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中规定债权人优先受偿,也表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就因撤销而回复由债务人直接控制的财产获得清偿,与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而获得清偿,相差无几。我们认为,单单赋予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时的优先受偿权,违反了相似的事务相同处理的公平理念。 既然如此,不惜大面积地破坏民法制度及其理论,赋予债权人的债权优先受偿的效力,有些得不偿失。就此看来,“入库规则”最具合理性。 有鉴于此,对法释[1999]19号第20条关于“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的规定,可不作债权人就次债务人的给付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解释,而将之解读为:它并未否定“入库规则”,而是在无其他共同债权人主张或依债务人的指令所为诸种情况下,次债务人交付标的物或提供劳务的中性的路线图。 四、关于情事变更原则的限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为法释[2009]5号)第26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该条司法解释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将不可抗力排除于情事变更原则的构成要件之一的“情事”之外;二是扩张了情事变更原则另一构成要件,即构成情事变更原则,不但“履行显失公平”为其要件之一,而且“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同样为其构成要件之一。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不合适的。 法释[2009]5号第26条将情事变更原则成立的情事限制在“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显然缩小了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范围。之所以如此,据负责该司法解释的法官介绍,是因为理论上和实务中都有混淆情事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的现象,司法解释有必要将二者明确区分,于是法释[2009]5号第26条应运而生。 对于此类基于个别专家学者混淆情事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的现象,就“听风就是雨”地制定司法解释的路径及方法,笔者仍持否定见解,详细剖析如下: 法释[2009]5号第26条尚未真正而恰当地界分二者,反倒弄巧成拙,不适当地缩小了情事变更原则适用的范围。原来,不可抗力发生,若造成了合同不能履行,则在合同效力方面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1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可行使解除权将合同解除;在违约责任方面,当事人可援用《合同法》第117条第1款的规定,主张免除责任。与此有别,不可抗力发生,没有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但继续履行合同显失公平的,基于情事变更原则变更合同乃至解除合同。其例证不在少数,如境外的智利矿石案(Chilesalpeter all)⑥、加油站出租案(Vermietung einer Benzintankanlage)⑦、鞋厂广告案(Befreiung eines Schuhfabrikanten von Anzeigenvertrag)⑧、甜菜价款案(Der Rübengeldfall)⑨,等等。在中国国内,如甲乙双方于2002年11月1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乙承租甲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门面房屋用于经营餐饮业,但2003年4月“非典”肆虐京城,顾客锐减,导致乙入不敷出,根本无力依约交纳租金。于此场合,乙援用情事变更原则,主张减少租金,应当得到支持。在这里,相对于甲乙及其系争租赁合同而言,“非典”及其导致的顾客锐减,符合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构成,应属不可抗力,但它并未造成系争的房屋租赁合同不能履行,即乙支付租金的义务不存在不能履行的问题,不过,乙继续依约交纳租金确实显失公平,应当获得相应的救济。但乙无法援用《合同法》第94条第1项的规定解除系争房屋租赁合同,因为难谓乙因不可抗力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也难以援用《合同法》第117条第1款的规定免责,因为系争房屋租赁合同尚能履行。唯一的救济之道是,乙援用情事变更原则,主张减少租金乃至解除系争房屋租赁合同。 对此,有专家学者辩解道,《合同法》第94条第1项关于在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场合产生解除权的规定,已经包含了不可抗力影响合同效力的情形,法释[2009]5号第26条的规定并无不当。而笔者认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无法涵盖所有的不可抗力影响到合同履行的情形,如汶川地震使得开发商无法按照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的期限交付房屋,需要延期3个月,对于作为投资者的买受人来说,不可说其合同目的落空,无法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1项的规定;倘若适用情事变更原则,延后交房的日期,则可适当地解决该种纠纷。 这告诉我们,《合同法》第94条第1项关于在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场合产生解除权的规定,延伸到了大陆法系的情事变更原则适用的某些领域(或者说案型),但不能处理另外的若干情事变更原则所能解决的案型。换句话说,法释[2009]5号第26条的规定将不可抗力排除在情事变更原则中的情事之外,确实欠妥。⑩ 从另一个侧面说,既然《合同法》第94条第1项已经就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可以产生解除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不可抗力以外的其他客观情况(通常事变或曰意外事故)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1项的规定,那么,情势变更原则就不应当适用于此类场合,否则,就是人为地造成《合同法》第94条第1项的规定与情事变更原则的交叉、重叠,产生乱象。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大陆法系上的情事变更原则不适用于履行不能的领域,仅仅管辖履行可能但实际履行会显失公平的案型,英美法上的合同落空原则适用于上述两类情形。中国《合同法》第94条第1项等所谓不能实现合同接近于大陆法系的履行不能,只有履行可能但实际履行会显失公平的法律调整在中国《合同法》上尚付阙如,形成法律漏洞。填补此类法律漏洞,只要引入本来意义上的情事变更原则就足够了,再添加通常事变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则,并且将之纳入情事变更原则之中,不但逻辑混乱,而且无端地生出许多混乱。这是极不适当的。 在笔者看来,关于情事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之间的关系,正确的理解应为:不可抗力的发生未影响到合同履行时,不适用情事变更原则;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时,在德国法上由风险负担规则解决,在我国合同法上发生合同解除,也不排斥风险负担,亦不适用情事变更原则;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履行十分困难,但尚未达到履行不能的程度,按合同约定履行显失公平的,方适用情事变更原则。(11) 五、关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认定 违反何种法律规定,合同才无效,我国民法的态度及规定前后变化不小。《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5项前段规定,违反法律的民事行为无效。就其字面含义而言,这将违反任意性规定的民事行为(包含合同)也纳入无效的范围了,显然不妥。制定《合同法》时认识到了这一点,形成的共识是,任意性规定是为民事主体提供范本,其作用主要是示范,并非强制。如果个案情形不适宜照任意性规定这个“葫芦”画“瓢”——签订合同,那么,缔约人完全有权变更乃至排斥任意性规定,自由地选取合同类型,商定合同条款。如此,违反任意性规定的合同不再规定为无效,只有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归于无效。于是,《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应运而生。(12) 《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相较于《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5项前段,是个明显的进步。这是法律人了解境外民法及其理论,经历我国实务,用心体悟的结果在立法上的表现,值得肯定。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视野的开阔,实务经验教训的总结,开始意识到《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未区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将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也一律规定为无效,也有失权衡。有鉴于此,需要限缩《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适用范围,法释[2009]5号在这种背景下于第14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在笔者看来,法释[2009]5号第14条不再将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一律认定为无效,明确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该条司法解释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将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一律不认定为无效,这又不恰当,也是将某些案型升格为普适性规则的表现。实际上,有的合同违反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同样无效。例如,我国现行法关于建设施工企业资质的规定,本为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超越资质等级的,该合同无效,但承包人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建设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等级,当事人请求按照无效合同处理的,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1条第1项)。这表明,法释[2009]5号第14条的规定未能涵盖所有的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的情形,又形成了新的法律漏洞。 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注意并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5条关于“正确理解、识别和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维护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并遵循第16条关于“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的规定办理。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误将个案处理的结果上升为普适性规则的不足,再通过一个案例予以说明。在河南花园置业有限公司与河南鑫苑置业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一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是行政管理部门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土地在办理土地使用权权属变更登记问题上所作出的行政管理性质的规定,而非针对转让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花园公司在收取占有鑫苑公司部分土地转让费后,以自己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反而主张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13)有学者对此表示赞同,认为人民法院不能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认定当事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下简称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1项所订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 笔者对此表示反对,分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1.对于违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1项和第39条第1款的情形,宜作类型化的分析。第一种类型,用地者受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后全无开发,便将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他人,这严重违背立法目的,纯属炒地皮,应予禁止。第二种类型,用地者已经尽力开发,只是在数量上没有达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9条第1款要求的程度。对此,可以容忍。 针对第一种类型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1项的规定,应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为此时此刻的该项规定目的在于反对拖延开发,禁止炒地皮,避免炒地皮而层层加价。这也就从源头上避免了最终使商品房售价抬高,损害作为消费者的购房者的利益。这些方面的利益,应该是社会公共利益了。既然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1项的规定还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吗?! 至于第二种类型,《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1项的规定不应适用,在技术处理上,应当是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1项的规范意旨,限缩该条项的适用范围,即它不适用于第二种类型的未达《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9条第1款要求的开发程度的情形。 2.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一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关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1项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9条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意见,法释[2009]5号第14条关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司法解释,存在不妥之处。这是因为,总的说来,违反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未必有效,也未必无效,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上文已述,不再赘言。 3.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一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的目标是不支持恶意之人关于系争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其实现路径是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1项排除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范围,接着运用恶意抗辩的理念:“花园公司在收取占有鑫苑公司部分土地转让费后,以自己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反而主张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对此,笔者评论如下:从系争合同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必须无效,而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则不一定无效的理念方面观察,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一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力图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1项排除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范围,在解决前提性的问题上的路径并非全无合理性。因为它若坚持《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1项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就达不到目的。但是,如同上文“1”已经分析的那样,不可否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1项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就此说来,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一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在解决前提性的问题上还是走向了歧途。不如像笔者那样,区分违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9条第1款的情形,把开发建设用地未达《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9条第1款要求程度不太严重的情形,排除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1项的适用范围。在系争案件不适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1项的情况下,对于恶意之人关于系争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就毫无障碍了。 六、结语 债权平等、相对乃债权的本质属性,这既是立法者汇集众人智慧、利益衡量的结晶,是债法乃至整个法律自身规律的表现,也是它们所作用的社会生活本质要求在法律上的反映。立法机关制定债法规范,法律人解释债法规则,都应尽可能地尊重它们,据此行事。 诚然,由于某些个案的特殊性,特别是受制于证据以及举证方面的制约,机械地依据债权的平等性、相对性处理案件,可能会出现极不适当的后果,只有回避债权的这些法律性质,才能达到公平正义的结果。于此场合,需要暂时将具体的债法规则放在一边,依据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确定个案的解决方案。这种裁判案件的思路及方法,是法律适用及解释所允许的。不过,同时要遵循“一事一议”的原则,而不得将这些处理方案上升到普适性规则的高度,取代债权的平等性、相对性等本质属性,适用于各种债的关系。一物数卖、债权人代位权的构成、情事变更原则的构成、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如何认定,等等,均应如此把握。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些方面的若干债法司法解释却将个案的处理方案、少量判决的经验体会升格至普适性规则的层面,普遍适用,破坏了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在另外的案件处理时会造成不当的后果,需要检讨。 注释: ①Ludwing Raiser,Dingliche Anwartschaften S.49.转引自申卫星:《期待权基本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2页。 ②转引自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台北:三民书局,1980年,第7页。 ③⑩(11)崔建远:《合同法》(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41~442、121、121页。 ④存在“反对说”:代位权人受领的债务人对于第三人债权,与债务人对代位权人的债权,在性质上不许抵销。见中国台湾“民法”第334条但书;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0页。 ⑤张广兴:《债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207~208页;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5页;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396~397页;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3页;崔吉子:《债法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⑥RGZ90,102(1041),(1917).转引自彭凤至:《情事变更原则之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第102页。 ⑦RGZ94,267(1919).转引自注⑥彭凤至书,第117页。 ⑧OLG Frankfurt,JW 1919,940.转引自注⑥彭凤至书,第119页。 ⑨BGHLM § 284 Nr.2.转引自注⑥彭凤至书,第139页。 (12)《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还涉及法律位阶的层面,即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才无效,违反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规章的合同不因此而无效。关于此点,请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第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105页。 (13)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一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黄松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民事案件解析》(第5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55页。标签:法律论文;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论文; 合同变更论文; 合同管理论文; 买受人论文; 债权人债务人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契约法论文; 民事判决书论文; 民法论文; 代位权论文; 不可抗力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