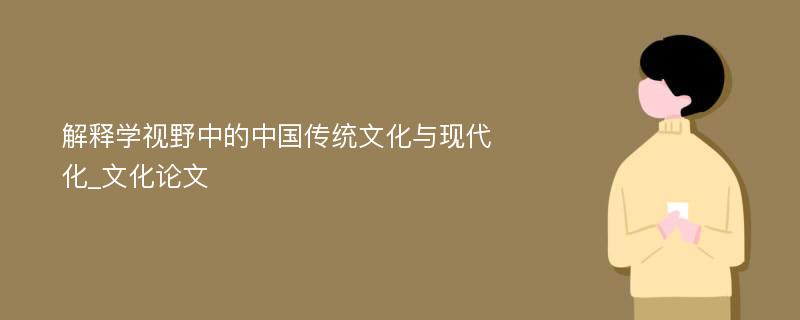
从解释学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释学论文,文化与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存在着“法先王”和“法后王”之争。前者被称作向后看的历史观,后者被称作向前看的历史观。我们对这种二元对立提出质疑。向后看必然否定向前看吗?向前看一定不需要向后看吗?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向后看不是为了向前看的。也没有任何向前看不需要向后看的。问题不在于向后看还是向前看,而在于如何看。换句话说,“法先王”和“法后王”争论的实质,在于如何正确看待传统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本世纪60年代以后,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新解释学开始在西方出现,并且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认为,新解释学之所以新,就在于它从人的存在的本体论入手,正确地阐释了传统与现实的关系。
人是怎样存在的?在伽达默尔看来,人以“教化”的方式存在。在“教化”中,人才脱离了天然的动物性,向着普遍性的人性提升。“教化”是一种外化和内化的运动,用黑格尔的话说,精神首先把自身外化为对象,又通过对象化的中介返回自身。在《精神现象学》里,黑格尔以劳动为例,说明人的精神是如何外化为劳动产品,又通过劳动产品认识自身的。伽达默尔赞同黑格尔对“教化”的看法,他还进一步指出:“每一个单独个体在脱离其天然的在,向着精神性的在的提升过程中,都会发现某种既定的材料性的东西,象学习语言那样,他要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真理与方法》,纽约英文本第15页)
既然人以“教化”的方式存在,我们便有理由把个人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化而文之”的过程。如果我们广义地把人类社会的劳动产品——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称为“文明”,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人们对这些劳动产品的吸收和同化称为“文化”。伽达默尔在《文化和词》一文中谈到,英文culture一词出自拉丁文,在古罗马, 这个词原指农业,西塞罗扩大了它的含意,即赋予它以精神上的意义,从此,culture便指物质或精神上的播种与收获的中间过程。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也有两种含义,作为名词,它和文明相近,意指人的劳动产品或结果,如“半坡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作为形容词,它意指一种把人的劳动产品(尤其是精神产品)内化于自身的程度或成份,如说“这是一个文化人”。和伽达默尔一样,我们强调人的存在方式的内在的动态的方面,在我们看来,这是“文化”的主要含意。
因此,只要人存在着,他就不断地“化”着。不过,现代人的“化”首先表现在他对自己时代文明的同化上。他通过学习现时代的语言、宗教、艺术、科学、哲学而使自己化为这些东西的一部分。例如通过学习语言,他的语言就汇入了本民族的语言中,他同化了他的民族语言,这也意味着,他被他的民族语言所同化了。由于人同化了他现时代的文明,他便成了现代文明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获得了某种现代的“世界观”。
那么,一个具有现代文化的人,或者说,一个具有现代世界观的人,是否仍然需要传统文化或传统世界观呢?传统文化或传统世界观究竟对现代文化有什么意义和影响呢?对此,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当代西方解释学是这样回答的:
首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伽达默尔认为,传统文化不能理解为过去存在、现在不再存在的东西。传统文化不是语法上的过去时,过去的东西并不就是传统,只有过去存在现在依然影响着我们的东西才能称为传统。传统不仅包括过去的意思,还包含有“承传”的意思。传统就是承传下来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传统文化相当于语法上的现在完成时。传统从来没有过去,它始终向着传统的承传者开放,不仅向我们,而且向未来开放。
伽达默尔认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一致性表现在对传统的解释中。每一次解释都是一次承传。伽达默尔反对把传统理解为既定的“客体”,理解为一种固定的意义结构。在他看来,传统文化,包括任何文学的、历史的、宗教的、艺术的“文本”,都是一种开放的意义结构。这种意义结构不但离不开解释者,而且恰恰是通过解释者的理解和解释,得到保存和发展的。他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真理与方法》,纽约英文本,第267页)
当然,解释必然包含解释者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文本”在解释者的理解中变得“失真”了。因为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不但是在历史进程中并为历史进程所规定的理解,而且由于理解是历史的和连续性的理解,因此任何个人理解的片面性都会在同时代的和以后时代的人的理解中得到补充和纠正,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本”所包含的潜在意义才得以越来越充分地被阐释出来。关于这一点,被伽达默尔所称道的卡西尔举了富有说服力的例子。他在《人论》中谈到,有各种各样的苏格拉底,有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有斯多葛派的、怀疑论派的、神秘主义派的、浪漫主义派的苏格拉底,还有唯理论派的苏格拉底,他们全都不一样。色诺芬和柏拉图看到了一个伟大的辩证法家和伦理学家;蒙台涅看到了一个反独断论者;施莱格尔和其他浪漫派思想家则看到了一个伟大的讽刺家。然而,他们又全都揭示了苏格拉底精神一个独特的方面。正是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中,我们才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意蕴。(参见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88页)
其次,传统文化对我们有扩大视野、更新知识的作用,伽达默尔批判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即把某一时代或个人的理解夸大为绝对的和唯一正确的理解。他问道,历史人物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就没有局限性吗?我们不也和前人一样,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生活吗?所以,问题不在于某一时代或个人的理解有没有局限性,而在于这种局限性是怎样突破的。在伽达默尔看来,突破我们的局限性,其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传统文化的作用。
伽达默尔象海德格尔一样,认为任何理解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理解的“前结构”,理解的目的则是突破理解的“前结构”,走向“事情本身”。不过伽达默尔指出,要突破理解的“前结构”,只能借助于“否定的经验”。因为任何“肯定的经验”都无非重复我们先前已经证实了的东西,只有先前未曾经验到的并违反我们先前经验的东西,才能扩大我们的视野,增进我们的知识。在这里,传统文化便显示了它的重要意义。在传统文化中,我们不仅遇到了某种与我们不同的语言,而且遇到了某种与我们不同的世界观。传统文化正是用它的语言、它的世界观来同我们“对话”。倾听传统,并不等于放弃我们自己的观点而接受传统的观点,这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做到。而是意味着,把我们原来的视域融入到另一个视域中,修正我们原来的视域,从而形成一个更广大的新的视域。例如,我们习惯于用理智的观点看问题,对我们来说,世界是一个理智化的世界。传统却告诉我们,在这个理智化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非理智化的世界,那里的一切都带有想象和情感的色彩。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会把理智化的世界看成唯一的绝对化的世界了。
第三,传统文化在承传过程中必然包含批判的因素,因此对传统文化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应当仅仅理解为一个主观的观念的过程,而应当理解为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或传统本身自我扬弃的过程,伽达默尔指出、正如“文本”不是“客体”一样,解释者也不是“主体”。在最终意义上,“文本”和解释者都必须以“事情本身”的逻辑为转移。因为在“文本”和解释者的“对话”中,双方都发生了改变,“文本”扬弃了它形式上的客体性而解释者则扬弃了形式上的主体性。正如在柏拉图对话集中苏格拉底和他的对手都要围绕问题本身旋转那样,解释者对传统“文本”的解释归根到底要服从“事情本身”的逻辑。在伽达默尔看来,“事情本身”的逻辑其实就是时代精神。他指出,传统文化得以承传下来,主要不是来自权威,而是来自理性。任何传统都要经受时代的检验,检验则是一种(广义上)理性的行为。理性在检验传统时就处在与传统的关系中了,它必然接纳一部分传统而扬弃另一部分传统。这样一来,得到接纳的传统便由于适合时代的需要而成为合理的传统了。不过,必须看到,合理不合理只具有相对的性质,即过去认为是合理的现在不一定是合理的,现在认为是合理的将来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前言中举了关于对爱斯基摩部族历史的看法以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此外,伽达默尔还指出,在合理性问题上,并非只有一种尺度。他说:“即使哥白尼对地球的解释成了我们知识的一部分,太阳也不会因此不在我们面前升起降落。”(《真理与方法》,英文本,第407 页)这个感性的太阳对我们来说仍然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我们可以说,除了科学的和感性的太阳以外,还有一个艺术的太阳,它向我们呈现美。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的、科学的、伦理的、艺术的标准都可以成为尺度,我们不能用一种尺度代替或排斥其它尺度。例如,在伦理学上,麦克白的野心、查理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忌都是不合理的,可是在莎士比亚戏剧里,这些都成了合理而必要的情节,没有它们,不但莎士比亚的戏剧成了不合理的,连剧本反映的生活也成了不合理的了。从解释学角度去理解传统文化,我们会看到传统文化对我们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传统文化并非一半是糟粕,一半是精华,而是有待我们提炼的合成物,有待于我们加工、制作的原材料,它是现代文化赖以生长的养料。
正如希腊传统神话和宗教成了西方文化的源泉和土壤一样,中国传统神话和宗教也成了中国文化的源泉和土壤。一切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也是这样。中国现代文学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汲取了非常丰富的艺术题材和艺术形式。中国现代哲学从《易经》、《论语》、《天论》、《庄子》、《原道》、《正蒙》、《二程全书》、《朱子语类》中汲取了多少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宝贵思想啊。中国现代的政治家、管理家、军事家们,不正在孜孜以求地从《老子》、《孙子兵法》、《韩非子》、《隆中对》中寻找治国安邦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么?中国现代医学不正在从传统医学那里得到启迪和借鉴么?……当我们这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竟是这样地须臾不可分,以致离开传统文化,我们的现代化立刻就会因为极度贫乏而显得苍白无力。孔子有句名言:“温故而知新”。我们正是在重温传统中,才获得了众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的。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法先王”和“法后王”的问题。孔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又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国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这些话曾被当作典型的“法先王”态度加以批判,似乎他生来就是一个主张复古倒退的反动派。可是,在1989年召开的“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讨论会上,复旦大学的吴浩坤先生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指出,孔子所说夏殷二代“文献不足征”以及“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都是事实。因此从文献学角度看,孔子所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能是鉴于周朝有“百二十国宝书”的丰富典籍而对夏殷二代文献缺乏的慨叹。(见《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77 页)至于“行夏之时”云云,吴先生指出,这完全是“择善而从”。例如他说:“孔子主张‘行夏之时’确是属于‘择善而从’的性质;如果据此以为是孔子守旧复古的证据,未免不合情理和苛求于古人。 ”(同上书, 第389页)
我们认为吴先生的考证很有道理。从解释学观点看,它证明了并非“向后看”就等于复古倒退。退一步说,即使孔子真的认为只有用先王的典章制度规范现时代,才能改变春秋诸候争雄、“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那也是一种“向前看”的态度。我们可以理解为,孔子希望以西周为榜样,建立一种上下有序、尊卑有分的统治形式。任何社会,治国总是需要一套政治法律制度和礼仪形式的,连马克斯·韦伯也承认,现代社会离不开“官僚体制”,韦伯说:“显然,从技术上看,现代国家是完全建立在官僚体制基础上的。国家越大,它的力量越大,就越是这种情况……和外部磨擦的范围越大,对内实行统一管理的需要越迫切,这种情况越不可避免,这就要在形式上导致官僚结构。”(马克斯·韦伯《经济和社会》第二卷,英文版,第971页)
在这种意义上,孔子的“吾从周”有点象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国》是根据埃及的种姓制度构思出来的,因此可以说,柏拉图也是“向后看”的,不过柏拉图“向后看”却正是为了“向前看”。他对雅典奴隶主民主制曾寄予希望,后来目睹了这种民主制的各种弊病,他怀疑了,动摇了,希望建立一种更为坚实可靠的社会制度。他不是重复古埃及的种姓制度,只是想以此为蓝本,建立一种更好的制度。当然,他的“理想国”有些脱离现实,用黑格尔的话说,“还不够理想”。不过黑格尔又指出,“柏拉图并不是一个玩弄抽象理论和抽象原则的人,他的真实精神曾经认识了并表述了真实的事物。这不能是别的,而只能是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真实事物,也只能是那唯一很好地生活在他本人和希腊里面的〔时代〕精神的真实事物。”(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商务印书馆,第248 页)孔子不也是为了“向前看”才“向后看”的吗?从解释学观点看,“向前看”和“向后看”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没有一种“向后看”不是为了“向前看”的,简单地把“法先王”或“向后看”称为复古倒退,是没有根据的。
和“法先王”相对的是“法后王”。商鞅、荀子、韩非等法家被认为是“法后王”的代表。例如商鞅说过:“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君书·更法》)荀子说过:“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劝学》)韩非说过:“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击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五蠢》)仅从这些文字上看,似乎他们真要和过去一刀两断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商鞅并没有完全否定过去,他也说过这样的话:“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商君书·更法》)可见他认为传统的礼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他的“君操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大体篇·群书治要》)和孔夫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出一辙,我们从荀子身上不仅可以找出老庄的痕迹,更可以找出孔孟的痕迹。他直接继承了孔子“正名”的思想。他说:“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正名》)他认为“正名”可以“上以名贵贱,下以别同异”(《正名》),在政治上伦理上认识上都有重要价值。荀子的“法”、“术”、“势”恰恰是熔各家为一炉的产物。毫无疑问,上述三位思想家都是“向前看”的,但没有什么“向前看”可以脱离历史、脱离传统,只能在历史和传统的基础上“向前看”。借口“向前看”而拒绝传统、排斥传统或忽视传统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心主义。最简单的拒绝传统就是“焚书坑儒”,稍微复杂一点就是“革命大批判”,再复杂一点就是借口传统无非是传统而“束之高阁”,这些都是历史虚无主义,是我们建设现代化社会应该避免的。
其实,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传统都伴随着我们。我们不但在历史上找不到现代和传统的绝对界限,在自己的头脑中也找不到这样一个绝对界限,传统文化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时代文化则是传统文化在新的形态下的表现。以《礼记》中的“大同”思想为例。《礼记·礼运篇》勾画了“大同社会”的朦胧图景。这种社会理想,不知在历史上被重复了多少次,不过每一次都补充了富有时代色彩的内容。华东师大的冯契先生指出,洪秀全砸了孔子牌位,但又在《原道醒世训》中引用了《礼运篇》的“大道之行也”一段话,把大同理想重新提出来。康有为写了《大同书》,描绘了一个资产阶段启蒙主义的“乌托邦”。孙中山讲“天下为公”,先是以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为主要内容,后来又强调它与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见《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第43页)如果有人说,这不是牵强附会吗?不是把“文本”所没有的东西强加在“文本”上吗?我们的回答是,一点也没有。从解释学观点看,“文本”从来不是“客体”,而是向解释者开放的意义结构。传统文化这个大写的“文本”,正是在不断地解释和运用中才保存下来并得以发扬光大的。
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给我们做出了榜样。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思想,从这点看,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并没有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而成为纯粹的“过去”,因为它们被保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了。但这种保留又不是原封不动的保存,而是在新的形态中的升华。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歪曲或否定德国古典哲学,只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从新的视域进行了统括。从当代解释学观点看,任何现代理论或现代文化都发轫于传统,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则在于不断地解释和再解释之中。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确切地说,是对立统一。人类文化是一条河流,它从传统走来,向未来走去,而且,正如黑格尔所说,离开其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
至于谈到我们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应有的看法,我们愿意借用莱布尼茨的话说:“后退才能跳得更高。”(转引自卡西尔《人论》,第277页)
标签:文化论文; 儒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人论论文; 解释学论文; 真理与方法论文; 国学论文; 伽达默尔论文; 向前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