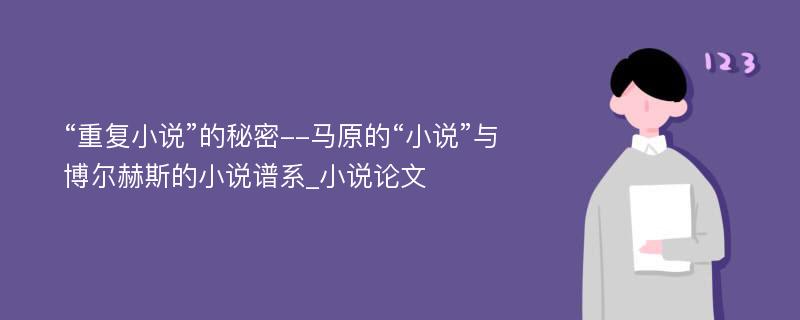
“重复虚构”的秘密——马原的《虚构》与博尔赫斯的小说谱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赫斯论文,谱系论文,博尔论文,秘密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原的《虚构》是近些年来我反复阅读的小说,我总觉得那里面隐藏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文学变革的最初奥秘。尽管人们都会认为,1985至1989年,中国当代文学转折玄机四伏,那是由众多的事件、人物和文本构成的,一篇小说能有多少奥妙?但我总觉得《虚构》是一篇蹊跷诡异之作,每一次阅读它,随着我的心境、随着我对理论问题的兴趣不同,它能释放出不同的意义①。数年前我专注的主题是:马原这篇玩弄虚构圈套的小说,实际上是为他进行诡秘体验作遮掩。这篇故作惊人之论的“虚构”小说,固然有意混淆现实和虚构界线,在那时也扰乱了小说规范,开创了先锋小说的虚构道路。这篇被强调挑战传统小说的作品,也依然在寻求一种内在的统一性,至少有一种重新整合的内在机制。那就是在“性”作为人的生存的不可逾越的关键处,小说叙述把不相干的故事结合到一起。“我”与麻风女的性爱、小个子男人与众多麻风女的生殖行为、哑巴老人与母狗的丑恶秘密,都在“性”如何构成人的生存不可逾越的难题这点上交合在一起,从而达成一种共同的解释。我当然承认这样的解释在今天也依然是我理解这篇小说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但今天再读它却有更为奇妙的问题吸引我。我会看到马原这篇如此胆大妄为的小说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例如,与博尔赫斯文本以及海明威小说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创作方面的相似、模仿或承继这些直观的解释就可打发;只有进入到互为文本的修辞游戏中去审视,才可看到那个时期文学创新的文本发生学。文学文本的内在谱系是以细节和标志性的象征符号的形式建构起来的,而这也是文学最为内里的一种关系。这样的阅读太让我激动,我现在更加关注:马原如此声称“虚构”,以虚构之名来写小说意味着什么?他在题辞中为什么要说“重复虚构”?他重复了什么样的、或者谁的“虚构”?“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像是一句誓言,又更像是一句谜语,甚至是暗号。他要和谁接头?和谁里应外合?这些问题,也许无关乎当代小说理论革新问题,也许无关乎当代文学史的“重写”问题;但至少、也可能是作为文学文本最富有文学趣味的问题。
一、开头、题辞以及“我就是那个叫做……”
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写道:“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这种叙述句式,把现实中的人物与小说的作者完全混同起来。传统的叙述人,只是伪装的叙述人,甚至只是客观历史的转述人。而这篇名为“虚构”的小说,开宗名义地表明,作者就是叙述人,叙述人就是现实中的作者。他讲述的是他的直接经验。
“我”的叙述在新时期小说中并不鲜见,但所有这些“我”的叙述,都是转述,叙述人与现实中的作者不可能发生直接关联。即便像《伤痕》、《班主任》、《绿化树》、《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同一地平线上》这类十分切近叙述人直接经验的作品,也隔着一层转述的鸿沟。也就是说,作者是隐匿不见的。现在,马原直接出现在文本中,他要宣布他在讲述一个故事,他在虚构一个故事。他只是把文学/小说表述为他虚构的故事。
“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他的讲述从他开始,这是他讲述的故事,也是他讲述的“他的故事”。他的故事构成了文学,构成了全篇作品。什么人这么狂妄自大?他不再是人民的代言人,而是一个讲他自己的故事的人。他为用汉字写作而得意,而且自诩为“好作家”。
“虚构”实则是一次宣言,开辟回到文学本身的新小说时代的宣言。
小说为什么一开始就喋喋不休地发表了关于“马原”和“写小说”的议论,现在读起来没有什么新鲜感,但在当时却显得有此必要吗?“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这样来写小说开头,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大相径庭。传统现实主义总是为了创造逼真的效果,把小说的叙述人隐去,躲在幕后,给出一个客观自在发展的生活世界。这个叙述人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人。而“马原”这个叙述人跳进小说中,那么这个叙述人就成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这个“我”就要以他的视角和经验来推动小说。小说议论了一通他自己的经历之后,说到“为了杜撰这个故事,把脑袋掖在腰里钻了七天玛曲村”。这里的叙述转入真实性效果的制造:“我叫马原,真名。我用过笔名,这篇东西不用。”
这篇准备虚构的小说实际是要带领读者进入故事。这样的虚构是在虚构一个进入故事的方式,这既是对这个文本的虚构,也是对当代小说另辟蹊径、重新开启一种叙事方式的“虚构”。新小说如何开头?这是个难题,从构造历史的巨大客体转化为讲述个人经验,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变故,这本身是一个离奇的“耸人听闻”的故事。这对马原来说,尽管在那时看来是一场恶作剧,但其中隐含的困难和不自信也一样溢于言表。马原不得不东拉西扯来掩饰他进入故事的困惑。
故事如何起源?现实主义是自我起源的,总是要从时间地点的自我起源开始,那总是创世纪的翻版。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有一辆马车驶入一个新的村庄的进入方式,那就是革命进入一个地区的开始,叙述由此打开一个本来封闭的神秘去处,现在则是日益要发生变革的村庄。但新小说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叙述的自我起源,叙述从对叙述的合法性的反思开始,新小说或先锋小说不管多么激进,都无法摆脱开头的不可能性的梦魇。这使它的叙述总是要建构一种合法性和合理性,这使叙述的革命性又变得不彻底。
《虚构》的叙事有备而来,他要开辟马原自己的小说叙事。他一直讲述一个叫做马原的汉人的故事,他为写作而跑到西藏,这都是他区别于前此的作家的地方。小说也在向着现实的马原的故事延伸。1982年,马原确实跑到西藏去工作。到了1986年,文坛关于马原的传说已经很多。他把自己作为一个文学传奇来讲述。西藏确实给他强烈的冲击,他写出了一系列关于西藏那神秘诡异岁月的故事。
“我就是……”如同宣言,宣告着马原在文坛诞生,文学写作要从这里开辟出另一片天地。在此之前,马原的《拉萨河女神》、《西海无帆船》、《冈底斯的诱惑》等一系列小说已经让文坛刮目相看,接着,《虚构》发表于1986年,马原正是跃跃欲试,随后《错误》、《大元和他的寓言》、《游神》、《大师》等接连发表。马原在1986年下半年走红,直到1987年上半年,全国关于他的研讨会大概有十多场。如此短的时间,如此多的讨论,可见马原给文坛带来的震撼。那时他的作品加起来只有二十多篇,这二十多篇小说对于“向内转”的当代文学居然足以构成强劲的推动,看来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变革别无选择。在马原这里,当代中国文学有底气说回到文学文本,回到文学形式。马原的出现使“向内转”的理论期盼有了具体而实在的文本承载。
“我就是……”的叙述语式,最重要的在于,开始叙述一个关于“我”的故事,最单纯的“我”的故事,这个“我”,甚至与历史、现实无关。这个“我”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其实,马原如此自信,与其说如此自信,不如说他如此无知。“无知者无畏”,这是王朔数年后说出的话。马原和王朔,就是两个无畏的无知者。王朔的无知,是他与文学的当代历史谱系毫无干系,他的文学只从个人经验中来。他是歪打正着,处在一个期待个人自我经验的时期。个人自我经验在剧烈变动的年代又显示出特殊的诱惑力,它日新月异,散发出蛊惑人心的光芒,王朔就这样生逢其时。而马原,也同样与文学的历史无关,他的文学来自另外的源泉,那就是西方文学与西藏异域文化。后者如他作品中不断呈现出来的世界;而前者就是海明威和博尔赫斯。这个时期,博尔赫斯几乎就是马原文学写作的引路人,这个瞎子给予他看清自己文学道路的眼睛。
如果把马原的《虚构》与博尔赫斯后期的短篇小说集《沙之书》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马原如何深受博氏的影响。
在《沙之书》1975年出版的前言里,博尔赫斯写道:
我并非是为了少数精选的读者而写作的,这对我毫无意义。我也并非是为了那个谄媚的柏拉图式的整体,它被称之为“群众”。我并不相信这两种抽象的东西,它们只被煽动家们所喜欢。我写作,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我写作,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②
这段话可以从国内1983年出版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中读到,相信酷爱博尔赫斯的马原一定曾读到它,它足以让马原鼓起勇气沉迷于自己的小说世界。博氏的“我写作……”,如此断裂的拒绝和声称,就可以在马原的“我就是……”这样的语式中找到中国回声。马原说,他为用汉语写作而得意。他得意的是,博尔赫斯的汉语回声只有马原自己知道。
博尔赫斯出版《沙之书》时已经七十六岁,他的小说越发显得纯粹而诡异。《沙之书》有一句题辞:“……你的沙之绳……”③马原的《虚构》也有题辞:“各种神祇都同样地盲目自信,它们惟我独尊的意识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它们以为惟有自己不同凡响,其实它们彼此极其相似;比如创世传说,它们各自的方法论如出一辙,这个方法就是重复虚构。”这段题辞声称引自《佛陀法乘外经》,但这本书不可考。它也是一本虚构之书,或者也是“沙之书”。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神祇、惟我独尊、创世传说、重复虚构。为什么马原要写下这么一个包含这些关键词的题辞?小说开篇就说“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这个马原写小说具有神祇的意味,它以惟我独尊的意识来建立自己的“创世纪”。吴亮曾说:“马原的方式就是他心中那个神祇的具体形象,方法崇拜和神崇拜在此是同一的。如果说马原最终确实为自己创造了一些独特的小说叙述方法,那么也可以有把握地说他同时是一个造神者。……马原的有神论即是他的方法论。”④80年代中期是狂热崇尚方法论的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崇尚方法,文学创作也在寻求现代派的方法。显然,只有马原逃离了现实化的时代精神,他才能找到更为纯粹的方法,于是,马原试图给他的叙述方法以“创世纪”的意义。
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追究,为什么要说神祇都有权力建立一个创世纪传说?既然是“创世纪”,何以又是“重复虚构”?对中国当代小说来说,马原的写作具有非法性,他不再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谱系中写作,而是另立一套,以其“耸人听闻”的虚构来替换中国占据主流地位的反映现实的叙事。反叛者的心虚与狂妄自大,几乎是互为表里。但是,马原是独创么?是真正的“创世纪”么?《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放在那里,《沙之书》放在那里,他能做什么?他只能“重复虚构”。这或许是这份题辞(也是在“虚构”名下)的全部秘密。“虚构”是什么?“虚构”就是“沙之书”,“沙之书”就是“虚构”,这是互为文本:“重复虚构”。
小说集《沙之书》中有一篇同名小说。它讲述一位深居简出的老人在家遇到一位找上门来的卖书人,这个来自苏格兰北面的奥尔卡达群岛的人,手头有本神奇的圣书,那就是“沙之书”,因为那本书像沙一样,无始无终。书的编码极其荒诞神秘,翻动书页也显出某种神秘感。后来“我”拿一部保存了多年的花体字的威克利夫版《圣经》,换下了这本书。珍藏这本书成了生性孤僻的“我”的负担,晚上多半为此失眠。某一日,“我”只好把它放入国立图书馆,让它消失在书的世界里。
《虚构》当然显示不出与《沙之书》直接相似,我也没有任何证据来证实二者有什么直接关联,这里仅仅是把这两个文本放在一起,看它们是否有可能重合之处,看《虚构》是否有可能“重复虚构”《沙之书》。
《虚构》开篇关于小说写作和“真实性”的种种议论,与《沙之书》开篇关于“真实”和“虚构”如出一辙。《沙之书》的讲述者是一位独居的老人;《虚构》的讲述者马原“现在住在一家叫做安定医院的医院里”。《虚构》在“重复虚构”时,确实比《沙之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与《沙之书》的作者不同,后者是在谨慎声称真实的情形下,一步步走向离奇和神秘;而前者一开始就声称他住在“安定医院”。当然,住在安定医院未必就是精神病患者,但是这种说辞无疑嘲弄了读者对“真实性”的期待。
这就是“重复虚构”的胆大妄为,我倾向于承认马原的“重复虚构”是面对着中国当代的文学现实进行尖锐的挑战。他不是一个神圣战士,而只是一个住在“安定医院”的写作者。周围是一些“老人”,他显然与这样的小环境既没有不协调,也不见得协调。他在安定医院,这是一部在安定医院虚构出现的“传世之作”。
小说中明确提到海明威,那个美国佬,他喜欢用枪;但博尔赫斯也喜欢用枪。《虚构》开篇后接着就亮出了枪。有些迫不及待,他要从海明威和博尔赫斯结束的地方开始。这或许就是马原“重复虚构”的意义所在。
一个断然宣称要开启新小说时代的“虚构”,它不幸、也是侥幸面对着博尔赫斯“重复虚构”。
二、老人、“我”的经验与困难的虚构
对于马原来说,这个开头是如此艰难,既自以为是,又心虚顾虑。经历了漫长的一整节的言说,才进入故事。第二节的故事却突然换了一个叙述人,那个哑巴老人的独白构成了故事的真正开始。这样的开头令人摸不着头脑,依然让人想起《沙之书》的那个老人。虽然二者的故事完全不同,但在小说中的角色功能却有相同之处。《沙之书》有个类似博尔赫斯的老人在叙述,而《虚构》开始也是那个类似马原的人在叙述。为什么要让小说“真正开始”由老人来叙述?这实在是不协调之举。既是有意制造不协调,也是重复《沙之书》的叙述。这个故事,本来可以转向老人的叙述,老人叙述他的漫长而神秘的历史——那就回到了中国既定的历史叙事中。但马原放弃了,他要那个来自奥尔卡达群岛的人来叙述。《虚构》其实是两个故事,一个是老人叙述的故事,另一个是“马原”叙述的故事。“马原”后来居上,用他的叙述压制了老人的叙述,“马原”顽强地要把老人的叙述转变成他的叙述,叙述他的故事——“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的故事——这才有当代中国小说革命的发生。老人/博尔赫斯只变成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一个隐藏的神秘而有罪的人物。这个人物在小说中如此不协调,如此神秘莫测,却又如此重要。在玛曲村,这两个人都是外来者:老人是一个潜伏者,而“马原”则是闯入者。这是一次里应外合的接头。他们都是不法者,那个哑巴老人一直没有语言,不能说出他的历史,他是罪犯或是什么样的人?而“我”/马原则是一个从安定医院跑出去的人(或者是将要去到安定医院的人),作为一个非法的写作者,“我”如那个哑巴老人一样,他潜伏于麻风病村,“我”住进安定医院。
老人是博尔赫斯晚年小说中常出现的形象。《沙之书》小说集里的那篇精短的《圆盘》,叙述人是一个穷困的樵夫,某天打开门进来一个高大的老人,老人裹着一条褴褛的毯子,脸上有一条长长的刀疤。这个老人自称是国王,说他手心握有一只圆盘,却无影无形。结果这个樵夫说要拿一箱金币与老人交换(穷困的樵夫显然是想设一个骗局)遭到拒绝,待老人转身离去,樵夫朝老人背后砍了一斧头。老人死后被扔到河里,但樵夫并未找到那个圆盘。这个故事如博氏其他故事一样简单明了,这个老人的形象,却是因其背后神奇古怪的历史而令人惊异。这样的老人不知给马原留下何种印象?
《虚构》中的老人,或许重叠了多个博尔赫斯式的老人,《沙之书》的那个蛰居老人最有可能是其母本。只是这个博尔赫斯式的老人,被中国历史改写,被中国的暴力与革命驱逐。他是哑巴,只能在山上对“马原”这个闯入者说。他(在玛曲村的漫长岁月里)不能说,他不能作为叙述人。于是,只有“马原”,这个叙述人如同那个奥尔卡达群岛的人一样——马原从他身上看到叙述及故事的另一种转机。
这样的转机都很突然,都有一样神秘的东西出现。《沙之书》里是那本圣书,《虚构》里则是哑巴老人的那把枪。“他像变戏法一样,突然从一个可怜的老人变成荷枪实弹的强盗……他动作迅捷模样凶狠,我从声音和外型可以断定他手里的是真枪。他用枪口对着我的脸……”⑤
在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倒数第二小节,如此写道:“阿尔贝站了起来。他高高的个子,伸手打开高高的写字台的抽屉;有一忽儿,他背向着我。我已经准备好左轮手枪。我十分仔细地开了枪:阿尔贝立刻倒了下来,一声都没有吭。”⑥
确实,我不能说这两个掏枪动作有多少相似之处,持枪者的年龄、身份、掏枪的动机都不同,也不是说他们的掏枪动作有几分神似。但那个俞琛博士掏枪击毙汉学家阿尔贝的动作实在是给人印象深刻,任何读过博尔赫斯小说的人,都会为这个动作所震惊。倒不是这个动作在小说中的描写有多么出色,而是它对于整个现代小说来说,是一个最为经典的时刻。1941年,博尔赫斯开出的这一枪,是对现代小说致命的一击,现代小说突然变得千疮百孔,破碎零乱。在现代小说还是鼎盛时期,博尔赫斯就埋下了后现代的伏笔,打响了向后现代进发的枪声。直到60年代初期,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在美国出版,巴思、巴塞尔姆、品钦、冯尼戈特这些人,才如梦初醒,美国的实验小说这才知道后现代的方向在哪里。
在中国,这个故事晚了四十五年,还差五年,就整整半个世纪。这个掏枪的动作只好由一个哑巴老人来做,显然,他已经是一个老人,错过了开枪的最佳时机。他不可能开枪,他也无力开枪,这个老人,这个伪装几十年的哑巴。“枪口从我眼前慢慢移开垂向地面……”,随后,老人举臂,左手食指扣动扳机,向空中开枪。
俞琛扣动“左轮手枪”,在马原这里变成了用“左手”食指扣动扳机。这些细节即使没有直接联系,也确实是耐人寻味。他用左手扣动扳机,那是二十响盒子枪,开始是剩了七发子弹(那十三发子弹的去向并无交待),老人朝空中打了一枪剩下六发子弹。他只能朝空中打枪,他不可能把“我”打死。他成不了叙述人,他是属于历史的,而他的历史已经被隐瞒了,而今天只是当作一个离奇的与麻风病村的怪异故事混淆在一起的故事。“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从那个老人的枪口下逃了出来,这仿佛是死里逃生,其实是一场虚张声势的游戏。“我”成为叙述人,“我”获得了或者说保持住了叙述人的资格。
对于马原来说,“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这不只是空洞的声称,而是一句誓言。博尔赫斯的老人式的叙述,他要改变为一个年轻的“我”冒险进入西藏的叙述。“我”的年轻化,洋溢着生命欲望的自信和自以为是的誓言,“我”要讲述的是“我”的故事。博尔赫斯固然老到,然而,“我”却是一个年轻的冒险家,用汉语写小说的冒险家。“我”依靠的是经验的奇异性,那个老人完全从博尔赫斯的谱系中剥离出来,转移到中国的历史中去,转移到那个神秘的暴力的历史中去。而且要让他沉默无语,要让他被其他的更为怪异的故事所掩盖。
小说直到第四节又重新开始,进入故事发生的地点,在第四节,“我”(马原)潜入玛曲村。也就是说,小说的故事现在找到发生和发展的线索,才变成“我”的叙述,并可以顺着这条主线发展。“我”好容易才驾驭住这个叙述。
叙述由此转向了个人经验,而这一独特的个人经验被引向西藏异域风情,再加上麻风病村,马原显然还嫌此不过瘾,还要有更多奇异的不可思议的故事发生。博尔赫斯所有的小说故事,都是离奇古怪的异域传说,或者是来自不可考的史料,现在马原用他的“亲身经历”来对抗博尔赫斯的那些怪诞传说。这显然是对布鲁姆关于“陌生化”理论的挑战:马原铆足了劲就是要超出一般的陌生化效果。不仅仅靠形式上的新奇之举,那些关于叙述本身,关于虚构和写作本身的奇谈怪论无法提供充足的陌生化效果,小说还是要在个人极端怪异体验的意义上给出超出陌生化的极端经验⑦。
这篇小说于是出现了双重怪异化的经验:其一是关于叙述本身的经验,那是虚构文本的陌生化。其二,在“虚构”名下讲述的奇异的个人经验故事,故事和经验本身要获取/超过陌生性。很显然,这双重陌生化在马原的小说叙事中并不协调,形式的陌生化是一些关于“虚构”的议论,是一些外在的无法进入小说的困扰,是一些喃喃自语。这些无法开始的叙述没有进入这篇小说,始终外在于故事,始终在故事之外徘徊,那几乎是在与博尔赫斯和海明威格斗。但小说表现出来的却是在中国小说形式的暴力革命,它要通过对故事的颠覆来建立马原小说的“创世纪”。但是,依然是博尔赫斯的阴影,“怎么讲”从来也不可能完全超出“讲什么”,马原的幸运在于他确实有讲故事的才能,这又使他不得不回到汉语小说的故事传统中,所以,他说他“用汉语写作”,那是他想逃脱博尔赫斯的一句冠冕堂皇的托辞。这就不难理解,到了小说的第十九节,“在讲完这个悲惨故事之前”,马原再次跳出来,他面临着要给小说结尾,就像小说的开头异常困难一样,这个要虚构小说的人,现在已经给出一个活灵活现的可还原为现实性的小说。
虚构是什么呢?虚构就是叙述,正如所有的叙述都是虚构一样。马原现在不得不再次指认他的结尾是杜撰的。那个结尾果然使他的小说变得相当完整。就在“我”与麻风女道别时,枪声响起来了,哑巴打死了那条母狗,哑巴也自杀了。“我”打着手电筒到了哑巴的屋里,再次看到了座垫底下的国民党党徽。谜底也被揭开了,这个杜撰的结尾在整个故事的解释中显得如此重要,它使这个故事合乎传统小说的全部规范。最后还是要回到传统小说中的因果律、可理解性和完整性。马原只是不断地依靠叙述来打碎文本,把叙述人的个人经验介入进去。他努力想破坏传统小说的自足性,要把一个客观地生成的小说世界,变成一个叙述人的经验世界。这里的冲突,是个人与客观世界的冲突,是生存的事实性与现实的事件性的冲突,是经验的例外与世界的连续性的冲突。
奇异的真实,一直是博尔赫斯追求的效果,马原在这点上无疑是博氏的中国传人。越是奇异,越具有真实性。这不可思议的真实性是如何造就的?博尔赫斯依靠那些老人,他作为老人在叙述,或者是他笔下的一些老人在叙述;但他更经常依靠古旧的历史资料,一些声称在图书馆里或者某处意外发现的手稿,那些手稿通常残缺不全,介于真实的史料与不可考据之间。现在,马原以他的历险、以他声称住在精神病院的经历来使他的故事也介于极端真实和难以置信之间。
奇异的真实本身是分裂的,总是在双重性的结构中变换不定。这种紧张关系并不能在文本内获得和解,叙述制造的虚构效果,与故事追求的极端真实总是相互矛盾。正因为此,马原一直在玩弄虚构/真实的圈套,不管如何打乱文本的叙述,不管如何颠覆再重来,小说依然顽强地给出一种真实。马原自己也总是被制造真实性的效果所诱惑。与其说他真的是在有意颠覆真实,不如说他始终摇摆不定,形式诱惑着他,真实也吸引着他。叙述人也总是会陷入那种幻觉。小说到了结尾又一次声称:“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⑧这个段落就在混淆虚构/真实的界线。“住在安定医院”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嘲弄性的,这是一个疯子的语言,到底是真是假?那个个子高大长着胡须的家伙,与马原的外貌很相符,现实性与虚构又混淆在一起。
博尔赫斯的奇异的真实,总是向着形而上延伸,他没有那么充分复杂的故事情节,但马原总是迷恋曲折多变的故事,最终总是落入故事中,想用叙述圈套来逃离故事,逃离又难免要回望。根本在于,马原对个人的独异体验有一种天生的自恋。年轻人的自恋与老人的厌世构成了一种鲜明的悖反。这或许是马原与博尔赫斯后期带有某种“晚期风格”(late style)小说的主要区别。
总之,被称之为“叙述圈套”的“方法论的神祇”(吴亮),其实只是马原无法调和传统小说规范与新叙事探索之间的矛盾的应急之举,现在看起来它是如此生硬,这些形式无法融入故事本身,它看上去就像渴望突破的马原陷入的窘境。在虚构的博尔赫斯式的叙述方法与对真实的个人经验的迷恋之间,马原无法找到平衡,因为他一直在崇尚着海明威,那个最擅长讲“真实故事”的美国佬。马原想调和博尔赫斯与海明威,实在是异想天开;也许正是这样的异想天开,成就了马原。因为,他就自己去干,他逃离了博尔赫斯,他进入玛曲村,他不只讲那个老人的故事,他还要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新小说的革命,就是在这样的窘境中走“自己的”路。
三、“我干了”:疾病与爱欲
“我不是个满足于‘想一想不是也很好吗’的海明威式的可以自己宽解愁肠的男人。我想了就一定得干,我干了。”在一篇声称“虚构”的小说中,马原如此强调“我干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进入到玛曲村,他亲历了异域奇异的生活,如同世界之外的生活,那是生命的极限:疾病与爱欲。“虚构”了什么?不是“虚构”本身能解决问题,虚构另一种存在,另一种非现实,另一种不存在。博尔赫斯的故事以其异域传奇的神秘性而产生形而上的意味;博尔赫斯不需要复杂曲折的故事。但马原不同,他还到不了形而上的层面,他的故事就要以异域的神奇怪异、极端的生存体验来制造独特的效果。这可以使他在虚构的反现实性与故事的反常规化这两方面富有革命性。
他要亲历疾病与爱欲,这使他抵达生命的极限,创造神奇至极的效果。
这部小说里有很多怪异的关键词:“虚构”、“精神病院”、“麻风病”、“枪”、“性”、“生育”、“病”、“割礼”、“神像”、“神秘”、“游戏”、“不可知性”等等。可见它对怪异经验发掘到了相当极端的地步。这个故事的主导经验就是“麻风病”,这就够离奇的了。麻风病今天已然绝迹了,但只是在媒体和公共空间绝迹,实际上,中国当代还有一些麻风病隔离村庄⑨。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马原提起麻风病隔离村,仿佛谈的是完全不存在的世界。
在这里“麻风病”是一种象征,是一个被隔绝的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它也几乎是不存在的存在。现在,马原要以他个人的亲历经验来替补虚构。一方面,他要“虚构”;另一方面,他又要强调他的亲历经验。他用“虚构”来颠倒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观念;再用“我干了”的亲历经验来颠倒“虚构”。他的亲历经验就充满了冒险,对于他的故事,对于他的写作来说都是一次冒险。
这无疑是一次死亡的冒险,只有面对死亡,才是真正的冒险。而明知死亡却还要冒险,这样的冒险又有英雄气概。
那个“马原”进入玛曲村后遇到麻风女病人。对此,马原写得很细致委婉,包括她的外形、心理、动作以及“我”对她的感受。通过这些来表现他的情感如何一步一步走进麻风病人。令人恐怖的麻风病,被赋予一种素质,一种意味,甚至一种美感。这是恐怖之美,这是惊惧之美。马原是要拿出奇异的绝对陌生的东西来展开他独特的故事。我们确实不得不去思考,文学给我们的审美感受是什么。一个男人和麻风女做爱,是这个故事的重点部分,是高潮部分,也是要害。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经验、这样的场景?叙述如此不知不觉地进入到那种氛围:“这个玛曲村之夜是温馨的。”小说接着叙述道:
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的激情。我知道这种激情的后果也许将使我的余生留下阴影,但我绝不会为此懊悔。我当时并不清醒,我的理智早被她的热情烧成了灰烬。不过如果有机会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还是不要那该死的理智。我做了一次疯狂的贡献。后来我们睡了,在梦里我们仍然紧抱在一起,羊毛被使我们浑身汗津津的。我们睡得真沉。我真心希望就这样一直睡到来世。⑩
在这里,小说对非常规情境的描写,总是提到“疯狂”、“梦”、“来世”等,那么这些构成了什么呢?小说只有穿过这些词语的时候,它才变成创造异域的陌生化经验。这些奇异性效果是如何产生的?现代文学艺术作品并不创造美,也不一定追求美好。它最重要的意向是表达非常规经验,也是陌生化经验,它并不追求美感,或者也不考虑正常与否,甚至是否合乎“道德规范”。确实,文学最根本的东西,也就是那些构成作品最重要的因素、品质、素质,经常是一些非常反常的经验。如果这篇小说去掉这些段落,做得温和些或更合乎常理些,会是什么结果?其实,前面也有温馨美好的描写:“竟有微弱的月光从窗子照进来,我想一定是弯弯的月牙。借着月光,我看到她裹了一件翻皮毛的藏袍,她的脸侧向外面,只听见酣睡的鼻息。她的一条光腿从袍襟伸出来,圆滚滚地泛着浅浅的光泽。……我把羊毛被轻轻盖到她身上,特别为她盖上裸露的小腿。”(11)这里充满了浪漫情调。但麻风病的存在时刻威胁着人们的正常思维和感受,尽管写得很美,到了这里,小说还是要发疯,那些平静的数数、温柔的描写都是为了疯狂的到来。如果小说没有这些极端体验,这些温馨的存在会失去根基,美好的感受依附于怪异反常的经验。这种怪异的经验隐藏在文学艺术作品的某个部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小说叙事不断向着这个极端冲击,也向着这个极端推进。
我们不得不承认与麻风病人做爱是一个疯狂之举,正是它把作品定住了。这是很美的事情吗?这是疯狂的激情,这是一种病症,“我”正是在病中做下这件事。它本身是病,又像做梦一样,而且它暗示了来世,因为跟麻风病人做爱注定要死去。
虚构要依赖的是死亡冲动。只有死亡冲动,这样的虚构是向死的虚构。也就是说,虚构在向死的虚构中死去;而死亡在虚构死去之后存留下来,构成文中的那些最为引人注目的经验。这就是虚构的方法论活动,最终让位给死亡经验的文本博弈。马原一开始就摆好姿态,他要“重复虚构”博尔赫斯的小说经验,他所能抵达的摆脱博尔赫斯的去处,就是自我的经验,当然也是自我最极端的经验,那就是历经疾病、爱欲直到死亡的经验。
马原其实并没有与博尔赫斯博弈,并没有追寻博尔赫斯的踪迹去到方法论的神祇世界,那也是当代小说的死亡之地。他宁可追寻海明威,那个说自己的故事的能手。马原边说边干,他亲历的故事。如此看来,当代中国小说的革命,在马原这里,走得并不算太远,也不可能走远。它还是回到故事,只是在虚构的名义下,可以虚构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而已。马原的“虚构”说穿了,就是“耸人听闻”的故事。
当然,“爱欲”的经验在这里达到极端,与麻风女交媾,不管是以多么神秘的、异域的、疾病的形式展开,都是极端的交媾。80年代中期,正是中国当代小说初尝性文化禁果的时期,从张贤亮的《绿化树》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尤其是那个时期有关性文化的书籍开始在街头巷尾不胫而走,性文化其实成了填补意识形态现实想象的及时内容。马原的异域风情的“性”,在“虚构”的方法论活动名下获得了一些合法性。人们都认为马原追求小说的“叙述圈套”,追求小说的方法论活动。实则“方法论”是马原的障目法,马原最为热衷于书写的,是那种极端的生命体验,极端怪异的具有异域情调的生存事相,而所有极端如果通过性经验体现出来,就达到马原理解的生存世界的极致体验。“虚构”最终虚构了与麻风女交媾的这个时刻,这是当代小说经验在个人化写作达到最高限度,在马原那里,一出手就抵达了这个极限。“虚构”因此变成托辞,“重复虚构”因此而能超越博尔赫斯——在博氏的另一侧面落荒而走。
四、神祇、枪与时间
吴亮说马原的神祇就是他的“方法论”。实际上,方法论从来都不可能构成小说的神祇,也不会构成小说家的神祇。即使像博尔赫斯这样的方法论大师,也要依靠奇异的故事,或故事的奇异性。博氏方法论通过故事的奇异性转向了形而上意味;马原则通过方法论活动转向了自我经验。马原当然知道他的故事无法完成形而上的转化。他常写中篇,他写不了短篇,他过分热衷于故事的传奇性,免不了总是要进入故事的复杂、转折和意外。所谓迷宫般的故事,也只是一种说辞;再复杂的故事,都是可以拆解的,都不难找到头绪。文字叙述的世界无法完全逃离理性逻辑,马原的小说因其漫长的特性,以中篇为主要的体裁——这也是80年代中期,中国小说走向所谓的成熟的标志,实际上,也因此,中国的小说艺术变得半生不熟。好大喜功的中国小说,有对规模篇幅的热爱,中篇小说大行其道,就要依靠故事、而不是技巧来推动小说叙事。马原应运而生,这也是他要把博尔赫斯与海明威嫁接在一起的缘由。马原其实并不想过分停留于小说的方法论活动,否则他就不会热衷于中篇小说。后来又转向长篇小说——那显然是他所不能习惯的小说体制。
马原试图把方法论塑造成神祇,但却三心二意;他倒是用这个神祇来迷惑读者,让读者对它顶礼膜拜,他就可以对小说为所欲为。马原影响最大的两部中篇小说《冈底斯的诱惑》和《虚构》,其实各自都是由三个短篇故事构成。《冈底斯的诱惑》这里不加细谈。《虚构》是由“我”和麻风女的故事、“我”和小个子的故事以及“我”和老人的故事构成。这三个故事只要略加修改就可以分别写成三篇精炼的短篇小说。虽然麻风女、小个子、老人之间可能发生关系,但在小说中都是以单独与“我”的关系为结构展开故事,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例如,“我”与麻风女的故事在第十一节麻风女与“我”完成交媾就可结束。自第十二节开始,麻风女就不占据主要地位。“我”与小个子、与老人单独构成了故事线索。
实际上,“我”与麻风女的故事,那是“我”马原的故事,是“我”马原要逃脱博尔赫斯而顽强地创造个人的奇异经验。而与小个子和老人的故事,则还是在与博尔赫斯对弈,还是试图“重复虚构”博尔赫斯。
方法论无法真正构成神祇,那么神祇就要在小说中重新显灵。小个子的故事就与神祇沾上了关系,这故事乃是一个补充;正如麻风女的故事是老人的故事的替换一样,小个子的故事试图给疾病、爱欲、怪诞以神秘的合法性。
如果读一下博尔赫斯的《布罗迪报告》(12),可能会有另外的收获。这里并不是要把它与马原的这篇小说做对比,因为从1983年至1986年,在马原追随博尔赫斯的年月里,相信他没有其他途径读到这篇小说。它讲述一个极为奇特的雅虎部落的故事,那里的国王由四个巫师选择和控制,国王由身上有特殊胎记的孩童选拔而来,一旦选为国王,就被刺瞎双眼,砍去手脚。国王住在山洞里,只有四个巫师和两个王后可以接近他。打仗时,巫师把他从洞里弄出,由士兵抬出到战斗前线,激励士气。敌方扔出石头,国王立即驾崩。这个部落的惟一快乐游戏就是惩罚罪犯,众人向罪犯扔石头。
在《虚构》中小个子是珞巴人,珞巴族是藏南较为原始的部落,那里还时兴刀耕火种,崇尚性或生殖神。小个子奇怪地懂得现代文明的娱乐方式打篮球,他更重要的职业是雕刻神像。“我”(马原)表现出对他的神像极高的兴趣和尊崇,但那个神像似乎只有头和身体,没有提到手脚,而额头上刻着一座山。小个子雕刻神像处有两棵神树,妇女们在那里转神树。这样的神圣崇拜的场景可以与《布罗迪报告》做一个对比,这是一项敬神的活动,但其神圣性语焉不详。小个子不断地与当地的麻风女交媾,生了很多孩子。而这些孩子出生就意味着灾难。生殖在这里是一项罪恶,从现代文明的角度会被指控。但他们有什么办法?麻风女说:“不干这种事他们干什么?”(13)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生活惟一的快乐和安慰,生存剩下最后一点属人的行为。在性中,生存才可能超越死亡,因为在麻风村它就是死亡的一种形式,就是死亡的变形。性总让新的生命产生出来,因而它又可以蔑视死亡和超越死亡。小个子仿佛是惟一自然的人,他把性看成自然,同时又如神谕。到底是自然,还是神谕?
小个子是“我”与麻风女交媾的补充,是这个浪漫交媾的神祇的依托。一方面,马原要建立起小个子背后的神祇,另一方面,却要以现代文明来予以抨击。但最终现代文明让位于神祇。这次让位,给那个病态的疯狂的奉献式的交媾找到合法性,神祇的合法性。就像“我”的疾病不再需要担忧一样,这里的交媾和生殖拥有神祇作为护佑,并且具有仪式和自然的双重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怪异的性、神祇与枪,可以构成一种关系。为什么要构成一种关系?
本来枪的故事贯穿着始终。枪的功能一直具有历史的实在暴力,它却要具有打断虚构的能力。只有它可以阻断时间的虚构,只有它是实在之物,只有它要回到历史中。
小说中出现了一个简短的关键词式的句子:“国民党军帽。淫狗。痴呆相。”(14)
马原无法深化他的历史暴力的秘密,而是把它转化为反常的性经验。这是成功的转化吗?很值得怀疑。哑巴老人再也没有任何肯定性的出现,所有关于他的叙事只是否定性的秘密和怪诞。哑巴的那杆枪也无法在历史暴力方面延续下去(展开故事),最后只能用于打死那条母狗,这样以性的怪诞与变态来替换,却让历史草草关闭了。
这么一把始终炫耀的枪,却并没有派上大的用场。神祇与性联系在一起,枪也与性联系在一起,不过却是用以打死那条隐晦的也是丑恶的母狗。枪并没有更深地介入故事,也没有介入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
哑巴老人本来属于另一个故事,马原无法处理这个故事,要让它进入虚构的整体性,只有依靠怪诞的性。这部小说以性为支点,企图以此来建立一个中心,一个深不可测的人性的绝境——性如何成为人的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个绝境与神祇重叠,那就是小个子男人雕刻神像。反常的经验与隐秘的故事,这就是马原追求的怪异性。奇异性并不具有更为内在的震撼力,于是神性赋予性的怪异性以某种深度与可能的内在统一性。《虚构》不同于《冈底斯的诱惑》,它是马原的小说中惟一试图寻求一种深度的统一性的小说。看上去拼贴了几个故事,也试图打乱虚构与现实的界线,但却要在性的怪异上与神性沟通,获得共通(而不是共同)的深刻性,把怪异性转化为深刻性。深刻性导致统一,这就是神性的深度,这就是小说寻求思想深度的后果。
那把枪不管是来自博尔赫斯还是海明威,都没有发挥更富有暴力的作用。
博尔赫斯的小说《秘密的奇迹》用枪来阻断时间,或者说用时间来延缓枪的暴力。关于艺术的想象,居然可以阻止暴力,在想象中的阻止与实际上的失败,完成了对枪的暴力的控诉。枪与时间、艺术想象,构成了奇妙的三角关系。枪在小说中的功能被发挥到极致。这篇小说讲述1939年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剧作家拉迪克的故事,他被德国人逮捕,判处死刑,距行刑时间还有十天,这十天,他天天沉浸在对死亡方式的想象中。他曾经与人论辩说:“只要一次重复就足以显现,时间就是欺骗。”(15)在临刑前,他终于转移思绪,去构思一部剧作《敌人们》。他祈盼时间停滞,在盖世太保枪决他之前的两分钟,他完成了《敌人们》的构思,那是他一直未能写完的最后两幕。小说最后一句话是:哈罗米尔·拉迪克死在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点零二分。
马原的《虚构》在时间的处理上,很明显受到博尔赫斯这篇小说的影响。至少结尾都用时间做标记:“我机械地重复了一句:五月四日。”
《虚构》试图用时间的错乱重叠来强调虚构。马原在小说的开头就说“为了杜撰这个故事,把脑袋掖在腰里钻了七天玛曲村”。小说结尾处计算他在麻风村的时间,说他是五月一日进藏,路上走了两天应该是五月三日,经过数天在玛曲村逗留,离开时应该是五月七日或八日,结果他听到收音机里报的时间是五月四日。此前,他有两次睡觉做梦的经历,一次是在玛曲村与麻风女交媾完之后做梦;另一次是小说临近结束,他一路走着,在极困的情形下推开藏族养路工住处的房门,昏昏沉沉睡去,早上醒来,阳光灿烂,才知道是五月四日。《虚构》与《秘密的奇迹》最后一句话,都是时间标记,而且是被重复的时间或被折叠的时间。
马原关于“枪”的叙述很可能是受到海明威的影响(海明威是用火枪自杀的)。马原曾谈到他对小说的理解,他很欣赏海明威的“枪”。海明威有一篇小说叫《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16),软弱无能的麦康伯和夫人到非洲狩猎,在围猎狮子时,他临阵脱逃。麦康伯夫人与陪猎人威尔斯偷情,被丈夫发现。在围猎时麦康伯遇到野牛,结果麦康伯夫人失手打死了丈夫。马原曾经表示,他佩服海明威是因为他把谜底始终藏得严丝合缝,你永远无法断定麦康伯夫人是不是有意杀死她的丈夫(17)。这一枪使谜底封存在小说的深处,使整个解释变得困难。海明威的“枪”与《虚构》的“枪”是否有直接关系我无法断定,根据马原写过的谈创作的文章,我推测可能有关系。
但是马原这一枪却并未使整个故事“重新虚构”,而只是关闭了哑巴老人的暴力历史,把哑巴的故事从整个故事中排除出去。哑巴一直是个局外人,他的故事是另外一个故事,或者充其量只是一个补充的故事,本来要作为叙述人的哑巴老人,最后却只是另一个故事中的人物。他只是潜伏在玛曲村里的一个隐瞒历史的过客。他每日爬山,倒是使人想起红色经典小说《红岩》里每日跑步的装疯的华子良,这实在是一个隐晦的反讽,一种怪异的颠倒。我、麻风女和小个子,三个人的故事在性与神祇的结合中达成统一;这个故事完整了,而哑巴的故事则出局了,也草草收场。
枪没有进入小说的核心,没有进入人物的核心结构,也没有打破人物的整体性。枪与神祇没有内在关系,因而,小说的时间又变成外在了。枪没有击碎时间,也没有使时间的虚构发生变化。虚构说到底是在时间中的虚构,马原深谙此道,但枪如此重要的道具,在小说一开场就亮出来的东西,却只是一个玩具,并没有在时间中“重复虚构”。这是虚构的神祇没有建立起来的关键,也是“重复虚构”没有真正进入“重复”的缘由。
五、在不可能的虚构中完成的小说变革
把马原的《虚构》放在博尔赫斯以及海明威的作品之间来阅读,并不是说马原在模仿它们,也许在马原最初的写作中,相当认真地阅读了这些作品,使它们之间构成某种文本的相似性。有些是直接的,比如,马原确实有意识地借鉴了这些作品;有些则是无意识的,它们只是在追寻个人独异经验的极限处相遇。当然,我更感兴趣的在于,中国当代小说最具有挑战性的创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这些影响在文本中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些影响变形又意味着什么?在这些变形中有可能发生创新。创作,恰恰是那些最具有挑战性的创作,往往是在和诸多大师的文本对话中产生的,没有文本间的对话,文本的艺术生产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所有的虚构在这个意义上,都不是凭空的虚构,只能是也必然是“重复虚构”。这就是虚构的不可能性,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在马原这样的绝然另辟蹊径的挑战者这里,虚构也成为一个不可能的神话。但却是在这样不可能的虚构中,马原完成了当代中国小说最有挑战性的叙事革命。在此之后,汉语似乎没有什么不能写,怎么写也都有可能。
马原的“虚构”至少有以下几点意义:
其一,《虚构》的“虚构”篇名命名,那是作为一项宣言,作为一项誓言。
其二,马原的“重复虚构”,是对博尔赫斯的重复虚构。但是,他把老人的叙述——博尔赫斯的带有“晚期风格”的叙述——改变为年轻的“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的挑战性的虚构。
其三,这也是对海明威的重复虚构,那是“我”的个人极端经验。不再是方法论的活动,方法论的神祇无法建构,神话也无法建构。
其四,历史的实在性的放逐。老人的故事再也不能用现实主义手法重述,哑巴的历史已经缄默,哑巴开口说话却是虚构自己的故事,谁也无从知晓他的历史真相。中国的历史暴力无法处置,马原放逐(回避)了历史经典叙事后,宁可“虚构”怪诞的性的故事。这代作家无法直面历史,只有让老人变成哑巴,甚至无法在他沉默的地方虚构他的故事,而是把他的故事丑化,那是与母狗交媾的丑陋故事。把历史动物化,剥夺了其属人的历史。形式主义实验从关闭的历史之门开始。
其五,时间的虚构。只有在时间里才能故弄玄虚。这是惟一的虚构。但五月四日是一个革命的节日。又一次嘲弄了历史,却又盗用了历史。历史只剩下一个虚构的时间。
虚构的历史停留于五月四日,又一次的文学革命自五月四日开始。这是终结还是开始?抑或如五月四日,这样的时间可以重复虚构吗?其实我们每年都经历一次,每年都重复虚构这个日子。伟大的日子可以被虚构,那么“虚构”何以不可能虚构呢?我的阅读一如“重复虚构”一样,可是“我的沙之绳”呢?
注释:
①数年前,我曾经以《虚构的圈套与诡秘的体验》为题,读解马原的《虚构》,发表在丁帆主编的《扬子江评论》创刊号上,承蒙丁帆教授错爱,不胜感谢。该文是我2004年在北大中文系讲课的录音整理而成,读起来还有明显的口语成分。今年春天,我再度开设“当代小说文本分析”课程,想把讲稿修改一下,原来只是打算做语言修饰。不想,一边修改,一边却在重新“虚构”这篇解读文章,连主题都发生变异,完全重写了这篇文章。
②③⑥(15)《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第379页,第82页,第111页。
④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原载《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引文参见孔范今、雷达等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资料》中,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页。
⑤⑧⑩(11)(13)(14)参见陈晓明主编《中篇经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第80页,第67页,第66页,第73页,第75页。
⑦陌生化理论最早来自什克洛夫斯基,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一书中把它视为文学创新的“美学特质”。
⑨例如,据2007年12月15日央视网络电视台报道:四川越西县大营盘村,现有80户人家,麻风病人105人,800个健康后代。参见http://news.cctv.com/society/20080224/102178_1.shtml。
(12)参见《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王永年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386页。
(16)参见王佐良编选《美国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17)参见马原《小说是纯精神,现在人生活里不需要精神》,载《南方周末》2001年8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