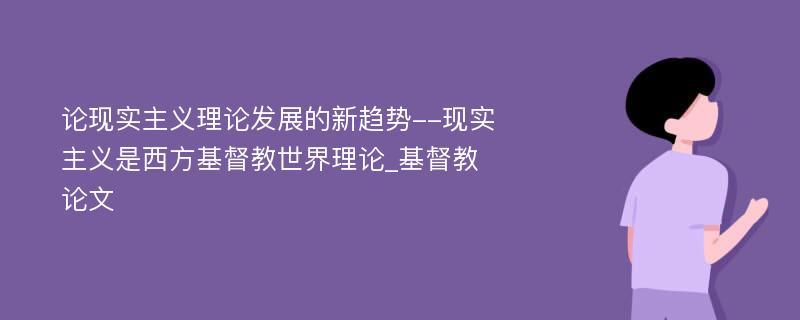
有关现实主义理论发展新趋势的争鸣笔谈——现实主义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笔谈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新趋势论文,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理论,因为国际关系的概念、体系、逻辑都源于西方,反映西方思维,这一点本毋庸置疑。可是具体分析起来,人们往往忘记了这一点,甚至产生国际关系理论“源于西方而属于世界”的错误认识,潜意识认为西方“发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理论的解释、运用则超越西方,具有普世性。这反映出中国人对理论的渴望——传统中国文化不善于产生西方那样的理论,对中国特色理论的向往,更重要的是对西方、对现代性的迷信。 对国际关系理论最原始、最经典的现实主义理论分析表明,西方并非发现而是发明了现实主义理论,并在西方遭遇非西方世界冲击时产生出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流派,然而本质上我们仍然生活在西方世界或西方化世界,故种种关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都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分歧。 一些人以乌克兰危机进一步证实现实世界仍然是现实主义世界,其实应补充一句,仍然是西方基督教内部世界,因为俄罗斯的东正教也是基督教的一支(另两支是天主教、基督新教),俄欧(美)矛盾仍然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矛盾。美国试图通过乌克兰政变消除俄罗斯从文明道统上挑战基督教文明的合法性及俄复兴可能性。俄罗斯自称“第三罗马帝国”的,笃信东正教,不受教皇管制,有自己的独立而分散的教派体系。俄罗斯的历史和宗教发端于“基辅罗斯”。没有作为俄罗斯文明发源地的乌克兰,俄罗斯在文明道统上便无法挑战西方。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不断挤压俄罗斯复兴空间。乌克兰是“俄罗斯帝国的钥匙”,也是华盛顿“策反”乌克兰的主要动机。美国外交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乌克兰对俄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失去了乌克兰,俄罗斯将不再是个帝国;有了听从使唤且服从(俄国)意志的乌克兰,俄罗斯自动成为帝国。”①美通过乌内部政权更迭,试图赶走俄罗斯黑海舰队,使之在克里米亚无法立足,砍断俄罗斯藉此影响中东事务的地缘—军事途径,导致俄罗斯策动克里米亚公投入俄及东乌克兰脱乌运动,演变为乌克兰危机。 中国学界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探讨并未跳出西方的逻辑,认清其本质。现实主义理论不是被证实或证伪的,它只能被超越。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便是这种超越的集中诘问。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 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在最原始、最经典而流行最广的现实主义理论身上得到最鲜明的体现,集中在以下方面: 1.思维起点:神性—人性—国家性 现代西方国际关系起源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的诞生,也就是先有“国”再有“际”。三十年战争(1618~1648)诞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民族国家、主权、外交、国际法等基本概念,使得国际关系概念产生于欧洲,并传播至亚洲、非洲、美洲等地。 葡萄牙是西方第一个民族国家,最早实现王权—教权分离——把凯撒的给凯撒,把上帝的给上帝,此后便迈入对外扩张的征程。可以说,国际关系是西方基督教内部关系,在“均势—打破均势—均势”间维持动态平衡,但其背景则是基督教的向外扩张。因此,尽管欧洲之外的地区也存在势力均衡现象,但并非近代欧洲的均势;产生于欧洲的均势论,也就不适用于其他地区。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推动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三十年战争又将国家性予以释放,诞生现代国际关系理念。这就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起点:人性本恶,故权力本恶;国内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国际是民族国家林立,势力均衡。人性的张扬导致国家性张扬,西方基督教内部是血腥厮杀,对外则是野蛮扩张、掠夺、殖民。这就产生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逻辑:以权力追求安全,以实力争取利益。 2.思维方式:国内—国际二分法 为了表明人性张扬导致的国家性张扬合法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杜撰出一个先验论——无政府状态(anarchy),以便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区别开来——其本质是国际关系缺乏像国内那样的中央政府权威,并非真正的无政府(chaos)或无序(disorder)。望文生义的翻译常常导致对西方理论的误解。其实国际关系中仍然有法则的,古典现实主义推崇实力均衡法则就是对自然界平衡法则的延伸;基督教的普世价值为民族国家的基本共识。因此,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描述的国际社会并非无法无天,现实主义各流派对国际法、国际道德、国际规范也是承认、尊重的,只是从根本上不相信它们能维护安全、保护利益而已——权力才是根本的。假定“无政府状态”是为了引进“自助体系”(self-help)概念。民族国家的结盟(alliance)、跟着强者走(bandwagon)、均势(balance of power)等逻辑就是在“天助自助之人”的信念下展开的。这种假说在柏拉图的“原初状态”、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假说中一再得以体现,是非常基督教式的思维方式。 现实主义的挑战者——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只是在修正“无政府状态”假定和“国内-国际”二分法,然而本质上并未动摇其逻辑,而是国际关系不完全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关系的折射及西方无法主导世界的反映,但毕竟国际社会迄今未走出西方世界或西方化世界的影子。因此,现实主义仍然是最有说服力的,在中国也是信徒云集。 3.思维过程:原罪论导致宿命论 现实主义理论反对线性进化论思维,认为世界历史走不出某种循环,颇具宿命论色彩,更证实了基督教的原罪假定。 如前所述,人性本恶的原罪假定,导致国家权力本性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假定。人与人如狼、国与国如狮的霍布斯状态,使得战争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尽管按照米尔斯海默的分类,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所谓人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其共同属性为宿命论,只是应对宿命论的方法不一。米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便公开宣称,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4.思维结果:你是现实主义的,我是自由主义的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发明的,理论来源于西方,却是为别人发明的。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对此做了很好的阐述。他写道,“(美国人)认定美国是世界政治中的慈善力量,而把美国现实或潜在的敌人看成误入歧途或胸怀恶意的麻烦制造者”。② 欧洲的情形更进一步,笃信线性进化论,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眼光看世界,就觉得其他国家尚生活在自己的历史中,还在玩现实主义那套,而自己则要去规范他们。因此,在欧美学界产生“中国只懂现实主义逻辑”那种鄙视性认识。一些中国学者也因此盼望中国尽快以康德、洛克而非霍布斯思维看待世界,似乎在力争上游。 自美国崛起为西方首强,国际关系的西方性就呈现出鲜明的美国性。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以理论性替代理论,正如以普世性装扮普世价值一样,试图主导国际话语权。这一点,在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米氏以美国基督教强烈的天定命运观——开始是开发西部,后来是让其他国家人民皈依美国基督教——直接奠定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基础——最大权力才能获得最大安全,而最大权力不可企及——米氏说的是海洋的阻遏作用使全球霸权不可能——其实是国家非上帝,不可能获得最大权力——因而不可能获得最大安全,故此产生大国政治的悲剧。 二、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性 梁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指出,“洋为中用”之前,先得搞清楚“洋为洋用”是怎么一回事。③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的结合,也是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基因。因此,要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必须首先明白国际关系何以为理论。 笔者曾提出“国际关系的理论性”命题,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到了追本溯源、反思其主体性的时候了。从回答“国有际吗”、“国际有关系吗”、“国际关系有理论吗”这三个基本问题入手,文章反思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自身维度问题(即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探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先天不足与终极趋向。④ 的确,国际关系的提法是值得推敲的,何谓国,何谓际?西方基督教语境下的international relations其实是interstate relations。换言之,国际关系并未涉及国民关系层面——近年来公共外交大行其道就是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吧。Nation-state在日文里翻译为“国民国家”,的确更贴切。此外,“际”是否为“inter”,而不是“intra-national”、“trans-national”或“super-national” relations呢? 中国并非民族国家,作为世俗文明的中国也不会产生西方那样的国际关系理论,这就不足为怪了。⑤所谓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只是模糊认识,本质上,在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不以nation-state为基本单元探讨国际关系理论,这就有待后西方世界的真正来临。 三、现实主义何以回归现实世界 人的认识往往滞后于时代变迁;国际法则也往往滞后于权力结构的变化。我们仍然生活在西方世界或西方化世界,故此现实主义大行其道不足为奇。所谓西方世界或西方化世界,是指其他地方仍然依照西方法则、在西方影响下行事。比如东亚,传统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垂直“天下”体系,近代以来西方传入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横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造成东亚纷争不止。要让亚洲成为亚洲,这是亚洲远离西方现实主义的前提基础,而非美国人所担心的“门罗主义”。 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引领后西方世界来临的希望集中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身上,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将第十章改写为“中国能和平崛起吗”,就准确抓住了时代矛盾。也就是说,将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最终检验。作者就中国崛起后亚洲出现战事的必然性做出了有力论述:“简而言之,我的看法是如果中国在经济上继续增长下去,它会希望像美国统治西半球那样统治亚洲。而美国会百般阻挠中国实现这种区域霸权。北京的多数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和越南,都会和美国联手来遏制中国的势力。这样一来就会有一场激烈的安全竞赛,战争的可能性相当大。”这是21世纪的核心战略问题。“在历史中,我们很少看到权力从一个霸主转向另一个霸主的过程是和平的”。⑥ 其实,不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问题,而是西方(主要是美国)能否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问题,或西方基督教世界能否接受世俗文明崛起的问题。美国的天定命运观与例外论在这个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美国政府领导人口口声声说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但当中国真正和平崛起为像美国那样的国家时,美国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的。正如奥巴马总统2010年4月15日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所言,“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所以中国领导人会理解,他们不得不做出决定去采取一个新的、更可持续的模式,使得他们在追求他们想要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应对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挑战”。⑦这也是中国梦提出,提醒中国人做有别于美国梦的时代背景。 现实主义源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循环,止于多元世界的来临。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命运是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西方基督教世界不再成为主导,现实主义也就如决斗一样过时,像青铜器、纺织机一样要放在历史的博物馆了。 说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在证实或证伪现实主义理论,那是太抬举现实主义理论了。中国崛起,推动世界回归正常的多样性状态,超越了西方理论,毋宁现实主义理论。因此,无论是美国华裔学者许田波、王元纲还是一些中国学者,以中国的历史来验证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往往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或提出中国的古代现实主义理论,要么削足适履,要么沦为与西方一般见识,忽视中国并非国家,而是有别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独立文明体系。 注释: ①[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美]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③[加]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序。 ④王义桅:“国际关系的理论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4期。 ⑤详见王义桅、韩雪晴:“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 ⑥[美]罗杰·科恩:“中国把‘门罗主义’用到亚洲”,《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年5月10日。 ⑦Interview with Barack Obama,15 Apr.,2010. http://www.news.com.au/national/president-barack-obama-says-prime-minister-kevin-rudd-is-smart-humble/story-e6frfkvr-1225854306896.